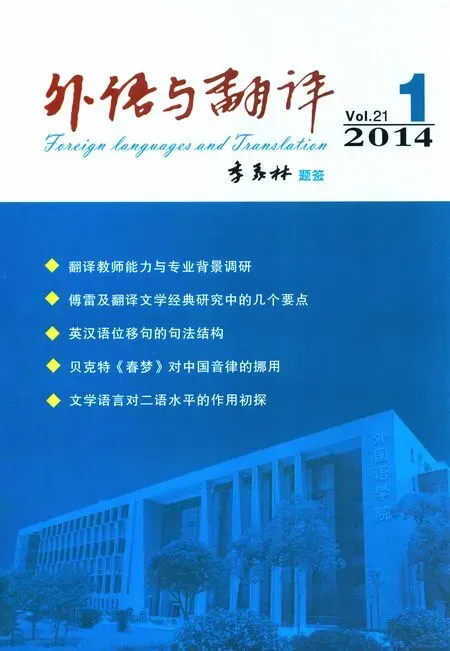关联理论视阈下的口译记忆∗
齐涛云
中国翻译协会
关联理论视阈下的口译记忆∗
齐涛云
中国翻译协会
本文从关联的角度研究口译学习和实践中与口译记忆相关的各种策略。关联理论将交际视为明示推理的过程,口译作为一种特殊的交际形式包含两个这样的过程。文章首先论证了口译首轮交际过程中最佳关联的特殊性,指出口译员面临的交际困境,然后在此基础上从瞬时记忆、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三个维度解释口译学习和实践中相关策略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关联,口译,记忆策略
1.引言
关联理论由Sperber&Wilson(1986/ 1995)提出,是认知语用学理论基础,其目的是识别存在于人类心理的内在机制,从而解释人类交际的方式。口译作为交际的下义范畴,是一种特殊的语际间交际形式,其动态交际过程可以较好地用关联理论进行解释。通过在“中国知网”进行文献检索发现,国内学界对于关联理论在口译中的应用研究涉及了口译认知过程、口译理解、推理思维、意义选择、口译笔记和口译策略等,尚不存在以口译记忆为对象的关联研究。
人类记忆是大脑对经历过的事物的反映,从结构上可分为三种,即瞬时记忆、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记忆在口译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对发言内容清晰、牢固的记忆,译员就不可能产生准确通畅的译文(雷中华,2007:53)。本文旨在利用关联理论对于口译学习和实践中与记忆相关的各种策略进行解释,以期拓展关联口译理论研究的维度。
2.基于关联理论的口译交际过程分析
关联理论是一个有关语言交际的理论。他否认了基于索绪尔符号学的信码交际模式。认为任何一套确定不变的解码原则,都不能弥合语义表达和言语意图之间的分离现象。这种分离现象是靠认知过程来弥合的。交际得以实现,正是交际者提供了有关自己意图的行为依据(如话语)以及接受者能根据这种明示(ostension)行为推导出交际意图。这是一种推理交际模式。这一推理思维三个关键因素是:明示话语和语境为前提,付出努力进行加工处理为过程、实现最佳关联获得认知效果为结果。所谓最佳关联,就是以最小的处理努力得到足够的认知效果。如果话语既能产生足够的语境效果,又只需为此付出最小的处理努力,那它就最有最佳关联性。任何一个推理交际行为必须保证其最佳关联性。(D.Sperber&D.Wilson,1986/1995)
口译是一种通过口头表达形式,将所听到的信息准确而快速地由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进而达到传递与交流之目的的交际行为,是人类在跨文化、跨民族交往活动中所依赖的一种基本的语言交际工具(梅德明,2000:6)。一般交际是一轮明示推理过程,而口译则包括两轮这样的过程。第一轮过程中,口译员与源语讲话人形成交际双方。源语讲话人将信息明示给口译员,口译员感知信息后进行信息加工推理,从认知的所有假设中选出符合原交际意向的假设,结合自己原有的图式进行瞬间的合成,实现最佳关联。第二轮过程中,口译员和目的语听众构成交际双方,口译员把经过推理得到的源语讲话人的意图信息传递给受体。可见口译员、源语讲话人和目的语听众之间形成了三元关系。(如图所示)(杨跃、齐涛云,2006: 91)

3.口译首轮交际过程最佳关联的特殊性
口译员真正的动机是为了实现源语讲话人(下文简称A方)与目的语听众(下文简称B方)之间的沟通,译员只起到一种转换和传递的作用。按照关联理论,如果A方和B方之间进行直接交流,那么B方根据自己的语境假设来寻找与A发出的明示信息相关联的内容。在口译活动中,由于语言的隔阂,这种寻找关联性的工作实际上是通过译员来真正实施的。
口译员需要在两轮交际中的两个角色中转换,他跟普通的单语听众相比承担了更多的责任。我们假设存在另一单语听众B’,B’与B的行业技术背景完全一致,即二者百科知识认知语境完全一致。A与B’的交际实现语境效果(contextual effect)为CE1,A与口译员的交际实现语境效果为CE2,A与B(通过口译员)最终实现语境效果为CE3。理想状态下,应该有CE1= CE3。单语听众B’通过对于原交际者A的明示行为进行推理,寻找最佳关联,获得源语讲话人的意图信息。一旦交际双方实现彼此互明(mutualmanifestness),即标志着二者之间交际过程的结束。而口译员在完成上述过程后,随即进入第二轮交际,并在其中担任讲话人的角色,将其在首轮交际中获得的源语讲话人的意图明示给目的语听众。因此口译员在首轮交际中存在“表述动机”(刘和平,2005:19)。“表述动机”要求口译员在首轮交际中不仅要通过推理获得原交际者的意图信息,还要记忆住这些意图甚至原交际者表现意图使用的明示形式。换句话说,口译员在首轮交际中既要理解源语讲话人的主要观点,又要记住这些观点和支撑这些观点的主要证据。单语听众则无需记忆,作为直接听众,他们甚至有时可以只关注源语讲话人明示信息的部分内容,因为并非全部明示都与所有听众具有足够的关联性。基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口译员在首轮交际过程中所获得语境效果要大于单语听众,即CE2>CE1=CE3。
除了两轮交际角色及任务转变带来的挑战,实际工作中口译员还面临着不少其他的困难。首先,如果译员听入的是非本族语信息,对信息可能会少听入或未听入,甚至误听,尤其是当发言信息地方口音严重,不满俚语或古语时更是如此。其次,译员可能并不熟悉发言涉及的行业知识,对于原交际者的理解可能会不到位。口译交际具有即时性特点,译员不可能查询工具书或有关参考资料,也不可能频频打断说话者,要求其重复所讲的内容(梅德明,2000:8)。因为上述困难的存在,口译员的认知语境(cognitive environment,包括语言和百科知识等)往往小于单语听众(C2<C1)。
综上可见,在口译首轮交际中,口译员的认知语境小于单语听众(即C2<C1),而其所要实现的语境效果却要大于单语听众(即CE2>CE1)。这种“交际困境”便构成了此轮交际中最佳关联寻求过程的特殊性。我们不妨借用Sperber&Wilson的交谊舞比喻来阐释这一特殊的“交际困境”。Sperber&Wilson认为,原交际者就是领舞,单语交际者是跟舞者,跟舞者只要具备跟舞的能力,交际就可以成功(1995:43)。而口译员作为跟舞者,其跟舞能力很可能比不上单语听众,但却不得不在跟好舞的同时,迅速掌握领舞的能力,为随后的领舞角色做准备。这一特殊“交际困境”对于口译学习和实践中诸多策略都有很好的解释力。本文主要基于关联视角从瞬时记忆、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三个维度解释口译记忆相关策略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4.口译记忆相关策略的关联解释
4.1 瞬时记忆
瞬时记忆,又称感觉记忆,是记忆系统的初始阶段,负责在极短的时间内对外界信息进行感知并接收。人的感官前沿随时都会收到大量外部刺激(即感性信息),瞬时记忆是大脑根据外界刺激的物理性质进行生物电意义上的编码,是这些感性信息的真实拷贝和贮存,但保持的时间仅为0.25-2.0秒。在这一短暂的贮存期,有的信息会受到注意(神经网络的生物电刺激强化)而保持下来,进入短时记忆;而绝大部分信息则自动迅速消失。(鲍刚,2005:150)
处于某一情境之中的行为者,如果感官机能正常便可通过本能获取大量瞬时信息,但该行为者必须能够很快地从中筛选并注意到有用信息,赋予其意义并存入短时记忆,才能实现其行为目的。行为者必须熟悉有用信息的编码方式,才能辨识出此类信息;然后以其行为目的为指向进行感知聚焦(即注意),才能筛选出与行为目的真正相关的信息,即有用信息。
在单语交际中,听众对于讲话人使用的语言没有理解,他们只需以自己的兴趣为指向对讲话人的明示信息进行认知聚焦,筛选出对他们有用的相关信息,然后通过推理获得交际意图,即可实现最佳关联,完成交际。而在口译首轮交际中,口译员存在“表述动机”,讲话人的所有明示信息对他来说都是有用和相关的。另一方面,讲话人使用的语言如果并非口译员的母语,口译员对该语言编码方式的熟悉程度比不上母语使用者。比如,讲话人明示信息中的古语、俚语、因语速过快出现的连读吞音、口音以及某些艰深的行业术语等等,这些编码形式都可能对口译员带来辨识上的困难。就是说口译员语言知识认知语境不如单语交际者,但是处理的明示信息量却大于单语交际者。瞬时记忆是整个口译交际的基础,是口译员的信息之源。如果口译员无法辨识出足够多的讲话人明示信息,就无法对于信息进行处理、推理进而获得足够的语境效果,也就意味着口译此轮交际不能成功地完成。
传统口译教学理论十分重视学员语言基本功的训练,尤其是源语的外语听辨能力,认为就口译而言,听辨能力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听辨”是口译过程中的第一阶段,如果一个人的听辨水平不足,无论他的语言表达能力有多强,都很难胜任口译工作。为了实现外语听辨能力的突破,有的口译培训体系甚至要求学员进行1400磁带小时(tape hour)的音频材料精听训练,并要求保证练习材料在题材、语音和文体上的多元化,以促进学员熟练掌握该语言的各种编码形式(包括口音等变体编码形式)(范守义,2004)。外交部的优秀译员在进行口译实践之前,如果条件允许,在准备阶段常常会去听讲话人以前的录音资料,并积极收集、整理、学习与会议主题相关的词汇表,目的是为了熟悉该讲话人的讲话的口音以及可能会用到的专有名词等特殊语言编码形式(戴庆利,2004)。这些口译学习和实践策略都是为了提升口译员认知语境中的语言知识,使其与单语交际者更加接近,以便更加准确完整地辨识瞬时记忆中的有用信息,为随后实现口译员和讲话人之间的最佳关联奠定坚实的基础。
4.1 短时记忆
短时记忆保持的是某些经过筛选的瞬时信息,贮存在人脑的海马区内。实验证明,短时记忆保持时间为1分钟左右,容量为7+2个组块(chunk)(鲍刚,2005: 151)。短时记忆是记忆系统的中转站和信息处理中心,部分信息会被迅速遗忘,部分信息则通过复述不断加强记忆痕迹,进入保持时间更长的长时记忆,成为长期保存的知识。
组块是指有独立意义的信息单元,可以是数字、字母、单词或音节等单个信息,也可以是这些信息的同类或相互组合,比如大型数字、句子、段落甚至篇章等。单就组块的数量来看,短时记忆的容量十分有限,但组块内容的可扩展性决定了短时记忆容量的可扩展性。将小单位联合成大单位,对于信息进行加工、组织或再编码以克服短时记忆局限的手段叫做组块化(chunking)。(陈晓春,2008:125)
在单语交际中,听众基于讲话人的明示信息推理得出其交际意图,即意味着交际的成功,无须刻意记忆这些意图,因为记忆活动需要付出较多的努力,不符合最佳关联原则。在会议型交际中常常有人专门做会议纪要,交际完成后留在听众大脑中的信息往往都是被动记忆的结果。即便是在某些以传授知识为目的讲座型交际中,听众也只是有选择地进行主动记忆。而在口译首轮交际中,口译员由于存在“表述动机”,在完整推理得出讲话人交际意图的同时还要付出努力准确地记忆这些意图以及讲话人表现这些意图使用的某些明示形式。口译员的大脑“中枢能量”要同时用于推理和记忆两项“智力活动”。口译员认知语境的不足及其“表述动机”的存在决定了他的推理活动所消耗的“中枢能量”要大于单语交际者。一旦推理和记忆两项信息加工处理活动需要的能量之和超出了大脑恒定“中枢能量”,就会出现“能量危机”,导致总语境效果不足,引发口译首轮交际的失败(王甦、汪安圣,1992)。因此采取相关策略减少记忆活动耗用的中枢能量具有很高的必要性,而组块化便可以达到这一目的。
口译员在记忆实践中经常采用的一种具体策略是跳过音节或词汇,而将意思作为主要记忆对象,因为他们认为记意思比记词汇更简单(刘和平,2001:58)。如果以音节或词汇等孤立的语言形式代码作为记忆对象的话,短时记忆最多只能容纳7+2个单词。若干个孤立的语言形式代码组合在一起才能表达一个意思,可见意思是对于这些语言基础代码进行组块化的有效方式。
口译员还会对听到的意思进行积极的逻辑分析,找出这些意思之间逻辑层次关系,并以树状的形式将这些意思组合成语篇意义进行记忆。(张筠艇,2006:268)。比如下文:
Popular leisure time activities in Japan are different from age and family structure.Young people like going shopping in CD shop,driving in the city,playing tennis or baseball,going to amovie and eating out at fast food restaurants.Families with young children like to go to amusement park and have picnic there.Recently there are some parks where children can commune with nature.Aged group like me likes gardening,chatting with friends,going tothe artmuseum and walking around the riverside.
记忆这段信息时,口译员通过对诸多意思进行逻辑分析发现,该信息共包含四层意思。第一层意义和后三层意思是总分关系。而后三层意思之间是以年龄为主线分别对不同群体展开介绍的。通过这种方法,口译员实现更高层次的组块化,扩充组块容量,使其可以包括几层意思,从而提升短时记忆的效果。
口译员还经常使用视觉化(visualization)的策略来提高记忆效果。视觉化又称形象化,是指听众将所听到的意义或内容(而非语言形式)迅速在大脑中生成生动的形象或图画、场景,以视觉的方式跟踪事态的发展(刘和平,2001)。如下文:
Getting food to Ethiopia is a lot easier than actually delivering it to the people in need.The main port at Assab and the main airfield at Addis Ababa are badly jammed:the roads leading to the interior are clogged and there’s also a shortage of petrol.Sometimes it’s a question of having too much with too little coordination.
口译员在听这段信息时,可以边听边将听到的内容形象化,脑海中生成出埃塞俄比亚石油短缺,机场公路十分拥挤等画面。这些画面所传达的意思也会很清楚:埃塞俄比亚不是得不到食品,而是缺乏协调,无法将食品送到需要的地方。通过这种方法,口译员同样也把较多的意思实现更高层次的组块化,将视觉形象所承载的意思都归结到一个组块之中,进一步扩大组块的容量,从而提升短时记忆的效果。
将意思而不是词汇或音节作为记忆单位、对意思进行逻辑分层处理以及对意思进行视觉化处理,是口译员在口译实践中为有效提升短时记忆效果最经常采用的三种策略,他们从根本上都可归结为组块化的不同形式。在口译首轮交际中,组块化策略的合理使用节省了记忆活动占用的“中枢能量”,更多的能量可以用来进行明示信息的推理,有助于避免“能量危机”,进而保证获得足够的语境效果,实现最佳关联。
4.3 长时记忆
长时记忆信息存贮位置不再局限于海马区,而是在空间大得多的大脑皮层。长时记忆是大脑长期保持信息的主要手段,它的保持期限可从1分钟直至终身,而且信息容量非常大,大到几乎可以说是没有限度。脑皮层的编码往往按照信息的意义予以归类,其信息加工水平一般较高,编码方式也有视觉、听觉等各种形式。
长时记忆是一个人认知经验的知识库,包括个人的特定经历、语言知识、百科知识等,构成了交际者认知语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口译交际中,口译员和单语听众处于共同的上下文语言语境(linguistic context)和即时物质语境(situation of utterance)之中,二者认知语境的主要差异来自于他们的长时记忆。根据前文论述得知,在与交际密切相关的长时记忆的两个维度——语言知识和百科知识——上,口译员与单语听众相比往往处于劣势,与此同时口译员的“表述动机”又要求其获得比单语听众更多的语境效果。口译员面临的这一“交际困境”要求他采取相应的策略加以应对,尽量缩小与单语听众的认知语境(长时记忆)差距。这首先要求口译员加强交际源语言的学习,持续提升其各项语言能力,不断向单语交际者的语言知识语境靠近。另外在加强百科知识积累的同时,针对每一项具体的口译任务,还需要进行认真的译前准备工作。比如说深入学习会议文件(包括幻灯片、演讲稿、相关文本等),开展会议相关主题的扩展阅读(浏览相关网页、收集并学习同主题学术论文等),或者与演讲人沟通交流会议内容等译前准备工作,都可以在较快时间里帮助口译员建立起口译交际要求的百科知识语境,这些策略与传统口译教学理论的要求和职业口译员的实际工作流程是完全一致的。此外口译员还习惯积累很多预构置语块(prefabricated chunk),比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五位一体”或者我国政府关于对台政策的陈述性段落等。这些预构置语块在丰富口译员认知语境的同时,还可有助于他们尽快的进行组块化。如果在首轮口译交际中接收到这样的明示信息,直接组块即可,不需要现场进行额外加工处理,也可以节省中枢能量,避免“能量危机”,进一步保证口译员实现更多的语境效果,实现最佳关联。
短时记忆信息经过一定的加工处理(复述)可在大脑皮层形成记忆痕迹,从而转变成长时记忆。痕迹的持久性是加工深度的直接函数(刘和平,2001:129)。即加工深度越大,信息保持越牢固。加工水平较高的模式识别、意义汲取等留下的痕迹,相对来说要比加工水平较浅的一些物理感觉、语音识辨留下的痕迹更容易保持得长久一些(鲍刚,2005:163)。在口译交际中,口译员通过对语音和词汇等明示信息进行听辨并推理得出意思(交际意图)后将意思作为记忆对象的做法可以加深记忆痕迹,延长记忆时间。上文提到的将意思进行进一步逻辑分层处理和视觉化处理的“组块化”方式是比意义汲取(交际意图推理)水平更高的信息加工方式,自然形成的加工痕迹也更深,记忆时间更长。超前逻辑预测是另一种对短时记忆信息进行深加工的方式。口译员对讲话人后续明示信息的预测会随着语言链的不断发布和接收得到印证、否定或修正,这种预测和真实明示信息之间的相互作用也会加深记忆痕迹,延长记忆时间(刘和平,2001: 10)。可见,意义提取、组块化和超前逻辑预测等策略都会将部分短时记忆信息转变成长时记忆信息,为更多的短时记忆活动释放出了大脑海马区的空间。这些策略不仅可以提升记忆语境效果,避免“能量危机”,保证当前口译交际的成功,还可以丰富口译员的百科知识认知语境,为后续口译交际获得更多的语境效果提供坚实的基础。组块化策略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因此得到了双重解释。
长时记忆也被称为潜在记忆或被动记忆,需要激活(activate)后才能提取。在实际口译操作中,长时记忆和短时记忆相互配合发挥协同作用,有时还需要口译笔记的支持,具体过程简要概括如下:口译员利用长时记忆和上下文等认知语境对于短时记忆中讲话人明示信息进行推理得出交际意图,通过组块化等方式将这些意图加工处理转移到长时记忆,每个组块承载的内容仅需要将几个关键词或逻辑提示符留在短时记忆的组块中即可,在口译第二轮交际中口译员进行明示行为时,他只需基于短时记忆中的关键词或提示符来激活长时记忆内容,完成其表述任务。如果这些关键词或逻辑提示符超出了短时记忆的容量,或者交际现场需要这些信息存储较长的时间,超出了短时记忆的能力,可借助口译笔记记下这些关键词或逻辑提示符,然后口译员在笔记的提示下激活长时记忆,完成第二轮交际。因此口译笔记作为大脑记忆辅助工具的必要性,甚至口译笔记若干原则(如“要记关键词和逻辑关系”等)的合理性也得到了解释。针对口译笔记的相关问题,笔者已经另文进行了详细的论述,鉴于篇幅有限,本文不做过多赘述。
5 结语
口译交际可视为两轮明示推理的过程,口译员在两轮交际中分别充当听众和讲话人的角色。在口译首轮交际中,口译员的认知语境小于单语听众,而其所要实现的语境效果却要大于单语听众。这种“交际困境”构成了此轮交际中最佳关联寻求过程的特殊性。口译实践和学习中的诸多与记忆相关的策略都有助于口译员更好的应对这一交际困境。例如加强源语(尤其是外语)学习,增强明示信息辨识能力,提升瞬时记忆;对明示信息进行逻辑分层和视觉化等形式的组块化处理,扩大短时记忆容量,增强记忆语境效果;积累语言和百科知识,进行会前准备,提升长期记忆,缩小与单语听众的认知语境差距等等。关联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些策略,为他们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进一步提供较强的理论依据。
Sperber,D.&D.Wilson.1986/1995.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Oxford:Blackwell.
鲍刚,2005,《口译理论概述》[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陈晓春,2008,从口译的记忆机制论口译记忆效果的改善[J],《绥化学院学报》(12):125。
范守义,2004,外交学院英语系高级翻译培训的一点经验[J],《中国翻译》(1):64
何群,2011,《外交口译》[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刘和平,2001,《口译技巧》[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刘和平,2005,《口译理论与教学》。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雷中华,2007,交替传译教学中的短期记忆训练[J],《语文学刊》(2):53。
梅德明,2000,《高级口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王甦、汪安圣,1992,《认知心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杨跃、齐涛云,2006,关联理论与口译推理思维[J],《外语教学》(3):91。
张筠艇,2006,交替传译教学中的记忆训练[J],《外国语言文学》(4):268。
(齐涛云:北京合创道拓翻译有限公司副译审)
通讯地址:100036北京市海滨区莲花池西路莲花小区2号楼2门506室
2013-10-19
∗本文口译指交替传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