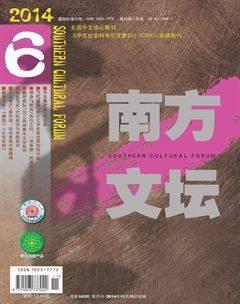审美的位移及其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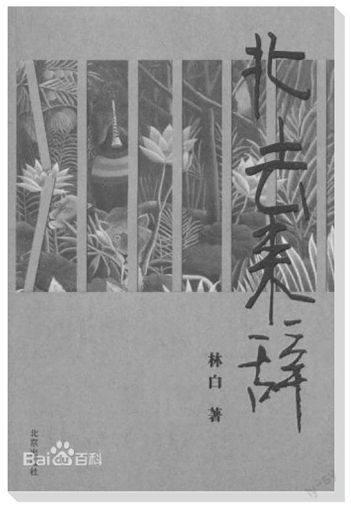
林白长篇新作《北去来辞》出版之前发表在《十月》杂志,发表时以“北往”为题。就标题的变化,林白显然有她的考量。字面上看,“北往”简约明朗,但其意义是单向的,而“北去来辞”包含着“去”与“来”,其意义则是双向的,因而意蕴更丰赡更复杂。就文本来看,我们认为,“北去来辞”更切合小说叙述实际。与那些只是反映“北漂”者在皇城脚下的个人遭际和生存现实的作品相比,《北去来辞》的叙述更为客观、冷静和宽厚,也更具社会辐射力和历史纵深感。这是因为小说的叙述始终保持着一种审视的向度。从北漂者的生存反观女性自我的来路与去路,是林白把握女性命运的重要线索。而逃离现实会有怎样的出路?同样,回归故土,重返原乡,又如何能让焦虑的内心平静下来?这种双向结构,构成这部作品审美张力中的重要一环。这种结构及其所带来的艺术新变,充分展示了林白试图逾越女性叙事框架的强烈意愿。
目前对这部作品的讨论大多从女性主义出发,在社会学层面探讨女性生存的出路,或者从人物与时代的关系入手分析女性所面对的现实困境,揭示当代城乡社会结构的巨变。无可否认,这些阐释基本属于社会历史批评或文化批评模式,对人物和主题等层面的解读有一定深度。但我们发现,似乎很少有研究者从叙事审美或叙事诗学层面,去观察这部作品在林白创作中的重要转向,以及这种转向所彰显的审美生机,及其可能潜伏的叙事陷阱。本文从作家创作生成机制的角度进入,初步探讨这种创作转向对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某种参照意义。
一直以来,林白生活在逃离中。这不仅是指她从故乡北流到南宁,再从南宁前往北京这种地理学上的迁徙,更指她对自己所建立的女性叙事范式的一再反叛。这个意义上,我们尝试着用“逃离”这个词指称《北去来辞》所隐含的双重意义指向。一是主人公海紅自我逃离的精神行为,二是林白志在挣脱旧有的女性叙事路数的审美逃逸趋向。
当然,《北去来辞》所讲述的,不仅仅是关于逃离的故事,对林白来说,重返乡土与逃离故乡具有同质性。海红最后决定重返乡土实际上也是一种逃离,是对某种生活状态或情绪状态的逃离。从南宁到北京,再从北京到武汉,然后又回到北京,最后从北京前往湖北浠川……来自哪里,究竟又要去向何方,这是小说主人公在每个人生节点所必须面对的精神进向。具体而言,不断逃离,在逃离中寻找,是小说中第一主角海红的精神路线。从人物来看,小说中的两个主角,海红和银禾,都是逃离者,属于北漂族。如果往前追溯,海红的逃离始于少女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考入中山大学文科学习,这种选择必然与以学医为贵的家族文化相悖。后来是,踏着林白的足迹,主人公来到南宁,不久又迁往北京。这个意义上,海红隐喻着另一个林白,一个逃离者,一个追梦者。北京是文化中心的符号,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但那种文化“他者”的异质性,对来自边疆的文学青年构成无形的精神压制,不可避免地让他们不断滋生灵魂逃逸的冲动。海红辗转于北京和武汉,何处是归程?她无从知晓,只能悬浮地生存。后来,在银禾的世界,她看到了生机。于是,重归乡土的冲动时刻牵动着主人公的神经,而当她走进乡村现实,却又不免失望。这种不断逃离自我的结构,应该是林白小说叙事的动力装置。
小说主人公海红的文学青年气质,在人生经验上与林白构成交集,但凭这一点,还不足以说明《北去来辞》对林白,乃至对当代中国小说创作的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在写作的意义上,与海红一样,这次写作对林白来说也是一次寻找自我与逃离自我的旅程。城与乡、历史与现实的交叉叙述,自然异于《一个人的战争》的私人化书写,也不同于《致一九七五》的历史狂想式叙事。林白的叙述试图逾越封闭的女性空间,突显生命个体际遇的同时,兼及个体所处的历史、社会与政治。而且这种历史、社会与政治,从《玻璃虫》所面向的书生意气的80年代到《一个人的战争》书写身体觉醒中的90年代,直至延伸到多元文化并存的新世纪。林白深受后现代文化气息的感染,她开始对自己的叙述有所调适。《北去来辞》便是她艺术调整的结果。林白的叙述变得斑驳陆离,又杂乱零碎,时而妖娆,时而平实,思想随笔式文字不时插入其间,山野游记的笔法间离着冗长沉闷的讲述,等等这些,显然是作者在这部新作中所作出的审美尝试。
尽管自《说吧,房间》开始,林白的叙事便有了向社会敞开的种种迹象,但那种敞开毕竟是很有限的,尚不足以构成女性个体与现实社会、与自然宇宙之间的张力空间。这个意义上,《北去来辞》对林白无异于一次审美的历险。因为,这种人物繁多、面向宽广的写作并非林白所擅长。基于由内向外拓展的诉求,作者力图扩充女性叙事的审美疆域,在城市与乡村、中心与边缘的两极视阈中去观照女性命运的尴尬,并以此探入历史,在时代变迁中找寻人性裂变的轨迹。
创作主体的审美视野由个体向社会延伸,不断变换方式向前突进,这种路数当然归根于人物不断逃离自我的冲动。这种逃离似乎缘于主人公对梦想的追求,而且这种追求有时候甚至显得毫无理性可言。我们看到,海红与大她很多岁数的离异男人道良的结合,并非因为二者之间存在多少爱情,而似乎完全出自某种偶然,偶然的邂逅,偶然冒生出走的念头,又偶然中与道良同居。这种偶然性与女性天生的感性人格有关,这种感性经验贯穿于海红的每段人生。或者说,女性的自我逃离多半来自感性经验的作用。这种作用,具体到海红这样的浪漫女性,表现为那种“超现实主义”的冲动,那种多少有点失去理智的穿梭与突奔。作者把这种“超现实”的人生取向形容为带有反讽意味的“响尾蛇”,那是一股蛊惑人心的魔力,它“啸叫着咬着了她的精神,她中了毒,病态地热爱”。并使她认为“现实都是庸俗的,日常生活是臭大粪”。文艺青年为梦想而脱离现实,甚至有些疯狂,也是林白很多小说女主人公所具有的典型气质。
那种诗意的幻想让女性远离世俗,躲避在精神审美的城堡。这种自我隔离使她们只能长久地飞行在幻想王国,而难以着陆于粗俗的现实中。所以,当海红走进现实世界,必然处于漂浮、纠结和迷乱的状态。这些鲜活而丰富的感性经验,具有非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这种特征取决于海红的特定人格。她不愿做一个四平八稳的人,飘荡、躁动、狂放,才是她的本色。从审美生成来看,这些感性经验部分来自作者自身的个体记忆。作者坦言,海红这个人物有一定的自传性,但我们不能因此认为,海红=林白。一方面,海红这个人物是林白向个体记忆索取经验的结果,按照林白的说法,这种经验实际上是一种“实感经验”,出于林白早年的文学情结。另一方面,在把自身经验赋予人物的同时,作者试图“为书中的人物找到属于他们的个人经验”①。这个意义上,海红是一种“化合物”。一是作者自身的个人经验,二是想象的个人经验,两种经验交织于作者内心,最终化合成主人公海红的独特经验。
如上文所说,感性的因素暗中主导着个体不断逃离旧我、奔向新我的自我更新的过程。而我们也看到,《北去来辞》相对于林白此前的作品更具理性化的气象,这不仅仅表现在,大量散落在叙述中的那种具有哲理性的小体字段落,而更多是主人公对女性生命、对个体命运的自我审视,以及她对自我与社会、自我与宇宙之间复杂牵连的思考。已知天命的林白越来越意识到,“一个人是不能孤立存在的,必与他者,与世界共存。”②《一个人的战争》中,多米要挣脱女性与生俱来的困境,就必须告别私语化的封闭空间,投入现实世界的洪流中,经受摸爬滚打的人生历练与磨砺,以此构成不断反省自我的经验结构和精神自觉。所以,在《北去来辞》中,林白尽力让“海红突破她与现实的疏离感,同时希望自己也能找到与世界的真切联系,若非如此,人的存在怎能够真确?”③以此看来,海红是多米生命的自然延续,她似乎已经明白,“一间自己的房子”对于现代女性的生存而言远远不够。女性要获得发展,实现梦想,不仅要在物质和精神上取得独立,还要走出这间自我囚禁的“房子”,摆脱狭隘逼仄的室内纠缠,将个体汇入泥沙俱下的广阔洪流中。
海红一生都在逃离,逃离那不如意的现实,同时她又在不断寻找,寻找自我安顿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建立个体与世界的真实联系。这是文本的核心指向,也是我们理解人物的重要依据。如何在这个大变动的时代中确立自己的精神坐标,找到灵魂的依托之所,这个终极性问题始终困扰着她。在逃离和寻找中,海红游走在中心与边缘之间。北京是文化中心,是文学青年实现梦想的地方。然而,海红在这里并非如鱼得水,轻松实现自己的作家梦。因为她无力真正融入这个中心,而是纠缠其中,精疲力竭。然而,那种青春的理想情怀虽不能兑现,却总是难以遏止,挥之不去。小說中这样写道:“那些支离破碎的文字没有获得成功,偶有发表,从未得到重视。但她仍然沉浸着,那是一处地洞,避难所。她钻进去,像一只地蚕。”那种沉闷的家庭气氛,那种淡漠的人际关系,那种执拗与不甘的心态,促使她再次产生逃离的冲动,逃离这个不属于她的“中心”。显见的是,海红的反复逃离与艾丽斯·门罗小说《逃离》中主人公卡拉的逃离模式既有联系,又判然有别。卡拉是在善与恶之间抉择,弃恶而逃,择善而依,但她的逃离是不彻底的,这种无法逃离的苦衷源自女性自身的脆弱无助和依赖惯性。这个意义上,由于女性的脆弱无力,海红与卡拉有着相似的人生轨迹。海红与道良离婚后,在外飘荡多年,无论走多远,但海红在精神上还是依赖于那个并非她所爱的道良。而海红与卡拉不同的是,海红逃离的最初动因,不在善恶对峙的内心纠葛,而是出于女性自身去边缘化的内心冲动所催生的个人寻梦情结。这种不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海红与卡拉虽然属于同一谱系(逃离女性),却又个性迥异,人生形态亦相去甚远。
某种意义上,人物的逃离模式决定了林白审美逃逸的路向。从文本中,林白审美逃逸的志向并不十分坚定,她似乎还是有所犹疑。我们发现,小说的叙述确实显示出创作主体的内在挣扎,以及这种挣扎带来的审美纠缠。需要说明的是,选择“逃逸”这个词,只是为了理论表述的方便,给出一种美学分辨的视角而已。之所以将林白此次创作概括为审美的逃逸,当然有个话语设定的前提。正如海红对自我的逃离那样,林白也在试图逃离自创作《一个人的战争》以来所确立的那种女性叙事美学。如上所述,林白此前的叙事多局限于女性的室内经验,相对封闭狭窄,这种个人化叙事有赖于作家的个人记忆与个人经验。与90年代相比,新世纪的文化语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网络文化迅猛发展,为人们尤其是女性提供更为辽阔的生存空间,人们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也随之变化。有了这个平台,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容易也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每个人都愈来愈无法脱离社会而存在。这种情势下,多元文化意识形态对作家写作方式和审美观念的影响,当然不可小视。我们发现,《北去来辞》中的人物之众多,空间之开阔,几乎是林白以往任何一部作品所无法比拟的,这种变化自然呼应了小说叙事寻求空间拓展的需要。
《北去来辞》的多声部叙事由各种异质并存的音调组合而成。海红无疑是这部小说的真正主角,而道良的内心风暴,银禾的乡土根性,与海红的浪漫诗性相映成趣。下一代中,喜雨的野地气质,春泱的温室成长,两种生命形态各异,生机与危机参差并存。而这些次要人物的重要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些次声部的组合,极大地丰富了海红这个主声部的旋律。其次,这部小说中,林白试图对她所心仪的记忆美学实行部分逃逸。在《玻璃虫》《说吧,房间》等作品中,林白的叙事主要还是依赖于个体的记忆与经验。而我们发现,《北去来辞》的叙事视角不仅仅是“向后看”,以捕捉和描摹记忆中的历史图像,而随着人物追梦情节的展开,叙述视角不断延伸,直至进入当下的形形色色。用作者的话说,这次写作“往前走了一步”④。这样,《北去来辞》的叙述常常徘徊在历史和现实的两极,构成一种审美张力。而且,这种历史与现实的交替叙述越是到后面,书写现实的部分所占比重越大。这种处理与作者开辟新的叙事疆域的审美企图有关。因为林白意识到,这个时代,倡导女性独立、强调女性身体觉醒的女性主义文学已经不合时宜,她认为:“自我的半径需要扩大,不然这个自我只是一个逼仄的自我。”⑤林白试图让女性自我的世界与外部世界相交融,让主人公在更为广阔的现实中找寻自我与世界的联系,使这个“逼仄的自我”在不断变得丰盈和坚实的过程中,确证女性之为女性的某种本质性生存。
至于为什么逃逸,到底逃向何方,创作之初,林白可能并不十分明确,因为《北去来辞》不是一部观念先行之作,也不属于那种一气呵成的长篇。林白的创作过程充满变数,文本在创作中也因之发生了数次审美变异。文学史上,叙事文本在写作中发生变异,逃逸出作家审美预期的情况相当普遍,而且这种变异后的叙事走向,甚至可能与创作初衷完全相悖。托尔斯泰、鲁迅等前辈作家都曾有过此类经验。小说创作中出现某种变异看似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随意性,但它往往萌生于作家遵循某种美学尺度的自觉。这种在复杂的自我牵扯中完成的写作,由于无形中增加了审美变数以及随之产生的文本内部的复杂性,常常可能成就不朽之作。例如,但丁和托尔斯泰尽管有意要在作品中宣扬一套宗教或道德哲学,但艺术直觉驱使他们推翻了这种意图而成就了伟大艺术。然,这并不是说《北去来辞》是一部无可挑剔的伟大作品,而是说,很大程度上,《北去来辞》美学上之所以发生位移,在于作者的审美习惯和审美自觉,以及由这种气质所决定的小说叙事偏离预先审美轨道的某种可能。换句话说,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潜与积淀,林白找回了属于她的叙述,找到了她的人物和独自的叙事向度。
据作者自述,《北去来辞》脱胎于《银禾简史》,且历经反复推敲和删改而成。后者的主人公银禾是具有典型传统乡村文化人格的农村妇女,应该说,这样的人物在当代农村普遍存在,但银禾自有她作为文学形象的“这一个”的艺术魅力。虽然我没有阅读过这个最初版本,但仍能大体推断这部书的审美脉络,它可能基本延续着林白《妇女闲聊录》对现实的思考,所不同的,不过是文体形式上存在某些差异。对现实的关注是林白近期创作频频显现的审美意向,但若是过于期待林白对现实的深度表达,可能不免失望。因为,“林白是天生的记忆型作家,上帝赋予她想象的翅膀,是为了让她往后飞,飞到记忆中的故乡。一旦降落到现实的大地,林白的行走便会显得举步维艰。”⑥这也是《妇女闲聊录》《米缸》等反映现实的作品之所以遭受诟病的原因。林白这一代作家,包括苏童、余华、格非等,近期创作中对现实的表达多少有些急功近利,让他们不能从容体验和感受现实中人性的复杂性以及人性嬗变的文化深度,他们对现实的艺术化处理,显然不如张炜这样的作家那般娴熟和有力量。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银禾简史》到《北去来辞》,这其中所隐藏的审美位移,对林白无疑是一次拯救。就作家气质来看,从自身的个人记忆中撷取叙事资源,创作具有个人化叙事作风的小说,对林白可能会更得心应手。只是,这种艺术潜质有待某种机缘的唤醒,正是在这个节点上,一个新的人物海红神秘降临。这个人物诞生于林白的一念之间,说来有些神秘和飘忽之感。遥想住宿红海的林白,在那月圆海阔、天风浩荡的诗境中,海红这个人物“咚的一下”闪现在我们作者的脑海中。这个人物的神秘降臨,以及那闪现的灵异时刻,对林白的创作无疑具有点化的功效。从人物命名(海红诞生在红海)便可看出,这次神秘的启悟对林白的创作转折有多重要。为什么重要?这无非是因为,林白从这个人物看到了她自己的面影,看到了她所熟悉的审美路数。所以,她决定“扑到初稿上”,“推倒重来”。渐渐地,这个“后加人物”开始持续牵动着作者的灵魂,并劫持了她,主导着她的叙事路向。就这样,海红便后来居上,其重要性超过了银禾。这部小说的审美面相由此彻底改观,它不再是纯粹地面向现实,批判现实,而是接上了林白个体叙事的血脉,沾染了林白女性叙事所独有的审美趣味。
上文提到,人物寻梦的人生模式,以及女性天生的感性冲动,是促使小说叙事向现实挺进的内在因素。或者说,人物的精神渴求与灵魂追索内在地决定着叙述的走向。于是,林白那妖娆杂碎的叙述,让我们不但看到两代,准确地说,可能是三代女性的生存意境,还目睹了她们身边最切肤最真实的现实境况。但我们也遗憾地看到,林白借人物之口对现实的讲述往往停留在现象式的碎片化呈现,不能自然而然地融进属于她自己的那部分叙述。即使是那些可能给叙述带来活力的关于民俗风情的部分,也显得有种堆砌感,游离于人物本身的生命呈现。这种拼贴之感还表现在她对海红与银禾这两个人物的处理,《银禾简史》到《北去来辞》,两个文本之间的审美位移所造成的后果是,海红几乎淹没了银禾,银禾身上那些本来具有的生机勃勃的野性人格被压抑了,消失在海红对诗性的追求和妥协中。这种拼贴之感,固然可能是海红与银禾之间所存在的无法弥合的精神裂隙所致,但也让我们看到了林白处理现实题材时与同代作家所共同面临的困境。
【注释】
(1)②③林白:《北去来辞》,418、419、419页,北京出版社2013年版。
④⑤范宁、林白:《“战争”更野性,“北去”更丰富》,载《长江文艺》2013年第8期。
⑥王迅:《记忆、感知与碎片诗学——林白小说创作论》,载《南方文坛》2011年第5期。
(王迅,供职于《南方文坛》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