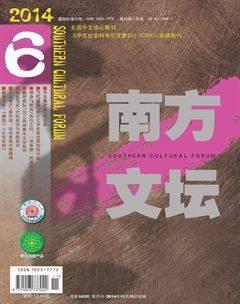“神实主义”与“耳朵识字”
在当代文坛,阎连科是一位风格独异、辨识度非常高的作家,其独树一帜的风格,在当代作家中恐怕无有能出其右者。对于阎连科的写作,从来就是褒贬不一,争议不断。有人惊呼,阎连科的小说是令人拍案叫绝的中国“奇小说”,是纪念碑式的作品,丝毫不逊色于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对此,阎连科将自己称之为“写作的叛徒”,并将其对小说的“发现”,升华为“神实主义”的创作理论。阎连科阐释说:“神实主义,大约应该有个简单的说法。即在创作中摒弃固有真实生活的表面逻辑关系,去探索一种‘不存在的真实,看不见的真实,被真实掩盖的真实。神实主义疏远于通行的现实主义。它与现实的联系不是生活的直接因果,而更多的是仰仗于人的灵魂、精神(现实的精神和实物内部关系与人的联系)和创作者在现实基础上的特殊臆思。有一说一,不是它抵达真实和现实的桥梁。在日常生活与社会现实土壤上的想象、寓言、神话、传说、梦境、幻想、魔变、移植等、都是神实主义通向真实和现实的手法与渠道”,“它在故事上与其他各种写作方式的区别,就在于它寻求内真实,仰仗内因果,以此抵达人、社会和世界的内部去书写真实、创造真实。”①在《什么叫真实?》中,阎连科说:“我以为,生活是没有什么真实可谈的,只有一些经验可供你回忆,而今天真实的,也许明天就是假的了;今天我们误以为是假的,一段沉静的对白之后,也许我们就会看清它是真的了。一个作家,应该有自己的真实标准。应该创造自己的真实标准。应该坚信自己的真实标准。可以不相信生活的真实,但不能不相信自己内心的真实。重要的,是一个人要有属于自己的真实的内心。”②有学者指出:“‘神实主义称谓虽新,但理论则谈不上新颖。相当程度上是以自己方式‘复述了一些‘明日黄花的话题”,“理论上显然没有超越加洛蒂们的看法。”③阎连科这种虚无缥缈,根本不存在的真实和海市蜃楼一样的“神实主义”创作理论,就像那些沉溺于“人体科学”,坚信自己能够通过意念来发电,凭借其特异功能,完全可以通过耳朵来识字的江湖“奇人”,不用眼睛就能看清生活的真相。基于这种有悖常理、匪夷所思的创作理念,我们看到,阎连科的小说就像是误入了迷宫而不能自拔,以致乱象丛生。
一、妖魔化与类型化的乡村故事
在阅读阎连科的小说时,我们发现,在其思维定式的制约之下,阎连科认识世界的方式几乎就是非白即黑,一成不变的二元对立。在阎连科的笔下,纷繁复杂的现实社会,一概被简化成为一个个妖魔化的故事。这就是,城市的发展是一部荒唐的闹剧,它完全靠的是“妓女经济”。一个地方的经济之所以飞速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的,必定是美容院、洗脚城、按摩院和宾馆茶楼里的小姐们;越是穷乡僻壤,甚至各种残疾人扎堆的地方,就越适合人类居住,越令人向往;那些身体健全的人,反而不如残疾人生活得舒心自在。在《受活》中,为了获得到残疾人聚居的受活庄落户的资格,县长柳鹰雀义无反顾,不惜用故意制造车祸,压断双腿的方法来取得残疾人的认同,融入残疾人“受活”的世界。为了迎娶灵秀丽质的残疾人花嫂为妻,一个年轻的知府居然把自己的左手一刀砍掉,以此来赢得花嫂真正的爱情,并对花嫂说:“不残了你会嫁给我吗?”诸如此类比天方夜谭还天方夜谭的描写,在阎连科的小说中早已成为了家常便饭。在《最后一个女知青》中,知青李娅梅好不容易通过各种努力才回到了日思夜盼的省城,并通过一路打拼,成为商界女强人。但越是成功,越是有钱的李娅梅,婚姻就越是不幸,大都市养尊处优的生活,无时无刻都让她感到身心疲惫,最后不得不逃离城市,回到自己当年下乡的那个偏僻山村张家营。小说中的主人公李娅梅,则被阎连科塑造成为了一个仿佛高唱着:“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的现代版的女陶渊明。倘若当今城市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真的都像阎连科小说中描写的那样,有百害而无一利,只能给现代人的生活带来无穷的困扰和痛苦,那么人类最好的归宿,就是回到原始社会,大家都去刀耕火种,茹毛饮血,甚至当个没有烦恼的傻子。英国作家伊利莎白·鲍温在《小说家的技巧》中说:“小说是什么?我说,小说是一篇臆造的故事。但是,故事尽管是臆造的,却又能令人感到真实可信。真实于什么?真实于读者所了解的生活,或者,也可能真实于读者感到该是什么样子的生活。”④阎连科的“神实主义”创作手法强调的所谓“内真实”,仰仗的所谓“内因果”,可说是把片面当成了深刻,把小说的虚构艺术等同成为胡思乱想和胡编滥造。
正是出于这种主观的“臆思”,在阎连科的笔下,农村的女人要想挣钱,唯一的出路,就是到城里去出卖肉体做小姐。城里的女人要想赚大钱,就必定要去找那些钞票胀满腰包的外国人。除了张家营人,到城里看看,有几个女人不从外国人那儿挣钱?更不要说洛阳、省会和南方了。仿佛偌大的一个中国,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淫窟,所有的男人都在不分白天黑夜地寻求刺激,所有的女人都在为了金钱而寡廉鲜耻,自甘堕落,而唯有小说中的张家营,才是阎连科心目中最后的一片净土。因此,女人卖身和性描写,就成为阎连科小说中总是乐此不疲、反复书写的“重头戏”。某个乡村富裕了,就必定是这个村去城里做小姐的人多了。上级领导来农村视察,就必定是另有所图,他们觊觎的是那些如山花一样,盛开在原野上,淳朴美丽的乡村女性。每当这时,村干部们为了巴结上级领导,无不如出一辙地像好客的东道主为客人奉送土特产一样,随意就可以将村里漂亮的年轻女性“馈赠”给那些垂涎欲滴的政府官员,而当地的村民们为了能够尽快摆脱贫困,人人都摇尾乞怜地赞成村干部们的这种荒唐行为。在阎连科这种漫画式的极尽夸张的描写中,几乎所有的官员,尤其是那些农村的基层干部,个个都是无法无天、利欲熏心、脑袋发热、乌七八糟的人渣。在《受活》中,起初只是一个小小副县长的柳鹰雀,居然狂妄到了要想花一笔钱,到俄罗斯去购买列宁遗体,安置在双槐县的魂魄山,然后大收门票,让全中国和全世界的人都像观看动物一样,发疯似的前来参观。《日光流年》中的司马笑笑就公然宣称:“我是村长,我就是王法。”在《金莲,你好》中,阎连科用揶揄的口吻写道:“刘街倘若是了一个国,村长就是这个国家的皇上或总统,刘街如果是兵营,村长就是这座兵营的总司令,若刘街仅仅是一个大家族,那村长也是这个大家族中的老族长,德高望重的祖爷爷。”哪个党员、干部敢跟村长说一个不字,村长就会破口大骂,日他祖先。在《坚硬如水》中,即便是曾经给八路军送过信的老支书,同样是一个贪图私利、滥用职权的堕落分子。为了让才貌出众的高爱军能够成为自己的乘龙快婿,他居然冠冕堂皇地对高爱军说:“我是看你爹死得早,也算革命后代哩,在县一高学习成绩又不错,才同意你订婚的,结了婚生个娃儿我就把你送到部队上,在部队上入个党,回来我就把你培养成为村干部。”而那些要想出人头地的农村青年,只要攀上了村干部做女婿,其美好的前程便指日可待。在《炸裂志》中,炸裂村村长孔明亮既是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的土皇帝,又是耙耧山脉中诲淫诲盗的最大“黑老大”。他利用手中的权力,不但将年仅十七岁,容貌姣好的程菁强行霸占,而且还公开煽动和授意炸裂村的村民们违法乱纪。于是,私欲膨胀的炸裂村,为了钱,整个村子的人都疯掉了!男人们统统都成为疯狂抢夺的飛车大盗,女人们则统统都被赶到城里去做了勾引男人、贩卖色相的“鸡”。为了能够尽快致富,炸裂村的男人们就像当年的“铁道游击队”一样,在偏僻的耙耧山脉中八仙过海,各显神威,对南来北往、经过炸裂村的列车疯狂地进行抢夺。
阎连科的这些乡土小说,就像是从一条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工业品一样,完全是一种皮相的、程式化的写作——因为村干部们个个都无恶不作,坏得来头顶长疮,脚底流脓,所以就如同种下了孽缘,必定会遭到恶报。他们不是老婆因病长期卧床不起,就是女儿个个都长得像丑八怪一样,甚至连其侄子也都是个瘸子。在《金莲,你好》中,村长的女儿月丑得像个鬼:“脸上如小麦杂面地黑灰,无论如何有粉也是涂盖不下,盖得厚了,反而有些青色,如在冰天雪地冻了一番。加上她左边那只上吊的斜眼,每当看人的时候,那只眼球就躲到一侧,眼白铺天盖地地露在外边。还有她的双腿,那样的短,那样的粗,立在地上如两个麦场的石磙呢。”即便是长得如此之丑,月却偏偏还要臭美,即便是在初冬,有人早早穿了毛衣,月却偏偏还要穿着毛裙,腿上裹尸样穿了一件紧身的呢绒弹力裤,露出自己的大腿。總之,不该涂的地方,月却要一个劲地涂,并以为自己是在乡间引领新潮。如此的丑女,要不是其父亲是村长,恐怕即便是嫁得出去,最多也只能是找一个残疾人或是瘸秃。在小说中,一表人才,曾经发誓“杀了我都不会娶村长家姑女”的老二,为了在村改镇后能够当上派出所所长,居然违背自己的良心,不惜以婚姻作为通向金钱和权力的桥梁,违心地娶了村长丑陋无比的女儿月。在长篇小说《坚硬如水》中,阎连科就像玩弄文字游戏一样,只是将《金莲,你好》中的月改换一下姓名,就成为老村长的三闺女桂枝。桂枝“在她姐妹几个中,长得柳不绿,松不翠,满坡黄土飞,比我小一岁,看上去比我大了三五岁。我不知道她为啥看上去竟会比我长五岁,是因为个子矮?因为皮肤黑?还是因为她爹是支书,所以她就胖,连头发也可以朝朝暮暮都像没梳的模样儿”。小说中的主人公高爱军,在见到桂枝的模样时,喉咙如塞了一团棉花想要吐出来。为了能够在不远的将来飞黄腾达,高爱军居然以婚姻作交易,和丑得令人恶心的桂枝结了婚。而《情感狱》中的连科,则完全就是高爱军的翻版。他“高中毕业,学习好极,爱过的姑女爹当县长了,她也远走入城了。一腔义愤回到村,曾为大队秘书的位置眼红过,为娶支书的丑女奋斗过,为当村干部、乡干部、县干部……朝思谋、夜思谋,到头来,仍还是站在自家田头上”。回到村里,连科为了今后的仕途,又开始赶紧追求长相丑陋的村长的三姑女,但即便是这样,连科企图通过与村长女儿的婚姻来改变命运的企图也最终化成了泡影。是副乡长的儿子夺去了连科眼看就要到手的婚姻。尽管村长的三姑女长得丑,但副乡长的男女孩娃却长得更是歪瓜裂枣,为了巴结即将成为乡长的副乡长,颇有心计、内心肮脏的三姑女,为了实现自己今后当村长的野心,在快要与连科成婚时突然变卦。而被三姑女抛弃的连科,为了能攀上副乡长,又转而开始向只有小学文化,长相丑陋的副乡长女儿发起了爱情攻势,并美其名曰是因为副乡长的女儿心好。总而言之,在阎连科的笔下,那些家境贫寒,有才有貌的农村青年要想出人头地,唯一的独木桥,就是找一个拥有实权的农村干部长相奇丑的女儿结婚。
由于写作视野总是局限于其固有的生活经历上,阎连科的乡土小说,简直就如同克隆人,长得几乎都是一个模样。
二、以旧充新的大炒冷饭
莫言在与王尧对话时说:“我记得在军艺读书时,福建来的孙绍振先生对我们讲:一个作家有没有潜能,就在于他有没有同化生活的能力。有很多作家,包括‘红色经典时期的作家,往往一本书写完以后自己就完蛋了,就不能再写了,再写也是重复。他把自己的生活积累、亲身经历写完以后,再往下写就是炒冷饭。顶多把第一部书里剩下的边边角角再写一下。”⑤孙绍振先生的话,不幸在阎连科的身上被言中。阎连科究竟有多少同化生活的能力,这是一个有待学界深入探讨的问题,但阎连科小说中惊人的重复,却是当代作家中极为罕见的。其小说被某些学者广为称道的创新,最多也只是形式上的新瓶装旧酒式的“创新”。在阎连科的许多新作中,我们都能看到其旧作的影子。
如阎连科新近出版的《炸裂志》,完全就是一部将其大量旧作进行搅拌和混搭之后的拼凑之作。小说的故事,几乎都在阎连科以往的小说中出现过。只不过《炸裂志》在表现手法上比以前的小说更夸张、更加极端。在发表于1997年的中篇小说《金莲,你好》中,村长去上边跑动,想把刘街改为镇,改为镇后的刘街的街道就成黄金宝地,生意就天天顾客盈门。为了让刘街在行政区域上,从一个村委升迁成一个镇党委,他终日跑县里,跑地区,吉普车的轮胎都跑爆了两只。刘街上下都为刘街改镇而出力,村长的嘴唇着急上火,燎泡白灿灿长了一层。为了对上级领导进行性贿赂,村长决定以到李主任家做保姆的名义,将漂亮的金莲“奉送”给不同意刘街改镇的李主任。村长对金莲说,你去村人给你开工资,每月要一千、两千、三千都可以。你这是帮刘街几万人口的忙,帮了忙几万人都会感激你。你去了村里把老大(金莲因病死亡的丈夫)按烈士对待,在他坟前立块碑,将来你是烈士家属了,在村里无论啥都照顾你。在《炸裂志》中,阎连科对乡村干部用性贿赂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的狂想和描写,迅速登峰造极。炸裂村庞大的性贿赂团队的八百个姑娘哪也不要用,全部用在拉拢那些论证炸裂改市的院士、教授和专家身上。只要谁拿下一个专家或教授,奖他们五十万或者八十万,把一个权威人士弄到床上了,最少奖给她一百万块或者一百二十万,如果这个权威人士刚好是投票的组织者,则最少奖给她二百万。2004年,阎连科发表了短篇小说《柳乡长》。小说中的槐花,因为家庭贫穷,到九都市去打工,一年后又把她的二妹接到城里,两年后她三姊妹在城里开了一个叫逍遥游的美容美发店,三年后包下一个娱乐城。那里的小姐保安都有几十个。钱儿呢,每日每夜就像关不住的水龙头样哗哩哗啦往城外流。为了带动全村人发财致富,柳乡长把槐花当作了全村人学习的楷模,并说:“我作为柏树乡的一乡之长,没别的报答槐花姑娘哩,我只能给槐花姑娘竖这么一块碑,只能号召全乡各村的百姓都向槐花姑娘学习哩。”为此,乡里专门在碑上刻上了海碗大的七个字“学习槐花好榜样”。在《炸裂志》中,从小生活在农村、相貌出众的朱颖刚到城里才是一个理发店的服务员,如今却在省会开了一个娱乐城,一次洗澡能容下九百男人和女人,每天挣的钱都能买几辆小轿车,或者盖一栋小洋楼!乡长说:“咋能不给朱颖立碑呢?”朱颖不光自己家盖了楼,而且还帮乡里出去的一百多个姑娘家家都盖了瓦房和楼房,不仅如此,朱颖还主动并动员上百的姑娘捐款,让刘家沟和张家岭两个村庄通了电、水和路。乡长说:“我作为一乡之长,没有别的报答朱颖这姑娘。我只能给朱颖姑娘竖这么一块碑。”于是,一块巨碑上镌刻上了篮子一样大的十个字“致富学炸裂,榜样看朱颖”。在我看来,《炸裂志》的写作,可说是当代作家自我复制的典型的标本。阎连科的“创作”方法只不过是,在其原作上稍微动一动手术,整一整容,就改头换面地成为一部被新闻媒体大肆炒作,被某些学者极力追捧的“神实主义”力作。如:
一村的青年男女便哗的一下都去了。
人走了,村落像过了忙季的麦场一样空下来。可那人挤人的一车椿树村的青年男女们,被乡长亲自送到几百里外九都市里火车站旁的一个角落里,将卡车停在一个僻静处,乡长下了车,给每个椿树村人发了一张盖有乡里公章的空白介绍信,说你们想咋儿填就咋儿填去吧,想在这市里干啥你们就去找啥儿工作吧,男的去给盖楼的搬砖提灰,女的去饭店端盘子洗碗;年龄大的可以在这城里捡垃圾,卖纸箱,扫大街,清厕所,年纪小的可以去哪儿当保安、当保姆,去当宾馆服务员,总而言之哦,哪怕女的做了鸡,男的当了鸭,哪怕用自家舌头去帮着人家城里的人擦屁股,也不准回到村里去。说发现谁在市里待不够半年就回村里的,乡里罚他家三千元,待不够三个月回到村里的,罚款四千元,待不够一个月回到村里的,罰款五千。若谁敢一转眼就买票回到村里去,那就不光是罚款了,是要和计划生育超生一样对待的。——《柳乡长》
全村的青年便哗地一下都去了。
人走了,村里像过了忙季的麦场一样空下来。可那人挤人的几车炸裂男女们,被乡长和村长亲自送到几百里外市火车站旁的一个角落里,将卡车停在一个僻静处,乡长和村长下了车,给每个炸裂人——尤其是刘家沟和张家岭的人,都发了一张盖有乡里、村里双公章的空白介绍信,说你们想咋儿填就咋儿去填吧,想在这市里干啥你们就去找啥儿工作吧,男的去给盖楼的搬砖提灰,女的到饭店去端盘子去洗碗;哪怕去找朱颖做了鸡,当了鸭,用自家舌头去帮着人家擦皮鞋、舔屁股,也不准回到村里去。说发现谁在市里呆不够半年就回村里的,乡里罚他家三千元;呆不够三个月回到村里的,罚款四千元;呆不够一个月回到村里的,罚款五千元。若谁敢一转眼就买票回到炸裂去,那就不光是罚款了,是要和计划生育超生一样对待的。——《炸裂志》
在《炸裂志》中,几乎整章整章,整段整段都是将《柳乡长》和阎连科其他的小说用“复制+粘贴”的方法,写进这部“神实主义”力作的。在小说中,阎连科一如既往地施展了以“性”作为看点,以怪异的性噱头来吸引读者眼球的拿手好戏。在《风雅颂》中,小说的主人公,清燕大学副教授杨科在分析《诗经》中的《唐风·葛生》时说,这是写一对恩爱夫妻,正当他们共享幸福和欢乐时,丈夫不幸离开人世(可能是心脏病。也可能他和妻子做爱时,心脏病发作,他就死在了妻子的身上)。在接下来的描写中,《诗经》中做爱死亡的故事在现实中戏剧性地发生了——死了男人的付姐到城里打工,最后和两百多斤重的吴胖子勾搭在了一起,在和付姐做那事时,因为过度兴奋,吴胖子心肌梗死,大人小孩都知道,吴胖子死在了付姐的身上。在《金莲,你好》中,老大因为身材矮小,生理功能有障碍,在到武汉求医成功之后,兴高采烈地回到村子里,与妻子金莲做爱,因为过度兴奋,突发脑溢血,暴死在了金莲的身子上。在《炸裂志》中,村长孔明亮的父亲在儿媳朱颖的唆使下,来到“天外天”销魂,最终因为极度亢奋,出人意料地死在了一个姑娘的身子上。如此之多的小说,都在书写同样的故事,由此可以看出,阎连科的小说,的确是喜欢拿“性”来找乐子。至于这些“性”描写究竟有多少必然性和艺术性,只有阎连科自己才知道。
三、粗制滥造的文字大杂烩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汪曾祺先生在《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中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小说使读者受到感染,小说的魅力之所以在,首先是小说的语言。小说的语言是浸透了内容的,浸透了作者的思想的。我们有时看一篇小说,看了三行,就看不下去了,因为语言太粗糙。语言的粗糙就是内容的粗糙。”⑥汪曾祺先生甚至把小说的语言提高到了作者人格的高度,认为小说的语言体现的是作者对生活的基本态度。阎连科一团乱麻的小说语言,几乎可以用“病入膏肓”来形容,其沉疴在身的病象,就像秃子头上的虱子,一望便知。遗憾的是,多年来,在众多专家学者对阎连科小说的研究中,不但鲜有人提及,甚至反而还被认为是阎连科小说语言的一大特色而大加赞赏。这里我们来看看阎连科的中篇小说《桃园春醒》中的这样一些描写(文中的着重号均为笔者所加):
张海回家,进门时脸色是青色,朝门上踢了一脚,像那柳木大门,曾经是着仇家。媳妇在院里做饭洗菜,手在水里泡着,粉红着,两朵花一样,听见门的暴响,慌乱抬头,问说你又喝了?
喝吧,媳妇说,喝了醒酒。又说,晚上吃米饭,你在南方米饭惯了。
你是存心蓄意,要把这日子过得仓空屯泄,败家败财;存心蓄意,要把家里那点存钱花干弄净,分文不留不是?!
这当儿,有邻居耳了吵闹,风进来,群股着,一下把院子里塞实挤满,都说打啥呀,打啥呀,多好的日子,有啥可吵可闹可打哩。
那边的婆母,六十几岁,辈正威处,坐在上方先自端起饭碗,动了筷子,却并没有真正夹菜,只是望着儿子,说快吃饭吧,一家人都在等你。
在读阎连科的小说时,我们总是有一种疙疙瘩瘩的感觉,那种古而怪之的语言,犹如一锅夹生饭一样,让人实在是难以下咽。我不知道,是阎连科根本就不懂得现代汉语的语法知识,还是为了要标新立异,故意与现代汉语的表达方式对着干。在现代汉语中,“着”是一个时态助词,它的主要作用是附着在动词之后,表示进行态。但“曾经是着仇家”中的“是”字,是一个表示判断的特殊动词,不能与表示时态的“着”字连用。而“粉红”显然不是动词,在其后面添加上“着”字,纯属不伦不类。“名词动用”是古代汉语中一种常见的语法现象,但名词用作动词,有其特定的规律性和习惯表达,并不是想当然就可以随便乱用。阎连科小说中一个生活在偏僻农村的妇女,怎么能说出“米饭惯了”这样在古人的文章中才有可能出现的话?阎连科在小说中,常常是脱离小说人物的文化知识水平和所处的环境,任意为其“代言”,说一些与他们的身份根本就不相符的话。农村妇女吵架,居然也像古代的冬烘先生写文章一样,文绉绉的雕词琢句。诸如什么“存心蓄意、仓空屯泄、败家败财”。像“耳了吵闹,风进来,群股着”这样犹如外星人一样的语言,使读者在阅读阎连科的小说时只能是根据前后文的意思去瞎“蒙”。而像“辈正威处”这样的话,恐怕很少有读者能够说出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在我看来,阎连科或许是把写小说当成了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如将“本来”写成“本来着”;将“结果”写成“结果着”;将“可是”写成“可是着”;将“其实”写成“其实着”。所有这些“着”字,无一不是违反语法,多此一举的附赘悬疣。正因如此,我们在读阎连科的小说时,无时不感到字里行间有着太多的汤汤水水和花里胡哨的形容词。
阎连科小说语言的另一个显著病象,就是象声词的胡乱使用。在其小说中,像“叮叮当当”之类的象声词,简直就像决堤的大坝一样,汹涌而出,四处泛滥。如:
杜柏立在门口,朝西屋的棺材盯了一阵,走过去一下掀开棺盖,日光呼呼啦啦打在杜岩的脸上,他眯着双眼,如风吹了一样,身子叮叮当当猛然哆嗦起来。
他汗水落在她脸上,叮叮当当顺着她的额门往下流,把她的那颗痣洗得如一颗黑星星。
司马蓝按照瘦护士的吩咐,一动不动马趴着,听见刀子割皮的声音和他剥兔皮、羊皮压根不一样,剥兔皮、羊皮那声音是红得血淋淋、热辣辣,有一股生腥的气息在房前屋后叮叮当当流动着。
司马蓝用笔在手心上记下了一个钱数,太阳便从他们头上走将过去了。时光流水样叮叮当当。——《日光流年》
英国作家伍尔夫说:“在法国和俄国,人们严肃认真地看待小说。福楼拜为了寻找一个恰当的短语来形容一棵洋白菜,就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托尔斯泰曾把《战争与和平》改了七次。他们的卓越成就,也许有一部分是得之于他们所下的苦功,也有一部分是他们所受到的严格评判所促成的。”⑦然而,对于像福楼拜、托尔斯泰这样的文学大师的创作方法,阎连科是不以为然的。阎连科甚至公然宣称:“真正阻碍文学成就与发展的最大敌人,不是别的,而是过于粗壮,过于根深叶茂,粗壮到不可动摇,根深叶茂到早已成为参天大树的现实主义”,“从今天的情况来说,现实主义,是谋杀文学最大的罪魁祸首。”⑧对于现实主义恨之入骨的阎连科,愤然高举起“神实主义”的大旗,对现实主义痛加挞伐。然而,我们看到的是,阎连科粗制滥造和公式化的写作,不但根本无法超越福楼拜和托尔斯泰,反而使其小说在“神实主义”的装点之下,成为一种僵化死板的文字游戏。如写目光,无一不是用“噼啪”或者“噼噼啪啪”“砰砰啪啪”“噼里啪啦”这样的象声词来描写:
回头客把一张五十块的钱票递给四十时,极不尽兴地盯着藤像盯着一朵还未开盛的山坡上的花,眼里不断有火光噼噼啪啪响出来。
她们就那么天长地久地僵持着,两个人的目光在半明半暗的屋子里砰砰啪啪,撞落在地上如红火落地一样。一个屋子都燃烧起来了。
女人们像一片棉花样堆在路口上,一片哑然,一片苍白,眼里的惊愕石板样噼里啪啦砸在棺材上……——《日光流年》
如果要写脸上的表情,则一定有如同树叶,或者花之类的东西往下掉。如:
他们蹲在一边抽着纸烟,脸上又堆又砌地码满了“没有我们这水能流到村头的吗?”的兴奋,望着村里的女人和孩娃,眼角的孤傲和得意落叶一样哩哩啦啦往下掉。
竹翠说,你挑水呀四十姐?说这话时,脸上的笑厚厚实实堆得花叶样一片一片往下掉。
这样叫的时候,司马虎脸上的笑,就如熟透的红柿子,香香甜甜从脸上坠下来,弄得一地红红灿灿。——《日光流年》
阎连科小说中这种手工编织袋一样,毫无新意的描写,完全是一种专走捷径、放弃难度的写作。也就是说,阎连科的小说,都有一种驾轻就熟的写作套路。如写求情,则一定是用下跪来表达。在《黄金洞》中,老大和爹包养的城市女人桃发生了乱伦关系,被爹发现后,为了求得爹的原谅,老大给爹跪下了,桃也给爹跪下了;《日光流年》中的司马蓝,为了发泄自己的情欲,在蓝四十面前山崩地裂地跪下了。司马蓝不仅把下跪当成了习惯和生活方式,动辄就在父亲面前下跪,而且还逼迫其与村长蓝百岁有染的母亲,为了赎罪,山崩一样地给父亲下跪;在《受活》中,百姓们朝县长磕头,跪满了一个县城;在《最后一个女知青》中,同是下乡知青的“郝狐狸”,为了得到李娅梅的爱情,“如同悬着的木桩从半空中落下来”一样,又一次跪在了李娅梅的面前。李娅梅当年的一个同学,返城后待业,曾可怜地跪在一个主任面前想求份工作,说清道工、锅炉工都成;在《金莲,你好》中,老二为了谢绝美丽的嫂子金莲的爱情,“仰着头天塌地陷地跪下了”。酒店赵老板,把前台的迎宾小姐强奸了,在当上派出所所长的老二面前,不仅吓尿了裤子,并且失魂落魄地跪下了;在《风雅颂》中,清燕大学副教授杨科,在目睹自己的妻子和副校长李广智偷情时,居然万分窝囊、晴天霹雳地跪在地上向妻子和李广智求情:下不为例好不好?在《名妓李师师和她的后裔》中,李师师为了永远和周邦彦在一起,突然跪在了周邦彦的面前,说,邦彦,我生是你的,死也是你的;在《炸裂志》中,村长孔明亮的大哥孔明光与家中的保姆小翠勾搭在了一起,他们的父亲孔东德又与老大家中的保姆小翠暗中偷情,被儿媳朱颖发现后,孔东德不顾一家之长的尊严,匪夷所思地跪在地上,用膝走到朱颖的面前,用双手扒着她的身子说:“我老了老了,每天每夜都想小翠想得睡不着,想得用手抓床帮和墙壁,用手把我自己的身子揪得抓得到处都是青紫和淤血,都想半夜起来撞死和上吊。”阎连科在《炸裂志》中的这段描写,几乎就是《黄金洞》里父子亂伦的翻版。无跪不成书,人间无处不在乱伦,这一幕幕既荒唐又雷同的描写,或许就是阎连科所说的“神实主义”的“内真实”。
四、百孔千疮的知识硬伤
1982年,王蒙先生在《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中,谈到了中国作家的非学者化问题。
王蒙先生说:“靠经验和机智也可以写出轰动一时乃至传之久远的成功之作,特别是那些有特殊生活经历的人,但这很难持之长久。有一些作家,写了一部或数篇令人耳目一新、名扬中外的作品之后,马上就显出了‘后劲不继的情况,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缺乏学问素养。”⑨三十多年过去了,与现代作家们学贯中西,深厚的学养相比,当今一些著名作家的学养,实在是不敢让人恭维。阎连科的小说尽管蜚声中外,但其文史知识的匮乏,却非常令人揪心。如《炸裂志》中这样一段描写:
从北向南,爬上山的火车一般都是拉着矿石、焦炭和木材,从南向北来的火车都是拉着北方人要用的日用品,如电缆、水泥、建材和橘子、香蕉、芒果等在北方鲜见的鲜果实。
所谓“日用品”,是指人们日常应用的物品,如毛巾、肥皂、牙膏、梳子等。这里的电缆属于工业品,水泥属于建筑材料,而水果更是与日用品毫不沾边。阎连科先生怎么能够眉毛胡子一把抓,笼而统之地将其称之为“日用品”呢?并且水泥本身就是建材中的一种,阎连科在此将其与建材并列使用,无疑使小说呈现出一种句式杂糅和逻辑混乱的严重病象。
在《受活》中,阎连科写道:“清朝盛世之期,国泰民安,有一个从西安穿过伏牛山到双槐县里做县任的年轻人,嫌了路途遥远,他就寻着捷道穿过耙耧山脉去伏牛山那边的双槐县,到了受活这儿,口干要喝水,到花嫂家里讨了一碗水,他就碰到花嫂了”,于是,这个年轻人便对虽然残疾,但却美丽清纯的花嫂一见钟情。这个上任的七品知府就决定不再去双槐县做他的县官了。为了表示对花嫂的爱情,“知府就把他去上任的御书和御印及一路为进求功名背的书籍,一下子取出来,从梁上扔到了沟底去”。而花嫂的父母却对这位年轻人说:“我们一家人都是残人,哪能娶一个圆全健康的人来做女婿。”这样短短的一段描写,充分暴露出了阎连科可怜的文史知识。阎连科根本就不懂清代的行政区划和古代的官制。在我国的明清时期,一个省分为数道,道下分为府和州,府州的长官称为知府和知州。一个知府至少相当于今天的地委书记,让一个地委书记去做县官,无异于是严重的降职处分,怎么还能称之为是“上任”?况且,一个堂堂的知府如果去上任,还不早已是前呼后拥,车马相随,哪里还用得着一个人翻山越岭,饥渴难耐,像个叫花子似的,跑到一个普通的农家去讨水喝?难道阎连科不知道《儒林外史》中就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样的说法?况且,在清代根本就没有七品这样低等的知府,只有七品的县官。而“御书”和“御印”,则是专指皇帝的书和印章。想想看,清代的皇帝,再怎么糊涂,也绝不会把自己的书和印章单独交给一个年轻人随意背在身上。更为可笑的是,这位年轻人为了表示对一个农家女子的爱情,就像扔掉一双破鞋一样,一股脑就将“御书”和“御印”扔下了山梁。倘若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个年轻人和花嫂还不立即脑袋搬家,株连九族,满门抄斩?我们知道,在汉语中,“娶”字指的是把女子接过来成亲,而花嫂的父母却连嫁女儿和招女婿都分不清。脑袋稀里糊涂,这并非是他们的错,而是因为阎连科汉语知识的根底不深,词不达意的缘故。
缺乏扎实的功底,只是凭着一股热情和闯劲什么都敢写,早已成为了当今某些作家的一大通病。阎连科小说中花样百出的文史硬伤,真是让人大跌眼镜。阎连科在长篇小说《情感狱》中写道:“就那么一天,日子是古历黄道初九,清高宗乾隆一道诏书把我叫去了。我一到金銮大殿,文武百官分站两旁,齐刷刷地看着我。那大殿呀,金砖金瓦金柱子,连香炉、灯座都是金做的。到皇帝面前,我正要下跪,乾隆皇帝一招手,说:‘免了免了。跟着,乾隆皇帝又摆了一下手,文武百官就都退出了大殿。这当儿,大殿里余下我和皇帝俩人啦。皇帝说:‘听说你的象棋杀遍天下?我说:‘不敢皇上……皇帝说:‘听说你从九岁开始下棋,整整下了六十年?我说:‘不敢皇上……皇帝说:‘我清高宗想和你下盘棋。”稍有一点文史常识的人,看到这段如此缺乏古代文化常识的描写,恐怕都会笑掉大牙。“清高宗”,是乾隆皇帝死后的庙号,小说中的“我”,在乾隆皇帝在世时居然就称其为“清高宗”,他究竟有几个脑袋?更为荒唐的是,乾隆皇帝居然自己称“我清高宗”,这不等于乾隆皇帝自己说自己是死人?
在《斗鸡》中,阎连科写道:“姥爷斗鸡是从清末开始的,那时候,老姥爷三十几岁,姥爷十几岁。老姥爷已经有了近十年的斗鸡生涯,每逢斗鸡,都要将姥爷带去,让姥爷从中取乐。”姥爷说,姥爷和方老板开斗是在午时。其时,太阳移至正顶,显得十分温暖,黄光如温水一样流淌在庙会各处。梨园班子的压台戏紧锣密鼓,各类买卖生意正处火口,吆喝声此起彼伏,接连不断。尤其卖饭的到了这个时候,把平生力气都用在了嗓眼上:“该吃饭喽——包子啊——羊肉馅——”,“拉面拉面拉面——正宗的兰州拉面!”看到阎连科这样的描写,笔者不禁想到了如今那些劣质的古装剧。这些影视剧,虽然描写的是古代,其背景和说话却完全是现代的,甚至居然出现了电线杆和高速公路。阎连科不知道,在清末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兰州拉面这样一个人人皆知的饮食品牌,正宗的兰州拉面,是回族人马保子于1915年所始创的,其时已是中华民国。在《名妓李师师和她的后裔》中,初次相见,李师师向周邦彦弹了一曲《春江花月夜》。弹琴之时,周邦彦本是站着,待一曲过了,他不知什么时候坐了下来,双手扶着下颚,说:“师师,《春江花月夜》好像很长的。”事实上,在宋代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春江花月夜》这个名字的古曲,它的原名叫作《夕阳箫鼓》,最早记载于清代姚夑的《今乐考证》。生活在宋代的李师师,怎么会子虚乌有地弹出《春江花月夜》这支在当时根本就没有的古曲呢?
在阅读阎连科的小说时,我们总是看到,那种大而无当、夸张无度的比喻和屡屡出现的语法修辞错误。如《黄金洞》中的这样一段心理描写和叙述:“我现在就想杀了桃,只消上前一步,把桃用力一推,桃就掉到身边的沟里了。沟有南京到北京那么深,沟底有好几个偷偷垒的炼金炉,炉边上都有铁砧子。”想把桃杀了的,是小说中的二憨,对于一个长年生活在偏僻大山里的傻子来说,他的脑子里怎么知道南京到北京的距离有多远?如果那个山沟真的有南京到北京那么远,肉眼凡胎的二憨又是怎么看到溝底那些偷偷垒起的炼金炉和炉边上的铁砧子的?这种“神实主义”的写作方法说明,二憨长的根本就不是一双肉眼,而是高科技的千里眼智能摄像头。如此不合逻辑的比喻和描写,难道真的就是阎连科所说的“被真实掩盖的真实”?
【注释】
①阎连科:《发现小说》,181—182页,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②阎连科:《阎连科文论》,22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③李运抟:《现实主义的开放与原则——与阎连科商讨“神实主义”及其他》,载《南方文坛》2013年第4期。
④伊利莎白·鲍温:《小说家的技巧》,见《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19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⑤莫言、王尧:《莫言王尧对话录》,204页,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⑥林建法、乔阳主编:《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1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⑦伍尔夫:《论小说与小说家》,瞿世镜译,34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
⑧阎连科:《寻求超越主义的现实》(代后记),见《受活》,391页,2009年版。
⑨王蒙:《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见《蝴蝶为什么美丽——王蒙五十年创作精读》,郜元宝、王军君选编,71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唐小林,供职于深圳市大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