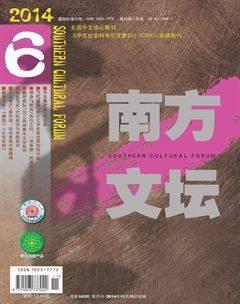《飘窗》:证见我们的纠结和不安

如果不是百岁以上的人瑞,年龄在今天很难成为耸人听闻的新闻点。但年过七旬的老作家刘心武在暌违二十年之后忽然拿出一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飘窗》,沉甸甸地撂在全国各地的书架上,怎么来说也是件出人意料之外的事——这些年来文坛新人辈出,不少老前辈也常常老夫聊发少年狂,但实在没有几个人能拿出像样的新东西,也许他们习惯了坐主席台的前排,习惯做评委,习惯拿着话筒,习惯面对摄像机谈锋正健,但年事不假力,创造不从心,有点模样的东西都杳如黄鹤,十年无一篇,想想也很残酷。《飘窗》的出现,同龄不同龄的,同行不同行的,都不能不咋舌,这刘老还真是铆足了劲,自顾拿着一杆长矛,直入时代深处。不过,吃惊归吃惊,但并没有几家媒体拿年龄来说事,闻风而动的采编们关注的是刘心武,是《飘窗》,是那个让人要正襟危坐的现实主义,是那个可以让大家东攀西援说些个话题的文本。然而,新闻报道的纷纷繁繁,借机自说自话的形形色色,但深入解读这个作品的并不多见,好比迎亲的爆竹热热烈烈地响过之后,露面的大多数是晃来晃去并非主角的宾客。这倒让人觉得有好好谈谈的必要,特别是把《飘窗》的种种奇特之处、创造之处、深入之处、幽隐之处,那些个大家浑然不觉的地方,一一开列出来,参透并评注这个为我们难以把握的时代。
其实,《飘窗》的面世,一开始就与众不同。细心的读者应该注意到,有文学国刊之称的《人民文学》杂志在2014年5月全文刊载《飘窗》,我這个老订户5月初就拿到了刊物,当时就有点惊异。《人民文学》创办以来,很少刊登长篇小说,是不是当年茅盾有意与巴金做了分工,大部头的长篇作品留给《收获》这样的大型文学期刊,自己专职做中短篇及散文诗歌这样的小本买卖?这次全文刊发一个长篇,占了上百个页码,是少见之少见;编者按语中,将《飘窗》直接定位在刘心武本人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钟鼓楼》之列,“地气丰沛、思力深沉,性情、感应和生趣都格外丰饶”,评价之高,褒扬之盛,也是令人惊奇。这些恐都不能简单看作后辈编辑对前辈老主编的尊崇,而只能说是杂志对作品的高度重视。在《人民文学》刚刚上市不到一个月,漓江出版社即隆重推出单行本,设计印制用料精良不说,而且版权页显示首印就是5万册,这对于一本纯文学又是现实主义的长篇小说来说,显然是一个很了不起的首印数。一刊一社,定位如此一致,配合如此准确,显然在“所见略同”之外,还有很好的业务默契。这恐怕是近十年来中国文坛独一无二的事了。
这些外表上的事,具有丰富的传媒意蕴,因与本文的主旨无多紧密关切,这里一笔带过。本文仍然相信文学批评最要紧的,就是面对作品深入作品,而不是边际研究。我要说这个作品不是《带灯》,不是《繁花》,不是《亲爱的生活》,更不是民情汇编《第七天》。《飘窗》的视野之广袤,意蕴之独出,风格之奇崛,结体之绵密,近年难觅二个,每一层都值得好好讨论,但本文无法面面俱到。这里仅谈谈这个作品提供给读者的在斑驳社会人情万象中的我们不能他见的特见,和观察毒辣究问深刻所别开的思想新面,此般花果很是值得一一欣赏。
“飘窗”当然是一个视角,不少评论人都特别在意刘心武的这个视角。其实我觉得这倒没有多大意思。好的作家总会选一个恰当的视角,比如莫言写《天堂蒜薹之歌》,选的是“蒜薹”,写《蛙》,选的是“计划生育”,刘震云写《我不是潘金莲》,选的是“截访”,阎连科写《炸裂志》选的是“炸裂村”,都是很不错的视角。只是在这视角之后,写出了哪些新东西,写得是否波澜起伏、惊心动魄,把作品与作品区别了开来。《飘窗》写的是什么呢?是否是环保或者蒜薹或者计划生育或者截访这样单纯的热门事件?不是。是不是乌坎这样的有点社会学探索价值的事件?也不是。《飘窗》写的是人,具有人性的人。从飘窗看的是市井人生,写的也是市井人生,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延伸的故事与意义,或者一个抽象的寓言,而是一个地方、一段日子、一些人群,他们的生活、生命、思想和情感的状态。因为他们交往,彼此牵连,甚至相互冲突,所以结成了社会,产生了阶层,分别了群体,所以作品在这里展开了社会的状态、阶层的状态、群体的状态,乃至人性的状态。他们都是活动在这个时代之中,在这个时代的国家、民族、政治、经济、道德、主义的框架下浮动,相互依傍,相互交融,相互冲突,相互阐释,既是针针线线,也是点点面面,文化的底子、制度的影子、人性的根子,纤毫尽见,所以作品也就成了时代的证见。
我以为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作品所证见的“状态”。在《飘窗》里,在红泥寺街的地盘上活跃五个群体,一个是底层的市井细民,一个是力争上游的知识群体,一个是吃香喝辣的土豪群体,一个是隐隐约约又无所不能的官僚群体,还有一个漂浮在这四个群体之间的小白领群体。如果作家在做完类别性的分别之后,再作特征性的归纳,那么阅读旨趣高大上的读者恐怕就难以满意,以为过于简陋,他们喜欢内容繁复气势恢宏的大手笔。一个老到的作家,更是时代的思想者,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急剧转型的时代,他有着太多的发现、感受和沉思,他固然年高,但那只增添他的阅历,他依然头脑清晰,视力敏锐,超越常人,他发现所有的蠢动、渗透和变异,善于在类别之中,发现复杂,表达复杂,从而写出类别之中的类外,类外之中的类别。比如市井细民阶层,那些在转型时代社会与经济地位起伏跌宕的底层百姓,那些要被人道主义作家给予饱满丰富同情的“被侮辱与损害者”,在这里固然寄予了作家亲切的理解,但同样演绎了复杂多元的故事,呈现出斑驳的状态,而时代变化发展的曲致尽在其中。歌厅里的糖姐和薇阿,麻爷身边的庞奇和二锋,开面馆的二磙子和卖水果的顺顺夫妇,洗车的何司令和送啤酒的赵聪发,开武馆的庞奇叔叔与开中巴的唐广立,都是当今的底层人,但他们的生态如此不同,精神的质地更不符合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规律。除了“自食其力”这个勉强能够概括他们的共同境遇的词汇之外,我们还能找到他们有多少根本性的一致?糖姐和薇阿做的是涉黄娱乐生意,却有着不同的趣味和算盘,你能想到一个卑微的歌厅准妈咪满口唐诗,“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而且居然还是一个文娱行业的超级粉丝?做了黑社会老大的保镖的庞奇,来自被拆迁的乡野,朴厚可教,想的竟然是人生的拯救这样的启蒙话题,可同样来自乡村的雷二锋却盼望着接替庞奇的位置成为老大的贴身保镖。顺顺夫妇的勤劳和努力也掺和了时代的罂粟,为了绑住“铁人”,他们四处寻找机缘,胶结机缘,奉上他们微薄的收成。那个已经沦为城市贫民的何司令,曾是呼风唤雨的造反派,而此刻他怀揣的不是发家的美梦,也不是阿Q式的昔日辉煌,却是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他盼望的是“革命”重来,是像他那样的人重新登上历史的舞台,主宰社会。如何体认这种底层的意识形态,显然是一个全新的政治哲学命题,它不仅跨越了群体,而且交叉了群体,颠覆了我们一直拥有的学科常识和纯色的人性记忆。
《飘窗》中知识群体的状态虽然没有这样斑驳,但同样特别,富有高度的独见,你若是与《飘窗》擦肩而过,你就错失了这片诡奇的风景。看过《钟鼓楼》《四牌楼》的人,都会承认在当代作家中写市井人生的,无出刘心武之右,但写知识群体的,却历来不乏其人,佳作丰饶,钱钟书杨绛夫妇可谓造诣深厚,建树尤多。但这次《飘窗》问世,我可以大胆地断言:在刻写“今日”知识群体方面,目前恐也难有堪与《飘窗》比肩之作,此后若干年也难以产生更新更为出色的作品。这样说,包括三种意思。一是《飘窗》写的知识人,是今日的知识人,不能后退十年,大概也不能前进十年,就是此时此地的知识人。何谓此时此地?就是在经济出现大跨越大发展的十多年的中国大陆,也就是进入21世纪之后的中国。不是新时期,也不是1990年代。这十多年,西方打够了中东,就碰上了金融危机,中国呢,全国上下致力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抗住了危机,经济大步快跑,跃居到世界第二,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站起来了,万邦来朝,财气十足的中国游客漂洋过海,四处观光购物,那信用卡刷刷地大方劲儿,叫比尔盖茨都自愧弗如,洋鬼子对中国人露出了殷勤的笑脸,假洋鬼子自然掉头还乡,那些以西方为视角的知识人尼罗之流和管理人林倍谦之流都放弃了立场,转变了视角,开始礼赞开始膜拜这块曾经被他们抛弃、鄙夷的热土,东归与登陆是最新的时潮。同样因为经济的发展,权力掌握着巨大的资源和财富,所以一些知识人如夏家骏之流对于权力、位置的热心、追逐也令人瞠目结舌,若说他鲜廉寡耻那过于笼统过于道德评判,最好不用,在《飘窗》这里,最需要注意的是攀缘技术的表演。只能用“技术”来定位他们交接权要、献媚取宠固位的努力,从他们掌握的“技术”水准,来推断时代的幽默性和人性的弯度。覃教授的出现,也是一大创举,虽然现实中覃教授这类知识人走街串巷人前人后,早已成为“时代特色”,但他们不是“传统”的名利场中人物,他们饱学的是自由主义理论学说,口中滔滔而来的也不是对权力的迎奉,相反却是批判,无情的批判,他们抨击最厉害的是“专制”,他们以此成为“时代良心”,成为“意见领袖”,成为数百万粉丝拥趸的“公知”,然而他们却不能容忍不同的意见,他们以“绝对性”笼盖、管制着那些纯洁的“羔羊”,他们同样出入会所,交结权要,谈笑风生,不同的是他们盘踞在价值高地,口若悬河,宛然“另类权威”领袖群伦,从而获得他们优越的存在,至于青年需要借鉴的探索的热情、正确的知识和对于问题的发现、宽容的气度,他们却一筹莫展、无可提供。在这些知识人的对面,站着(不是坐着)一个彷徨的清瘦的退休多年的高级工程师薛去疾。他不是作家,却有着作家敏感的心,他怀揣着传统知识人的正直和良知,但他被撂在“死角”。他没有惊天地泣鬼神的宏大理想,也没有咸鱼翻身的挣扎,既然在江湖,就置身于江湖,像市井细民一样生活,一样五谷杂粮,一样悲欢沉浮,他有度人之心,悬壶却不济世,然而洁身自好也颇为乏力,一再遭受命运的戏谑,从飘窗内的观者遽变为被观者。“遭受命运的戏谑”,可谓是这类知识人三十年命运的标签。
麻爷的出现,是当代中国文学人物画廊中的一个异数。这类大体上可以用土豪来标示的人物,正是中国经济社会在发展中必然出现的一种社会性产物。我不想过多地谈论土豪们财富累计的途径、方法、过程和生活的糜烂程度,这种大同小异的东西早就构成了当代批评家们关于财富与财富人的常识,我想说说的是麻爷的焦慮和不安。麻爷既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之一,没有社会财富的巨大丰富,就不会出现这么一批敛聚财富的人物,虽然他只是一个中间人、代理人,但他还是一个合伙人、共谋者。他们钻进社会的肌体,疯狂吸食健康的血液。他们像蚂蟥一样,皮肤黝黑,充满着弹性。他们最大的不安来源于财富本身的非法性,所以他们出入前呼后拥,打手成群,甚至连替身都随时预备着;也因为这种非法性的敛聚,手段之黑,藏匿之深,所以他们得不到真正的社会尊重,他们醉生梦死,如同沉入地底的幽灵渴望回到地面,甚至变态到希望看到有尊严的人匍匐在他们面前,他们以此来平衡内心的躁动不安。这正是当今中西人物在财富的感受与处置上迥乎不同的地方。在麻爷的周围还活跃着一批往来频繁的中下层官员、公务员,他们的特征一个是“狠”,一个是“敛”;在他们之上还有各种各样的大咖,A咖,B咖,这些人物在作品中隐隐约约,面孔模糊,远远不像《红楼梦》中的北静王那般玉树临风,形容清晰,他们诡异的存在和神秘的行踪,构成了时代的坚硬墙角。
小白领大概是无法划到上面任何一个阶层中去,他们的社会角色、工作、收入乃至他们的观念、趣味和生活的方式都非常独立,不能被简单地归纳收编。他们没有公权,自然不能进入官僚群体;虽然受到很好的教育训练,但他们不是以知识为生存的手段和主要的志业,不符合韦伯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所以不是知识人;他们在各种各样的写字楼上班、下班,挣的是薪水而不是利润,虽然幻想富贵但从来没有高高在上的收入,但也不至于出卖苦力,日晒雨淋,所以他们既不是土豪,也不是底层百姓。他们关心什么?想象什么?大概找不到一个共同的圆圈。冯努努、钟力力、海芬,还有薛去疾的儿子薛恳,都是各式各样的小白领。他们的状态很不统一,有的关注工作,因为需要工作,有的关注爱情,因为需要爱情,有的关注性,因为需要性,有的关注财富,因为需要累积,他们还在过程之中。又因为是白领,所以他们与上下左右都有着各种各样的关联,他们具备一定的潜质和愿望,所以今日是白领,将来就会走进不同的阶层中去,所以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相对独立的群体性,也看到了以后的过渡性,就像海芬若干年之后未必不是一个女将军,钟力力未必不是一个归来的土豪,而薛恳呢,也许像他的父亲一样,重新沦落为市井细民,漂泊人间。
我们很难推测返回乡村的访民和都会小白领的未来状态,因为在一个变动不居的时代,过多的预测往往都会显得荒诞不经。也似乎不用假设那些土豪与小咖大咖们的前途,在全面反腐的今天,这种假设虽然可以成为影视文学的题材,但难以成为很有深度的思想命题。我以为最值得关心的是,这种种杂色为何能成为一个浑然的整体,难道仅仅是作家天才的构思?无论人们来自何方,身处何处,怀有何种理想或者操守,或者毫无理想,毫无操守,但不能不面对“财富”。创造也好,猎取也好,承继也好,抢夺也好,善用也好,糟蹋也好,群体或者个体,机构或者社会,无不因为“财富”,产生无数的规划、计划、任务、制度、方案、沟通、协商、争议、争吵、诉讼、获得、交换、使用、存储、消费、转移、收藏、忧虑、期盼、欢喜、失落、痛苦……《飘窗》的好,就在于发现了这种种蠢动、种种形象,发现了它们的位移、它们的能量、它们的地理布局和群体布局,它们的交往、冲突、流通和转折,而且发现了它们的共同根源。我记得1980年代刘心武主政《人民文学》的时候,有一期的编者话的标题是“让我们更自由地煽动文学的翅膀”,我这里借用一下“煽动”这个词,把它与财富连接起来,组成对这个根源的简单判断——“被财富煽动的欲望”,它流贯在每一个阶层、每一个群体、每一道程序、每一个设计、每一个行动、每一个梦想的血脉之中,它改变并书写着社会的状况、人生的状况乃至人性的状况、文化的状况,从而建构了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意识形态。在这个真正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下,种种的纠结和不安便如烟四起,弥漫在社会和时代的上空,成为我们生存的标志,它不仅显示了在经济社会大发展的同时加快体制改革的迫切性,而且显示了从更为宽广深远的文化视野和健康恢宏的人类精神层面来展开社会文化调整与公众心灵建设的重要性。
读完《飘窗》,掩上书卷,进入眼帘的是这封面上的图案,像窗子也像车轮,还像分割的明暗交错的社会与人生,恰如刘心武带给我们的生活与世界,一种久违的心灵震动仿佛从远古而来。文学很久没有这样激动我的感受,引起我的种种思绪与联想。这或者只是一个个人的体验?那年,高密的说书人莫言捧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杯,让举国欢腾,让中华自信,让要员驰电嘉勉,让书商大发其财,但那仍然只与奖有关,与人有关,与作品没有多大干系。谁知道莫言写了些什么呢!谁述说过莫言的作品带给他的惊惶和慨叹?我搜寻了2012以后的关于莫言的文字,殊少对他的作品的认真解读。相比之下,二十多年前,在莫言还是个愣头青的时候,他的《红高粱》红遍了天,大江南北争看红高粱,争说莫家郎!再往前,是刘心武,是《班主任》,是救救孩子的呼声,响遍白山黑水长城内外,而今呢?只有奖呀奖的,钱呀钱的!这真是天大的笑话!这个笑话见证了文学与社会隔膜既久,见证了精神与人类渐行渐远。而今,《飘窗》问世了,《飘窗》以其特立的锋锐,进入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内部,精神的内部,照见了我们的仓促、纠结和不安,可有多少人能与它精神相遇?在我的眼前,更多苍白的身影蜷缩在潮湿的蜗居里,在那无边的虚拟的世界中,或者在嘈杂的百货超市、摩肩接踵的风景名区,消费着似水流年。我们忘却了飘窗外面的世界,忘却了那些带给我们灵魂惊悚与战栗的文字和声音,我们的明天依然会爬满蜗牛与蚯蚓。
2014年6月21日
(邱仪,上海财经大学外语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