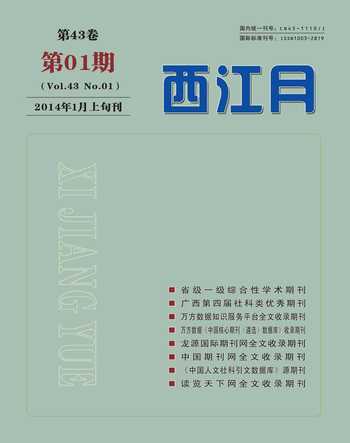继承发扬戏曲的讽刺传统
郭鑫
【摘 要】中国戏曲有着深远的讽刺传统,可以上溯到先秦的诗歌及古优人的活动。后世的戏曲,吸引了这种传统并发扬之。自唐宋以来,历代艺术家们创作无数讽刺戏,在戏曲史上占据着一席之地,为我们今天学习继承戏曲的讽刺传统,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在社会主义的今天,讽刺戏同样具有不可低估的效用。
【关键词】戏曲;讽刺;发扬;传统
中国戏曲有着深远的讽刺传统,可以上溯到先秦的诗歌及古优人的活动。后世的戏曲,吸引了这种传统并发扬之。自唐宋以来,历代艺术家们创作无数讽刺戏,在戏曲史上占据着一席之地,为我们今天学习继承戏曲的讽刺传统,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在社会主义的今天,讽刺戏同样具有不可低估的效用。
孔子曾经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孔子从诗歌的创作实践中,总结了兴、观、群、怨的理论,指出了讽刺是先秦诗歌的重要社会作用之一。先秦、两汉的优人的讽刺传统,在戏曲中得到了良好的继承。优人活动启于先秦,历代不衰,至唐而正式确立起滑稽讽刺的喜剧形式,至宋而大盛。唐代的参军戏,初有两人演出,以滑稽讽刺为主戏曲的角色行当最初由参军戏正式确立起来,参军,苍古,一正一副,一捧一逗,都属于滑稽性质,也就是说,中国戏最早出现的角色是“丑”。近代戏班中仍有重丑角之风,是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的,至于说重丑角之风是因为某位帝王曾扮过丑的说法,我以为都是附会之词。宋杂剧从唐参军戏脱胎出来,代表着讽刺戏发展的一个更高的水平,从现存宋杂剧名目,可以看出滑稽讽刺剧目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宋杂剧共有五个角色,其中三个是有滑稽讽刺性质的,即副净、副末、引戏,占全部角色的五分之三。宋杂剧演出形式分为艳段、正杂剧、有时加演杂拌。据吴自牧《梦梁录》卷二十三《妓乐》,可以知道正杂剧“大抵全以故事,务在滑稽、唱词。应对通编。此本是鉴戒,又隐喻鉴净。”就连杂扮,也多以滑稽、讽刺、戏虐为能事。从现存名目,角色体质以及演出形式,都足以证明宋杂剧是以滑稽讽刺为主的戏剧。
元杂剧已是一种十分完备的戏剧样式了,它不复是前代戏剧那样以滑稽、讽刺,调侃为主,以资笑乐,它已具备了首尾完整的故事,比较丰满厚实的人物。当然,现存近160种元人杂剧中,似无整体意义上的讽刺戏。但是元杂剧却不曾丢弃宋杂剧、全院本所具有的滑稽讽刺传统。元杂剧之继承讽刺传统,采取了两种形式:(1)把院本(即宋杂剧)作为有机部分直接插入元杂剧中演出,(2)把滑稽讽刺付之于剧中人物。元杂剧形成之后,古老的院本并未消亡,仍流行着,有时二者同台演出。元杂剧中的“衙内”泛指蒙古贵族,什么“杨衙内”、“白衙内”屡屡出现,他们“嫌官小不做”、“嫌马瘦不骑”,打死了人“如同捏杀个苍蝇相似”。这种素描似的讽刺在元杂剧中极为常见。元杂剧并不现有对这些蒙古贵族的讽刺,也把讽刺的锋芒指向其他多种人物。有善意的讽刺,也有恶意的冷嘲。同是讽刺守财奴,《看钱奴买冤家债主》和《崔府君断冤家债主》却不同,讽刺形象各臻其妙,开卷展读,令人捧腹。
经过宋、元两代的创作实践,讽刺戏积累了经验,到了明代,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无论是短小的杂剧还是长篇巨制的传奇,都产生了具有独立意义的讽刺戏,即以讽刺形象作为全剧主人公的戏。比较出色的讽刺杂剧如王九思的《中山狼》、徐渭的《歌代啸》、《狂鼓吏渔阳三弄》、竹痴居士的《齐东绝倒》、徐复祚的《一文钱》、茅维的《闹门神》等等,都各具特点,一般来说都很短小,可以目之为匕首和飞丸。就说徐渭的《狂鼔吏》吧,它属于讽刺戏中骂剧的一种,演三国时的祢衡裸体横眉,掉板掀槌,翻古调作渔阳三弄,借狂发愤,大骂曹丞相的故事。而茅维的《闹门神》借幽冥中神鬼的形象,画世间官场中那些丑恶的嘴脸,与《狂鼓吏》有异曲同工之妙。
明清传奇同样继承了古来的讽刺传统,而呈现出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单出讽刺戏,另一种情形是全本讽刺戏。明清传奇有这样一个特点,在动辄几十出的大戏中,每一出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是可以单独演出的。有些全本传奇非属讽刺戏,但其中个别出目是讽刺戏。这些出目从原本中脱离出来,经过艺术家的再创造,成为一个独立的讽刺短戏而盛行于舞台。这些讽刺短剧广为人熟知,而其祖本却鲜为人晓,正如昆曲的名剧《狗洞》,谁不熟悉呢?可是了解阮大铖《燕子笺》传奇的恐怕就不太多了。
除了以零出形式出现的讽刺戏外,整本的讽刺大戏,当首推万历年间问世的孙仁儒所撰《东郭记》。《东郭记》出现在明代晚积累,也是时代的产物。万历年间正值明王朝由盛至衰的时期,也临近封建王朝的末期,举国动乱。虽有万历初年政治家张居正等人励精图治,却亦无法挽救行将灭亡的明王朝。这位首辅死后,反动势力立刻复辟,变本加厉地奢侈腐化起来。贪污行贿成风,终日穷耳目之所好,极声色之所欲,二十几年后,便断送了大明朝。另一方面,从明中叶起,资本主义在我国南方萌芽,新的思想随之而纷起,思想界异乎寻常地活跃。以李贽为首的地主阶级进步思想家,起来与传统的封建道德进行斗争,抨击时弊,倡导先进的思想。
清代花部兴起之后,出现了一些讽刺短剧,像《借靴》、《张古董借妻》、《打面缸》等都很出色。由于清代文网严密,花部中的讽刺戏得以保存的并不太多。到了近代地方戏时期,讽刺戏犹如雨后春笋,数目之多,举不胜举。顺手拈来如川剧的《借亲配》、《骂相》,湖南常德高腔的《祭头巾》,广东粤剧的《骂城隍》,云南滇剧的《九流鬧馆》,小戏曲《界树下》等等,都可称为讽刺的佳品。
以上拉杂所述,可以看出中国讽刺戏是渊远流长,历代不衰。任何一部讽刺戏,总在不同程度上站在正义一面、真理一面、人民一面。其矛头所向,多为反动的、丑恶的事物。都或多或少地代表了人民的利益。规律告诉我们,广大人民的喜爱是艺术生命之所在,焚是焚不完的,禁也是禁不住的。
从孔子提出诗可以兴、观、群、怨,肯定了诗歌的讽刺、谏诤作用,到太史公为优人立传,从而在理论与实践中肯定了讽刺在文学艺术中的地位。这一点,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元杨维桢《朱明优戏序》明确地指出戏剧讽刺有回天倒日之力,评价可谓高矣!但也并非过誉之词。明代思想家李贽干脆把孔子论诗的言论拿到戏曲上来,说:“孰谓传奇不可以兴,不可以观、不可以群、不可以怨乎!”明言戏曲具有兴、观、群、怨的社会功能。当然,无论是孔子,还是杨维桢和李贽,他们在论述戏曲的讽刺功效时,着眼点主要都放在对帝王的谏诤上面。这固然是讽刺戏的功能之一,但并非仅此一点。大多数古典戏曲的讽刺戏,其矛头所向,已遍及社会上一切丑恶的事物。
社会主义时期的讽刺戏和一切新时代的文学艺术一样,不是平地起楼台,不能割断它与传统的联系。要发展新的讽刺戏,必须研究传统、继承传统。讽刺戏作家必须立足于现实生活、立足于人民之中,用共产主义世界观去观察、去分析,把那些阻碍社会主义事业,危害四化建设的事物,艺术地再现于舞台。其中应当有无情的鞭挞,但更多的恐怕还是善意的讽刺,是“为了人类愉快地和自己的过去诀别。”所以,社会主义时期的讽刺戏作家,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更重要的是研究现状,不能生搬硬套前人的手法,尤其不能因袭前人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