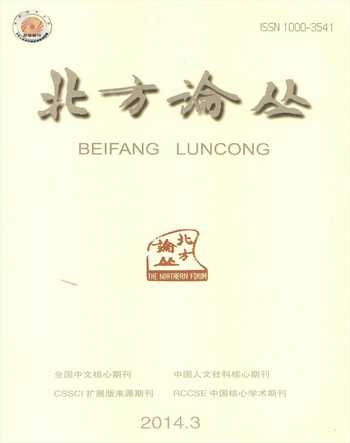“个人化写作”与新时期先锋诗歌批评
崔修建
[摘要]“个人化写作”是一个充满张力的命名,也是新时期先锋诗歌批评中不可忽略一个十分重要的关键词,通过对具体历史文化语境中的“个人化写作”策略的选择和演变流程的梳理,对“个人化写作”的欲望化书写的深刻批判、对“个人化写作”复杂性和差异性的细致剖析,更为深入地解读了新时期以来的先锋诗歌中“个人化写作”的丰富内涵和诗学意义,也由此进一步地探索了先锋诗歌创作与批评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个人化写作”;先锋诗歌;欲望化书写;差异性
[中图分类号]I207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14)03-0029-05
伴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伴随着商业文化和大众文化无孔不入的肆意侵袭和挤压,传统的精英写作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颠覆和解构,呈现个人立场、突出个人体验、强调个人品性的“个人化写作”,日渐成为先锋诗歌写作的主潮。作为诗人在不同语境下处理个人与世界、个人与写作关系的一种写作策略,“个人化写作”至今仍在不断修正和发展中,其不断“扩容”和“增殖”的内涵和外延,在许多诗人和批评家那里仍存在很大争议,其变动不居的演变历程中存在,诸如清醒与迷失、反抗与沉沦、独立与互仿等矛盾和悖论,但其一路前行的先锋姿态,还是赢得了批评家们的广泛关注和热情批判,并已成为新时期以来先锋诗歌批评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词。
一、“个人化写作”策略选择的深度考量
早期有关“朦胧诗”的论争,批评家们便已注意到:弥漫在“朦胧诗”中的怀疑和反叛背后正是诗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张扬,诗人们对个人命运的思考,对“我”的尊重、召唤和持守, 显然是对过往的意识形态指令性写作的有意疏离,是对共名的“集体化书写”的强力纠偏,借助于对“个人”的尊重和关怀,拆解专制对人及人性的压抑,使诗人不拘的心灵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自由翱翔。
外在不乏个人独立姿态的“朦胧诗”,其内里依然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着古典文化传统和话语范式,仍坚守着深厚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精英思想,“朦胧诗”大写的“我”正是时代大众的启蒙者和代言人,朦胧诗人虽然从个人体验切入,但最终的指向仍未能超出个人的公共意义,只不过是将诸如个性、自由、民主等现代意识渗入诗歌写作,提供了一种现代价值选择,其启蒙的定位和取向不容置疑。一些看似“个人化”的言说,其实还有着明显的集体启蒙特点,个人的时代代言人的身份依然明显。正如罗振亚所言:“它将矛头对准了前代诗歌集权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可‘修正的结果不过是把政治意识形态转换成了人性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公众性、社会性、启蒙性的‘言志主旨倾向,表明它个人的言说还处于‘集体无意识的权力话语控制之下,个人只是一代人的类思想情感代言者。”[1]在谢冕、王光明、陈仲义等评论家的文章中对此多有论述。譬如,有论者在剖析“朦胧诗”与“第三代”诗的差异时,便认为:“朦胧诗”在主题上公众性、社会性、启蒙性与在艺术上的个人性、边缘化倾向之间很难产生事实上的和谐与统一。“表面上独立的个人无法将类型化的经验转化为个体生命的深切体验,无法摆脱种种潜在的或显在的束缚,真正从‘个人(经验)到‘个人(阅读期待)地自由言说”[2]。因为“朦胧诗”时期权力话语系统仍然处于主导地位,“个人话语场”尚未建立起来,自然更多的只是个人精神高扬的“集体性写作”。
对“朦胧诗”更为强烈反叛和“断裂”的“第三代”诗,不满于已成主流诗潮的“集体书写”的裹挟和掌控,他们采取更为激进的方式,继续对“权力话语”进行猛烈的颠覆。 诗人兼批评家沈天鸿在20世纪80年代就敏锐地洞悉了“朦胧诗”后诗人“个人化写作”倾向:“从诗人自己即个人出发,个人经历遭遇便是即时场景而无须布置,通过个人的经验或直观感受暗示整个人类的境况。”他从现代诗写作的特质这一视角,指认“第三代”诗坚持:“强烈地反对‘非个人化的现代主义诗学准则。他们要求诗歌更加亲近更加直接地涉及个人。他们或是使诗成为产生于人类黑暗处——对诗人自身和内心超出理性的意识探索所发现的形象(如翟永明等人的诗),或是体现个人对外部世界的发现及个人经历这些发现时对其做出的反应(如韩东于坚以及阿吾的‘反诗等)。”[3]显然,类似这样的建立在对同一时代诗人及文本细致考察基础上的批评,不仅破解了“朦胧诗”的浪漫主义乌托邦崩溃的秘密,而且还引发了对后现代诗潮中的“个人化写作”的深入思考。
正如一些批评家指认的那样——“第三代”诗反抗“朦胧诗”的策略,是更加偏激地强调写作的个人性,注重个人的感觉和体验,自觉地消解精英意识和历史责任,突出生命意识、神话写作、口语化写作等,展开多向度的“对抗”和“断裂”,再加上大量采用现代主义诗歌表现技巧,这些凸显个性的先锋写作都在一定程度上松动和解构了意识形态写作,增加了写作的多种可能性,显示出与叛逆、否定、自我拯救等密切相关的“现代性”,而“突破”和“超越”方式的多样性,也预示了“个人化写作”的巨大发展空间。
而对于这一时期的许多诗人回归日常生活,采取反讽和自嘲的方式,将自己降到一个最低的位置,甘愿做一个平凡,甚至平庸的人和生活、读者平等对话的转向。批评界普遍认为,这种写作策略的选择,尽管主要是出于消解传统和精英意识的考虑,出于寻找反叛、突围路径的考虑,但在客观实践中确实造成了“自我的高度膨胀”,大大激发了个人化实验和探索的热情,拓宽了诗歌写作的疆域,为后来更为沉潜的“个人化写作”做好了铺垫。
需要注意的是,随着现代和后现代思潮泥沙俱下的猛烈冲击,共同的精神空间被打碎了,原有的价值体系被打碎了,在“去中心”的年代,诗人们强烈希望发出个人的声音,他们随心所欲地营构自己的话语系统,揭掉习惯性“意义”对个人灵魂的掩蔽,充分显露世界的本真面目,但逃避知识、思想、意义和超越逻辑、理性、语法等,过度凸显主体精神和迷恋个人自由言说的“第三代”诗,在狂热的“叛逆”中,有时不免又走入“不及物”写作的误区。
正如某些批评家分析的那样——“第三代”诗写作是策略性的、过渡性的、实验性的写作,无论是“非非”、“莽汉”,还是“他们”等,声势浩大的流派,虽然涌现了一些优秀诗人,奉献了一些优秀文本,但大多不过是缘于影响焦虑而急功近利的集团造势的运动式写作,以“诗群”面目出现的“个人生命体验”不免要对“个人”造成新的束缚,反而在喧嚣地叫喊“张扬自我”的混乱之中陷入了明显的“类”写作的泥淖。扫描一下1986年的“现代诗歌群体大展”,打量一下那些宣言林立、旗帜招展的所谓流派,就能够看到在那些鼓噪的个人自由言说下遮掩的,正是另一种圭臬退场后盲动的“集体狂欢”,一些貌似离经叛道的“个人化写作”不过是其孱弱心灵的一种掩饰而已 。
而到了启蒙失落、代言式微、激情退却的20世纪90年代,随着大众文化的不断浸淫,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得以确立和流布,“个人化写作”愈演愈烈,也自然地引起诗人和批评者们的高度关注。
“个人化写作”何以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真正地确立起来,很多批评家从先锋诗歌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的变迁着眼,将“个人化写作”视为既是新诗自身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必然选择,也是诗人从独立的个人立场出发,以不可通约的个人体验对社会现实的自由言说,是先锋诗歌在特定的语境中的自然转型。的确,“个人化写作”把一种独立的写作精神与个人立场内化为写作品格,外化为一种独立的写作姿态,致力于个人化经验的发掘,有效地解构了中心话语,在寻找和创造的多样、差异状态中建构了自己的诗歌伦理。
从“朦胧诗”到“第三代”诗,再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先锋诗歌,有关“个人化写作”的批评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过程,通过对“个人化写作”生成、演变历程的考察和梳理,批评者充分论证了“个人化写作”在不同语境中的转型和分化,对至今仍在嬗变中的“个人化写作”的选择策略,进行了多方面的梳理和阐释,进而从整体上把握了“个人化写作”的先锋指向及演变规律。
二、“个人化写作”中欲望化书写之批判
“个人化写作”中存在大量的感官描写、欲望宣泄和语言游戏等,它们挑战道德、伦理和日常规范的肆无忌惮和无所不为,同其他文学样式中的欲望化书写一道形成了大胆嘲弄高雅、非礼精英、挑逗严肃的“言语狂欢”。对此,有诗评家认为,这种“安于庸俗,张扬平凡,满足性感”的写作,实际上是从传统/现代、大众/精英、解构/建构二元对立的逻辑思维出发,对欲望化书写生成和展开的背景、依据和现实价值的充分肯定,这也成为诸多诗批评家的一种共识。
实际上,从20世纪80年代“朦胧诗”对真诚、纯洁、尊重、坚定等美好情愫的热切呼唤中,机敏的批评家就已看到诗人们流露其间的对人性压抑、尊严受辱、个性丧失的不满和反抗,只是鉴于传统诗学观念和表达方式的深重影响,朦胧诗人表达内心真实欲望的方式还十分内敛、含蓄和隐蔽,个人欲望的强化和张扬要等到“第三代”诗潮的爆发。所以,关于早期的“朦胧诗”批评,更多关注其人性意识的觉醒和启蒙精神、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弘扬,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对“朦胧诗”和“第三代”诗进行深层反思时,批评家蓦然发觉:“毋庸讳言,现代社会已经形成了一套压抑身体的完整机制,欲望的禁锢或者转移是这一套机制的首要主题。”[4](p216)正是此前多年高度的人性禁锢和压抑,才有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社会文化语境变化后迅疾而来的欲望大释放、大泛滥,并在商业文化和消费文化推波助澜下愈演愈烈。
欲望化书写并非洪水猛兽,它不过是以身体来反抗现实的一种方式,并非像有的批评者草率认定的只是简单地“用身体思考”,它依然是较为认真地用灵魂在进行思考,即使是那些一再强调肉身感觉的写作,其实并非拒绝灵魂的参与,只是诗人们以对身体的特别关注替代了对灵魂深彻的触及和探掘,企图以离经叛道的肉体快感,肆无忌惮地打破某些固有的禁忌和既定的秩序。在谢有顺的《文学身体学》中,我们看到批评家对灵魂和身体同一的指认,已经洞穿了精英表达中的“灵魂超越身体”和粗鄙的“身体写作”中“身体逸出灵魂”的本质差异,但遗憾的是,批评家并没有对“下半身写作”极端的反抗方式所具有的诗学建构意义予以情绪化的轻率否定。显然,批评家也已认识到,这种肉身欲望的呈现,是对传统道德不屑或挑战,是对泯灭感性的集体情绪的反抗,在对“欲望”的拥抱中达到对商业/市场权力话语的抵制。同时,诗评家们细致地观察到诸多欲望化写作有着自足的逻辑、语言、意象和情绪,它们经常首先或同时对自我进行戏谑、丑化、矮化,进而达成对权威、神圣、严肃、道德等所负荷的某些道貌岸然的传统要义进行无情的讽刺,对学院、知识分子和某些所谓精英们的虚伪、自命清高等进行痛快淋漓的“打击”,在率性的话语狂欢中直刺某些言不由衷或言不及意的灵魂深处。显然,欲望化书写不仅旨在反抗“欲望禁锢”,更是为了颠覆“欲望”专制,而在感性化日嚣尘上的大众文化时代,对欲望化写作的关注和批判,显然不失为一条深入探究“个人化写作”的重要途径,因为这二者往往是纠缠在一起的,很难简单地将它们割裂开来。
在对欲望化写作分析时,诸多批评者看到某些因世俗化侵袭而产生的对精英文化的不屑和戏弄,外在的嬉皮笑脸掩不住的是内在的严肃认真,在表面的轻松和无所谓中,有时正隐藏着很难察觉的沉重和刻意追求。也就是说,先锋诗歌中的欲望化书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诗人以世俗价值抵制和颠覆精英价值的策略和方式,是“个人化写作”推进的一个重要取向。只是欲望化书写在冲破现实政治和物欲文化的压制,肆意地解构“宏大叙事”的同时,有时又不免陷入欲望沉沦之中。许多批评家和读者对“下半身写作”诟病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其过度的欲望书写中消减了欲望反抗的锋芒,而变成了赤裸裸的欲望展览和欣赏,导致“个人化写作”呈现出一种深刻的悖论,姿态上的个人激进反抗与欲望化书写中的自我沉沦,对欲望化过分的追求,反而消解了反抗的力度。
因而许多批评家认为,警惕欲望化书写是拒绝与欲望时代合谋,因为,欲望原始的反抗意义最终为欲望的沉沦和精神的自虐所代替,过度地沉湎于个人情欲的宣泄,对社会公共领域和人类命运的漠视与逃避,只能使诗人成为现实的“零余者”,成为个人命运的疏离者。而这时的“个人化写作”不过是个人欲望的窥视和自恋性的抚摸,是“私人性”的写作。
“个人化写作”在走向“个人化”反抗的途中,唯有告别欲望展示,从欲望之所脱身,进行自我超越,书写个人独立精神、美好生命体验和心灵悸动,挖掘和表现潜藏在现实景象背后的生活本质,先锋诗歌的欲望化书写才能真正发挥出其特有的反抗作用。
三、“个人化写作”差异性的多重审视
一路颠簸的“个人化写作”,不仅打碎了启蒙、崇高、神圣等浪漫主义的乌托邦, 还对大众文化背景下诗歌和诗人的尴尬、无奈进行了戏谑,其在不同时期对写作策略、路径、技术等探索,为先锋诗歌的繁荣开辟了极为广阔前景,但由于复杂、多元的艺术取向和纷繁、嘈杂的个人化言说方式,其对固有秩序、标准、范式、价值和话语体系等,进行了全面的清洗、改造和颠覆,许多公共意义空间被觉醒的个人意义空间搅得支离破碎,曾经为传统习惯认可的意义结构系统,也大多破裂为失位失名的、需要重新审视和指认的零散的意义碎片,价值判断的个人性、模糊性、随机性也随之呈现出来。因而,对于“个人化写作”的辨析和意义碎片的找寻、打捞和清理,自然就成了先锋诗歌批评重要而艰难的任务。纵观批评者们对“个人化写作”无限可能性阐释的多样性、矛盾性和暂时性,正好印证了“个人化写作”丰富的差异性。
“个人化写作”作为一个不断演变的开放性的概念,从它被命名之日起,诗人和批评家们便对其进行了多方面的界定和阐释,那些多元互补的丰富论述,不仅澄清了许多指称不一的理解上的歧义和混乱,还揭示了它所蕴含的诸多诗学意义。譬如,早期的关于“个人化写作”的批评,许多诗人和批评家常常将“个性写作”、“私人写作”等,混同于“个人化写作”。其实,在“朦胧诗”乃至此前的一些“地下诗歌”写作中,都不乏突出主体精神的“个性写作”,北岛、舒婷、顾城等诗人的作品,都显现出很个人性的主题、意象、意境和修辞风格,只是这种彰显“个人性”的写作倾向,并未脱离当时的意识形态话语系统的笼罩,尚未建立起自足的个人化言说的空间,因而还只是在“大我”的阴影中有限的“个性写作”;而“私人写作”是一种过于自恋而自我陶醉的自语性的言说,是只有“个人”而没有或鲜有其他指涉的自闭性言说,因过分的自顾而缺失了必要的对外敞开,仅仅满足于对个人体验和经验的沉溺性把玩,结果陷入了自我封闭的狭窄天地中,成为纯粹的“个人的(或曰自己的)”写作。而且真正的“个人化写作”应该是诗人“不再把自己定位于直接表达时代共同想象的关系上、不再直接为主导文化编码,而是传递个人的表达、呈现历史在个人身上的‘反应物,同时力求对历史加以‘个人化的分析、思考,以及超越、纠正”(王昌忠语)。这样,借助于对“个人化写作”在特定语境中的不同表现形态的考察,指认出其变动不居的主要特征,使得批评家对其丰富的内涵的界定和诠释更加准确到位。
也有批评家侧重于对“个人化写作”对抗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而突出个体感受和想象特征的考察。虽然这种将“个人化写作”与代表主流话语或官方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对举,突出前者彰显个人独特感受和独特言说的论断,的确指认出“个人化写作”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较为普遍和容易被读者接受的一种判断。然而,这类概括和推理也存在着明显的疏漏,因为宏大叙事本身也是一个内涵复杂的概念,其所指和能指也存在着较大张力,不能脱离具体语境加以简单否定。试问:我们经常言说的现代、后现代难道不也是一种宏大叙事吗?文学创作追求历史和文化的厚度和深度,难道不是在追求宏大叙事吗?那种动辄便将宏大叙事当做“个人化写作”的对立面或超越的一个障碍的思维习惯,其实是颇值得怀疑的。
而从诗人的个人经验的“介入”和呈现方式切入,一些批评家发现:很多“个人化写作”提倡者都强调个人经验在写作中的重要性,但个人经验并非天然地构成对集体话语和主流话语的反拨,如果没有对个人经验独特的转化,个人经验的表达就很容易成为“自我封闭”的个人言说,“个人”如何走出纯粹的经验自足,成为处理经验并发生意义的“场”。对此,一些诗人和批评家分析了整体性、转换性和自我调节性的“个人写作话语场”与“个人写作”的深层互动关系。程波认为:“从逻辑发展上看,不可通约的个体生命体验、具有独特个体性质的经验转化方式(心理机制)、个人独特的话语方式应是‘个人写作的内涵所在。”[2]这种重视历史文化语境与个人体验之间的互动,借助于对言说场域的形成、作用及影响的研究来揭示“个人化写作”特质,应该说是选了一个很好的视角。
面对注重个人独特体验和感受的“个人化写作”探索,一些诗人有意或无意地与现实生活拉开一定距离,自然会造成个人与历史、时代生活的疏离和断裂,并由此招致种种非议和诟病。对此现象,批评家陈仲义通过《诗写的个人化与相对主义》给予有力的辩驳,并强调要拨开事态的表象、追究文本的“潜在对话”“隐性交流”的互文性,更细致入微地观照“个人化写作”的运行方式及产生的实际效果,使得批评抵达敏感问题的根部。
“个人”必然置身于一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必然与历史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个人情感、意志乃至于言说方式等,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摆脱历史文化语境的影响。“个人化写作”在强调“个人”的同时,自然也要强调“个人”与“历史”的协调、融合及互动,将个人化的表达与时代、历史的言说有机地整合起来。因而从个人的现实、历史承担角度去审视“个人化写作”就显得十分自然和必要。事实上,许多诗人和批评家都已意识到,“个人化写作”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命名,它不仅意味着对于自我经验的强调和对于公众经验的远离,更意味着自由的莅临和自我的重新发现,最终达到以个人的方式来实现对历史的某种承担,即“个人写作恰恰是一种超越了个人的写作”(王家新语)。显然,注重诗人从个体身份和立场出发,充分审视和考证诗人如何独立地介入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以个人方式承担人类历史的命运和文学诉求,以独特的个人生命体验和经验以个人的话语方式,达到对个人话语的捍卫和超越,不失为深入“个人化写作”内部的一条有效途径。
在对“个人化写作”的价值和意义评判时,诸多诗人和批评家们着眼点不同,得出的结论有着很大的差异,但它们的相互补充和印证进一步挖掘出“个人化写作”不可替代的诗学意义。譬如,孙文波就指出,“个人化写作”突出的意义,在于“它使得一些诗人在写作的过程中,始终保持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对来自各个领域的权势话语和集体意识的警惕,保持分析辨识的独立思考态度,把‘差异性放在首位,并将之提高到诗学的高度,但又防止了将诗歌变成简单的社会学诠释品,使之成为社会学的附庸”[5](p14)。放逐了代言人式的集体性抒情,对更加细微的具有原生态特质的日常生活进行细致打量和深度挖掘,通过对具体事象的凝注和透视,借助灵性闪耀的叙述,确实发现了许多被遮蔽的诗意,这也促成了许多先锋诗人在世俗化、物质化、感性化、娱乐化的大众文化时代,进行诗歌精神求索和重建诗歌秩序的不约而同的选择。对此,批评家们在对于坚、韩东、伊沙、张曙光、王家新、西川、欧阳江河、臧棣、翟永明等重要诗人的诗学主张和诗歌文本研究中,既充分地肯定了他们可贵的探索精神和不俗的佳绩,也直言不讳地指出了“个人化写作”因观念的偏失而陷入的某些误区,及时反思“个人化写作”探索误区的批评,从另一个向度上诠释了“个人化写作”的复杂性。
也有批评家通过考察“个人化写作”主体的个人性差异,探寻其内在的驱动力和个体差异所形成的多样化的写作格局。他们看到诗歌创作标准和评价尺度的难以规范,反而促使着诗人们积极地探索个人经验转化和表达的方式无限可能性和多样性,努力展示与众不同的主体独特的个性,企图使“个人化写作”彻底到位。在诸多的批评的文章中都可以看到这样较为一致的认识,高度重视个人经验的差异性和对其处理技术不一致的创新,成为“个人化写作”的突出表征和发展方向。无疑,主体意识高度自觉的“个人化写作”,一旦与社会、时代和个人生存等复杂关系建立起来,便具有更加丰富而深刻的诗学内涵。
“个人化写作”也是对历史与现实反思的一种方式。通过对一些代表性诗人的典型文本的解读,我们不难看到“个人化写作”延展的脉络,看到其穿越历史和现实所折射的非凡意义所在——真正有力量的“个人化写作”不仅仅是一种自觉地追求和捍卫个体独立品格的写作,还必须是一种穿过信仰的废墟,告别一味的自我迷恋的“个人抚摸”,秉承坚毅、执着的自由意志和永不妥协的批判精神,勇于自觉地承担与时代、生命相始终的责任和使命,主动地维护大众生存、尊严和权利的、源自于个人又超越个人的写作。洪子诚、陈超等人也在很多文章中提醒:强化面对现实、处理现实的品格和能力,保持个人对历史、现实、文化的参与精神和美学批判,应该是先锋诗人实现真正的“个人化写作”所应当认真思考的问题。因为“个人化写作”只有保持昂然的独立精神和写作姿态,重获“对历史的发言”和“对时代噬心主题”的介入能力,保持“历史关怀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张力关系”,才能在“历史个人化”、“个体承担”的写作中,达成“历史声音与个人声音的深度交迭”(程光炜语)。
在诗人和批评家们对“个人化写作”慷慨地奉上赞赏的同时,质疑、责难“个人化写作”的声音也一直没有停息,不仅因为真正有分量的大诗人和优秀文本乃至“个人化写作”已成气候的当下仍很稀少,缺憾和焦虑自然在所难免,还因为其理论主张和实践操作中存在大量的矛盾、悖论,探索中的许多歧途和误区显而易见。正像有些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个人化写作”并不是退避到“个人的港湾”,不能片面、偏激地理解为“非历史化”和“私人化”的写作;当诗歌写作拒绝对时代、现实、历史进行思考和发言,降低了主体精神的提升和文本思想深度的挖掘,借口反抗权力话语而迷恋自言自语,过度沉迷于感性化、平面化的宣泄,沉迷于写作技艺炫耀和语言的狂欢,不免会因相似的阅读和处理方式使“个人化写作”变成了流行的、面目相似的普遍化写作。这类中肯、峻切的直面现实的批评,反映出诗评家们对“个人化写作”保持着必要的警醒和理性,即使在他们的某些不无偏颇的指责中,也依然对“个人化写作”寄予热情的关爱和热切的期待。
应该说,“个人化写作”是一个充满张力的命名。关于“个人化写作”的批评,无论是与先锋诗歌创作同步乃至超前的批评,还是时空变幻后“不在场”的追踪反思,都是相当活跃并卓有建树的。在人们激赏新时期先锋诗歌“个人化写作”正行走在无限可能和歧义纷呈的探索之路上时,不应忘却也无法忘却那些同样有着无限张力和魅力的批评。
[参考文献]
[1]罗振亚“个人化写作”:通往“此在”的诗学[J]中国文学研究,2004,(1)
[2]程波“个人写作”与“个人话语场”[J]山东文学,2004,(4).
[3]沈天鸿总体把握:反抒情或思考[J]诗歌报,1988,(6)
[4]南帆身体的叙事[C]//汪民安《身体的文化政治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5]孙文波我理解的90 年代:个人写作、叙事及其他[C]//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作者系哈尔滨师范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吴井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