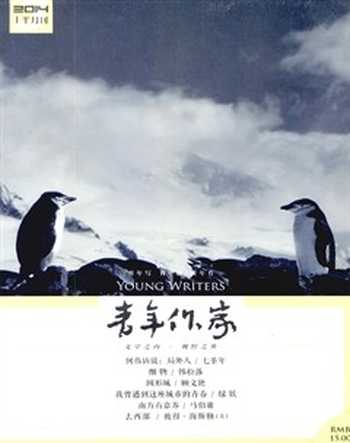活在海里,或死在岸上
阿贝尔
谁能想到,这些活着时被否定、被侮辱、被流放、被逼自杀与瘐死的诗人(我是说曼德尔斯塔姆、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死后倒成了那个世纪文学与人性的巅峰?自然是在今天看来。越是高拔的巅峰,越是需要退远了来看。越是高拔的巅峰越是险峻,而险峻本身也是所付代价的积累。
被一个时代、一个政体、一个独裁者抛弃和扼杀的人与创造,反过来成了那个时代人格与艺术的标高,算不算是对那个时代的否定?看不见却存在于人们心中的巅峰,把那个时代和执掌那个时代的独裁者比下了地狱,也把由趋炎附势者构成的主流比下了地狱。
观察他们的人生与创作,阅读他们的作品,深入他们多爱与相对自由的个人生活,便会重现那些我们未曾经历的年代,甚至走进那些年代,与他们达成交流。死而不朽的他们,为我们呈现出那个世纪的轮廓、质地、恐怖、浓稠的黑暗。但依然有昏暗的灯光,以及灯光投在窗纸上的爱的剪影;依然有璀璨的星光,和躺在露水濡湿的草地上看星光的恋人。
那些年代最珍贵也是最温暖的,就是爱了。也只剩爱了。这个爱是性爱,是俄罗斯特殊的文化背景保留下来的个人自由。性爱为身体取暖,写作为灵魂取暖。
在我看来,1917年革命之后的俄罗斯,特别是斯大林执掌的俄罗斯,就是一片死海,每个人都在泅渡、都在挣扎。多数人都是为生存泅渡,个别人既要为生存又要为灵魂、为俄罗斯精神泅渡。这是个人救赎,也是民族的救赎。是这种救赎的自觉或者本能,成就了他们的伟大。
很多人死在海里,只有少数人上到岸上、死在岸上。仅仅作为肉体的人死在海里也就死了,跟一条死在海里的鱼没有两样。然而诗人不同,肉体死在海里,诗歌还可以上岸,精神还可以上岸。不止上岸,还可能上到大陆,扎根萌芽,长成森林,为可能来临的下一次泅渡制造诺亚方舟。
1938年11月曼德尔斯塔姆死在了海里。他不知道他的古拉格离岸还剩多远。好在曼德尔斯塔姆并不是很想上岸,他知道他的诗歌能捎带他的灵魂抵达大陆,回赠肉体不朽的荣光。
1941年8月,茨维塔耶娃死在了海里。海里有一颗钉子有一根绳子,她用绳子将自己了断。她从巴黎回来,不了解这片海的水性,遇到惊涛骇浪就慌乱了。她不如曼德尔斯塔姆自信,她去死仅仅是活不下去,没有殉道的意思。
四个人当中,两个人死在海里。海水有多苦、多成,没有人知道。被海水呛死有多难受、多绝望,没有知道。海水的咸度里是政治;归根结底是权力欲望,是人性的邪恶在个人身上奇迹般的积淀。
曼德尔斯塔姆有诗:
我们活着,觉不出脚下的国家,
十步之外便听不见我们的话音,
而在那吞吞吐吐者所有的地方,
人们提到了克里姆林宫的山民,
他粗壮的手指,如同蛆虫一般肥。
……
曼德尔斯塔姆就是以这首诗获罪的。自然,他心里想到、没有写在纸上的“罪行”要更多、更大——照布尔什维克和斯大林个人的法典。
谁都希望能上岸。不是上岸去死,是上岸去活。活在花草树木中,活在累累果实里,活在性爱与诗朗诵的温暖中。但是谁能上岸谁不能上岸,不是自己可以保证的;都是落水的人,呛水之后的扑腾谁能保持头脑清醒?
曼德尔斯塔姆身上有一种高贵、不屈而又敏感的基因,他所以上不了岸。茨维塔耶娃富有激情,自己时常决堤,在个人决堤的时候她没逃脱时代的决堤。
1960年5月30日,帕斯捷尔纳克死在了岸上。他是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死的,可不可以说,他是被这个世界性的巨奖压死的?阿赫玛托姓说过,帕斯捷尔纳克没能承受住他的荣誉。这话要从时代的深度去理解。
帕斯捷尔纳克对世界天生有种恐惧,从他的两个眼眸可以看见。还有他紧张的马脸。紧张是内心的恐惧在约束自己的言行。他也因此才没有落得曼德尔斯塔姆的结局。要说内心所想,他犯下的“罪行”一点不亚于曼德尔斯塔姆,但他审时度势,知道万万不可写在纸上。
1966年3月5日,阿赫玛托娃在四个人当中最后一个离世——死在岸上。己算是死在大陆的深腹。她是四个人中唯一生前享受到荣誉的人,不管这荣誉是不是她想要的——她毕竟没有拒绝。
究其一生,究其一生的选择与经历,阿赫玛托娃是四个人当中最渴望上岸、死在岸上的人。是海岸的美丽轮廓和陆上的生机支撑了她。还有就是她在海里的淡定与“无作为”,为她节省了体力。在一次次恋爱中偷闲,在一次次婚姻中偷生,用获得个人享受与折磨转移注意力、麻醉自己,用承受婚姻细致而深刻的折磨去忽略政治迫害。
阿赫玛托娃有着不同于曼德尔斯塔姆和茨维塔耶娃的泅渡方式。选择这种方式使得她朝帕斯捷尔纳克靠近了一步,而在个人存在与精神向度上与前两人有了微距。不过,在现实中她要比帕斯捷尔纳克勇敢,一贯地支持曼德尔斯塔姆。
贵族气质会让人考量肉体的尊严。阿赫玛托娃的一生都在照顾她活着的尊严,从不太过忽略日常生活的细节像曼德尔斯塔姆那样偏执于精神追求。这样,在保全她上岸的同时也或多或少限制了她诗歌表达的深度。
我愿意把死海理解为布尔什维克执政的俄罗斯。死海两岸有七十四年的宽度,深度则是1917年暴动和斯大林的恐怖,但却是以阿赫玛托娃和曼德尔斯塔姆的诗歌精神与人性光芒来丈量的。最深的海域是1937年大清洗,最深的一条海沟是曼德尔斯塔姆之死。它吞噬了那些真正代表俄罗斯的年轻生命,让这个民族的心灵与良知碎裂。碎裂却未毁灭,它们从死亡的肉体分离出来汇集在诗歌和散文里,把俄罗斯的白银留传了下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四个人都是船,都是桥梁,虽不曾抵岸便倾覆了沉没了、坍陷了断裂了,但他们把俄罗斯的种子带了出来,不至于使胚芽在咸度浓重的海水里完全坏死。每一位流亡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也都担当起了保存种子的责任。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土不允许善与美生长,那么就把它带到异国他乡去。
也可以说四个人都死在海里,没有人上岸,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死去的1960年代还不是岸,它只是近海、浅海或大陆架,或者一个叫赫鲁晓夫的岛礁。不过站在这个岛礁上已隐隐约约看得见陆地了。
布罗茨基接过了他们的桨,代替他们泅渡了死海,上了岸。
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斯塔姆、茨维塔耶娃和帕斯捷尔纳克四个人构成的关系,是文学史的一处迷宫,亦是人性的一个迷宫。它是美妙、玄秘的,同时又是苦涩、不可知的。它是一副扑克牌,玩过之后再没人知道它的玩法。探究四个人的关系,等于探究一个世界一个诗歌的世界,一个男人女人的世界,同时也是一个俄罗斯的世界。四个当中,两两都有组合,这非常让人着迷。异性相吸,同性也相吸,但无论同性异性也都相排斥。四个人都是单独的,各自有自己的个人生活,在自己的恋爱和婚姻生活中自成一个星团。星团运转,扇动着大气、云层释放出电荷——阿赫玛托娃与库图佐夫(画家),与阿图尔·卢里耶,与古米廖夫(第一任丈夫),与莫迪利阿尼(画家),与涅多布洛沃,与鲍里斯·安列普(画家),与希列伊科(第二任丈夫),与普宁(第三任丈夫),与加尔洵;茨维塔耶娃与艾夫伦(丈夫),与帕斯捷尔纳克,与罗泽维奇,与里尔克曼德尔斯塔姆与米哈伊洛夫娜(画家、美人),与茨维塔耶娃,与安德罗尼科娃,与奥尔加-阿尔别宁娜(演员),与奥尔加·瓦克赛尔,与玛丽娜·谢尔盖耶夫娜,与维拉·阿尔图洛夫娜,与娜塔莉亚·施滕佩利,与娜佳(妻子);帕斯捷尔纳克与叶莲娜·维诺格拉德,伊达·维索茨卡娅,与叶夫根尼娅·卢里耶(第一任妻子),与茨维塔耶娃,与杰娜伊达·奈豪斯(第二任妻子),与伊文丝卡娅。他们各自独立,偶尔摩擦。星团无法爆炸重组,但诗歌却把他们扎成了一架筏子,漂流在布尔什维克死海。
筏子上的两个女人,阿赫玛托娃与茨维塔耶娃,一生见面不多,更谈不上亲密,她们分处筏子的两端,各自经历着风浪。这里有茨维塔耶娃在外流亡十七年的原因,更有两个女人皆为独立星团不可交汇的原因。尽管如此,亲密还在发生,早年互有献诗,茨维塔耶娃回国后两人又有见面,即使在茨维塔耶娃离世十年的1950年代,阿赫玛托娃仍感到她与茨维塔耶娃之间存在着竞争,视她为“亲密的敌人”。
两个女人的亲密主要体现在彼此钦佩与仰慕里。玛丽娜对安娜的仰慕是羡慕和崇拜,称后者是“俄罗斯的安娜”;安娜对玛丽娜的仰慕除了钦佩还有戒备——她一直担心玛丽娜把自己比下去,风头盖过自己。活在时比下去,死后比下去。
年轻时,玛丽娜写下数首献给安娜的诗。晚年,安娜把曼德尔斯塔姆和茨维塔耶娃的照片放在一起置于案头,念念不忘玛丽娜送过一枚自己带过的饰针给她。安娜一度把玛丽娜写给她的献诗揣在手提包带着,直到稿纸碎为纸屑——曼德尔斯塔姆证明确有其事。
阿赫玛托娃活着时不喜欢别人拿她跟茨维塔耶娃比,或许不是害怕比输,但绝非不屑于,虽然她说过茨维塔耶娃更接近马雅可夫斯基。她还说过茨维塔耶娃是一个厌世主义者,在哪里都过得不快乐。或许奈曼说得有道理,茨维塔耶娃是一个没有天堂的诗人,而阿赫玛托娃有天堂。
阿赫玛托娃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今天,可以说茨维塔耶娃的名声盖过了她。晚年的阿赫玛托娃有种明澈的自知,曼德尔斯塔姆和帕斯捷尔纳克这两个男人她是比不过的,唯一可比的只有茨维塔耶娃。茨维塔耶娃走了自杀之路,但她未必就是真的厌世主义者,或许她是太过爱世,勇于创新,不加克制,追求多声部,像炉中煤燃过便成灰烬。阿赫玛托娃天生冷漠、克制,以不变应万变,属于“慢工出细活”与“细水长流”一类。就活着时能享受到荣誉这一点,无疑是阿赫玛托娃笑到了最后。
在死海中泅渡,什么是救命稻草?阿赫玛托娃抓住的是爱情。其实说爱情,超出了实际的感情成分,准确地说是性爱、情欲。至少早期是情欲。后来年龄渐长,情欲消退,才变成一种可以慰藉人的社会关系。情状也如被老虎追逐掉进枯井中的人,面对井下血口大张的巨蟒和井上等着吃人的饿虎,干脆伸手去采吃井壁的鲜果。
在四个人各自的爱情与男女关系中,阿赫玛托娃是比较肉欲的,她写过“在湿漉漉的惰怠中,重又吻着肩膀”这样的诗句。茨维塔耶娃和曼德尔斯塔姆都有精神恋的倾向。帕斯捷尔纳克现实,或浪漫有度。
俄罗斯文化有一种好,准许采吃鲜果。这好是俄罗斯本身的道德土壤结合了西欧文化特别是法国文化才得到的。也可以说是俄罗斯白银时代留给苏维埃死海的遗产。
阿赫玛托娃一生有过十一个男人,还不包括仅有精神暧昧的,比如以赛亚·伯林。茨维塔耶娃有过十八个男人,但有的只是精神恋,比如里尔克。曼德尔斯塔姆爱过的女人有九个,他如果活到帕斯捷尔纳克的年纪还会增加。帕斯捷尔纳克最少,也有六位。
这不只是诗人多情,更有特殊的文化背景,那就是俄罗斯个性解放的传统。俄罗斯人也讲“忠”,但不是道德范畴的,而是发自内心的、属于自我感觉的。中国人的“忠”更多是道德的,以牺牲个体感觉与个体价值为代价,虽然往往做不到,但普遍认同。俄罗斯没有中国式的婚姻道德,准确地讲是男女关系道德,它的爱情和婚姻自由,男女关系属于“亚性自由”。中国人在男女关系上的道德感已经积淀成全民的心理素质(古时更多的是女人的道德与心理素质,今天是普通百姓的道德与心理素质)。“亚性自由”是前苏联诗人生活的大背景,即便是在斯大林的大清洗时代这个背景也不曾改变。这要归功于俄罗斯基因(其实也是人类共有的基因),只是中国人更虚伪而己。大清洗时代,爱情自由(也是性自由)都不曾被禁止,不能不说这是俄罗斯民族长于我们的地方。
一个在任何时代都不让泯灭个体的民族是幸运的。个体存在最本质的表现不是吃喝拉撒,而是爱情自由和思想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讲,爱情自由做了四个诗人渡海的诺亚方舟。有时候就是一只舢板,诗人把身体托付给它,把灵魂也托付给它。
俄罗斯(西方)文化背景——也可称作人性的文化背景,即有完整的个人生活的背景。在这种背景下实现的自然是个性释放,包括“性的自由”——性在爱(内心)或精神引导下的实现,而非臆想的乱交。
人性的文化背景是温暖的洒满阳光的天空,即使局部阴云密布,也能洒下一些阳光在大地上;专制文化背景则是黑夜,不可能有阳光分派到大地上。吾国人讲“忠”,从一而终,身体不能分属,思想也不能分属。“忠”是把个人作为牺牲献祭,条件是心死。“忠”过去是男人对女人的专制,君主对臣民的专制,现在颠倒了,更多变成女人对男人的专制。
曼德尔斯塔姆与阿赫玛托娃不存在性的关系,虽然前者爱上过后者。曼德尔斯塔姆是个多情种子,爱过的人众多。他对阿赫玛托娃的爱或许是真的,但一定只是某个时期或一瞬。阿赫玛托娃已是少妇,年轻漂亮,诗写得好。曼德尔斯塔姆偏爱少妇,几乎同时,也爱上了同是少妇的茨维塔耶娃。茨维塔耶娃也是多情种子,回馈给他的感情有点暖昧,不像阿赫玛托娃界定得那么明确,所以很吊他的胃口。阿赫玛托娃只承认友情,跟他的来往坦荡磊落。曼德尔斯塔姆经常坐在她的书桌旁,为她朗诵自己的诗作。她最烦听朗诵,但他除外,她晚年对奈曼说“唯有曼德尔斯塔姆的朗诵有如白天鹅在滑翔”。阿赫玛托娃对他是一种亲弟弟和好朋友的感觉,她善意地讥笑他爱上她,讥笑他是个情种。
曼德尔斯塔姆小阿赫玛托娃两岁,对阿赫玛托娃的感情里有恋母的成分。他的天才深得她的认可,他的忧郁很吻合她的审美。他们是知己,彼此掏心掏肝。他很满足于跟她在一起,看见她,闻到她的味道,包括无意间身体的接触。彼此间有种很深的精神沟通。在革命发生后的一段日子里,他们经常乘坐出租马车穿行在马路的车辙和营火之间,背景是噼里啪啦的枪声。像一对浪漫的热恋中人,却又不是,是诗歌和一种宿命的亲爱让两个人在一起。出租马车穿过涅瓦大街,穿过营火和古拉格,停在了俄罗斯文学的峰巅。枪声响过是死寂,接着是朗朗的读书声——童声。
曼德尔斯塔姆寄居在斯列兹涅夫斯基家那两年,阿赫玛托娃经常去看他,一起参加朗诵会。到了三十年代,两个人的关系愈加紧密,内务部和但丁把他们紧紧地拴在一起。但丁是他们两个诗歌的根,从生命与审美的最深处支撑他们。1933年,两个人一度沉浸在但丁的《神曲》里,她为他朗读《炼狱》的第一部分,听得他潸然泪下。
四个人中,阿赫玛托娃唯一对曼德尔斯塔姆不曾有过异议。不是因为他死得早、死得悲催,是因为他死得完美、死得悄然。得知他的死讯,她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像是在预料之中,只觉得更孤独了。
他死了,不能陪她一起泅海,留下遗孀娜佳陪她。他对她说过,她是他唯一可以在想象中交谈的两个人之一。灵魂的交谈。
时隔八九十年,我们无法去想象两个人交往的细节——语言、目光、手势与姿态,更不要说去捕捉大脑与心灵的电荷,以及时刻变化的天气。他们谈诗,总会产生无上的默契与共鸣。诗歌对于他俩,最初都是作为乐句在耳边鸣啭的;他们习惯了等候,直到它的轮廓毕现才动笔记录。
虽然他们不是恋人,没有性爱关系只是友谊,但这仍然要感谢俄罗斯开放的文化背景。即使只是友谊,也是很特殊的友谊,两个人时常互访,彼此寄居在对方的家里。她提着她著名的小提箱,敲开纳晓金胡同他和妻子分到的新宿舍。她穿着鲜红的睡衣住在他家的小厨房。1934年5月14曰凌晨他第一次被捕时她就在现场。她冷静地、眼睁睁地看着内务部的人抄了他的家将他带走。
怎样活,怎样活过类似斯大林的大清洗时代一直泅过死海上岸,这是件特别考量一个人神经与灵魂的事。活着,又不能“活死”,又不能学“水上漂”的轻功。
曼德尔斯塔姆没能上岸,他死在了海中央。他太天才、太伟大、太完美了,死在海里也便是活进了历史。不管是哪种结果,都会不朽,因为他的灵魂以诗歌的形式震塌一个暴君一个专制帝国的基石。茨维塔耶娃也死在海里,也活进了历史。她不是以死活进历史的,但她的死给予了她与历史的衔接以传奇。曼德尔斯塔姆进入的是历史的正页,茨维塔耶娃进入的则是历史的插页,不过插页和正页同样漂亮。
1938年冬天在普宁封坦卡的房子里,阿赫玛托娃身穿一袭黑色晨衣,缝隙露出一线肉身的苍白,没有一点不安。她时常蜷缩在扶手椅上,把光脚丫放在身子下取暖。她像巫又像猫。她的这个姿势可以被看作涉世的姿势。她的涉世也即是避世。想象扶手椅下就是大海,海皮如黑夜中的原油汹涌,她蜷缩在椅子上渡海,经历得太多,有了睡意。不过她还不能睡去,她想活着穿越、上岸,为了目睹罪恶的时代结束,也为了自己被新的时代看见。
那个冬天,曼德尔斯塔姆在遥远的弗拉迪奥斯托克以死给他安宁。
死也是一种穿越。勒痕、血迹、呻吟、拽卡的声音,咽气的声音留了下来,加上不死的灵魂成了诗歌。
帕斯捷尔纳克以肉身泅渡,灵魂稍显沉重,影子拖得很长。他不在云层,他走历史之路,战战兢兢,但内心坚定。他不如阿赫玛托娃看重上岸,他不希望上岸只带着肉身,所以要写《日瓦戈医生》。
我喜欢帕斯捷尔纳克。喜欢他的马脸,和马脸上两个眼睛的冷漠与恐惧。它真实,真实地承载时代的恐怖。一个生命,与时代抗争,无法超越时代和抛弃时代,在生命的最深处(也是最敏感处)与时代原油般的黑暗相通,这本身就是一种伟大。
帕斯捷尔纳克的理性让他不能像曼德尔斯塔姆那样跟专制较真,他必须在现实中马虎一点,表里不一一点。他借现实中的马虎保护自己,好有机会在写作中较真。他本身也有胆怯,一种敏感的对肉体的不信任,让灵魂无法超出肉体。他是四个人中最具人性真实的一个。惧怕而坚持,敏感而理性,战栗而不改初衷,冷漠而充满想象。
曼德尔斯塔姆有点英雄主义。精神至上,不怕牺牲。茨维塔耶娃有点理想主义,忽略物质。阿赫玛托娃有种贵族气质,不拒绝物质给予人的尊严,但不依赖物质,她不相信没有肉身的爱情和没有肉身的尊严。
曼德尔斯塔姆爱过茨维塔耶娃,对后者的身体有过非分之想,但茨维塔耶娃不曾从性爱的意义接受过他。两人不多的相处里始终有种紧张与不适,毫无他跟阿赫玛托娃的亲和。
茨维塔耶娃与帕斯捷尔纳克有公认的恋爱关系。他俩的通信,加上跟里尔克的通信,被编辑成今天著名的《三诗人书简》。两个人没有现实的性爱关系,只有想象的精神化的性爱关系。茨维塔耶娃在想象中完成的要多一些。他一度是她的梦中情人,她借了他穿越她流亡的现实和厌倦的婚姻,他借了她安慰苦闷、获得慰藉。有七八年,他都是她想象中的性爱与诗歌的救命稻草。
在两个男人之间,我没有发现“伟大的友谊”,只发现争论与默认。从“浪荡狗”开始,他们没有少见面,但两团星云似乎很少有过吸引,通常都是彼此注意到,看一眼,即使回家翻出对方的诗来读,也不会把感想、热泪回馈给对方。这两个男人,甚至不曾在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这两座母桥上相遇。比较意外的有两个时刻:1924年1月24日,两个人夹杂在上万人当中目送列宁的灵柩;1932年11月11日,在曼德尔斯塔姆的诗歌晚会上,两个人为艺术自由的话题争吵不休。
在我的想象中,帕斯捷尔纳克永远都只能望见曼德尔斯塔姆的背影。后者走得辽远,身后是漫天风雪的西伯利亚,他渺小却确定,像一颗他深爱的但丁诗歌中的灵魂。帕斯捷尔纳克有一个高大的肉身,它在曼德尔斯塔姆看来是一堵墙,它囚禁了他的灵魂。
以赛亚·伯林不这么认为,他说:“实际上,只有约瑟夫布罗茨基的成就可以与帕斯捷尔纳克媲美。阿赫玛托娃和曼德尔斯塔姆都差得远。”如果真的如他所说,为什么布罗茨基在他的神殿里供奉的神祗首先是曼德尔斯塔姆和茨维塔耶娃,而不是帕斯捷尔纳克?
曼德尔斯塔姆被捕的当天,斯大林给帕斯捷尔纳克打电话,要他评定曼德尔斯塔姆作为诗人的地位,帕斯捷尔纳克犹豫了一下没有回答,他想换个话题,斯大林挂了电话。无论后来他怎么说曼德尔斯塔姆是一个大师都于事无补,他当时毕竟没有一口说给斯大林听。
帕斯捷尔纳克会不会像阿赫玛托娃在暗中跟茨维塔耶娃较劲一样,也一直在与曼德尔斯塔姆较劲?如果真是这样,他的真实又会多出一丛汗毛。或许作为男人,他不会像阿赫玛托娃那样看重身后事。
活在海里时,四个人都有尊严,曼德尔斯塔姆活得最有尊严,茨维塔耶娃流亡海外也保住了尊严。
单就死,自然是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有尊严,他俩死在岸上。当然,这尊严是肉体的。
曼德尔斯塔姆的肉体最无尊严,第一次流放沃罗涅日就精神崩溃,等到第二次被捕押解去弗拉迪奥斯托克,想必已经瘫软不能直立。暴力加到病躯,灵魂挥发,活人也是死人。
我与阿赫玛托娃在这个世界上共时不满半年。在她离世四十七年后,我梦见四个诗人聚在了我生命的某处。
“奥西普,你走得早,你还记得弗拉迪奥斯托克的古拉格么?”
阿赫玛托娃半躺在一张四人沙发上,眼睛看着茨维塔耶娃。
“告诉我们,你究竟是瘐死还是被枪杀?告诉我们真相。”帕斯捷尔纳克插话说。
“还有这个必要吗?这地儿干干净净,我们有必要抓屎糊脸么?”
曼德尔斯塔姆从阿赫玛托娃脚边坐起来,在东倒西歪的三个人面前打转。他的额头光光的,像十八岁,看不见一个思想的梯子框。
“你知道吗?那个长着蛆一样手指的人早死了。他一死,便有人要打倒他,揭示真相,把他的尸体从墓穴拉出来……”
阿赫玛托娃说着坐直身子,她的坎肩滑了下来,把半个胸脯亮了出来。
茨维塔耶娃的视线滑过阿赫玛托娃的乳房,下意识地停在了自己的胸脯。
“鲍里斯,你的胆子也太小了,要是我的话,我才舍不得拒绝瑞典学院那么大一笔奖金呢。”茨维塔耶娃闭上眼睛说。
“玛丽娜,把门关上!”曼德尔斯塔姆说,“不好意思,谁叫你坐在门边?”
“都什么季节了,还怕吹?”帕斯捷尔纳克问曼德尔斯塔姆,“你还不知道啊,苏联早没了,已经是俄罗斯啦!”
“鲍里斯,奥西普哪里是怕风?他是怕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进来。”阿赫玛托娃说。
“我不是怕他,我是恶心他!”曼德尔斯塔姆说。
说着,四个人开始喝酒。布罗茨基从里屋走出来,一只手拿着四个杯子,一只手拿着一瓶启开的酒嚷嚷着:“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这地儿没有时间,我们什么都不用怕,什么都不用恶心。”他半蹲在阿赫玛托娃前面边说边为她斟酒。
酒过三巡,奥西普朗诵了他在白银时代写给玛丽娜的献诗。玛丽娜朗诵的是她写给鲍里斯的献诗。鲍里斯读了他的《人与事》中《三个影子》的片断。
阿赫玛托娃没有出声,她只是静静地听。布罗茨基替她朗诵了她的《安魂曲》:
巨石般的词句压向
我一息尚存的胸膛,
没什么,我已经有了准备,
无论怎样我都能承当。
今天我有很多事要做,
——致阿赫玛托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