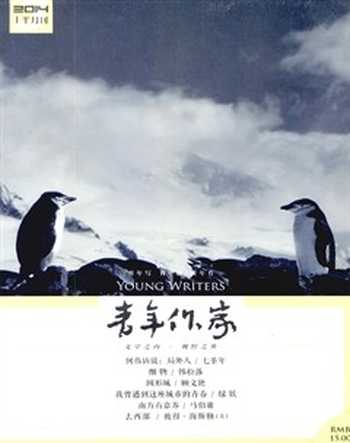我曾遇到这座城市的青春
绿妖
说到北京,亮起的第一个画面,2001年11月22日,小雪。赖声川的《千禧夜,我们说相声》。小雪夜未下雪,但极冷。这是我人生中第一个“现场”,头一回与许多人一块儿,在封闭空间,笑声朗朗地看一个剧,虽然笑得悲凉。散场后,长安大戏院前的地下通道寒风刺骨,人们低头急行,或眼疾手快地从人群中逮个熟人一起吃饭。我的饭局有程灵素姑娘、编剧史航,还有千里迢迢赶来的海口文学青年二黑。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坐飞机看演出的人。已是熟极的网友,真人相对,竟是陌生。我静静听他们如数家珍,谈“表演工作坊”。这是我头一个北京饭局。
原来,北京是这样的。
那时我刚到北京,房间十平方米,一桌一椅一床一书架而已。据说要拆迁,房间里没安电话,厕所老旧,一副克难临时气氛。但它有一个白色阳台,以一扇削瘦修长的门与外界相隔,门刷着古雅的棕漆,高处镶玻璃方格,掩着白色布帘。我常在深夜推门,往楼下的马路上看。北京的深夜,路灯还是亮堂堂的,永远不会一片漆黑。这对一个刚到北京的、有着不稳定的神经,不稳定的睡眠,不稳定的情感的年轻人来说,是莫大安慰——你失眠,世界也醒着。黯淡的马路,犹如一幅宽银幕幕布,时有汽车经过,也有醉汉。还曾有人在楼下深夜伫立,但那晚我睡着了,毫不知晓。我是八月份来的,到十月,在一个杂志社工作。而秋季是北京最好的季节,走在街上,迎面吹来淡金色的风,荡开衣襟。光线里仿佛有细细的金沙,干爽明亮。这是别处没有的风。用《日瓦戈医生》中的一段话来形容被这风吹过的感受:“整个空间是如此清明透彻,似乎为你打开了洞穿一生的眼界。这种稀薄空寂的感觉,如果不是如此短暂,而且只是在秋季短短的一天的末尾、接近提早到来的傍晚时刻出现的话,那真是难以忍受的。”
之前,我在县城一所变电站上班,上一天,休三天。主要工作是用拖把清洁值班室地板及黑色皮革绝缘垫。时间太充裕了,对于一个县城青年来说,充裕到让人绝望。我拿这么多时间干什么?县城太小,像一件不合身的外套,像紧身衣,捆精神病用的。县城的夜晚,过了十二点,只有我的窗户还亮着灯,视线所及,一片漆黑。这漆黑也让人发疯。
我只是嫌故乡太小,但命运给了我一个巨大的、巨大的城市。
很多人对北京之“大”印象深刻。头一回去航天桥‘九头鹰参加饭局,出租车开啊开啊,始终在水泥高架桥上行驶盘旋,从这个角度看,北京城荒凉、可怕,没有人气,像太空城。开呀开,我睡了一觉还没到。大得让人仓惶。
我给许多时尚杂志写采访,每月写近一万字外稿,能有三干元的稿费,加上三千元工资。这是很大一笔钱。我的房租才三百块。办公室是独栋小洋楼,在东四九条胡同里,深棕色木地板,踩上去,犹如老式风琴的风箱,发出温柔悠长的声音。同事都下班后,我几乎每天写到晚上十点四十五,赶115路电车回家。陪伴我的只有北京的风。冬天,北京会有狂风。
它们尖利地溜着电线在空中怒飞,声势之大,仿佛窗外立起一个海洋。我侧耳听一会儿,继续写。这时网上,开始有人直播饭局盛况,都有谁,喝的什么酒。我扫一眼,继续写。有时写到晚上,下雪了。立在窗户前看一会儿,继续写。看门的大伯觉得我很忙,比主编还忙,每次都同情地冲我点点头:下班啦?
胡同两侧是青灰色的平房,有月亮的晚上,月亮也是青灰色的。所以没月亮时,我走在青灰色的胡同里,也像是走在月之清辉中。整个平安大道就是一条青灰色的大街,这还是陈希同时代统一刷的颜色,虽然这种整齐划一为美学家诟病,但在那时,这条大街是我的游乐场。再往北,或南,东直门大街有东方银座,天安门长街有国贸西单王府井,平安大道夹在这两处喧闹之间,是一个落寞的存在。不喝酒的日子,我和朋友一起散步,走上几公里,身边是绵延不绝的青灰色砖墙。作为背景,它们足够安静。走累了,就坐马路牙子上,继续聊。那时的我们有说不完的话,像要把自己倒出来,剖开了给朋友看。一定是颠倒,在青春期,我活得像中年人。而在二十多岁的那段日子,我现出青春期的种种症状,包括,怀着巨大而盲目的热情,包括,急切想把自己剖开了给朋友看。平安大道是单调的,一直是统一高度的平房,一直是青灰色的两岸,一直是宽阔的街道,还有街道边的路灯。但是,如果你跑起来,路灯就会像海洋,把你托在水面。这是我一个朋友告诉我的。
每天晚上,我坐115回家。临近末班的电车,有的是空位,我坐在窗户边,头靠玻璃,风从敞着的窗户灌进来,精疲力竭的身体里,仍然有东西在飞舞。我记得,那路电车的座椅,都刷着浅蓝色的漆。是上世纪工业中常见的淡蓝。同时期工业中常见的绿色也美极,绿色矿灯长销不衰,那种深绿色配玻璃罩,是一流审美。在2001年,这些上世纪的美色仍处处可见。我凝视着黑暗中时隐时现的一个个浅蓝色空位,这就是我要的生活,沮丧、疲倦,然而自由。
而饭局是我生活中的白色阳台,供我眺望。
2002年2月,张立宪,江湖人称“老六”,ID“见招拆招”,组论坛“饭局通知”,挂在西祠“影视”类下,妄图与影视大版“后窗看电影”一别苗头。为凝聚人气,他疯狂组织饭局,同时在版内连载“记忆碎片”系列,这系列日后成书,名为《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文风诙谐,娴于卖萌。
饭局。我到早了,空荡的包间里,只有一个人等在巨大的圆桌前。抬头,国字脸,酱色面皮,不怒自威。彼时老六是某出版社副总编,多年修为,读书人本色压根遮挡不住。这哪儿是网上萌物见招拆招,我差点夺门而去。
在日后,我不止一次地发现,网络人格和现实人格,常截然相反。网上攻击性极强,生活中往往绵羊般无辜无害。幽默的段子手,现实里常忧伤,仿佛抑郁症患者。《西游记》中,妖怪都有两种形象:人身,以及被观音一指,现出的原形。那时候,我认识的人也都如妖怪,有至少两种身份、两个名字。日后数年,我不断地验证这ID与真人之间的反差,看到一只只妖怪,卷地一滚,现了原形。
饭局,是大规模的妩陉现形日。
经常去的地方。建国门“罗杰斯”、航天桥西北角“桥头火锅城”、蒋宅口面馆、三里屯青年旅馆楼下酒吧(扎啤五块钱一扎)、太阳宫桥“乡老坎”……它们,都不复存在,关门大吉。2013年一个春夜,在火锅店,我们扳着手指,逐个盘点那些年被我们克死的饭店,“红番茄呢?也不在了。桥头火锅城呢?没了!罗杰斯,整个连锁在北京都消失了……”惟一一个有眼色的人、桑格格终于按捺不住,低声:饭店老板还在旁边呢,听着不好。恍然大悟,急忙收起我们的饭局死亡赋格曲。有时,饭局不得不临时转场,因为来人太多,且大有源源不绝之势。老六一度恐慌,如此无休止扩充,“恐怕以后北平没有饭馆装得下越来越壮大的吃货队伍了。”这支队伍终于在达到四十多人时,晃几晃,惊险地稳定下来。
如今想来,那像是老六的一个诡异的青春期:漫无目的地组织饭局,吃饭喝酒,喝多后,领唱“亚细亚的孤儿”,深夜散场,整条马路都是我们的人,踉踉跄跄的醉步印满长街。几年之后,老六开始做《读库》,深居简出,整日看稿,修炼内力。狂歌烂醉的阶段一去不返。电话里,我对这个严肃的男人,也越来越难叫“老六”,而讷讷地称之以“六哥”。
那也是我的青春期。离开了紧身衣,再也没有人说我是神经病——我的神经质,在北京这所大精神病院里,显得微不足道,特别正常。深呼吸。好像被埋了很久,嘴巴露在地表上,外面下过一夜细雨,空气是淡绿色的。
彼时北京城仿佛都在青春期。离我们不远处,音乐乌托邦“河”酒吧正拉开大幕,歌手和诗人喝五块钱的青岛啤酒混迹一堂,当时在“河”酒吧当酒保兼乐手的张玮玮回忆,那段时间,看什么,眼前都似乎隔着一股热气——就是那种感觉了。2001年,北京房价尚未搭上火箭,“蚁族”“胶囊公寓”尚未出现。二环、三环尚能租到房子。从朝外到呼家楼,有许多四五层小砖楼,通常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筑,砖是青灰色,一块块堆砌的青灰格子图案是很美的。还有一部分,比如我住的呼家楼那一带,小楼刷成红色,粉笔那样的淡淡的、略带潮湿的一种红。掩在银杏树后,衬着无轨电车五线谱一样的电缆,美得静穆。这粉笔红,和平安大街的月光灰混合,就是我记忆中最初的北京,又激烈,又宁静。
楼下面馆,一碗西红柿鸡蛋面三块钱。夏利车起步价一块二,从单位打到住处,12块。房价?没人关心房价,03年的贡院六号,每平方米四万,老六当新闻贴到版内,大家对这暴发户式房价一通嘲笑。直到04年,市区也就五千每平方米,2002年,我认识的朋友谁会关心房价呢?大家关心电影还来不及,关心话剧还来不及。谈恋爱还来不及。
老六出过畅销书《大话西游宝典》,也出烂书。饭局,正值他怀疑人生时,“2003年的全国图书订货会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召开,俺去那些展厅采风。到处都是‘做出来的书,挂羊头卖狗肉,扯虎皮做大旗,为婊子竖牌坊,拿肉麻当有趣。俺对这个行业的反感和绝望到达了顶点……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俺一方面编着老廖的书,以及其他的杂碎,一方面被那种无力挣脱的幻灭感撕扯着,实在找不到解决之道。”
那时很多人都刚到北京。被贾樟柯称为“像上世纪二十年代刚从苏联回来的革命家”的Liar,写影评,出书,创“晃膀子联盟”,组织年轻影评作者,与学院派打笔仗,指点江山,意气风发。2012年,沉寂已久,他以本名李霄峰出了本书,叫《失败者之歌》,我采访他,原来当年他是从比利时休学,擅自跑回北京,学费花完后,到一个朋友家打地铺。以长帖《等待是一生中最初苍老》蜚声西祠的顾小白,那时还不是著名编剧,而是铁通职工,单位还分他一套小房子。看上去他完全没理由辞职。他只是焦虑。而在当时,我以为只有我的人生干疮百孔,即使在最欢乐的酒局,朦胧四顾时,心里都有个声音高喊:你跟他们不一样!——后来想想,很多人,于此时或许已有抑郁症的伏线。2012年深冬一次饭局,一桌人,有四个得过抑郁症。
而在2002年,我们对此一无所知。犹如一群等待上场的演员,期待着“真正的生活”,坚信“一切价值将被重新评估”,而与身边世界格格不入。当我们来到饭局,犹如进入另一次元。现实世界被稀释,不再那样坚硬。而精神世界,在火锅店缭绕的白烟之间,在中南海点8的青烟之间,凝固成发光的空中楼阁,我几乎忍不住要伸手触碰。我再也没见过那么多夸夸其谈的人,性情比作品更像艺术品。如果有少壮派“晃膀子”的加入,满屋子“嗡嗡嗡”都是黑泽明七武士费里尼安东尼奥尼。经常谈论的名单:罗大佑、侯德健、崔健、赖声川、孟京辉、刘小枫、克尔凯郭尔、杜拉斯、里尔克、杨德昌、侯孝贤、贾樟柯、岩井俊二、宫崎骏、阿莫多瓦。《巴黎烧了吗》《流放者归来》《光荣与梦想》《伊甸园之门》……谈电影比文学多。
我想是因为DVD。刚到北京时,文艺青年都是到小西天买刻录碟:黄色牛皮纸袋,装一张裸盘。许多大师片不出VCD。但进入2002年,碟店开始有大量大师作品的DVD。刚看到时,站在货架前,止不住地发抖:这么多的基斯洛夫斯基!这么多的费里尼!这么多以前只在书上看过的名字!我们像饥饿已久的难民,掠过京城碟店,一茬茬地收割。回家看完,聚会就聊。那是一个急剧补课的时代。世界如一匹宽银幕,在眼前缓缓舒展。
那时聚会,还没有人手一部智能手机,滴滴答答发微博。大家出门,要么带书,要么带碟,见面先问:最近看什么了?犹如两只蚂蚁相见,先以触须互碰,一闻而知,对方是否同类。那时候的时钟走得比较慢,时间挥霍不尽,只能大段大段看书。提到一个作家,饭桌那侧总有人应声而起,伸手来握:我也喜欢他——这触须互碰的片刻,如此珍贵,在当年,一个个赶稿崩溃的深夜,提醒我: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其实,虽然自称吃货,所吃饭馆并无奢侈名馆,人均五十的自助餐己算昂贵,因为座中还有学生。饭馆同时要满足如下需求:能容纳四五十人的包间、过十一点不打烊。为了找到一家合适的饭局地点,老六曾一下午打掉四分之三的电池。常常是火锅店,或“九头鸟”之类大众饭馆,若是“罗杰斯”,则包下二楼。而无论在哪里,超过十一点,服务员的脸色都会越来越难看,白色塑料桌布被醉鬼的手蹂躏得满目疮痍。地上啤酒瓶林立,打翻的啤酒带着白沫流出来,沿着地上躺着的兄弟,蜿蜒曲折地画出人形。在散场后犹如一场凶杀案的勘探现场。
我开始有了朋友。腥红的、芭蕉、咣咣、天狗……我们交朋友,就是看能否一起喝二锅头。红星二锅头,56度。深绿色玻璃瓶(又是这种绿!),标签是白底大红色块。每一种颜色都饱满,充沛。后来它模仿扁瓶装威士忌,出过款灰色磨砂瓶。拙劣。它不知道自己原先已很美。二锅头的度数像一条拒绝平庸的分割线:要么不喝,要么喝醉。那时,只要有一个人问:谁喝二锅头?应声而起者,于我都格外亲切。犹如一个声明:你们慢慢喝,我们先走一步。烈酒喝醉的,哭和笑都格外投入。喝多,出丑,就消失一段。直到大家与自己都忘掉那次失态,或,有更厉害的,掩盖了这次失态。
和网上的飞扬快意不同,Liar、小白、我,芭蕉、公路……现实中都极沉默,话少得令人难堪。这样的人,相聚一堂,也如独处囚室。我们心怀热情,却像密码不对无法接头的情报员。或者像一个个沉默密封的啤酒瓶,渴望能来一把启子。而酒能帮助越狱,打破孤绝,触到隔壁伸来的另一只手。狂呼烂醉,大概只求这白驹过隙的片刻,我知道你的存在。我知道你的迷惘。
交谈常在酒醉之后开始,在理智模糊的边缘,那是一种超出理性分析判断的友情,我们用所有直觉与潜意识对话、交谈,分辨忠奸。倘若你曾跟人,痛痛快快地醉过一场,那样交上的朋友,总有一种格外的亲昵。
时常已经无话可说,却都不愿散去。门外就是黑夜,人群自有温度。一次酒后,乃哥指挥大家唱罗大佑的《无言的表示》:“风雨中人们,一样的孤单,奔向那无尽的沉默夜晚”,一帮男女认真地、大声地、颠三倒四一遍遍地唱这首歌,那情形,又凄怆,又滑稽。醉后合唱的经典曲目还有《海阔天空》。如果,老六开始眼泛桃花,动情地自抚酥胸,继而,伸出兰花指,那么多半可以期待接下来的罗大佑,《亚细亚的孤儿》《告别的年代》《恋曲1980》《恋曲1990》……罗大佑的歌天然适合在这样的场合合唱,他的音乐里总有一种行军节奏感,音节铿锵,慷慨激昂。
常喝的酒依次为:普煎普通燕京扎啤、二锅头、桂花陈、螺丝刀。姑娘们普遍选二锅头,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啤酒让人发胖。并且,啤酒喝到醉,需要川流不息地上厕所上厕所上厕所。不如喝二锅头,四两,就能让你醉得如愿以偿。更重要的是:它便宜。席上,我和腥红的喜欢点小支装二锅头,简称“小二”,大瓶虽划算,但“小二”,深绿色小扁瓶更具流线美。同时,一支小二一支小二地喝,有节奏感。音乐和喝酒,节奏感都很重要。但喝空两支之后,又无所谓节奏感了。
二锅头好喝吗?难喝。像沙尘暴。但这和北京的粗粝是一个气味,一个体系的。难以想象,在上海的饭馆,会有人喝得躺到桌子底下去。但在北京,这是可以的。这种不体面,只能发生在铺着白色塑料桌布的廉价饭馆,以及喝了五块钱的二锅头之后。当一个城市,件件事都有了统一的风格,就会呈现某种美感,哪怕这风格是由丑陋的元素组成。而究其根本,青春与生命力的绽放,本身就是有力的,哪怕是垃圾堆上的绽放,哪怕是废墟里的青春。这种力量难分好坏、美丑——它只是来了,带着生命力本然的动人,感人至深。
有人酒后磕破了脸,有人摔破下巴,鲜血直流。我的裙子挂栏杆上剐破。咣咣抱着老六在他家的厕所地板上打滚。还有两个姑娘拥抱着滚倒在雪地里,大声说:你是我一辈子的朋友!
那种喝法,就像没有明天。
只有非常非常年轻时,人们才能那么用力地,去喝酒、交朋友、打人耳光,往人脸上泼酒,才能如此猛烈地摧残自己。青春期的人,动作总是变形的,每一样感情的流露都放大了一百倍,爱和恨,孤独与喜悦,都是。
酒上的日子,几位酒神于云端发光。
咣咣。二锅头党,饭局监酒。2013年火锅店的春夜,他说起一次喝多了,他与老六同去厕所,心情激荡,但觉一切都很美好,遂拥抱。觉拥抱尚不足以表达,就亲了老六一口。大家笑得东倒西歪,什么时候的事?咣咣讪讪地:就过年前。啊,难道这么多年之后,咣咣依然如故?
一大半醉酒记忆都与他有关。他的破捷达,曾在北京上演各种惊险:百米逆行、撞电线杆、挡泥板被生生刮掉……那时对醉驾还没概念,但人有求生本能,一般酒后并不开车。最可怕的是他喝得大醉,固执起来非要开车,其他醉鬼如一群小鸟,欢乐地争先恐后地挤上来,就因为他车上放的音乐更好!一个醉汉拉着一群醉汉,在深夜的北京疾驶。如今想来,那犹如一个死亡邀请。死神的天鹅绒华丽黑披风,湿淋淋紧裹着我们。
有次跟史航聊天,他说,咣咣是这种人——如果你中奖得了五百万,可能有人会嫉妒,可是咣咣中奖大家就都服气。是的。大家服气,因为他会把这五百万都用来请喝酒,最后算算还倒贴点。他对待钱、地位、面子、生死,总一派随随便便,不粘滞的清洁。咣咣做过开颅手术,手术完用他老婆手机群发短信,告诉大家他手术失败不治身亡。发现这是个玩笑时,狂怒的老六几乎没把他宰了。
2013年春夜,散场时正逢北京降温,狂冷,众人急急找出租车的空当儿,咣咣与格格拥抱并互把对方抱起,小孩儿玩摔跤般,隔老远听到“咚”一声。七手八脚揪起格格,头上己鼓起大包。那一瞬,昔日重来,十年前的大饭局,要没这么个结尾简直不算完。
听说,摔了格格,咣咣在出租车里哭了一路。在KTV,当瑜老板唱起歌,我挽起格格的手做人浪翻滚,咣咣起身加入我们。我没有遇到第二个男人像他那样,从不怕丢失男性宝贵的颜面,所有这些柔媚动情在他都是自然而然。
咣咣喝酒,有“死便埋我”的痛快,在他心里,只有审美与喝酒是正经事。咣咣是魏晋中人。
腥红的。我在饭局最早交到的朋友。我以为我喝酒就够拼命,她比我还拼。一次酒局结束,外面瓢泼大雨。朋友去开车,我和腥红的笑着,仰着脸,在雨中跳起舞来。跳着跳着腥红的失去踪影,我们找了几条街,最后发现她倒在她家楼下,水泥地上,睡了。一度她信了佛教。后来又成为一名基督徒。她去广州、上海分别生活了几年,最后又回到北京。但当年那个腥红的己不复存在。贯穿这一切动荡的是,她一直写作。
她小说中有一段北京和年轻姑娘的关系,是我看到过最好的一段,写北京的文字:“在北京,一朵花就是在一夜之间横空出世,啪地照亮整片夜空。没有来路,也没有去路,她要么是一朵跳出光线的花儿,成为光本身,要么什么都不是……北京和那些花儿的关系是有些特别的。只有在这些花儿面前,北京有特别卑躬屈膝,特别迁就的一面。是什么?有什么是它没有,所以要向她们得来的呢?……它唯一缺乏的是气味……没有这些花儿连续地、日夜地开放,这座城市将痛苦地面临自己真实的衰老和死亡。”
芭蕉。曾有几条好汉与她拼酒,最后好汉倒卧,她无恙。她喜欢约在三里屯青年旅馆一楼,后来,她和兔子在劲松的住处成为酒鬼们的“欢乐家园”,座中客常满,冰箱酒不空。家中常备一条大红色睡袋,供醉汉使用。我也几次留宿。她并非沙龙女主人,她不艳丽、风情、长袖善舞。她连话都懒得说。她不应酬谁,所以,在她身边,就舒展,自由。所谓“林下风度”,大概就是这样。她和咣咣很像,在对许多事的不粘滞上。但咣咣说,芭蕉其实非常冷血。是的,相比咣咣酒后动辄热泪盈眶,芭蕉无情得多。她不欺人,也不自欺,她有多少热度,就展现多少。犹如冰层下流水,看似冰冷,探手进去却有微温。
芭蕉是平静的亡命之徒。
兔子。小圆脸,成都女子,皮肤极好。那两年,她仿佛饭局的盆景。一推门,就看见她盘坐桌上,在一堆盘碗碟盏之间,缓缓起势,把双腿放到自己肩头。或者站在地上,把腿搁在别人肩膀上。她的脚神出鬼没,出现在种种匪夷所思之处。比她的脚更匪夷所思的是她的直接。她的那种直接,会被不敏锐的人误认为放纵,只有很深的世故,才能看出她的单纯。
当年这些酒中仙,如今只有咣咣一人,仍徜徉酒海。我有时会诧异,所有人都变了,他何以不变。继而想,所谓“智极成圣,情极成佛”,他之纯粹,接近得道。
还要写一个人,虽然她不喝酒。1995年时,我最喜欢的一份报纸叫《音乐生活报》,投稿,写黄舒骏,发表了。足足快乐了一个月。十几年后,认识当年报纸的编辑,重返61号公路。她在一个荒诞的年代,仍不合时宜地保存了哥特气质。她之哥特,不是穿鼻钉化浓妆,而是骨子里的狂狷。杨葵看《寻找小糖人》,说看R0drigLlez想到她,因为那“半属半羞涩的表情”。准确。她永远穿黑衣服,抽中南海,微笑看醉汉玩闹。公路不太喝酒,对我们这群醉汉,却有舍命陪君子的气概——她是少有可用“气概”形容的女子。她的情感像一尊颈窄口狭的古瓮,贮存极深,却耻于言说。公路不喝酒,但比醉汉还疯狂。她近视,不戴眼镜,高速公路敢超过两百迈。去京郊爬山,盘山路极窄,她眯着眼把车开得虎虎生风,每一次对面来车,都惊险万分。和芭蕉的亡命不同,公路是玩命。
这么多年,公路,也没变。只比当年更削瘦。仍穿黑裙子,抽中南海。眯着近视眼半蔑视半含笑地看着世界。她也是我认识的少有的知行合一者。她之原则,如上阵带兵,无形在她与别人之间划出边界。这条线划得凛然,也杜绝了人生种种情感变得雾数。很奇怪,是在一个女人身上,我看到古龙说的“风骨”。
还有那些北京的过客,一次次犹如流星闪过。每个外地网友到来的日子,也必定是饭局之夜。在广州的桑格格说,那时下飞机,都是直接投奔饭局。想到北京有这样一群人,就觉踏实;欢送土摩托赴美饭局,在“九头鸟”一间地下室,推开门,看到四十多头吃货,蔡一玛说:那是她第一次参加饭局。惊恐地看着眼前,她懂得了什么是江湖。
是的。江湖。那是饭局的另一面,更复杂更无以言说。对于新人,它就是一个江湖。我该怎么描述一个新人在其中感受的一切?自卑、失落、惊恐、仓皇、焦虑……就像成长从你身上揭掉一层皮,鲜红的嫩肉和密密麻麻的神经丛都裸露在外,一螫一跳。我的每一次喝醉也是壮胆,笨拙的演员只有喝醉才敢上场。散场后,在深夜,一个人长路迢迢回住处,呕吐,刷洗被吐脏的地板和鞋。这独处的空白像对之前盛宴的消解和清洗。在一次次饭局和一个人的空白之间,时间过去,新的皮肤长出来,我开始能看懂更新的人,他们第一次落座时的眼神,也有仓皇,也有欣喜。
庆幸我遇到的是这样的江湖,这样的论坛。是啊,光我遇到论坛的黄金时代,已经值得庆幸。和“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式的博客、碎片化的微博比,论坛时代,更像一个众声喧哗的班级,它就是用来亮活的。
那也是我写作最不费力的时候。第一本书《我们的主题曲》,许多文字写于那时。不用构思,像被一股热气推着走,一气呵成。想要绽放的欲望压倒一切,就像迫不及待要在他们面前展示洒量(为此我曾一口气干掉一杯扎啤)。不只是我,而是,几乎所有人都陷入一种迷狂的写作状态,老六的《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写于那时,芭蕉为长篇小说《天使记》的修改而频频约人喝酒。那时的人,看完一个话剧,晚上就抛出一个上万字的帖子,第二天我们拜读毕,动辄就回几千字……虚荣也好,绽放也好,我再也没遇到过那么多写得好的,聚在一起,几乎是迫不及待地交流、迫不及待地拼文字。那种迫不及待里,有一种仓皇,仿佛一个短命天才,预知自己时日无多,爆发式地写作。果然,进入博客时代,他们消失一批。微博又不见一批。
我怀念那个短暂的绽放,好像八十年代的文学热——一条长长伏线,隐埋身世,在新世纪头一个十年登场亮相,事了拂衣去,飘沓如流星。
转入2003年,遇到非典。大街上空空荡荡。我们仍然喝酒、爬山,路上有人发烧,全体人员都视死如归。非典之后,时钟突然拨快。街上行人变得匆忙。房价起飞。夏利取消。有一度,聚会时空气里嗡嗡震动的不再是黑泽明七武士,而是房子啊房子。最初,饭局上谈论房子,还会被鄙视。到06年,房价飙过两万,大家如梦初醒,房子的嗡嗡声再也压不住——现实,以排山倒海之力,长驱直入。一碗面条要十五块的时候,你是无法坐而谈论小津安二郎了。旧建筑越拆越多,新建筑里没有我们的一席之地。北京犹如一个气球,被无限地吹大,我们是气球上的图案,随着它的急剧膨胀,脚不沾地飞向四环、五环、管庄、通州、燕郊、香河、天通苑、回龙观,“所有星云都在彼此互相远离,而且离得越远,离去的速度越快”。碟店关门,DVD濒临灭亡。朋友们陆续皈依佛教或基督教,我戒了酒。许多人开始信风水占星宿命。有人在中年改名,希冀改运。有人跳槽,跳来跳去总是不满意。一半的人都换了工作,甚至行业。老六只是其中之一。他砸掉体制内工作,出来做报纸,倒闭,自己做《读库》,沉静下来。有人创业。有人破产。有人换房子。有人失恋。有人离婚。有人再婚。有人酗酒。有人患抑郁症。有人染上赌瘾。有人自杀。有人猝死,在他的葬礼上,据说有人,握手,泯恩仇。
之前的饭局犹如一场大梦。真正的生活,早在无声无息之间来临。
谁曾在年轻时到过一座大城,奋身跃入万千生命热望汇成的热气蒸腾,与生活短兵相接,切肤体验它能给予的所有,仿佛做梦,却格外用力、投入。摸过火,浸过烈酒,孤独里泡过热闹中滚过。拆毁有时,被大城之炼丹炉销骨毁形,你摧毁之前封闭孤寂少年,而融入更庞大幻觉之中;建造有时,你从幻觉中寻回自己,犹如岩石上开凿羊道,一刀一刀塑出自己最初轮廓;烈火烹油中来,冰雪浇头里去。在现实的尘土飞扬与喧嚣之中,你迟早会有一瞬,感到自己心中的音乐,与这座城市轻轻共振,如此悠扬,如此明亮。谁的生命曾被如此擦拭,必将终身怀念这段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