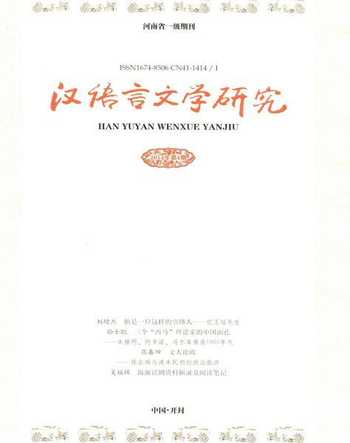鲁迅“杂感”文体的确立与文学观念的变迁
王晨辰
摘 要:“杂文”作为鲁迅最重要的文体之一,并非是一个同质的存在。鲁迅使用的“杂感”、“短评”、“论文”和“杂文”等的概念之间有着细微的文体差异。本文从较为复杂的“杂感”文体入手,并以1925年为鲁迅思想和杂文文体变化的关键时间点,讨论其“杂感”在文体上的确立过程以及它与“论文”、“短评”之间的关联与差异。文体变迁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思想的转变,本文将探讨鲁迅“杂感”文体的确立与其文学观念变化之间的复杂关系。
关键词:鲁迅;杂文文体;杂感;文学观
引言
“杂文”被公认为鲁迅最重要的文体之一,无论在论述的内容还是文章的体式上,都对后来者的“杂文”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杂文”在鲁迅那里并非是一个同质的存在,也非一出手就确立了写作的范例。陈平原认为相比于其他体裁,鲁迅杂感的体式是“很杂乱”的,并认为鲁迅所指称的“杂文”分为两类:一是“不管文体”的文章集合,二是独立的文章类别{1}。本文主要是从文类的角度讨论鲁迅的“杂文”。不同于研究界将他除小说、散文之外的文章统称为“杂文”,鲁迅有自己的概念,并细致地将他的文章称为“杂感”、“短评”、“论文”和“杂文”。仔细辨析他所指称的不同类型的文章,确实存在不同的体式。本文所使用的术语包括“论文”、“杂感”、“论战文”、“短评”等,全部回归鲁迅使用这些词语的意义。
从头开始考察鲁迅的“杂文”写作历史,从“新青年”时期的“短评”和《坟》中收录的“论文”,到1924-1925年的《华盖集》,文章的写法有着显著的变化。同时,他在《华盖集·序言》中提到自己行文的一些变化:“意见大部分还是那样,而态度却没有那么质直了,措辞也时常弯弯曲曲,议论又往往执滞在几件小事上,很足以贻笑于大方之家。”{2}我们可以发现《坟》、《热风》与《华盖集》在文体上的不同。这三本杂文集所收录的文章既有时间的先后顺序,又有在同一时间创作出不同文体,随后被编入不同文集的现象。按照时间顺序编年,1925年成了鲁迅杂文创作突出的时间点:一方面是杂文创作的数量明显高于前几年,另一方面,杂文文体也较为多变③。木山英雄把鲁迅散文“已经完全确立了内在的自由”的时间点定为1926年,这是以他的整体散文为考察对象而言。具体到他的杂文写作,1925年的变化已见端倪。{4}1925年之前,鲁迅的杂文多为《坟》中的“论文”形式,以及《热风》中的“短评”系列。1925年,出现了《忽然想到》、《这个与那个》、《补白》、《咬文嚼字》一类的文章,它们大多由几个并列的社会批评组成,各部分之间又有内在的关联。相比于《论雷峰塔的倒掉》、《论睁了眼看》等论说性质的文章,笔法多转折与漫衍,结构更松散,行文更自由灵活。这种文体并非凭空而至,它与“论文”以及“短评”之间的关系,可以细加辨析。1925年,鲁迅卷入了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写出了一系列的论争文章,由此开创了论辩式的杂文文体。他在1925年之后杂文创作的主体基本上可以被以上提到的几种类型涵盖,在具体的文章中会略有差异,不过也只是几种文体之间的“创造性转化”。为了方便讨论,本文在考察鲁迅“杂感”的建立过程时,先从1925年这一转折点入手,并以此在时间上加以回溯和延伸。
当然,1925年的杂文中也包含有其他的体式。如有几篇类似《野草》的文章,如《战士和苍蝇》、《夏三虫》、《杂感》、《长城》,这类文章在鲁迅之后的杂文集中几乎消失不见,究其原因,可能是同时编辑《野草》和《华盖集》两本集子,存在选择上的标准问题,也可能受同时期写作《野草》的影响,惯于写作此类文章;语录体文章,如《论辩的魂灵》、《牺牲谟》、《评心雕龙》;书信体文章,如《通讯》、《北京通信》、《答KS君》;《青年必读书》则是表格的形式。由于此类文体不占他杂文文体的主流,在此不细加分析。
文体变迁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思想的转变。回到《华盖集·题记》,鲁迅解释这种笔法变化的原因:“我幼时虽曾梦想飞空,但至今还在地上,救小创伤尚且来不及,那有余暇使心开意豁,立论都公允妥洽,平正通达,像‘正人君子一般;正如沾水小蜂,只在泥土上爬来爬去,万不敢比附洋楼中的通人,但也自有悲苦愤激,决非洋楼中的通人所能领会。”{1}这表达了鲁迅对于文体的某种期待,为的是“我活在人间,又是一个常人”{2},因此论战之文在他就有了意义,《忽然想到》之类的“漫谈”、“漫说”文章,也在情理之中。我们再反观《坟》,它的《题记》和《写在〈坟〉后面》都强调,这里面收录的文章“不过是我的生活中的一点陈迹”③,“此外,在我自己,还有一点小意义,就是这总算是生活的一部分的痕迹”{4}。由于这两篇文章都写于1926年,鲁迅回头整理《坟》中的旧文,已然有种“今之视昔”的断裂感,这可以从旁证明他在1925年前后思想上的某些变化。当然,这种变化并不斩截,“埋藏”的另一面是“留恋”,这种左右摇摆的“困惑”之感,可能预示着鲁迅思想的一次“转折”。以文体的转变为因由,牵引出思想选择的可能瞬间,是本文希望达到的目的。
一、论说文与“忽然想到”
鲁迅写于1925年的“论文”有《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论“他妈的!”》、《论睁了眼看》、《坚壁清野主义》、《寡妇主义》、《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另外,《华盖集》中的《导师》也属此类。
鲁迅的《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可以看出他论文的行文特点。由通信得知雷锋塔倒掉的原因,随后感慨中国人大抵患有“十景病”,经过一系列材料的铺垫后,很快得出全文的论点,后来一转折:“然而十全停滞的生活,世界上是很不多见的事,于是破坏者到了,但并非自己的先觉的破坏者,却是狂暴的强盗,或外来的蛮夷。”{5}他接着讨论两种无用的“破坏”:“寇盗式的破坏”和“奴才式的破坏”,后者正好与开头的乡下人挖雷峰塔一事呼应,由此收束全文。
文章的思路是由某件事引发作者的议论,得出论题,之后围绕此一论题展开讨论,例证大抵旁征博引,但不离正题,结构也井然有序,层层深入。这种紧凑周密的论述是典型的“正论文”形式,即“基于正理以立论也”。
另一类论说性质的文章虽也围绕某一“正理”,但议论稍有枝蔓,结构上也更为自由。此类文章以《坟》中的《看镜有感》、《春末闲谈》和《灯下漫笔》为代表。《看镜有感》与之前相比,行文显示出某种变化。文章从自己翻出一面古代铜镜说起,由此说到“海”字的用法,接着谈汉、唐、宋、清对待外国事物的态度,不时讽刺现代保存“国粹”的行为。随后一转,回到“铜镜”,包括推断“铜镜”正在逐渐被“日用镜”取代的命运。之后又回到“宋镜”,由其简陋,引发“自出新裁”和“取材异域”的议论,最后一段又转回到“铜镜”的典故上,暗讽“国粹”,以“这一点终于猜不透”作结,留下回味的尾巴。
文章的论题虽然在结尾出现,但其间的讨论已经时有支离,由一代说到另一代,再以一转折往复回来,回到什物本身,结论的得出也是顺水推舟之事。相比于正论式文章明晰的行文逻辑,此类文章往往从事物的叙述中慢慢推出“正理”,而叙述的过程则比较自由,看似信手拈来,其实暗扣论题,这是一种更为灵活的论述方式。
形式上更为松散的一种类型是《从胡须说到牙齿》和《杂忆》。《杂忆》由四个部分组成,每一部分之间靠某一关键词连接,这符合联想的特点。第一部分说到英国诗人拜伦在清末中国被接受的原因与当时的革命思潮有关,接着叙述一番当时流行的应革命而生的诗文书籍,以及它们实际上于革命的用处很小。这一部分已经表达了完整的意思,可以自成一篇小型的议论文。第二部分与第一部分在叙述上有时间的联系,分别是革命前文学的种种宣传和革命兴起以后的事,以“革命”一词相连接,仍围绕“复仇”讨论。第三部分的开头以“复仇”接上文,同时立论,之后转而谈及“复仇”问题。第四部分开头说到中国人不向强者反抗,却向弱者发泄的问题,就与上部分的翻译动机相呼应。但两部分不是直接承续,而是用“毋友不如己者”一句岔开,由此说起,再巧妙地暗合第三部分,由于所开的题目不同,议论的结果必然不同,最后的结论则转为对国民“智”与“勇”的期待。这既是此一部分的结论,也是全文的结论。
此类文章与上面两种差异较大,近似于《忽然想到》之类文章。它们常常分为几个部分,有些部分可以视为一篇独立的小论文,互相之间用关键词连接;或者另起一头,在论述中又会自然而然返回此前的话题。总体看来,各部分能够围绕着某一中心,似断实续地讨论;各部分可能递进,也可能平行,或者兼而有之,交叉进行;在蓄足了势后,结尾部分的议论往往既是一部分之内议论的延续,又能涵盖整篇文章的讨论。
《忽然想到》达到了鲁迅这段时间写作的文章体式的灵活和跳跃的极高程度。其中的一至四和五至六是社会批评,七至九和十至十一则是论战之文。和《杂忆》相比,《忽然想到》(一至四)可以见出形式上进一步的发挥。
《忽然想到》(一至四)中的第一部分开头:“做《内经》的不知道究竟是谁。”以疑问句起首,此乃突兀之笔。接着谈到《内经》和《洗冤录》虽有错误,却被人们奉为经典。第二段又是一个问句:“牙痛在中国不知发端于何人?”于是追溯一段中国的牙痛史以及“我”的牙痛史,然后感慨中国人治牙痛的态度。第三段突然说到康有为主张跪拜一事,联想而及北京恢复杀头。三段之间基本上是并列的,关系在于每段末尾将三件事算作“天下奇事”之一、二、三。第二部分的开头也是凭空而来,“校这《苦闷的象征》的排印样本时,想到一些琐事——”,由此引发“我”对于书应该留白以及学术书中夹些笑话之类的议论。这两部分归为下面的议论:“上述的那两样,固然是比牛毛还细小的事,但究竟是时代精神表现之一端,所以也可以类推到别样。”于是,两部分的材料用“时代精神表现之一端”联系起来了。第三部分出现几段语录体的文字,中心词是“民国”和“国民”,最后一段是这部分的观点:需要好好写一部“建国史”。第四部分接着“史”开始,谈历代杂史记载中的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情形何其相似,接着,文章对于“国民性”是否会改变的问题作了假设:国民性可能会变,然而因为“伶俐人”的存在,中国依然免不掉轮回的命运。文章收束在问句中:“‘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用了这许多好材料,难道竟不过老是演一出轮回把戏而已么?”{1}
文章的第一、二部分是平行并列的关系,两者都是社会批评,第三部分的开头:“我想,我的神经也许有些紊乱了。否则,那就可怕。”{2}一变而为一句一段的形式。第四部分紧承前面而来,由“历史”引发感慨,对于现状的不满,呼应了第一二部分。与《杂忆》略有不同,《忽然想到》系列文章各部分之间虽有勾连,但关系较为松散,段落之间也相对跳脱。如果抽去区分作用的分节数字,《杂忆》尚可以看成一篇论说文,《忽然想到》则更像不同文字片段的类编,各部分之间话题的断裂较为明显。
另外,《这个与那个》则是将四个独立的小型的论文排列在一起,各部分皆以两事对举,包括“读经与读史”、“捧与挖”、“最先与最后”、“流产与断种”{1},以此展开现实批评。各部分之间纯粹是平行关系,关联度甚小。自此,鲁迅将此类“漫谈”性质的文章发挥到了极其自由的境地。
二、鲁迅论战文的产生
1925年杨荫榆出任女师大校长,她的一系列行为很快引起了学生的不满,于是引发“女师大风潮”。鲁迅公开支持学生的反对运动,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开辟“闲话”专栏,对“女师大事件”表达了与鲁迅不同的态度。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笔战开始。他收在《华盖集》中的论战文都是与“现代评论”的交锋之作,包括《“碰壁”之后》、《并非闲话》、《我的“籍”和“系”》、《咬文嚼字》(三)、《“碰壁”之余》、《并非闲话》(二)、《十四年的“读经”》、《并非闲话》(三)、《我观北大》、《碎话》、《“公理”的把戏》、《这回是“多数”的把戏》。
《我的“籍”和“系”》可以看出论战文与“漫谈”体的关联。文章从中国人引经据典的妙法说起,笔法与其他的“杂感”相同,用“至于近事呢,勿谈为佳,否则连你的籍贯也许会使你由可‘尊敬而变为‘可惜的”{2}引出论辩事由。下一段岔开一笔,转而写到宋人不准南人做宰相一事,“至于‘某籍人说不得话,却是我近来的新发见。”③转回话题,之后开始摘录引用陈西滢的原话:
于是乎我说话了,不料陈西滢先生早已常常听到一种“流言”,那大致是“女师大的风潮,有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现在我一说话,恰巧化“暗”为“明”,就使这常常听到流言的西滢先生代为“可惜”,虽然他存心忠厚,“自然还是不信平素所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无奈“流言”却“更加传布得厉害了”,这怎不使人“怀疑”呢?自然是难怪的。{4}
句子之间的关联词很多,并且以转折词为主。如“不料”、“恰巧”、“虽然”、“无奈”、“怎不”,最后用“自然”,在语义上迂回而来。
后面两段围绕“我”的“籍”和“系”展开,接着引出对“挑剔讽刺”这一批评的辩驳,“何以一有流言,我就得沉默,否则立刻犯了嫌疑,至于使和我毫不相干的人如西滢先生者也来代为‘可惜呢?”{5}与之前的“现在我一说话”相呼应。再由此想到古代关于“流言”的“鬼格言”,接着有一段关于“尊敬”的议论,文章的中心论题出现于结尾处:“然而无论如何,‘流言总不能吓哑我的嘴……”⑥
这样的论战文章在写法上与其他的“杂感”相差无几,不同处在于,论敌的话引出感想或者成为表达观点的材料,并用论敌惯用的词语充当句子成分。文章各部分之间转折虽多,仍互相呼应,其间有引经据典之处,亦有直接的议论,有岔开一笔的写法,亦有属文连类的自然联想,不过各部分大致围绕中心议题展开。
《并非闲话》是一篇更复杂的论战文。文章开头即说明写作的缘起:女师大学潮后,“我”与“现代评论”的反应不同。之后引用了一段“要紧”的“闲话”,对此,鲁迅先说陈西滢有“超妙的识见”,因为相信“流言”与不查籍贯。这里的辩驳主要在“语言”使用的层面。接着对陈西滢以“偏袒一方”为“可惜”一事作出解释,之后突然一转:“可惜的是西滢先生虽说‘还是不信,却已为我辈‘可惜,足见流言之易于惑人,无怪常有人用作武器。”{1}转到“流言”的话题。
之后转向驳斥陈西滢的另一条说法,即把学校比作“臭毛厕”,鲁迅抓住这个论断中包含着的“饭店开会”和“把守校门”两件事的时间先后问题,认为陈西滢的说法违背了事实,可以看成是“偏袒”。然后绕回到“偏袒”二字上:
其实,“偏袒”两字,因我适值选得不大堂皇,所以使人厌观,倘用别的字,便会大大的两样。况且,即使是自以为公平的批评家,“偏袒”也在所不免的,譬如和校长同籍贯,或是好朋友,或是换帖兄弟,或是叨过酒饭,每不免于不知不觉间有所“偏袒”。这也算人情之常,不足深怪;但当侃侃而谈之际,那自然也许流露出来。然而也没有什么要紧,局外人那里会知道这许多底细呢,无伤大体的。{2}
虽由“偏袒”一词引出中国“人情”的议论,但锋芒处处暗指陈西滢和杨荫榆等人。之后谈到解决学校风潮的办法:先关闭饭店。最后又一转:“但是,世上虽然有斩钉截铁的办法,却很少见有敢负责任的宣言。”又是一通社会批评。
鲁迅在文中发挥了“杂感”中常用的“咬文嚼字”的写法,将对方话语中的“关键词”作出抽离语境的理解,以证其言辞不通或自相矛盾,进而认为其用心险恶。《并非闲话》中有一段:
可惜的是西滢先生虽说“还是不信”,却已为我辈“可惜”,足见谎言之易于感人,无怪常有人用作武器。但在我,却直到看见这《闲话》之后,才知道西滢先生们原来“常常”听到这样的流言,并且和我偶尔听到的都不对。可见流言也有种种,某种流言,大抵是奔凑到某种耳朵,写出在某种笔下的。③
此段围绕“流言”引发议论,说明陈西滢等辈对待“流言”的别有用心,并揭示出“还是不信”、“可惜”、“常常”等修辞的虚假性。
这篇文章由论敌的论断起,指出其中的用词错误以及事实错误。鲁迅有时会因为词语上的联想而岔开议论,议论的方式则与其他“杂感”相同,不同在于议论的机锋暗指具体讽刺对象。他喜欢寻找对方在措辞上的漏洞,在短暂的议论以及辩驳之后,往往又会回到对方的其他说法上,再次辩论。鲁迅主要是抓住对方语言上的问题,一般不深究其背后的逻辑。由于对方不同的言论在“文字”上有所关联,鲁迅在议论的时候往往将相关的内容联系起来一起讽刺。文章有一些关键的词语贯穿始终,但没有中心论题,谈到哪里就到哪里。这样的文章缠绕在“文字”之间,兜兜转转,“抒情释愤”。
关于卷入这场笔战的原因,他的说法是:“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4}这里的意思是,“正人君子”们把“公理”、“正义”等宏大的词语作为压迫对方的手段,这些名词内含着道德优势,但只是虚假的“面具”,用来压制对方,构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强权”。鲁迅写作论战文就要揭去对方的“面具”,“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他在《华盖集续编·小引》中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你要那样,我偏要这样是有的;偏不遵命,偏不磕头是有的;偏要在庄严高尚的假面上拨它一拨也是有的,此外却毫无什么大举。”{5}反对“遵命文学”和“庄严高尚的假面”,都可以见出他反抗由文字形成的各种形式的“强权”。
鲁迅也承认有“执滞于小事情的脾气”。“李四光教授先劝我‘十年读书十年养气,还一句绅士话罢:盛意可感。书是读过的,不止十年,气也养过的,不到十年,可是读也读不好,养也养不好。”⑥。他在《无花的蔷薇》中更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其实呢,被毁则报,被誉则默,正是人情之常。谁能说人的左颊既受爱人接吻而不作一声,就得援此为例,必须默默地将右颊给仇人咬一口呢?”{1}鲁迅论战文中体现出来的“被毁则报”的“人情之常”,有时不免带有些许偏执与激愤。
相比于从逻辑上“平正公允”地攻击对方,鲁迅更习惯于展开语言攻势,以自己的言语系统直接攻击对方的言语系统。对方的言语系统被他视为需要揭去的“绅士”的面具,以此露出“本相”。这样的文章写出来自然是嬉笑怒骂、酣畅淋漓,但由于其主要作用于对方的语言与人格,未能触动立论的根基,辩论的实际效果恐未必佳。
三、“论文”与“短评”
在《华盖集》之前,鲁迅编过两本杂文集:《热风》和《坟》。《热风》收录的是他在1918年到1924年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以及《晨报副刊》上作的“短评”,《坟》中所收的文章被他称为“杂文”或者“论文”。鲁迅对于“论文”和“短评”存在着区分,《写在〈坟〉后面》说:“于是除小说杂感之外,逐渐又有了长长短短的杂文十多篇。”{2}“杂感”指《热风》中的文章,“杂文”则是《坟》中的“论文”。
鲁迅在留日期间,写过几篇论文,包括《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和《破恶声论》,其中部分收录《坟》中,这种论文以说理为主,间或采用相关论据。到了五四时期,他为《新青年》写作“短评”,虽说是“评”,但也有相对稳定的体式,文章一般由一件事或一句话引起,由此又想到其他的材料,最后得出某些结论。表面上“有感而发”,其实内含着自己的判断。③与他之后的其他杂文相比,“短评”受限于篇幅,观点往往来得较快。再看《坟》中写于1918、1919年的《我之节烈观》,尚是标准的议论文,直到1924年的《论雷峰塔的倒掉》、《说胡须》、《论照相之类》等文章开始有了变化。论文不单以说理开头,也可以由一时事引入正题,这可见《热风》中“短评”的影子。之后的论文越发向“漫谈”的方向发展,于是有了上述从“论文”到“杂感”的变化。
“短评”有时也会被鲁迅称为“杂感”,因为鲁迅在广义上用“杂感”称呼自己除“论文”以外的文章。这似乎更为强调《华盖集》对《热风》笔法的延续。然而,《热风》中的“短评”与《华盖集》中的“杂感”实不能混为一谈。“短评”受制于篇幅,往往很快进入论题,且每一时事的指向基本一致,一般不会出现岔开一笔的现象,而如上分析的“杂感”则有着更为复杂的文章架构。例如,《随感录》(五十八)一开始引他人的反面议论:“人心不古”,之后用了两则历史材料,说明中国的人心“古已有之”,最后感慨“中国式理想”在现今难以实现{4}。写作思路可谓清晰而简单。这样的“短评”更多提供的是一种发挥议论的思路,不可能直接过渡到“杂感”。鲁迅强调的是以《华盖集》为代表的“杂感”,背后延续的是“短评”“纵意而谈”的内在自由。
鲁迅在1918到1924年1月之间,既写作“短评”,也写作“论文”,数量上以前者为主,两种文体是独立平行、互不影响的。这之后,他开始把“短评”手法融入“论文”之中。从时间上看,可以明确见出这种趋势的是写于1924年10月28日的《论雷峰塔的倒掉》,此时他已经停止了“短评”写作。
且看《论雷峰塔的倒掉》,开头即是“短评”的口气:
听说,杭州西湖上的雷峰塔倒掉了,听说而已,我没有亲见。但我却见过未倒的雷峰塔,破破烂烂的映掩于湖光山色之间,落山的太阳照着这些四近的地方,就是“雷峰夕照”,西湖十景之一。“雷峰夕照”的真景我也见过,并不见佳,我以为。{1}
之后围绕白蛇传说以及“我”在感情上一直希望雷峰塔倒掉展开,最后讽刺了法海不该“横来招是搬非”,躲在蟹壳里出不来。此外,同样写于1924年的《说胡须》、《论照相之类》与此相类。
《华盖集》之后的《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收录的是包括“漫谈”和论战文的“杂感”。三十年代,鲁迅为《申报·自由谈》写作了一系列“短评”文章,体式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揭载的刊物有些不同”,以短小的篇幅适应新的栏目风格。之后,由于“杂文”热,他又以《坟》中“立论”的形式写了一批文章,包括《拿来主义》、《门外文谈》、《中国语文的新生》、《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等。鲁迅的三种主要杂文文体——“论文”、“短评”、“杂感”——分别出现在《坟》、《热风》和《华盖集》中,三种文体之间彼此又有着时间上的过渡关系。1925年,鲁迅的这三种文体都已出现,这确乎是他杂文写作的一个关键时刻。
四、“出了象牙之塔”
鲁迅写于1907年的《摩罗诗力说》,可以视为其文学观念的起点。他表彰了“纯文学”,“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同时,他构建了一个从“个人”(“精神界之战士”)到“群体”(“凡人”)的思想路线。“盖诗人者,撄人心者也,凡人之心,无不有诗,如诗人作诗,诗不为诗人独有,凡一读其诗,心即会解者,既无不自有诗人之诗”。诗人作诗,然后凡人“心即会解”,“美伟强力”则得以发扬,污浊之平和“则得以破除”,“人道”也就立起来了。文章总结摩罗诗人“统于一宗”:“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2}诗人所发之“雄声”,作用于“国人”,从而作用于“其国”。文章描述的是由“个人”及于“民众”的“启蒙”过程。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到《呐喊》时期的小说创作的目的是:“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③鲁迅在1924年之前主要抱持“启蒙”的文学观。
鲁迅在《华盖集·题记》中写到自己文字上的变化,对此的解释是:“然而那又有什么法子呢。我今年偏遇到这些小事情,而偏有执滞于小事情的脾气。”遇到的“小事情”,当然包括陈西滢、章士钊等人对他的污蔑,这是文章变化的外部原因,更关键的则是“偏有执滞于小事情的脾气”。《题记》接着解释了这一点。他幼时曾经“梦想飞空”,但至今仍在地上“救小创伤”,“也自有悲苦愤激”,这一段比喻写出了他文学观的变化过程,此时的他更关心身边的“小事情”。{4}《华盖集续编·小引》中再次提到了自己文章的写法:文章写的是“我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说的”,以此来“释愤抒情”,并不理会所谓“宇宙的奥义和人生的真谛”{5}。无独有偶,《有趣的消息》中说:“厌世诗人的怨人生,真是‘感慨系之矣,然而他总活着;连祖述释迦牟尼先生的哲人勗本华也不免暗地里吃一种医治什么病症的药,不肯轻易‘涅槃。”⑥他认为并没有真正超脱尘世的文学,那些关于生死的言论都必须以生存为其根本。鲁迅此类表达可以概括为“我活在人间,又是一个常人”。
他在《华盖集·题记》中所叙述的“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云云,强调的是“杂感”写作的畅快淋漓,合乎秉性。1924-1925年翻译的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一书中提出的“社会批判”,也与他这一时期的想法相吻合。“出了象牙之塔”后的鲁迅选择了“杂感”一类的时事批评。这一方面体现为他将主要的写作精力放在杂文上,另一方面,也影响了杂文文体内部的笔法变化。不同的杂文文体,其写作风格与承担的功能有着细致的差异。鲁迅杂文写作的起点是《热风》中的“随感录”,同时写作的还有《坟》中的“论文”,前者以实事而起评论,后者则由论点而起,1925年后逐渐演变为几件时事串联而成,以及与对方论辩的新的杂文形式,可谓是“短短的批评,纵意而谈”。这不同于“论文”,被称为“杂感”,延续的是《热风》的写作方式。这种转变的背后一方面是杂文写作手法的熟练以及自觉的文体经营;另一方面,走出了“象牙之塔”,从而“活在人间”的鲁迅,其杂文关注身边小事,坚持社会与实事批评。这种选择从1924年已开始,于是“论文”中逐步渗透进“短评”的因素。1925年的文章则更“散”,发展到“漫谈”和“忽然想到”。
鲁迅在《华盖集续编·小引》中说:“还不满一整年,所写的杂感的分量,已有去年一年的那么多了。”{1}可见此时其主要创作重心在“杂感”上。《华盖集续编》中删去了《大衍发微》一篇,《而已集》则重新收录了此篇。从选择文章编辑集子的标准言,到了《而已集》时期,鲁迅界定的可以入集的“杂感”范围逐渐扩大,以至于他收录了此时所有落实在纸上的文字,正如《而已集·题辞》所言:“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而已集》编于1928年,此时的“杂感”已然成为他对社会发言的唯一文体。至此,鲁迅终于在“出了象牙之塔”后,在旧有文体的基础上,以及时事的刺激下,确立了新的适合于自由表达与言说的“杂感”文体。
“活在人间”的主张背后是他对于“文学”功用的反思,鲁迅在这一时期的文章中开始思考自己所写的究竟是“真话”还是“谎话”,以及文字表达的可能性问题。
从《无花的蔷薇之二》开始,鲁迅杂文的关注点由讽刺“现代评论”派过渡到评论“三一八”事件。之前的学生运动虽然猛烈,当局尚不敢直接采用武力。这次学生请愿,在执政府门前被开枪打死,随即在当时文人圈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应,更有陈西滢等人在报上公开为政府辩护。周作人将这种情况归因于“北京的智识阶级——名人学者和新闻记者变坏了”,“五四之役,六三之役,学生们烈烈轰轰闹得更要厉害,那时政府只捉了几个学生送交法厅,或用军警捕捉讲演的学生送往北大三院监禁在那里:那时为什么不开枪的呢?因为这是舆论所不许。”{2}而鲁迅的反应则集中到了文字效力的问题上:“已不是写什么‘无花的蔷薇的时候了,虽然写的多是刺,也还要些和平的心。”他将“墨写的”与“血写的”相对应,认为前者终抵不过后者。最后他感慨:“以上都是空话。笔写的,有什么相干?”③接着他在《怎么写——夜记之一》中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血写的文章,怕未必有罢”。“墨写的”文章本“应该和时光一同消逝,假使会比血迹永远鲜活,也只足证明文人是侥幸者,是乖角儿”。{4}为纪念“三一八”惨案,鲁迅写作了一系列文章,其中不乏对暴力事件的愤怒之情,亦有对于“笔写的”价值的怀疑。之后,他在《革命时代的文学》这篇演讲录中明确表达了“文学无用”的观点:“加以这几年,自己在北京所得的经验,对于一向所知道的前人所讲的文学的议论,都渐渐的怀疑起来。那是开枪打死学生的时候罢,文禁也严厉了,我想: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即使幸而不被杀,但天天呐喊,叫苦,鸣不平,而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杀戮,没有方法对付他们,这文学于人们又有什么益处呢?”{5}其中提到两个现实原因:一是“三一八”事件;二是国民政府设置的“文禁”制度。这让他感到“文学”在“实力”面前的脆弱。
《写在〈坟〉后面》中否认自己的文字“是说真话的”,“我自然不想太欺骗人,但也未尝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大约只要看得可以交卷就算完”。他出于生存的考虑,不想得罪人。“因为,我还没有这样勇敢,那原因就是我还想生活,在这社会里”。同时也害怕自己的东西“毒害了这类的青年”。“我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罢。但也偶尔想,其实倒还是毫无顾忌地说话,对得起这样的青年。但至今也还没有决心这样做”。选择说“真话”还是“谎话”既与现实环境有关,又指涉言说的伦理。鲁迅的策略是“所以我说话常不免含胡,中止”,以馈赠给读者一个“无所有”。{1}相比于“论文”形式的观点鲜明,“杂感”的随意性和延伸性无疑增大了许多,大部分文章以相关事件或话语呼应与勾连,语言上的发挥相对自由,观点的表达倒在其次。这可以视为他在“意见大部分还是那样”时,用“弯弯曲曲”的“措辞”巧妙回避了“真假”问题。
鲁迅在《怎么写——夜记之一》中说:“虽然不过是蚊子的一叮,总是本身上的事来得切实。能不写自然更快活,倘非写不可,我想,也只能写一些这类小事情,而还万不能写得正如那一天所身受的显明深切。而况千叮万叮,而况一刀一枪,那是写不出来的。”{2}这段话表达了两层意思:第一,题材上偏爱切己的小事,这是他此期多次表达的;第二,文字未必能传达出真实的感受,体验是无法用写作表达出来的。他在《热风·题记》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③一方面是写作未必能表达所想,另一方面写作如果应时事而生,它的时效性有限,生命力也有限。既然如此,则大可不必端起一副“文学家”的架子,“就是随便写写罢”。这是“文学无用论”的另一种表达。鲁迅在二十年代的“文学无用”论基本上针对两方面而言:一是“实力”,二是写作本身表达的可能性。
从大体上言,鲁迅接受过两种意义上的“文学”:西方“文学概论”中带有“启蒙”作用的“纯文学”和乃师章太炎以文字为中心的“大文学”。鲁迅此时超越了西方意义上的“纯文学”,趋向以“文字”为中心的、具有现实战斗性的“文章”观念——让“文字”本身,而非某种观念发挥战斗性。这一点在论战文中尤其明显。《华盖集》中的“杂感”发挥了文字本身的联想功能,相互之间有所勾连即可。这既是他在文网下存活的一种方式,也是其写作到达一定阶段后形成的“内在自由”,以此与外部世界保持复杂的对话关系。
结语
“杂感”作为鲁迅1925年写作的新文体,由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论文”和“短评”这两种杂文体式演变而来。随着书写的熟练、时事的变动以及思想的变化,文章的结构渐趋自由灵活,以至发展出诸如“漫谈”一类的“杂感”。与此同时,为了回应“现代评论”派,鲁迅以“杂感”的思路写作了一系列论战文章,延续的是“漫谈”类的写作方式。相比于论辩技巧,他对文章的经营更胜一筹。之后的《华盖集续编》以及《而已集》,在文章的编辑上,他收录了之前所未予入集的文章,这意味着“杂感”文体已然成为其对外部世界发言的主要而又直接的工具。此时,鲁迅的文学观念由留日期间的带有“启蒙”功用的“纯文学”,逐渐演变为以生存为第一要义、以文字为核心的具有现实战斗性的文章。以上所讨论的鲁迅“杂感”文体的确立过程,正是他文学观念变化后的可能结果。
【责任编辑 穆海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