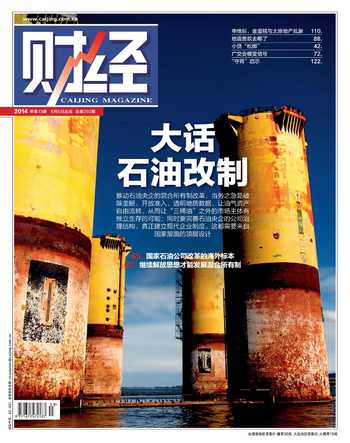为何来中国
审诸历史可见,中国以往虽然孤芳自赏,但并未抹灭其吸收力。西方人带给中国的每一项技术,最终都能为其消化。西方人以专业技术粉饰意识形态,企图强迫中国全盘接受,这正是中国人断难容忍的,即使在中国最孱弱的时候,也意识到依外国条件接受外来意识形态乃是屈从。这种自尊与疑虑是反天主教的先驱沈、杨光先,19世纪的政治家林则徐、曾国藩,以及蒋介石和毛泽东这对宿敌所共有的。
回顾1620年到1960年这段历史,西方人以唯我独尊之姿来到中国。这种优越心态起于两大因素:西方人拥有先进科技,自认师出有名;西方人自认目标崇高,他们的建议是中国迫切需要的,因而一副君临中国的姿态。若是中国质疑其目标的妥适,不接受其建言,他们便不知如何是好,抑或恼羞成怒。
西方人受其愿景驱使,多与中国有很深的情感纠葛,他们要的不只是中国的报酬,但没能认清中国人以契约观点看待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以雇主的身份保留终止双方协议的权利。这点误解会滋生严重的后果。以美国为例,他们曾在晚清和民国积极扮演顾问的角色,却又出现背叛与“失去”中国的论调。不过,美国并未遭到背叛,美国人只不过重蹈昔日覆辙。中国不是美国的禁脔,也不是罗马天主教欧洲、大英帝国和苏联的附庸。傅兰雅、戈登、赫德之辈只不过是胡美、史迪威、托德的前车之鉴。
西方人仍对自己的文明感到自豪,深信自己师出有名,急欲“开发”他们视为落后的民族,这些西方顾问的境遇实可作为借镜。傅兰雅和丁韪良坚忍不拔,汤若望、李泰国及托德精力充沛,胡美和鲍罗廷洞察敏锐,戈登和史迪威精明干练,赫德和魏德迈善于组织,南怀仁和伯驾匠心独运,华尔和陈纳德勇气卓绝,白求恩无私奉献。他们每个人都把一生的精华贡献给了中国。
这些人的故事是警示教训,而非鼓舞人心的宣传。他们个性中的负面特质,如傲慢、急躁、偏执、笨拙、愚蠢,惹得中国人在不同阶段抗拒西方人。还有更深刻的问题有待探索,其中症结不仅涉及在中国工作的西方顾问,还与仍在其他国度试图从事相同工作的人士相关。
这些人的基本动机是什么?希望达成什么目标?为这番事业所付出的个人代价是什么?凭什么前往中国?
当然,其中一个动机是协助中国提振精神或道德的贫困。这似乎是本书讨论的所有西方人共同怀抱的愿望,无论这些人出于自愿或受邀前往中国,还是受上司的青睐被派往中国。协助意味着使中国更像西方国家,使中国按西方人所理解的定义来改变。所以,西方人并不在意他们所触动的一连串事件,而后果是他们根本无力决定的。但是,在他们行动的背后其实有着更复杂的动机,他们的牟利之心不下于帮助中国之心。大多数西方顾问皆有冒险患难与渴望毕其功于一役的性格,这种性格又会因他们在家乡所经历的恐惧和挫折而被激化。中国似乎提供他们发挥的自由,给予他们以一己之力扭转历史的契机,从而证明了他们存在的价值。
多数西方顾问确实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心理满足,可以想见,他们为如此经验付出的代价也很高。即便某些中国人对他们善待有加,但更多人会冷落、蒙骗、敌视他们。每个人都想以某种手段控制中国的命运,但他们终究会明白这是不自量力。他们意识到自己被中国人利用,而不是在利用中国人,他们渐渐被自己的科技专业吞没,会找其他的办法,避而承认他们的期望已落空。其中有些人焚膏继晷,以当下的自得掩盖未来的不确定:有些人痛斥中国人不值得西方伸出援手。
他们凭什么前往中国?他们信心满满,深信自身的文明虽有种种缺点,还是能提供中国所没有的东西。他们之所以有权如此,是因他们有能力、信念及驱动力。随着他们的改变,世界也为之一变,中国自然难以置身事外。事情就是如此。中国若欲抗拒变革,是没有道理的,就好比抗拒潮起潮落或旭日东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人对西方法律及目标的绝对信心已摇摇欲坠,历经越战的美国人对此亦产生动摇,但若就此说西方人的优越感已全然不再,也太过荒谬。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今天的中国似乎已强大到足以让他们确信,若西方人以顾问的身份前来中国,就必须按中国人的规矩行事,绝不坐视西方顾问夹带别的价值观。然而,若是就此以为中国会轻易吸纳他們看似受欢迎的力量,那也同样荒谬。如果中西双方都对自己有新的了解,至少还有机会不让由来已久的误认再度发生。
《改变中国》,(美)史景迁著,温洽溢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4月。本文摘自该书“结论”,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