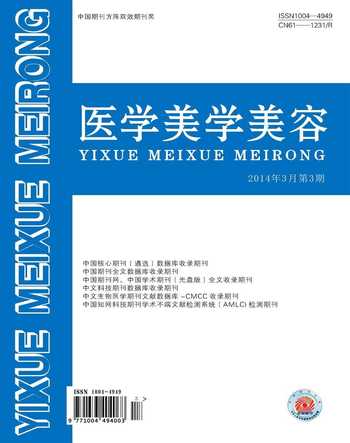抗生素影响肠道菌群研究现状
徐先林
【摘要】肠道菌群与人体健康密切相关。近年来,关于抗生素对肠道菌群组成影响以及导致肠道菌群庞大耐药基因分布和转移研究越来越多。本文就肠道菌群及抗生素对肠道菌群影响现状等相关方面进行综述。
【关键词】肠道菌群;抗生素;耐药基因
【中图分类号】R332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4-4949(2014)03-0461-01
定植于人体肠道的细菌种类及其分布是维持人体健康重要因素。来自于环境和临床的抗生素使用在杀灭和/或抑制细菌生长的同时给予细菌抗生素筛选压力而致耐药基因在各个微生物生态环境包括人体肠道菌群系统中广泛传播,菌群失衡易引发各种肠道内、外疾病。
1肠道菌群结构、功能及影响因素
人体肠道内定植有数量庞大的细菌、病毒、真核生物和古生菌等微生物,它们通过相互影响以及与人体相互作用而组成一个复杂的微生态系统。细菌是肠道微生物的主要组成部分,大约由1000到1150种细菌组成[1]。Eckburg等[2]通过高通量16S rRNA基因测序技术研究表明肠道细菌大部分属于厚壁菌门、拟杆菌门、放线菌门、变形菌门、梭杆菌门和疣微菌门,其中厚壁菌门和拟杆菌门是优势菌门。肠道菌群结构复杂,不同个体肠道菌群组成各异,但人体肠道定植着至少160种细菌[1]。
大多数肠道微生物对人体是无害或者有益的,它们与机体保持共栖或互惠共生的关系,在肠腔形成一个天然的保护屏障抵御病原菌入侵,保护和促进肠上皮细胞发育,产生短链脂肪酸等,因此肠道菌群被称作一个“被遗忘的器官”,对人体健康发挥着重要作用。肠道菌群是可变的,易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研究表明,孕期菌群暴露和胎龄、分娩方式、喂养方式、饮食、环境、年龄、抗生素等[3]都会影响肠道菌群组成结构乃至正常功能发挥。
2 抗生素与耐药基因
自青霉素发现以来,各种抗生素广泛应用于临床、兽医、水产养殖、农业及其它人类活动相关领域中,通过作用于细菌生物合成通路中必要生物分子,如核糖体、拓扑异构酶、DNA和RNA聚合酶、细胞膜和细胞壁、二氢叶酸还原酶等而干扰细菌生长[4]。抗生素大量使用、滥用和习惯性使用导致抗生素不能完全被吸收和代谢,大部分以代谢物形式通过粪便和尿液排放到环境中[5]。在我国多个省份以及国外许多国家环境中都能检测到高浓度抗生素残留物[6]。抗生素直接给予细菌筛选压力,细菌菌群携带着大量的耐药基因并通过不同途径广泛传播。研究表明,耐药基因大多由质粒、转座子、整合子和噬菌体等多种移动遗传元件介导在细菌群体中水平转移,易致各个微生物生态环境组成耐药基因储库。
3 抗生素对肠道菌群影响及耐药基因在肠道菌群间传播
近年来,抗生素使用引起肠道菌群组成结构改变及导致菌群中耐药菌株和耐药基因增多并广泛分布引起全球高度关注。Jernberg等[7]研究表明连续7天克拉霉素使用后肠道菌群拟杆菌属急剧下降,两年内不能恢复到其最初组成状态,而且相关抗性基因erm(B)、erm(F)、erm(G)等增加并持续存在。直接的抗生素筛选压力短期内即能改变菌群组成并导致特异性耐药基因出现并持续保持。环境耐药菌株及其携带的各种耐药基因可以通过空气、水、直接接触,尤其是食物链等[8]方式进入人体肠道而致肠道菌群中耐药基因增多。肠道菌群是一个庞大、复杂的微生物生态系统,细菌个体间紧密接触更利于耐药基因通过水平基因转移在菌群间传播,因此肠道菌群组成一个耐药基因储库,可以介导菌群之间多种耐药基因持续、广泛传播。
细菌间耐药基因交换和转移需要特定的条件,必须保证受体菌与供体菌相互接近并能接纳供体菌相同耐药基因载体(如质粒、整合子)。虽然细菌可以主动或被动交换DNA,但会受到细菌特异的防御机制来抵制外来DNA的入侵以限制基因转移;质粒不相容性也会限制部分质粒介导耐药基因传播。即便细菌顺利交换和转移,外来DNA必须能自我复制或者整合到基因组,否则受体菌并不能表达耐药特性。如Ⅰ型整合子是研究参与耐药基因转移比较热点的移动元件,研究表明[9]即便Ⅰ型整合子能成功在细菌间传播,但当整合酶基因失活时会限制整合子基因盒中耐药基因表达,且整合酶基因表达受SOS修复系统调节。
4 小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肠道菌群结构、功能复杂,且影响因素较多,婴幼儿期是肠道菌群定植的过渡时期,此时期菌群結构将长时间影响机体免疫应答和代谢功能等;新抗生素开发受限,现有的抗生素仍会持续运用各领域中,抗生素耐药及耐药基因会持续在各个微生态系统中广泛分布和传播,人体肠道复杂和高密度的微生物组成无疑是一个耐药基因储库以及促进各种耐药基因转移的场所。
面对肠道菌群结构独特性,研究肠道共生菌群包括有益菌和条件致病菌等耐药菌株分布情况以及其携带和传播耐药基因的方式和途径的差异,对于深入了解和控制肠道菌群抗生素耐药以及对人体的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Qin J, Li R, Raes J, et al. A human gut microbial gene catalogue established by metagenomic sequencing[J]. Nature, 2010, 464(7285): 59-65.
[2]Eckburg P B, Bik E M, Bernstein C N, et al. Diversity of the human intestinal microbial flora[J]. Science, 2005, 308(5728): 1635-1638.
[3]王文建, 郑跃杰. 儿童肠道菌群的建立及影响因素研究进展[J]. 中国微生态学杂志, 2013, 25(006): 727-730.
[4]von Nussbaum F, Brands M, Hinzen B, et al. Antibacterial natural products in medicinal chemistry—exodus or revival?[J]. 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2006, 45(31): 5072-5129.
[5]苏建强, 黄福义, 朱永官. 环境抗生素抗性基因研究进展[J]. 生物多样性, 2013, 21 (4): 481-487.
[6]Bu Q, Wang B, Huang J, et al. Pharmaceuticals and personal care products in the aquatic environment in China: A review[J].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2013, 262: 189-211.
[7]Jernberg C, L?fmark S, Edlund C, et al. Long-term impacts of antibiotic exposure on the human intestinal microbiota[J]. Microbiology, 2010, 156(11): 3216-3223.
[8]Stanton T B. A call for antibiotic alternatives research[J]. Trends in microbiology, 2013, 21(3): 111-113.
[9] Starikova I, Harms K, Haugen P, et al. A trade-off between the fitness cost of functional integrases and long-term stability of integrons[J]. PLoS pathogens, 2012, 8(11): e1003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