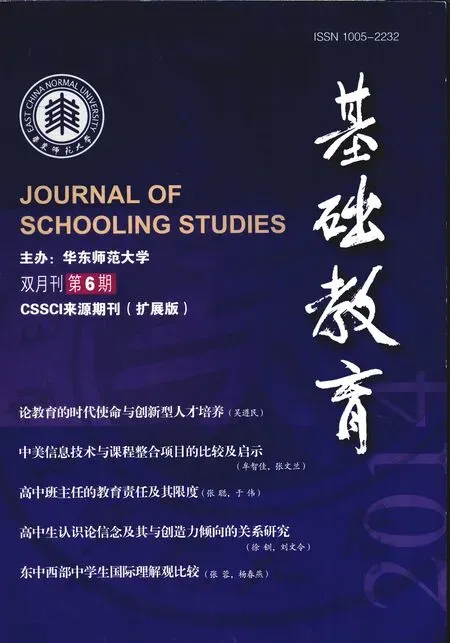政治家型教育家的成长机制寻绎——以张之洞为例*
王喜旺
(河北大学 教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我们身处一个呼唤政治家型教育家的时代,因此,探讨政治家型教育家的成长机制便成为教育理论工作者不得不面对的严肃课题。在中国近代史上,张之洞是一个集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等角色于一身的伟大人物。对于这样的人物,可以用一个恰当的称谓来指称他,那就是政治家型教育家。在笔者看来,作为政治家型教育家,其主要特征是:具有政治家的全局眼光,善于把教育置于整个社会中来思考、实践;具有政治家高瞻远瞩的气度,能够对教育进行超前思考、长期规划;具有政治家的巨大影响力,能够把自己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方案变成区域、国家的教育实践。如果说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呼唤教育家的时代,最为迫切的呼唤应该是对此类教育家的呼唤。因为此类教育家对于整个教育思想“地形图”的变化及教育实践格局的转型具有全局性影响,是塑造整个时代教育大势的人物。从张之洞的成长历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此类型的教育家成长的一般规律。这对于我们当代造就这样的教育家,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下面,笔者不揣浅陋,试对此谈几点不成熟的见解,以求证于方家。
一、教育家人格是政治家型教育家献身教育的不竭动力
张之洞之所以能够成为政治家型教育家,与其诸多人格取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这些人格的萌芽与生长,为张之洞成为教育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使之克服种种艰难困苦,力推其教育思想与实践迈上一个又一个新的境界,终至成为大家。就其要者而言,以下几方面的人格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热爱教育事业。张之洞在进入事功领域后,在浙江乡试副考官任上,能够以“经世致用”为标准选拨人才,为当地营造了士人必为实学的氛围。既赢得了浙江士人的高度赞誉,也对浙江地区实学风气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在湖北学政任上,张之洞大力整顿湖北士子的学风,建立经心书院,提拔、奖励有真才实学的士子,颇得众望。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在成都建立尊经书院,延请名儒,分科讲授,对四川地区的人才辈出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为了能够对更大范围的士人发挥影响力,张之洞专门撰写了《輶轩语》一书,对士人应该如何修养德行、如何读书、如何作文等做了详尽的论述。为了把其治学的金针传于四川的广大学子,张之洞还专门撰写了《书目答问》一书。1881年出任山西巡抚后,深感在整顿吏治、清理财政状况、严禁鸦片、编练军队等事业中的人才不足,竭尽心力创办了令德堂书院,使三晋学子受益者良多。接任两广、湖广及暂署两江总督期间,除了兴办各种实业外,其声名卓著、影响巨大者,即是开办新式学堂。在此期间,他创办了军事学堂、实业学堂、方言学堂、普通学堂、师范学堂、警察学堂等种类齐全、数量繁多的新式学堂。与创办新式学堂并行,在这一时期,张之洞对传统教育的改造也是不遗余力。对经心书院、两湖书院做了适应时代要求的改革,使之由传统的旧式书院逐渐向近代化学堂转轨。在致力于国内教育改革的同时,张之洞还十分重视留学教育,积极提倡、推行学生到国外留学。在向欧美国家派遣留学生的同时,张之洞特别注重派遣学生去日本留学,致使留日中国学生中,湖北籍留学生达千人之多。除了在教育实践领域进行大刀阔斧的兴革之外,张之洞还对教育理论建构经之营之,其最为显著的成果便是《劝学篇》的诞生。在《劝学篇》中,张之洞面对教育领域如何处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这一时代最大的焦点问题,巧妙地借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在当时渐成气候的思维模式作为思想系统建构的工具,对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是什么、如何处理它们的关系、中国的教育发展蓝图如何描绘等问题,都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论述。这就为中国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的教育理论思辨与教育实践走向,确定了“中西融汇”的基本思维范式与实践基调。这对于中国的近现代教育而言,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意义。在政治生涯的最后冲刺阶段,张之洞入主军机,主管教育事务,在全国的教育总体规划,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留学教育等的改革上,耗尽了生命的最后一丝精力。就此而言,我们说张之洞一辈子热爱教育事业,始终对教育事业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高度关注、倾力投入,是一点都不过分的。
第二,超越世俗功利的情怀。对于教育事业的倾情投入,可能有两种动机:一是世俗化的个人功利之心驱使,一是超越性情怀的驱动。在这一分际,教育家的高下立判。考之于张之洞,我们就会发现,其之所以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教育事业中,实有一种高尚的情怀推动着,那就是对祖国的生存、发展的高度关切。对此,四川总督赵尔巽在张之洞去世后盛赞张氏:“其生平精神所寄,尤在振兴教育,储养人才,以备国家缓急之需,而救当世空疏之习。”[1]可见,赵尔巽在此想要说的是,张之洞之所以将其毕生精力致力于发展教育事业,目的在于为国家储备可用之材。这可以说是知人之言。征之于张之洞在不同时期的言论,我们也可看到这一点。
在1885年上呈的《筹议海防要策折》中,张之洞痛切地指出:“宜急筹者三也。”那么,这三条筹策是哪些呢?他的回答是,“储人材”“制器械”“开地利”(采煤铁)。对于这三个筹策,张之洞指出:“斯三者相济为用,有人材而后器械精,有煤铁而后器械足,有煤铁、器械而后人材得以尽其用。”不过,三者相比较,“当时急务首曰储人才”。可见,他是把人才培养作为“自强之道”中的首要内容来看待的。1895年7月19日,张之洞上呈《吁请修备储才折》。在这份奏折中,其写道:“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不蓄而求,岂可幸至?惟敌国愈强,则人才愈不易言。泰西诸大国之用人,皆取之专门学校,故无所用非所习之弊。”[2]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张之洞是站在立国与立学的关系高度,对教育的重要作用进行定位的。一句“古今中外不易之理”,将张之洞对教育之于国家富强所起奠基作用的坚定信仰表露无遗。1896年2月1日,在张之洞即将卸去两江总督之前,向朝廷上呈《创设储才学堂折》。该折很快便得到批准,储才学堂因之得以创立。对于创办储才学堂的宗旨,张之洞认为,是为了给国家“规划富强之本源”。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张之洞看来,“国势之强由于人,人材之成出于学。方今时局孔亟,事事需材,若不广为培养,材自何来”[3]。显而易见,在此时,张之洞对教育事业之于国家强大的重要意义体认更深切,表述更明确了。
总之,正是由于张之洞深切认识到教育事业之于国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他才将毕生精力倾情投入其中。这充分说明,具有超越性的爱国情怀是其热爱教育事业的巨大助力。
第三,对学生的仁爱之心。爱国情怀固然使张之洞不会因为私利而将热情投注于教育事业,给其热爱教育之情赋予了一定的超越品格,但其可能有的缺陷是,易于把教育事业与受教育者作为为国家服务的工具来对待。好在张之洞富有对学生发自内心的仁爱之情,正好可以弥补这一可能存在的缺陷,使张之洞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具备了内在的、人本的指向。张之洞具有自觉的儒家续统意识, 一向以“儒臣”自居。在与友人的通信中,他声称自己“弟儒家者流”[4]。在其撰写文章时,也这样夫子自道,“余当官为政,一以儒术施之”[5]。他不仅以儒学作为自己人生践行的指南, 而且在训诫后代时,也以儒家伦理作为子孙安身立命的圭臬。这典型地体现在为其后代确定的子孙辈二十字排行上,“仁厚遵家法,忠良报国恩,通经为世用,明道守儒珍”[6]。由此可见,张之洞所崇尚的是儒者人格。而在儒者人格中,“仁”是其灵魂与基石。作为儒者人格崇奉者的张之洞,自然有着深沉而博大的仁爱之心。作为一方百姓的父母官, 张之洞时时体恤民情。如其僚属赠白瓜三枚,张之洞食后,生发出如此的感慨,“仙枣曾传海上瓜,今尝珍顽玉无瑕。清凉已足还思雨,尚有农夫转水车”[7]。一次,天降大雪, 则引发出其对民生疾苦、农事堤工的顾念,“既幸汉口粥场空,复愁南楼灯市少” ,“偏心独忧荆襄堤,誓掸人力侯天道”[8]。在这些诗句里,自然流溢的是对子民的体恤、仁爱之情。作为时时关心教育事业的教育家、师者,对学生也有着深挚的爱心。在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如果没有对广大士子的热切关爱之心,不可能在繁忙的政务中,专门抽出余暇撰写《輶轩语》一书,对士人应该如何修养德行、如何读书、如何作文等进行详尽的论述。更不会专门撰写《书目答问》一书,把其治学的金针无私地授予广大学子。在成为封疆大吏后,虽然政务繁钜,但是,只要有闲暇,张之洞总会到书院或考核、督促诸生,或为之讲说文章、提点治学之道。甚至在进入廷枢的行列以后,仍然按季调阅诸生卷牍。对此,其在一封信函中称,“鄙人于每年四季亦得时修旧学商量之业,案牍如山,抽空披览,相隔数千里,恍若对面讨论,诚可乐耳”[9]。如果没有对学生的深挚的关爱之心,哪会在如山的案牍中辟出一片空间为学生披览作品,又哪会在披览学生的作品时发自内心地感到愉悦呢?
总之,在张之洞的生命历程中,热爱教育事业的情怀是其将心血倾注于教育事业的直接动力。而超越功利的爱国情怀与对学生的仁爱之心则作为辅翼,使得其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变得更加持久化、内在化。就此而言,张之洞能够异乎寻常地将毕生精力投注于教育事业,确实是由来有自。
二、权变的智慧为政治家型教育家搭建了长袖善舞的舞台
政治家型教育家的成长不仅需要高尚的人格为其献身教育事业提供内在、持久的精神动力,还需要在教育上建立功业的阔大舞台,毕竟教育家的成就是需要外在的功业证明、证成的。中国近代历史可以说为张之洞献身教育提供了几乎是其他汉人难以企及的阔大舞台。青年时两次任统揽一省教育事务的学政,中老年时几易封疆大吏,生命的最后两年还登上了军机大臣的宝座。不论是在生命历程中的哪一个阶段,时代都为张之洞提供了足以施展其教育抱负、挥洒其教育热情的巨大舞台。这一个个逐渐升高、增阔的舞台,都不是靠侥幸得来的,而是仰赖于其高超的权变智慧。
对于权变的智慧,素来为张之洞所推崇、倡导。如其在不惑之年就倡导,“度德为进退,相时为行藏”[10]。在渐入老境时,更是如此明确申述,“穷则变,变通尽利,变通趣时,损益之道,与时偕行”[11]。不论是主张随着时势地转移决定行藏,还是突出强调顺应时势变化而采取相应的损益之道,都是孔门“通达权变”之要旨。张之洞不仅这样大张旗鼓地倡导权变,更在其政治、教育实践中践行权变之道。这一点,我们从其几个重要的人生转折点上的决策就可看到。
张之洞之所以能够成为政治家型教育家,从清流干将向洋务派人物的转折是第一步。这一步的跨越,正是其审时度势的结果。张之洞从政初期,“皆儒术经常之规,绝不敢为功利操切之计”[12],表现出“清流议政”的特点。光绪初年,张之洞以翰林院谏官入党清流,与张佩纶、陈宝琛等清流大员相互援引,奏弹国家大政、立国本末,成为当时清廷的一股重要政治力量。在平反东乡冤狱、改订《中俄条约》、裁抑阉宦权势等重大政治事件上,张之洞“不避嫌怨,不计祸福,竞以直言进”[13],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被誉为“清流健将”。然而,时局变化之剧烈,正如张之洞所言,“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14]。对此,张之洞清晰地认识到,“方今环球各国,日新月盛,大者兼擅富强,次者亦不至贫弱,究其政体、学术,大率皆累数百年之研究,经数百年之修改,成效既彰,转相效仿。美洲则采之欧洲,东洋复采之西洋”[15]。其意思是说,西方之所以成为“列强”,无非是研究先进国家,相互效仿、调适的结果。由此进行逻辑引申,张之洞满怀信心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只要能够学习西方,革除积弊,变法图强,也可进入富强的行列。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凡普天臣庶,遭此非常变局,忧愤同心,正可变通陈法,以图久大,不泥古而薄今,力变从前积弊,其兴勃焉。又何难雪此大耻。”[16]因此,张之洞对于反对变法图强的保守者,极其不以为然,力斥之曰,“万世之巧,圣人不能尽泄,万世之变,圣人不能豫知。然则西政西学,果其有益于中国,无损于圣教者,虽于古无征,为之固亦不嫌”[17]。可见,在他看来,圣人虽然至聪至明,却也难以预知后世之变。因此,即使西学非圣人所发明,于史无征,只要其是有益国家富强的,亦可采用。正是因为如此,他才果断地从清流的思想桎梏中解脱出来,踏入了“洋务健将”的行列。
戊戌变法的前夜,张之洞刊出《劝学篇》,又是其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正是张之洞在慈禧太后、维新派人士(包括光绪皇帝)等复杂的人事、政治势力格局中,敏锐地洞察到慈禧太后和维新派人士的表面和谐、内里分裂的关系,并预见到维新派人士的步步革新可能触及慈溪太后的政治底线而导致政治上的大变,张之洞才在戊戌变法的前夜果断地刊发《劝学篇》,既向慈禧太后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与主张,表示对慈禧太后政治主张的拥戴,同时实现了与维新人士划清界限,洁身以免祸。这一成功的审时度势既使其保住了封疆大吏的高位,又使其赢得了广泛的文化声誉,可谓一石二鸟。
在“新政”时期,张之洞与刘坤一联衔会奏《江楚会奏三折》,使其理政方略(包括教育方略)成为新政的纲领,为其入主中枢、位极人臣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结果,也是张之洞审时度势的结果。如果没有张之洞在清廷的最高统治者、督抚大臣之间往复探测他们的真实政治倾向与时政见解,并在他们的政见之间作出合理的损益,断难使督抚大臣与最高统治者都对《江楚会奏三折》心悦诚服,也不会有公推其为新政改革纲领的结果。
总之,正是因为张之洞在其政治生涯中以权变智慧处理政务,其才能在晚清政治的惊涛骇浪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攀上一个又一个政治峰顶,铸就了一个又一个一展其教育襟抱的舞台。就此而言,权变智慧对于政治家型教育家而言,实在是不可或缺的。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美国学者斯腾伯格的成功智力理论来得到解释。在斯腾伯格看来,一个成功的社会实践家,其获得成功必须具备这些智能特征:良好的分析性智力、非凡的创造性智力和实践性智力[18]。斯腾伯格之所以强调这三种智能,正是因为它们是社会实践中的权变所必须的。审时度势首先需要实践主体分析具体面对的真实情境,其间,分析性智力是必须的。而要根据时势制定合适的行动策略,必须产生创造性的想法并把想法落实到实践中。要完成这两项任务,创造性智力与实践性智力正是必不可少的支撑。这也就是说,权变智慧是分析性智力、创造性智力、实践性智力的综合,为实践主体在社会实践(包括教育实践)中搭建长袖善舞的舞台所必须。
三、良好的知识素养和道德操守为政治家型教育家赢得了同仁高度、广泛的认可与拥戴
作为一个政治家型教育家,要想在搭建的舞台上长袖善舞,必须获得业内人士的认可、拥戴。其认可、拥戴的程度越高、越广泛,获得的支持力就越大、越多。否则,就会遭到业内人士的抵制,其成为政治家型教育家的道路,就会受到阻隔。张之洞从小就接受了严格而系统的儒学教育,对于四部之学都有相当精深的钻研。否则,他不可能在而立之年便撰就《书目答问》那样的综罗百家的经典。至于教育方面的知识,年青时代在浙江充任乡试考官、在湖北与四川出任学政,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教育知识与经验。后来,在出任封疆后,不论是改造旧式书院、改革科举,还是创办新式学堂,都要和学政、教育机构的掌事者、精通教育事务的幕僚往复商讨。如在《江楚会奏三折》的成稿过程中,为了就科举变法制定更切要、周备的方案,张之洞邀请为其主要搭档刘坤一拟稿的张謇和沈曾植到武昌面谈。对于这次面谈,据张謇说,从上午8点一直谈到下午5点,“所谈甚多”[19];沈曾植也说,张之洞“谈兴甚浓”[20]。由此足见张之洞咨询二人意见之多、之细。在张之洞与张百熙、荣庆共同磋商学务,着手制定癸卯学制时,张之洞不仅亲自到京师大学堂“考察学务”[21],还经常约请京师大学堂的总办、总教习、日本教习等到自己的寓所共同商讨学制制定相关事宜[22]。在这一切磋、琢磨中,其教育知识与经验自然日长月化。再加上他还不时派出属员出国获取新知,待其归来后招之相与讲习。如在1901年8月,张之洞为了使湖北学制系统的建构更为妥帖、稳健,专门派出罗振玉、刘洪烈等人到日本考察学校教育。当时,张之洞指派给罗振玉的任务是“考求中小学堂普通学应用新出教科书本,董理编译事宜”,指派给刘洪烈的任务是“考究教法、管学两事暨访购书籍”[23]。其间,罗振玉详细收集了有关日本教育制度的各种章程达110份之多。回国后,张之洞专门召见罗振玉,“畅谈日本见闻”[24]。这就更使其教育知识的进益不断获得源头活水。因此,清廷管学大臣张百熙才会在两次面对皇帝的奏对中,起初盛赞张之洞“留心学务最早,办理学堂亦最认真,久为中外所推重,是该督二十余年之阅历,二十余年之讲求,于学堂一切利弊知之较悉,自与寻常不同”[25]。后来,其又将张之洞称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26]。这充分说明,张之洞对教育知识的通晓是得到同行高度认可的。
除了学术素养与教育知识,人格操守之高洁也是张之洞获得同行高度认可的重要条件。毕竟从事教育事业的人物必须具备良好的道德操守是我国悠久的文化传统。在道德品质上, 张之洞堪称士人的楷模。他笃信先儒教诲的“修己以安人”[27],故一生从来都是清廉自守,“自居外任,所到各省,从不用门丁,不收门包,不收馈赠礼物”[28]。辞世之时,“竟至囊粱萧然,无以为子孙后辈计”。就连治丧费用,也出自门人、僚属的资助。对于公私之分,其泾渭分明。因此,他极力主张,“私利不可讲,而公利却不可不讲”[29]。在湖广总督任内,张之洞曾选派无数的青年学子到海外留学,却未让其长子张仁权列名其中,而是“自备资斧”,送其赴外国考察,让其“开扩胸襟,增益不能”[30]。正是做到了这些,虽然张之洞一生中所树政敌不少,但对其品行,却极少见到指摘之辞。一个如此品行高洁的人物,自然在同行中人人钦仰,“一时称贤”[31]。
总之,正是因为张之洞具有深厚的学术素养、教育专业知识素养以及高洁的品行,他才能够在教育界、政界获得广泛的认可与高度认同,为同行所拥戴。这是其凝聚同行的力量,在自己搭建的社会实践舞台上长袖善舞、获得举世公认的成就的重要前提。
四、创新性思想指引下的教育实践成就了政治家型教育家的影响力
政治家型教育家之所以能够被判定为是教育家,是有其显著标志的。其主要标志是:形成系统而新颖的教育思想,具有富有成效的教育实践,且这样的思想与实践对当时与后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而这样的成就的获得,往往遵循着这样一条路径:先形成系统而新颖的教育思想,再以之为指导进行富有成效的教育实践。张之洞便是循着这样一条路径将自己熔铸成教育家的。
在青年时期与中年时期改造传统书院、创办新式学堂的实践经验积累的基础上,中国传统教育与西方教育在思想上的融合日渐成为可能。于是,在渐入老境之时,张之洞的教育思想也进入了瓜熟蒂落的综合创新期。其最为显著的标志便是《劝学篇》的诞生。《劝学篇》这一著作虽然篇幅并不大,但其在教育思想上的开创之功,却是无与伦比的。它面对教育领域如何处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这一时代最大的问题,巧妙地借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思维模式作为思想系统建构的工具,对于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是什么,如何处理它们的关系,中国的教育发展蓝图如何描绘等问题,都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论述。这一著作所确立的“中西融汇”的基本思维范式与操作基调,遂成为张之洞后来教育实践的指南。在《劝学篇》出笼之后,无论是以张之洞为主导推行的书院改制、改革科举、厘定新学制等破旧立新之举,还是开办崇古学堂这样被目为守旧的举动,都把“中体西用”的思想投射在其中,使《劝学篇》刊出以后的教育实践成为“中体西用”思想的具体化、实在化。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最具有趋新意味的新学制的厘定与最具有守旧色彩的崇古学堂的开办的精神一致性见其端倪。
《奏定学堂章程》在“立学宗旨”一栏中,如此开宗明义,“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稗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浦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32]。其强调“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不就是“中学为体”的另外一种表述吗?“以西学浦其智识,练其艺能”,使之“各适实用”,不正是“西学为用”之意吗?就此而言,从《奏定学堂章程》的办学宗旨当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中体西用”的精神印迹。创办崇古学堂的举动常常被作为张之洞晚年思想转向守旧的主要证据。[33]事实上,这是对张之洞思想的极大误解。如果我们抛开意识形态的立场,仔细体察张之洞在提倡创办存古学堂中的一系列言论,我们就会发现,在张之洞的晚年,即使是其从地方大员变为军机大臣之后,也根本不存在所谓思想从趋新到守旧的转向。对于为什么要创办存古学堂,张之洞在呈给皇帝的奏折中曾经这样说,“近来学堂新进之士,蔑先正而喜新奇,急功利而忘道谊,种种怪风恶俗,令人不忍睹闻。至有议请废罢四书五经、有中小学堂并无读经讲经功课者、甚至有师范学堂改定章程声明不列读经专科者……正学即衰,人伦亦废。为国家计,则必有乱臣贼子之祸;为世道计,则不啻有洪水猛兽之忧。微臣区区保存国粹之苦心……以延正学而固邦基”[34]1766。在这段话中,张之洞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他之所以要创办存古学堂,是因为其看到,自从新式学堂开设以来,存在着一种值得忧虑的倾向:人们把传统的经史之学弃之如敝屣。这带来的恶果是,传统经史之学衰微,传统的纲常伦理被遗弃。如此发展,国家必然陷入动荡不宁之中。因此,非常有必要开设迥异时流的学堂,以对抗滔滔浊世,使传统的经史之学能够得到保存,为国家的安宁奠定文化基础。由此可见,张之洞是站在延续传统文化的命脉,为国家的安定奠定文化基础的立场上来提倡创办存古学堂的。其“中学为本”的意旨一目了然。在强调以“中学为本”的基础上,他如此进一步申论,“要之,孔子所言温故而知新一语,实为千古教育之准绳。所谓故者,非陈腐顽固之谓也。盖西学之才智技能日新不已,而中国之文字经史万古不磨,新故相资,方为万全无弊”。[34]1764这就把其真实的思想表达的很清楚了:张之洞之所以提倡创办存古学堂,是为了在保留国之命脉的基础上,使“日新不已”的西学能够补给“中学”,保得国家的“万全无弊”。这正是“西学为用”之意。
张之洞之所以能够成为在当时的中国名重一时的教育界的大人物,并对近代中国的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仰赖的便是《劝学篇》中构建的教育思想所具有的开创性、系统性,以及《劝学篇》出笼后的教育实践对中国近现代教育产生的塑造作用[35]。这充分说明,如果离开具有开创性的教育思想指导下的教育实践,是不可能成就一位政治家型教育家的。
综上所述,从张之洞成长为政治家型教育家的机制问题探讨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如果要造就一个政治家型教育家,需要我们从以下方面努力:第一,塑造教育实践主体的高尚人格。始终站在超越个人功利的立场上热爱教育事业、热爱学生,是成就全身心献身教育事业的教育家的内在驱动力。这是成就教育家的最为内在、原始的动力。因此,我们必须把这些教育家人格的塑造作为铸就教育家的必要前提。另外,在一个有着悠久的注重教育家人格节操传统的国度,教育实践主体的一般人格操守是决定着同行认可、拥戴程度的重要因素,因此,对于教育实践主体一般人格的塑造,也要特别重视。第二,磨砺教育实践主体的分析性智力、创造性智力、实践性智力。之所以提出这样的主张,其理由有二:一是教育实践主体在内在情怀驱动下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活动是需要施展舞台的。这一舞台的搭建,离不开教育实践主体顺应时势,因势而为。而这种权变性实践,离不开前述几种智力的有力支撑。二是教育实践主体要想成为教育家,必须形成具有创造性的教育思想并将其有效实在化。而这两项任务的完成,都离不开上述三种智力的强力支持。第三,充实教育实践主体的一般学术素养与教育专业知识素养。良好的一般学术素养与教育专业知识素养是教育实践主体获得同行广泛认可的必要条件,因此,欲使众人之志共同成就教育实践主体的伟业,决不可忽视其良好的一般学术素养与教育专业知识素养的奠定这一问题。
[1]王树柟.张文襄公全集(卷首上)[M].北京:北京文华斋刻本,1928.
[2]张之洞.吁请修备储才折[M]//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张之洞全集(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1129.
[3]张之洞.创设储才学堂折[M]//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张之洞全集(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1130.
[4]张之洞.致袁慰亭[M]//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张之洞全集(十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8: 10268.
[5]张之洞.付鲁堂诗集序[M]//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张之洞全集(十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10059.
[6]吴剑杰.张之洞年谱长编(上卷)[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23.
[7]张之洞.谢周伯晋惠上海三白瓜诗[M]//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张之洞全集(十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10541.
[8]张之洞.湖北三得大雪微雪无数除日赋诗[M]//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张之洞全集(十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10544.
[9]张之洞.致广雅书院分校马季立等[M]//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张之洞全集(十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10345.
[10]张之洞.连珠诗[M]//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张之洞全集(十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10527.
[11]张之洞.劝学篇·变法第七[M]//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张之洞全集(十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9794.
[12]张之洞.到山西任谢恩折[M]//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张之洞全集(一).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632.
[13]张之洞.直言不宜沮抑折[M]//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张之洞全集(一).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633.
[14]张之洞.劝学篇·序言[M]//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张之洞全集(十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9704.
[15]张之洞.遵旨筹议变法谨以采用西法十一条折[M]//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张之洞全集(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1236.
[16]孔广德.普天忠愤集[M].石印本,1895.
[17]张之洞.劝学篇·会通第十三[M]//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张之洞全集(十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9766.
[18]R.J.斯腾伯格.成功智力[M].吴国宏,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86-90.
[19]张謇.张謇全集(六)[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455.
[20]王尔敏,陈善伟.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六)[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2582.
[21]荣庆.荣庆日记[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63.
[22]癸卯六月十二日致管学大臣吏部大堂张,癸卯六月十七日致大学堂总办于、代总教习张、总提调李、编译局李[G]//张之洞函稿·京寓函稿.北京: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档甲:182-213.
[23]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张之洞全集(六)[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4155-4156.
[24]王晓秋.近代中日启示录[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232.
[25]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65.
[26]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7:306.
[27]论语·宪问.
[28]张之洞.抱冰堂弟子记[M]//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张之洞全集(十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10630.
[29]黄兴涛.辜鸿铭文集[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202.
[30]张之洞.致鹿滋轩[M]//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张之洞全集(十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10226.
[31]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4:12382.
[32]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 [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98.
[33]把增强.近五年来张之洞研究的新进展[J].历史教学,2003(7):75.
[34]张之洞.创立崇古学堂折[M]//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张之洞全集(三).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35]蔡振生.张之洞教育思想研究[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266-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