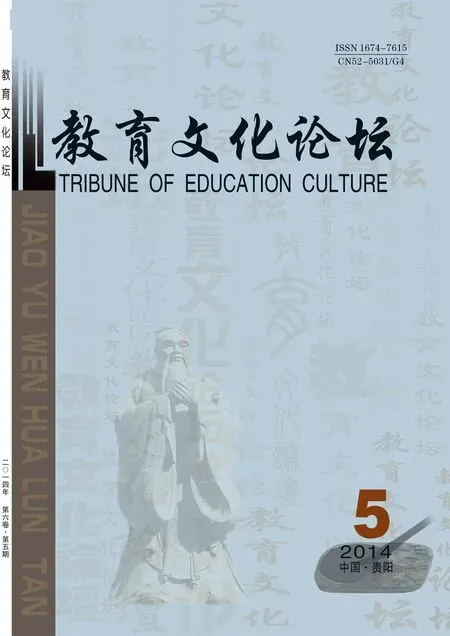论《挪威的森林》的写作范本
——与《了不起的盖茨比》和《魔山》的比较研究
李国栋 刘雨潇
(贵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村上春树深受西方文学的熏陶,其代表作《挪威的森林》中曾多次提到美国作家弗朗西斯·司哥特·菲茨杰拉德及其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同时也多次提到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和他的《魔山》。村上春树在各种场合表达了自己对菲茨杰拉德和托马斯·曼的欣赏和认同,甚至把菲茨杰拉德称为“我的老师,我的大学,我的文学同事”[1]。本文拟从叙事学的角度对《挪威的森林》、《了不起的盖茨比》和《魔山》进行文本分析,找出三者在视角、故事空间和象征意象运用上的相似之处,进而论证菲茨杰拉德和托马斯·曼对村上春树创作模式的影响。
一、叙述视角与叙述者的多元化
视角与叙述者是叙事学中的核心概念。整体采用第一人称内聚焦型视角,局部采用外聚焦型视角与叙述者的多元化设置是《了不起的盖茨比》和《挪威的森林》的相似之处,也是村上春树借鉴菲茨杰拉德最为明显的一个方面。
菲茨杰拉德在创作中很强调对距离感的把握,“既身在其中,又身在其外”[2]是他使用的叙述手法。《了不起的盖茨比》整体上是用第一人称内聚焦型视角进行叙述的。小说的题目虽然是“了不起的盖茨比”,但菲茨杰拉德设计了尼克这一特殊人物作为故事的叙述者,他以一个见证人的身份向读者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1922 年夏天发生在纽约郊外的盖茨比故事。尼克既是整个故事的叙述者,又是故事中的关键人物。作为叙述者,尼克采取了旁观者具有的客观态度,保持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来叙述整个故事;作为参与者,尼克又是重要的登场人物,也是联系其他人物的纽带和桥梁。
“inclined to reserve all judgments”[3]的尼克说:“I was within and without, simultaneously enchanted and repelled by the inexhaustible variety of life”,这句话既表明了尼克对现实的双重态度,更揭示了叙述者与作品中其他人物以及读者之间的距离。尼克身在故事中,使得他的叙述真实可信,拉近了叙述者与故事的距离,使读者比较容易融入到故事里;同时他又身在故事外,这也使其叙述呈现出相当的不确定性,给读者提供了想象空间,使其站在更高的层次来观察整个故事的发展。通过尼克客观、理性的叙述,整个故事始终与读者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从而显得更为客观和真实。
村上春树在2010年接受松家仁之的采访时说道:他喜欢的小说几乎都用第一人称写作,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就是。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法在《了不起的盖茨比》这种篇幅的小说中发挥得尽善尽美,菲茨杰拉德用第一人称写的小说更自由,情节更灵动。因此他刚开始写小说时,对用第一人称写作没有丝毫犹疑。因而村上春树大多数小说采用的都是第一人称内聚焦型视角,视角的承担者既是叙述者,也是小说中的重要人物。村上春树在采访中又强调:他初期的小说,有些部分是从自己的视角展开,以自己的视角进入故事,目睹事件,产生反应,并描写这一状态。读者也是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或者说与“我”同化的形式,目睹并体验了呈现在眼前的事情。故事如此向前推进,和角色扮演游戏一样,读者也能自然地和主人公一起展开行动。他把这种手法称为“视角同化型”。[4]
《挪威的森林》的主人公渡边就承担了这一角色,小说一开始就是三十七岁的渡边以回忆的口吻讲述十八年前自己青春时代经历的爱情故事。在整个故事中,渡边既是讲述者,同样也是故事的参与者。因此,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也能随着渡边的视角展开行动,目睹事件的全过程。
为了使故事情节更加丰富和完整,菲茨杰拉德在作品整体上运用第一人称内聚焦型视角的同时,在局部也运用了第三人称外聚焦型视角,让其他人物来完成叙述。在《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第四章,菲茨杰拉德使用乔丹·贝克作为临时的叙述者,尼克充当听众,和读者一起听乔丹回顾盖茨比和黛西初次相识和恋爱的经历,让读者进一步了解盖茨比想与黛西重修旧好的原因。
无独有偶,村上春树在整体上运用第一人称内聚焦型视角的同时,也在局部采用了第三人称外聚焦型视角。在《挪威的森林》的第六章,村上春树起用玲子作为暂时的叙述者,渡边自己作为听者,由玲子向渡边和读者讲述了她作为精神病患者的故事。
如上所述,多元化视角的设置和“既身在其中,又身在其外”的叙述手法是《了不起的盖茨比》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村上春树承认自己对菲茨杰拉德的借鉴和学习,而两者在视角的运用上又呈现出如此惊人的相似之处,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村上春树在叙述者和叙述视角的设计方面确实接受了菲茨杰拉德的影响。
当然,由于上述叙述视角和叙述者的设置,村山春树的小说显示出强烈的西化倾向,但我们也应注意到,较之菲茨杰拉德,村上春树的叙事中主观感受性的东西更多,显示出日本传统文学的“物哀”特色,即日本传统文学特有的忧伤、纤细的美感。总而言之,村上春树对叙述者和叙述视角的处理实际上是西方叙述方式和日本“物哀”美学的有机融合。
二、生死并存的故事空间
故事空间是指叙述的人和事所发生的场所。故事空间在叙事作品中具有重要的意义,除了为人物提供必须的活动场所,它也是解释作品题旨的重要方式。
托马斯·曼在《魔山》中设置了一处位于瑞士高山之上的肺病疗养院。这一疗养院远离都市,与世隔绝,到处充斥着死亡的阴影,是生与死并存的空间,因此可以称作“魔山”。与“魔山”相对应的是象征现实世界的“平原”,山上和山下的地理落差显示着人类难以逾越的生与死的距离。山下的世界是一个忙碌、世俗的常人世界,而山上则是与世隔绝、没有时间概念的非常人世界。“魔山”中住着来自世界各国的病人,他们虽然国籍不同、信仰不同,但每个人的肉体里都充满了结核病菌,无法治愈,只能静静等待死亡的来临。主人公汉斯在疗养院的七年时光中目睹了许多病友的死亡:他的表哥约阿希姆、莱拉·戈恩格罗斯、“两个都”的两个儿子、明皮尔·皮伯科恩、纳夫塔等等都在他的眼前相继逝去。[5]
同样在《挪威的森林》中,村上春树也设计了一个位于京都深山老林中的疗养院——阿美寮。与《魔山》中的肺病疗养院一样,阿美寮也是非常世界的象征,也是生死并存的空间。不过与《魔山》中的肺病疗养院不同的是,住在阿美寮里的病人不是承受肉体上的病痛,而是被精神上的疾病所困扰。他们是因为无法融入现实世界而被抛弃的“不正常”的人。
当然,在村上春树的笔下,阿美寮是一个“世外桃源”。这里的人们“生活基本自给自足”,“在远离人烟的地方大家互助互爱,同时从事体力劳动……从而使某种病得到彻底治疗”[6]。但是,即使在这种地方也同样飘荡着死亡的阴影。疗养院的病人都是像直子一样,由于无法适应现实世界,无法同现实世界沟通和交流,为了躲避现实才来到这里的。而现实毕竟无法逃避,最终只能走向死亡。因此,阿美寮同样也是象征死亡的“魔山”。
主人公渡边第一次到阿美寮探望直子时,从食堂的光景中就感受到了阿美寮与现实世界的不同。在食堂就餐的人们“每个人讲话的音量都相差无几,既无大声喧哗,又无窃窃私语,既无人开怀大笑和惊叫,也无人扬手招呼。每个人都用大体相同的音量悄声交谈”。在这“奇妙的静寂”中,渡边感到心里缺少踏实感,他开始怀念纷繁嘈杂的现实世界,甚至“觉得自己似乎孤零零地置身于整理得井井有条的一片废墟之中”。
渡边在阿美寮中读的书就是托马斯·曼的《魔山》,村上春树的这一设计成功地将抑郁的死亡气息注入了小说的字里行间,使直子最后选择在“如同她内心世界一般混黑的森林深处勒紧了自己的脖子”这一情节显得顺理成章。渡边阅读《魔山》这一行为本身就在暗示渡边和读者,直子不会在阿美寮得到痊愈,最后只能走向死亡。
托马斯·曼虽然在《魔山》里描写了死亡和疾病,但《魔山》并不是一部死亡的小说,音乐是托马斯·曼用于救赎的武器。音乐在汉斯精神自救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是一种崭新意义上的“精神的回归”,是一种强有力的“灵魂的魔术师”。在最后一章“和谐的乐章”中,疗养院里添置了一些娱乐设施,其中最吸引汉斯的就是一台留声机。他热衷于一个人逗留在活动室里,独自放着唱片,直到深夜。他在音乐里,特别是从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创作的歌剧《阿依达》中得到了救赎。“他所感受的、理解的和享受的,都是音乐艺术,人类精神成功地理想化了的东西。这种东西可以从卑劣、丑恶的现实中创作出人类无法抗拒的美来”,因此“比起其他唱片,这种美好的慰藉对这位聆听音乐的青年起了非常好的作用,因而他更钟爱这首曲子”[7]。正是因为音乐对他的熏陶,他不断成长,不断自省,并最终变得成熟起来。
汉斯在音乐中得到了救赎,从而在小说的最后离开了疗养院,投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正如托马斯·曼在后记中写道:“汉斯·卡斯托普在山上的经历中,克服了天生的对死亡的好奇心,到达了普通人所不能达到的高度。他理智地忽视了死亡,毫不蔑视生命中的黑暗与神秘,能认真思考它,却不让它控制自己的思想。他逐渐意识到一个人必须经历死亡和疾病,才能达到更高、更健康的境地。”
与汉斯一样在疗养院待了七年之久的玲子之所以没有选择死亡,最终得以回归现实世界,也正是由于音乐的救赎。玲子从小就具有音乐天赋,在进疗养院之前是一位钢琴教师,阿美寮里没有钢琴,所以玲子自学了吉他,平时也教其他病人音乐。玲子认为,“在过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人就不能不为自己演奏,所谓音乐就是这么一种东西”。玲子在音乐里找到了精神上的寄托,从而熬过了在阿美寮里漫长的岁月。
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中对于死亡是这样描述的:“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这是渡边在好友木月自杀后的领悟,而这个领悟同《魔山》中的人文主义者赛特姆布里尼对生和死的谈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赛特姆布里尼是这样论述生与死的:“对待死亡唯一健全、高尚、虔诚的方式,就是把它视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理解和感受生活的不可侵犯的条件”。由此可以看出,村上春树对生与死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托马斯·曼的影响,二者都认为生中有死,死中有生,生与死相互依存,不可分离。也许正因为如此,托马斯·曼和村上春树都在作品中设定了生与死的主题,小说中的人物也都穿梭往返于生与死之间。
综上所述,《魔山》和《挪威的森林》的故事虽然发生在不同年代、不同国家,情节也少有共同之处,但两部小说都共同设置了远离都市、与世隔绝的疗养院这一故事空间。两座疗养院都象征着死亡,两部作品的主人公在疗养院也都真真切切地接触到了死亡。由此我们可以判定,在故事空间的设置上,托马斯·曼的《魔山》是《挪威的森林》的原型。
三、象征意象的运用
象征手法是用具体的人、物或活动来代表某一抽象概念,通过客体来喻指本体,其目的在于加深作品意蕴。在《挪威的森林》中,村上春树借鉴了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大量运用的象征手法,两部作品在象征意象的选择及其喻意指向上显现出许多相似之处。
事物的象征意象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随处可见, 但最具有深远意义的是海湾对面黛西家码头尽头处的“burns all night”的绿灯。它首次出现在第一章的结尾处:
He stretched out his arms towards the dark water in a curious way, and, far as I was from him, I could have sworn he was trembling. Involuntarily I glanced seaward and distinguished nothing except a single green light, minute and far away, that might have been the end of a dock.[8]
在这里,“green light”这一意象被赋予了多层的象征意义。首先,它象征着盖茨比耗尽生命追求来的辉煌事业,它是金钱、成功、名声的化身。然而,无论得到多少名利,盖茨比都得不到满足,他依然只渴望重新获得黛西的芳心,黛西才是他所有追求的核心,他把自己的思念和希望都寄托在这盏“green light”上。
后来,盖茨比终于如愿得与黛西重聚,但这时雾气却笼罩了“green light”。重逢后盖茨比发现现在的黛西已不再像他心中想象的那么美好,被雾气笼罩的“green light”也渐渐失去了往日那令人神往的魔力。可以说,“green light”因黛西的美丽而美丽,因黛西的黯淡而黯淡,它就是黛西的化身。
另一方面,菲茨杰拉德将个体的象征与社会历史的象征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这盏“green light”被他赋予了更深层次的含义。菲茨杰拉德从盖茨比对理想的追求与破灭中揭示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狂热追求“美国梦”的人们注定要遭到毁灭的结局。
同样,在《挪威的森林》中村上春树也运用了“灯光”这一意象。在渡边第一次去阿美寮看望直子的那个夜晚, 村上春树描写了这样一幕:
我穿过杂木林, 在一座小山包的斜坡上坐下身来, 望着直子居住的方向。找出直子的房间是很容易的, 只消找到从未开灯的窗口深处隐约闪动的昏暗光亮即可。我静止不动地呆呆地凝视着那微小光亮。那光亮使我联想到犹如风中残烛的灵魂的最后忽闪。我真想用手把那光严严实实地遮住,守护它。我久久地注视着那若明若暗摇曳不定的灯光, 就像盖茨比整夜看守对岸的小光点一样。[9]
此刻的渡边能够理解盖茨比整夜眺望“green light”的心情,因为他感觉到了自己像盖茨比对黛西一样, 对直子充满了爱。在渡边的心中, 直子窗口那微弱的灯光如同直子一样, 是他精神的寄托和灵魂的归宿。直子的爱就像在风中摇曳的灯光一样,给渡边的心灵以温柔的抚慰,化解了渡边的孤独与无奈。这微小的灯光就是他生活下去的希望,是他所要守护的精神家园中的一片净土。
当然,《魔山》在象征手法上也对《挪威的森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两部小说的书名本身都是象征意象。“魔山”象征着与现实世界相对应的死亡世界,仅从书名就能体会到充斥于小说中的阴郁的死亡气息。而“挪威的森林”题目本身就是著名的甲壳虫乐队所演唱的一首歌曲的名字。歌曲所要表现的是“我曾拥有过一个女孩,她带我参观了她的一片美好的挪威森林,等我醒来的时候,我独自一人,鸟儿早已飞走”。这是一个宁静而又忧伤的故事,正如直子所说:“一听这曲子,我就时常悲哀得不行。也不知为什么,我总是觉得似乎自己在茂密的森林中迷了路。……一个人孤孤单单的,里面又冷,又黑,又没一个人来救我”。这片森林既是直子破碎心灵的象征,也是其生命被吞噬的地方。小说的开头,渡边在飞机上听到了这首曲子后开始追忆往事;而到了小说的结尾,在渡边和玲子追思直子的音乐葬礼上,玲子又弹起了这首曲子。小说犹如挪威的森林,充满着孤独与绝望。
综上所述,在象征意象的选择和运用上,村上春树借鉴和模仿了菲茨杰拉德和托马斯·曼。除了使用“灯光”这一意象来象征主人公的精神寄托之外,在书名的设定上,也使用了象征意象来加强主题,烘托小说的氛围。由此可见,在象征意象的运用方面,《了不起的盖茨比》和《魔山》也是《挪威的森林》的西式模板。
《挪威的森林》深深地渗透着西方文学,尤其是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和托马斯·曼的《魔山》那种特有的气息,在视角、故事空间和象征意象的运用上都表现出极大的相似性,由此我们可以断定,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的创作过程中深深地受到了菲茨杰拉德和托马斯·曼的影响,甚至可以说《了不起的盖茨比》和《魔山》就是《挪威的森林》的写作范本。
[1] (日)加藤典洋,三浦雅士.群像日本作家第二十六集·村上春树[M].东京:日本小学馆,1997.
[2] (美)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F.S.).了不起的盖茨比[M].巫宁坤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3][8] (美)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F.S.).了不起的盖茨比[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7.
[4] 安妮宝贝.村上春树三天两夜长访谈[J].大方,2011.
[5] 赵佳舒,唐新艳.托马斯·曼对村上春树的影响——比较《魔山》和《挪威的森林》[J].译林,2008.
[6][9] [日]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M].林少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7] [德]托马斯·曼.魔山[M].陈丽丽,姜静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