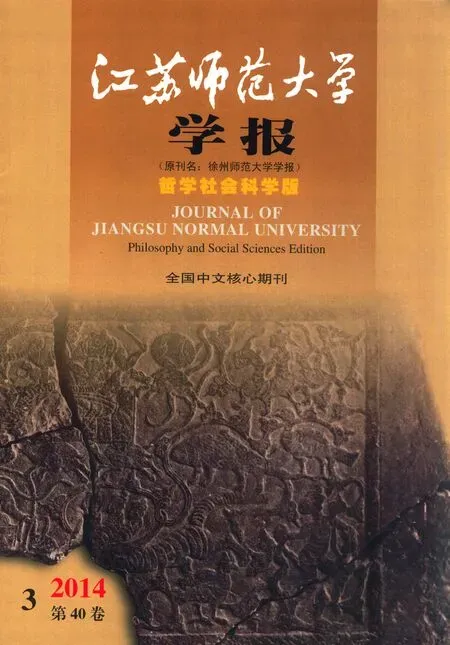凋落于深渊中的“女人花”
——曹七巧与灯芯形象论析
赵 青
(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江苏淮安 223000)
凋落于深渊中的“女人花”
——曹七巧与灯芯形象论析
赵 青
(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江苏淮安 223000)
《金锁记》;曹七巧;《深宅活寡》;灯芯;深渊;欲望
上个世纪40年代,张爱玲在其经典之作《金锁记》中,以一种全角叙事的方式刻画了曹七巧这一悲剧性的“寡妇”形象。无独有偶,21世纪的新生代作家许开祯在其著名长篇小说《深宅活寡》里,也用全角叙事的方式塑造了灯芯这一复杂立体的“寡妇”形象。七巧和灯芯,可谓是不同时空下凋落于同境深渊中的两朵“女人花”,有着值得探究的共性,也有着让人瞩目的异彩。不平等的悲剧婚姻,虚幻的爱情,对金钱、权力的掌控欲等等,都让她们渐渐褪去了鲜润的本色。
在上个世纪40年代的中国作家中,张爱玲是难得的一个集才情、智慧于一身,能在作品内外自由出入的女性作家。她的出现,对当时的上海文坛而言,是颇有些“惊天动地”的,人们甚至誉之为“天才”。她的小说总能在无形之中给人以震撼。其实,让我们惊讶的还不止这些,比如她作品的主角大多是女性,而她在塑造或刻画这些女性的时候,又大多能做到:于不动声色之中,让人感慨万分,思虑万千。她的中篇小说《金锁记》可谓是此类经典之作。由此,人们知道了曹七巧这个人物,知道了那个时代的生活中存在着曹七巧这一类的悲剧女性。而对于灯芯,也许现在仍有很多人不甚了解——事实上,她和七巧一样,虽贵为大户人家的少奶奶,但婚后却因丈夫的病残而无法获得正常的夫妻生活,长期守着活寡——她是21世纪新生代作家许开祯的长篇小说《深宅活寡》中的主人公。曹七巧和灯芯虽然属于不同的时代,人物各具特色,但她们在婚姻爱情、性格发展及命运结局方面又有着诸多相似或相近之处。婚姻为她们打开的不是幸福之门,而是将她们一步步推向悲剧人生的深渊;她们由自保而日渐变得自私、冷酷,直至亲情远离,爱情幻灭。我们同情她们的遭遇,理解她们的挣扎,却更加叹恨她们的异变。就艺术形象的塑造而言,后者之于前者,是带有继承和发展意味的。
一、悲剧婚姻开启深渊之门,反抗之中走向自我迷失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原本是一个麻油店老板的女儿,她嫁到姜家后便一跃成为让人羡慕的二少奶奶。但由于她与姜家二少爷在出身及家世背景上的悬殊,她在姜家仅徒有二少奶奶的虚名,并没有真正获得与二少奶奶这一身份相符的待遇;而且,作为姜家的儿媳妇,由于丈夫身患骨痨,她不但无法享受到一个妻子应有的幸福,甚至连一个女人基本的生理需求都无法得到满足,这就使得她的双重身份都指向了虚无。这不由得使人联想到《深宅活寡》中的灯芯。虽然,灯芯作为新生代小说中一个新的艺术形象可能很少为人所知,但其在命运的悲剧意味上却与曹七巧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灯芯嫁到深不可测的菜子沟下河院,同样是门不当户不对,对方不过是想用她来冲喜而已。她的丈夫命旺是个身患痨病的傻子,她的出嫁,就是为了等到父亲刘中医所说的“那一天”。于是,她便毫无价值地成了这深宅大院里守着活寡的女人。为了生存,为了自己的目的,在熟知下河院的许多猫腻之后,灯芯同各种不利于己的势力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正是在这种明争暗斗中,灯芯从一个无知少女成长为一个成熟、机智、果断,同时又心机狠毒的少妇。也正是这种明争暗斗,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心地善良、渴望爱情和正常夫妻生活的灯芯那深藏不露的另一面。在下河院的淤泥中,灯芯越陷越深;透过下河院高墙内外发生的一切,我们看到,灯芯既是个毒如蛇蝎的少奶奶,也是个拥有美貌和魄力的大西北荒原女人。
可见,曹七巧和灯芯这两个女性形象被张爱玲和许开祯不约而同地规划在两个相似的环境及境遇之中:她们婚后都生活在封建的、封闭式的深宅大院——姜公馆和下河院——里,进而她们便都处于礼法秩序下的关系结构中;她们从“洞房花烛夜”起就都无可避免地走进了婚姻的悲剧;在毫无指望的家庭生活中,她们的心理和行为都逐渐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异常,甚而可以说,她们的人性已被渐渐异化了。
曹七巧出身低微,不幸又父母早亡,贪财的哥嫂把她卖到了姜家,嫁给了活死人一般的姜二少爷,由此她变成姜公馆的二少奶奶,但同时也开始了她以殉葬美好的青春为代价的守活寡的生活——丈夫是个垂死的病人,连个摆设都不如,对她来说相当于没有。虽然,由于姜公馆老太太的一念之差,她阴差阳错地成了正头奶奶,但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她的底细,所以看似飞上枝头做了凤凰的七巧,在众人眼里仍是个低三下四的人。她费心尽力地去讨好姜公馆内的每一个人,可她所做的一切不但没有为自己换回应有的尊严,反而使她让人更加地瞧不起;她挖空心思地寻求安全保障,却愈加发现自己深处于种种不安全因素的包裹中。于是,七巧便将目光转向了黄金,她开始坚信只有黄金才能使她真正地获得安全。慢慢地,她给自己戴上了“黄金之枷”,并继而用它“劈杀”了一个又一个人,她甚至亲手毁掉了一双儿女的幸福。婚姻是令人遐想的,对许多人来说它是人生的美好归宿,但曹七巧却从踏进婚姻大门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了她人生的悲剧。她在那个名存实亡的婚姻生活中,在那个了无生气的高墙大院中迷失了自我,葬送了青春。
同样,灯芯也是一场悲剧婚姻的牺牲品——她是为姑表弟冲喜并应父亲刘松柏的指点而嫁进下河院的。或许,灯芯原本就不过是父亲向往下河院权利而掷出的一枚棋子,因此,当她踏上去下河院的路上时,即已开始了自己一生的悲剧。灯芯在迈出了沉重而可怕的第一步后,就隐约地窥察到了下河院难以测摸的阴森。于是,成了下河院少奶奶的灯芯,面对一个个人面兽心的魔鬼,每天都紧绷绷地生活着。她在众人面前谨言慎行,在公公面前不露声色,隐秘而巧妙地把一个又一个计划付诸实施,费尽心机地将那些害人的魔鬼一个个铲除,而她自己也在勾心斗角中一步步滑向了罪恶的深渊。悲剧婚姻带来了身心两方面的痛苦,使她逐渐迷失——最终也成了一个冷酷无情的杀人者。在经历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件之后,在承受了一个女人无法承受的煎熬苦痛之后,灯芯终于获得了下河院的绝对权力,她成熟了但也变得复杂了。
灯芯和曹七巧一样,在一场悲剧的婚姻中,埋葬了青春,毁灭了自我。在权力争夺中,灯芯似乎是个胜利者。但对于整个人生而言,灯芯又何尝不是个凄惨的失败者呢?可以说,灯芯是21世纪的新“曹七巧”,但又焕发着别样的神采。
曹七巧和灯芯这样的人物,在其他作家的作品中也不难找到。如新生代作家毕飞宇笔下的玉米(小说《玉米》的主人公),就是这一类可悲可叹的悲剧女性。她为了家族、为了权力,不惜成为革委会副主任的“晚期老婆”。不同的是,她是亲手将自己关进了无爱的婚姻。这些典型的文学形象,是不同时代的作家对于人类因各种欲望而牺牲子女、他人或自己的婚姻幸福而发出的呼告,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二、虚幻爱情助推深渊之坠,抗争无果而邪欲滋生
爱情与婚姻一直是女人世界的中心,一个女人婚姻的成败几乎左右着她的一生。张爱玲就曾说过:“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1]然而不是每个女人都能得到真爱、拥有幸福的,曹七巧没有,灯芯也没有。
七巧在麻油店做姑娘时,是一个穿着蓝夏布衫裤的普通姑娘,然而,正是十八九岁的好时光,性格直率泼辣而又带着些可爱——胳膊滚圆,上街买菜时敢把袖子高高地挽起,露出雪白的手腕;在柜台里忙活时也敢和熟人开些玩笑。“喜欢她的有肉店里的朝禄,她哥哥的结拜弟兄丁玉根、张少泉,还有沈裁缝的儿子。”[2]她也曾经幻想过,“如果她挑中了他们之中的一个,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3]那时的七巧是渴望爱情的,然而她还没有来得及拥有一段真实的爱情就被卖到了姜公馆,少女时的那点梦幻就此被匆匆抛埋。可令她万万想不到的是,婚后,她竟然被更加彻底地弃置于爱情之外了——丈夫了无生气,对小叔子的喜欢也只是不可能得到真情回报的单相思!
在畸形的交换婚姻中,七巧是一个牺牲品,她甚至还没来得及选中一个小伙子,轰轰烈烈地爱一场,就被当做交换条件嫁给了身患骨痨的姜家二少爷,成了姜公馆的二少奶奶。面对冷冰冰的二少爷,七巧连最起码的性欲都得不到满足,爱情于她而言就更是种奢望了。在备受压抑之后,她将炙热的情感转向姜家三少爷季泽。对于七巧来说,或许三少爷只是个可以满足其情欲需求的一个现实目标,或许他多少也激起了她的一些真情,但是不管怎样,这份雾里看花的婚外情终究是没有结果的。七巧渴望得到三少爷季泽的爱以及他的身体,她甚至主动去挑逗季泽,她痛苦的单恋着,却终未得到自己所幻想的爱情。
多年以后,当三少爷季泽主动找上门来时,她的内心是充满喜悦和甜蜜的,但又是矛盾的——对于爱情和金钱难以抉择的矛盾。对此,张爱玲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
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这些年了,她跟他捉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可不是,这半辈子已经完了——花一般的年纪已经过去了。人生就是这样错综复杂,不讲理,当初她为什么要嫁到姜家来?为了钱么?不是的,为了要遇见季泽,为了命中注定她要和季泽相爱。她微微抬起脸来,季泽立在她跟前,两手合在她扇子上,面颊贴在她扇子上。他也老了十年了,然而人究竟是那个人啊!他难道是哄她吗?他想她的钱——她卖掉她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仅仅这一转念,便使她暴怒起来。就算她错怪了他,他为她吃的苦抵得过她为他吃的苦么?好容易她死了心了,他又来撩拨她,她恨他。他还在看着她。他的眼睛——虽隔了十年,人还是那个人啊!就算他是骗她的,迟一点儿发现不好么?即使明知是骗人的,他太会演戏了,也跟真的差不多罢?[4]
此刻,七巧的脑子里虽然已经千转百回了一番,但她还是及时地拉回了自己的思绪:“不行!她不能有把柄落在这厮手里。姜家的人是厉害的,她的钱只怕保不住。她得先证明他是真心不是。”[5]结果当她真的戳穿了季泽的诡计,叫骂着拿团扇赶走了他后,她又禁不住赶紧提着裙子慌慌忙忙、跌跌撞撞地跑到楼上去,以便能在楼上的窗前再看他一眼。她痛心自己彻底失去了爱,“他不是个好人,她又不是不知道。她要他,就得装糊涂,就得容忍他的坏。她为什么要戳穿他?人生在世,还不是那么一回事?归根究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6]这时七巧自己编织多年的爱情梦想已完全破碎,她似乎后悔揭开了季泽的真面目——为她的钱而来。她还留恋着季泽,可让她假装糊涂任他欺骗,用自己一生换来的钱去拴住他,她又是极不情愿的,于是她不得不亲手揭开了令人痛心的现实。这是何等复杂的感情,这是爱在七巧心里的最后一次挣扎,这是七巧与自己的爱的决绝!其实她何曾得到过爱情呢?显然没有!那又何谈失去呢?此时,虚幻的爱情无疑成了她坠向深渊的助推力,她在爱情幻梦与失去金钱的恐惧中挣扎,最终当惨痛的现实击碎她的热望时,她“终于亲手掐死了自己心中的爱情之花”[7],变成了邪念和贪欲并蒂滋生的“疯女人”。
七巧终身没有爱情!灯芯的经历与曹七巧有相似之处但又有所不同。作者对灯芯婚前的生活未作详细介绍,她的感情生活主要集中在婚后。灯芯是作为冲喜的工具嫁进下河院的,丈夫命旺是个奄奄一息的傻子。灯芯身负使命来到下河院,似乎有种英勇就义的感觉。她精心照顾着命旺,真心希望他能早日好起来,这和她在下河院的地位有着密切关系,他们之间是没有所谓的爱情的。对救了自己一命的二拐子,她心存矛盾,利用的同时又防备着他。灯芯深知下河院的礼数,极力遏制自己的欲望,不敢越雷池半步。但当菜子沟的人谣传她是只不下蛋的母鸡,而公公又为了延续香火准备给命旺娶二房时,她终于忍无可忍了。为了自己日后的地位,她不得不铤而走险,与二拐子私通,借种生子。小说的最后一章主要写了七驴儿与灯芯之间的故事——灯芯用了同样的手段,借助七驴儿怀上了下河院的第三个孙子,她对七驴儿同样谈不上爱,更多的是利用,然后再残忍地借机杀人灭口。
值得一提的是灯芯和老管家和福的儿子石头之间的情感。他们之间以姐弟相称,却又隐隐约约传递着一种暧昧的关爱,说不清是爱情还是亲情。初次见面作者就将他们俩置于云里雾里的复杂情感之中。“你是石头?”“你是下河院少奶奶?”“像是心里装了多少年,梦里又等了多少年,终于见面了似的,都在心里惊叹了一声,而后便盈盈笑在了一起。”[8]多么美好而羞涩的场景。这份感情直至石头因病去世多年,仍在灯芯心头环绕。或许灯芯心里装的东西太多,或许灯芯把下河院看得太重,总之她在女人最鲜艳的年龄里终未能开始一段真正的爱情。她的一切的行动指南似乎都是金钱、权力和地位,她要掌控一切以证明自己并得到一辈子的保障,她害怕失去,失去她在下河院苦心经营而得来的一切。因此,灯芯和七巧一样,在情不自禁的贪欲之下,将自己异化得面目全非。有些人在她的眼中看到了狼一样的蓝光,这哪里还是那个他们喜欢仰慕的、温情本真而又可爱可敬的少奶奶啊?
三、亲情缺失催生杀人心魔,被害者滑向害人者的深渊
每个人的亲情都像一条河,只不过每条河里承载的东西不同,有的是爱与责任,有的却是恨和迫害。
对于亲情,七巧和灯芯有着不同的诠释。有人认为,曹七巧是“一个因失落的爱而泯灭了自我,泯灭了人性的女性形象”,“是让人有彻骨之寒的一个人物”[9]。七巧的不幸起源于娘家人的贪财势利、不讲亲情,她是以一个被亲人出卖的“被害者”的身份出场的,这桩封建买卖婚姻正是她一生悲剧的开始。可以说这时的七巧是让人同情的——唯一的亲人将她推向火海,亲情在她身上是一片空白。婚后的她常年守着活寡,却因出身卑微而得不到婆家任何一个人的关爱、理解和尊重,甚至连下人都不拿她当回事,亲情于她而言,更成了遥不可及的东西,她“自己也知道这屋子里的人都瞧不起她”[10]。她孤独地挣扎着,在这冰冷的世界中,“兄嫂给她的是屈辱和辛酸;残废的丈夫给她的是压抑和厌恶;左右的人给她的是白眼和作践”[11]。她只能以泼辣和口无遮拦的诉说来向别人不断地强调着自己的存在。
亲情的缺失本应让七巧更加理解爱的意义及价值,可分家之后,她在带着长白和长安独居的日子里,却陷进了失去金钱的恐慌和敏感中,她变态地残害女儿和儿子,变成了一个可怕的魔鬼母亲。“当人的理性不断地剥落直至最后完全毁灭”时,“这个人就已经不是人,而是个疯子,但她又有‘疯子的审慎与机智’,那就是人性中的‘魔鬼’”[12]。曹七巧恋子妒女的变态行为让她成了一个“魔鬼似的疯子”,她是“人类堕落历史的象征”[13]。七巧不仅没有把自己缺失的爱与亲情转化成对儿女的悉心呵护与万般疼爱,相反,她还把自己的不幸加倍转嫁到孩子身上。此时的七巧仿佛已不是一个母亲,而是一个敌人,一个杀人不见血的恶魔,她仇视一切带有爱和幸福的东西并且用变态的手段去摧毁它们,制造了长安和长白一生的悲剧。女儿长安找了个留学生童世舫,脸上带了点笑容,她见了就有气。童世舫第一次登门拜访,长安还未露面,她就好像等不及了似的对童世舫说:“她再抽两筒就下来。”[14]一句话使童世舫脸变了色,婚事告吹,七巧亲手葬送了女儿的幸福。对儿子长白,七巧又有着严重的恋子情结,想像占有黄金那样占有儿子,任何和她争夺儿子的人都成了她的冤家对头。长白娶妻子,她处处和儿媳过不去,用刀片似的语言“杀”死了两个媳妇,以致“长白不敢再娶了,只在妓院里走走”[15]。在这个过程中,血缘亲情被金钱这个利剑一寸寸摧毁。
家本来应是温馨的港湾,是庇护和关爱子女成长的所在,而七巧给予儿女的却是一个充满冷暴力的无爱的家庭氛围。在亲情中,她和儿女都被推向了一道深渊,一种悲剧的连环!一如方方的小说《风景》中所描述的:在一个河南棚子家庭,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姐弟之间,弥漫的尽是暴力,相互间以伤害为快乐。这又与张爱玲《半生缘》中的曼璐有着某些相似,曼璐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为了拴住祝鸿才的心,不惜牺牲妹妹曼桢,理直气壮地毁掉了曼桢一生的幸福。
相较而言,作品中对灯芯这方面的描述就没有那么精彩和明显。灯芯背后一直有一个后盾,即指点道路的父亲刘松柏,嫁进下河院就是父亲的意愿。或许灯芯隐约能体会父亲的苦心——完成姑姑松枝未完成的心愿,与父亲里应外合,一步步完成他们的计划。灯芯将父亲的指点视为对自己的爱,可通读全文,我们不禁怀疑:灯芯的中医爹当初的决定带给她的是幸福吗?或许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也或许女儿只是他的一步棋而已。在下河院,灯芯对丈夫、公公、儿子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是亲情使然,但细究起来,却又让人无法确定。对公公,灯芯是小心翼翼地察言观色,在这个特殊的大家庭中,这对翁媳之间的关系是敏感而特殊的。公公对灯芯是一边考验一边又不由得大加赞赏,却吝于表达——他只是放在心里,或只流露于细节而含蓄不语。说实话,灯芯对这个家还是上心的,“这段日子,灯芯在给公公和命旺缝冬天的棉袄和棉裤。这些活往年都是奶妈顺仁嫂做的,今年她想自己缝”[16]。这些都透露出了她对这个家的维护,对公公与丈夫的关心,但这种维护与关心背后却又隐藏了一种暗暗地较劲和利益关己的算计。这个家及家中的所有成员,甚至是奶妈仁顺嫂,都是对她藏了心机的。她很少能感受到亲情的温暖,公公冷淡而严肃,丈夫命旺痴傻且时常癫狂,她要保住自己的地位,防止下河院有一天落入他手,就要拿出十二分的智谋来不断地获取斗争的胜利。于是,窥视整个下河院的管家六根,偷油贼马巴佬,惹是生非的李三慢、日竿子、芨芨,精明过头的七驴儿,可恶可憎的二拐子等,相继被她除掉。对此,她怕过,“我怕,我怕啊,老天爷,求求你了,再也不要让血腥出现,再也不要让沟里陷入到没完没了的搏杀中……”;“少奶奶灯芯的怕是打管家六根死后开始的,等马巴佬让乱石打死,这怕,又深了一分”[17]。但这种怕并没有阻止她去实施一个又一个杀人计划,她把捍卫下河院,准确地说是捍卫“下河院那些雪片一般来流水一般去的银子”,当成了自己的绝对使命,“她必须要捍卫,否则,不等她把命旺冲过来,怕这下河院,就让那些看不见的黑手连抢带掠地给弄成了个空架子,那么,她豁了命嫁来,还顶啥用?”[18]因此,在她的逻辑里,这些人都是自己作孽找死的。马巴佬让乱石打死,她比任何人都痛苦,“仇是甚,恨又是甚,比起命来,哪个重要?”[19]但倘若她再不依计行事的话,那马巴佬兴许还在活泼乱跳地把油偷运出去赚私钱呢,“要不是不思悔改的马巴佬再起贪心,她是说甚也不走那一步的。是他逼的呀!贪,贪,你到底贪个甚?”[20]“三年大灾带给她的感受太深了,打内心,她不想再死人,真的不想,可……”[21]。就这样,灯芯由被害到反击再到害人,一步步地滑进了罪恶的深渊。
四、追金逐权,终究被欲望的深渊吞噬
曹七巧和灯芯在封建家庭中同各种力量的斗争,矛头的指向都是金钱和权力,只不过在此过程中,两者采用的方式和获取的“成果”存在着差异而已。
曹七巧对金钱的追求是执着的、热烈的。她不甘心自己牺牲了终身的幸福换来的只是“二少奶奶”的虚名,她要寻求补偿——情感补偿既然得不到,那就只好在钱财方面找补了。她越来越明白,只有金钱才是最实在最可靠的了。于是,她咬紧牙关苦熬死守,终于熬到了丈夫和婆婆去世,盼到了分家的那一天,这“是她嫁到姜家来之后一切幻想的集中点。”[22]此前,她已对姜家在青岛、天津、上海、北京等处的房子和地产作了调查,分家当天她又使出了麻油店女儿泼辣的本事哭诉自己的艰辛,但最终“孤儿寡妇还是被欺负了。”[23]她用黄金的镣铐锁住了自己,心中无爱,财富便成了她唯一的追求。为了守住这能给她安全感的金钱,她异常谨慎和敏感,成了一个视财如命的守财婆。对自己幻想多年的至爱季泽的来访,她心中先是充满了浓情蜜意,但一转念她的天平立即转向了金钱。她神经似的暴怒,疯狂地将他逐出家门。侄儿春喜陪长安玩,她也厉声对春喜吼道:“你那狼心狗肺,你道我揣摩不出么?你别以为你教坏了我女儿,我就不能不捏着鼻子把她许配给你,你好霸占我们的家产!”[24]有人给长安做媒,若是家境差一点的,她便疑心人家是贪她的钱,长安的婚事就这样被耽搁了下来。金钱是这场悲剧的总导演,它瓦解了人性的善与美,扭曲了正常健康的欲望,摧毁了人与人之间的脉脉温情。“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她知道她儿子女儿恨毒了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她娘家的人恨她。”[25]
七巧对金钱的渴望走向了一种变态的疯狂,这也更加暗示了她内心的空虚。但总体来看,她对金钱庇护的手段是简单的、明显的、直白的,不含一些弯道和心机,她对所有的人喊出来:“我爱黄金!”
同样,灯芯真正关心的只是银子,“是的,银子,这才是灯芯所关心的根本”[26]。命旺是富得难以想象的下河院的独苗,嫁给命旺,就等于嫁给了金矿。这是她甘愿给奄奄一息的命旺冲喜、忍受一切痛苦委身于下河院的根本原因。“比之男人命旺的死活,下河院那些雪片一般来流水一般去的银子,才是她发誓要捍卫的东西。”[27]为此,就是付出再多的代价,她认为也是值得的。较之曹七巧,灯芯追金逐权的手段更多、更高明,也更大胆精细。灯芯在嫁入下河院之后,在父亲的引导和自己的观察下,不露声色而又机智勇敢地和各种不利于己的势力斗争着。聪明的女人有时是可怕的,灯芯没有七巧的大呼小叫及面上的那股泼辣劲,她理智地一步步实行着精明而有魄力的计划。她的大计划是从收拢菜子沟人心开始的。新媳妇未开怀就出门,按照下河院的规矩是该罚的,但她却理直气壮地走出下河院,并和菜子沟的老老少少打成一片,完全没有少奶奶的架子,让沟里的大人孩子受宠若惊,个个都觉得这新人不一样——亲切!“灯芯会时不时在某个场上停下来,跟赶着毛驴转的沟里人聊上一阵,有时也会冷不丁抱起场上玩耍的孩子,亲热的咬上一口,那一口立即就让她跟沟里女人亲近。少奶奶灯芯会给年迈的朱二奶奶梳头,呦嘿嘿,真是个新鲜事。”[28]这一连串对沟里人的亲近热乎的举动是让人开心的,不知不觉间少奶奶灯芯的口碑好了起来,这也为她和管家六根的斗争打下很好的群众基础,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
灯芯更多的聪明和干练显示在和管家六根争夺下河院权力的斗争中。她不动声色地摸清种种明暗关系,干净利落地除掉管家六根;为封住菜子沟男女老少的嘴,巩固自己的地位,她先和二拐子偷情借种,后又和七驴儿苟且;“为了维护她的‘尊严’和利益,她又一一设计铲除了二拐子和七驴儿”[29]。在这一系列的运筹帷幄中,我们看到了灯芯“作为一个女人少有的魄力和心计”[30],但说实话,她的这些聪明和干练的言行又无不让我们脊背生凉,脚底起寒;没有这些筹划与谋杀,我们是怎么也想不到灯芯的心竟能狠毒到如此地步的。
不过,灯芯在长达三年的天灾中仍能做出“坚持舍饭赈济灾民的义举”,能和下河院的长工一起赶着百头牛羊长途跋涉奔赴凉州城变卖,并在途中露宿荒原遭遇一群饿狼之时能和长工们共同战斗,是让人敬佩的。她获得了下河院的绝对权力,但又未像七巧那样守财如命。她将南山煤窑全部交给草绳男人管理,将油坊交给木手子经营,煤窑和油坊的入项双方五五分成。如果说七巧是极端的、刻板的,那么灯芯则是灵活的、理性的。可不论怎样,她们能止住对金钱和权力的贪恋与追逐而回归纯善吗?她们最终是否真正得到想要的东西了呢?也许,七巧至死也不会明白她是多么地令人讨厌,即使知道了,她也会破罐子破摔,她根本不懂得她最该珍惜的是什么?她宁愿戴着“黄金枷锁”凄惨孤独地死去,也不愿相信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儿女。可灯芯又如何呢?灯芯是有脑子的,可她还是要除掉一个个异己,她觉得她必须那样做,只能那样做,“不要怪我,谁也不要怪我,都是你们自找的!”[31]其实,无论是七巧,还是灯芯,她们最后都已被欲望——对金钱和权势的贪欲——的深渊彻底吞噬而难以自救了。
五、不约而同的作品指向——命运的深渊
如果说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多少有些偏执,性格中多少有令人不安的畸形成份,是趋于变态的言行让她变成了一个恶魔的话,那么,许开祯笔下的灯芯则多少是令人敬佩的、让人能接受的,有魄力的一个大女子。
的确,七巧没有享受过真正的爱和正常的夫妻生活,在这方面,她是一个“被害者”,但这不能成为她去葬送别人幸福的理由。被害本身已是悲剧,而害人则是更大的悲剧。我们知道,张爱玲关注的焦点始终是人性,对人类本性的书写是其最高命意,她以一个女性真实的体验和独特的人生感悟平静地展示了人性丑恶的一面,辛酸而不无美感地反映了生命的本来面目:一切都是赤裸裸的真实,有美也有丑,有爱也有恨,而且爱在一点点地毁灭。因此,“《金锁记》中曹七巧这一人物”,“被论者誉为‘新文学中最复杂、最深刻、最成功的妇女形象之一’”[32]。
与此同时,笔者认为许开祯笔下的灯芯也可算得上是当代文学中不可多得的、成功刻画的女性形象。
灯芯从“冲喜”出场到“痛失”中最后亮相,她的性格和生活是多元化不断发展的,也是立体而丰满的。她从一个不谙世事被人当成“冲喜”工具的少女,到成为主宰下河院一切的主人,走过十多年的人生道路,成熟了,也复杂了……作为一个艺术典型,下河院少奶奶灯芯的形象还是很耐人寻味的,可以说是继《红楼梦》中王熙凤之后又一个值得注意的女性典型[33]。
通过对《金锁记》与《深宅活寡》的再度解读及对七巧和灯芯的形象论析,我们惊奇地发现这两部作品的创作时间尽管相差了半个多世纪,却有着不约而同的指向——命运的深渊。
七巧和灯芯同为女人,同为大院媳妇,一个想用金钱控制生活中的一切,一个想借权力叱咤风云、捍卫财富,但最终的命运结局都是一样的——曲终人散,梦想破灭。曹七巧一路走来,她的悲剧一开始就有着命运无法摆脱的戏弄,虽然她后来的发展更多的是自己主动选择的结果,但我们也不难明白作者的言外之意——每个人都无法真正地摆脱命运的安排,当你走上一条通往深渊的路时,你的一生就绝不会终结在无忧的天堂。我们同情七巧的遭遇,理解她的境况,但随着人物性格的发展畸变,我们在对她的感情里,憎恶已经大大超过了同情和理解。可以说,即使曹七巧最后能够成功地让姜公馆里的每个人对她既喜欢又信服,她也不可能阻止这个封建大家庭的衰败,而她自己——一朵本该美丽绽放的女人花,也会凄惨地凋落于其中。较之曹七巧,灯芯可以算得上是玩弄权势的高手。她有着那些庸常女人所没有的智慧和魄力,同时还不乏柔情,这些都让我们对她心生敬佩和喜爱之情,可她为了扫清障碍而表现出的狠毒冷酷又让我们倍觉恐怖。许开祯通过《深宅活寡》,向人们充分地展示了他的“善于运用多种笔墨描摹复杂社会生活的能力”,他“也通过描写下河院里勾心斗角的故事”,告诉人们“不管东家庄地如何精明,少奶奶灯芯如何能干,这座百年的封建大院仍然逃脱不了衰败的命运”。这是历史的必然,是大势所趋[34]。
六、结语
悲剧的婚姻,虚幻的爱情,对金钱权势的热望与追逐等,把七巧和灯芯这两朵本可以散发出迷人清香的“女人花”推向了不知底的深渊,直至无声凋落。婚后,她们都有过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挣扎或反抗。然而,七巧的挣扎多出于本能的自保,很多时候,是无力且无果的,这使她越来越神经质,她戴着黄金铸就的“枷锁”,异化为一个以折磨家人为乐的变态狂;相较而言,灯芯的反抗则有着主动出击的意思,她是背负着使命嫁到下河院的,一开始她就是父亲谋夺权产的一颗棋子。在下河院的明争暗斗中,在与周围人的智勇相较中,她也变了,变得狠毒、自私、阴险、冷硬,堪比王熙凤。她良心未泯却又为了权益而残害他人;她悉心照料着精明的公公、残弱的丈夫,有发自本心更有暗中较劲的成分;她时刻小心不敢懈怠,因为她深知和他们紧密相连的,是整个下河院的财富和绝对权力。可以说,七巧和灯芯,是两朵红尘中的女人花,是两朵不同时空下凋落于同境深渊中的女人花,因为无论她们以怎样的方式向旁人宣示着自己,最终,她们都无可避免地随着身处的深宅大院一起走向了衰败。
对于七巧,张爱玲的态度是冷然的、理智的,到了后来,作者甚至是引领着读者一起来厌恶她;对于灯芯,许开祯则是爱恨交织的。作者如此,读者又何尝不是?这两部作品给我们昭示的最终指向不就是:谁也无法摆脱命运的深渊吗?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是多么聪明且善于算计或是愚蠢地自以为是,无论你拥有多少财富,握有多高的权势,你都无法改变命运的最终安排。
[1]张爱玲:《张爱玲典藏全集》(散文卷1:1939-1947年作品),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第99页。
[2][3][4][5][6][10][14][15][22][23][24][25]张爱玲:《张爱玲典藏全集》(中短篇小说:1943年作品),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第45、45、21-22、22、24、6、43、45、16-17、19、25、45页。
[7][12][13]万燕:《女性的精神——有关或无关乎张爱玲》,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9、36、39页。
[8][16][17][18][19][20][21][26][27][28][29][30][31][33][34]许开祯:《深宅活寡》,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4、69、277、35、256、256、277、35、35、37、2、2、283、2、1页。
[9][11][32]刘立杰:《爱的失落泯灭了她的人性——也谈〈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形象》,《北方论丛》,2000年第5期。
"The Women Flowers"Which Had Withered in the Abyss——The Discussion About the Images of Cao Qiqiao And Deng Xin
ZHAO Qing
(The Chinese Department of the College of Huaiyin Normal University,Huai'an 223300,China)
The Golden Cangue;Cao Qiqiao;A Widow In A Deep House;Deng Xin;abyss;desire
In the 1940s,Eileen Chang used the whole narrative way to depicted an tragical"widow"image for us in one of her masterpieces—The Golden Cangue.This woman image was Cao Qiqiao.Not coincidentally,Xu Kaizhen,a writer of the new generation in twenty-first Century,used the same way with Eileen Chang's to depicted an tragical"widow"image for us in her famous long novel which was named A Widow In A Deep House.This woman image is Deng Xin,a complex and solid character.We may say that Qiqiao and Deng Xin were two woman flowers who were in the same space-time had withered in the similar abyss.They had some exploring similarities,also had remarkable strange glory.Some things made them fade in fresh color,such as the unequal and tragic marriage,the illusory love,the controlling to money and power,etc.
I207.65
A
2095-5170(2014)03-0024-07
[责任编辑:周 棉]
2013-06-16
赵青,女,江苏宿迁人,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曹七巧形象的另一种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