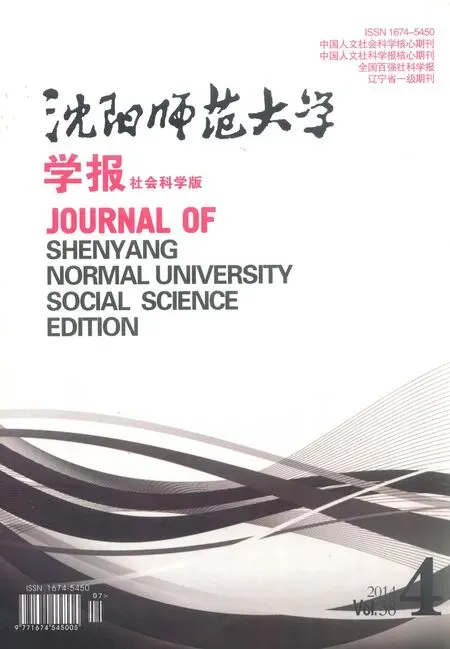蒙古族民间童话中蟒古斯形象与少年的弑父情结
李 芳
(包头师范学院 科技处,内蒙古 包头 014030)
平魔故事又叫镇压蟒古斯故事,属于蒙古族童话故事的一种。这类故事的基本情节是:蟒古斯侵犯草原——少年(或者可汗)受命与蟒古斯作战——少年战胜蟒古斯成为英雄。故事中的反角——蟒古斯也称蟒古思、蟒盖、蟒嘎特害等,是蒙古族民间文学中对恶魔形象的统称,它是一种多头的蟒蛇,穷凶恶极,变化无常。这一形象源自蒙古族神话,经过蒙古族英雄史诗、民间童话的丰富和充盈,逐渐凝固成典型的恶魔原型。在神话中蟒古斯作为恶神的出场,其与善神的征战及其最终被征服,反映着早期人类关于善与恶的二元思考。当其进入民间童话以后,由于人代替神成为了故事主角,这类故事表现的重点开始向人位移,人与自然的冲突、人与社会的冲突、人的内心冲突逐渐上升为主导,于是蟒古斯的象征蕴意变得多元起来。关于蟒古斯的象征意蕴在学界基本达成共识,仁钦·道尔吉、赵永铣、陈岗龙等都一致认为它是自然灾害和社会恶势力的象征。如在《蒙古族文学史》中就有这样的概述:蟒古斯“既象征了草原上使人类和牲畜面临灭顶之灾的瘟疫、虫蟊及变化无常的恶劣气候等自然灾害,又是对嗜杀、掠夺成性,使草原惨象环生的奴隶主及一切邪恶形象的比喻。”[1]但笔者认为,作为降妖除魔故事中的“恶魔”形象,它的“能指”绝非仅限于来自外在的侵略行为,更应该包括来自人类内在的邪恶或者困扰心灵的“心魔”。尤其民间童话,它所“关心的不是有关外部世界的有用信息,而是发生在个人心中的内在变化过程”[2]。恶魔形象的象征意蕴更可能是来自人类内心的魔。而对于民间童话最重要的接受群体——少年来说,这个“心魔”很可能是父权。如果这种假设成立的话,那么蒙古族民间童话平魔故事(镇压蟒古斯故事)就极可能是蒙古族少年成人仪式的隐喻,只有通过了斩杀蟒古斯的考验,蒙古族少年才能顺利地被成人社会所接纳,进而取代“父亲”在家庭与社会中的位置。
一、蟒古斯与父权
作为构成蟒古斯这一形象最基本的动物原型——“蛇妖”在中外民间文学中相当常见,这些故事在不同程度上体现着原始人关于蛇的图腾。关于图腾之起源的说法很多也很复杂,但就猛兽图腾的起源,国内外的学者多倾向于因恐惧而认亲求安的说法,将之称为“父亲”“祖父”“爹爹”“兄长”等,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得到庇护并免于伤害。有两方面因素构成了蛇崇拜的主线条:一是死亡,蛇妖被看作是邪恶的化身,在故事中常常扮演“吞食者”“劫持者”“冥国的守护者”等与死亡密切相关的角色。二是生殖,它的外形与男性的生殖器十分相似,而且它能够长达几个小时交配,充分显现了男性的能力和强大的繁殖力。尤其是多头蟒蛇,更将其强大的生殖力量招摇于世,无数的蛇头将男性的力量强化到了极致。流传于世界各地以头生育的神话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这种“以上易下”的神秘对应。如果单纯地将蟒古斯理解为外在的自然灾害或社会恶势力的象征,很可能只关注了死亡这一主线。而事实上在平魔故事中,蟒古斯强大的生殖力也是故事强化的恶魔特点之一,它到处劫掠美女,占为己有,而且据《征服蟒古斯》[3]38-50故事中讲,母蟒古斯马鲁勒一下能生出9999个小蟒古斯,这些蟒古斯一离开母体就可以参加战斗,这也从侧面影射了多头蟒古斯强大的繁殖力。于是,我们是否可以预设,蟒古斯形象是与性别有关的,它与拥有掌握世界能力的男性,或者说“父亲”具有直接的对应关系。我们这里探讨的“父亲”,既包括生理意义上的父亲,也包括文化意义上的父亲。将“父亲”上升为一个文化的概念以后,其外延就产生了相应的扩大:它包括有着血缘联系的父亲,包括与父亲有着同样文化背景的父辈,包括一个族群或国家的统治者,即一国之父,也包括被人们推崇为神的父神。
没有人能肯定在民间文学作品中蛇妖最初的性别就是男性(父亲),甚至在印度和中国的神话中蛇神皆为女性的化身,但可以肯定的是,当人类进入父系社会以后,部落和族群的神和祖先就多与父亲有关了。父神(Father-god)替代母神(Mother-goddesses)统治了人类,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父权制绵延至今。蒙古族民间文学中的蟒古斯形象在进入英雄文化时期以后,多头蟒蛇的形象逐渐清晰和固定了下来,与蟒古斯作战成为蒙古族父权氏族时期以男性为首要地位的征战文化的再现:男性与自然的抗争,男性与恶势力的抗争,男性之间对于权利、土地、财产和美女的争夺大战。蟒古斯作为征讨对象,其性别特质自然也是指向男性的。当然我们不能否认,产生于母系社会的蒙古族民间文学中的蟒古斯形象最初可能是女性,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进入民间童话时期,蟒古斯形象作为男性的可能性就更大了。无独有偶,在很多民间故事中,对于男性恶魔和女性恶魔的称呼也有区别:男性称为魔,即蟒古斯;女性称为妖,即姆斯。只是后来进入阶级社会以后,蟒古斯故事的社会性不断加强,蟒古斯有了亲属和部下,于是蟒古斯妻子,蟒古斯女儿以及蟒古斯喇嘛的形象才逐渐多起来。在讲故事时也逐渐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当提到“蟒古斯”时,它多指向公的;如果是母的,一般都会冠之以“母蟒古斯”或“蟒古斯妖婆”;当提到它们的女儿时,直接会称之为“蟒古斯女儿”。
当然,将“父亲”象征为蟒古斯,这绝非现实的存在,而是基于作为梦幻的文学世界而言的,尤其是民间童话,它的幻想属于荣格所说的“非个人性质”的幻想,它无从归结到个人过去的经历上,因此也就不能作为个人的现象来解释,它与一般人类心理的某些集体无意识相对应。“它们就像人体形态因素那样,是遗传的”,“原型出现在神话和童话故事中,正像它出现于梦幻和精神病患者的妄想之中”,它是集体无意识的投射和表达。[4]其实,将父亲恶魔化的提法早已有之,在文学作品中这种倾向也相当常见。《说文解字》对“父”字的解释是:“矩也,家长率教者,从手举杖。”父亲是一家之主,在家庭中地位至尊,凌驾于整个家庭成员之上。马林夫斯基对此也做出过相当精当的分析:“我们的社会里不论种别和社会阶级的分别,父亲都还保有父权制的地位。他是家庭的头目,血统的联络者,也是经济的供给者。”“在父亲面前,子女是要循规蹈矩,振作精神,并且有所举动和表现。父亲是权威的根源和责罚的由来,所以他就变成一个恶魔。”[5]恐惧什么,什么就成了心中的魔,这是人类原始崇拜的根源之一。对于孩子来说,在家庭中,这个魔是父亲;在社会里,这个魔则是比血缘父亲势力更强大的父权世界。
二、杀死蟒古斯与弑父
在平魔故事中有一个反复出现的意象,那就是英勇的少年提着战刀将蟒古斯的头一个个地砍下。该意象总会出现在故事的高潮,成为故事中最抢眼的一幕。如《云青马》[6]645-648中,“胡德尔骑着神奇的云青马紧紧尾随,一直追到了居延海的西边,一刀砍下了魔鬼(蟒古斯)的头颅”。再如《阿能莫日根汗》[7]中,“当阿能莫日根汗砍掉十五颗头黑莽古斯的主头时,士气大增,其他勇士们像割韭菜一样,一个一个砍掉了其它十四颗头”。又如《格斯尔可汗铲除十五颗头颅的蟒古思昂得勒玛》[8]中,“格斯尔汗再次举起九庹磁钢宝剑,照头砍那昂得勒玛,只听得‘当’的一生,火星四溅,如同砍在岩石上一样坚硬无比,如同碰在冰山上一般,滑开了宝剑”。如果说蟒古斯是“父亲”的象征,那么在平魔故事中不断出现的“砍杀蟒古斯”原型作为儿童的集体无意识,即象征着男孩弑父心理的实现。而像《兄弟战蟒古斯》[3]102-107《七兄弟斗蟒古斯》[6]708-710之类的作品则反映出子一辈联合起来推翻抵抗父辈的斗争。
前面我们提到,多头所象征的含义中有强大的生殖力的蕴意,那么砍头则象征着对父亲的阉割,这是对作为男权象征的父亲的彻底摧毁,同时也宣告了父亲的永久死亡。“子阉父”原型在希腊神话中的父子大战中就有呈现,赫梯神话中更有儿子咬掉父亲阳具的情节。人类学家列举过很多事实来证明,儿子阉割父亲是一种反抗父亲性政治的被迫之举,是长期降服于来自父亲的阉割恐吓的爆发与宣泄。这里我们不想探讨流行于世界各地的“割礼”对儿童身体的实质性的益处,就“割礼”行为本身带给儿童的心理恐惧与创伤就足以成为一代代儿童永远的梦魇。如果说身体“阉割”的痛苦可以通过时间的流逝渐渐消失,但是心理阉割之于子辈的却是一种人格的异化和永久的臣服。心理阉割作为身体阉割的“并发症”,其后果更为可怕,它消解的是子辈叛逆的原初动力和行动的效力。“自从有了阉割的伟大发明,人类意识到可以有效地改变生物的先天病性,训话野性,减弱攻击性。在简单质朴的经验性推力作用下,人们误以为雄性动物的性器就是其也行和攻击性之根源,一旦失去了此物,动物就显得温顺起来;而当人的阉割流行之后,人们同样发现性情方面的类似变异”[9]153。在现实世界中,驯顺是不贰的选择,然而在心理世界,反抗却成为挥之不去的主旋律。“正是这一激烈地反叛父权的举动,象征儿子彻底消解了父亲对自己的性压制,从而获得了显意识中向往已久的性自由。”文学世界的“子阉父”原型“充分显示了人类学家和生物学家所共同关注的雄性之间以性为中心的代际冲突”[9]37。这是少年走向成人的真正意义的成人仪式。万建中曾就成人礼与恶魔形象做过分析,他认为,“成人礼,作为‘过渡仪式’要求受礼者从原有的生活环境中走出,要求受礼者和妇女完全脱离,不能像从前一样无拘无束地与妇孺交往。从甜蜜温馨的母权世界过渡到竞争激烈的父权世界,这一转变给长期沉浸在母性关怀的部落少年所带来的心理冲击是巨大而又可怕的,必定会造成受礼者的抵触心理。…………于是父权阶层被投射为狠毒的天神或恶魔”[10]。
更有意味的是,在很多蒙古族平魔故事中,不仅是蟒古斯的身体,甚至是蟒古斯的灵魂也要受到追杀。如《有九十九个儿子的汗》[11]《格斯尔可汗铲除十五颗头颅的蟒古思昂得勒玛》等。应该说这样的故事情节反映了原始人类“灵魂寄存于体外”的观念,相信灵魂可以长期或暂时离开身体,灵魂的最终死亡才代表生命的终结。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作为精神存在的灵魂与思想、文化密切相关,因此杀死蟒古斯的灵魂是否代表着将施加于子辈的“性压制”的文化根基彻底铲除。因为只有铲除这种文化根基,子辈的自由时代才能真正来临。
三、结论
平魔故事应该属于与蛇妖作战母题一类,这类母题极其古老。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或者说国家观念形成以后,发达形式的与蛇妖作战的故事几乎在世界各地都有流传。普洛普认为,“与蛇妖作战的母题是从吞食的母题发展而来的。吞食最初是一种在授礼时举行的仪式,这个仪式赋予青年人或未来的萨满以神力”[12]。由此可知,平魔故事的历史根源即是古老的成人仪式,通过这种仪式,少年从孩童进入成年人的行列,并被氏族部落接纳为正式成员。很多思维定式都是在人类发展历程中经历“生理——心理——文化”模式凝固而成的,如果说原始部族中的成人仪式是一种以生理行为为中心的仪式,那么随着社会的发展,仪式的逐渐消亡,成人仪式则可能内化为一种心理活动(一种在心理上的“弑父”),甚至上升为一种隐形的文化意识。民间童话正是这种隐形文化意识的最好呈现。蒙古族民间童话借用蟒古斯压迫及其被消灭,将少年推翻父辈走上人生舞台的过程仪式般地呈现在故事中,这也许是解开为什么少年成为平魔故事“真正的接受者”的原因,只有他们真正被这种故事打动,为之着迷,并将其上升为人生的终极理想。平魔故事顺应了他们心里欲求,并赋予了他们成为伟大的人的希望。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少年童话。
[1]荣苏赫,赵永铣.蒙古族文学史:第一卷[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325.
[2]贝特尔海姆.永恒的魅力:童话世界与童心世界[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5.
[3]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文化馆,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民间文艺研究会.前郭尔罗斯民间文艺资料之五蒙古族民间故事[M].松原: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印刷厂,1982.
[4]阿兰·邓迪斯.西方神话学论文选[M].朝戈金,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327-329.
[5]勃洛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两性社会学:父系社会与母系社会之比较[M].李安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9.
[6]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内蒙古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内蒙古卷[M].北京:中国ISBN中心,2007.
[7]哈达奇·刚.内蒙古民间故事全书·阿拉善右旗卷(下)[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1:584-587.
[8]张锦贻,哈达奇·刚.寻找第三个智慧者[M].昆明:云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1:1-11.
[9]叶舒宪.阉割与狂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10]万建中.中国民间散文叙事文学的主题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44.
[11]王清关巴.蒙古族民间故事[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139-161.
[12]普洛普.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M].贾放,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