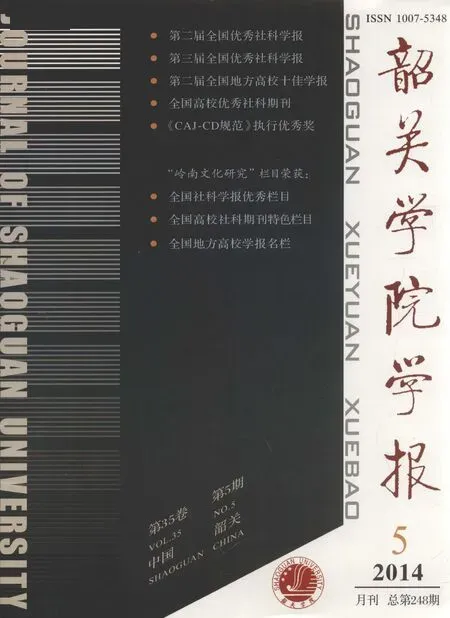主体的困境与救赎——《织工马南传》中的主体建构
周秀华
(广东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0)
马南的生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他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在灯笼广场生活,快乐而自足,却遭好友陷害同时失去了对宗教的信仰和人的信任。第二个阶段他蛰居在拉维罗村的边缘,几乎与世隔绝,像昆虫一样机械的劳作,但并没有驱走他的孤独。第三个阶段因养女哀皮的出现,他又充满了希望和幸福。无论在哪个阶段,作为一个形式上的主体,为了生活能够正常运转,马南都必须对这个主体进行不断的建构。可是这个主体又应该如何进行建构呢?拉康认为,人的存在属于承认的法则,所以人总是在他人的话语中参证自己。离开了他人和他人的话语,主体就无法对自我进行有效的建构。“现实生活中的人与人之间通过言语互相呼唤、质询和应答,每一天每一刻建构起主体”[1],即使这个人将自己孤立于他人,拒绝与周围的人发生任何实际言语意义上的应答,这也并不意味着这个人对自己的主体建构就会停止。他的孤立、沉默,或许还有对外界的冷漠或敌意都将投影在无数个他人的眼中,映照在一面没有人可以摆脱的社会之镜中。
拉康的主体建构过程永远摆脱不了他者的介入和控制。首先,在想像关系的镜像阶段,主体对自我的概念是从他人(小他者)和虚幻的镜像中获得的。其次,在以语言能指主宰的象征世界中,他者就是那个借助语言而在任何关系中涉及的一个场所。主体在这个言说的关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主体无法逃脱这个巨大的象征之网,他可以选择在这个他者的场所对自己进行积极的构建,通过不断地向前“投射”自己而被言说和定义,塑造一个完整的主体形象,过着人的生活。主体无法停止对自己的构建,为了生存下去,他必然面临着选择,无论他的态度或生存状态是积极活跃还是沉默退避,只要他做出了选择,他就是对他人,对生活的质询做出了应答。通过这个应答,他已然承认了他人的存在,承认了主体与他人之间存在的无法切割的关系,同时也承认了那个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他者对自己的主宰。
一、主体的碎裂
在马南来到拉维罗以前,他的生活像条平静的溪流,在上帝的指引下,在工作有条不紊的节奏中缓慢地向前流淌,充满了有方向、有目的的安心。在灯场这个隐蔽的小天地里,马南是“很受尊视的……他是出了名的有模范的生活、热诚的信仰”[2]8。在这个工业革命前夕,由圣公会教所统治的狭小世界里,这群没受什么教育的小手工业者生活的中心就是工作和信仰。人人都仰仗上帝的救赎,一个人是否信仰虔诚关乎到这个个体的罪可否被赦免和天堂之路是否为他开通。尽管灯场在这个小团体的教义中,个人的救赎是由上帝来拣选和决定的,但是一个人的虔诚和坚定难道不是他被上帝选中的最好的佐证吗?在这样的前提下,马南又是如何来认识和建构自我的呢?在拉康的理论中,个体的人是无法成为认识对象的,我们所要认识的是,是什么建构了一个这样的主体。“一个人只能在他人身上认出自己”,只有通过他者这个介体才能成为其所是之人[3]。在马南灯场生活期间,上帝是一个自始至终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大他者,以他的全知全能控制和影响着人们的观点和生活。
作为一名织工,马南是贫苦的小手工业者中的一员。他们工作努力却收入甚微,他们满怀信仰,虔心敬奉上帝,怀着“死后灵魂必可获救”的希望,同时又夹杂着被上帝抛弃的恐惧。“非常活跃,富有想像,看重友情”,以及“生活堪称楷模,信仰又很虔诚”是马南从他人的眼中看到的自己的形象。而且,他非常努力地去构建这个形象:他在工作之余积极地参加教堂的祈祷和教会组织的各种活动,并且把自己的大部分收入都捐献给了教堂的事业。在这个阶段,他的每一分钱“都有一个目的”,他重视的是金钱的用途而非金钱本身。将大部分的所得献给上帝的事业让他快乐而有目的地工作和生活。因为信,他感到爱,包括上帝的爱、教友的爱和朋友的爱。信和爱使马南感到自己作为一个主体的完满。但是拉康式的主体一开始就是一个伪主体,这个主体是三个不同要素的不稳定的共存。首先是那个说话的身体,它是实际发言的无意识主体;其次是那个说话身体的话语中的“我”,即象征主体或者叫陈述的主体;第三是在镜像阶段所建构的想像的自我,它赋予了主体一个它实际上欠缺的身份[4]26。所以马南所感受的完满是建立在一个不稳定的基础上的,这个主体结构就像建于流沙之上的房屋,随时都有坍塌的危险。这个想像的自我虽然是一个误认,是从镜像之中和周围的人的眼神之中建立起来的,但是无论如何,它赋予了主体一种完满自足的感觉。
镜子超越了镜像阶段在生活中无处不在。通过镜子,人看到了一个自以为是完整的自己,并在想像的关系中给自己一个身份。每个人都会面临“我是谁?”这个关于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关于主体建构的问题。拉康认为,想像界、象征界和真实界是构成主体存在的三个维度。在生命的初始,主体需要依靠镜子或他人的目光、面容之镜来认识并认同自己的形象,这还属于主体建构的想像关系阶段。想像界“是前语言的,并依赖视知觉,及依赖于镜子的想像。婴儿误将镜中的那个整体的人当成自己,并且通过(错误地)认同这个理想自我而建立起自我统一感,由此虚构一个决无缺乏的自我”[5]。这种统一感和完整感对主体在社会中的正常生活予以最基本的支撑,尽管这种统一感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虚幻的。因为他的工作,马南在社会之镜中看到了一个织工;因为他的信仰,马南在教友的眼中看到了一个虔信上帝的教徒;因为他和威廉·德恩的友谊,马南在他人的眼中看到了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因为和萨拉的婚约,马南可以在未来之镜中投射自己作为丈夫的形象。将这些镜中之像综合起来,马南得到了一个看起来完满的自我形象。
这个看起来完满的自我形象,是借助他人才得以建立起来的,也是主体所构筑的一个想像的自我。但是镜中之像本来就是虚幻的,这也就决定了这个想像的自我,这个自以为统一的主体也是虚幻的。镜子本来也是不可靠的,镜中形象只是主体欲望的折射。因此马南所看到的自己作为一个“有着模范的生活、热诚的信仰”的人归根结底是一个虚幻的影像。但就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虚幻的影像,马南才能踏实快乐地生活,通过不断地向前“投射”自己的影像而创造一个有希望的看得见的未来。这样一个影像很快就被象征世界的残酷打碎了,马南的好友威廉·德恩陷害并诬告他盗了教会的钱。
为狭隘的教义所限,牧师和教友抛弃了对犯罪证据的搜集,转而求助于抽签的方式,让上帝来揭示马南有罪还是清白。虔信的马南相信全知的上帝定能让教友们看清是非黑白,然而,抽签的结果显示马南有罪。至此,马南对上帝的虔信被击得粉碎。马南并不像乌斯地的义人约伯,约伯在经历财产尽失、儿女皆亡,从头到脚生满毒疮的打击后仍然保持对上帝谦卑的信仰,而马南对上帝的虔信远没有这样坚韧,在他遭到上帝误判的一刻,他就抛弃了上帝——“从来就没有公正的上帝统治世界,只有说谎的上帝,诬陷无辜。”“可怜的马南心灵上绝望了——对上帝对人都失了信心。”[2]20在言语主宰的象征世界里,马南就是一颗任由言语摆布的棋子,被言语定义和言说。抽签事件发生过后,在他人之镜中,马南看到的是一个被魔鬼附身的、狡猾奸诈的贼的形象。在他者的言说中,他成了一个不可信任的朋友,一个连上帝也抛弃了的教徒。未婚妻萨拉对他的放弃进一步动摇了他作为一个主体的有意义的存在。在过去的灯场生活中,他藉了他人目光之镜所得到的完满统一的自我影像随着这些镜子的改变而变得支离破碎。在象征世界中由“言说”而编织的那个“我”也被现实的谎言鞭笞得鲜血淋漓、无处可遁。最终马南辛苦建立的主体被剥离得体无完肤了,他所能依靠的,就只剩下织机和工作了。最后,当萨拉和威廉结婚后,马南黯然出走,离开了灯场。
二、物化的欲望
离开灯场后,马南来到了远离市镇的拉维罗村,在荒僻的石坑附近找了个小屋住了下来,并以为村人纺麻织布谋生。拉维罗村村民的生活受自然的约束,所以除上帝外,他们还依赖巫术,相信巫术影响自然的非理性力量,所以在小孩生病或大人染恙等情况下,除了向上帝祷告,他们也向塔列的巫婆求助。这样的信仰跟马南过去的灯场宗教经验是迥然不同的。当然,除了因为工作与村民们进行简单的对话外,马南也完全无意与周围的人有任何交流,或与他们的生活产生其他任何交集。马南摒弃了上帝与他人之后,他从行动上将他者排除在自己的生活之外,免受他们的影响甚至是迫害。但是,他者是无处不在的,它就是那个全在全能的上帝。他者是主体无意识的场所,是言语活动得以展开的真正场所,它在主体的生存维度中占绝对的地位,人类除了认同它,似乎别无他法。“承认了他者的在场且与之进行认同,主体的言语才会得到他者的认可,从而得到社会文化的认可。”[6]102-104主体才能借助他人来解决自己破碎、无法独立这一难题。相反,拒绝了他者,就等于关上了进入以语言为载体的象征世界的大门,那么这个主体永远只能停留在以镜像关系为代表的想像世界。停留在想像世界是一件危险的事,主体于镜像之中得到的始终是一个自恋的自我,这样的主体最终只能限于癫狂。马南的癫狂体现在他对织布和工作的迷恋。他以一个教徒的虔诚来织布,又以一个迷途者的迷狂来崇拜他的金币。
如果说在象征关系中,主体的欲望是欲望着他者的欲望,期待他者的承认,那么在想像关系中,欲望则是要篡夺他人的欲望,占据他人的位置,这意味着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村人的好奇、蔑视、同情和猜疑同马南的冷漠、抗拒之间当然也是一种对话,只不过这是发生在想像层面的,没有回应、没有承认功能的对话。从马南一入村,他的影像就投影在村人的眼中了——面目苍白、目光呆滞、身形佝偻兼形迹可疑,他精湛的纺织技术也为他抹上了神秘、巫术的色彩。19世纪初的英格兰,尽管工业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人们对于职业的分化的见解还很落后,对特殊的“技术”仍赋予巫术的色彩。像马南这种具有纺织技术的人在拉维罗这样偏远的村庄非常少见。村民认为这样的人必有巫术的庇佑,或在背后与魔鬼有某种交易。马克斯·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描述道,拥有“特殊”技术的人,由于禁忌而与一般人(农民)的共同社会有所隔离,他们通常也不能拥有土地;这些人在拥有自然原料的古老团体中,先是以“闯入者”的身份提供技术,稍后则以定居在此共同体内之个别异乡人的身份提供其技术。相信每种特别的技术皆具有巫术性质的这种信仰,使得这种技术团体沦为贱民种姓,他们的行业与技术则被予以巫术定型化[7]。马南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进入拉维罗村的,所以他首先获得的是一种“闯入者”、“异乡人”的身份。
到了拉维罗村后,异乡人马南的生活完全被织机所占据,他仿佛变成了织机上的织虫——没有对过去的记忆或未来的展望,只有现在,没有其他的生活,只有工作。对金钱的欲望促使他把目光聚焦于面前的织机,其他一切都在他的视线之外。“欲望使人不安并促使他行动。行动源于欲望,目的是为了满足它,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通过否定、消灭,或至少是改变欲望的对象。”[4]51马南的欲望指向是由织布所换来的金银币。每天晚饭过后,他最大的乐趣就是抚摸闪闪发光的钱币,它们成了他孤寂生活的惟一慰藉。金币于马南而言,不是带给他购买和消费的乐趣,而是他的精神寄托和伴侣(如果他还有精神残存的话)。通过改变或消灭欲望对象的功能,欲望对象在主体那里变得比较可控而不受外在世界的影响。马南和他的金币的共存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但是,人作为欲望的“我”本身是空洞的,在“我”建立自己主体的时候,人内化了无数的欲望以建立“我”。而人与动物非常重要的区别在于,人的欲望不只是指向物,他还有为己和为人的更高精神追求。空洞的“我”的欲望如果只是指向物,那么,“它就会成为它所同化的东西——一个物性或动物性的自然的我。”[4]51因此,当金钱成为马南惟一的欲望对象时,他作为“人”的存在就停止了。他不再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而是与他的织机和金币融为了一体。他的劳动来自于他的本能冲动,而不再是有意识、有意义的。
但是马南这种动物性的存在由于铁匠的妻子萨梨·欧提斯的病而有了转机。马南小时候从母亲那里获得了一些草药知识,萨梨痛苦的样子勾起了他的恻隐之心,这慈善的举动使马南感觉“来到拉维罗之后第一次把过去生活与现在衔接起来。也许从此可以渐渐把他从织虫的生活中拯救出来”[2]20。萨梨的好转让村人认为马南一定有巫术,于是纷纷上门求药求符咒。这本是一个与拉维罗村民产生对话,与他们的生活开始交织在一起的很好的契机,但是马南拒绝成为村民所欲望的“欲望”。在这里,村民欲望的朝向正是马南所占据的位置:神秘的,有知识、技术和超能力的一个人物形象。当这个欲望无法得到满足时,村民因而对他生出敌意,在无意识层面上也是欲除之而后快的。对马南而言,村民只是可以为他提供钱币的载体,是他报酬的来源,他们的面孔、情感和欲望并不投射在已经物化了的马南的身上。物化了的马南也无法内化拉维罗村的习俗、文化、信仰和约定俗成的规则,而这些东西正是象征世界的主宰,是那个大写的他者。无视他者的存在,也就无法顺利进入对话的象征关系,无法心平气和地交谈,处于想像阶段的那种剑拔弩张的关系就无法消除。
三、主体的救赎
成了织虫的马南在这种物化的状态中生活了十五年,直到他所珍藏的钱币被盗。这些钱币就像马南的孩子,是带给他寂寥生活的惟一欢喜,失去金钱对马南来说无疑是最后的致命一击,他成了一个目光空洞、苍白瘦削的骇人的幽灵。本来,人欲望对象的位置由不同的人或物所填充,但是马南欲望的对象只有惟一的金钱,而可触并可控制的金钱在它主人的欲望里本来代表一种可以信赖、可以依托、永远也不会背弃他的某种关系,这也正是马南遭背弃后所要追求的东西。这种关系的打破促使马南寻求村民的帮助,并将他推入象征的大网,他和村民间的关系也开始缓和。
由于卡斯绅士的长子高佛来抛弃与他秘密结合的妻子毛丽,转而追求本村漂亮的南茜,毛丽气愤之下,于圣诞风雪夜抱着不到两岁的女儿来找孩子的父亲,却不幸死在路上。孩子从死去母亲的怀里挣脱,顺着路前方的灯光一直爬到马南的石屋里,在温暖的火炉旁沉沉睡去。而马南这时却由于癫痫症的发作失去知觉,僵立在门口瞭望远方,期待金子的返回。待知觉恢复,他深度近视的眼睛看到金子的光泽在将熄的炉火旁闪耀。马南为金子的返回欣喜若狂,当他伸手触摸时却摸到了孩子柔软的金发。马南收养了这个女孩,并为她起名哀皮,哀皮勾起了马南对过去生活的无限回忆,温暖、哀伤和爱的感觉又慢慢在他身上复苏了,冻结了的“人性”也开始融化——他的过去和现在作为人的存在冲破否定、压抑和摒弃的隔阂而浮现。这时,他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作为织虫的物性存在,而是因为与哀皮的关系而重新张开双臂拥抱那个象征的世界,并再次建构作为“人”的主体了。马南爱这个孩子,为了她的幸福,他愿意去做一切对她有益的事。拉维罗村民在马南失金、收养哀皮之后对他的态度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以前他们当他是 “一个有用的鬼怪”,现在他们愿意给他“坦白的笑脸,愉快的询问”,觉得他的快乐和痛苦也似乎是可以理解的。推开象征世界的大门,马南走出想像的局限,慢慢地接受那个无所不在的他者对自己的重新定义。
为了哀皮,马南接受了邻居温兹罗帕夫人的建议,开始尝试进入拉维罗村的宗教实践和社会生活。他带上哀皮去揽活时与村里人闲聊,去礼拜堂听牧师布道,带她去石屋边的草地玩耍,努力回答她无数好奇的问题。这时候,在他人的眼中,他是一个需要帮助的、毫无养育孩子经验的父亲,一个遭窃的可怜人、一个技术很好的织工。这是在镜像之中马南再次获得的“自我”形象。同时,对宗教的再次拥抱和对拉维罗村社会生活的参与,象征着马南将自己放进了象征之网中,接受盘踞在象征之网中心的那个无所不在的他者的统治、审查和设定。“对拉康来说,无意识就是他者的话语,而他者不是别的就是语言,就是一整套给定的约定俗成的规则。”[8]作为“我”的马南和作为“他”的他人之间必须要引入这样一个“他者”,经由“语言”,“我”与“他”之间才有了对话的可能,才能建立起信任或认可的关系。“主体与他人建立的信任或认可的关系,并不是一种自我和他人之间想像的所谓相互认可或承认的关系,而是基于共同第三者他者的‘间接’认可或承认关系。”[6]107所以,在哀皮到来之前,织虫一样生活的马南和村民之间除了在镜中瞥见彼此的影像外,并无任何对话的可能,因而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充满了隔阂、怀有敌意并陷入了僵局的。但是当双方都进入以语言为代表的他者世界时,他者就起到了作为斡旋者的作用,他们之间紧张关系的化解就成为了可能。马南承认他者存在,他者才有可能承认马南为一个主体和他作为主体的价值。只有马南和村民都承认这样一个共同的他者,这个他者才能承认他们作为主体的存在,他们才能在他者编织的网络中,用彼此理解的语言对话,进而发展出相互信任的关系。
马南和哀皮之间发展出深厚的父女之爱。由于对养女的爱,马南才将自己从织虫无知无觉的冬眠状态中唤醒,开始接受那个代表着语言和社会法则的大他者加在自己身上的所有规则和约束,并积极建构自己作为象征世界的“主体”。尽管这个“主体”在拉康的眼中实质上还是个苍白的空无,是在受到他者暴力侵凌的情况下建立的,但是,离开了这个大他者,主体只能是一个自说自话的空无,行走在癫狂的边缘。敞开怀抱,拥抱大他者对自己的定义和约束,从某种意义上说,主体重获了相当的主动性,通过和环境、和他者的持续交往和应答而实现自我。但是这样的我又不是任何“他者”的复制品,因为每一种爱的独一无二,“我”因而也是独特的。如果没有爱,主体难以形成自己“属人的、具有个性特征的人格基型”。爱,在这里为主体打开了一道救赎之门,向冰冷的象征世界里射入一束温暖的光。
[1]张一兵.不可能的存在之真[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219.
[2]乔治·哀利奥特.织工马南传[M].梁实秋,译.台北:大地出版社,1993.
[3]张一兵.拉康:从主体际到大写的他者[J].江苏社会科学,2004(3):1-2.
[4]严泽胜.穿越我思的幻象[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
[5]汪震.实在界、想像界和象征界[J].广西大学学报,2009(6):80-83.
[6]黄作.不思之说——拉康主体理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7]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M].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27.
[8]马元龙.语言、言语与能指:从索绪尔到拉康[J].北方论丛,2005(6):48-51.
——拉康对《孟子》的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