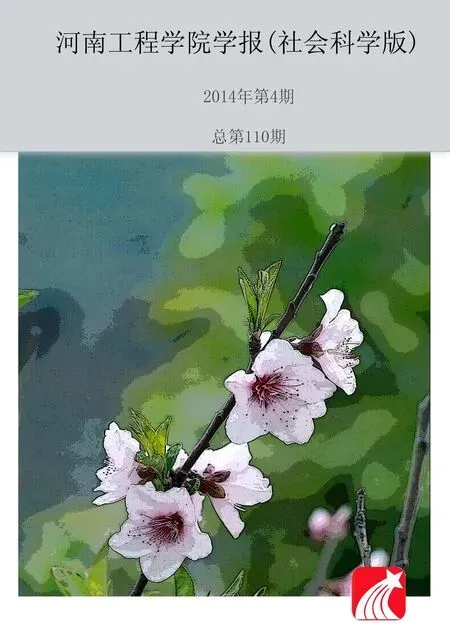杂文的幽默文辞
刘福智
(商丘学院 文学院,河南 商丘 476000)
食品要讲究“味”,文章也要讲究“味”。唐代司空图把“辨味”作为品诗的第一要务。因此,诗之优劣的判定,只需简单地品一下有无“诗味”以及诗味的浓与淡,有诗味而且诗味浓的就是好诗。
杂文之优劣,则在于“杂文味”。“杂文味”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幽默感。在各种文体中使用幽默最多的应是杂文。从某一角度来说,杂文就是一种幽默文辞。
杂文本是一种社会论文,其论题往往是严肃的、庄重的;杂文又是一种语言艺术,其笔法往往是调侃的、诙谐的。杂文家将庄重和诙谐结合起来,造就一种庄重中见诙谐的艺术风格。
当然,并不能为了幽默而幽默。善于运用幽默的杂文家,往往是在让人发笑之后,立刻收敛笑容,进行渗入骨髓的反省,领悟那嘲笑的对象所隐藏的本质。作者似乎不动声色,纵意而谈,而笔锋所及,却显示出深刻的社会意义。幽默往往是从平凡中揭示非凡,从荒诞中揭示理智,从可笑的表层揭示可恶的内核。幽默不是肤浅的玩笑,而是一种深刻的智慧。
齐鲁杂文《说“老公”》有如下一段文字:
人们似乎展开竞赛,看看谁能在粗俗方面拔得头筹,使人想入非非,就会财源滚滚。于是,《水浒传》就被改名为《三个女人和一百零五个男人的故事》或《孙二娘和她的一百多个男友》,《红楼梦》被改头换面为《女儿国的秘密》,《西厢记》则成了《少女失身之后》,就连马恩列斯的著作竟也成为《世界上最有魅力的四个男人》。这里的所谓“魅力”,不知是否包括“性感”?因为当今一提起男人是否中用,首要的因素不是他的精神气质和性格涵养,也不是他的白色收入和灰色收入,而是他的性感如何。可见,当今不少女人所追求的,并不是什么精神享受和物质享受,而是其他享受。这可否称之为社会的进步呢?弃庄重于不顾,追粗俗而成俗,这显然是当今社会语言令人瞩目的变化。[1]
这段文字谈到某些名著的书名被人从“性”和“性感”出发改得不伦不类,的确可笑。而此文的思想主题正是在于从可笑的表层揭示可悲的内核。其可悲之处就在于“当今社会语言令人瞩目的变化”——弃庄重于不顾,追粗俗而成俗。
幽默是有生命力的,它甚至能超越蔑视。因此,有人说,棍棒或许能扑灭豪笑,但镣铐永远锁不住幽默。[1]地动说的创始人被绑在火刑柱上并不屈服,他幽默地说:“地球仍在转哪!”[2]宗教裁判所可以烤杀他的性命,却无法烤杀他的这份幽默。在这种场合中,幽默成了嘲讽的武器。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拥有幽默。别林斯基说:庸人们“一般地还不会笑,更不懂得‘喜剧性’是什么”[1]。中国人固然不能算是庸人,但是相对来说,也不是善于笑着生活的民族。相对于西方民族来说,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往往显得严肃有余而轻松不足,正经有余而幽默不足。这不是我们的缺失,而是我们的不幸。因为我们有数千年的贫困和数千年封建伦理观的重压,有“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思想禁锢,那么,幽默便无所附丽。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尤其是汉族,处于中外反动势力的重重压迫之下,一部分人在重压下挣扎,一部分人在重压下反抗,那么,中国文艺的主旋律自然表现为呻吟、呐喊与战斗。从总体上来说,同西方文艺相比,也就缺少幽默的情趣。
有人认为,中国人也有所谓传统的幽默,不过那是一种畸形的幽默,是一种插科打诨,是一种庸人俗士之间的“互相奚落和讨便宜的戏谑”[2]。例如,北方人乐于戏称自己的友人为“孩儿他舅”,就是一种讨便宜的戏谑,意为自己占有了对方的姐妹。列宁说:“幽默是一种优美健康的品质。”[2]没有这种品质,也就不是幽默,也就沦为市井街巷里的油腔滑调和学生宿舍里的低级趣味了。正如笑话会毁于说笑者先发的笑声之中,幽默也会毁于油腔滑调和低级趣味之中。幽默一旦与低俗相勾结,就会沦于油滑,甚至使人肉麻,就会失去幽默本身。用油滑、肉麻和低级趣味来装点自己的作品和谈话,必然是败胃的,必然同油滑、肉麻、低级趣味同归于尽。
西方有所谓“黑色幽默”,中国人,甚至高等学府里的中国人,却有着“桃色幽默”,即有关男女之间婚外情的内容,还有“黄色幽默”,即有关色情和性的内容。且看齐鲁杂文《幽默的色彩》中的两段文字:
中国有所谓“桃色幽默”,它大多闪现于“桃色新闻”之中。以往的中国人还不大开化,只要一对非婚关系的男女未能保持令人认可的交情而有所“不轨”,比如同处一室未能正襟危坐,同行一途未能规步矩行,同谈一事未能字正腔圆,而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亲近,那么,往往会爆出“桃色新闻”。那新闻的编纂者似乎握有此事的“专利”并深知其价值,于是逢人便讲,广为推销,讲着讲着,便不免“幽它一默”。听者们被那“桃色幽默”的柔媚色彩所吸引,不禁大悦,于是哄然一笑。这种幽默和笑声,使人总感到不是滋味。
中国又有所谓“黄色幽默”,其色彩更为靓丽。不幸的是,自从美国出了一本名为YELLOW CHILDREN的杂志,历来被中国人视为“帝王之色”的黄色,就成了“色情”和“性”的代名词。以往的中国人还不大开化,一谈起“性”,便想方设法以图正襟危坐、规步矩行、字正腔圆……而今天勇敢的中国人,一谈其“性”,便不免眉飞色舞、得意忘形、唾液四溅,谈着谈着,便不免“幽它一默”,但那幽默便不免泛出黄色。那种谈论和引发的哄然一笑,听起来不免使人感到肉麻。[1]
作者齐鲁归结的所谓“桃色幽默”和“黄色幽默”因为不具备“优美健康的品质”,所以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幽默。着意炮制这种所谓幽默去取悦于读者的,往往失之于油滑和肉麻。鲁迅无心做什么幽默大师,他却是一个地道的幽默大师。他以机智、鲜活的幽默灌溉了他的杂文,给人以种种艺术享受。鲁迅非常赞赏“外国的平易地讲述学术文艺的书,往往夹杂些闲话和笑谈,使文章增加活力,读者感到格外的兴趣,不易于疲倦”[2]。其实,杂文也应是一种使思想趋向形象化和幽默化的艺术。
而不同的幽默确实有不同的特色。下面拟从四个方面探讨杂文的幽默文辞。
一、端庄
所谓端庄,就意味着端正、庄重,就意味着健康、高尚。端庄的幽默,就不是油腔滑调和低级趣味,就不是“桃色幽默”和“黄色幽默”。端庄的幽默应表现为一种端庄的美感。
杂文家的幽默文辞,也许借助于反语,却不失其正;也许借助于夸张,却不失其真;也许借助于含蓄,却不失其锐。鲁迅往往操纵灵活自如的“曲笔”来论事说理,他的许多妙语就妙在反中悟正,假中见真,曲中显直,甚至无中生有。
杂文作者流火有《“雪隐”与文明》一文,认为厕所的面貌往往标志着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其中一段如下:
其实,中国古代本来也很重视厕所的。庄子是春秋时期道家的代表人物,有人问他“道”之所在,庄子答曰“无所不在”,转而强调“道在屎溺”。他认为,身处不洁之地能够领悟生活哲理。当今的中国人不得已进入那不洁之地,又巴不得火速逃离,因为其不洁的程度难以使人在其间从容领悟什么哲理。我们似乎没有继承庄子在这方面的思想,不再重视环境对精神的影响。于是,即便都市新建的楼群,也会有人依墙搭起厨屋柴棚,让滚滚的炊烟弥漫那狭窄的空间;也会有人就地垒起鸡舍狗窝,让鸡犬之声与电子音乐交鸣齐奏;也会有人扯起麻绳铁丝,让婴儿的尿布如同万国旗迎风招展。[1]
这段文字最后3个以“也会有人”领起的排比句就颇为幽默。作者以散文的笔调描绘都市新建的楼群脏乱差的情况,表现庄子之后的中国人“不再重视环境对精神的影响”,这种描绘给人以幽默感,这种幽默是一种端庄的幽默。
鲁迅《而已集·小杂感》有如下的文字:
要上战场,莫如做军医;要革命,莫如走后方;要杀人,莫如做刽子手。既英雄,又稳当。[2]
这段文字是在传授世故和圆滑吗?不。作者是以幽默的文辞嘲笑世故,讥讽圆滑,在入世未深的青年人面前戳穿并展示某些虚伪而丑陋的灵魂,使人们知耻而退。这也显示了端庄的幽默。
二、苦涩
杂文家揭露黑暗,抨击罪恶,也往往采取幽默的笔触。这种幽默,使人在笑意方生之时就感到一种辛酸和苦涩。
鲁迅的幽默是深刻的。他善于透过皮面的笑容窥见内心的阴云,透过现时的辉煌发现历史的荒冢。他以其幽默的文字所诱发的笑,有时是苦味的,甚至是含泪的。他的《华盖集·牺牲谟》一文,是以对话体描写一个贪婪的暴发户劝说一个赤贫者把仅有的一条破裤子送给自己收作女仆的灾民的女儿。其中一段写道:
“你还能走几步罢?不能?这可叫人有点为难了,——那么,你该还能爬?好极了!那么,你就爬过去。你趁你还能爬的时候赶紧爬去,万不要‘功亏一篑’。但你须要用趾尖爬,膝踝不要太用力;裤子擦着沙石,就要更破烂,不但可怜的灾民的女儿受不着实惠,并且连你的精神都白扔了。先行脱下了也不妥当,一则太不雅观,二则恐怕巡警要干涉,还是穿着爬的好。我的朋友,我们不是外人,肯给你上当的吗?舍间离这里也并不远,你向东,转北,向南,看路北有两株大槐树的红漆门就是。你一爬到,就脱下来,对号房说:这是老爷叫我送来的,交给太太收下。你一见号房,应该赶快说,否则也许将你当作一个讨饭的,会打你。唉唉,近来讨饭的太多了,他们不去做工,不去读书,单知道要饭。所以我的号房就借痛打这方法,给他们一个教训,使他们知道做乞丐是要给人痛打的,还不如去做工和读书好……”[2]
《牺牲谟》一文的构思很奇特,全由一个人的讲话构成,另一个人的对话则略而不述。没有任何人物和场景的描写,也没有任何议论和感慨穿插其间,但是,一个骗人的富人和一个受骗的牺牲者的形象却跃然纸上,入木三分地揭露了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的贪婪性及其手法的残酷性。然而,这样苦涩、悲凉的主题却是以幽默、风趣的语言来表达的。如果说这其中有笑意,那是让人忍泪吞声的苦笑;如果说这其中有趣味,那是令人不寒而栗、哀伤悲凉的苦趣。
鲁迅《且介亭杂文·隐士》有如下一段:
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有了“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的幸福的,倘不然,朝砍柴,昼耕田,晚浇菜,夜织履,又哪有吸烟品茗,吟诗作文的闲暇?陶渊明先生是我们中国赫赫有名的大隐,一名“田园诗人”,自然,他并不办期刊,也赶不上吃“庚款”,然而他有奴子,汉晋时候的奴子,是不但侍候主人,并且给主人种地,营商的,正是生财器具。所以虽是渊明先生,也还略略有些生财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没有酒喝,而且没有饭吃,早已在东篱旁饿死了。[2]
此段文字也颇幽默。作家的意思如下:首先,隐士是一个闲人,否则如农夫一般一天忙到晚,他哪有工夫去“隐”;其次,隐士是一个富人,起码“略略有些生财之道”,就像渊明先生那样,否则,就会“在东篱旁饿死”,也就不会有“悠然见南山”了。
有关陶渊明,鲁迅在《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中也有一段幽默的文字: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渊明的好句,但我在上海学起来可就难了。没有南山,我们还可以改作‘悠然见洋房’或‘悠然见烟囱’的,然而,要租一所有点竹篱,可以种菊的房子,租钱就每月总得一百两,水电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两。单是这两项,就是一百十四两……[2]
这段文字,其实是一种“戏言”,谈到现今要学陶渊明有多难,还正儿八经地算了一笔账,所表现的也是一种苦涩的幽默。
再读鲁迅《而已集·小杂感》中的一段文字:
革命,不革命,反革命。
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2]
这段绕口令似的文字极为幽默,它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革命和反革命两大阵营的残酷斗争以及被卷入其中的中间派的惶惶不可终日。它表现了当时人们动辄得咎的心理状态,也是一种苦涩的幽默。
失去了幽默,杂文恐怕就会失去“杂文味儿”。如果说到“味儿”,可作这样的比喻:散文是果糖,少年嗜其甜腻;杂文是花茶,成人爱其苦香。杂文之苦,往往来自于香。幽默之引人入胜,就在于其“香”,这种香,是带有苦味的香,也就是苦涩的幽默。
三、辛辣
幽默和讽刺不同。讽刺本属于动词,其意为:以比喻、夸张等手法批评、揭露不良的或愚蠢的言行。而幽默本属于形容词,其意为:有趣、可笑而意味深长的。讽刺带有辛辣、犀利的特点,而幽默则蕴含平和、深沉的韵味。不过,讽刺和幽默有时也是难以区分的,讽刺往往包含着幽默的意味,幽默有时闪现着讽刺的锋芒。因此,幽默而散发着辛辣意味也属于常态。
请读鲁夫杂文《美丑倒挂》其中两段:
报刊谈论最多的大概是“脑体倒挂”,这是一种对于正常的社会分配形式的颠倒。其实,还有种种波及很广、影响更大的“倒挂”,举其要者,就有母子倒挂、主仆倒挂、公私倒挂、买卖倒挂……
俗话说,小公鸡儿,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其实,时下许多“小公鸡儿”在娶妻生子之后,不但忘不了娘,而且充分发挥老娘的主观能动性,使其兼任保育员、炊事员、采购员和勤务员,那儿子却俨然一副小爹甚至小祖宗的模样,这不是“母子倒挂”吗?[1]
所谓“倒挂”,是指某些社会现象原本很正常而变得不正常的状况。所谓“母子倒挂”,就是对正常母子关系的颠倒。这段幽默的文字是对当前家庭中母亲终日劳碌、儿子养尊处优这一社会现象的嘲弄。从一句俗话谈起,说到儿子让母亲包揽各种杂务,讲到“那儿子却俨然一副小爹甚至小祖宗的模样”,实在尖刻辛辣!
鲁迅《华盖集·这个与那个》一文中有一段文字:
记得有一部讲笑话的书,名目忘记了,也许是《笑林广记》罢,说,当一个知县的寿辰,因为他是子年生,属鼠的,属员们便集资铸了一个金老鼠去作贺礼。知县收受之后,另寻了机会对大众说道:明年又恰巧是贱内的整寿;她比我小一岁,是属牛的。其实,如果大家先不送金老鼠,他决不敢想金牛。一松开手,可就难以收拾了,无论金牛无力致送,即便送了,怕他的姨太太也会属象……[2]
这段文字意在讽刺收受寿辰贺礼的知县的贪婪和得寸进尺。尤其是“其实”一语之后的那几句发挥,令人称奇。得了金老鼠想金牛,这是知县能想到的,而“姨太太也会属象”,知县却未必想到,不过,只要有贪欲,什么奇思妙想都会有的,因此,作家接着说:“象不在十二生肖之内,似乎不近情理罢,但这是我替他设想的法子罢了,知县当然有我们所莫测高深的妙法在。”贱内“属牛”,姨太太“属象”,实在是辛辣的幽默。
鲁迅在《而已集·小杂感》中有这样两段文章:
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
中国人的想象唯在这一层面能够如此跃进。[2]
这两段文字所显示的也是极端化的幽默。作家所表现的其实是“性禁锢”造就的“性幻想”。两千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处于“男女授受不亲”的思想禁锢之中,因此,人们总是“谈裸色变”。每个人从小就被反复灌输这种观念:裸体就是风骚淫荡,就是奇耻大辱,就是伤风败俗。对于半裸,人们也会深恶痛绝,对于全裸,简直认为罪大恶极,所以“一丝不挂”往往惊天动地。其实,禁之愈久则会思之愈切,两千多年的性禁锢,则造就了丰富发达的性幻想,造就了鲁迅在文中所谈的6个“立刻”。作家并不批判封建伦理观念造就的“性禁锢”,转而以幽默的文辞描述那种畸形的“性幻想”,其实是选择了另一角度进行批判,也带有辛辣的意味。
四、轻松
幽默也可以以轻松的形式出现。鲁迅对嘲讽的对象,大多是用“嬉笑”的方式代替“怒骂”,用“轻描淡写”代替“剑拔弩张”。即便是满腔的憎恶和愤怒,也用喜剧式的智慧掩护起来。鲁迅生活在一个黑暗而愚昧的时代。他每每以如椽的巨笔无情地扫荡丑陋与腐恶,这时就表现为“匕首与投枪”,但有时却调动喜剧因素,展示各种社会病态,轻松活泼,别有风趣。其《热风·随想录三十五》谈论“国粹”问题,有如下两段:
什么叫“国粹”?照字面来看,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换一句话,便是特别的东西。但特别未必定是好,何以应该保存?
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2]
幽默有时是要特意制造的。鲁迅在这两段文字中就两次有意地制造了幽默。首先,他把“国粹”解释为“特别的东西”,接着说某人脸上的瘤、额上的疮也很“特别”,于是,“可以算他的‘粹’”。其次,采用“析词法”制造幽默。所谓析词法,就是把本来不能拆开使用的多音节词语故意拆开使用,以获得幽默的效果。这里,将“国粹”一词有意拆开,而只用其中的“粹”,有所谓“他的‘粹’”。这两处幽默都有轻松活泼的特点。
鲁迅的幽默文辞,诙谐里迸射着思想火花,含蓄中闪耀着感情色彩。作家这种“谈笑斗敌顽”的策略,使得“杂文味儿”显得异常浓郁。即使在怒火中烧的情况下,鲁迅有时也不怒骂,而在论敌的要害处顺手一击,极有分寸,恰到好处。他曾对许广平谈及为文之道:“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2]即便杂文,也应写出诗一般的美来。
杂文作者齐郎有《从铁门到警铃》一文,谈到社会治安恶化,都市住户安装防盗门和警铃的问题。作者写道:
森严的铁门加上灵敏的警铃或许能使盗贼望而却步,可同时也把邻居拒之门外。偶尔想串个门儿,一看到主人如此复杂完备的防卫措施,雅兴便失去大半。而主人开门之前,先是通过问话判定来者,继而通过“猫眼”验明正身,最后才打开一道道保险,启动一道道门,这更使客人于心不忍。万一触响警铃,即可惊动四邻,顿然窘相百出。[1]
社会治安恶化本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作者却写得轻松活泼,风趣横生。尤其是“透过‘猫眼’验明正身”一句颇为幽默。所谓“验明正身”,本指处决死刑犯之前验明、确定该罪犯的身份,在这里却用作确定来访的邻居,不禁令人哑然失笑。
五、结语
杂文的幽默可以是端庄的,杂文家在采用幽默的时候并不失去人格;可以是苦涩的,使人们面对惨淡的人生而感到无奈;可以是辛辣的,能使嘲笑对象狼狈不堪,无地自容;又可以是轻松的,能使杂文在谈笑之间升华出一种“诗美”。学习鲁迅,也包括学习他的幽默艺术。鲁迅不屑于插科打诨和油嘴滑舌式的所谓幽默,却开创了一种崭新的幽默文风。鲁迅所开创的中国新式幽默,既可傲视于古代东方朔式的滑稽,又可自豪于西方那种玩世不恭的所谓黑色幽默。早已站起来而正在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在幽默方面也正在越来越富有。幽默已经成为中国人重要的精神素质。
幽默是言谈和文章的佐料,是生活和交际中的润滑剂。幽默能使我们的言谈和文章更有美感,使我们的生活和交际更有情趣。幽默帮助我们趋向道德,领悟真理。恩格斯认为,幽默是具有智慧、教养和道德上优越性的表现。[1]
我们需要幽默参与我们的生活,进入我们的文章,使自己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有修养的人。
[1]刘福智.中国的泼皮士[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2]鲁迅.鲁迅杂文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