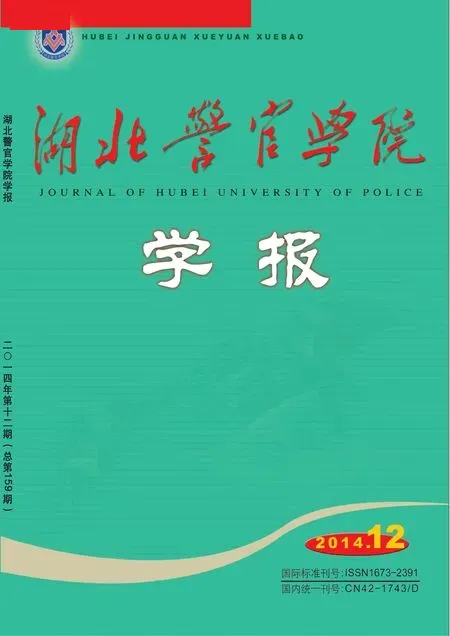当事人和解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梁紫玉
(武汉大学,湖北武汉430070)
当事人和解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梁紫玉
(武汉大学,湖北武汉430070)
2012年新刑诉法规定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和解制度是一种新型的利益争端解决方式,通过自愿平等协商的方式解决纠纷,标志着刑罚权由国家独占向非国家化的过渡,使传统刑事司法模式下被害人与加害人紧张的敌对状态得到缓解,有利于纠纷的彻底解决以及社会关系的恢复。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对公诉案件和解的适用范围、程序和方式、和解协议的效力等问题做出了规定,但很多具体制度和细节还有待完善。对当事人和解制度的概念、适用范围、程序启动、法律效力以及检察机关在当事人和解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探讨。
当事人和解制度;概念;适用范围;启动程序;法律效力
一、当事人和解的概念如何理解
关于当事人和解的概念,新刑诉法表述的是“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教学上或者实践中约定俗成的称谓是“刑事和解”。“刑事和解”是由西方victim-of-fender-reconciliation(简称VOR)翻译而来。VOR更确切的翻译应该是“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是指在犯罪后,经由调停人,使加害人和被害人直接相谈、协商,解决纠纷冲突。其目的在于恢复加害人和被害人的和睦关系,并使罪犯改过自新,复归社会。[1]翻译为“刑事和解”并不准确。
除了翻译的问题,西方的“刑事和解”与我国的“当事人和解”有诸多不同之处,不可混为一谈。西方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是恢复正义理论、平衡理论以及叙说理论。恢复正义理论强调犯罪是对政府规范的违反,同时更强调犯罪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伤害和被伤害的关系,其首要特征是强调犯罪不仅是对法律的违反、对政府权威的侵犯,更是对被害人、社会甚至犯罪人自己的伤害,把加害人和被害人看作首要当事人。[2]我国并没有恢复正义理论、平衡理论以及叙说理论。关于犯罪的本质,我国采取的是法益侵害说,认为犯罪是对法益的侵害,主要考虑的是犯罪对国家利益的影响。虽然和解制度比传统刑法更注重被害人的利益,但并没有把被害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考虑。因此,西方的和解制度与我国目前刑法理论有诸多不相融合的地方。我国适用和解制度,需要与我国刑法理论、刑事诉讼理论相契合,在我国刑法理论和刑事法律尚未发生根本变革的情况下,暂时不宜采用西方“刑事和解”的概念和理论。
另外,加害人与被害人能够达成和解的部分只能是刑事附带民事部分,因此,和解主要围绕经济赔偿的问题展开,是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讨价还价”的过程,司法机关则在其中充当调解人的角色,对双方进行说服劝导,缩小当事人关于赔偿金额的分歧。因此“刑事”和解,本身也存在歧义。实践中,也容易使公众产生和解就是“花钱买刑”的不良印象。
笔者认为,概念必须以最简洁的语言反映事物最本质的特征。因此,本文拟采用“公诉案件中当事人和解制度”这一称谓,简称“当事人和解”。所谓当事人和解,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方式得到被害人的谅解,被害人要求或者同意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从宽处理而达成的协议。其模式是受害人和加害人直接交谈、共同协商达成经济赔偿和解协议后,司法机关根据具体情况作出有利于加害人刑事责任处置的诉讼活动,它包括经济赔偿和解和刑事责任处置两个程序。[3]
二、当事人和解的适用范围如何界定
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了当事人和解制度的适用范围:下列公诉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一)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二)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不适用本章规定的程序。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规则》)第五百一十条第二款进行了补充:上述公诉案件应当同时符合下列条件:(一)犯罪嫌疑人真诚悔罪,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二)被害人明确表示对犯罪嫌疑人予以谅解;(三)双方当事人自愿和解,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四)属于侵害特定被害人的故意犯罪或者有直接被害人的过失犯罪;(五)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我国和解制度只适用于轻微刑事案件和过失犯罪,两者分别以故意伤害案和交通肇事案为主要代表。
(一)如何理解“三年以下”
法律规定的“三年有期徒刑”是指法定刑还是宣告刑?实践中存在不同的理解。笔者认为应理解为宣告刑。法定刑是立法机关在制定刑法的时候确定的,宣告刑是人民法院在处理具体案件的时候确定的,是法官依据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在法定刑的基础之上,对犯罪分子宣告的应该执行的刑罚。因此,将这里的三年有期徒刑理解为宣告刑,更符合个案的具体情况,更能体现适用和解程序案件的“轻微性”。
(二)是否适用于“重罪”
我国目前还没有“重罪”的概念,一般认为,可能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独立使用附加刑的是轻罪,此外为重罪。陈瑞华教授指出:对于那些可能对被告人适用死刑的最严重的犯罪案件,被害方与被告方达成和解协议,并且明确表示不要求适用死刑,法院审查后确定被害方的请求是真实自愿的,也可以此为根据仔细考虑是否适用死刑。陈光中教授指出:死刑案件适用刑事和解(当事人和解——笔者注,下同)将有望成为我国对死刑进行司法控制的一个新的着力点,死刑案件适用刑事和解不仅贯彻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落实了少用、慎用死刑的方针,并且使得被害方与加害方的利益得到了更好的平衡,实现了个案的平和裁决,不仅促进社会和谐还能够维护司法的权威性。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了和解制度的适用范围,“重罪”和解没有被立法采纳。笔者认为,扩大和解范围,“重罪”和解是世界潮流,随着我国社会的进步和法制的完善,“重罪”适用和解是必然趋势。
(三)适用和解程序是否以加害人的行为构成犯罪为前提
根据法律规定,适用当事人和解要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但没有规定是否要求加害人的行为构成了犯罪。有学者认为“案件性质难以界定的案件和存疑的刑事案件同样可以实行刑事和解”。[4]但是,“刑事和解并非是辩诉交易,并非是建立在减轻控方被诉风险基础上的妥协,和解必须是在犯罪人真诚悔罪的前提下进行,如果犯罪人认罪了,但案件事实还未查清,或者是有待查清,那么我们对于这种认罪的自愿性就会打上问号。同时,在没有查清是非的情况下达成的和解也会容易造成反复,留下隐患”。[5]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当事人和解应以加害人行为构成犯罪为前提。
三、当事人和解程序如何启动
目前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对和解程序的启动做出具体规定。和解程序的启动,首先要确定启动权的归属问题,即启动的主体;其次,和解程序启动后的具体操作方式是怎样的。当事人和解制度必须对这两个问题进行细致的设计。
(一)启动的主体
根据我国实践中的做法,笔者把程序的启动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依职权启动(亦称积极的启动),另一种是依申请的启动(亦称消极的启动)。
依职权启动模式,即办案人员认为一个案件可以适用和解程序,先填写启动和解程序审批表,经主管部门负责人审核批准后,向当事人送达适用和解程序的通知书,在当事人同意和解后确定和解的时间、地点、和解内容、参加人员等。
在依申请启动模式中,司法机关对于符合适用和解程序案件的当事人,不主动提出和解的建议,而是告知其有和解的权利。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后,向司法机关递交《当事人和解申请书》,经司法机关审查并确认其效力。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依职权模式还是依申请模式,都必须遵循自愿的原则,征得双方当事人的同意。如果一方当事人不同意和解,就不能启动和解程序。
(二)和解程序的具体操作
关于和解程序的具体操作,实践中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形:
第一,由办案人员作为调停人来主持和解,对双方当事人进行劝说教育,促成当事人和解协议的达成。这种做法的优点有二:一是办案人员熟悉案情,能够较快地介入和解,提高效率;二是办案人员代表国家公权力,更具有公信力,当事人更容易信服。这样做的隐患在于,办案人员本来是代表国家行使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在和解程序中却执行起调解的职能,这是否是一种权力的异化。另外,实践中还存在办案时间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时间到和解程序中,工作量增大,压力不降反升的情况。如何理顺司法机关的诉讼职能和和解程序中的调解工作,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第二,双方当事人自行达成和解,然后经司法机关确认。双方当事人事先已经自行达成了和解协议,提交给司法机关,司法机关对和解协议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审查合格后予以确认,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从宽处理的决定。这种做法的优点是充分体现了和解的自愿性,处理起来快速简洁,更节约司法资源。其隐患在于,当事人不精通法律,可能存在诸多漏洞,同时缺乏国家专门机关的监督。
第三,由调解委员会主持和解,在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后,调解委员会将和解协议书副本等有关资料移送司法机关,司法机关对和解协议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审查合格后予以确认,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从宽处理的决定。这种模式既避免了第一种做法由办案人员主持和解时职能方面的困惑,也避免了第二种做法当事人自行和解而不受法律监督的情形,还能充分发挥调解委员会的社会功能,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第三种做法在实践中得到广泛的运用,将来应成为我国当事人和解制度的主要模式。
四、当事人和解的法律效力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九条的规定,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
当事人达成和解的法律效果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过,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并获得宽缓的处罚。然而,我们面临的实际情况比理论要复杂得多。比如,和解协议还没有达成或者还没有经过司法机关的审查确认,被害人就接受了赔偿,并从此消失,杳无音讯。此时和解协议的效力如何,能否推断被害人默认了和解,能否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宽处罚。再比如,和解协议生效后,当事人一方反悔,不积极履行或者不接受履行;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确实真诚悔过了,也获得了被害人的谅解,但由于经济状况不好,暂时无力履行经济赔偿,能否确认和解协议的效力,能否在履行之前就对其作出从宽处理的决定,作出之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又反悔怎么办,等等。现实是复杂的,这些问题都有可能存在,而法律却没有明文规定。
解决这些问题,应该从完善法律制度入手,进行细致无漏洞的程序设计,从而减少甚至杜绝上述情况的发生。对于一件适用和解程序的公诉案件,首先,由于和解的自愿性、契约性,必须保证双方当事人都要参与其中,缺少任何一方都不行。如果被害人接受赔偿后消失,则不能认定和解协议的达成,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适用和解程序而作出宽缓的处罚决定,但是可以考虑适用刑法情节方面的规定来酌情处罚。其次,通常情况下,和解程序的进展顺序是,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并经司法机关审查确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被害人进行了赔偿—司法机关作出从宽处理的决定。所以,从宽处罚要在积极赔偿之后进行。为了解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但暂时无力赔偿的问题,可以引进取保候审中的保证人制度,规定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这样可以促进案件的尽快审结,也更人性化,不仅充分照顾了当事人的意愿,也有利于保障协议的履行。
五、检察机关在当事人和解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
新《刑事诉讼法》、《解释》以及《规则》规定了检察机关有审查和解自愿性、合法性,以及主持制定和解协议的职责,但对检察机关能否主动主持当事人进行调解以促成和解,法律尚未作出规定。
根据《关于湖北省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办理当事人和解刑事案件情况的调研报告》[6],一些检察机关办案人员对检察机关在当事人和解案件中的地位存在两种认识上的误区和偏差。一种是过于积极主动地介入当事人和解。少数地区检调对接机制还不顺畅,有的当事人和解案件在办理过程中很少依托人民调解组织进行调解,检察机关直接主持并全程参与双方当事人进行和解的过程,使得当事人和解的任务集中到了检察机关。一种是受到传统刑事司法理念的制约,认为对犯罪嫌疑人的追诉只能由国家进行,不允许和解,害怕和解会损害检察机关的权威。具体表现为对一些危害不大、情节轻微的案件根本不告知和解权利或是消极对待和解,无论是否符合相对不起诉条件,都统统先起诉到法院以规避风险。不愿启动和解程序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当事人和解往往要经过告知、调解、签署协议、履行协议,以及结案、审批、检委会讨论、宣布等环节,而且一旦调解不成,案件还要重新回到起诉环节。这样拉长了办案周期,花费的精力更多,基层院“案多人少”的问题更突出,“吃力不讨好”。
关于检察官能否主持当事人和解这一问题,理论界存在不同的意见。有些学者认为,检察官应当主持和解,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大都希望由办案机关主持和解。也有学者指出,检察机关不具有调解的职权,主持调解违背其职权。
目前实践中主张检察机关来主持刑事和解的比较多。“第一,检察官的职能不单单是在于对刑事被告人的追诉,并且也在于国家权力的双重控制;作为法律的守护人,检察官既要使被告人免于法官之臆断,也要保护其免于警察之随意。换言之,检察官自创设以来,自始具有处于警察、法官两重国家权力的中介性质。第二,在大陆法系传统上,检察官具有客观公正义务和诉讼关照义务,需要对社会利益进行衡量与裁量。检察官不是,也不应该是片面追求打击犯罪的追诉狂,而是依法言法,客观公正的守护人,有利不利一律注意。第三,我国宪法明确赋予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能。”[7]因此,由检察机关来主持当事人和解无论是从法律地位还是社会公众的接受度来讲,都是比较合适的。当然,这一问题还有待法律作出明确的规定。
六、结语:我国当事人和解制度的未来走向
和解制度在国外的发展趋势是适用案件范围的扩张和适用阶段的扩大,有些国家在司法实践中突破了轻罪的范围,将和解制度运用于严重犯罪之中。例如在美国,除了众多突破了轻罪案件的刑事和解计划外,在美国的死刑案件中还出现了“基于辩护的被害人接触”计划,辩方派出专门的被害人联系人与被害人家人接触,了解他们的想法和要求,并积极促成被害人家人与被告人会面,协助双方达成和解。[8]
我国当事人和解制度才刚刚起步,其适用严格限制在法定范围之内,并且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随着和解理论的深入和实践的发展变化,我国的当事人和解制度也必然由不完善走向完善,由不成熟走向成熟。可以预见的是,我国当事人和解的发展趋势必然会顺应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放宽和解适用案件的范围以及诉讼阶段,以更好地发挥当事人和解制度的优点,最终实现社会的稳定和谐。
[1]刘凌梅.西方国家刑事和解理论与实践评价[J].现代法学,2001 (1).
[2]Gehm,John R:Victim-Offender Mediation Program:An Exploration of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s,Western Criminology Review 1(1998).
[3]陈卫东.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336.
[4]刘守芬,李瑞生.刑事和解机制构建根据简论[J].人民检察,2006 (14).
[5]武艳,张清.我国刑事和解制度论略[J].湖北社会科学,2012(12): 155.
[6]程华荣,刘克强,杨思哲.关于湖北省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办理当事人和解刑事案件情况的调研报告[J].检察发展研究报告,2012 (3).
[7]郭云衷.刑事和解现状调查[A].恢复性司法理论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2007:81-83.
[8]Kristen F.Grunewald and Priya Nath,“Defense-Based Victim Outreach:Restorative Justice in Captial Cases”,Washington& Lee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Captial Defense Journal,Spring, 2003.
D915.3
A
1673―2391(2014)12―0124―04
2014-07-29责任编校:陶范
——以“被告人会见权”为切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