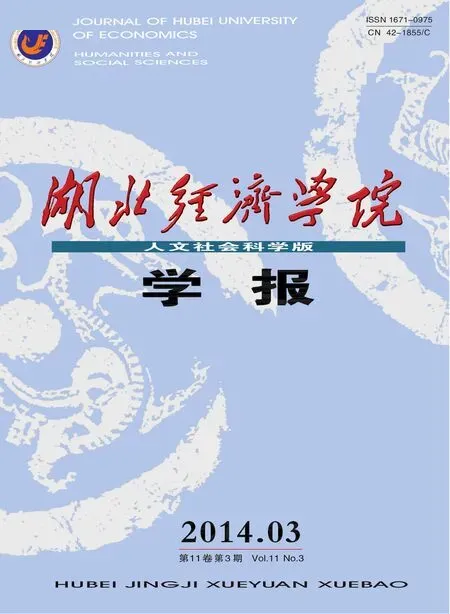魔鬼与孩童:论《铁皮鼓》中奥斯卡的伦理身份
阳亚蕾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430079)
长篇小说《铁皮鼓》(《Die Blechtrommel》)是君特·威廉·格拉斯的代表作,于199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自1990年《铁皮鼓》中译本首次出版以来,关于《铁皮鼓》的国内研究现状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研究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用叙事学的相关理论分析、对小说中荒诞这一艺术手法的研究、人物形象的研究、意象和象征的研究。国外的研究起步于《铁皮鼓》写作出版后两三年,明显早于国内,研究主要集中于历史背景,探讨文本中的主题、人物、象征等。伦理问题是《铁皮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然而国内外的研究现状都缺乏从这一角度进行探索,因此,本文选取伦理这一角度,首先探讨奥斯卡成长的伦理环境,探究其成长过程中挥之不去的伦理困惑,其次重点探讨其几次重要的伦理选择,最后探究奥斯卡关于伦理身份探寻的过程,以期对奥斯卡这一形象做出多角度全方位的解读。
一、伦理困惑:生父之谜
奥斯卡的母亲阿格内斯在同阿尔弗雷德·马策拉特成婚之前即同表兄扬·布朗斯基有着亲密而暧昧的关系,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她临死之前。在同马策拉特结婚之后,扬依旧肆无忌惮地出入阿格内斯和马策拉特的房子,以外人难以察觉的方式同阿格内斯调情,然而年幼的奥斯卡却将母亲和表舅的这一系列通奸行为都看在眼里,对到底谁是自己的生父惶惑不已。他在刚出生时便感受到人世昏暗,想要回到娘胎中去,可是无奈脐带已经被剪短,他再也回不去了。在连自己的生父都不能确定,以及察觉到成人世界的丑陋之后,奥斯卡决定永不长大,既然不可能再回到娘胎中去,那他便选择了用天真孩童的外形隐藏自己,有意同成人的世界保持距离。这种对于生父的困惑成为了日后他“杀害”扬和马策拉特死因的导火索。
奥斯卡在两个父亲间摇摆不定,在他长到一定年纪,他又让这种“生父之谜”在自己身上重演。母亲阿格内斯被罪恶压得喘不过去来,选择了自杀,母亲死后,一个叫做玛丽亚的姑娘来到马策拉特的店里帮忙,此时的奥斯卡已经成长为一个年近十六岁的有着懵懂性欲的少年。他将玛丽亚视为自己的初恋,可是十七对的玛丽亚却只是把他当做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经常帮他洗澡换衣。在汽水粉的引诱下,奥斯卡让玛丽亚怀上了自己的孩子,可是此后不久,马策拉特也将玛丽亚占有了,他娶了玛丽亚,使她成为了奥斯卡的继母。随后玛丽亚诞下一名叫库尔特的男孩,库尔特名义上是奥斯卡同父异母的弟弟,事实上是他的儿子。随着伦理身份的转变,奥斯卡同玛丽亚成为夫妻的愿望成了奢望,在这种绝望情绪的牵引下,他开始了自己前往前线的表演生活。然而让儿子库尔特成为同他一样的鼓手的愿望驱使着他在儿子三岁生日的前一天赶回来送他一面铁皮鼓,他甚至像用办法让库尔特像他一样永远保持在三岁时的身高,永不长大。“必须在击鼓的父亲身边摆上一个击鼓的儿子,必须有两个矮小的鼓手由下而上地观察大人们的所作所为。”(《铁皮鼓》,337页)正是由于幼年时对于自身伦理身份的困惑,才使得他生出强烈的占有欲,他要让自己的父亲身份得到最明晰的确立。
二、伦理选择:“懵懂”与蓄意
对于伦理身份的困惑使得奥斯卡在生死临头的关键时刻做出了惊人之举,两位父亲都直接或间接地葬送在他手里。一九三九年德国入侵波兰,但泽纳粹党徒围攻波兰邮局,身为波兰人的扬同其他人一起死守邮局,同纳粹党展开了殊死搏斗,奥斯卡在扬身边亲历了这场战斗,甚至在扬的战友死时为了安慰他,轻声地叫了他一声爸爸,这让扬一度情绪崩溃,而这父子相认的一幕就发生在民兵闯进邮局前不久。在民兵闯进邮局后,“奥斯卡想起自己是个侏儒,想起三岁孩子对任何事情都无需负责。”(同上,231页)他来到民兵面前寻求保护,让他们以为这个无辜的三岁孩子是被拖进邮局当防弹的盾牌的,“怕自己是扬的亲戚而受到牵连。”(同上,234页)
在生和死之间,求生的意识使他做出了“杀父”的选择,扬死后他本可以写出一份证明扬不想守卫邮局的证词来替他开脱罪行,可是奥斯卡并没有这样做,虽然他被一种罪恶感折磨得不得安宁,还因此发高烧、神经发炎,住进了医院。奥斯卡并不是一个毫无感情的冷血的恶魔,然而为何他在死亡临头前选择了同自己的生父彻底撇清关系?这是因为他长期处于对自己身世的困惑中,他对死亡的感知远比“父亲”这个伦理身份背后的意味要深刻得多,“儿子”这个确切的伦理身份才确认不久,尽管扬的确是他的生父,但是为了求生,他还是选择了同生父决裂。然而他隐隐觉察到自己行为犯了某种伦理禁忌,这使得他陷入深深的罪恶感之中,身心都受到了极大的煎熬。
如果说“出卖”扬一半出于懵懂无知,那么陷害马策拉特实际上一种蓄意的谋杀行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俄国人攻入但泽,手持纳粹党徽章的马策拉特在俄军搜查时惊慌失措地想要将徽章藏起来,奥斯卡从库尔特手中抢到了徽章。孩子的外形使俄国兵对他放松了警惕,甚至将他抱在怀中逗乐,本来马策拉特可以趁此机会逃过一劫,可是奥斯卡却将徽章重又递给了马策拉特,拿到徽章的马策拉特想将徽章咽下毁尸灭迹,却没想到被它卡住,这明显的举动引起了俄国兵的注意,他们开枪将马策拉特扫射而死。
奥斯卡的行为是蓄意的,读者可以从他在马策拉特坟前的心灵独白获知党徽的别针是他故意打开的,他将这块会刺人、会卡住的党徽故意交给马策拉特,目的就是要置他于死地。由于扬的“生父”地位在奥斯卡心中确立,马策拉特死后,他痛失的只是是他再也品尝不到出自马策拉特的美味食物而已。由于没有违反伦理禁忌所带来的本能的恐惧,对于马策拉特的死,奥斯卡并没有表现出半点罪恶和伤心。“玛丽亚的事我决不原谅他。”(同上,393页)奥斯卡是如此真挚地爱着玛丽亚,然而马策拉特却从他手里夺走了他,此外,他蓄意谋害马策拉特的最重要原因是,他希望对于库尔特而言自己 “父亲”这一伦理身份得到唯一的确立,因为“奥斯卡厌恶父亲们这个词儿。”(同上,392页)
三、伦理复苏:缺失身份的找寻
在奥斯卡身上,理性意志和非理性意志呈现出不断搏斗的过程,在对伦理身份的困惑之下,他的一系列行径都骇人听闻,在这一阶段,他人性中的非理性意志并不受理性意志的控制。在摔下地窖楼梯,让自己永不长个儿后,他虽然在外人看来变成了一个痴呆儿,不会说话,可是他却获得了“唱碎”玻璃的特异功能。他唱碎诊所里的玻璃器皿里的标本,让诊所一片狼藉。他唱碎教室里的玻璃,唱碎老师的眼镜,让课堂陷入一片混乱当中。他故意趁着夜色的掩护,将商店的玻璃橱窗唱碎,引诱路人偷窃,故意激发路人人性中的恶。青少年时期的奥斯卡在诱骗玛丽亚怀孕之后,玛丽亚却要嫁个马策拉特,这让奥斯卡心生怨恨,他不愿意“父亲”这一伦理身份被马策拉特夺取,因而他宁愿采取极端的做法——让玛丽亚流产,让这个孩子不可能降生到人世,既然他成不了父亲,那么马策拉特也休想成为他的儿子的父亲。他故意用鼓棒撬道梯子,让在梯子上装饰店铺的玛丽亚摔了下来,可是玛丽亚只是扭伤了脚,并没有流掉孩子。在伦理身份得不到确立的情况下,他选择了离家出走,随贝布拉的戏剧团一起到前线演出。
从戏剧团回来后,奥斯卡成了一个破坏组织的领袖,在被警察拘捕后,他又“扮演起被半成年人诱拐的、咧嘴冷笑的三岁孩子的角色,毫不抗拒地接受了庇护。”最终无罪释放。在他孩童外形的掩护下,奥斯卡人性中的兽性因子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然而他又赖于孩童的外形,每次都能够从罪责中逃离出来。本来他可以一直这样下去,然而马策拉特的死却让他对自己的伦理身份又开始认真思考。在很久以前,他就确定扬是自己的生父,如今马策拉特死了,无人可以再在现实中同他争夺库尔特的“生父”这一伦理身份,无人可以再用父亲的身份压制自己。奥斯卡在马策拉特坟前反复思考的“我该不该”的问题,事实上指的就是该不该一步步夺回自己的伦理身份的问题,他的答案是肯定的,而要在已经比自己高的库尔特面前树立起父亲的威严,他必须让自己长高,于是他让库尔特乱扔的小石子击中自己,又开始长个。在同玛丽亚和库尔特一起搬到她姐姐那,开始黑市生意后,长高但变形了的奥斯卡多次想要在库尔特面前树立起自己的权威。当他询问库尔特的火石来源却没有得到答复后,他总是固执地追问,因为在他看来,“我身为父亲,有权知道我儿子的来源。”(同上,420页)由于需要靠玛丽亚和库尔特养活,没有劳动能力,他在家中备受他俩的轻视,库尔特总是故意不理睬他,丝毫不把这个父亲放在眼里。
为了确立自己的父亲地位,他拿出了当年扬从橱窗里偷来的送给阿格内斯的红宝石项链,在黑市上兑换为一个真皮的公事包和十五条美军香烟,还去干在墓碑上刻字的活,承担起了养家的重任。眼看着里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近,他壮着胆子向玛丽亚求婚,却遭到了拒绝。由于币值改革,他丢了刻碑的工作,转而开始靠当裸体模特养活玛丽亚和库尔特,然而玛丽亚却因为他的工作用“脏猪”、“堕落的家伙”等不堪入耳的字眼咒骂他,并说出了永远不想再见到他的话,这促使奥斯卡搬出同玛丽亚同住的房子,开始了独自一人的生活。
在试图建立起自己的“父亲”身份的过程中,奥斯卡的理性意志制约着非理性意志,他既没有再唱碎玻璃,也没有再干出什么邪恶的事情,然而即便这样,一切也只是徒劳。在一座名叫洋葱地窖的酒吧里,奥斯卡放声大哭,他想到了妈妈、扬、阿格内斯以及玛丽亚还有小库尔特,出生时的那种厌世情绪又从他心底蔓延出来。
奥斯卡的一生都是围绕着伦理身份这个关键词中展开的,孩童时期,他为谁是他生父这个问题困惑不已。青少年时期,他为同马策拉特争夺谁是库尔特“生父”这一伦理身份做出了骇人听闻的举动。壮年时,他为了在库尔特面前确立自己的父亲身份,毅然从封闭的世界里走出来,不再利用孩童的外表同成人的世界保持距离,而是毅然担负起了养家的重任,然而最终一切只是徒劳。奥斯卡并不是一个披着孩童外衣的恶魔,他反复提到自己只想在外祖母的裙子下安静地过完一生,他打从娘胎其便意识到世界的丑恶,有意同这个世界保持距离,然而身份问题却迫使他一步步从自我封闭的世界里走出来,他也想做出改变,可是世界最终还是让他失望了。奥斯卡的一生给我们这样的启示:伦理身份是个人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词,只有明晰了自己的身份,才能在恰当的时刻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伦理的人。
[1]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J].外国文学研究,2012,(2).
[2] 聂珍钊.“伦理禁忌与俄狄浦斯的悲剧”[J].学习与探索,2006,(5).
[3]格拉斯.铁皮鼓[M].胡其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4]陈文育.“论《铁皮鼓》中的畸形侏儒形象”[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