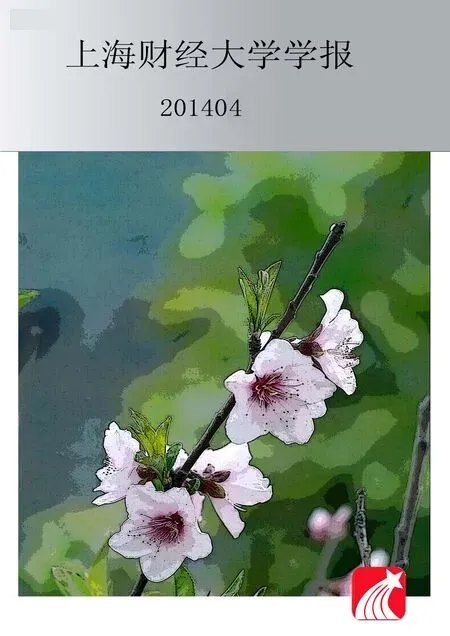破解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的困局
——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的视角
吕 江
(山西大学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山西 太原 030006)
对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的研究,是近年来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均进行了相应的智识阐释。有的是从历史的维度,对气候变化谈判历程进行史实性分析。*高小升:《国际政治多极格局下的气候谈判——以德班平台启动以来国际气候谈判的进展与走向为例》,载《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4期,第52-60页。有的则是从政治视角对气候变化谈判中的新情况、新变化给予新的理论解读。*参见于宏源:《试析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格局的新变化》,载《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6期,第9-14页。而更多的讨论则集中体现在对气候变化谈判中不同国家立场的剖析上。*参见冯存万:《法国气候外交政策与实践评析》,载《国际论坛》2014年第2期,第57-62页。刘大炜、许珩:《日本气候变化政策的过程论分析》,载《日本研究》2013年第4期,第1-8页。谢来辉:《气候怀疑论、民主与美国气候政策的阻滞》,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6期,第132-140页。康晓:《国际气候秩序建构与中国的气候外交》,载《国际论坛》2013年第5期,第31-36页。无疑,这些理论研究加深和丰富了当前对气候变化谈判问题的认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的实践并非如人们所愿,一个致力于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制度安排,迄今为止始终无法有效构建起来。对此,我们认为,缺乏有效的制度创新乃是其难以构建的症结所在,而制度创新无疑又端赖于理论上的升华。因此,只有加强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与理论前沿的关联性研究,才有助于破解这一气候困局。
近年来,在契约经济学中,美国经济学家哈特等人提出了契约之不完备性及其产权治理模式的不完全契约理论,极大地丰富了契约理论的当代研究。毫无疑问,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与契约理论具有某种相当紧密的关联性。特别是当前的不完全契约理论亦表明,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本身就是一个不完全契约的缔结过程,其谈判旨趣就在于制定一份全球碳排放的产权治理模式。而这一过程中,不完全契约理论提出的套牢问题以及对剩余控制权的言说,都无疑与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的实践呈现出相当程度的吻合。为此,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不完全契约理论,纳入对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理论的解读中,势必带来一种更为有力的理论指导。而在此基础上,中国可考虑在未来的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中,首先,应加强对气候变化谈判程序性事项的控制,逐步提高自身谈判的议价能力;其次,应在碳排放产权安排的谈判中尽可能地凸显中国立场,为碳减排提供适宜的中国绩效;再次,应将未来的制度安排放在新能源及其技术研发上,达到有效规避气候变化的套牢问题;最后,旨在构建起一种“碳纠缠”的模式,以期实现对气候变化剩余权的制度控制。
一、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进程亟待理论创新
毋庸讳言,当前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已进入一个关键时期。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第十九次会议(2013年11月华沙会议)的决议,加强行动德班平台特设工作组(Ad Hoc Working Group on the Durban Platform for Enhanced Action, ADP,以下简称德班平台)将从2014年第一次会议开始,进一步细化谈判草案的要素。而更值得关注的是,德班平台在其2014年的工作报告中就已明确指出,其2014年的工作目标将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第二十次会议(2014年12月利马会议)上出台2015年协议的谈判文本草案。无疑,这将意味着规定全球2020年后温室气体减排的“2015年协议”的谈判,将从各国立场汇集和材料的准备阶段进入案文谈判的实质阶段。
毫无疑问,自2009年联合国重启气候变化谈判以来,全球气候格局已发生深刻变化。一方面,后京都温室气体减排(2013年-2020年)的制度安排并不顺利。首当其冲的是作为既是排放大国又是发达国家的美国,并未被纳入强制减排行列中;而更有甚者,规定强制减排的《京都议定书》也出现了裂痕,首先是加拿大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之后日本、俄罗斯和新西兰都明确拒绝参加《京都议定书》第二期的减排承诺。[注]裴广江、苑基荣:《德班气候大会艰难通过决议》,载《人民日报》2011年12月12日第3版。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内部也出现不同的气候声音,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以中国、印度、巴西、南非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发展迅猛,温室气体排放逐年扩大,国际社会尤其是那些受气候变暖影响较大的小岛屿国家,要求发展中排放大国进行强制减排的呼声也愈演愈烈。[注]Jon Barnett & John Campbell, Climate Change and Small Island States, London: earthscan, 2010, p. 16, pp. 95-96.
当然,尽管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进程受到上述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制订一份全球性温室气体减排的初衷并未由此减弱。这是因为,首先,作为气候变化领域的积极倡导者,欧盟意欲强化其领导核心的立场始终未动摇。特别是在目前谈判进展不顺利之际,它不惜采取单边主义的举措,迫使其他国家回到谈判桌前。[注]Lavanya Rajamani,“EU Climate Change Unilateralism”,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 23, No. 2, pp. 469-494.其次,对于气候变化谈判的消极者美国而言,由于国内页岩气革命的成功,其温室气体排放大为减少,未来重新回归并领导国际气候舞台的政治欲望也在不断增强。最后,就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谋求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间合作,以及通过机制安排,实现国内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亦变得越来越紧迫。因此,制订一份具有全球性质的气候变化协议仍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主流观点。
然而,未来的气候变化协议充满诸多变数,且仅就中国而言,尤为担心的是,它是否会对中国经济发展形成新的桎梏。这表现在:第一,中国的经济转型仍需要一定的排放空间。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消除贫困和改善民生仍是当前中国的主要任务,特别是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较快的经济增长,势必使温室气体排放呈上升趋势。因此,不合理的减排安排会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第二,能源结构调整需要一个稳妥的过渡期。尽管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3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趋势》的报告,截至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国,仅2012年的投资就增长了22%;[注]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Global Trends in Renewable Energy Investment 2013, Frankfurt: UNEP Collaborating Centre, 2013, p. 11.但不容忽视的是,中国的自然禀赋是以煤为主,这决定了能源结构由“高碳”向“低碳”的调整,将是一个依次渐进的过程。然而,2015年协议一旦将中国纳入不合理的强制减排中,不仅会影响能源结构调整的顺利完成,而且更会危及中国的国家能源安全。第三,也是最为关键的是,2015年协议对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的制定将产生直接影响。不言而喻,2015年是中国“十二五”规划的最后一年,同时又是“十三五”(2016年-2020年)的规划年。鉴于2015年协议和“十三五”规划都是在2015年年底出台,因此二者之间难以协调。倘若前者对于减排目标的规定高于后者,为履行条约义务,中国将不得不在“十三五”期间作出重大调整,从而对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潜在影响。
因此,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的“2015年协议”犹如一柄双刃剑,它在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同时,也加深了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因此,加强对“2015年协议”文本草案的研究,尽可能规避因制度设计不合理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无疑将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当今,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学术研究已远远超出自然科学范畴,政治、经济、社会等学科均已涉猎于此。就经济学而言,早在2006年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师、英国经济学家斯特恩就曾发表《气候变化的经济学:斯特恩报告》一文,运用经济学分析气候变暖所带来的危害。[注]Nicholas Ster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98,No.2,2008, pp.1-37.然而,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将气候变化谈判作为一次缔约来认识,无论是在经济学界还是其他领域都鲜有著述。因此,将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前沿成果不完全契约理论运用于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中,不仅能认识到气候变化谈判的实质问题,而且也能为中国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的决策带来新的理论和制度思考,从而有力地维护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利益。
二、不完全契约理论对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的诠释
所谓不完全契约理论(incomplete contracting theory),是指基于缔约双方难以完全预见履约期内所发生的重要事件,且当重要事件发生争议时,第三方亦无法强制执行的事实,而进行的理论分析和治理机制的设计。因其主要理论贡献来自于美国经济学家哈特(Oliver Hart)与另外两位学者格罗斯曼(Sanford Grossman)、莫尔(John Moore)分别合作完成的两篇经济学论文,对此学界又将其称为格罗斯曼—哈特—莫尔模型或GHM模型。
对于这种“无法预见并难以强制执行的事实”,格罗斯曼和哈特在其文章中阐述到,由于生产配置对于“世界的状态”的依赖关系在事前是难以预测并描述清楚的,且某些事前投资可能因为它们过于复杂以至于难以描述,或是因为它们所代表的一方的努力决策(对于第三方,譬如法院)是无法证实的,从而难以写入合同中。[注]Sanford J. Grossman & Oliver D. Hart,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Ownership: A Theory of Vertical and Lateral Integration”,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4, No. 4, 1986, p. 698.同样,在另一篇文章中哈特和莫尔也认为,对于缔约者而言,缔结一份包含每一个不可预测事件的当前和未来可能行动的长期合同,其成本将是高昂的。因此作为结果,书面合同往往是不完全的。[注]Oliver Hart & John Moore,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Nature of the Firm”,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 98, No. 6, 1990, p. 1122.
正是基于以上事实,哈特等将不完全契约与产权理论联系起来,提出相应的治理机制。他们认为,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必然产生特定权利和剩余权利,前者是指能在契约中明确规定的权利,而后者则是指那种事前不能明确界定的权力。[注]Oliver Hart, “Incomplete Contracts and the Theory of the Firm”,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 Organization, Vol. 4, No. 1, 1988, pp. 121-125.当存在交易成本或不对称信息而有碍于事后重新谈判时,掌握剩余控制权就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将影响到事后剩余的规模和分配。[注]Oliver Hart & John Moore, “Incomplete Contracts and Renegotiation”,Econometrica, Vol. 56, No. 4, 1988, pp. 755-785.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而言,剩余控制权就是所有权,只有将其交给契约中不可或缺的行为人才是最有效率的。[注]参见[美]哈特著:《企业、合同与财务结构》,费方域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4-68页。Oliver Hart & John Moore, “Incomplete Contracts and Ownership: Some New Though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7, No. 2, 2007, pp. 182-186.
那么,如何看待契约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联呢?换言之,为何契约对人类社会如此之重要呢?美国契约法专家麦克尼尔不无感慨地指出,这是因为“现代技术世界是一个典型的以契约为基础的世界……权力和行使权利则司空见惯,契约不仅远未死亡,而且已经横扫世界——正如悲观主义者可能说的那样——像瘟疫一样”。[注][美]麦克尼尔著:《新社会契约论》,雷喜宁、潘勤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5页。毫无疑问,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也概莫能外。契约,特别是不完全契约的诸多特性都凸显在这一谈判过程中。这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看出:
(一)气候变化谈判是一个不完全契约的缔结过程
从不完全契约理论来看,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的本质就是一个不完全契约的缔结过程。这表现在,一方面,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是一个缔结长期契约的过程。这一缔结长期契约过程最早可以追溯到199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45/212号决议。根据该决议,联合国成立了气候变化公约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具体负责《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谈判和制订工作。[注]Bert Bolin,A History of the Science and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68-69.尽管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正式通过,但这并不意味着气候变化谈判的结束;相反,前者却以缔约方会议这种框架形式将气候变化谈判制度化了。无疑,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2007年的《巴厘路线图》、2009年的《哥本哈根协议》,一直到今天的德班平台,都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缔约方会议推动下达成的议定成果。因此可以说,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是一个长期契约的缔结过程,而不是某种可一次完成缔约意向的个别契约。
另一方面,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存在着可观察但不可证实的执行问题。不完全契约理论曾给出了可观察但不可证实的经济例证,亦即,甲企业为一发电厂,乙企业为发电厂附近的煤矿。双方签订长期的供销合同。如果甲对燃煤锅炉进行改造,可以燃烧较低质量的煤炭,从而降低了煤矿企业的成本,也可提高自己的总利润。但这种前期投资就是可观察但不可证实的,尽管锅炉改造降低了乙的成本,使乙受益,但第三方无法证实甲的锅炉改造是专门为乙所做的。如“使用经济学术语表达就是,因为世态、质量和行为(对合约当事人而言)是可观察的,但是(对于外部人而言)是不可证实的,所以出现了不完全性”。[注][美]奥立弗·哈特、本特·霍姆斯特龙:《合约理论》,罗仲伟译,载[美]奥立弗·哈特等:《现代合约理论》,易宪容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4-65页。
不言而喻,国际法很大程度上凸显了这种不完全契约理论中的“可观察但不可证实的执行问题”。正如制度经济学家埃格特森所言,“由于缺乏有效的世界政府,国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与无国家社会的产权制度相类似,因为这两种情况下都没有作为最终权力来源的第三方强制合约的执行”。[注][冰岛]思拉恩·埃格特森:《经济行为与制度》,吴经邦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73页。无疑,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的议定结果也必将带着国际法上的这种烙印。[注]吕江:《〈哥本哈根协议〉:软法在国际气候制度中的作用》,载《西部法学评论》2010年第4期,第109-115页。
(二)气候变化谈判是一种对碳排放产权的不完全契约安排
碳排放权,乃是在全球气候变化制度安排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一种产权制度。该制度认为,地球上的大气容量存在一定限制,当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超出这一限制时,将破坏地球的大气平衡。由此碳排放的有限空间就具有了一种产权属性,从而能在国家或个人之间进行产权分配和交易,以达到保持地球大气平衡的旨趣。无疑,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正是旨在制订一份能在各国之间进行全球碳排放分配和交易的产权安排。
对于产权而言,在一定意义上,它也是不完全契约理论的核心基础。这正如不完全契约理论GHM模型的创立者哈特所言,“为什么实物或非人力资产的产权是重要的呢?回答是,在合同不完全时,所有权是权力的来源。……既然合同不可能对每一种情况下资产使用的所有方面都作出规定,那么谁有权利来决定合同未提及的用法呢?按照产权观点,有关资产的所有者拥有这种权利。”[注][美]哈特:《企业、合同与财务结构》,费方域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5页。可见,契约的不完全性决定了产权对于所有者的意义。而且也正是建立在这种产权观的基础上,不完全契约理论才相应地提出了自己独特的企业理论和一体化理论。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大气显然是一种公共产品。它对所有人开放,而且不可避免地出现“搭便车”问题,对此,英国经济学家斯特恩不无感慨地指出,“温室气体排放的外部性造就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市场失灵”。[注]Nicholas Ster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8, No. 2, 2008, p. 1.毋庸讳言,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正是意欲通过制订一份碳排放的国际产权安排,来纠正这一失灵问题。然而,从不完全契约理论的视角看,这种碳排放权的产权安排却存在着巨大的困难性。其原因是,尽管碳排放权的分配和交易安排在整个气候变化谈判中将居于核心地位,但是由于气候变化协议具有的不完全性,比如在碳排放权的准入问题以及适用范围的规定不同,就可能对缔约方产生不同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碳排放权不同于一般产权,它具有较强的动态性,这与产权的稳定性存在一定的冲突。[注]Holly Doremus, “Climate Change and the Evolution of Property Rights”,UC Irvine Law Review, Vol. 1, 2011, pp. 1091-1123.因此,作为一种对碳排放产权的不完全契约安排,如何实现二者的动态平衡,实属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不得不面临的重大问题和挑战。
(三)气候变化谈判凸显不完全契约的“套牢”问题
“套牢”问题(hold up)是不完全契约理论中的一个基础问题。它又被称为“敲竹杠”,是指缔约一方为了履行合同,进行了关系专用性投资,当再谈判的时候,投资一方会面临被对方“敲竹杠”的风险,即这种专用性投资产生的剩余利益会不可避免地被对方分享。
就气候变化谈判而言,不完全契约的“套牢”问题可以在欧盟的排放交易机制上发现。欧盟排放交易机制(European Union Emission Trading Scheme, EU ETS),是欧盟实施的一种总量控制与交易的减排规则体系。[注]J. Robinson, J. Barton, C. Dodwell, M. Heydon & L. Milton,Climate Change Law: Emission Trading in the EU and the UK, London: Cameron May, 2007, pp. 51-70.2003年欧盟通过《欧盟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指令》正式创建这一机制。然而,从欧盟排放交易机制的运行情况看,试运行阶段由于排放配额过于宽松,几乎所有的企业都达到了排放要求,为了激励更多的减排,在正式运行阶段开始后,欧盟对排放交易机制意欲进行一些改革,主要是引进拍卖方式。但是,尽管如此,自2013年第三阶段开始,由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排放交易机制的运行并不理想,其完善与修改甚至存废都成为当前欧盟排放交易机制的尴尬窘境。[注]Dirk Bohler, “The EU Emission Trading Scheme-Fixing A Broken Promise”,Environmental Law Review, Vol. 15, No. 2, 2013, pp. 95-103.
毋庸置疑,从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套牢”角度可较好地解读当前欧盟排放交易机制的处境。首先,欧盟排放交易机制是世界上较早从事温室气体减排的灵活机制,也是全球最大的区域性排放交易机制。通过建立这一机制,一方面,可以凸显欧盟在气候变化领域中的政治话语权;另一方面,又可为欧盟企业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积累经验,为未来参与全球减排创造比较优势。其次,尽管利用排放交易机制,欧盟可提高其未来的经济竞争力,但气候变化谈判的不完全性却使欧盟陷入“套牢”的境地。这是因为,倘若未来的气候变化协议不安排或拟订新的减排灵活机制,那么欧盟企业在前期的投入就会变成“沉没资本”。这正如经济学家埃格特森所指出的,“当一家企业或一个国家早已按他们的标准进行了投资,那么向国际标准的转变往往成本极高,只有自己的标准被其他国家采用的一方例外”。[注][冰岛]思拉恩·埃格特森:《经济行为与制度》,吴经邦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74页。最后,如上文所言,欧盟的排放交易机制运行并不理想,但为了解除“套牢”,前者则只能不遗余力地向国际社会推销其减排机制,甚至不惜采取单边主义的方式。
(四)气候变化谈判的实质乃是对剩余权力的控制
在契约与权力的关系方面,哈特等人指出,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对剩余权力的掌控就具有决定性意义,亦即“一项资产的所有者一旦拥有对于该资产的剩余控制权,就可以按任何不与先前合同、惯例或法律相违背的方式决定资产所有用法的权力”。[注][美]哈特:《企业、合同与财务结构》,费方域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5页。
当然,在不完全契约理论的早期文献中,哈特等人将剩余控制权仅仅局限在对所有权或物质产权方面的控制。然而,随着不完全契约理论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剩余控制权的范围远远超出产权范畴,如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拉詹和津加莱斯就认为,关键资源的控制是权力的源泉,关键资源或是机器、或是思想,抑或是人力,对这些资源的准入能提供比所有权更有效的激励。因此,准入权就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注]Raghuram G. Rajan & Luigi Zingales, “Power in a Theory of the Firm”,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3, No. 2, 1998, pp. 387-432.
毋庸置疑,从不完全契约理论的角度看,气候变化谈判就是对剩余控制权的一个争夺过程。这种争夺可以体现在对作为产权的碳排放权上的争夺,亦可体现在对气候变化准入权,亦即对气候变化信息、资金、技术等领域的争夺。而争夺的形式则表现在对未来气候变化协议的制度安排上。
从目前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的进程看,欧盟占据着一定的争夺优势。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欧盟在气候变化的观念领域居于主导地位。[注]Rudiger K. W. Wurzel & James Connelly, “Introduction: European Union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Politics”, in Rudige K. W. Wurzel & James Connelly ed.,The European Union as A Leader in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p. 3-20.二是欧盟在碳减排方面已取得一些实质性的成果。这不仅体现在欧盟整体温室气体排放的下降,而且体现在其排放交易机制的区域制度安排上。未来,尽管美国以及“基础四国”或都可能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对欧盟的这种领导权形成挑战,但从不完全契约理论看,为了解决因排放交易机制所形成的“套牢”问题,欧盟只有扩大其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剩余控制权,才能有更多的选择余地。
三、不完全契约理论视角下气候变化谈判的中国应对
如上所述,既然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是一个不完全契约缔结的过程,那么中国应采取何种谈判策略,或者说应在未来协议中构建一种什么样的规则才更符合中国的气候核心利益呢?毫无疑问,不完全契约理论在治理机制方面提供了一些有所裨益的参考。因此根据前者,我们可将气候变化协议分为事前和事后两个方面来采取不同的策略,其中,事前多采用结构治理的模式,而事后则多采取实效原则。具体制度安排可从以下四个方面思考:
(一)加强对气候变化协议中程序性事项的设计:协商一致或特定多数
毋庸讳言,“权力在契约中受到一种既规定其设置又规定其限制的规范的约束”。[注][美]麦克尼尔:《新社会契约论》,雷喜宁、潘勤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1页。在这一方面,程序性事项往往展现了契约对权力限制的这种本性。对此,不完全契约理论认为,由于契约本身存在不完全性,当出现新的状态时,缔约各方就有可能对原有契约进行重新修订或再谈判,而剩余控制权的配置将决定再谈判时缔约方的议价能力。[注]Oliver Hart & John Moore, “Incomplete Contracts and Renegotiation”,Econometrica,Vol. 56,No.4,1988,pp.755-785.无疑,契约当中的程序性安排亦是剩余控制权当中重要的一环,它对剩余控制权的配置起到制约的效果,同时也能为再谈判的启动提供合适的依据。
就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而言,截至目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的《议事规则》始终未能确定下来。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7条第2(k)项的规定,缔约方会议必须“以协商一致方式议定并通过缔约方会议和任何附属机构的议事规则和财务规则”。然而,自1992年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开始涉及制订这一规则起,到目前每次缔约方会议都首先要讨论该问题,但均未能以协商一致通过《议事规则》。[注]吕江:《〈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制度及其影响》,载王继军:《三晋法学》(第6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313-326页。究其原因,主要是在《议事规则》第42条表决程序上存在分歧较大,即关于缔约方会议的实质性事项应采取何种特定多数通过方式。毋庸讳言,缔约方会议的表决程序关系到气候变化谈判议定结果的控制权配置。换言之,任何缔约方只要掌控表决程序,就能实现对议定结果的干预。
当然,从缔约方会议的实践看,尽管存在《议事规则》的争议,但并没有影响相关协议的出台。这可能存在两方面原因:其一,虽然气候变化谈判较为激烈,但大国之间的气候合作始终没有破裂,因此,一定意义上协商一致的表决方式起到其应有的作用。其二,自1997年《京都议定书》以来,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没有再出台具有“硬法”性质的议定书,而不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软法”形式的协议则易于被通过。
然而,自2011年德班气候变化谈判时起,俄罗斯以及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墨西哥分别提出两个修正提案,特别是后者直接针对《议事规则》。虽然截至目前,这两个提案都处于非正式磋商之下,但这并不代表中国在未来气候变化谈判中,可忽视这种程度性事项的安排,相反,更应重视利用程序性规则,以期规避对中方不利的制度安排。这是因为当前全球气候变化的政治形势更加复杂,气候变化协议不同走向的可能性亦在增强。在实质性内容无法完全预判的前提下,加强程序性规则的掌控具有更大的现实意义。为此,中方应继续积极支持协商一致的表决方式,但不排除考虑特定多数通过表决方式的可能性,前提则是中国在特定多数中应占有重要的表决份额。
(二)对气候变化协议中碳排放权的设计:中国核心利益与实质绩效的挂钩
在气候变化协议中,对碳排放权的分配无疑是协议内容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众所周知,多年以来,碳排放权的分配一直受到西方国家的利益驱动,而这种只反映一方利益的分配机制遭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多次诟病。特别是随着近年来,亚洲在全球经济和能源领域地位的崛起,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发挥亚洲的作用,提出亚洲立场和方案的呼声越来越高涨。[注]Christine Loh, Andrew Stevenson & Simon Tay ed., Climate Change Negotiations: Can Asia Change the Game? Hong Kong: Civic Exchange, 2008, pp. 23-27.
这对于中国而言亦是如此。近年来,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影响力日益凸显。一方面,强劲的经济发展带动中国温室气体排放的扩大。毫无疑问,要限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规模,没有中国的参与是难以想象的。另一方面,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已做出相应的成绩,尤其体现在与气候变化相关联的新能源投资方面。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3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趋势报告》的统计,中国在可再生能源上的投资已连续两年超越美国,稳居全球第一。[注]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Global Trends in Renewable Energy Investment 2013, Frankfurt: UNEP Collaborating Centre, 2013, p. 11.毋庸置疑,从不完全契约理论可以得出,鉴于中国在碳排放产权上具有的重大影响力,而且一定意义上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只有在碳排放产权安排方面充分考虑中国的气候变化立场和核心利益,才能使这种制度安排发挥其真正的实效。
如果气候变化协议中不考虑中国气候变化的立场和核心利益,又会怎样呢?这从哈特和莫尔对不完全契约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他们认为,初始契约为交易关系提供了参照点,一方的事后绩效依赖于其是否获得契约所给予的权利。如果未得到期望结果,那么一方将减损其绩效,而这将给契约带来一个净损失。[注]Oliver Hart & John Moore, “Contract as Reference Point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23, No. 1, 2008, pp. 1-48.基于这种理论分析,可以发现,未来的气候变化协议,如若考虑了中方气候变化的立场和核心利益,那么后者将愿意继续提供一种实质绩效,亦即扩大自己在气候变化上的行动。反之,中方若未能感知从气候变化协议中得到其所期望的结果,那么就会减损其实质绩效,亦即拖延或不作为。更有可能,如中方感知自己的核心利益被协议所侵犯,那么会形成违约激励。这无疑最终将使全球气候变化协议成为一纸空文。
因此,气候变化谈判在碳排放权的制度设计方面,应考虑到中国气候变化的立场和核心利益,对中国的碳排放应采取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强制性的减排只会使问题变得更糟,以致湮灭人类长期致力于气候变化治理的美好愿景。
(三)防止气候变化协议中对中国套牢的制度设计:构建新能源的主导地位
毫无疑问,欧盟在气候变化谈判中的“套牢”问题所引发的教训是深刻的。因此,防止未来气候变化协议对中国的“套牢”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欧盟的“套牢”问题中,我们可以得到三个方面的经验教训:首先,针对气候变化而开展的专用性投资是引起“套牢”的主要原因,但进行这种专用性投资却是未来气候变化协议的必然要求。换言之,只要存在为气候变化而进行制度安排,就必然存在“套牢”问题,这是缔约各国所不能回避的。其次,专用性投资的不足将会成为未来气候变化协议力图规制的主要内容。最后,欧盟被“套牢”的关键是因为它的制度设计是为“气候”而进行的“气候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设计无法最终实现气候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注]吕江:《科学悖论与制度预设:气候变化的立法旨归》,载《江苏大学学报》(社科版)2013年第4期,第7-13页。
对此,我们认为,未来气候变化协议的制度设计不应仅围绕着气候展开,而是应更多地围绕能源展开。如果说不完全契约理论指出了这种“套牢”的必然性,那么历史制度主义则从路径依赖的角度更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按照后者的观点,“套牢”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种路径依赖,而社会制度的变迁是不可能脱离路径依赖的,但路径依赖却有优劣之分。[注][美]B. 盖伊·彼得斯:《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第二版),王向民、段红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9-85页。显然,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在于能源利用,那么以能源发展来解决气候变化的突破口就更具可行性。
此外,对中国而言,以能源发展为方向的气候变化协议的制度设计会有如下裨益:第一,可以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同步协调。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改善民生仍是当前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因此,尽管中国当前不得不面对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带来的诸多压力,但单纯地牺牲经济保护环境的发展模式却不具现实性。当然,这也决不意味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不可协调性。相反,以能源为突破口的治理模式,将不仅有助于中国经济转型,更会带动环境质量的提高。而且,从世界各国环境保护的发展历程看,无一不是走着这样一条道路。[注]吕江:《英国新能源法律与政策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13-221页。第二,有助于解决中国能源安全的现实困境。自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能源安全形势始终处于较为严峻的态势。尽管中国加强了海上和陆路能源通道的建设,但未来中国能源安全的保障力量仍将在于自身能源结构调整的完成。[注]Tatsu Kambara & Christopher Howe,China and the Global Energy Crisi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7, pp. 107-127.因此,以能源合作构建气候变化协议的主体,将有助于获取先进的能源技术和资金,从而促进中国能源结构调整的顺利完成。
(四)加强对气候变化剩余权力的控制:信息的最大化与碳纠缠模式
尽管上面提到的程序性事项、碳排放权以及防止“套牢”的问题,都是从规范的角度对剩余权力加以控制,但是“法律可以说是全部契约关系的内在组成部分,是不可忽视的部分,但法律不是契约的全部”[注][美]麦克尼尔:《新社会契约论》,雷喜宁、潘勤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因此,仅仅依靠事前的安排,依靠规范的保障,仍不能保障对气候变化剩余权力的控制,特别是气候变化制度安排的不完全契约性更决定了这一点。因此,未来在气候变化剩余权力控制方面,中方更应关注以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来发挥影响力的主战场。这是因为:
一方面,存在着不利于中国剩余权力控制的制度空间。从当前来看,已有两个制度领域涉及气候变化的剩余权力控制。一个是联合国安理会。2007年、2011年和2013年,联合国安理会曾三次以不同的主题或形式讨论了气候变化问题。另一个则是欧盟欲将全球航空纳入其排放交易机制之下。尽管二者都遭到了大多数国家的反对,但它们无疑都存在着分散气候变化制度安排的可能性,特别是在欧盟的压力下,2013年国际民航组织更是通过了2016年出台全球航空碳排放协议的决议。
另一方面,存在着针对中国进行碳报复等贸易战的可能性。由于气候变化协议的不完全性,当不能通过其解决因专用性投资形成“套牢”问题时,国家极有可能运用单边行动解决这一问题。[注]Anu Bradford, “The Brussels Effect”,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 107, 2012, pp. 1-67.其中碳关税等贸易报复手段就必然会被大量运用。
为此,中国应采取三种策略:第一,积极参与各种制度中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讨论和研究。这是因为只有获得更多的关于气候变化信息,才能有效防止出现契约理论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才能在气候变化谈判中把握更大的主动权。第二,利用自身影响力,始终将各种制度安排限定在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下的制度安排上,防止出现架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的各种制度预设。毫无疑问,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下,中国已积累了一些谈判经验,并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应对策略和模式。反之,若不以其为主要谈判场所,势必分散中国谈判的议价能力。第三,应紧密加强与各区域、各国展开气候变化相关制度的构建,形成“碳纠缠”模式,以期发挥中国气候变化的影响力。毫无疑问,“碳纠缠”模式,从不完全契约理论的视角看,会形成一种所谓的共同所有形式,从而使得任何一方在采取行动之前,都须谨慎考虑。特别是对于在气候变化谈判上实力较弱的情况下,其可较好地牵制其他缔约方。
四、结 语
契约法专家麦克尼尔曾深刻地指出,“权力和团结属于现代世界的社会问题领域,并且在不确定的将来仍会如此”。[注][美]麦克尼尔:《新社会契约论》,雷喜宁、潘勤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3页。毫无疑问,这句话昭示着,我们在注意对剩余权力控制的同时,亦不应忘记合作的益处,因为后者远比孤立更能使国家受益良多,这显然是不言而喻的。此外,我们也应看到,契约本身只具有“现时性”,而意欲对未来的规范也只能建立在此基础上。因此,旨在通过气候变化协议完全实现对未来一切的掌控,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会使我们迷失对当下现实规范重要性的认识。因此,无论气候变化谈判最终的结果如何,把握住正在进行的气候变化行动和治理才是最为关键和明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