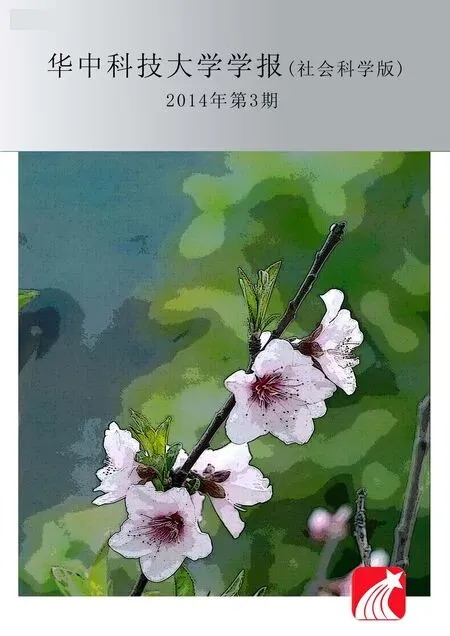善·理性·美德
——霍布斯的伦理思想解读
周湘梅,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28
17世纪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被公认为西方近代政治哲学的奠基者之一。他是第一位对西方传统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做出了全面和深入的思考的哲学家。有学者认为,要把握近代政治哲学思想,必须得从霍布斯这里开始探究。笔者认为要把握霍布斯的伦理思想,须得从善、理性与美德三个概念入手,它们是霍布斯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本文以《论公民》和《利维坦》为文本依据,从伦理学角度对善、理性与美德的概念内涵及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解读,重新审视霍布斯的伦理理论,以期获得对霍布斯伦理思想内在的精神实质更进一步的把握。
一、善
霍布斯曾多次提到自然权利是人有按照正确理性去运用他的自然能力的自由。“这种自由就是用他自己的判断和理性认为最适合的手段去做任何事情的自由。”[1]97何为正确理性?霍布斯在回答这一问题时,引人了善与恶的概念。基于人性论假设,霍布斯分析了善恶概念,并一再强调在一切善中只有自我保存才是最根本的善。那么,为什么自我保存是人类最根本的善?让我们先来看霍布斯是如何定义善的:“任何人的欲望对象就他本人来说,他都称为善,而憎恨或者厌恶的对象则称为恶;轻视的对象则称为无价值和无足轻重。因为善恶等语词的用法从来都是和使用者有关的,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单纯地、绝对地是这样。也不可能从对象本身的本质中得出任何善恶的共同准则。”[1]37霍布斯在这里告诉我们,善恶是由人的主观欲望决定的,没有任何共同的标准。善就是人们所欲望的事物,而恶则是人们所回避的事物。古代哲学家中被霍布斯批评最多的亚里士多德则这样来表述善和恶:因为事物的善,我们欲望并追求;因为事物的恶,我们憎恨并回避。在亚里士多德这里,善恶是事物本身固有的属性。善恶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霍布斯似乎要彻底颠覆这种传统的善恶认识论,使善恶成为主观意愿性的东西。霍布斯的这种善恶观也就难免被人们称为道德相对主义。大卫·高契尔对霍布斯的善恶论主观性特征的评论代表着一般看法,他认为霍布斯“接受一种由个人主观性偏好所决定的价值,而且他也会欣然接受把这种偏好作为标准,如果这些标准是可能的话……”[2]548-549,但这种说法未免太简单,我们仔细研读霍布斯的著作,会发现他的善恶观认为人追求各种主观的善,但自我保存是最根本的善,是每个人都必然要追求的善。因此,霍布斯把自我保存看成是客观的善。接下来,让我们来看霍布斯是如何论证他的这一观点的。霍布斯认为只要人们从各自的欲望来自由地判断善恶,人就始终处于战争状态。因为人本性的贪婪,不可能摆脱自己这种不理性的欲望,即为现在的利益(善)而抛弃未来的利益(善),从而不可避免地要带来无法预期的恶。但是,霍布斯接着又告诉我们,这种悲惨的战争状态并不是永恒的状态,还有希望和平。人们作为既有欲望又有理性的存在,尽管无法就当下的善达成协议,但他们却可就未来的善达成协议。因为当下的事是感官感知的,而未来的事只有靠理性来认识。理性使人们做出正确的判断:战争状态是恶的,而和平是善的。和平的目的是自我保存,自我保存是最根本的善。因而达成和平、求得自我保存的方式和手段,如正义、感恩、谦虚、公道、仁慈以及其他自然法(美德)也是善[1]121-122。在此,我们会注意到霍布斯论证善的思路与亚里士多德惊人地相似。亚里士多德认为,“善有双重含义,一者就其自身而言就是善,另者则通过它们而达到善。”[3]14-15比如幸福本身就是善,是众多善中的最根本的也是最高的善,但幸福也需要外在的善作为补充,比如朋友、财富以及幸运等,这些外在的善因为能达成幸福的目的而成为善,是手段的善。但霍布斯不同意亚里士多德把幸福当成最根本的、最高的善,也否认存在最高的善。“旧道德学家所说的那种终极的目的和最高的善根本就不存在。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欲望终止的人,和感觉与映象停顿的人同样无法生活下去。幸福就是欲望从一个目标到另一个目标不断地发展,达到前一个目标不过是为后一个目标铺平道路。原因在于,人类的欲望的目的不是在顷刻间享受一次就完了,而是要永远确保达到未来欲望的道路。因此,所有的人的自愿行为和倾向便不但要求得满意的生活,而且要保证这种生活,所不同者只是方式有别而已。”[1]72在霍布斯看来,恶有至恶,暴力致死是至恶,但善没有至善,自我保存是最根本的善。原因在于,人本性追求的各种欲望是多样而复杂的,且永不停歇。霍布斯总结了人的欲望可以分为两类:无限追逐权力和自我保存。人们为满足自己的欲望,必然要努力争取最大的权力,因为,得其一思其二、死而后已、永无休止的权势欲是人类的普遍倾向,当然也就没有什么至善[1]72。但在自然状态下,这种对权力的无限追求必然引发冲突,这种冲突最坏的后果就是处处充满对暴力死亡的连续恐惧和这种死亡的危险。暴死的恐惧使得人们理性地判断:生命是最珍贵的,没有生命,就无法进一步追求利益、权力和幸福。自我保存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追求的善,尽管是个体的善,但得到每一个人的认同,具有一种普遍性,是客观真实的善,应该成为衡量人们行为的标准。因此,霍布斯把自我保存作为评价人们行为善恶的基本标准。
二、理性
霍布斯笔下的人们从不缺乏理性,无论是在自然状态还是公民社会。但是我们不禁要问:同样是具有理性的人们,为什么在自然状态下会导致冲突和战争,而公民社会能保持和平?霍布斯给我们的答案是:理性有私人理性和公共理性之分。霍布斯认为理性是人最本质的属性,它是人们的一种认识和推理能力,它和“人”这个词“范围相等,互相包容”[1]20。也就是说,只要是人都具有理性,且在理性上人人平等。自然状态下只有私人理性,因为自然状态下没有一个统一的公共标准,每个人自由地推理和判断;没有任何法律限制,人们可以自由地采取任何行动;没有公共权力,只有每个人拥有对任何事物的权利。人们按着自己的理性判断采取的任何手段寻求自我保存,都是正当的(善的),没有人能够对此提出任何异议。私人理性导致的冲突不可避免,最终结果就是战争,自我保存只是一句空话。暴力致死的恐惧使人们通过“理性发现了自然法”[1]97。自然法的目的是自我保存。自我保存这个根本的目标(善)确定后,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手段达成这个目标,自然状态下的人们依然会有不同的看法。因为人们对“什么东西是有价值的”持有不同的信念或观念,在实现自我保存的手段的选择上存在着多种可能性,而且人们并不清楚哪种手段才是真正有效的、合理的和善的。霍布斯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尽管所有人都褒扬和平和自我保存所需要的手段,如正义、感恩、谦虚、公道、仁慈等美德,但他们在那些美德的自然即每种美德到底何在的问题上还是存在着分歧。哲学家迄今为止还找不到补救这种困境的办法,原因在于他们看不到行为的善在于其获取和平的倾向,而恶在于与之相反的倾向[4]39-40。但霍布斯自认为找到了旧哲学家所没找到的办法即建立国家,树立公共权威。每个人的理性中都有私人理性和公共理性,公共理性使人们立约建立一个国家来保障人们的安全。国家成立后就由其代表公共理性。这个公共理性确立了人们行为善恶的共同标准,限制人们一部分自由。人们的私人理性要遵循公共理性,从而才能真正信守和平,求得自我保存,进一步追求自己的合法利益,并过上幸福的生活。为什么公共理性可以使人们信守和平和自我保存呢?霍布斯告诉我们,从人们发现自然法、遵循自然法、建立国家、遵守法律与道德规范这一过程中,是正确理性在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对于何为正确理性?霍布斯在《论公民》中的一个注释里解释说:“就人在自然状态中的正确理性而言,许多人意指的是某种永无过失的天赋,而我意指的是理性思考的行为,也即人们对自己行动正确的理性思考(true reasoning),这种理性思考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好处,或给别人带来损失。”[4]41他认为在共同体中,民法(即公共理性)是正确理性,是人们行动的依据;在共同体之外,除了参照私人理性之外,无人能区分正确理性与错误理性,而私人理性又往往是偏私的、不公正的。正因为这个观点,霍布斯用正确理性来论证自然法的神圣和国家主权的合理
三、美德
国家建立之后,人们进入公民社会,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并存,二者时有冲突,如果人们私人理性偏于私人利益,总是把个人利益和当前利益看得很大,缺乏公共理性,缺少对公共利益的关注和维护,这种冲突不能及时化解,则必然导致战争状态。除了国家的强制惩罚权,霍布斯还强调用自然法来解决这一冲突。有学者指出霍布斯的理论中涉及对自然法的论述都可以还原为一种美德理论[5]56-72。笔者赞同这一看法,并试着对霍布斯的伦理理论进行梳理和解读。霍布斯对公民和主权者都提出了相应的道德要求,我们先来看他是如何阐述公民美德的。
霍布斯的伦理理论中,自我保存是终极的道德原则,是目的善,自然法则是由正确理性演绎出来的具体道德原则和主张,为自我保存服务的手段善。而民法(或实证法)是自然法的延伸,是体现自然法精神的具体法规。自然法一共有十九条,涉及正义、感恩、谦虚、公道、仁慈等美德。
第一条法则指出每个人为了自我保存,必须追求和平。
第二条法则指出每个人在别人也同意的情况下承诺放弃或转让对一切事物的权利。在自由方面,允许自己对别人有多少自由,他也必须允许别人对自己有多少自由。这条法则相当于福音书上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第三条法则指出所订信约要遵守。这一条法则是正义美德。正义来源契约,契约出现之前是不存在正义和非正义之分的,“在订立信约之后,失约就成为不义,而非正义无非就是不履行信约,任何事物不是不义,就是正义。”[1]108-109霍布斯区分了人的正义和行为的正义。“用于人时,所表示的是他的品行是否合乎理性;用于行为时,所表示的则不是品行或生活方式,而是某些具体行为是否合乎理性。”但霍布斯又认为“仅仅行为正义并不能使人获得正义之名,而只能说是无罪”[1]113。真正的正义不仅仅是行为正义,而且具有产生正义行为的“一种罕见的高贵品质或狭义的勇敢精神,在这种精神下,人们耻于让人看到自己为了生活的满足而进行欺诈或背信”[1]113。霍布斯把行为的正义分为“交换的正义”和“分配的正义”。“交换的正义是立约者的正义,也就是在买卖、雇佣、借贷、交换、物物交换以及其他契约行为中履行契约。”此种正义,在霍布斯看来,它就是交换主体按相互立约的报酬进行平等的交换。“分配正义则是公断人的正义,也就是确定‘什么合乎正义’的行为。”该种正义是公断人将各人的本份额平等地分配给每一个人。霍布斯后来又详细地论述了公断人的美德即另一自然法,即“公道”也就是分配的正义,它要求公断人不得偏袒任何一方,不得贪污受贿,要秉公处理[1]113。霍布斯的正义是以自我保存这一首要法则为基础的,始终离不开公民和国家的公共理性。对个人来说,正义就是信约的遵守,受约不仅仅是一种行为,更是一种美德。对国家来说,正义的实现需要公共理性的制度和秩序来保障。
第四条自然法是感恩美德。它规定:“接受他人单纯根据恩惠施与的利益时,应努力使施惠者没有合理的原因对自己的善意感到后悔。”[1]115霍布斯强调此美德,是因为施恩有助于和平。人们的自愿行为的目的都是为了使自己得到好处,施惠也是这样。如果得不到回报,恩惠或信任也就不会有了,从而互助和人与人之间的谅解也就不会有了。“这样一来,人们便会仍旧处在战争状态当中,这跟首要的和基本的自然法所主张的寻求和平便会背道而驰。”[1]115此处,霍布斯的论证是从他的个人主义演绎出来的,利己利他,人与人之间良好的信任关系有助于和平。
第五条自然法是顺应或合群美德。它要求“每一个人都应当力图使自己适应其余的人。”[1]115霍布斯认为,人就其社会适应性来说,由于其情感的多样性而本性多样,像砌在一起准备建筑大厦的石头,如果一块石头凹凸不平,安下去要占其他石块的地方,有碍建筑,这种石头就会被建筑者认为不好用而被扔掉。同样的道理,“一个人如果性格乖张,力图保持对自己没有必要、而对他人又必不可缺的东西;同时又性情顽固,无法使之改正,这种人就会被认为妨碍社会而被抛弃或驱除。”[1]115-116因而,人的本性是尽一切可能力求自我保存所必须的一切,如果为了不必要的东西而违反这一点就应当对因此造成的战争负责。那么,作为公民就应该心甘情愿地服从民法,服从主权者。此处,公民服从的不仅仅是代表公共理性的主权者,还服从自己内在的公共理性。
除了正义、公道、感恩与合群等美德外,霍布斯还列举和论述了仁慈、谨慎和谦虚等美德。这些自然法(美德)是人们理性发现的法则,其目的是为了人的自我保存。霍布斯声称“自然法是不可改变的,是永恒的,它们所禁止的绝不可能成为合法的,它们所规定的绝不可能成为非法的。”[4]38但是,霍布斯又坦承自然法并不总是有约束力,它们是内在法则、一种良知,即使人们都褒扬这些美德,但对其作为自我保存这一目的善的手段,善该如何使用,追求着各自利益的人们的看法依然存在着分歧。所以在具体实施中并不具有真正的强制力,社会还是处于混乱之中。为求得和平,自然法必须借助于契约所建立起来的公共权力的强制力量。对于握有绝对权力的主权者,霍布斯对其也有道德上的要求,相比公民美德,主权者遵循的美德更为具体和严格。
首先,主权者必须确保人民的安全。“主权者所有的义务都包含在这样一种说法中:人民的安全是最高的法律。”[9]133霍布斯所说的安全是高标准的安全,“我们不应该把安全仅仅理解成任何条件下的求生,而应该把它理解成尽可能过一种幸福的生活。”主权者“如果不去做法律所能允许做的一切,以确保给公民不仅充分提供生活所必需的所有好东西,而且充分提供享受生活所必需的所有好东西,那么,他们的行事就违背了自然法……”[9]134霍布斯列举了公民可以享受的好东西,分为四类:(1)不受外敌侵扰;(2)内部和平的维持;(3)获得与公共安全尽可能一致的财富;(4)充分享受合法的自由[9]134。为了实现这一职责,面对个人提出的控诉,主权者要对其加以保护使之不受侵害,还要为全体公民提供总的公共理性规划,制定良法。良法是什么呢?霍布斯的的解释是“为人民的利益所需而又清晰明确的法律。”[1]270
其次,主权者“对所有各等级的人平等施法。”[1]268也就是说,无论贫富贵贱者,只要受到侵害都要得到纠正,违法行为都要得到惩罚;对于富贵者的违法行为还要加重惩罚,因为作为富贵者没有必要犯下这些行为。该要求包含自然法的公道美德,主权者和普通老百姓都要遵守,但主权者的宽恕不能违背公道美德。对于违法行为,纯粹关涉国家的,可以予以宽恕而无害于公道;对私人的侵犯,如果得不到受害者的同意,或进行合理的赔偿,就不能予以宽恕。霍布斯还谈到公平税收,也属于平等正义范围。鉴于荣誉对公民的重要,主权者的奖罚要分明恰当,及时消除人们之间的怨恨和人民对主权者的怨恨。
再次,主权者必须让公民学说的正确原理记录成文,并在国内所有的大学传授。年轻人掌握了这些东西,就可以就公私事物上去指导普通人。为了人民安全之故和自身的利益,主权者不能让那些错误的观念如基督教学说和叛国之言论根植于公民的头脑中。至于什么是正确的公民原理及其具体内容,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有详细地阐明,主要包括自然法、主权的性质等。对于教导方式,霍布斯强调教育和论辩的民主方法,“观点植入人的思想中不是通过命令而是通过教育,不是通过惩罚的威胁,而是通过论辩的明晰来达到。”[4]137除了以上的道德要求,霍布斯还要求主权者选择好的参议人员和军队统帅。参议员要选择最能干的,没有受过什么坏意见影响,在有助于和平与保卫国家的事业方面所具有的知识又是最丰富的人。军队的统帅必须是勤劳、勇敢、和蔼、宽宏又忠诚的人。
四、结语
前文对霍布斯政治哲学的善、理性和美德三个基本概念内涵及相互间的关系和蕴含的伦理思想进行了梳理和解读。现对霍布斯伦理思想的理论特征作进一步的归纳。
第一,霍布斯的伦理思想是以他的人性论为基础来展开论证的。
古典哲学是以自然法为基础的理论论证传统,它认为自然或自然秩序存在着约束人类行为的客观规范标准,而近代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从霍布斯开始不再依赖于外在的永恒、客观的标准,转而关注人类固定不变的本性,试图在人性中寻找约束人类行为的规范。霍布斯认为人在本性上就是趋乐避苦的动物,他们必然会利用包括经验和理性在内的一切手段追求那些使他们快乐的东西,而努力回避那些引起痛苦、带来损伤的东西。人欲望的东西就是善,憎恶的东西就是恶。每个人都极力追求自己的利益(善)必然会导致冲突,进入战争状态,孤独、悲苦、伤残甚至暴力致死。具有私人理性的人同时又是公共理性的存在,人的公共理性(正确理性)使人认识到暴力致死是最大的恶,自我保存是根本的善,愿意自己活,也愿意别人活,利己利他才能和平。因此,人们依赖正确理性发现自然法和立约建立公共权力。这种公共权力是公共理性的代表,是人们善恶行为的公共标准制定者,是迫使人们守约的道德保障和惩罚机制。尽管霍布斯的利己主义的人性论假设一直被人们认为带有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但仔细研读霍布斯的著作,我们可以发现,霍布斯其实对人性并未完全失望,因为人本性中的理性会促使人们走向和平之路。霍布斯的伦理理论让人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创造和构建个人的和共同体的生活模式,包括政治的与道德的模式。霍布斯为论证自己的理论,同样以人性为基础,通过两条途径来支持他的观点的。一条叫做理性之路(霍布斯称之为“科学的方法”),他希望建立的是像欧几里得几何学那样有力的公理体系,比如自然法的推演。另一条是经验之路(霍布斯称之为“审慎的方法”),霍布斯想通过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观点,并且希望能让所有的人都接受。经验的方法是一种较低层次的方法,依赖于每个人的经验,这不取决于他有没有文化。这一级的方法以我们的感觉、经验为基础。霍布斯相对古典理性主义传统,更注重感觉、经验在人的认知中的作用,并指出激情与意志是人行动的推动力,所以霍布斯的伦理理论既是理性主义的,又是经验主义的。
第二,霍布斯的伦理思想突出了公民的主体意识。
霍布斯笔下的公民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首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来源于个人相互间的协商同意。相对于以往只强调义务而忽视权利的道德哲学相比,霍布斯明确提出了个人权利的概念,为其道德体系寻找一种切合人性的基础。人是趋利避害的动物,自我保存是人最基本的权利和善,自我保存需要和平。出于保护个人自然权利的目的将寻求一种绝对权力(国家)来保障和平。这种权力(权威甚至专制)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契约来达成的,这种契约是一种道德秩序和义务。而遵守这一责任和义务不是来自外在的约束,而是个人相互间的协商同意的一种内在约束,是自我施加于自身的。由此,霍布斯的伦理理论突出了公民的自律意识。其次,国家和个人的关系中,突出个人的优先性。人们立约建立国家后,国家以保障公民安全为首要的任务,国家权力是满足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需求的工具,除此之外,国家不再具有任何其他的目的,因而,体现了公民权利优先的原则。在霍布斯之前的专制社会,国家权力总是优先于个人权利的,而在霍布斯这里,个人权利被置于国家权力前提位置进而获得对国家权力的优先性。这也是霍布斯被公认为现代政治哲学奠基人的主要原因之一。再次,公民具有公共理性。霍布斯认为公民在利益(善)平衡和价值选择以及重大事件面前,能够从实际出发,不被个人偏见所左右,理性地选择对每个人都有益的东西,注重对公共利益的关注和维护。比如,为了每个人的自我保存,建立国家主权;为了每个人的自由,放弃自己的一部分自由;为了公共福利,服从统治者。最后,公民富有宽容精神。霍布斯笔下的公民具有正义、感恩、谦虚、公道、仁慈等美德,这些美德使得他们富有宽容精神。公民承认别人有权利做出与自己不同的选择,发表不同的见解,对那些与自己不同的政治主张、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给予必要的理解和尊重,以促成公民社会的自由、和谐与进步。
第三,霍布斯的伦理理论兼具规范伦理学和美德伦理学的理论特征。
规范伦理学寻求可普遍化的道德规范和原则,美德被定义为一种按照道德原则来行动的内在倾向,强调行为主体对义务和责任的承担,关注的焦点是“一个人应该如何行动”这个问题;美德伦理学认为道德与人性的完善具有本质的联系,而且是一个人的幸福的构成要素,以行为主体的品格作为关注的焦点,关注的焦点是“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这个问题。霍布斯的伦理理论在于如何寻求一套合理的道德法则以及该道德规则体系应该如何有效发挥作用,强调了公民和主权者的义务和责任。从这方面来考察,霍布斯的伦理思想具有规范伦理学的理论特征。据此,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在哲学史上被人称为现实主义的政治哲学,它不同于古典理想主义政治哲学之处在于,不再把追求至善、有德性的生活和人的完满作为政治生活的目标,而是把“大多数人和多数社会在大多数时间里所实际追求的目标作为政治生活的目标”[6]451。国内有学者认为霍布斯理论中的美德是对规范的补充[7]41。但是,对规则和行为之间,是什么促使行为主体恪守规则呢?霍布斯建议我们还是回到行为主体——人本身。如此,我们会发现霍布斯的伦理理论不仅仅是如何解决行为合理性的问题,还是行为主体本身有没有良好的品质和美德的问题。如果从美德伦理学角度来分析霍布斯的自然法的话,我们会发现他的自然法不再是一种原则约束或教导我们应该遵循哪种行为,而是出于理性而培养的品性。霍布斯的理性既是一种推理能力,能正确判断在具体情境下应该如何行动;还是一种实践智慧,能培养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指引人应该拥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霍布斯曾经告诉我们,即使在自然状态中我们也要修整自己的个性,使其与自然法保持一致。“这些自然法由于只对欲望和主观努力具有约束力,我所指的是真诚与持久的努力,所以便易于遵行。既然自然法所要求于人的只是努力,努力履行这些自然律就是实现了它们,实现了自然法的人就是正义的。”[1]113所以霍布斯在谈到正义美德时,区分了正义的行为和正义的人,说明有德性的品质才是判断行为主体的基本标准。他暗示了自然法要得到恪守,就不仅仅在于选择某个具体的行为是否正确的问题,而是如何长期保持一种习惯性倾向的问题。尽管霍布斯的伦理思想与古典美德伦理思想不同,古典美德的语言的确被霍布斯猛烈抨击,视为“无意义的语词”乃至叛乱的重要根源,然而我们似乎也不宜过分夸大霍布斯与古典美德伦理思想相断裂的一面。霍布斯对古典美德伦理思想的批判也是为了更好地构建自己的伦理理论体系。因为古典美德只是少数人的美德,那只是少数几个圣人才能过的生活,而普通人并不喜欢这种生活,现实也不允许过这种生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以哲学家的标准来规范普通民众的生活,所以只能是乌托邦的想法而已。霍布斯不反对把美德引入政治,只是反对把错误理解的美德引入政治。他对古典美德伦理学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建构适合大多数普通人的伦理理论体系,这种伦理理论既注重制度和秩序的构建,又极为关注“人”的问题,兼具规范伦理学和美德伦理学的理论特征。因此,不少霍布斯的研究者都认为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含有丰富的美德伦理思想。贝尔科维茨认为,无论霍布斯所言的公民抑或主权者,都有美德方面的要求,并认为美德乃是霍布斯复杂政治机械各关节与构件的润滑剂[8]39。迪兹更表示要将霍布斯看做一位公民美德的理论家,政治化的“十诫”(Ten Commandments)成为其公民美德的核心要求[9]108-111。
[1](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2]David Gauthier.Thomas Hobbs:Moral Theorist,Journal of Philosophy,Vol.76,NO.10,1979.
[3]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4](英)霍布斯:《论公民》,应星、冯克利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5]David Boonin - Vail.Thomas Hobbes and the Science of Moral Virtu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6](美)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李天然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7]刘科:《从“愚人”问题看规范与美德》,载《道德与文明》2012年第2期。
[8]Peter Berkowitz.Virtue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Liberalism,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
[9]Mary D.Dietz.“Hobbes’s Subject as Citizen ”,in her ed.,Thomas Hobbes and Political Theor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