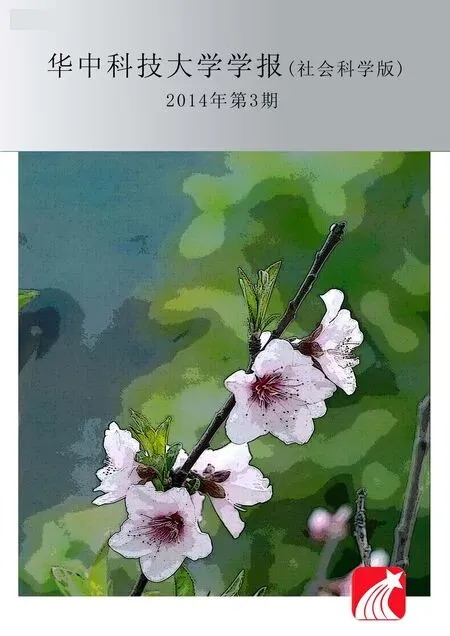联合外出家庭:一个包工头家庭共同体的变迁
程士强,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与人口学院,北京 100872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中国的农村和农民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社会转型,那就是近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进程。将农村放入现代化的视野中,就不能离开城市孤立地看农村,城乡人口流动是中国城市化和农村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方面。流动人口(农民工)处于城乡关系的“连接点”,也位于社会经济急剧变迁的“前线”[1]6,所以,流动人口是探究中国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的重要研究对象。但是,现有的流动人口(农民工)研究却存在着一种“劳工偏见”,似乎流动人口只是些打工者,这种偏见阻碍了我们对这一群体及其所处的社会转型过程形成全面深刻的认识。
包工头及包工制度在城乡流动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与普通农民工相比,包工头具有一些特殊的意义和重要的差异。包工头是相当一部分农民工日常工作生活的组织者,也是城市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中介力量,是他们将农村的劳动力和城市的工作岗位连接起来。更重要的是,包工头并不是简单的“打工者”,而是农民工中的精英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一种表现,在一定意义上,包工头在城市经营的是“微型企业”,而他们自己是“企业家”和“创业者”,他们的经营活动中包括了普通农民工较少涉及的市场开拓。所以,尽管大多数包工头在城市中也是普普通通的草根阶层,但他们的经营活动和日常生活却要比农民工复杂得多。由于包工头比普通的农民工更深层地参与了城市生活和市场经济的大潮,他们身上可能具有透视中国社会转型的更深刻和更丰富多彩的研究主题。
然而,目前研究大多关注的都是“广义的农民工”或“流动人口”,对该群体的研究缺乏进一步的细分,包工头很容易被更为热门的普通农民工研究所遮蔽。仅有的相关研究也多不是以包工头为中心,而是把包工头作为影响农民工的一个外在因素进行阐述。已有的研究或者以农民工为中心把包工头作为影响农民工的一个外在因素,或者宏观地分析包工制度,或者间接地涉及包工头某方面的行为特征的,即没有从包工头的主体性的角度开展研究,而这正是本文的努力方向之一。
徐勇认为,家户制是对中国现代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基础性制度和本源型传统,从中可以寻求当今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历史脉络和未来走向[2]。那么,家庭组织在城乡流动中的延续与变迁,自然也就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基础性问题。但是,以往的流动人口研究多是以个体或社区为分析单位[3][4],即使涉及家庭,也多是用整体的、抽象视角进行分析[5][6]。而本文则力求将家庭放入分析的中心,旨在探讨包工头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单位具体如何运作,及其在城乡流动中如何变迁。
(二)文献回顾:关于家庭结构现代化的争论
黄宗智指出,主流的社会科学理论以及中国当前的现代化意识形态都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以家庭为主要单位的小农生产模式将被个体的产业工人生产模式取代,三代家庭也将会被核心家庭取代[7]。确实,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家庭结构会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趋向于核心化,家庭规模变小,功能趋于单一化。杨善华和沈崇麟指出,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家庭规模都存在小型化的趋势,而且,家庭功能将逐步减少,适应市场经济的新型家庭制度更强调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分离,并把家庭看做私人生活的领域[8]8-9,248。王跃生在农村家庭结构变迁的研究中也指出,当前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影响着农村家庭的核心化水平,人口迁移流动会加速大家庭的分解[9]28,158。
对于这种主流观点,也有学者根据中国家族企业和家庭工厂等方面的情况对上述家庭结构现代化视角的部分观点提出挑战,表明家庭的经济生产功能并没有剥离出去,家庭或家庭共同体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黄宗智认为,中国经济史的实际与西方理论图式十分不同,家庭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经济组织,三代家庭也持续了下来,家庭单位的经济行为也展示了与一般经济学理论很不一样的逻辑[7]。陈秋虹指出,河北北镇在乡村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家庭工厂是一种跨越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组织,它属于家庭经济,产权归家庭所有,核心家庭和生产的高度同构,它的经营和管理模式与传统家庭内的角色分工极为类似[10]24。除了核心家庭外,更多的研究说明了家族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的经济功能,例如,李晓兵和李东认为,家族企业是家族与企业的结合体,家族的管理特点会深刻影响到家族企业的管理,中国的绝大多数家族企业管理受到家族文化及精神的影响与制约[11]。
以上两种视角都有其现实依据和理论意义,但又都失于片面和简化。笔者认为,对以上理论争论的一个有益补充是回到日常实践,笔者希望通过个案分析来探究家庭在城乡流动这一现代化过程中究竟发生什么样的变迁,以此呈现新的观察视野、发现新的知识。
二、包工头家庭:一个经济组织与外出单位
本文的案主——张家*即张占军一家,根据学术惯例,本文中提到的所有人名和地名均经过技术处理。,在笔者开展调查期间居住在北京市海淀区D镇某外来人口聚居区。他们的家乡是河北省Y县,张占军今年43岁,在家排行老大。1996年10月份,张占军来到北京打工,跟着别人做家庭装修。1997年,张占军开始创业,自己做起了包工头,带着一帮工人搞家庭装修,他的妻子郭明霞则在北京金五星市场租摊位卖服装和小礼品。他的四弟张占征、二弟张占华也先后随他进京打工。兄弟三人各自的核心家庭之间既独立又合作、既分化又聚合,形成一种特定的家庭共同体,这就是本文所指的包工头家庭。
除了做装修外,张占军还承包过一家移动信号设备公司的施工工程,后来在北京的郊区租地建房出租,并以此发家,完成了从农民工到小包工头、再到有一定实力的经营者的转变。他的两个弟弟张占征和张占华一开始跟着他打工,2006年之后张占征和张占华也先后开始创业,2006年张占征自己干起了装修,2008年张占华从张占军那里接手了移动信号设备安装的工作。之后三兄弟基本是各干各的,但在经营活动和日常生活中也存在着比较密切的联系和互助。在这个家庭共同体中,老大张占军的经济实力最强,经历最丰富,人也有威信。用他妻子郭明霞的话说,是从“几毛钱的公交都舍不得坐”到“在北京有房有车”,本文的行文逻辑主要是以他的经历为线索。
虽然把研究对象称为“包工头家庭”,但张占军一家的家庭经营具有明显的多元化特点。除了做包工头外,张占军和妻子在金五星市场有摊位,他后期也主要做租地建房出租的生意,而且在2008年把移动信号安装的工作转给二弟张占华后,他就基本退出了包工头的行列。尽管如此,在北京的16年里,他干包工头的时间占到了12年,而从大的家庭共同体的角度来看,他的两个兄弟目前也还在做包工头。所以,即便这个家庭在16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仍以包工头家庭来统称它。
对于这个包工头家庭来说,家庭既是一个情感共同体,又是一个经济组织和外出单位。在张占军进城之后不久,他的妻子郭明霞也来到北京和他一起创业,在北京金五星市场经营摊位。自此,他就以家庭而不是以个体为单位进城创业。张占军一直以“家本位”的态度来看待金五星市场的经营:虽然一开始不赚钱,但是可以先让郭明霞过来有个事做,“这就有个家了”。张占征和张占华的妻子也分别先后随丈夫来京,张占征说:“结婚后一个人在外面,一个人在老家,不是个事儿。”另外,在一段时间内,张占征和张占华也都跟着大哥张占军干,“给自己兄弟干活,自然会卖力”,这就在监督和激励上省去了不少麻烦。张占军在没事时会到金五星市场帮妻子运货,这种对劳动力的充分使用也是家庭在作为一个经济组织时的特殊优势。
按照韦伯的观点,随着理性化的进程,企业经营将脱离家庭共同体。他认为,原先家庭成员零用钱与商业组织融为一体的情况将演变为一种分离出来的、在一个“企业”内部从事的“职业”,使原有的家庭、工场和账房的三位一体瓦解了,其中决定性的因素是家庭与企业在“簿记”上和法律上的分开。但是,张占军一家城乡流动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生韦伯所说的家庭与经营的分离。经营活动与家庭消费之间、家庭内部的不同经营领域之间,均没有明确的资金和财务分割,所有的投资与消费、盈利与亏损最终都统一于家庭。
三、兄弟家庭之间的产业转移与互助合作
包工头家庭是一个经济共同体和外出单位,但这并不代表它的结构在城乡流动的过程中会一直保持稳定。从2006年开始,张占军的两个弟弟改变了跟着他打工的状态,先后自己创业做起了包工头,开始有了各自的事业。张家的经营领域进一步扩展,其家庭结构也开始分化。
张占征主要是在一个建材城做店面装修,也兼做一些家庭装修。张占华的创业则是直接从张占军手里承接的项目。从2004年开始,经北京的一个亲戚介绍,张占军开始固定和一家移动信号覆盖公司合作,承包这家公司的设备安装工程,也就退出了装修行业。2008年,张占军把移动信号覆盖设备安装的工作转给了张占华,自己也就不再包工。转让的原因也有几分“家本位”和道义经济的色彩,张占军说:“一方面是租地盖房那边太忙,自己不想太累,另一方面是想让他(张占华)尽快发展起来,想帮他,不能说自己发展挺好,兄弟们都不行,如果他一直跟着我干,就只能是个工人。”
这样,兄弟三人都有了各自的事业,并且基本上分开独立做。关于为什么兄弟们不一起合伙干同样的事,张占征说:“一开始我和占华都跟着占军干装修,后来有些事上想法不一致,在一起可能有些相互牵制,就分开吧。”
除了避免因意见分歧而产生冲突外,相互分化也许还可以整合更多的资源。分开各自独立干可以开拓更多的领域,也可以和家庭外具有不同优势的人合作,进而可以汲取和撬动更多的资源。正如张占征所说:“在一起只是一个方向,分开干就是多个方向。”
独立并不是孤立,分化不意味着分裂,张家在多元化经营的过程中仍然是一个内部密切联系的有机体。血缘和亲情的纽带作用仍然比较强大,他们在经营和生活上还存在很密切的联系和互助。张占军说:“如果以前我做装修时的老关系来找我,我都把活儿推给占征了。”张占华那边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也还是需要张占军来出面和公司联系。张占征则说:“占军这么多房,如果说房顶塌了,当时找外面人吧,人家可能不过来,跟我说一声,我第二天可能不去工地,我把这个活给他干了,不说钱,就是帮忙。再一个,我这儿有工人,占华那儿也有工人,偶尔缺人的话可以相互调一下,从外面临时找人自己不放心,这儿都是咱老家的人,去了也好使。”
除了这种日常性的经营互助外,他们日后在租地建房领域中还进行了更紧密的合作。张占军在租地建房中获得的高收益对他的两个弟弟产生了很强的示范效应,经过创业两三年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后,他们也先后开始进入这一领域。同租地建房中的高收益并存的是更大的资金压力和风险,因此,在投资、选址、建设等方面,张家三兄弟进行了比较密切的合作,表明分化后的家庭共同体在需要时仍存在重新整合的倾向与能力。
在城乡流动的过程中,张占军一家的家庭结构发生了相应的变迁,其家庭经济经历了一个结构分化和资源整合的辩证过程。在创业前期,家庭的一体化程度比较高,张占征和张占华跟着张占军打工,张占军也会到金五星市场给妻子帮忙。家庭内部的紧密联结有助于渡过艰难的“适应期”,在经济上也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这种内聚性却阻碍了对更多经济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张占军说:“要是两口子都在金五星干,收入肯定比一个人还多点,但是不会往大处发展。”所以,张占军逐渐和家庭以外的人合作,张占征和张占华也先后独立出去。这样,家庭结构发生了分化,形成了“多元经营格局”,但其内部根据不同需要还是存在不同程度的合作,整个家庭所能汲取和整合起来的资源也大大增加了。
从张占军、张占征和张占华三兄弟先后创业的经历看,他们之间的产业转移类似于东亚各国经济发展中的“雁阵模式”[13]。张占军做过装修和移动信号覆盖设备安装,而他的两个弟弟在创业时也先后进入这两个行业,他则从中相继退出,后来在张占军的带动下,他们又都进入了租地建房领域。这种“雁阵模式”使得他们之间可以进行直接或间接的互助,尤其是使得后来者不必孤立地进入陌生的行业。“雁阵”中的大雁独立而不孤立,在拥有多种汲取资源的渠道的同时,保持协同和资源整合的能力。在“雁阵模式”中形成的家庭经济共同体不同于家庭工厂和家族企业:家庭工厂由核心家庭独立经营,并将跨家庭的亲属关系排除在经营协作之外,家族企业则是多个家庭共同参与同一个企业的内部经营(陈秋虹,2011:7),本文的家庭共同体既不排斥跨家庭的亲属合作,又不是一个完全一体化的经营实体。
四、联合外出家庭:一种新型的家庭经济组织和流动人口家庭类型
关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家庭结构,以往研究以家庭结构现代化为主流,家族企业、家庭工厂等研究则与之针锋相对。本文所研究的包工头家庭展现了一种与这两个对立视角都有所不同的家庭结构形态,包工头家庭通过分化与整合的辩证过程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经济组织,张家兄弟在“雁阵模式”中形成的分立而不孤立的家庭联合体,具有“分”而不“离”,“合”而不“统”的特点。
首先,按照家庭结构现代化的理论,各种大家庭的分化和核心化是社会变迁的趋势,城乡流动则更会加速大家庭的分解。但是,张占军一家在流动中却形成了一种松散的联合家庭,呈现出一种联合化的趋势。从严格意义上讲,联合家庭是指由父母和两对及以上已婚子女所组成的家庭,或者是兄弟姐妹婚后不分家的家庭[14]105。之所以说他们的大家庭是“松散的”,就是因为张家兄弟分家后的核心家庭之间“合”而不“统”,兄弟家庭之间既有密切合作,又保持基本的独立性。这种核心家庭的联合化形成的家庭共同体更接近于所谓的“网络家庭”,即建立在父系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家庭单位联合体[9]454。不过,在这里,城乡流动加强了网络家庭的内聚力,而不是对其起分解作用,其内部关系也没有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变得功利化、理性化。张家的家庭共同体内部联系更加紧密和富有弹性,而且这种联系纽带更综合地涉及血缘情感、生存需要和经济发展等多种因素,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家庭经济共同体。更重要的是,这一家庭共同体的独特之处不在于核心家庭之间存在着相互关系,而在于这种关系的动态性——它会因不同情境而进行分化或聚合。
其次,关于家庭的经济功能,家庭结构核心化的理论倾向于认为家庭生活和经济活动是逐步分离的,家庭将只剩下消费功能和私人生活功能。在此,家庭工厂和家族企业的研究更符合包工头家庭的实际,包工头的家庭也承担着十分重要的经济生产功能。但是,本文中的包工头家庭并不像家族企业和家庭工厂那样是一个经营实体。从大的家庭共同体的角度来说,张家内部的各个核心家庭尽管存在密切的经济联系,但它们的经营是基本独立的。从核心家庭本身来说,尽管它是一个统一的资金库和收支核算单位,但其成员的经济活动主要通过与家庭之外的人的合作来进行。这种情况与家庭工厂中“家庭和生产的高度同构”形成鲜明对照。
如果把家庭作为经济生活中的一种“传统资源”,一般认为其基本特点是结构上的内聚性和封闭性,家庭工厂或家族企业的优势和劣势都被认为是来自于这种内聚性和封闭性特点。但是,包工头的家庭经济组织却显示了它开放性的一面:虽然家庭是他们的利益所在和情感的归宿,但他们的经营活动却超越了家庭。当然,并没有像现代企业组织那样发生家庭和经营活动的分离,正是这种“不分离”导致了经济组织的“家本位”色彩。在此,实践向我们展示了家庭和经济关系的复杂面向,也向我们展示了家庭结构的复杂性和家庭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在面对不同环境时的权变特点。
前文提到,本文的包工头家庭既不符合家庭结构现代化理论,也不同于有更强传统色彩的家族企业或家庭工厂,那么,这种家庭现象该如何归类呢?尤其是,作为流动人口家庭,它是不是一种既独特又重要的家庭类型呢?
李强(1996)根据对农民工的研究总结出了五种流动人口家庭类型:(1)单身子女外出型,即单身女子或单身男子外出打工。(2)兄弟姐妹外出型,即家中一个子女先在外面闯,等扎稳了脚跟,再把其他兄弟姐妹带进城。(3)夫妻分居型,即丈夫一方或妻子一方在城市中做民工,留下配偶、孩子和老人在家乡。(4)夫妻子女分居型,即年青的夫妻二人外出打工,留下老人与孩子在农村。(5)全家外出型,即夫妻子女的小家庭全家都外出打工,这种农民工的家庭一般仍有老人留在农村。
李强对农民工家庭类型的分析比较全面,但是,本文中的包工头家庭却难以归入这五大模式。张家以联合化的家庭共同体整体外出,在城乡流动的过程中既独立又合作、既分化又聚合,形成一种“分”而不“离”、“合”而不“统”的家庭经济组织,我们将这种流动人口家庭称为联合外出型家庭。
联合外出家庭与上面提到的五种家庭类型中的兄弟姐妹外出型和全家外出型比较类似,但又和二者中的任何一个都存在差异,更接近于二者的结合体。它一方面存在兄弟姐妹之间的相互带动,但又不仅体现在兄弟姐妹个人身上,而是兄弟姐妹的各个核心家庭的全家外出,这种全家外出不是单个小家庭的外出,而是形成一种联合化的家庭共同体。
从关系网络视角研究人口流动的学者提出了“移民网络”理论,以表明先前的外出者对后来者的带动作用和他们在关系网络中的相互支持[4]467[15]。联合外出家庭与这种“移民网络”也存在本质的区别,网络移民虽然依靠流出地原有的关系网络,流动到城市后也存在密切的联系,但是,组成关系网络的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人或家庭。而联合外出家庭是一个完整的共同体,其成员中先外出者是作为这个整体的一部分而外出的,他是整个家庭共同体外出的一个步骤,这里的外出是一个以联合家庭整体为单位的外出。而联合家庭的成员先后进城之后,他们也作为一个整体生活在城市中,形成的是一个分工协作的共同体,而不仅仅是一个网络,所以联合外出家庭在城市中联系的密切程度要大于“移民网络”。
五、结语
正如黄宗智(2011)所言,家庭在当代中国仍是一个重要的经济组织。对于进城创业的包工头来说,家庭不仅是情感的寄托、奋斗的动力,更承担着重要的经济功能。包工头以联合化的家庭共同体整体外出,在创业的过程中既独立又合作,既分化又聚合,形成一种“分”而不“离”、“合”而不“统”的联合外出家庭。
在进城创业的过程中,包工头家庭经济组织的结构变迁不符合现代化理论和关于家族企业的研究,也很难用流动人口研究中常见的关系网络理论来解释,联合外出家庭这种家庭经济组织具有明显的动态性、多元性和权变性,它同人们所熟知的家庭类型及经济组织类型存在较大差异:作为一种家庭形态,它既不同于传统的大家庭,也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核心家庭;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形态,它承担经济功能的方式既不同于富有传统色彩的家庭工厂、家族企业,更不同于正规化程度较高的现代企业组织;在流动人口家庭类型中,这一家庭的结构形态及其所体现的家庭和经济的结合方式均不同于以往研究中所提到的类型。
联合外出家庭的分布在流动人口群体中存在一定的规律,它多见于进城创业者,而不是普通的农民工。这里存在以下三方面的原因:首先,进城创业家庭的经济资源较多,可以供养家庭中的非直接劳动力,使得大家庭的流动成为可能;其次,创业比务工面临的经济机会要多,可以容纳更多的家庭或家庭成员作为劳动力共同参与;第三,创业的经济活动比较复杂,客观上需要更多的家庭或家庭成员的合作。
本文是一个带着特定理论问题的个案研究,理论观点是通过具体的个案分析中得出的。基于对个案研究局限性的认识,本文并不是要通过个案来推论总体特征,也不试图进行理论建构。笔者认为,虽然个案研究因为代表性的问题难以呈现普遍性的事实,但可以通过个案来深入地探讨某个理论问题,在深度的个案研究中提出新的理论观点。虽然这些理论观点难以由个案研究本身来验证,但这些观点的提出仍然是对普遍性的理论问题的一种贡献,而对这些理论观点的验证和进一步系统化的任务要留待后续的其他研究包括定量研究来完成。
[1]李培林:《译者序言》,载(法)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2]徐勇:《中国家户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
[3]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载《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4期。
[4]项飚:《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
[5]李强:《关于“农民工”家庭模式问题的研究》,载《浙江学刊》1996年第1期。
[6]陈文江、张咏梅:《城市流动人口的婚姻和家庭》,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7]黄宗智:《中国的现代家庭:来自经济史和法律史的视角》,载《开放时代》2011年第5期。
[8]杨善华、沈崇麟:《城乡家庭:市场经济与非农化背景下的变迁》,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9]王跃生:《中国当代家庭结构变动分析:立足于社会变革时代的农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10]陈秋虹:《家庭即工厂:河北北镇乡村工业化考察》,载郑也夫、沈原、潘绥铭主编:《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版。
[11]李晓兵、李东:《家族企业的人文制约及家族式管理》,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5年第9期。
[12](德)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3]罗丽娜:《东亚“雁阵模式”式微原因新析及启示》,载《特区经济》2006年第7期。
[14]潘允康、刘瑛:《家庭结构》,载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
[15]刘莹:《移民网络与侨乡跨国移民分析——以青田人移民欧洲为例》,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