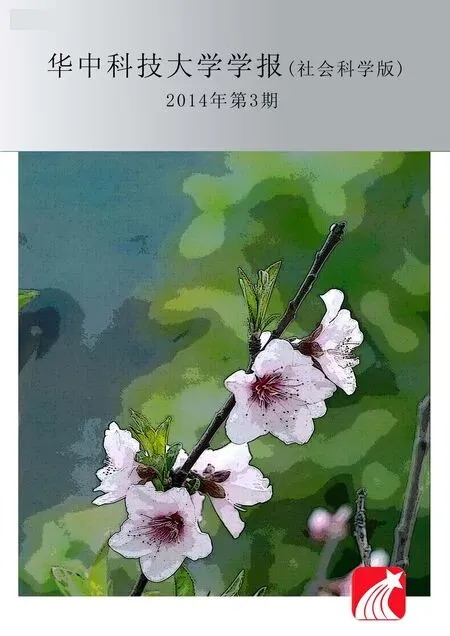想象与事实之间:调查研究中的文化障碍
方长春,
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8
调查研究基本程序是逻辑推演加经验证实。逻辑推演意味着对被研究者经验世界的一种预设,包括研究议题的设置、研究假设的提出和经验资料收集工具——问卷的设计;而经验证实则依据在研究预设基础上形成一套符码系统——问卷收集有关被研究者经验事实的经验资料,进而验证、修改之前预设中关于被研究者经验世界的各种规律性的认识。然而,由于可能存在文化差异,调查研究的研究预设有可能偏离被研究者的经验事实,进而影响到调查研究的有效性。这种偏离通常被调查研究形式上的程序完整性所遮蔽,进而建构出一种虚假的有效性,而研究者又往往因为对文化差异及其特殊性的忽略而无意识于这种虚假的有效性。
一、调查研究及其主客观障碍
调查研究是一种专业化、规范化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尽管这一专业化和规范化的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各学科中已经被普遍使用[1]38-43,但在汉语表达习惯中,人们对调查研究以及与之相关的“调研”、社会研究方法、社会调查方法等概念的认识还存在不一致的地方。这种不一致性 “一方面导致了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误用、错用和滥用,危害和影响着许多社会研究以及社会调查成果的质量;另一方面也影响着社会研究方法和社会调查方法的教学、研究及交流”[2]23-32。在笔者看来,在汉语表达习惯中,上述几个概念通常都被理解为“经验性的社会研究”,以区别于理论性的社会研究。正是由于人们在“经验性的社会研究”这一意义上使用,并且经常是同时或交替使用上述概念,才造成了相关概念的混淆。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社会调查其实只是众多经验性社会研究中的一种方式,经验性的社会研究,除了调查研究这一研究方式之外,还有实验研究、实地研究和非介入性研究等。就不同的研究方式而言,其方法论基础是不一样的,其对研究对象的基本假定、对认识研究对象的可能性与可能路径的基本假定是不一样的,由此导致的经验研究层面的程序和技术手段也是不一样的。因此,尽管在非学术语境中运用上述众多概念来指涉经验性社会研究并无大碍,但在学术研究过程中,混用上述概念则有可能导致人们对特定研究方式所隐含的有关经验世界的基本假定(即方法论)的混乱,以及与之相关的研究程序和技术手段的混乱。作为经验性社会研究方式之一的调查研究,是建立在实证主义方法论对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及其认识方式的基本假定的基础之上的,具体来说,调查研究是指“一种采用自填问卷或结构式访问的方法,系统地、直接地从一个取自某种社会群体的样本那里收集资料,并通过对资料的统计分析来认识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社会研究方式”[3]159。
从经验资料收集的角度来看,调查研究可以理解为一种以标准化问询的方式来收集资料进行研究的过程,其中自填问卷是一种标准化的书面问询,而结构式访问则是一种标准化的口头问询。所谓的标准化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其一是问询的程序、内容、方式和方法是统一或类型化的,人们的回答也是统一或类型化的*类型化是指问题或答案被分成若干类别,对于答案的类型化而言,在调查研究中可以分为事前类型化和事后类型化,事前类型化即为通常所谓的问卷中的封闭型问题,事后类型化则通常表现为问卷中的开放题。当然在有些调查研究中,对于开放题的回答并不做事后的编码处理,只是为了调查实施过程中缓解被调查者的被强迫感,以避免在调查实施过程产生不良情绪。;其二是不同被调查者面对被询问到的特定问题或事项有着统一的理解,并且这种理解也与研究者事先预设的意义是一致的。调查研究中的标准化问询是建立在研究者、调查员与被调查者互动的基础之上的*研究者与被调查者的互动通过问卷或访问员的结构式访问而发生,研究者对这一互动过程的直接影响体现在研究设计(包括问卷设计)当中。,而互动则依赖被调查者的配合,被调查者的配合程度也因此会影响资料收集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正是由于研究的主客双方互动的存在,研究者必须意识到在这种互动过程中可能存在影响人们对调查进行配合的各种障碍因素。风笑天曾对调查研究中影响被调查者对调查过程进行配合的主客观障碍进行了概括,认为阻碍被调查者合作的因素主要有两类:其一,主观上的障碍,即由被调查者心理上和思想上对问卷产生的各种不良反应所形成的障碍,比如问卷内容太多,问卷表太厚等导致的被调查者的畏难情绪,或因调查涉及个人隐私等敏感内容带来的不合作或抵触情绪;其二,客观上的障碍,即由被调查者自身的能力、条件等方面的限制所形成的障碍,比如被调查者的阅读能力、记忆能力、计算能力等带来的限制等[3]166-167。 在笔者看来,调查研究过程中阻碍被调查配合的因素除了这两类障碍之外,还有可能存在另一种类型的客观障碍,那就是与文化差异相关联的障碍。在调查研究的主客体的互动过程中(这里的互动,既包括研究者借助问卷或结构式访问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也包括调查员与被调查者之间的互动),由于研究的主客体之间可能存在的文化差异*本文所谓的“文化”指的是“在一特定群体或社会的生活中形成的、并为其成员所共有的生存方式的总和”(周晓虹, 1997)。,或者由于被研究者的文化特殊性的存在,被调查者对所问询的问题或事项的理解与研究者事先预设的所问询的问题或事项的意涵之间就有可能不一致。而这种不一致实际已经违背了前文提到的调查研究的标准化要求。简言之,文化差异存在,就有可能导致“答非所问”,这就是文化差异这一可能存在的客观障碍对调查研究可能产生的影响。尽管有时这种障碍并不影响调查的互动过程在形式上(具体表现为围绕特定内容的问询过程)的完整性,但其有效性则大打折扣。研究者如果忽视导致“答非所问”的文化差异这一可能性障碍的存在的话,那么就有可能误认为被调查者“答即所问”。由此,文化差异这一客观障碍所导致的缺陷也就有可能在研究者的无意识之中被遮蔽起来。对调查研究的经验证实过程分析,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可能存在的文化差异这一客观障碍对调查研究的影响。
二、作为经验证实的调查研究
如前文所言,每一种经验性社会研究的展开都是建立在一定的方法论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特定的经验性研究方式和方法一经被采用,其背后都有一些针对其研究对象的特性及认识和把握研究对象的可能性和可能的路径的基本假定,而不管研究者是否清楚地意识到这些假定(研究者有时无意识于这些假定,是因为其从根本上就默认了某些假定)。但值得注意的是,正是由于对经验研究背后的基本假定的无意识,有时候研究者会在不知不觉中混淆不同的假定,进而导致研究实践层面的逻辑混乱。
在社会研究中影响最为突出的是实证主义*需要说明的是,国内学者还存在一种对“实证主义”的误读,并常常把“实证研究”理解为一种是与“理论研究”相对应的“经验研究”,而不是从方法论意义上来理解所谓的“实证研究”。相关讨论参与蔡禾等早年的讨论(蔡禾和赵巍, 1994)。传统和人文主义传统及其对立。撇开两种方法论的诸多争论,仅从直接影响经验研究的层面而言,这两种方法论传统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认为人类行为及社会现象中具有某些普适性的规律存在,并且可以仿照自然科学对这些规律进行认识和把握。这种具有普适性的规律其实就是指超越个别、具体的一般性存在,作为实证主义的集大成者之一的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对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的界定正体现了对这种一般性存在的强调。他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事实[4]34,而根据涂尔干的界定,社会事实其实正是一种超越于个别之上的并具有强制性的一般性存在,并且涂尔干进一步指出,“一种社会事实的决定性原因,应该到先于它存在的社会事实中去寻找”[4]125,这是为把握一般性存在而对研究方法提出的准则性要求,涂尔干自己的经验研究也一直贯彻了这一准则,譬如他对社会整合程度与自杀率之间关系的研究[5]。此外,实证主义一直都强调经验证实的作用,强调“知识来自于对可感现象界的认识,任何知识的产生都应完全归于可证实的经验”[6]。而作为实证主义的进一步发展的逻辑实证主义的“实证色彩要比传统的实证主义强得多、严格得多”[7]。与实证主义不同的是,人文主义传统则对人类行为和社会现象中是否存在普适性的规律提出质疑,强调社会人文现象的个性、特殊性(如民族性、本土性以及语言、文化特性等),强调结合特定情境对特定社会文化事项的理解。
尽管有关方法论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但这并没有阻碍经验研究的持续。就调查研究而言,其方法论的基础是逻辑实证主义,即假定了人类行为及社会现象中具有某些普适性的规律存在(至少这种普适性在一定范围内是存在的),并且这些规律是可以被认识和把握的,社会研究的基本逻辑是演绎、假设加上经验证实。由此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调查研究:研究者依据自己所掌握的已有的(自己的或他人的)知识、经验和体验,通过逻辑推演对其所要研究的社会事实的规律性认识提出假设或假定(这一过程可以称之为“演绎和逻辑”过程),围绕这些假设或假定进行调查研究资料收集工具——问卷的设计,然后借助问卷所收集的经验资料验证逻辑推演所提出的假设或假定(这一过程可以称之为“经验证实”),以此达到对社会事实的认识和把握。
根据上述对调查研究隐含的基本假定的理解,在调查研究的研究设计过程中,研究者应该在其观念中事先形成一个关于被研究者经验世界的图像,然后依据问卷调查所获取的、来自被研究者经验世界的资料来证实、证伪或修正在其观念当中所预设的有关被研究者经验世界的某些规律性的认识。有关被研究者经验世界的图像的形成过程,实际上就是研究者对被研究者的经验世界的先验性的把握过程,并且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对被研究者经验世界中特定事项(往往是研究者所感兴趣的事项)进行类型化的预判,即围绕这一事项,对被研究者当中可能出现的所有情形进行类型化。例如,一项有关公众对地方政府雾霾治理措施的态度和看法的调查,研究者在研究设计过程中就要对公众中可能存在的各种态度和看法做出事先的预判,并围绕这些预判设计问卷中的问题,依此从被调查者中收集经验资料来验证被调查者的态度和看法符合事先预判的有关态度和看法的哪些类型。从这个例子来看,有关被研究者经验世界图像的形成过程中存在两个层面的预设:其一研究者预设了被研究者经验世界当中存在“对地方政府雾霾治理措施的态度和看法”这一事项,其二研究者预设了被研究者围绕这一事项所表现出的所有可能性。研究者的事先预设决定了调查研究资料收集过程的选择性(围绕研究者的预设来收集资料)。资料收集的选择性一方面是为了经验证实的针对性,另一方面也是为作为调查资料收集方法的问询设置界限,进而实现问询的标准化,否则经验资料就难以类型化和数量化,调查研究因此也就难以效仿自然科学。资料收集的选择性(选择性的具体表现为问询过程中具体该问什么问题)意味着逻辑推演,以及在其基础上形成预设的过程在调查研究中非常重要。逻辑实证研究中研究假设的重要性被普遍强调[8][9],但本文所谓的研究预设不完全等同于研究假设提出,研究假设是一种更加具体、明确的陈述[10]30-35[11],是在本文所谓的基本预设的基础上提出并进一步明确化的。那么研究者是如何形成本文所谓的预设呢?我们知道,在实地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往往以不带任何预设的方式参与到被研究者的生活世界当中,通过直接的、实地的体验和感受形成有关被研究者的经验世界的认识。调查研究的逻辑实证特征则要求研究者必须事先对被研究者做出预设,预设的基础如前文所述,是研究者依据自己所把握的已有的(自己的或他人的)知识、经验和体验。当研究者事先做出的预设偏离被研究者的经验世界时,甚至这种预设仅仅是研究者主观建构的产物(在被研究者的经验世界中根本不存在)时,依据这种事先的预设而设计的问卷,籍此收集来的资料所展现的其实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共同建构的一个世界(假如被调查者的经验世界中根本就没有“对地方政府雾霾治理措施的看法和态度”这一事项,那么调查实施过程实际上意味着研究的主客双方对这个原本不存在于被研究者经验世界中的事项进行建构),而研究者如果用这一由其与被研究者在问卷调查这一互动过程中共同建构的世界,去对比此前研究者因预设而形成的有关被研究者经验世界的图像,虽然完成了所谓的经验证实过程,但其所要证实的是研究者先验的图像与研究的主客双方共同建构的世界的一致性,而不是与被研究者事实的经验世界的一致性。文化差异这一可能存在的客观障碍正是导致研究者的事先预设失效的原因之一。
三、文化差异及可能的研究障碍
本文重点不是讨论各种方法争议,也不是要用一种方法论即关于人类行为和社会文化现象的基本假定去否定另一种方法论的相关假定。也就是说,在调查研究的语境中强调对文化差异的重视,而不是质疑和否定调查研究的合法性及其方法论基础。但在认同调查研究基本逻辑的同时,我们要强调的是,即便承认人类行为和社会文化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也要注意这种普适性的限度,即便一种所谓的普适性的规律确实存在时,也要注意在表述和展现(表现为前述预设的具体化过程,即研究假设的形成,以及围绕假设而设计的调查问卷)这些待验证的规律性“事实”的过程中,由于研究的主客体之间文化差异的存在而导致研究主客方在理解上的不一致。也就是说,即便研究者所预设的图像世界中和被研究者的经验事实中确实存在同一个文化事项,但由于研究主客双方文化差异(包括话语体系的差异)的存在,他们各自会对同一文化事项做出不同的“解码”和“编码”,进而导致调查的互动过程的无效性,即出现前文提到的 “答非所问”的情形。
文化的多样性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客观事实,文化差异是普遍存在的[12]17-19。我们在看到文化普遍性的同时,也不可忽视文化的相对性,这两者是“文化的重要特性,这两个方面都不能舍弃,而且它们之间是相互依存的”[13]6-8。所谓的“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讲的就是文化差异的普遍性。但是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有时会被调查研究的研究者们所忽略,他们会不自觉地假定被研究者(被调查者)与自己共享同一文化,或者彼此的文化有着某种或某些共同性。建立在这种不自觉的假定的基础上的研究设计和调查研究必然会遭遇文化差异这一客观障碍,而研究者往往并没有意识到这种不自觉的假定,由此导致的研究上的逻辑错误又通常被遮蔽得连研究者自身也没有意识到。
文化差异有可能给调查研究带来的最为严重的影响是研究者根据已有知识、经验和感受事先所预设的社会或文化事项在被研究者的经验世界当中根本不存在。为了说明这一情形,我们再虚构一个例子。假设有一项关于国家认同的调查研究,其中问到:“你觉得自己是哪个国家的人?”这一提问其实隐含着一些基本的假定:在被调查者的话语体系里面存在“国家”这一概念,并且对这一概念有着相同的理解。这只是一个虚构的例子,但这个例子足以说明研究者有可能在无意间犯下的错误,因为有些概念(指涉的社会或文化事项)只是在特定的文化共同体当中才有,而在另一些文化共同体中也许根本就不存在,或者人们对类似的社会与文化现象有着不同的理解。以这个虚构的例子来说,就现代话语体系中的“民族国家认同”而言,在有些文化共同体中,或许人们更看重的是自己所隶属的文化共同体(这个文化共同体有可能被多个所谓的民族国家在地域界限上做出分隔),换言之,就身份归属而言,被调查者实际想表达的是“我是犹太人”或“我是阿拉伯人”,而调查研究的强制性则帮助他们建构出我是XX国人这一自我观念。
文化差异给调查研究带来的另一种影响是由人们对同一社会文化事项的不同解读导致的。即便研究者事先所预设的社会或文化事项在被研究者的经验世界中确实存在,但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研究者对这一特定事项的“编码”和“解码”及其所依赖符号和意义系统与被研究者对这一特定事项的“编码”和“解码”及其所依赖的符号和意义系统之间不同,会导致研究者与被研究之间的沟通失效。例如,人类的情绪和情感表现及其产生,在不同的族群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但不同文化的成员对情感和情绪的表达,以及他们对特定情感和情绪表达的理解则存在文化差异[14]146-151。再举一个调查研究中的例子,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简称ISSP )2009年的调查(ISSP 2009)采用一种被公认的非常好的方法来测量不同国家的人们对其所在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的看法[15]94-119,并且这个项目首次涵盖了中国的调查。在ISSP的调查过程中,被访者被问到一些职业位置的实际和应得收入,例如,“在您看来医生/企业高层管理人员/销售人员/政府的高级雇员/体力工人的实际收入是多少?”“在您看来医生/企业高层管理人员/销售人员/政府的高级雇员/体力工人应该得到的收入是多少?”其中被问到的职业位置是按照不同职位在等级结构中的位置进行选择的,一些职业位置作为高职位(high status occupation)的代表,另一些职业位置作为低职位(low status occupation)的代表,通过比较人们对高职位者和低职位者收入不同的看法和态度,就可以了解人们对所属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的看法和态度。在研究者的预设当中,“医生”这一职位被当做其中高职位的代表之一,但笔者通过分析ISSP 2009数据,计算医生在职位等级中的相对收入,发现在中国和中东欧的一些市场转型国家当中,医生这一职位并不像研究者事先所预设的那样属于高职位(high status occupation)。也就是说,人们对“医生”的理解与研究者预设的人们对“医生”理解是不一样的,尽管“医生”这一职位普遍存在于不同的被调查者所属的国家当中,以及研究者的经验世界当中。关于“解码”和“编码”文化差异,我们也可以列举一个类似的例子。在众多有关不平等的感知和态度的调查研究中,另外一种比较常见的做法是直接询问被调查者对其所属国家/组织/群体的经济不平等的看法,譬如询问被调查者“你觉得你们国家当前的经济不平等程度如何?”(选项可以是“从非常严重”到“非常不严重”,以做到一个等级化的测量)。这里用到了“不平等”这个符码,但研究可能忽视的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这一符码可能有着不同的理解。其实在英文当中,与“不平等”相对应的符码是“inequality”,它是一个不涉及价值判断的概念,所表达的是(垂直意义上的)差异;而在汉语表达中,人们容易将“不平等”与“不公平”相混淆,后者对应英文为“inequity”,是对(垂直意义上的)差异的合理性与否定的价值判断。如果研究者的意图是想测量人们对“inequality”的看法,那么由于文化差异导致的人们对“不平等”这一符码的不同理解(有的理解为一种差异,有的理解为差异的合理性与否),则使得调查的标准化诉求难以实现,而测量的效度也因此大打折扣。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对文化差异的忽略,以及不自觉地假定被研究者(被调查者)与自己共享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如符号与意义系统,生活体验等),更容易发生在对本民族的研究当中,或者说更容易发生在那些被研究者与研究者隶属于同一个大的文化共同体的情形中。这是因为即便是在一个文化共同体内部,也存在不同的亚文化共同体,同一个文化共同体内部不同群体的话语体系和生活体验也是不同的。假设有一项关于农民工的生活状况的描述性调查,如果研究者(特别是研究的设计者)对农民的生活并没有直接的体验与感受,那么他在研究设计时事先形成的有关农民工生活的图像的逻辑和推演过程所凭借的信息的可能来源就只能是:其一,研究者依据自己作为中国人的个体生活体验,以及在与其他中国人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对一般化(或曰概化)的中国人生活的看法或观念,进而对农民工生活的可能状况进行预设;其二借助各种媒介(包括学术和非学术性的信息载体)来获得对农民工生活状况的预设。其实这两种信息来源都可能隐含着一定的风险(即研究者事先预设的所谓的农民工的生活可能并不是农民工的生活,或者研究者事先预设有关农民工生活的事项并不存在于实际的农民的生活当中)。就第一个预设来源而言,尽管农民工、研究者自身及与其交往的对象可能隶属于一个大的文化共同体,但存在的亚文化差别有可能使得研究者对农民工生活状况的预设变得并不可靠。我们还可以用一个问卷设计层面的例子来说明亚文化差异这一情形。假设有一项关于公众心态的调查,其中有这样一道题目:“有一项研究结果表明,80%中国人感觉生活很幸福,你觉得自己被幸福了吗?” “被XX”是一种网络流行语,在网民或青年人的亚文化中比较常见。如果这一虚构的调查所面对的是普通大众,调查问题的设计其实忽视了亚文化及其差异的存在,因为有些被调查者尽管能够看得懂或听得懂“被幸福”这串字符,但并不一定和熟悉这一词汇的网民或青年有着一致的理解。就前述第二个预设来源而言,撇开极端的反实证主义者对媒介再现事实的质疑之外,媒介所再现的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差异是不可忽视的。通过传播学者对媒介生产及其传播过程分析——如霍尔对电视传播及其编码和解码过程的分析[16],在媒介生产过程中,编码者所属文化及其符号和意义系统与媒介试图再现的经验世界之间的差别,以及受众在解码过程中的文化特殊性等都会影响媒介再现事实效度(研究者借助各种媒介预设农民工生活图像的过程其实就是解码和编码的过程)。笔者并不是要彻底否认依靠第二种信息来源进行研究预设的可行性,只是强调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所导致的其中可能存在的风险。
事先预设贯穿于调查研究的研究设计的全过程,因此,文化差异这一客观障碍不仅可能体现于研究的议题设置阶段(其最大的风险是所设置的议题是否属于被研究者的经验世界)、也有可能体现研究假设的提出阶段,以及问卷设计时的问题提出过程中。
四、实地探索与调查研究的研究设计
根据前文的讨论,调查研究的第一个环节是研究者根据自己或他人已有的知识、经验、体验或感受对被调查者经验世界进行预设,以形成一个待验证的图像,这个过程可以理解为一次解码和编码的过程(通过对已有知识、经验、体验或感受的解码*这一过程中的解码和编码其实涉及多个层面,其中还包括符码的转译过程,譬如研究者将一般性的经验资料进行学术话语的转译,以达到抽象和理论概括,当然这个过程中也包括对已有理论的演绎以解读一般性的经验资料。,以明确研究议题,提出研究假设和设计问卷,而议题和假设的提出以及问卷设计即为一种编码的过程);第二个环节是研究的主客双方在调查过程中所经历的互动,这一过程中涉及被调查的解码(即对在被问询内容的解码,结构式访问过程中还可能包含着访问员的解码和编码)和编码(这一编码过程被研究者标准化);第三个环节是研究者对问卷调查结果的分析,以验证或修正事先形成的有关被研究者经验世界的图像及其中的规律性存在(这一过程再次表现为解码和编码,解码是对问卷所收集的标准化了的信息的分析,编码则表现为依据潜在受众——如学术共同体——所能接受的符号和意义系统形成研究结果)。调查研究中的文化障碍可以体现于上述三个环节的每一阶段的解码和编码过程当中。就第一个环节而言,如果研究者所把握的知识、经验、体验或感受不是(直接或间接)来自被研究者的经验世界,或者研究者对已有的知识、经验、体验或感受的解读有误(这种解读或曰解码过程受到研究者自身的文化及其与他者的文化差异的影响),依此而形成的有关被研究者的图像,实际上是被建构出来的,是一种偏离被研究者经验世界的想象。就第二个环节而言,作为研究主客双方互动中介的问卷(其中隐含着研究者研究议题和研究假设)的形成过程意味着一种编码过程,这一过程同样受到文化差异或文化特殊性的影响,对作为符码形式的问卷及其中的问题所包含的意义的理解,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调查研究的互动双方就有可能表现出不一致(研究者在问卷设计过程中如果忽视文化差异,有意或无意地假定自己用以编码的符号和意义系统是被调查者能够理解的,那么这就是另一种想象)。第三个环节通常是研究者在自己所熟悉的(或与其研究结果的潜在受众共享的)符号和意义系统内完成,但其中涉及对前两个环节的符码及其意涵的转译过程,这一转译过程也同样有可能受到文化差异的影响而发生偏差。
为了经验研究的可持续性,在调查研究的展开过程中人们实际上搁置了方法论的争议(特别是搁置了极端的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之间的争论),而默认、接受实证主义对社会世界的某些基本假定。而有关各种方法论的主义之争其实是在理想类型(ideal type)意义上的争论,在研究实践当中人们实际所做的基本假定往往表现为偏向对立的理想类型的某一侧或另一侧,也就是说,人们有可能同时选择和认同两种或多种对立的理想类型中的某些成分。实际上,方法论上争议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融合的情形[17]147-150,人们在坚守实证主义基本假定的同时,也承认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之间存在本质区别,承认理论的相对性、历史性和发展性,以及研究视角的多元化。方法论上的融合及多元视角的存在意味着调查研究在保留自己基本假定的基础上,可以吸收和借鉴其他研究方式中的某些做法,以克服自身的不足。正是因为如此,调查研究者在默认有关人类行为和社会现象的普适性规律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并可以借助标准化的方式加以认识时,也不可忽视事实当中可能存在的种种文化差异(这种文化差异的存在恰恰是人文主义方法论的一个基本假定),以及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所导致的人们在表述(涉及编码过程)和解读(涉及解码过程)所谓的一般性存在时的差异。
文化差异这一可能存在的客观障碍对调查研究的可能影响的直接表现形式可以近似地表述为:研究者依“想象”而预设了有关被研究者经验世界的图像,以“想象”建构了一套用以采集经验信息的符码系统(表现为研究假设和调查问卷及其中问题)。建立在这些想象基础上的逻辑推演和经验证实过程尽管实现了研究逻辑上的完整性,却有可能远远偏离被研究者的经验事实。简言之,文化差异这一可能存在的客观障碍,容易导致研究者以想象代替被研究者的经验事实。克服调查研究中由文化差异这一障碍所带来的影响,研究者除了对那种凭借已有的知识、经验和体验对被研究的经验世界做出预设的做法保持警惕之外,还可以借鉴其他研究方式的做法,来减小或消除文化差异或文化特殊性可能带来的影响,其中最值得效仿的是实地研究的一些做法。实地研究是一种解释主义方法,解释主义者坚持相对主义的本体论,认为“事实”是多元的,因时间、地域、个人经验等因素的不同而不同,因此要求研究者深入实地,在自然环境中进行细致、长期的体察,采取“文化主位”的方法理解研究对象的心理、行为及价值观[18]92-95。在笔者看来,在调查研究的事先预设得以形成之前,研究者深入到研究对象的生活当中去观察、感受、体验和领会,用研究对象自身的眼光和思维去考察被研究者的经验世界,或许有助于研究者对被研究者做出事先的理解和把握,拉近其研究预设和被研究者经验事实之间的距离。而这种深入到被研究者的生活世界当中,试图达到对被研究者的理解恰恰是实地研究的基本做法。调查研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是建立在研究者对被研究者经验世界或观念世界中事实存在的议题的把握,以及对围绕这一议题被研究者所表现出的所有可能情形的把握。因此,为确保调查研究的有效性,同时又认定文化共享的有限性和文化差异的普遍性的话,实地研究其实是调查研究的研究预设得以形成的逻辑起点。
[1]方长春:《从方法论到中国实践:调查研究的局限性分析》,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2]风笑天:《社会调查方法还是社会研究方法——社会学方法问题探讨之一》,载《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2期。
[3]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4]涂尔干:《社会学方法的准则》,渠东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5]埃米尔·迪尔凯姆:《自杀论》,冯韵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6]沃野:《论实证主义及其方法论的变化和发展》,载《学术研究》1998年第7 期。
[7]孟建伟:《对科学的人文价值的忽视——逻辑实证主义科学观及其缺陷》,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4 期。
[8]Chafetz, J. S. (1978).Aprimerontheconstructionandtestingoftheoriesinsociology, FE Peacock Publishers Itasca, IL.
[9]Kerlinger, F. N. (1979).Behavioralresearch:Aconceptualapproach,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New York.
[10]孙健敏:《研究假设的有效性及其评价》,载《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3期。
[11]Salkind, N. J., & Rainwater, T. (2000).Exploringresearch, Prentice Hall Upper Saddle River, NJ.
[12]乐黛云:《文化差异与文化误读》,载《中国文化研究》1994年第2期。
[13]张传有:《试析文化的相对主义》,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14]王娟、朱云霞:《文化对情感表达与情感理解的影响:模型及研究证据》,载《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 期。
[15]Finseraas, H. (2009). “Income Inequality and Demand for Redistribution: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European Public Opinion”, 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 32(1).
[16]Hall, S. (1973).EncodingandDecodingintheTelevisionDiscourse:CentreforCulturalStudie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17]吉尔德·德兰逖:《社会科学——超越建构论和实在论》,张茂元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8]曾永泉、黎民:《刍论实地研究中的理论建构》,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