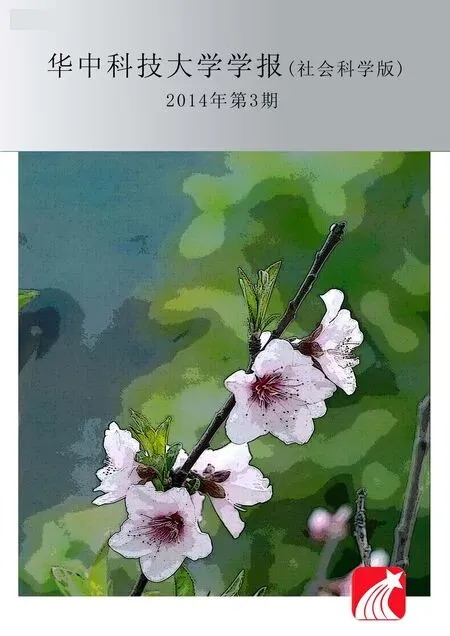从“托孤”到“监护”
——我国近代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转型
陈云朝,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 430074
托孤是中国古代相沿已久的民间习惯,它调整的是未成年子孙的人身照顾和家产管理问题。由于传统律典中并无直接规范托孤关系的律文,加之传世托孤遗嘱数量有限,学界对其关注甚少。近年来,学者们利用公开出版或私家收藏的契约文书档案对清代的托孤习惯进行了讨论。台湾学者陈瑛珣从遗存下来的台湾托孤文书入手,重点探讨了清代闽台女性在财产权上的独立性和自主性[1]。俞江先生以自藏的三件徽州托孤遗嘱为出发点,认为托孤遗嘱是中国古代遗嘱的典型代表,其主要内容包括指定监护人和委托管理家产。托孤制是家产制的一个子系统,对其理解不能脱离家产制这个背景[2]。上述成果为了解托孤习惯提供了很好的帮助,但仍有继续拓展的空间,如对传统托孤习惯的具体形态、清末修律以来如何以移植之监护对固有托孤习惯进行改造、托孤与监护的异同、近代监护制如何从法律文本走向制度实践等问题的研究,尚付阙如。本文力图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上述系列问题进行探索。
一、中国古代的托孤习惯
“托孤”是我国传统固有词汇。《说文解字》“托,寄也”,“孤,无父也”。先秦典籍中,有关托孤最早的文献记载为《论语·泰伯》:“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欤?君子人也!”曾子所说的“托孤”、“寄命”针对的是国家幼君,而非普通民众之间的托付。之所以可以托孤,是因为这样的君子具备高尚的品格。《管子·入国》的所谓“恤孤”:“凡国都皆有掌孤,士人死,子孤幼,无父母所养,不能自生者,属之其乡党知识故人”。此即政府应设“掌孤”之官,当孤幼无父母所养又不能自养时,委诸乡邻、熟人、亲故来抚养。实践中,三国时期已有“先主病笃,托孤于丞相亮,尚书李严为副”[3]891的历史记载。
在制度上,遍览古代法律典籍,唐以前的国家法体系中未曾见有托孤的法律规范。宋代在孤幼无人可托的情况下,制定出一项保护遗孤财产的法律制度——检校。“元丰令,孤幼财产,官为检校,使亲戚抚养之,季给所需。赀蓄不满五百万者,召人户供质当举钱,岁取息二分为抚养费。”[4]5904宋代将孤幼的人身照顾和财产管理一分为二:人身事务委诸亲戚抚养;财产事务则由官府收管,定时定量从管理的财产中向遗孤发放生活所需[5][6]。元承宋制“……若抛下男女十岁以下者,付亲属可托者抚养,度其所须季给。虽有母招后夫或携而适入者,其财产亦官知道数。如已娶或年十五以上,尽数给还。”[7]28-29明清以后,国家律典不再规定此制,官府退出孤幼财产的管理。当社会上出现孤幼无人照料、家产无人管理的危险时,通常订立托孤遗嘱,将孤幼和家产委诸亲族或友朋管理。久之,托孤逐渐成为一种民间习惯。“在托孤之一方类以选择贤良为主,在受托之一方,非素所亲厚不肯任责,此一般习惯所同也。但事态不齐,如寒素之家,人方以受托为累,纯任托孤者之自择。若富厚之家,觊觎者众,非亲不能干内事,非尊无以压众人。故其选择贤良有由亲及疏,由尊及卑之习例。惟每岁出入款目,须凭亲族核算,对于基本财产有不得擅行典卖之限制,是为普通习例。”[8]
上述材料,在观念和制度上粗略地呈现出托孤的历史概貌,然而更多制度细节的澄清,尚需大量托孤遗嘱等民间契约文献的支撑。清代民间契约文书档案的公开出版物中,托孤遗嘱极其少见,笔者仅收集有11件①分别参见《清康熙四十年十月陈继善立托孤约》(刘伯山主编:《徽州文书》(第一辑)第九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1页);《光绪十六年一月陈林氏托孤字》、《光绪二十七年三月梁文轩托孤书字》、《光绪十七年八月刘清河、妻张氏等托孤寄业字》、《同治十年八月陈氏托孤字》、《道光五年四月沈齐托交祀契字》、《光绪十五年八月王林氏遗嘱托孤字》、《光绪二年五月许祥洙托孤字》(孔昭明主编:《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九辑·台湾私法人事编》,大通书局1987年版,第743、743-744、744-746、746-747、747-748、748-749、749-751页);《乾隆三十八年洪廷 托孤遗嘱》、《乾隆五十六年王云樟托孤遗嘱》、《嘉庆十九年曹以玉托孤遗嘱底稿》(俞江教授藏)。。细心研读此11件文书,可以将托孤习惯分为如下方面。
(一)托孤原因
与其它契约文书相比,托孤遗嘱最大的特点莫过于在文中不吝篇幅地陈述原因。托孤通常在尊长顾虑自己亡后未成年子嗣和家产无人照理时为之。家中有未成年子嗣是托孤的原因之一。父母或其他尊长一旦去世,未成年子嗣面临着人身和财产无人照理的危险。为延续香火,保证烟祀,托孤成为必然之举。在托孤遗嘱中,往往重点阐述未成年子嗣可能面临的种种危险。康熙四十年陈继善因身患疾病,“惟恐利徒欺孤瞒幼,罩载钻谋。深虑二子幼小,难以持守”[9]311,无奈之下将幼子托付族人照理。实际上,如果不能妥善安排托孤事宜,往往意味着祖先祭祀无以维系,家产也将旁落。
家中有未成年子嗣并不必然托孤,尚需考虑家产是否有人管理。倘家内妻妇守志并足以执掌家业照顾幼子之时,家产因有人管理而不必托孤。同治十年陈氏“因先夫早逝,遗子聘尚在怀抱,薄有产业,氏躬亲执掌绰有余力”[10]746,未行托孤之举。此外,家中虽有成年男子,但成年男子不能管理家庭事务、不务正业或浪费家产时,因不具有行为能力,故需托孤保全家产。如刘清河夫妇年老体衰,虽有一子,但“愚蠢未谙,即一孙儿可望,尚属孩婴”[10]745。故此家产无人管理成为托孤第二个主要原因。
(二)托孤主体
托孤的主体包括托孤人、受托人、孤幼和其他参加人。
托孤人,即文书题首的“立遗嘱托孤人”、“立托孤寄业人”,是将家中孤幼和家产托付于他人照管的人。在遗嘱尾部,往往由托孤人率先署名。据台湾旧惯调查报告书记载,“托孤通常由幼者之父立之,若无时得由祖父立之,又无祖父时得由母或祖母立之。伯叔父母及兄弟等尊长亦得立之,但是尚无实例。”[11]642从 11 件托孤遗嘱反映出的身份来看,托孤人为父亲的4件,祖父2件,母亲3件,祖父、祖母共同立约1件。另1件较为特殊,托孤人将儿子与侄子同时托付族人照管。进一步证实了上述记载。
受托人,即接受委托事务,照顾孤幼身体、总理家产之人。从托孤遗嘱来看,受托人的选择不受性别与同宗限制,舅舅、女婿、儿媳、外孙、朋友皆可为受托人。为防止财产不被亲族侵夺,当家中女性尊长作为托孤人且受托人并非同宗族人时,往往在遗嘱中特殊说明。如陈林氏将子孙及家产托付与外孙郑拱辰代为经理,为预防纠纷,在遗嘱中强调“日后陈氏子孙不得异言藉端滋事”[10]743。此外,受托人数无固定限制,根据需要可托付一人亦可托付多人。受托人的选定并非托孤人的一厢情愿,而是双方反复协商的过程。接受托付后,受托人更多承担的是一项职责,在抚育孤幼和管理家产的过程中需付出辛勤劳动。受托人若非出于亲故,往往不愿胜任其职。有时所选受托人出于种种考虑,并不愿接受所托事项。如曹以玉本欲将其继子兆亨“意托二兄嫂代为关照,讵料不能领受”①《嘉庆十九年曹以玉托孤遗嘱底稿》,归户档24号·婺源县八都一图曹氏,俞江教授藏。,不得已托付侄儿曹元里照管。实际上,受托人必须是孤幼父母最为信赖之人,若受托人选择不当,孤幼则不能蒙受其利,反受其害。
孤幼不限未成年男子,女子亦可。其他参与人多属于地缘或血缘关系中德高望重之辈,主要包括参与托孤的族亲、戚亲、朋友等见证人和代书人。能堪受托者,总是平素诚实可靠之人。但人心不齐,尤恐其变,参与人既可监督受托人之行为,一旦日后出现纠纷又可作为见证人。
(三)托孤事务
受托人一旦选定,则进入约定托孤事项阶段。受托人具体的权限和责任无一定之惯例,主要依当事人协商签订的契约而定,大致包括照顾孤幼人身、管理孤幼财产、辅助其行为能力等。孤幼缺乏自我照顾的能力,对其人身照顾是所托事项的重要内容。托孤遗嘱中对人身照顾的约定多是概括性的,一般包括使其抚育成长、读书受教等人身事宜,如“以父子相待,任从教戒”等。但受托人毕竟不是孤幼的父母,“没有传统社会中的父母亲得以不孝忤逆等罪名送官究办的权力”[1],其权限受到一定限制。
孤幼在成长中最大的危机往往来自族内、族外人等对家产的觊觎,这一点无论从清代的公案小说还是州县有关孤幼争财的案件中都可以得到印证。为防止受托人不履行职责、吞噬财产,托孤人会在遗嘱末尾将家产一一列明,然后将各种财产契据交予受托人②《乾隆三十八年洪廷勷托孤遗嘱》:“将吾微产开列于后,所有契约俱托长婿收执,代为调剂。”归户档27号·婺源县十七都一图洪氏,俞江教授藏。。受托人据此管理财产,并将家产的日常收支和经营状况详细记载于账簿③《光绪二年许祥洙托孤字》:“凡家中事务同与儿妇共相料理,每年订四季亦同与儿妇取契检阅,并查其租谷家费,开余数项明白再交与各执收存。”载《台湾私法人事编》,大通书局1987年版,第749-750页。。受托人仅有代管孤幼家产之权,其处分财产的权限受到较多限制。此外,受托人根据约定可享有一定的报酬④《遗嘱托孤书式(二)》:“当众言明,每年酬谢金几十千文。”载《广西官报》1911年第100期。,还可依据具体托付事项,另行约定报酬⑤《嘉庆十九年曹以玉托孤遗嘱底稿》:“再余本门清明年头神会等件,亦托其经理,余愿贴谷廿八秤,今秋付元侄收。”归户档24号·婺源县八都一图曹氏,俞江教授藏。。有些托孤遗嘱中,还明确约定了家产的归还条件、期限以及欺孤霸产的惩处方式等事宜。
(四)托孤的成立
为使商议妥当的托孤事项成立,一般会订立托孤遗嘱,以防日后侵渔之弊。从传世的托孤遗嘱来看,其形制主要有两种:单契与合同。“托孤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概率较低,而且托孤的对象既可是一人,也可是多人,若托付与一人,自无采用合同的必要。但托付与多人时,则不排除采用合同形式。”[12]202单契,即只制定一份托孤遗嘱,由受托人收执;合同则意味着一式多份,分由不同人执管。从内容来看,单契与合同并无二致,主要交代托孤人、托孤原因、受托人、所托事项、财产清单、当事人以及参与人的署名,以此作为将来照顾孤幼、管理财产的凭证。托孤文书还起到预防纠纷以及外人侵吞家产的作用⑥《乾隆五十六年王云樟托孤遗嘱》:“藉诸位执此,以免内外人等侵削。倘有侵削之徒,望秉公呈究。”归户档13号·婺源县十四都四图洪氏,俞江教授藏。。当出现受托人不移交家产或外人侵占家产的状况时,托孤遗嘱是保证孤幼权益的有力证据,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托孤成立之时往往伴随特定的仪式。订立托孤遗嘱之后,托孤人会选择良辰吉日,祷告神明,设立酒宴邀请亲朋以及地方权威人物作为中见人,一则见证所托事项的真实性,二则监督受托人积极履行职责。庄重的仪式在于将托孤行为公示于众,并为将来纠纷的解决提供凭据。
(五)托孤的终止
托孤终止的时间并无具体规则可言,往往依特定事实而定。孤幼成年、结婚,或具备自行管理财产的能力,或遗嘱中约定的其他条件出现时,则终止托孤。如“俟至次孙国基长成二十岁以外,即交与自主”[9]744,是以孤子年满二十岁作为终止条件;“娶亲之日,元侄检点,原物交还,不能阻挡”⑦《嘉庆十九年曹以玉托孤遗嘱底稿》,归户档24号·婺源县八都一图曹氏,俞江教授藏。,是以结婚作为终止条件。托孤终止时,受托人应将代为管理的家产在亲族监督与核实下如实交付孤子。
综上所述,托孤作为民间相沿已久的习惯,具有较为固定的内容和操作程序,体现了儒家的社会理想。自明清以来,国家法律不再介入孤幼的财产管理,当围绕托孤出现财产争讼时,私人议定的托孤遗嘱往往得到官府的承认,并被视为断案的有力证据①详细案件参见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室编:《明清法制史料辑刊》(第一编)第13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291-298页。。当然,托孤习惯的形成自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作为支撑。在以宗法伦常和家族制度为社会基础的古代,家庭的延续成为一个家族最大的利益,在各类社会关系和制度安排中,始终表现出对家庭利益的维护。当父亲在临终前妥善安排托孤事宜时,并不是因为他对儿子应尽此种义务,而是因为父亲对儿子共同的祖先承担的责任,或者说是父亲对“家”承担的责任。因此,托孤不仅仅是对孤儿身体的照顾与家产的管理,其背后的价值在于孤儿所代表的“家族血脉”的延续。
二、托孤习惯与近代未成年人监护立法
(一)清末修律中的未成年人监护
清末民初是中国法律史上重要的转型期。面对大规模的法律移植,以德日民法为蓝本制定的《大清民律草案》将托孤习惯排斥在国家法之外,而将与托孤相似的监护制度引入国内。
我国古代律典中并无“监护”一词的制度称谓。“监”与“护”在古语表达中甚少连用。《说文解字》“监,临下也”,“护,救视也”。“监护”二字连用,为“督察、监督保护”之意[13]678。“监护”作为法学概念和制度进入人们的视野,是在清末移植西方法之际。因受日本法学词汇的影响,20世纪初,国内法学翻译中多采用“后见”一词。1903年汪荣宝、叶澜编纂的辞书《新尔雅》,在“民法”类词条中使用的是“后见人”②“父母早亡,或值他故。不能行其亲权,亦不能任孤儿之自生自灭,必有亲族中人为之经理。是经理人谓之后见人。”参见汪荣宝、叶澜编:《新尔雅》,上海文明书局1906年版,第32页。。1907年《新译日本法规大全》也译为“后见”③“后见于下列之时开始:一、对于未成年者,无行亲权者,或行亲权者无管理权时。二、有禁治产之宣告。”参见何佳馨点校:《新译日本法规大全》(第一卷),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83页。。同年,一篇匿名《论中国急宜编制民法》的文章使用的亦是“后见”④“凡未成年者为法律行为,须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所谓法定代理人者,行亲权之父或母及后见人是也。”参见《东方杂志》1907年第4卷第6期。。1911年《法政浅说报》设“法政名辞解释”一栏,专门解释法政术语,其中就有“后见人”与“被后见人”⑤参见《法政浅说报》1911年第23期。。由此可知,在《大清民律草案》制定之前,“后见”一词在法学翻译和研究中广为流传。直至1911年,“监护”始出现在清民草案中,并随着《民国民律草案》和《中华民国民法》的沿用,成为近代民法中正式的法律制度。
《大清民律草案》的立法者在起草“监护”一章时,摒弃日本立法例,转采德国模式。其立法理由谓:“日本旧惯上监护之制,甚不完备。其民法中之监护章乃参酌欧洲诸国之监护法而成,分为四节……今拟采德国民法监护章之编次,分为三节:曰未成年人之监护,曰成年人之监护,曰保佐。”[14]这既是对传统托孤习惯的突破,亦是近代监护制度的起点。近代监护有着严密的逻辑体系和成熟的制度体系。在与托孤习惯相似的未成年人监护中,《大清民律草案》第1410条确立了监护开始的原因:“未成年人,无行亲权之人或行亲权人不得行其亲权时,须置监护人。”该条采狭义监护制,即监护与亲权分立说。该说认为监护是亲权的延续和补充,将父母排除在监护之外,通常在未成年人无父母或父母不能行使亲权时,才构成监护开始的原因。同时,为防止数人监护时意见不统一以及由此导致的家庭纠纷,特规定监护人以一人充之。
在监护顺位上,确立了法定监护、遗嘱监护和亲属会议选定监护三种监护类型,效力上以法定监护优于遗嘱监护。同时,法定监护人的次序限定为:祖父、祖母与家长。其中,遗嘱指定监护人时,得指定监护监督人。若未指定监护监督人时,则须由审判衙门召集亲属会议选定监督人。亲属会议选定监护人时,应选定监护监督人。
监护事务,主要包括人身与财产两项内容。在人身监护上与托孤习惯无异。在财产属性上,由于家产制淡出国家法领域,一旦父母不能行使亲权,被监护人的财产在性质上不再是孤幼所代表的家产,而是被监护人的个人财产。监护的终止不再像托孤习惯那样不确定,而以被监护人具备行为能力为条件。
总之,《大清民律草案》中的未成年人监护采德国立法例,以权利为本位,目的是对未成年人行为能力的补充。作为整个民法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监护与民事能力、代理、婚姻、家庭和亲属有着密不可分的特性。由于《大清民律草案》采监护制,托孤习惯开始淡出国家法领域。但也有学者认为,清民草案对托孤习惯仍有注意。如第1413条:“父于临终时,因子之母不能行亲权者,得以遗嘱指定监护人。”学者在解释该条时认为,“此即古人所谓托孤者”[15]192。
(二)民国大理院时期的未成年人监护
民国肇始,法制阙如。民国元年大总统令宣布:“现在民国法律未经议定颁布,所有从前施行之法律及新刑律,除与民国国体抵触各条应失效力外,余均暂行援用,以资遵守。”在民事审判方面,“惟民律草案,前清时并未宣布,无从援用。嗣后凡关民事案件,应仍照前清现行律中规定各条办理。”[16]1-2这意味着旧律有关民事的规定,继续沿用于民国时期。由于托孤习惯在旧律中未得到直接或间接的规范,民初大理院在无法可据的情况下,以判例和解释例的方式创设了一系列监护规则。这些规则主要基于近代民法监护法理,同时尽量考虑到固有托孤习惯和家族制度。通过对相关案件的审理,固有托孤习惯得到改造,一套相对系统的监护规则初步形成。
在民国二年上字第64号判决书中,曾涉及当时司法界人士对监护与托孤的比较:“惟监护制度毫无明文之可言,而征诸一般通认之习惯法则,又有与其异名同实者,托孤是也。”[17]974表面上大理院认为托孤习惯与监护制度“异名同实”,实际上大理院的这种说法更多是基于一种解释策略上的考虑。在审判中,面对“监护”这一极其陌生的法律制度,大理院的推事们需要借助固有类似习惯“托孤”对其制度内涵予以直接或间接地解释。在解释过程中达到创制新法的目的。上述判决最后形成“判例要旨”:“托孤不必限于同宗,由最后行亲权之意思而定,且其效力恒强于族人之推选行为。”[18]246细细分析这则要旨,不难发现其包含三层意思:第一,所谓“托孤不必限于同宗”,是大理院对固有托孤习惯的承认。前文对托孤习惯的陈述中已指出,受托人选不受同宗限制,外亲、乡党、朋友亦可为之。第二,“最后行亲权之意思而定”,则以民法监护之法理去改造托孤习惯。按照未成年人监护理论,父母是未成年人的亲权人,而监护是亲权的延续。只有亲权人父母可以遗嘱监护的形式为未成年人指定监护人。由前文可知,固有习惯上,托孤人不限于父母,祖父母、伯叔父母等尊亲属亦有托孤之权。看似大理院的判例将托孤主体只限定为父母,实质上是将托孤遗嘱视为遗嘱监护。第三,“其效力恒强于族人之推选行为”,意在指出托孤遗嘱与亲族会选任监护在效力上谁更优先的问题。联系本条判例要旨“理由”:“律例中所称遗命、户族公议,即遗嘱及亲族会之变称。”[19]117可知,大理院将遗命类比遗嘱,以户族公议类比亲族会。换言之,当托孤遗嘱与亲族会的选任监护出现冲突时,托孤遗嘱的效力强于选任监护。
在大理院民国五年上字第622号判例要旨中,进一步明确了监护顺位:“凡对于父母俱亡之未成年人,除已经其父母生前指定监护人,或现有同居之近亲尊长外,自应由亲族会议为之选任监护人。而在两造涉讼之中争及监护者,审判衙门为事实上之便利,并应传集该亲族询取意见为之选定监护人。”[17]989该条要旨认为,父母的遗嘱监护优于法定监护,法定监护优于选任监护。大理院改变了《大清民律草案》确立的法定监护优先于遗嘱监护的做法,使其符合中国固有习惯和家庭伦理。
看似短短的几则判例要旨,实则凝聚着大理院推事们试图将固有托孤习惯与外来监护法理相融合的心血。诚如黄源盛先生所言,“大理院推事们常以权变的方式,用尽心力,企图将传统的刑律条文,透过新的法学解释方法,使其与近代法学理论相结合;甚至时而将律文‘旧瓶新装’,以解决新时代所产生的社会纷争问题。”因此,面对外来监护规则与固有托孤习惯之间的冲突,“大理院为了解决纷争,不得不尽力找寻民事法源,乃对当代民法上的监护人制度征诸传统观念上的所谓‘托孤’”[20]。
(三)《民国民法典》与未成年人监护
针对《大清民律草案》和《民国民律草案》在未成年人监护上脱离我国习惯、过多参考西制的弊病。1928年国民政府法制局在草拟的《亲属法草案》分说明之监护制度中指出:“我国旧律,关于老幼孤寡之收养,虽有明文规定,而用意仅在慈善。社会上虽有托孤之习惯,而范围多限于亲属。且权利义务,亦不分明,易生弊端。民国以来,法院判例,曾折中中西法律,而承认监护制度,惜其散见旁出,无系统之可寻。历次亲属法草案,关于此点,采纳西制,又嫌太过。”[16]3491930 年国民政府颁布《民国民法典》,吸取前述经验,在参考西制基础上,斟酌社会现状,更加尊重我国固有习惯和家族伦理。有关监护的规定除与“总则篇”民事主体部分有关外,主要部分被置于第四编“亲属”中。具体特点如下所述。
首先,以家庭自治监护为原则。在监护人的选择上,主要有遗嘱监护、法定监护、亲属会议的指定监护以及委托监护。在选任监护人上,民法典认为监护为家庭之私事,将法院选任监护人排除在外,将监护事宜委诸个人或亲属会议的自由选择。学者认为,“至于监护人之选任不由法院为之,而交由亲属会议,乃系受日本旧法影响,及斟酌大理院判决例与历次草案之规定而来。”[21]285换言之,父母、家庭和亲属是未成年人监护的职责主体。亲属会议作为权力机构,当出现法定情况时,可以撤销监护人。国家公权力和社会组织被排除在监护人之外。
其次,在监护顺位上,《大清民律草案》与《民国民律草案》皆以法定监护人为先,遗嘱监护人次之。《民国民法典》在监护人的顺位上采德国、日本立法例,将遗嘱监护置于前。实践中,父母通过遗嘱指定监护人在血缘关系上可能远于祖父母以及伯叔等近亲属,但父母与子女之间具有最亲密的血缘关系,父母以遗嘱的方式选择自己最信任的监护人,对子女的成长最为有利。
再次,法定监护人次序更加合理。一则,监护人数并不以一人为限;二则,与《大清民律草案》中以祖父、祖母、家长的法定监护次序相比,《民国民法典》法定监护人依照(1)与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母;(2)家长;(3)未与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母;(4)伯父或叔父的顺位充任。将同居视为亲疏远近的重要条件,体现了对传统习惯与伦常的尊重。
最后,在监护开始的原因上,第1091条规定:“未成年人无父母,或父母均不能行使、负担对于其未成年子女之权利、义务时,应置监护人。但未成年人已结婚者,不在此限。”《民国民法典》将结婚的未成年人视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从而,将已婚者排除在未成年人监护之外。
总之,《民国民法典》采家庭自治监护原则,以补充未成年人行为能力,保护未成年人利益为目的。其特点在于依赖家庭和亲属关系来承担未成年人的监护事务,避免公权力介入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同时,随着《民国民法典》的颁布,有关监护的法律制度、法学研究和司法实践逐步成熟。在中国传承数千年的托孤习惯,一方面在近代社会转型中,家制日益崩溃,家产制趋向个人财产制,托孤的社会结构渐趋消失;另一方面随着西方法的移植被未成年人监护制所取代,从而淡出人们的视野。
三、托孤习惯与近代未成年人监护之比较
“进行中西法的比较研究,其价值在于找到差异而非找到共性,其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认识别人,而是更清楚地认识自己。”[22]与未成年人监护制相比,托孤习惯存在的社会基础和伦常观念均有自身的特点。在传统宗法社会中,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结构,同居共财是人们的主要生活方式。基于共同生活的需要,幼年家属的人身照顾被置于家庭乃至整个家族之中。在家产制下,孤幼并无个人财产,家族尊长承担了家产的管理职责,其“人身和财产上的一切事务皆可委诸于家族内安排解决到位,未成年人的监护工作已淹没在家长权的家制体系中”[23]261,自无设立监护制度之必要。一旦发生孤幼无人照顾、家产无人管理的情况,托孤成为延续家族血脉的主要方式。托孤作为民间知识,是整个社会历史传统的体现。
在比较法的视野中,调整家庭关系的规范并非法律的逻辑,事实上是一种生活的逻辑。托孤不同于近代未成年人监护,其发生发展自有独特的逻辑。而这种生活逻辑的背后蕴含的无非是由传统沿袭下来的宗法伦常和家族制度。近代西方监护的设立,其制度理念以亲属关系为基础,并与民事主体、婚姻家庭、代理、民事责任等制度紧密相关。本质上,监护是基于权利保护而对被监护人行为能力补充效果的一种法律制度。其建立目的在于使行为能力残缺的人成为民法上的独立个体参与民事活动,以保障交易安全。具体言之,托孤与监护的差异体现为以下三点。
1.目的指向不同。在注重家族、伦理、义务本位的传统中国,所有的制度安排无不围绕着家族利益而展开。无论是在目的上还是功能上,家都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托孤遗嘱在中国古代真正受到重视的理由,不是它能自由处分家产,而是因为它具有可以为孤幼指定监护人和委托家产管理的功能。孤幼如果随之夭折,则家庭面临断绝的危险,且难以补救,这一危险后果让人想起就揪心,所以,保护孤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2]家庭能否延续,祖先能否得到后人祭祀,在古人看来无疑是最重要的事情。在家族伦理本位观念的支配下,基于“家”的伦理关系成为各种制度规范中的主体内容。个人不是作为权利的主体而存在,作为家庭的一员,个人的法律人格被家庭所吸收。故此,托孤并不仅仅是对孤幼自身权益的保护,更多的是保护孤幼所代表的整个家庭的利益。“在古代社会,托孤遗嘱直接为家的延续提供了保障,从这一意义上,它被作为一个重要的子系统纳入到家产制中。”[2]换言之,某一社会中的制度不能做孤立地理解,家产制下每一种行为都有具体的目的,即从维持家庭的利益出发,托孤习惯也不例外,对传统托孤习惯的理解应置于家制和家产制的社会结构中。
监护作为法学概念,其确定内涵来自近代民法,其渊源可追溯至古代罗马法。然而,如果梳理西方监护制的源流演变,可以清晰地看到,古罗马的监护制起初是为了保护家长的利益,而非为保护一般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而设。“在家长权强大时代,家族中之幼弱残疾者,皆在家长支配及保护之下,无另为家族个人置监护之必要。惟家长本人为幼弱残疾不堪管理家政时,始须为其辅佐代表,开始监护。故此时监护系仅就家长而成立之制度。”[24]649诚如梅因所言:“原始法律把它所关联的实体即宗法或家族集团,视为永久的和不能消灭的。”[25]73因此,最原始的监护制度是为了辅佐家长对家族进行统领、共谋家族利益进而维护社会的稳定所设立的。受“天赋人权”思想的影响,近代监护制以个人权利为本位,其设计的法理在于“每个人都具有权利能力,因为他在本质上是一个伦理意义上的人。”[26]120在独立人格观念下,当某一个体相应的行为能力明显不足时,民法为其设置监护人以实现其民事意愿。随之,监护的性质变为保护一般无能力人的身体和财产的制度。此时,家长以遗嘱为子女指定监护人和保佐人时,已不以家族的利益为重,而以子女的利益为重。这是托孤与监护的本质区别。
2.开始原因不同。在家族为社会单位的古代,父母俱亡情况下,孤幼人身的照顾由家长或家族尊长行使。在家产制下,家产由家长管理。故此,孤幼无父母时并不必然订立托孤遗嘱,只有当家中没有成年男子且有未成年子嗣,家产面临无人管理的状态时才考虑选择受托人订立托孤遗嘱。如王云樟在去世前将侄儿和孙子以及家产立遗嘱托付于儿媳洪氏,嘱托她“孝顺老姑,抚养幼子,以全宗祧。”①《乾隆五十六年王云樟托孤遗嘱》,归户档13号·婺源县十四都四图洪氏,俞江教授藏。故此,托孤的原因主要考虑的是家中有无成年男子,而不是孤幼父母是否健在或能否行使亲权。
近世欧陆民法认为监护是亲权的延续和补充。因此,当未成年人无父母或父母不能行使亲权时,始设立监护人。监护开始的原因是法定原因,即当条件成立时必须设置监护人。
3.财产性质不同。在中国古代社会,财产的归属并非个人而是整体性的“家”,其性质为“家产制”②参见俞江:《继承领域内冲突格局的形成——近代中国的分家习惯与继承法移植》,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俞江:《论分家习惯与家的整体性——对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的批判》,载《政法论坛》2006年第1期。。家产既是传统中国基本的财产制度,又是支配人们日常思维的财产观念。当财产全部归属于“家”的名下时,作为家庭成员的个人,不存在西方民法所有权意义上的财产权。当孤幼作为家产的惟一承继人时,外人虽可暂时受托管理家产,在有些情况下甚至可以因管理家产而获得一定的报酬,但却绝不允许外人侵吞家产。因此,委托管理的财产不能视为孤幼的私人财产,而是孤幼所代表的家庭的财产。根据托孤遗嘱的约定,将来受托人返还的是家产管理权。
中国近代民法则采个人、独立的财产所有制。《大清民律草案》与《民国民法典》在总则部分都规定“自然人”和“法人”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拟制的“法人”,其基础无疑是独立的个人。就未成年人的财产监护而言,其性质为被监护人的个人财产,围绕着财产的登记、代理、管理、使用和处分,都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被监护人的私人财产权益。
四、结论
古今中外,都存在未成年人无人照顾及财产无人管理的社会事实。对托孤与监护的认识,应分别把问题置于各自特定的历史语境和社会结构中进行综合审视,重点探讨它们在各自社会结构中发挥的功能而非简单地进行中西比较。家产制是以维持家的存在与延续为目的的制度,对托孤的理解必须置于家产制的系统之中。
由托孤到监护的转型,是近代法律史上的一个微观问题。托孤以家族为本位,不存在清晰的权利界定和逻辑体系,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民间习惯。监护以个人权利为本位,有着确切的概念内涵和制度体系,权利与义务之间有着明确的界限。托孤与监护的比较,不是为了凸显价值评判中的孰优孰劣,而在于还原两种不同社会结构中的法律事实。某种程度上,对法律事实的厘清远比价值评判更有价值。近代立法者已经注意到托孤与监护之间质的不同,在移植西方民法的过程中,大理院的推事们试图以西方监护法理,将固有托孤习惯嫁接到民法体系之中。最终定型的《民国民法典》并没有追寻西方最新立法潮流,盲目地从家庭自治监护转向国家监护,而是审时度势,在慎重考察固有家庭伦理和习惯基础上,权衡折中,从而制定了符合中国社会伦理的监护制度。
自从新的法律、新的社会结构、新的思想观念在百年前开始更为有力地破坏传统的家制和家产制之时,托孤习惯早已离我们远去。对托孤习惯的澄清,并非意味着在新一轮的民法典修订之时将其纳入国家法的规范,而在于挖掘习惯是否还有其存在的社会基础。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存在着父母后死的一方用遗嘱或者公证书等为未成年子女指定监护的情形,但是民法尚未规定遗嘱监护制度。未来立法中,如何在借鉴传统与西方法学理论的基础上制定符合实际的监护法,已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
[1]陈瑛珣:《从清代台湾托孤契约文书探讨闽台女性财产权的变与不变》,载《闽南文化研究》2004年第2期。
[2]俞江:《家产制视野下的遗嘱》,载《法学》2010年第7期。
[3](晋)陈寿:《三国志·先主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4](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一之六二》,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
[5]王菱菱、王文书:《论宋政府对遗孤财产的检校与放贷》,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4期。
[6]罗彤华:《宋代的孤幼检校政策及其执行》,载《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4期。
[7]郭成伟点校:《大元通制条格》,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8]《广西民事习惯人事部报告书》,载《广西官报》1911年第100期。
[9]《清康熙四十年十月陈继善立托孤约》,载刘伯山主编:《徽州文书》(第一辑)第九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0]孔昭明主编:《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九辑·台湾私法人事编》,台北:大通书局1987年版。
[11]陈金田译:《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第一部调查第三回报告书·台湾私法》(第二卷),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3年版。
[12]俞江、陈云朝:《论清代合同的分类——兼论不定型合同的成立》,载《制度因革与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华中科技大学近代法研究所2011年版。
[13]《古今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14]《中华民国暂行民律草案》,北京:法政学社1912年版。
[15]陈宗蕃:《亲属法通论》,上海:世界书局1947年版。
[16]司法行政部民法研究修正委员会编:《中华民国民法制定史料汇编》(下),台北司法行政部1976年版。
[17]黄源盛纂辑:《大理院民事判例辑存·亲属编》,台北:犁斋社2012年版。
[18]郭卫:《大理院判决例全书》,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2年版。
[19]《大理院判例要旨·民律刑律之部》(上),载《司法公报》1915年第43期。
[20]黄源盛:《民刑分立之后——民初大理院民事审判法源问题再探》,载《政大法学评论》2007年第98期。
[21]林秀雄:《论未成年人之监护人及“民法”第一千零九十四条之修正》,载谢再全等:《物权·亲属编》,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2]刘昕杰:《“中国法的历史”还是“西方法在中国的历史”——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再思考》,载《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4期。
[23]曹诗权:《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4]史尚宽:《亲属法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5](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26](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徐建国、王晓晔、谢怀栻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