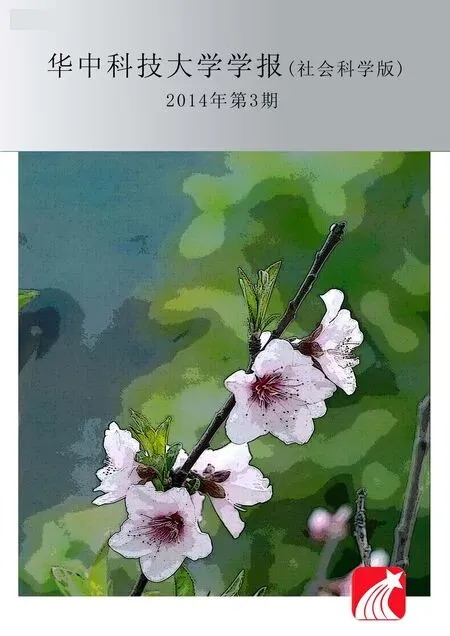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
——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有感
景跃进,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系,北京100084
笔者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关注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全会提出的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二是用“社会治理”一词取代“社会管理”。这两种表述各自包含着丰富的内涵,且都与“治理”有关。事实上,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一个月,在浙江杭州召开了“纪念毛主席批示‘枫桥经验’五十周年”大会,孟建柱在讲话中便使用了“社会治理”一词,而且据说他特地停顿了一下,提醒与会者注意不是“社会管理”而是“社会治理”。笔者的问题是,党的文件中的这种措辞变化是不是很重要以及《决定》中的“治理”一词意味着什么?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在此笔者想借用吴国光的“文件政治”概念来说明这一点。为便于理解,可以设想一个作为理想类型的连续谱,其中的一个顶端是肆意而为的个人独裁,另一端是实行法治的民主政治,“文件政治”恰好介于两者之间,既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法治,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人独裁,它是由少数人组成的领导集团来治理这个国家。文件具有一定程度的约束性,代表着统治集团的共识和集体意志。文件虽然不如法律那么刚性,但也不是随便而作。通常情况下,党的重要文件没有一年半载的时间是制定不出来的。确定文件主题、各种专题调查、起草之后的反复修改、征求各方意见……方方面面都要平衡。从功能替代的角度来看,中国政治的实质性过程不是在会上,而是在会前,也就是说,功夫在会前已经做足了,会议本身更多地是一个形式,也是最后一道环节,给文件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这与西方国家的政治过程明显不同。
文件政治意味着中国政治是自上而下地运作的,文件提供了这一过程的起点。因此,什么样的词汇能够进入党的文件不是随随便便的事情,而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政治安排。一般而言,一个重要词汇进入党的文件便会维持相对的稳定性,翻阅一下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党代会报告便可发现这一点。但是,“社会治理”对“社会管理”一词的替代似乎给出了一个例外。
笔者查阅了一下,“社会管理”一词最早出现在党的重要文件中是在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里笔者将在党的中央全会上通过的文件看做是党的重要文件),当时它指的是一般意义上的政府管理职能(之一),而不是现在理解的意义。接下来好几年“社会管理”一词未见踪影,直到2002年进入了党的十六大报告,随后它在重要文件中的出现频次不断增多,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社会管理”一词出现了15次,频率非常高。为何出现这一变化?其背景是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分化、社会矛盾加深和群体性事件迸发。如何维持社会秩序、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成为各级政府的棘手问题。如果说国内的社会背景为“社会管理”一词提供了内源支撑,那么来自国外的治理危机和教训则使得“社会管理”一词有了新的表达形式。2010年年底,突尼斯的一个小贩跟“城管”发生冲突,小贩的死亡导致突尼斯政局巨变,并引发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震荡。所谓的“阿拉伯之春”给中国领导人以极大的震惊,作为一种回应,“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成为中国政治的关键词。2012年秋天,“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进入党的十八大报告,其使用频率是8次(连同“社会管理”总共出现了16次),而且进入了新修的党章之中。改革开放以来能够同时进入党的重要文件、党代会报告和党章的关键词并不多见,而“社会管理”荣幸成为其中之一。
然而,这样一个重要术语在最高文件的殿堂里只呆了一年时间(2012年11月到2013年11月),便被“社会治理”取代了。这一变更是否意味着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上,《党章》还得再次修改?尽管“社会管理”一词继续在使用(频次很低),但是回到了1993年的原初含义,亦即作为一般性的政府管理职能之一。
前面说过,党的重要文件的用词不是随意而为的,哪些词能进,哪些词不能进是很讲究的。这就产生了两个需要解释的问题:第一,为什么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文件用词发生了如此的变化?这里存在两种可能的逻辑解释,一种解释是,在这一年中,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发生了某种重大的变化,以至于必须用新的词汇去反映这样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另一种解释是社会现实本身变化并不大,但是领导人的观念或认知方式却发生了重要变化。在这两种解释中,哪一种解释更为合理?读者不妨自己来选择。
第二个问题是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用词的变化,是否意味着领导人接受了governance的理念?我们知道,在西方从管理到治理(from government to governance)是一种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关键是承认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那么党的重要文件中的措辞变化是否意味着这种转变亦已在中国发生(至少在观念层面)?
在阅读李克强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时,笔者发现,报告使用了“多元主体共同治理”这个表达。笔者查阅了一下,在此之前的政府工作报告、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历届党代会报告以及其他形式的党的重要文件中,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一概念。我们知道传统上执政党强调一元化领导,对于“多元”这个词是颇为敏感的,所以在李克强总理报告中读到这一词汇时,开始觉得有点奇怪。因为从理论上讲,政府工作报告通常意义上不是一个涉及政治性的文件,为此,笔者特意将李克强总理的报告和以往的政府工作报告对照了一下,发现朱镕基总理任内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及政治体制改革的话题,这一提法在温家宝总理200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在其任内,温总理所做的十个报告中有九次提及政治体制改革。到了李克强总理这里,2014年的第一个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提出了“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重要命题。
笔者有一个直观的感觉,也许不一定正确: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在一些方面超越了党的十八大报告,而政府工作报告在个别方面又发展了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为什么中国的文件政治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发生了这样的变化?也许我们不能从这样的现象中去演绎什么东西,但从经验角度来看,新的领导集体上任一年多以来,中国高层政治的变化确实是挺快的。从学术研究的眼光来看,不少事情超越了我们的专业预期。就此而言,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措词变化,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折射出了中国政治过程的一些新特点,也预示着中国社会将要发生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