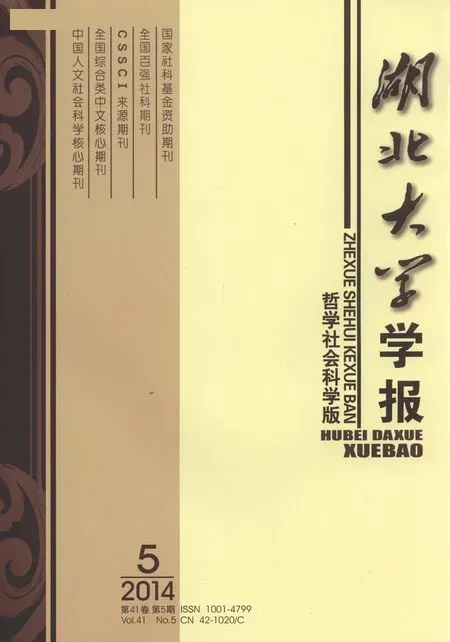西方经典女性主义理论家视域中的“日常生活”
陆兴忍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江苏南京210018)
日常生活是个有着自身意义和价值的领域,不论是从每个人类个体的角度看,还是从人类的整体生活结构的角度和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日常生活都在人类生活中有着不可取代的意义和价值。本文试图聚焦启蒙运动背景下几位西方经典女性主义理论家,探寻一下她们是如何看待日常生活的。
一、沃斯通克拉夫特:揭示男权意识对妇女日常生活的压制
英国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以其诞生于1792年的《女权辩》确立了“作为最伟大的好辩的女性主义者的地位”[1]1。这部被公认为第一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妇女理论著作,在批判启蒙主义哲学家卢梭的贤妻良母主义的女性观和女子教育观的基础上,展开了关于妇女在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领域的人权问题的论述,揭示和批判了男权意识对妇女日常生活的压抑和控制。
在卢梭看来,两性之间的生理差异是自然的安排,男的积极主动和身强力壮,而女的消极被动和身体柔弱,由此决定两性在社会上的角色。“男主外,女主内”在卢梭看来是不容置疑的、合乎自然的安排,男性负责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非日常事务,而女性则只能活动于日常生活领域,负责一家人的饮食起居、孕育、抚养小孩和照顾老人,同时女性作为天生的弱者,只能依附并服从男性,在日常生活中也要听命于父亲和丈夫等男性。这样,在卢梭及其同时代的男性看来,女性在社会中的价值就只是作为一个抚育孩子的母亲和照顾丈夫的妻子的角色价值。这些观念牢牢地控制着当时的妇女们,使妇女们把这些观念内化为自己的自觉行动。
对此,沃斯通克拉夫特一一予以揭露与反驳。她认为:“不仅在德行上,哪怕在知识上,男人和女人都是一样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女人不仅应被看作是有道德的人,而且也是有理性的人,她们应该和男人一样努力取得人类的美德,或者达到完美,而不应该被教育成如同卢梭笔下那个未开化的怪物一样奇特的半人。”[1]29之所以男人在科学、艺术创造方面占有优势,这并非是男女在理性方面存在的差别造成的,而是后天在教育方面的机会不均和以男性为中心的偏狭教育造成了两性的不平等:“整个妇女教育只应趋向一个目标——要使她们取悦于人。”[1]34大思想家卢梭所倡导的女性教育实际就是如何更好地服务于男权社会:“首先要母亲的身体好,孩子的身体才能好;首先要女人关心,男子才能受到幼年时期的教育;而且,他将来有怎样的脾气、欲求、爱好,甚至幸福还是不幸福,都有赖于妇女。所以妇女们所受的种种教育,和男人都是有关系的。使男人感到喜悦,对他们有所帮助,得到他们的爱和尊重,在幼年时期抚养他们,在壮年时期关心他们,对他们进谏忠言和给予安慰,使他们的生活很有乐趣[2]539;“一个女人应当具备的第一个重要的品质是温柔”[2]548——所有这些都是以男性为出发点的,服务于男性的利益的。
对于卢梭“这位片面的道学家”在“有计划地、花言巧语地提倡狡猾”,沃斯通克拉夫特反讥道:“(女人)倘若由于身心两方面的锻炼而变得体格强壮,智力健全,这时她还有必要去屈尊地使用巧妙伎俩,伪装柔弱病容以确保丈夫的爱吗?”[1]19对于男性中心教育观和道德观的自私和虚伪,沃斯通克拉夫特也毫不留情地表达了她的质疑:“遭到侮辱还能保持温柔,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也不反抗,并且甘心受罚,这颗心是用什么材料做成的呢?当男人用暴虐的手段来对待她,而女人却用她女性的温柔去抚爱这个男人,而由此来断定她的美德是建立在狭隘的观点和自私的基础之上,这难道是公平的吗?天性从未如此地赋予人不诚实;即便这种委曲求全可以称之为一种美德,但是任何一部分的道德是依靠虚伪而存在时,这种道德也就是暧昧不清楚的。这些只是应付一时、当时有益的手段。”[1]19
据此,沃斯通克拉夫特认为妇女最重要的不是培养什么居家过日子、相夫教子所要求的温柔的品质,而是发展理性,让男女享受同等的教育,只有这样才能使妇女具有独立的意志和人格,走出日常生活的狭小空间而取得独立自主。她力主男女的平等尊严:“我爱男人,就像爱我的同胞;但是绝不允许他那根不论是实有的还是篡取的权力之杖,伸到我的头上来,除非他的个人智慧令我敬仰;即便那样,我也是服从于理性而不是那个人。”[1]26要让妇女获得与男性一样的理性和知识,就必须推进妇女的教育,沃斯通克拉夫特指出:“为了让社会契约实现真正的公平,并且为了传播这些唯一能改进人类命运的启蒙性的原则,必须让妇女将她们的德行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之上,除非她们和男子们一样受到同样目的的教育,否则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她们目前已由于无知和低级趣味使她们处于次要的位置了,以致不配和男子相提并论了;否则,她们用和蛇一般的狡猾蜿蜒地攀登上知识之树,所得的仅仅是足以让男人们误入歧途的东西。”[1]582在她看来,“假如男人不让女人进步,妇女就会让男人堕落”[1]29。可见,妇女走出日常生活的狭窄领域,受益的不仅是女性,还有男性,还体现出整个社会的进步。
沃斯通克拉夫特通过对卢梭把女性才能限于对日常生活中柴米油盐的料理和照顾丈夫、生儿育女的男性中心女性观的批判,着眼于两性的共同利益和人类的命运,阐发自己的女性教育观和发展观,唤醒了现实中的男女去重新审视自己的生存状态和现存的生活理念,对于促进现实中的妇女走出卢梭式的男性中心女性道德观的束缚有着重要的意义。正如埃伦·默尔斯在《纽约评论》一书中指出的:“她希望告诉所有的女性不要屈服。从对她自己生活的观察中,从对她的姐妹、朋友、学生和老板的观察中,从广泛阅读哲学著作中,到她所热烈追求的同伴身上,沃斯通克拉夫特渐渐懂得社会条件决定了所有女性的生活方式,她开始公开指责妇女所承受的制度化的压抑——一个既存的社会事实。”[1]1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言论影响深远,直接启发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思考。
二、伍尔夫:呼吁女性独立的日常生活空间
英国职业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不仅在日常生活中处处显示出与男性的对抗姿态,在思想上也追随着其前辈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思路,继续揭露和批判男权意识对妇女日常生活的压抑与控制,并以其独特的才情继续对女性的日常生存作独到的探索,以一个铁杆女权主义者奠定了自己在女性文学创作史和女权主义运动史上不可磨灭的地位。
1.揭示囿于日常生活而无历史的女性生存状态。伍尔夫与沃斯通克拉夫特一样,痛彻地感受到男性中心社会从非日常生活领域的政治、经济、教育到婚嫁、衣着、家庭等日常生活方面对女性的压迫。伍尔夫对女性在日常生活里遭受的男权暴力进行了描绘:在伊丽莎白女王时代,“打妻子是大家公认的男人的权利,而且不论上等人或下等人一律如此做而不以为耻,……同样,假使女儿拒绝和父母所选定的男人结婚,就会被关起来,被鞭打,在屋里被推得东跌西撞,而大众却不以为怪”;而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统治整个机构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父亲,他拥有不容质疑的权力,毫不迟疑地把事物强加于他的儿女”[3]39。由一个个英国的家庭形成的庞大的父权制机构,致使女性只是作为一个男人的妻子、情人或者孩子的母亲而存在,生活范围局限于日常生活,充当繁重的日常生活事务的管理者。女性从小所接受着的教育就只为了女人终生惟一的职业——结婚:“为了结婚,她弹钢琴,却进不了乐团;画浪漫的家居风景,但却不允许研究人体;读这本书,但却不允许读那本书;受人引诱,被人询问。为了结婚,她接受形体训练——这一切是为了让她洁身自好,等待未来的丈夫。总之,对婚姻的顾虑影响着她的言语、思想和行为。否则又能怎么样呢?婚姻是她惟一的职业。”[3]39这样的教育只教会了女性日常生活中趋附男性的能力,却没有应对非日常生活事务的能力,从而女性在非日常生活领域没有发言权,被隔离于非日常生活领域之外。伍尔夫还指出了遍布英国各方面的男女不平等:男性不需通过婚姻就拥有英格兰几乎所有的资本、土地、财宝和任免权,而女性若不通过婚姻,在英格兰几乎没有任何资本、土地、财宝和任免权;在法律和商业、宗教和政治方面,女性没有任何影响力,海军和陆军的大门对女性关闭着;在教育上,男性在公学和大学中已经接受了五六百年的教育,女性则只接受了60年教育[4]93。由于政治、经济上依附和从属于男性,女性只能在吃喝拉撒的日常生活领域终其一生,在非日常生活的广阔领域毫无作为。伍尔夫说:“甚至在十九世纪,妇女也几乎仅仅在她的家庭和情感之中生活”[5]52;“因为每天都煮饭,洗盘碗,送小孩子上学,然后他们长大了到世界里去。一切都没有留下什么。一切都消失了。没有传记、历史提到一个字”[6]95。长期以来只活动于被男性轻视的日常生活领域,在非日常生活领域几乎空白的境地,导致女性在历史书写中的空白:“英国的历史是男性的历史,不是女性的历史。”[5]49
2.呼吁女性独立的日常生活空间。女性不仅被排除在非日常生活领域,即使在日常生活领域,女性也只是生儿育女、操持家务的代名词,笼罩在男权意识的监控下,没有一点话语权,没有自己的自主权和独立的生活空间。也即是说,即使日常生活是女性生活的全部内容,但那也不是属于她自己的日常生活,而是围绕着她的丈夫和儿女的日常生活。因而,伍尔芙渴望和呼吁女性要有自己独立的日常生活空间。如何获得独立的日常生活空间呢?在伍尔夫看来,那就是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每年五百磅入款”。“一年五百磅入款可以代表能沉思的力量,门上一把锁象征能替自己想的力量……”[6]112,“智力的自由全靠物质的环境”[6]114。在没有获得姑妈一年五百磅的经济支持前,伍尔夫这样描述她经济贫困时的体验:“第一,总得做我不爱做的工作,而且得像一个奴隶一样地作谄媚、奉承……不去奉承所冒的险实在太大了。再者,想到我那一点天才……它渐渐在消灭……”[6]44而有了一年五百磅的经济支持,她“觉得一笔固定的入款会把人的脾气改变这么多,实在真奇怪。……不但苦工挣扎都没有了,连憎恨怨忿也没有了。我用不着恨哪个人,因为他不能伤害我。我用不着奉承哪个人,因为我不要他的恩惠。于是不知不觉地我发现我自己对人类的那一半人采取了一种新的态度”[6]44。可见经济独立对女性解放有多重要:“其实一年五百磅就可以保持一个人在阳光里生活了。”[6]45从伍尔夫的描述可知,女性有了自己独立的日常生活空间,有如下好处:第一是物质条件的改善使女性不再依附于男性,看男性的脸色行事,并从琐碎的日常生活事务中解脱出来;第二是经济的独立使女性获得人格的自由和精神的自主,人生态度也更积极乐观;第三,独立的生活空间使女性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为女性创造力的发挥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提供了可能。然而,女性如何才能拥有自己独立的日常生活空间呢?并不是所有的妇女都有伍尔夫的幸运获得姑妈的赞助,这就要求女性从日常家庭生活中走出来,摒弃按男性价值标准规划出来的“房中的天使”的束缚,“在所有有赖于人类技能的职业和学科中都表现了她自己”[4]93,实现“英国妇女,从一种动摇不定、含糊暧昧的难以捉摸的影响,转化为一名选举人,一个挣工资者,一位负责的公民,这种变化使她在她的生活和艺术中都转向非个人化。她和外界的各种关系,现在不仅是感情上的,而且是理智上的、政治上的”[5]57。只有走出日常生活的私人领域,进入非日常生活领域就业,有维持生计的收入保障,女性才可能真正独立自主,拥有自己独立的日常生活空间。
三、波伏娃:挣脱男权指定的日常生活领域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其被誉为“有史以来讨论妇女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智慧”的《第二性》中以多学科的知识和众多的现实资料,客观描述了女性存在的历史、现状,揭示出父权制文化是造成女性贬为第二性的社会文化根源,并展望了两性的未来。
本着“我们的任务是发现女人的本性在历史的整个过程中是怎样受影响的;我们很想搞清楚,人类是怎样对待人类女性的”[7]40宗旨,波伏娃揭示了两性后天性格、能力的形成并非由先天的生物因素决定的,而是由社会文化因素所决定的;不管是在非日常生活领域还是日常生活领域,女性都被看成是具有劣等性的次要者——他者,女性“生活在男人强迫她接受他者地位的世界当中”[7]25。
男权社会还把女性指定在日常生活领域,以婚姻作为女人终生的也是唯一的职业:“他使她注定要过着周而复始的千篇一律的生活。……真正的活动,真正的工作都是他丈夫的特权:她只能做一些令人厌倦而又永远不会完全令人满意的事情。……正是他,把这种奉献当作她的最高信条和她生存正当性的唯一证明强加给了妻子。”[7]544对于男人来说,他首先是一个公民,一个生产者,其次才是一个丈夫;对于女人来说,她则首先是一个妻子,而且往往只是一个妻子[7]521。也就是说,男权社会把女人封闭在日常生活的有限范围,一个女人一生的全部内容就是日常生活,她们没有接近大事的任何机会,她们被剥夺了与社会、团体和更大范围的人接触的可能性,却又被指责为世俗、平庸、视野狭窄、功利主义。而有天赋的女性却被日常生活的琐事消磨才华,如夏里埃夫人一生“写了一些作品和几本书,但大部分生命都耗费在其琐碎、极无聊的生活小事上了”[7]543。波伏娃假设道:“假如一个男人具备泽里德(夏里埃夫人的笔名——笔者注)那样的天赋,我们敢肯定他不会在科隆比耶那单调乏味的孤独中浪费掉一生。他将会在这个由事业、斗争、行动和生活所构成的世界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7]543可见,传统男权社会把女性指定在日常生活领域是自私的和不公平的,它极大地扼杀了女性的创造力和才华。
与此同时,波伏娃也认识到,男权中心制度和文化不仅在压制和禁锢女性,也同时在压抑和误导男性,不仅女性,还有男性,都要从偏狭的、不利于两性共同发展的文化观中解脱出来。而女性则只有挣脱男权指定的日常生活领域,确立女性主体地位,才有可能获得独立与解放。她说:“夫妻两个人也都在受不是他们所创立的制度的压迫。如果断言男人在压迫女人,丈夫会大为愤慨;觉得他才是被压迫者——而他也确实如此;然而,是男性的法典,是男性依照自己利益所发展的社会,以某种形式确定了女人的处境,这种形式是当前男女两性都在受折磨的根源……为了他们共同的幸福,这种处境只能通过不许把婚姻当作女人的‘职业’来加以改变。……他让她自由的同时(就是说,在让她在这个世界上有事可做的同时),也就让自己获得了自由。”[7]548只有当女性“成为生产性的、主动的人时,它会重新获得超越性;她会通过设计具体地去肯定她的主体地位;她会去尝试认识与她所追求的目标、与她所拥有的金钱和权力相关的责任”[7]771~772。
然而,女人获得自己的社会职业并不等于获得了真正的独立和解放。波伏娃指出,由于女性最初的工作机会和工作报酬都比男性少和低得多,对众多女人来说,在婚姻框架内的“外部工作”,只不过是一个追加疲劳的问题。但是不能否认,女人融入非日常生活领域,经济地位的独立确实会内在地改变女性的精神面貌,而且经济的独立和自主这一因素在女性历史的演变过程中,曾经是并且依旧是基本的因素。但是最终的因素还取决女性自身的努力和道德的、社会的、文化的环境的改善[7]821。她说:“所谓妇女解放,就是让她不再局限于她同男人的关系,而不是不让她有这种关系。即使她有自己的独立生存,她也仍然会不折不扣地为他而生存:尽管相互承认对方是主体,但每一方对于对方仍旧是他者。……男人和女人首先就必须依据并通过他们的自然差异,去毫不含糊地肯定他们的手足关系。”[7]827男女双方在确保自身作为具有独立性的主体同时,又互为对方的他者,可见波伏娃倡导的是尊重和承认男女自然差异的既独立又合作的平等和谐的男女伙伴关系。她实质上已经把女性解放的问题提高到了人的解放的高度。
上述经典女性主义理论家富于智慧和胆略的言论无疑是振聋发聩、发人之所未发的。首先,她们清算和批判了把女性局限于日常生活领域的男性中心意识形态,并明确指出女性并不是劣于男性的生物族群,并不是只配在日常生活领域中当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女性应该还是非日常生活领域的公民和生产者。其次,她们强调了女性接受教育从而使自己的生活和精神空间都不局限于日常生活领域以及实现经济的独立和自主的重要性。再次,她们强调增进女性在非日常生活领域的权利更有助于两性生活质量的提高和人性的和谐与解放。总体来说,在启蒙运动背景下的经典女性主义理论家大胆地揭示了18世纪以前欧洲大陆女性作为日常生活领域的劳作主体而沦为非日常生活领域的纯粹他者的生活现实及其原因,并提出了种种改变这一状况的思路和想法。
可以看出,在第一浪潮女权运动背景中,日常生活是一个被西方经典女性主义理论先驱彻底否定的领域,她们也与那个时代的男性一样,认为日常生活是单调、琐碎、贫乏、无意义的代名词,是背景性的领域,是比非日常生活更低形态的领域。非日常生活与日常生活就像男人和女人的地位,非日常生活处于第一性的地位,而日常生活处于第二性的地位。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日常生活就应该是女人的领域,女人的世界。男人从小就被教育要在非日常生活领域干一番事业,女人则从小被教育要安于日常生活领域,精通各项日常家务,做一个会过日子的贤妻良母。对此,波伏娃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们把美妙的面纱抛到了女人那单调乏味的家务和母性负担中,使女人以妻子母亲的日常生活操劳换来了“女性化”这笔虚假财富。巴尔扎克劝告男人要把女人当作奴隶对待,同时又要让女人相信她是王后,目的也是让女性安于日常生活领域,好服务于男人。
西方经典女性主义理论先驱的目光无疑是犀利的,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她们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去看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的界限,在呼吁女性挣脱仅仅拘囿于日常生活领域的生存状态的同时,完全忽视了日常生活各种高峰体验给女性带来的快乐与满足、日常生活所具有的抵抗男性中心意识形态的空间等等日常生活本身所具有的价值,这些局限在第二、第三浪潮女性主义理论家那里有了改变。第二浪潮女性主义开始认识到日常生活对于女性物质和精神解放,尤其是精神解放的重要意义,她们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性、生育、母职、家务、心理等揭示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以促进现实的妇女的觉醒和妇女日常生活境遇的改善。但是第二浪潮女性主义也没能跳出启蒙主义式的从日常生活/非日常生活二元论的框架来认识日常生活,没能赋予日常生活以意义,没能在日常生活之内寻找意义和价值。受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影响,第三浪潮女性主义开始反思“与男性一样成为主体”是否必要,第三浪潮的女性主义即后学语境中的女性主义直接把日常生活作为自己的研究重心,直接关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身体、衣着、家居、购物等与女性的各种表征并努力去发现其中的价值和意义。
总而言之,日常生活本身并不是毫无价值的领域,然而如果男权社会非要把它与女性捆绑在一起,围困女性于其中而不能逾越,限制女性作为完整的人的发展,拒绝女人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那它肯定就是不合理的,必须抵制的。因为正如波伏娃说的,“女人在家里的工作并没有给她带来自主性;她对社会没有直接用途,既不能开拓未来,也不能生产产品。她只有在与越出自我的、超越自我的、在生产和活动中走向社会的生存者相联系时,才具有意义和尊严。这就是说,她的工作远没有让她获得自由,而是让她依附于丈夫和孩子们。她通过他们证明自己生存的正当性,但她在他们生活中只是一个次要的中介”[7]521。因此启蒙运动背景下的女性试图挣脱男权社会指定给她们的领域,要求参与到政治、经济、哲学、艺术、教育等非日常生活领域中,与男性一样平等地分享这些领域的资源和工作无疑是合理的,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对于她们来说,唯有进入到非日常生活领域,参与到政治和经济等领域的工作中,才能够获得经济的独立,从而摆脱依附男性的生活境况,成为与男人平等的另一种性别。只是这一阶段女权运动在要求分享与男性平等的权利的同时,往往一切向男性看齐,没有正视女性同男性的自然差异,以为女人的独立成功就要抛弃女性气质,实际上只是肯定了女性之为人的权利,并没有肯定女性之为女人的其他权利和价值,对于女性多样的特质和多样的生存样态还来不及思辨,这是时代的局限、历史的局限。正如美国当代女性主义理论家简·罗兰·马丁对沃斯通克拉夫特理想的女性教育观的批评:“这种教育把最重要的地位给了传统上和男性相联系的特征,这却是以牺牲传统上与女性相联系的特征为代价。”[8]18这一问题启发了后来的女性主义研究者,给他们留下了巨大的思考空间。
[1]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女权辩[M].谭洁,黄晓红,译.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5.
[2]卢梭.爱弥儿[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3]John Mepham.Virginia Woolf:A Literary Life[M].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1991.
[4]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随笔集[M].孔小炯,黄梅,译.深圳:海天出版社,1993.
[5]弗吉尼亚·伍尔夫.妇女与小说[M]//论小说与小说家.翟世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6]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M].王还,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7]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全译本[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8]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M].艾晓明,等,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细读《孔雀东南飞》
-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其它文章
- 略论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哲学基础
- 从“人口治理”到“关怀自身”
——资本、权力与生存美学 - 论晚清时期文官保举的基本特征①关于中国清朝保举制度的研究,无论是通史性,还是断代性的,学界已经有了不少著作,或涉及或设专章进行研究。如李铁的《中国文官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等对中国古代的文官选用、保举、考绩、监察和惩处等进行了分析。陈茂同在《中国历代选官制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中设有“荐举论”专章,认为保举是重要的选官途径,区分和确定了保举类型及标准,分析了保举的利弊。宁欣清晰勾勒“选举”制度变迁脉络,对中国的选人、任官制度进行了论述,其中包括了清朝的用人制度(《中华文化通
- 德沃金对罗尔斯分配正义理论的批评与发展
- 从协同正义看罗尔斯、诺齐克之争
- 德性伦理的启蒙话语
——休谟德性理论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