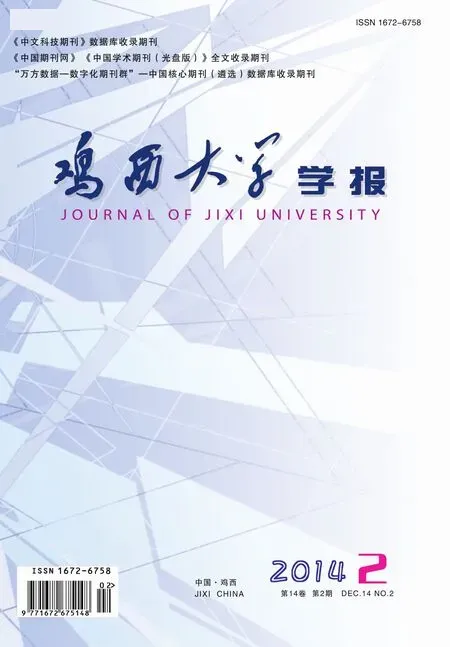孟子高昂的济世追求
张炜芳
(赣南师范学院 文旅系,江西 赣州 341000)
一 现实体验与高扬的价值使命
礼崩乐坏、新旧更替、百家争鸣这是人们对春秋战国时期的概述。然而,对身处其中的孟子而言,极尽的不是新旧更替、礼崩乐坏的体验,而是对时下现实社会的关注和自身作为时代个体的社会责任的思考。
一方面,在现实中极尽的是对百姓生存境遇的体验。孟子感知到弱肉强食,列国攻伐,纷纷以图霸的社会现实。各国之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整个国家“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百姓面临着“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的生存境遇。而统治者却“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孟子·滕文公下》)他们“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将终岁勤勤,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夫世禄,滕固行之矣。”(《孟子·滕文公上》)孟子眼见“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草。”(《孟子·梁惠王上》)看似为民父母行政的统治者,却丧失仁德,不免于车兽而食人,孟子深切地体会到“民”的妻离子散,乱世流离的景象。
另一方面,社会上“处世横议”,提出了许多治国济世主张,但在孟子看来,却都是充塞仁义,不可行的。“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诸子中,杨墨之学居于主导。但孟子认为“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梁惠王下》)对此,孟子扬言杨氏主张不能为统治阶级服务,而墨家的“爱无差等”实则是破坏“忠孝”和“仁义”,不合人道。杨墨盛行,势必天下大乱。孟子看来,“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现实社会只有推行孔子之道,才能真正利民,“着孔子之道”才能实现拯救社会,救百姓于水火。对此,孟子提出以“民”为中心的仁政之路的济世理想。
孟子认为自己就是“着孔子之道”忠实者,基于社会现实和理想的认识,孟子高扬地表示自己作为社会个体的价值使命。
一方面,他表示在当时社会环境下“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孟子·滕文公下》)自己不得不尽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改变当时“圣人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的现实,“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承三圣者”实属不得已而为之。
另一方面,又自信地把自己定位为“先知先觉”者,表示自己“将以斯道觉斯民也” ,(《孟子·万章上》)扬言“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 他直斥“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俱,安居而天下熄。”讽刺他们行“妾妇之道”。(《孟子·公孙丑下》)甚至对于管仲、曾西,孟子也表示“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孟子·公孙丑上》)自己不愿效仿。同时高扬“夫道一而已矣。”(《孟子·滕文公章句上》)自己掌握的才是唯一之天理,极尽了对其他学说的批判和对个人济世志愿的高扬。
二 自信与激扬的济世实践
孟子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他一生以孔子为榜样,坚持对社会的道义和济世理想,也选择了择善而“游”的人生。但相比于孔子的谦和,孟子对济世理想和社会道义个人情绪要表现得激扬得多。
从孟子济世实践的姿态看来,孔子虽然曾高扬自己抱有“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篇》)的自信。然而,孔子“游”的人生与坚持道义的价值选择,在人们看来,其境遇“累累若丧家之犬”,却远远没有孟子游说时“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孟子·滕文公下》)的姿态和规模;更也不用谈孟子济世实践的激扬。
针对各国政治行为,孟子是直率而猛烈地批判。基于对“民”的关怀,他犀利地指责梁国夺“民时” 、“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而“察邻国之政”的是“以五十步笑百步”荒谬的行为。说邹穆公“君之仓察实,府库充”,凶年饥岁百姓离乡背井,弃尸荒野。而齐国百姓“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却还“行匹夫之勇”、侵掠邻国,“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质问齐国“四境之内不治”、“凶年饥岁,子之民,老羸转於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等一系列社会现实。对当时践行“仁政”理想但现实却很是欠缺的宋国,孟子表示“今有人日攘其邻之鸡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孟子·滕文公下》)孟子一气之下,怒斥宋国君臣挂着仁政旗号却不急于实行的经济政策好似偷鸡的贼。对此,他也批判现实社会中的事君者,认为现实的良实则都是“约于国”、“好强战”并且贪图富荣的人,他甚至扬言他们是辅桀的“民贼” 。(《孟子·公孙丑下》)由此可知孟子的直率与张狂。
在对待国君的态度上,孟子更多的是率性而犀利的言责,甚至不顾颜面的批判。他的言行中少了许多对于君臣之礼的注重,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无畏的精神姿态。他直言齐宣王“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使齐宣王是极为尴尬的“王顾左右而言他 ”。(《孟子·梁惠王章句下》)而当齐宣王平心静气地向孟子询问有关公卿的事时,孟子毫无畏惧表示“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不听,则易位。”这种臣属的直言之色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齐宣王当场就“勃然变乎色”。孟子的狂妄展露无遗。见了梁惠王,直言梁惠王“望之不似人君” 。(《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准备去见齐王时,尚未出门,国君派人说:“国君因为临时身体不适不能前来,不知先生能否早朝前来”,孟子立刻回答说:“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孟子公孙丑章句下》)他也称病了。孟子是极尽了个人的喜怒哀乐,率性而为,始终以一份高昂的姿态行走各国。
在价值立场上,孟子极力表示不愿将就。对于未能采纳孟子政见的齐威王,他所赠予的为表示对贤人志士的尊重的上等金银,孟子表示坚决不受,认为“若于齐,则未有处也。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自己作为一个君子,未采纳他的主张,无故赠予,和收买无异,而君子是不可收买的,极尽了自己的立场和个性。他也直言表示要使自己“姑舍女所学而从我”而追随齐宣王,这好比让玉匠按他人想法雕琢玉石。(《孟子·梁惠王章句下》)他坚定地表明自己是不会为迎合君王的要求,而改变自己的主张和立场的。由此可见,孟子对价值理想的高扬。
综合孟子的游说,似乎总是“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下》)以压倒的气势向君王卿相们进言,从不把地位和权势放在眼里,不卑不亢,有话直说,以理服人,既不投其所好,也不委屈自己的学识和理想正如他自己所说:“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孟子·滕文公下》)自信而激烈的性格跃然纸上。以致,多年后明太祖朱元璋,读至《孟子》时,还“怪其对君不逊,怒曰:‘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时将丁祭,遂命罢配享。”面对孟子张狂的言行,以及那在他看来非人臣所应说的话语,朱元璋甚是大怒,这一怒之下还取消了孟子配享孔庙的资格,后来又大肆删减孟子原文,编订《孟子节文》,并明文规定科举考试不得以被删条文命题。①也难怪梁启超说“孟子盖热血磅礴人也。”他甚至用“狂狷”一字来概括孟子的个性,认为“孟子最进取者也,孟子最能任者也,故孟子亦狂者也”,“孟子最不屑不洁者也,孟子最能清者,故孟子亦狷者也,故不肯枉尺而直寻也”。②由此可见,孟子的犀利和狂妄。
三 自尊与洒脱的现实回归
孟子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各国游说,而结果却如焦循所说“曲高和寡,道大难追。”③大多数人认为“天下方务於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在梁惠王开口便问“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的社会,孟子却倡导“唐、虞、三代之德”的主张未能解决当时统治阶层的需要,他的价值理念在当时不但未能得到更多的反响和认同,反而“则见以为迂远而阔於事情”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子最终未能在游说中践行自己的济世理想,转而不得不面对“不得志独行其道”的现实。一次次的游说实践重创了他“王如用予,则岂图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的信念。孟子以孔子为楷模,有着与孔子相似的人生境遇,面对现实他表现出与孔子一样的强烈自尊,然而与深沉和困顿相比,又更多的是一种强烈自尊下的一副“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的洒脱。
对自己的济世追求,孟子表示“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孟子·告子章句下》)在他看来,自己的价值志愿“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孟子·梁惠王章句下》)也只能“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孟子·尽心章句上》)对他来说,更多的只能是尽人事,听天命。求自己“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后面转而“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逐渐走向一条独善其身的道路。这实则也隐藏着有志于道却对于现实的无奈下的一种安慰。
孟子表示欣然接受现实,但对个人,孟子则表示会依然坚持自己的价值追求。“苟不至于仁,终身忧辱,以限于死亡。”虽然,济世现实未能理想,但自己依然以一身“浩然之气”立于世,“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他把“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称为人生一大乐事,要求自己以“浩然之气”堂堂立于社会而无惧。清晰地表示现实中“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吾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孟子·公孙丑章句下》)孟子表现乐于接受现实中的生存样态,但却不甘于现实,他依然会忠于理想,对所坚信的价值信念也表现出强烈的自尊。“往者不追,来者不拒。”他轻视轻言放弃,认为“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 因而,也始终坚守对自身所倡价值理念和社会理想的自信和追求,为此,他高昂地活在理想的世界里,以一种相对平和的心态去看待社会。
四 结语
正如钱穆先生所说,“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有一个共同特点:始终以人文精神为指导核心,其知识对象集中在现实人生政治、社会、教育、文艺诸方面;其生活理想集中在整体的共同的人文目标上。为社会全体服务,是知识分子最高的天职。”④
孟子作为战国时期的士人阶层,在当时“道术为天下裂”的时代,面对现实社会,尤其是对百姓疾苦的深切体会,甚至某种切肤之痛。因此,他在极力倡导仁政思想的同时,尤其关注“民”,倡导“与民同乐”“保民而王”。他抱着“苟不至于仁,终身忧辱,以陷于死亡。”的价值追求,自信地认为“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并积极奔走各诸侯国,以践行自己的济世志趣。他激昂地斥责各国时政,高扬“仁政”的济世理想。然而,却在一次次的游说实践中重创了自己“王如用予,则岂图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的信念。
孟子的济世志趣本顺应了当时社会知识群体的价值追求和政治需求,而在当时“天下方务於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的社会,孟子却倡导“唐、虞、三代之德”,他的这种主张又未能解决当时统治阶层的需要。因此他的济世理念,不但未能得到更多的反响和认同,反而“则见以为迂远而阔於事情”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子必须面对“不得志独行其道” 的社会现实。为此,他以一种洒脱的姿态,转而倡导“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而逐渐走向一条独善其身的道路,来实现自身对这个社会高姿态的需求。以此来维护自己强烈的自尊,这实则是给一度的自信和不可一世的自己找的一个台阶,是对自身尴尬境地的自我托辞。孟子高昂的济世追求也反映出战国时期知识群体的精神面貌,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后世知识分子的人格气节。
注释
① 张廷玉,等.《明史·列传第二十七钱唐传》中记载:“帝尝览《孟子》,至‘草芥’、‘寇仇’语,谓非臣子所宜言,议罢其享,诏有谏者以大不敬论。唐抗疏入谏曰:‘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时廷臣无不为唐危。帝鉴其诚恳,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复。然卒命儒臣修《孟子节文》云。”,北京:中华书局,1997.
②梁启超.论孟子遗稿[J].学术研究,1983(5):94.
③焦循 .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10):557.
④钱穆.国史新论[M].上海:三联书店,2005(10):134.
[1]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梁启超(清).论孟子遗稿[J].学术研究,1983(5).
[4]焦循(清).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5]司马迁(西汉).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2.
[6]钱穆.国史新论[M].上海:三联书店,2005.
[7]张廷玉,等(清).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7.
[8]董洪利.孟子研究[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