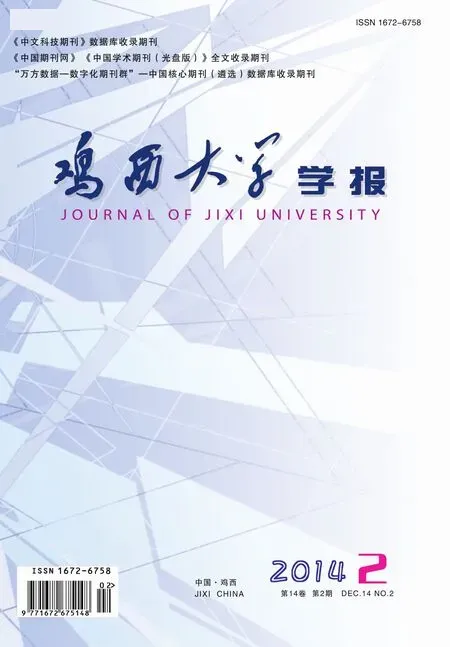论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尚实求真的审美艺术
岳振国
(西南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儒家传统美学思想宣扬真善美,摈弃假丑恶,从个体道德人格的修炼到文艺作品的大力倡导,千百年来一以贯之,不绝如缕。在这种思想的熏陶和影响下,中华民族培育铸就了优良的传统美德。文以载道,中国民族电影作为一种文艺形式,也负载着传承儒家传统美学的责任,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几代电影导演都非常注重通过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电影来弘扬真善美,鞭笞假丑恶,如冯小宁就说:“无论是拍战争片,还是历史片,我都在电影中极力宣扬人性的真善美,我希望观众能够通过我的电影净化灵魂,并使得大家更加具有凝聚力。不仅是民族凝聚力,而且是人类的凝聚力,就是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都应该以爱相待,使得大家凝聚在一起,来面对我们人类共同的困难。”[1]不仅是汉族导演如此,少数民族导演也在其执导的影片中宣扬美善,挞伐丑恶,如塞夫、麦丽丝就非常重视借助电影这种艺术形式来弘扬真善美,他们说:“我们是蒙古族导演,每时每刻都在对自己说:要发现你民族的优良,去鞭挞人类残存的丑与恶。”[2]别具一格的创作理念和卓有成效的艺术实践使得儒家美学思想在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得到艺术的传承和弘扬。
一 以真取胜
刘勰《文心雕龙·议对》中言:“事以明核为美,不以深隐为奇。”[3]求真尚实是儒家传统美学精神,建国以来电影工作者都非常崇尚这种审美精神,无一例外地在其所拍摄的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极力追求真实感人的艺术风格。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电影是对中国革命历程的艺术再现,有着显著的纪实性特点,所以真实是此类电影的基本要求,也攸关电影的成败。尚实求真的审美艺术追求,在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剧本创作上体现得尤为突出。在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题材选择和故事情节安排上,符合历史事实是首要考虑的因素。只有故事情节内容真实可信才不违背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创作原则,作品也才能打动人心。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大多反映的是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是有案可稽、信而有征的,何况有些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其剧本就是由编剧根据本人的真实人生经历创作完成的,因而电影所反映的情节内容确凿真实,令人信服。如电影《五更寒》的剧本是作家史超根据其在大别山根据地的亲身经历而写成的。《三进山城》的剧本是作家赛时礼根据早年的战斗生活创作完成的。《苦菜花》的剧本是由作家冯德英根据个人经历和家乡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发生的真实故事而创作完成的。《归心似箭》的剧本是由曾经是抗联战士的李克异根据战斗在白山黑水间的抗联队伍中真实的人物故事创作完成的。真实的人物和故事使得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生命力。
“真实,是艺术的灵魂,不真实的艺术不可能感染观众。”[4]例如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血战台儿庄》就是如此,该片着意追求纪实性,真实地再现了抗日战争中发生在台儿庄的那场悲壮感人的历史往事。影片上映后,反响热烈,许多曾亲历这场战争的人在观影后都大为赞赏电影的纪实性风格。这样的艺术效果也是编导者在最初拍摄这部电影时就确立的目标,“该片是在保证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发挥电影的特性,当真实性与电影特性发生冲突时,那一定以真实性为主。比如,闪回是电影常用的手法,但该片不允许出现闪回镜头,只能按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进行。”[5]这种不用闪回镜头,严格地按照时间顺序展开故事情节的拍摄方法极大地增强了电影的真实性,也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电影《西安事变》秉承纪实的风格,以真为美,以真取胜。电影不仅在故事情节上符合实际,还原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而且电影拍摄时也注意从光线的处理、色调的选择和氛围的渲染等诸多方面来营造一种厚重深沉的历史质感。该片摄影师陈万才说:“拍摄以前,导演成荫同志讲:《西安事变》要拍成一部文献性的历史故事片,首先真实性要强;从摄影、美工、化妆、道具、服装到置景等方面,特别是演员表演,都要真实可信。在影片风格上,要庄严,有气势;在基调上要浓郁,浑厚,有油画般的风味;影片意境要深,时代感要强,要拍成一部分量很重的历史正剧。”[6]“在《西安事变》影片总的色调处理上,我们偏重于古铜色,力求浑厚,有分量,有时代感,而不追求鲜艳华丽,尽量做到给人以肃穆庄严的感觉。”[6]由于编创者严谨的创作态度和富有艺术性的表现方法,《西安事变》真实地再现了抗日战争时期发生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成为一部经典的革命历史题材电影。
真实是艺术的生命,“因为艺术没有真实,艺术形象就成了失去灵魂的躯壳,艺术的美也就失去了前提。”[7]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大进军·大战宁沪杭》的拍摄中,导演别出心裁地采用历史时空和现实时空交叉组合的形式来叙述故事、讲述历史,一方面电影以逼真的画面和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穿越历史烟云回顾往事;另一方面,影片中穿插许多电影中所反映的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见证人对当年那些亲身经历事件的深情回忆,以这些人的翔实讲述和大量第一手的素材来强化影片故事的真实性,提高可信度,电影结构新颖独特,叙事过程中时空交错,契合无间。影片以精巧的结构、恢弘的场面、真实的叙述,艺术地表现出那段波澜壮阔、激荡人心的历史往事,让人观影时有身临其境之感,仿佛又回到那血雨腥风,动荡不安的战争岁月。为了追求真实性,如实再现历史场景,许多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就选择在影片所反映的历史事件的原址拍摄,以真实的山水景物、环境氛围来突出影片的纪实性,从而收到很好的艺术效果。例如《四渡赤水》就采用原址拍摄,影片摄制组扎营赤水河畔,拍摄时以逼真的服装道具,利用长镜头的拍摄手法真实再现当年红军浩浩荡荡横渡赤水河的壮观场景,以至于赤水河边围观的群众都产生了错觉,好像回到了当年的时空,完全达到了以假乱真的艺术效果。为了突出纪实性,《开国大典》全部是实景拍摄,完全遵照当年的实际情况来拍摄,该片导演李前宽说:“我们这次都是在实景中拍摄的。我们拍蒋介石逃跑的戏,就是从溪口到宁波、杭州、上海、南京,按照蒋当年逃跑的路线拍摄,一直追踪到蒋逃台时所乘的‘太行号’船。拍毛泽东在中南海的戏,就是在中南海拍的。拍宋庆龄的戏也是去上海宋庆龄故居拍的。我们是在真实的环境中再现当年的历史。”[8]电影《西安事变》在拍摄中非常强调纪实性,“为了体现历史真实,影片的大部分戏都决定在当时事件发生的地点拍摄。如‘国民党五全大会’的画面就是在南京总统府内拍的;‘美龄宫鸡尾酒会’‘何应钦官邸接见日本大使’‘西安南大街学生游行’‘华清池捉蒋’‘重庆戴公祠会客室内外杀害杨虎城父子’等等镜头,也都在实地拍摄。”[6]再如电影《佩剑将军》是选择在当年的淮海战役战场原址拍摄,以渲染真实的环境氛围。与上述电影对于真实性的追求相较,更有甚者,大型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周恩来》片中所有涉及的重要场景都是实景拍摄,“不仅这些场景的环境布置和当年完全一样,设施摆设全是真实原件,如西花厅的布置,总理办公室的布置,门上贴的那张大字报是原稿,康生、谢富治的签名都在上面。而且连总理身上的那套中山装、主席穿的睡衣,也都是真实原件。”[9]影片对于表现内容真实性的艺术追求可谓事无巨细,毫发无遗。电影采用这样的创作构想和拍摄方式,真实再现历史情景,极大地增强了影片的纪实性。秉承尚实求真的审美艺术追求,2009年为庆祝建国六十周年所拍摄的献礼影片如《建国大业》《天安门》《沂蒙六姐妹》,2011年为庆祝建党九十周年和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而相继推出了一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如《建党伟业》《秋之白华》《湘江北去》《第一大总统》《辛亥革命》《竞雄女侠·秋瑾》等,不但内容丰富多彩,情节曲折跌宕,而且无不是以尊重历史事实,反映历史事件作为影片创作的基本精神。
二 以情动人
“真者,精诚之至也”,艺术作品以情动人,出于作家真情创作的艺术作品自能感人至深。在中国的传统文学作品中,那些震古烁今的名篇佳构无不是作者食不甘味的倾心而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在其诗作中表达对家国的深切忧虑,那“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诗句,令无数忧国之士情为所牵,怦然心动。李煜那“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真情吐露,使多少失意之人感同身受,热泪潸然。书法艺术如颜真卿的《祭侄帖》,字里行间饱含着痛失侄子后的满腔悲愤。观此书帖,人们仿佛感触到这位唐代大书法家的情感脉搏。绘画艺术,如清初著名画家朱耷以纵肆狂狷的笔法书写其作为明代王公后裔,在国破家亡之后埋藏于内心的深哀剧痛。正是由于艺术家将充沛的情感贯注于艺术作品之中,才创作出那些感情真挚、引人入胜的佳作。
非独传统文艺作品以真挚的思想情感动人心魄,作为视听综合艺术形式的电影业概莫能外。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艺术魅力,不仅表现为追求故事情节的真实可信,还离不开对情感的书写和张扬。电影以情动人,首先是编导要热情饱满地投入作品创作,潜心创作,倾力而为。导演严寄洲曾言:“一部真实可信、有艺术价值的作品,不是作家脑子里凭空臆造出来的,不是灵机一动空想出来的,而是必须把思想感情的触角,扎扎实实地深探到生活的海洋中去用心观察,深入体验,辛勤积累,提高自己对纷繁芜杂的社会生活的认识力。在此基础上再加以精选、加工、增删和浓缩。通过自己的真挚感情,把燃烧起来的激情的火花,用心灵的熔炉去锻造出成品来。”[7]“一部有情感的电影一定是创作者的真情流露,感动了自己才会打动观众。”[10]编剧和导演只有怀着巨大的创作热情投入到电影的创作中,才能够创作出好的作品。电影艺术工作者不能全身心投入,情出于真,没有“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深切感受,其作品又如何能打动观众?回顾建国六十余年来那些脍炙人口的经典革命历史题材电影,无不是主创者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的艺术结晶。
其次,作品要内容生动,感情真挚。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真实地反映了志士仁人在谋求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的征途中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赵一曼》中革命先烈赵一曼那对于祖国和人民的赤忱情怀,《烈火中永生》中江姐等女囚在重庆解放前夕赶绣红旗,表达对新中国的美好祝愿,《可爱的中国》中方志敏对国家和民族的一往情深,《孙中山》中革命先驱孙中山为国家繁荣富强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无私奉献精神,莫不深深打动观众。这些影片所讲述的真实生动的故事,剧中人物高风亮节的品格,对国家民族的火热激情,使得电影充溢着浓郁的情感,令人心潮澎湃,情绪激昂。着意表现生动的内容和真挚的感情,是数十年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创制中一贯的审美艺术追求,如《野火春风斗古城》《红色娘子军》《英雄儿女》等经典电影,佳作纷呈,不胜枚举。尤其引人瞩目的是2011年为庆祝建党九十周年和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而推出的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秋之白华》《情归陶然亭》和《百年情书》三部影片,它们更是内容生动,情节感人。影片《秋之白华》表现瞿秋白和杨之华共同的革命理想和事业让他们冲破重重阻力,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情归陶然亭》则演绎了高君宇和石评梅生死不渝的凄美爱情,令人叹惋。《百年情书》中讲述林觉民和陈意映两小无猜、情投意合的动人爱情故事,为了民族解放,林觉民毅然抛妻弃子,以身许国,一封《与妻书》情郁于中,令无数观众泪眼滂沱,悲不自胜。三部影片的人物和故事众所周知,耳熟能详,长久以来为人津津乐道,影片真情流溢,感人肺腑。
再次,是电影演员对人物形象的准确把握和真情演绎。建国以来许多优秀的电影演员以丰厚的艺术素养、火热的创作激情、精湛的表演技艺,在银幕上塑造了一批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而对于如何才能塑造好人物形象,演员赵尔康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要创作有血有肉的生动、感人的人物形象,我认为必须抓住角色的思想线、感情线、行动线这三条基本线索去进行体验。只有这样,演员的表演才不会是盲目的,他才会明白自己该做什么、为什么做和怎样去做。庄子曰:‘何谓真?客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可见,对‘动于衷而形于外’的这条规律的认识,从古至今都是一样的。”[11]演员细心揣摩角色的内心情感世界并真情投入,是成功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因素。演员要准确把握角色的个性和情感,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以塑造英雄人物为主,但革命英雄并非只有英雄气,没有儿女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英雄的感情比普通人更为细腻丰富,深沉浓烈。比如电影《归心似箭》的主角抗联战士魏得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齐玉贞对魏得胜是一片痴情,魏得胜对齐玉贞也是感情真挚,影片在结尾玉贞送别魏得胜一节将魏得胜深沉炽烈的情感表现得毫发无遗。导演李俊就言:“我想起玉贞送魏得胜时最后一句话:‘记住,打完鬼子早点回来!’魏得胜也向玉贞说过:‘只要鬼子打不死我,打走鬼子我就回来!’这可以说是他们离别时的赠言。于是,我想到了用插曲来丰富情感,自己动手写了一首《雁南飞》的歌词。插曲非常真实自然,也把戏推向了高潮。”[12]影片结尾处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法深刻地表现出人物的赤诚情怀,《归心似箭》上演后万人空巷,轰动一时。其最大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对真情的宣扬和表现,“《归心似箭》之所以被公认为是那几年里最美的一部战争爱情影片,就在于它美在弘扬了鲜明的民族美德,美在表述爱情时深沉而又含蓄的风格,美在情真意切,美在情操高尚,而这一切又皆是以民族大义为前提。”[13]再如电影《周恩来》也是独具机杼,不是像寻常的对领袖人物塑造那样,歌颂其叱咤风云的人生经历,赞誉其“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领袖魅力,崇尚其挽狂澜于既倒的雄才伟略,而是另辟蹊径,“过去的许多描写领袖人物的片子都着重叙事,如主人公指挥了一场战争或做出了什么事迹等等,而《周恩来》则着意写情,‘透过一个伟人的喜怒哀乐,来显示他的心灵。’因为主人公所以征服人心,不仅在于其干出了多么惊天动地的伟业,更在于其人格的魅力,也就是做人应做什么样的人。从这个角度拓展,使传记片找到了以主人公晚年为重点、为高潮的叙事结构,同时也使片子在刻画人物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以感情、心态、人格为线索的表现手法,则如一条无形的红线,将总理的一生有机地串连起来。”[14]影片深入周恩来的内心世界,展现其对国家、对人民博大无私的爱和火热炽烈的情。电影《金沙水拍》也一改塑造领袖人物的刻板套路,影片侧重于对毛泽东内心细腻丰富情感的刻画和张扬,片中那对贺子珍深情的一吻,送别爱女的潸然泪下,让人怦然心动,情为所牵。
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的人物是以情动人,而演员也需要真情演绎,将自己融入角色之中,才能达到演员和角色之间的契合。活跃于新中国影坛的一大批优秀电影演员,以其饱满的创作激情和富有艺术才华的真情演绎,在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塑造了许多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如电影《红旗谱》中崔嵬扮演的朱老钟,《烈火中永生》中赵丹扮演的许云峰,《大河奔流》中张瑞芳扮演的李麦,《永不消失的电波》中孙道临扮演的李侠,《太行山上》王伍福扮演的朱德,《长征》中唐国强扮演的毛泽东,等等。
电影艺术家正是对于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纪实性艺术特质的敏锐把握,正是对于尚实求真传统美学精神的深切领悟和自觉追求,忠实历史,以严谨的创作态度和艺术的表现方法,从而创作出许多故事真实、思想深刻、人物生动、情感真挚的优秀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作品。这些电影既以纪实的风格演绎革命历史,塑造人物,同时也以感人的真情拨动观众的心弦。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尚实求真的审美艺术追求,令其在姹紫嫣红、繁花似锦的中国民族电影百花园中独放一道亮丽的异彩。
[1]冯小宁.电影的意识形态和艺术家的社会责任[J].绿叶,2008(5):87.
[2]塞夫,麦丽丝.蒙古往事[J].大众电影,1997(12):24.
[3]刘勰.文心雕龙[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246.
[4]杨光远,翟俊杰.《血战台儿庄》导演艺术总结[J].电影,1986(12):13.
[5]何厚桢.艺术≠历史——《血战台儿庄》导演兼答云贵读者[J].电影评介,1987(9):12.
[6]陈万才.《西安事变》摄影体会[J].电影评介,1982(4):26.
[7]严寄洲.《再生之地》创作琐谈[J].电影,1984(3):20,19.
[8]相韦.艺术地再现历史——长影导演李前宽谈《开国大典》[J].电影评介,1989(11):10.
[9]伟大人格的光辉艺术塑造——《周恩来》座谈会发言纪要[J].当代电影,1992(1):38.
[10]王坪.蒙山般的坚韧,沂水样的柔情——电影《战争中的女人·沂蒙六姐妹》导演阐述[J].艺术评论,2010(3):25.
[11]赵尔康.“动于衷而形于外”——扮演《归心似箭》中魏得胜的体会[J].电影艺术,1980(8):31.
[12]李俊.《归心似箭》有真情[J].大众电影,2006(22):43.
[13]王金山.《归心似箭》的故事[J].大众电影,2010(7):39.
[14]龙云.“情感是完整的”——访大型史诗性故事片《周恩来》执笔编剧宋家玲[J].现代传播,199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