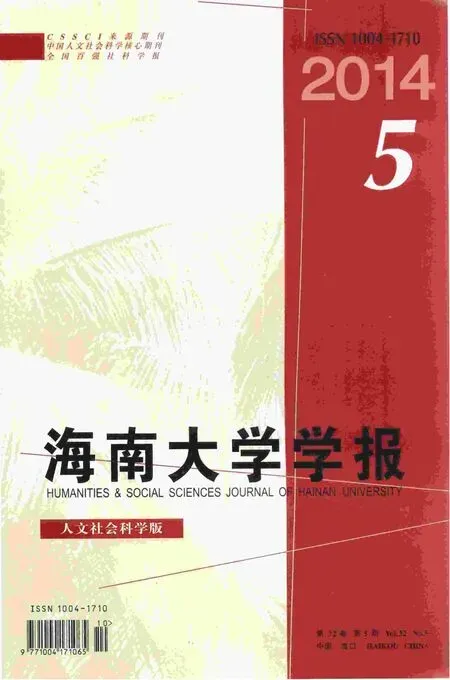论冯友兰“天地境界”的儒教特征
梁 忠
(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200234)
冯友兰无疑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具有开创性的人物之一。他以理、气、道体、大全四组概念,以“别共殊”的思想方法,以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四种人生境界,以及“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一贯标准,纵贯古今,融汇中外,编织了一个庞大的“新理学”哲学体系,大有包容众说,混一众流之势。
“新理学”体系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其人生境界说。在人生境界说中,冯友兰不仅把人生境界描述为一个从低到高递进的层级和过程,而且提出了“哲学高于宗教”的命题和“以哲学代宗教”的主张,并进行了深入论证。这些命题和主张无疑体现了冯友兰褒扬哲学、贬抑宗教的倾向。然而,在冯友兰提出这些命题和主张并进行论证的过程中,却不仅透露出冯友兰创建新的信仰模式的良苦用心,而且其“天地境界”本身就表露出明显的宗教特征,而这些宗教特征本质上可以归宗于儒教。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些儒教特征使得“天地境界”本身成为儒教信仰发展的新形式。
一、“以哲学代宗教”透玄机
表面看来,冯友兰是高扬哲学,贬抑甚至拒斥宗教的,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他认为哲学高于宗教,并明确提出了“以哲学代宗教”的主张。他说:“在未来的世界,人类将要以哲学代宗教。这是与中国传统相合的。”[1]9然而,正是在冯友兰关于“以哲学代宗教”的表述中,透露出冯友兰哲学的浓郁宗教气息,显示出明显的宗教特征。
在人类文明史上,哲学和宗教都是重要的文化现象。宗教甚至比哲学在历史上更为悠远,在受众上更为广泛,这反映出宗教在人类精神文化领域具有其独特且强大的功能,以致于古往今来的思想家没有明确提出宗教“取消论”者。冯友兰作为一个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同样也不例外。冯友兰曾清晰认识到宗教的不可取消性,他说:“放弃了宗教的人,若没有代替宗教的东西,也就丧失了更高的价值。”[1]9所以,他并不主张从根本上取消宗教,而只是像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及梁漱溟提出“以道德代宗教”一样,主张“以哲学代宗教”。
然而,从逻辑上说,要用一种文化现象代替另一种文化现象,那么,作为代替者的那种文化现象就必定要具备被代替者的文化功能,否则,代替者是无法代替被代替者的。
宗教那种只可代替、不可取消的独特功能是什么呢?在冯友兰看来,这种独特的功能就是满足人类“对超乎现世的追求”的先天欲望。他说:“对超乎现世的追求是人类先天的欲望之一,中国人并不是这条规律的例外。”[4]8他认为,其他的国家或民族大多把宗教作为人生的终极关怀和精神归宿,而中国人“不大关心宗教,是因为他们极其关心哲学。他们不是宗教的,因为他们都是哲学的。他们在哲学里满足了他们对超乎现世的追求”[1]8。也就是说,在冯友兰看来,中国人的哲学中有宗教那种“超乎现世”、“超越现实世界”的那个“存在”,因此同样可以满足人类对超乎现世的追求的先天欲望,故而具备了代替宗教的资质和可能。
实际上,冯友兰不仅认为哲学可以满足人类对超乎现世的追求的欲望,而且还把哲学当作是宗教的核心。他说:“宗教也和人生有关系。每种大宗教的核心都有一种哲学。事实上,每种大宗教就是一种哲学加上一定的上层建筑,包括迷信、教条、仪式和组织。这就是我所说的宗教。”[1]7冯友兰此论无疑是想要突出哲学相对于宗教的优越性。然而,或许冯友兰自己没有想到的是,他一旦把哲学当作是宗教的核心,他实际上就把哲学当作宗教的一部分,从而把哲学当作宗教本身了。
当然,在冯友兰的哲学中,他所认为能够代替宗教的哲学,是特指那种“即世间而出世间”、“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具有“最高底境界”的儒家哲学。而他所称的最高境界,实即他在《新原人》中所阐述的对“真际”、“理世界”、“大全”达到最高一层完全觉解的“天地境界”。冯友兰晚年坦承了“真际”、“理世界”的宗教性质:“在《新理学》里,我更明显地把科学底范围,加以限制,把科学与哲学对立起来,为哲学创立了一个虚幻的对象,即所谓‘真际’或‘理世界’。这个‘世界’,如上面所说的,其实就是宗教中的上帝底‘心’。”[2]
可以看出,这样一种能够代替宗教的“即世间而出世间”的具有“最高底境界”的儒家哲学,分明就是任继愈先生等人所论述的儒教(作为宗教的儒教,下同)。而“天地境界”作为这种哲学传统所追求的最高、最后境界,集中体现出儒教的基本特征。
二、“尽伦尽职”事、乐天
在冯友兰那里,如果说哲学是宗教的核心,那么“天地境界”则可以说是用以代替宗教的“即世间而出世间”、“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哲学的核心。在冯友兰对“天地境界”的论述中,集中体现了儒教的中心信仰。
根据任继愈先生的论述,儒教“信奉的是‘天地君亲师’”,其中“天是君权神授的神学根据,地是作为天的陪衬,师是代天地君亲立言的神职人员”[3]10;“宗教都要树立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名称各有不同)。儒教亦宣传敬天、畏天,……儒教还有祭天、祀天的仪式。”[3]10-11可见,儒教的最高的中心信仰就是“天”。而冯友兰对“天地境界”的论述,正是围绕“天”而展开的。
在冯友兰的论述中,“天地境界”是这样一种精神境界:“在此种境界中底人,其行为是‘事天’底。在此种境界中底人,了解于社会的全之外,还有宇宙的全,……在此种境界中底人,有完全底高一层底觉解。此即是说,他已完全知性,因其已知天。他已知天,所以他知人不但是社会的全的一部分,而并且是宇宙的全的一部分。不但对于社会,人应有贡献;即对于宇宙,人亦应有贡献。”[4]500又说:“上所说宇宙或大全之理及理世界,以及道体等观念,都是哲学底观念。人有这些哲学底观念,他即可以知天。知天然后可以事天,乐天,最后至于同天。此所谓天者,即宇宙或大全之义。”[4]565
显然,在冯友兰描述的“天地境界”中,其最高的存在是“天”,并认为此“天”即是宇宙、大全,这与《新理学》所阐述的最高概念“大全”是相呼应的。而在冯友兰对“天”的论述中,“天”不仅具有如上所说的至上性、终极性,而且其人格性、神秘性、彼岸性和创世性等宗教特征也显露无遗。
人格性 冯友兰“天地境界”中所谓知天、事天、乐天、同天的“天”具有明显的人格性。“天”不仅是最高存在,不仅是人认识的最高对象,而且还是人们从事各种事业所服务的主体性存在。冯友兰在“天地境界”理论中不仅提出了“事天”、“天民”的概念,而且强调在此境界中的人能自觉地为宇宙(天)做事,为宇宙(天)尽伦尽职,对宇宙(天)承担责任,对宇宙(天)有所贡献。显然,这样一个能接受人类服务和领受人类贡献的天、宇宙,具有明显的人格性特征。
神秘性 冯友兰在论述“天地境界”中的“大全”(即“天”)时,他说:“如以大全为对象而思之,则此思所思之大全,不包括此思。不包括此思,则此思所思之大全为有外。有外即不是大全。所以大全是不可思议底。大全既不可思议,亦不可言说,因为言说中,所言说底大全,不包括此言说。不包括此言说,则此言说所言说之大全为有外,有外即不是大全。不可思议,不可言说者,亦不可了解。”[5]134不仅如此,冯友兰在论述“天地境界”中的“同天”境界时,更明确声称物我界限、人我界限、内外界限皆不复存在的“同天”境界“本是所谓神秘主义底”[4]571。显然,这种不可思议的神秘主义已经超出了冯友兰自己画设的哲学的畛域。冯友兰在论述哲学的定义和性质时曾说:“在《新理学》中我们说:哲学乃自纯思之观点,对于经验,作理智底分析,总括及解释,而又以名言说出之者。”[5]143他明确认为哲学并不是不可思议的,相反必须是可以思议且能“以名言说出之者”。冯友兰后期哲学观提出的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也同样把哲学界定在“思”的畛域之中。所以,冯友兰所描述的“大全”、“天”所具有的“不可思议”、“不可言说”且“不可了解”的性质,不仅集中凸显出其所谓“大全”、“天”及由此而来的天地境界的神秘主义性质,而且其所谓“大全”、“天”、天地境界实际上已被明确划出了哲学的范围之外。尽管冯友兰曾申言其天地境界的神秘主义不同于宗教幻想,但是,一旦他肯认了其境界的神秘性和非哲学性,他实际上即已经肯认了其理论所具有的宗教的一个普遍性特征,而不论其是否属于宗教的“幻想”。
超越性和彼岸性 冯友兰的“天地境界”是对“天”、“大全”的完全的最高一层的觉解,而所谓“大全”则又是实际的世界和超越实际世界之上的“真际”、“理世界”的综合体。为了实现“以哲学代宗教”的目的,冯友兰正是要用这样一个具有超越性的“理世界”去代替宗教的天堂、天国的彼岸世界。他说:“宇宙或大全,理及太极,以及道体等观念……哲学以这些观念代替宗教中底上帝,天堂,以及创世等观念。哲学以清楚底思,替代宗教的图画式底想。”[4]590从逻辑上说,其之所以能代替宗教,正是因为它具备了被代替者的属性——超越性和彼岸性。因此,这样一个具有超越性的“理世界”,无疑构成了“天地境界”中的彼岸世界,只是在他看来,“理世界”作为彼岸世界是存在于“思”中的,而宗教的彼岸世界则是存在于图画式的“想象”中的。不仅如此,冯友兰还认为天国或天堂的观念也是对“理世界”某种程度的认识,只是“理世界”比天堂、天国的观念更加清晰而纯粹。他说:“天国或天堂,是人对于理世界只有模糊底、混乱底知识时,所有底观念。”[4]563这实际上直接肯定了其“理世界”的观念与天堂、天国的观念具有同质性。
创世性 在冯友兰的“理世界”中,其对所谓“动之理”的实现,以及“道体”等概念的论述,体现了宗教的“创世”特征。他说:“气必先实现动之理,然后方能有流行。……在《新理学》中,我们称之为‘气之动者’。后来又说:‘气之动者’可称为乾元(《新理学答问》)。可称为乾元者,言其有似于图画式底思想中,所谓创造者。”[5]131又说:“多数底宗教又都有所谓创世之说,以为神或上帝创造实际底世界。实际底世界是不完全底……创世的观念,是人对于道体只有模糊底、混乱底知识时,所有底观念。”[4]563“事实上虽没有只是流行底流行,但只是流行底流行却为任何流行所涵蕴。在逻辑上说,它是先于任何流行。它是第一动者。”[5]131也就是说,人们对于“道体”的知识不够清晰时,即有宗教所称的神或上帝创世之说;而如果对于“道体”的知识达到清晰时,则能认识到“气之动者”、“动之理”之实现以及“只是流行底流行”诸观念,并以这些观念代替宗教的神创说,因为前者(即“气之动者”诸观念)本质上是“第一动者”的体现,其本身有似于图画式的思想(即宗教思想)中的“创造者”的观念。
在冯友兰的“天地境界”中,不仅“天”具有如上所述的人格性、神秘性、彼岸性和创世性等宗教特征,而且实现与“天”的同一还是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在冯友兰论述的天地境界的最高层次即“自同于大全”的“同天”境界中的人,最终在精神上与宇宙、大全、天完全结合为一体,并获得了人生的终极快乐。这种“同天”的境界及快乐,与西方基督教神学所宣扬的“同基督结合为一体”的信仰状态极为相似。马克思论及此点时曾说:“同基督结合为一体可使人内心变得高尚,在苦难中得到安慰,有镇定的信心和一颗不是出于爱好虚荣,也不是出于渴求名望,而只是为了基督而向博爱和一切高尚而伟大的事物敞开的心。可见,同基督结合为一体会使人得到一种快乐,……这种快乐只有同基督并且通过基督同上帝结合在一起的天真无邪的童心,才能体会得到,这种快乐会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和崇高。”[6]只不过,“同基督结合为一体”采取的是让个人消融于信仰对象(基督)的方式,而冯友兰的“自同于大全”的同天境界采取的则是天人合一模式,这种模式体现了个体“与天地参”的主体精神,即个体与天地之间具有某种平等的意味,而不是单方面的一方消融于另一方。
三、“安身立命”寻归宿
冯友兰毕生以哲学及哲学史研究为志业,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抱负,其所创思的“天地境界”正是要为世人提供一个精神上的“安身立命之地”。他说:“宗教是神话的系统化。它也代表人对于自然的理解,代表一种对于自然的态度。神话和宗教,其目的和作用,都在于说明人和自然的关系,使人知道在自然界中所处的地位,从其中可以得一个‘安身立命之地’。这也正是哲学的目的和作用。”[7]225很明显,在冯友兰看来,使人可以得一个精神上的“安身立命之地”,本是神话和宗教的目的和作用,而他的工作则是要把这种原本宗教的目的和作用同样赋予哲学,要在他所建构的哲学中实现为人们提供精神家园和精神归宿的目的。而他所创思的“天地境界”则是其哲学的这种目的和作用的集中体现。在他看来,进入并能常住天地境界的人,即可得到一种精神上的“安身立命之地”。而且,冯友兰自认为其“天地境界”比宗教的境界更高,作用更纯粹。他说:“若有些宗教家,办医院,‘行善事’,不为求自己名利,亦不是专为社会服务,而是为神或上帝服务,为对于神或上帝底尽职。若他的目的真是如此,而又纯是如此,则他的行为,即是宗教底行为,他的境界,即近乎此所谓天地境界。……人由宗教所得底境界,只是近乎此所谓天地境界。严格地说,其境界还是道德境界。”[4]564正是在这种对比的意义上,他还认为:“天地境界是人的最高的‘安身立命之地’”[7]226。
那么,在“天地境界”中得到的精神上的“安身立命之地”,是一种怎样的精神状态呢?
首先,它表现为人生天地间的终极责任和终极归宿的一种自觉和体验。“天地境界”在天人关系上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天、宇宙、大全的人格性、神秘性、彼岸性等,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人在觉解天、宇宙、大全的基础上而有的对其在天、宇宙中所负责任和归宿的内心自觉和体验。在冯友兰看来,“天地境界”中的人,不仅自觉到自己是社会的一分子,是社会的民,自觉为社会做事,为社会尽伦尽职,而且自觉到自己同时是宇宙(天、大全)的一分子,是宇宙的“天民”,承担着为宇宙做事、为宇宙尽伦尽职的“天职”,应当对宇宙有所贡献,并由此体验到在宇宙层面上的心灵归宿。由于冯友兰所称的宇宙、天、大全是同时包含现实世界和“理世界”的完全之体,而其“理世界”的每一个“理”又都是先于物而有且能通过“气”而得以实现的存在(所谓“有理必有气”[5]129),故而“天地境界”中的人自觉和体验到的那种责任和归宿无疑都具有超越现世的终极意义。
其次,“天地境界”中的人,在精神上破除了生死羁绊。在冯友兰看来,“天地境界”中的人对宇宙、天、大全的觉解达到了知天、事天、乐天、同天的境界,而大全是无时间、无古今、无生死的,因此,知天、同天(即自同于大全)的人自然能顺物而化,自然也就无古无今、不生不死了,从而在精神上彻底破除了死亡对他的威胁。他说:“大全是无古今底……大全是不死不生底,因为大全不能没有,所以无死。大全亦不是于某一时始有,所以无生。大全是如此,所以与大全为一底人,亦无古今,不死不生。”[5]54这样,“天地境界”的人就在精神上最终破除了生死。而破除生死则是宗教特别是佛教禅宗修为的最高境界和根本信仰,并被宋明理学引入儒教。在冯友兰看来,张载的《西铭》即表达了儒者破除生死的精神信仰:“……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殁,吾宁也。”
再次,“天地境界”的人表现出一种“富贵不淫贫贱乐”的常乐气象和无畏品格。如果说破除生死只是“天地境界”的人所具有的一般性宗教特征的话,那么常乐、无畏的气象和品格则体现出儒教信仰者的特有本色。自从孟子向儒者心灵注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品格以后,经过后世儒者的阐释和发挥,到宋代被道学家们打造成了富有禅、道色彩的“气象说”。冯友兰则将“气象说”引入他的“新理学”,以表达“天地境界”中的人的精神气象和品格。在冯友兰看来,程颢的道学名诗《秋日偶成》即集中表达了道学气象和“天地境界”的人的精神品格:“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自豪雄。”
对宇宙、天、大全有最高一层的完全觉解,可以使人进入“天地境界”;而常住“天地境界”即可得到一种精神上的“安身立命之地”。那么,如何才能常住“天地境界”呢?在冯友兰看来,要常住“天地境界”,不能仅仅依靠哲学的“觉解”,而是另需要一种精神践履和修为的工夫,即所谓“须对如此底哲学的觉解‘以诚敬存之’”[4]592。这就是冯友兰强调的“居敬”修养理论。而这一理论是直接继承宋明道学的。在精神践履和修养方面,道学家的程朱一派和陆王一派两者的理论和方法虽有差异,但在用“敬”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这就是道学家的“共相”,也是宋明道学、宗教理论及冯友兰“新理学”的“共相”,而为一般意义的哲学理论所不具备。正是这种精神践履与修养理论,赋予了宋明道学和冯友兰“天地境界”以更加鲜明的宗教特色。
四、“命”、“运”观念新诠释
在冯友兰看来,“天地境界”的人,不仅要对天、宇宙、大全有最高的完全觉解,不仅在自己的心灵深处有一种超越现世的终极归宿感并对天、宇宙、大全始终存一种诚敬之心,而且还要对个体人自身的命运有一种符合大全的认识并抱一种超然的态度。而对天命、命运的信奉和尊崇,无疑是宗教特别是儒教的又一明显特征。
儒教的天命、命运观念,较早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孔子即多次谈到“天命”、“命”。他说:“五十而知天命。”[8]12“获罪于天,无所祷也。”[8]27“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8]157孟子也对“天命”、“命”作过专门论述,尤其是对尽人事、任天命作出过理论上的区分。孟子把“命”定义为“莫之致而至者”[9]。并说:“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10]先秦儒家对“天命”、“命”的论述尽管不能即被视为儒教,但是这些论述无疑体现了明显的宗教思想,且实际上成为后来儒教的先声。
到了汉代,伴随董仲舒在阴阳五行宇宙理论的基础上构造出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神学理论,汉武帝也将儒家学说最终上升为举朝尊奉的国教——儒教。在此儒教神学理论中,不仅社会变迁、朝代更替都是上帝、神明意志决定的固有宿命,而且社会个体的人生命运也都是出于上帝、神明的意志安排。从此,天意、天命、命运的观念普及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成为社会上普遍性的信仰,谶纬、占卜、算命也成为一种流行的行业。
由于时代的变迁,20 世纪的冯友兰不像古人那样把命运理解为上帝、神明意志的安排或者阴阳五行的预定,而是从“理”、“大全”的角度,对“命”、“运”概念作出新的诠释。冯友兰把命运解释为意外之所遇、无意中的遭遇、努力而不能战胜的遭遇,其中“命”是一生中的意外之遇,“运”是某一时的意外之遇。他说:“因将来之事之不可测,人常遇意料不到之事,即所谓意外者。因过去之事之不可变,人所遇之意外,虽系意外,而亦不可磨灭,不可改变。人所遇之意外,有对于其自己有利者,有对于其自己有害者。遇有利底意外,是一人之幸;遇有害底意外,是一人之不幸。一人之幸不幸,就一时说,是一人之运;就一生说,是一人之命。”[4]175又说:“不管将来或过去有无意外,或意外之幸不幸,只用力以做其所欲做之事,此之谓以力胜命。不管将来或过去之有无意外,或意外之幸不幸,而只用力以做其所应做之事,此之谓以义制命。如此则不因将来成功之不能定而忧疑,亦不因过去失败之不可变而悔尤。能如此谓之知命。”[4]176
冯友兰不是从上帝、神明的角度也不是从阴阳五行的角度去解释和论证人生命运,而是从日常生活的现象即人生际遇的角度去说明人生的命和运,似乎排除了宗教的因素。但是,肯认人生中不可知、不可测且不可战胜的意外遭遇的现实存在及其对人生幸与不幸的现实影响,这实际上也就从理论上肯认了命运的神秘性及其对人生祸福的主宰性。在人的认识把握之外而又确信其存在的神秘对象,显然不是科学认识的对象,也不是哲学思辨的对象,而只能是宗教信仰的对象。而且,如果把冯友兰的命运学说与其所论述的天、宇宙、大全的人格性、神秘性、彼岸性等联系起来考察的话,其命运学说的宗教内质将更加明显。因此,冯友兰对命运观念的新诠释,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为儒教的天命、命运等观念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论证。
那么,“天地境界”的人,又应当如何对待命运呢?在冯友兰“新理学”体系中,与“知天”相呼应,“天地境界”中的人应当“知命”,也就是了解命、运的意义并做到“以力胜命”、“以义制命”。而按照“新理学”的逻辑,“知命”的最高层次自然应当是“同命”,即自同于命运。自同于命运也即是同天境界的人“自同于大全”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所谓命运不外也就是大全中的一部分。
在冯友兰看来,对于自同于命运的人来说,一切都是顺理顺道,不存在逆境或不幸的问题,因为他已经可以从最高的终极存在“天”的观点来看命运了。他说:“从天的观点看,境无所谓顺逆。从天的观点看,任何事物,都是宇宙大全的一部分,都是理的例证。任何变化,都是道体的一部分。任何事物,任何变化,都是顺理顺道。从此观点看,则任何事物,任何变化,都是顺而非逆。在天地境界中底人知天,知天则能从天的观点,以看事物。能如此看事物,则知境无所谓逆。”[4]609正因为“天地境界”中的人作为冯友兰所定义的标准的“哲学的”人已经不存在逆境和不幸,对于他来说,有的只是幸、顺理、顺道,所以冯友兰声称:“人不一定应当是宗教的,但是他一定应当是哲学的。他一旦是哲学的,他也就有了正是宗教的洪福。”[1]9可见,与佛教《金刚经》宣扬真理即福报和基督教《圣经》宣扬真理即道路、生命一样,冯友兰在其“新理学”体系中亦宣扬完全觉解“天”、“宇宙”、“大全”之理并从而自同于大全、自同于命运的人,可以获得富有宗教神秘色彩的“宗教的洪福”。而追求太平福祉、宗教洪福,正是儒教作为宗教的基本信条之一。
五、结 语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释道三教当中,儒教源头之久远,流布之广泛,理论之普及,足可与其他二教相媲美。当历史进行到20 世纪的时候,东方儒教的昊天上帝已经无力与西方的耶稣上帝抗衡,而西方的教会势力本身又已日益衰微,在此背景下,以“阐旧邦而辅新命”、“为万世开太平”为人生使命的冯友兰,站在哲学的立场上,褒扬哲学,贬抑宗教,力图构建一套顺应时代要求、符合时代精神的哲学体系,以之作为新时期华夏兆民据以“安身立命”的精神依托。然而,吊诡的是,冯友兰毕生精心编织的“新理学”体系,特别是作为该体系最后归宿的“天地境界”,却体现出鲜明的宗教特征。这大概是冯友兰自己始料未及的。
诚如冯友兰自己所言,他的哲学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而宋明理学则是上承孔孟儒家道统的。对于儒学是不是宗教、宋明理学是不是儒教的问题,在中国当代哲学史上曾经引起较大争论。而当人们把目光投向作为中国现代新儒家的开山人物之一的冯友兰及其“新理学”体系的时候,可以发现,“接着”宋明理学讲的冯友兰的“新理学”讲到最后,讲到“天地境界”的时候,却情不自禁地走进了宗教的归宿。冯友兰“天地境界”的明显的宗教特征和最后的宗教归宿,有理由让人们将其归入宗教一系的儒教,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新时期儒教发展的新形式。
[1]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六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2]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十四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951.
[3]任继愈.论儒教的形成[M]∥任继愈.儒教问题争论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
[4]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四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5]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五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6]马克思.根据《约翰福音》第15 章第1 至14 节论信徒同基督结合为一体,这种结合的原因和实质,它的绝对必要性和作用[G]∥唐晓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宗教.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588.
[7]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一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8]杨伯峻. 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9]杨伯峻.孟子译注:上[M].北京:中华书局,1960:222.
[10]杨伯峻.孟子译注:下[M].北京:中华书局,196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