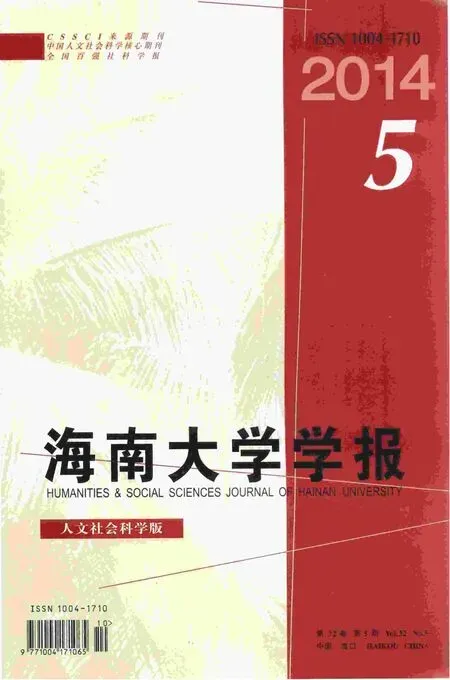形而上学与理性哲学——康德及其前后的形而上学维度
程志敏
(西南政法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重庆401120)
康德给自己设定的任务是:拯救已经陷入“无休无止争吵的战场”(Aviii)[1]3的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延伸到康德的时候已经破败不堪,并因其走向独断论而无人问津,令康德有赫卡柏之叹。但康德认为,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反倒要让形而上学重放光芒。康德凭借“不可抗拒的必然性法则”语重心长地劝诫道:“人类精神一劳永逸地放弃形而上学研究,这是一种因噎废食的办法,这种办法是不能采取的。实际上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有形而上学;不仅如此,每人,尤其是每个善于思考的人,都要有形而上学,而且由于缺少一个公认的标准,每人都要随心所欲地塑造他自己类型的形而上学。”[2]
“批判哲学在很多方面都是一种‘很深的’柏拉图主义”[3],不管人们如何理解这种“形而上学”,它的确是柏拉图主义。康德自认为比柏拉图更理解柏拉图,恰好表明康德似乎已经越过了柏拉图为哲学设定的界限,走上了过分形而上学的道路。
一
在康德看来,“形而上学是如何可能的”这个问题甚至不是一个理论上的大问题,反而是一个“验证人们的目光是否敏锐”的试金石[1]4,因为形而上学乃是人的本质属性,根本不值得剖开来讨论。世界上一直有某种形而上学存在,而且这个世界还将继续存在形而上学[1]31,因为“形而上学也是人类理性的一切教养的完成;形而上学是不可或缺的,即使人们把它作为科学对某些确定的目的之影响搁置一旁。因为它是按照理性甚至必然作为一些科学的可能性和一切科学的应用基础的那些要素和准则来考察理性的。至于它作为纯然的思辨不是用于扩展知识,而是用于防止错误,这无损于它的价值,而毋宁说赋予它尊严和威望,因为审查保障着科学共同体的普遍秩序与和谐乃至幸福,并防止其勇敢且有益的探究远离重要的目的,即普遍的幸福”[1]550。与亚里士多德一样,康德也把形而上学这门至高无上的学问视为幸福的保证、甚至幸福的源泉。
在拯救形而上学的过程中,康德把形而上学变成了一种真正的科学,同时也就把神秘主义从哲学中消解掉了[3]185。
形而上学是“纯粹理性的思辨科学”,不仅整体上必须是科学,形而上学的每一个部分也必须是科学[3]168。只要理性扩展到了思辨,就将永远存在形而上学。康德用一种形象的比喻来说明理性和形而上学的关系:“我们的理性,像生了自己的珍爱的子女一样,生了形而上学;而形而上学的产生,同世界上其他任何东西一样,不应该看做是出于偶然,而应该看做是为了重大目的而明智地组织出来的一个原始萌芽。因为形而上学有其不同于其他任何科学的基本特点,即它是自然界本身建立在我们心里的东西,我们决不能把它视为一个信手拈来的产物,或者是经验进展中的一种偶然的扩大。”[3]142-143形而上学与理性一样,内在于人的精神之中,甚至就是人的一种高级“本能”,对康德来说,人天生就是形而上学的动物(inherentlymetaphysical animal),有着“持续的形而上学的不安”[4]。
康德科学的形而上学能够让理性得到持久的满足,即彻底让理性实现理性化,从而完成形而上学的最后构建,以至于后人在形而上学的问题上不再有事情可做,在康德那里,“没有任何一个形而上学问题在这里没有得到解决”[1]6。从根本上说,经验之外的知识不能来自于外在的存在物,而只能来自于人的理性。于是,“理性”就成了整个近代哲学争相诉诸的最后原则,直至整个世界都内化成了理性的产物,或者反过来说,“理性”成了新的“造物主”或“上帝”。
二
理性取代传统宗教中的上帝,成为新的造物主,这个过程始于笛卡尔,尽管亚里士多德早就开辟并指明了这条道路。
笛卡尔之所以极力贬低传统,无非是为(纯粹)“理性”清除路障,即“清理和平整杂草丛生的地基”[1]9,或者说他(以及康德)埋葬传统,就是为了“吹尽黄沙”,甚至把传统夯实为思辨大厦的地基,或者把传统当做是新建筑的牺牲或祭品。笛卡尔“只听信自己理性提供的明证”[5]48,他不认为这种单纯的理性主义会“危害宗教、危害国家”[5]48,而这种唯理主义本身就与宗教针锋相对,甚至与国家的利益也多有冲突。在笛卡尔看来,“理性的光芒”是不容置疑的和终极的,因而直观乃是最可靠的认识手段,不能再往理性的纯粹光芒上面画蛇添足地增加什么东西了,归根结底即在于“一切科学只不过是人类的智慧,而人类智慧从来是独一的、仅仅相似于它自己的,不管它施用于这样不同的对象”[6],人的理性乃是万物的决定性因素。于是,在这种怀疑和批判之中看到了个人意识的自我膨胀:笛卡尔的《谈谈方法》和《第一哲学沉思集》恰好都是6个部分(上帝创世用了6天),这也许不是巧合,而是笛卡尔的“理性创世记”,笛卡尔似乎把自己比作了人类思想界的“上帝”。
之后的康德,在哲学上把理性推上了思想的巅峰。理性的登基是“时代成熟的判断力的结果”,这种“自我认识的工作”目的是保障理性,任何事情都需要按照理性永恒的和不变的法则来处理。如此一来,理性变成了法官,也成为了必然规律的“制定者”。康德有一段谈到“理性”地位的话被人反复引用的,在此值得再次重复他这段让人类的理性走向极度辉煌的宣言:
理性只洞察它自己根据自己的规划产生的东西,它必须以自己按照不变的规律进行判断的原则走在前面,强迫自然回答自己的问题,必须不让自己仿佛是被自然独自用襻带牵着走。……理性必须一手执其原则,……另一手执它按照其原则设想出来的实验走向自然,虽然是为了受教于自然,但却不是以一个学生的身份让自己背诵老师希望的一切,而是以一个受任命的法官的身份迫使证人们回答自己向他们提出的问题。[1]12-13
康德的先验哲学有一个基本的预设,即人类的先天认知形式和范畴都无法用来认识物自体,人只能认识经过先天认知形式整理过后的经验,而这些先天认知形式和先天认知范畴乃是理性的内容,因而,人们认识的东西实际上是理性预先置入现象之中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然的规律,其实就是理性设置的,此即“人为自然立法”之说。
既然理性有着如此高的地位,当然不会被自然牵着鼻子走,相反地它要拷问自然,逼迫自然回答自己的问题。康德之所以把自己的哲学叫做先验哲学,就在于它是“一个纯粹理性原则的体系,这体系揭示出自我意识的知性中普遍的和必然的成分,而不去处理对象,也不研究什么是普遍性和必然性”[7],这种研究固然是“超越的”,却由于过分超越而流于形式化。但这种抽象的理性却是知识能够成立的必要条件,而人们所能够看到的自然也是经理性加工整理过的,理性因而就是自然规律的法官,甚至就是自然的创立者。
除了本身又是每一个都在其中有发言权的普遍人类理性之外,人类理性将不承认任何别的法官;而既然我们的状态能够获得的一切改进都必须来自这种普遍的人类理性,所以这样一种权利就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1]498
黑格尔后来把“笛卡尔—康德”的理性哲学推到了新的无以复加的高度——这种理性是世界的灵魂,理性居于世界之中,理性构成世界内在的、固有的、深邃的本性,换言之,理性是世界的共性。
“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思考的认识在哲学中证明:“理性”——我们这里就用这个名词,无须查究宇宙对于上帝的关系——就是实体,也就是无限的权力。它自己底无限的素质,做着它所创始的一切自然的和精神生活的基础,还有那无限的形式推动着这种“内容”。一方面,“理性”是宇宙的实体,就是说,由于“理性”和在“理性”之中,一切现实才能存在和生存。另一方面,“理性”是宇宙的无限的权力,就是说,“理性”并不是毫无能为,并不是仅仅产生一个理想、一种责任,虚悬于现实的范围以外,无人知道的地方,并不是仅仅产生一种在某些人类的头脑中的单独的和抽象的东西。“理性”是万物的无限的内容,是万物的精华和真相。[8]
到了这种程度,理性的本质和地位本来已经超出了言辞所能表达的范围,但黑格尔就这样让人清晰地见识了理性这个“概念物自体”。至此,精神世界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哲学创立了一个永恒的上帝之国,圣灵继续生存在哲学的信众中,哲学的信众代替祭司阶层来照料真理。”[9]
三
对理性的研究和弘扬不是什么新鲜事——哲学本来就是理性的产物,或者如康德所说,理性像生孩子一样诞下了形而上学。且不说古希腊哲学大师对理性多有褒奖,就连伊索克拉底这样的非哲学家都有精辟的论述——
我们所有其他特征都和动物无异,实际上在速度、力量和其他一些方面我们不如许多动物。但是一旦我们获得了相互说服、向我们表明自己的愿望的力量,我们就脱离了野蛮,走到一起,建立了城邦,制定了法律,发明了技术。理性话语是我们所有发明的基础。它给予了我们给予正义和非正义、可耻和可敬的法律。……通过理性话语我们教导未经开化的人和考验富有智慧的人。……理性话语是所有行为和思想的指导,并且最明智的人最经常使用它,胆敢侮辱老师和哲学家的人应该像亵渎神明的人一样受到憎恨。[10]
这里的“理性话语”即逻各斯(logos),含义非常丰富,但后来的“理性”却变得越来越狭窄了。对此海德格尔说,灾难性的转折点在于把logos翻译成拉丁语的ratio,而ratio原先是古罗马早期的商业词汇。无论如何,过分甚至畸形地拔高理性,并由这种顶端高处把理性的范围缩小到认识论领域,试图由此演绎出整个世界图景,就难免堕入荒唐。
理性的纯粹性在于其自洽性,即不借助外来物,只在自己内部推演生成。康德还把这种纯粹性等同于先天性:“为了可靠地先天知道某种东西,除了从他根据自己的概念自己置于事物之中的东西必然得出的结果之外,不必给事物附加任何东西”[1]12,由此亦可得出“人为自然立法”的宏大结论——即认为自然的规律不过是人的理性早就设定好的。然而,哲学如果只研究“理性从自身创造的东西”[1]9,虽然可能极大地提高人的理性的能力,并由此提高人的主体地位,但从整全的角度看,这种研究无论如何都像人类的自说自话,这种自产自销式的自卖自夸,其实更像理性的监守自盗和自吹自擂。纯粹主观主义的哲学由于缺乏外界的参与、沟通和监督,总有些痴人说梦的意味。
理性所理解的东西本身就是理性预先置入的,当然不存在理解上的问题,这就是认识论“得以可能”的秘密所在。这种“认识论的循环”本身既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也不会产生多大的坏处,最多让人觉得是人类理性的一厢情愿而已。但由此进一步,认为理性产生万物,即便仅仅是哲学的推理,也让人觉得最理性的理性一定是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发疯了。“纯粹的存在”作为黑格尔整个思想体系的起点,其实就是“纯粹的思想”,也就是“纯粹的理性”,在黑格尔看来,世界的构成源于此——正是这个起点的逐渐演绎外化成为万事万物。也就是说,黑格尔的理性哲学主张用逻辑去还原和生成存在。对于存在本身而言,这无异于本末倒置。
其实,黑格尔自己也清楚,形而上学虽然被尊奉为“科学的女王”,但归根结底不过是一种知识,“形而上学是纯粹的、理性的、关于存在物‘一般’和存在物的主要领域中各个整体的知识”[11]。康德自己都说,理性本质上不过是“全部高级认识能力”,也就是说,康德的“理性”比古代的“理性”更狭隘,主要限于认识领域(实践理性也是如此)。黑格尔把哲学的目标界定为“认识真理”,其本质无非“思维考察”[12]。但这种考察怎能在真正的意义上进入“世界”,遑论产生出世界了。胡塞尔的先验主义本身也不过是在为理性哲学的认识论本质寻找更为深刻和可靠的基础而已,即便他后期努力向生活世界回归,终究没有能够摆脱狭隘的知识立场。“笛卡尔—康德—黑格尔—胡塞尔”的哲学路线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先验”,但实质上却都是某种形式的心理主义,他们把哲学从古代的客观主义转变为主观主义,不过是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而已。
四
就理性而言,“在康德的法庭上,理性担当的角色不少于五种。它既是被告,也是起诉人和辩护人,而且首先是法官,此外它还是颁布法官据以判案的法律本身”[13]。理性身兼这样多的角色,看起来像对人类理性的弘扬,实际上可能是对理性的亵渎。原告、被告、辩护人、法官以及法律,都由“理性”承担了,这种法庭还有什么公正性可言?不过是哲学的闹剧而已。理性固然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相当崇高的地位,但如此多的身份集于一身,显然比古代暴君自封的头衔还要多、还要荒唐。这种思想的极端情况,比专制社会中对人的控制更为严苛,实际上所欲实现的是理性的专制。哲学发展到这步田地,已经不是单单一个“变本加厉”一语可以形容了。
理性的失位来自于阐发者创制的无度和失控,故后来理性信仰的全面崩溃,不是来自于外力的挤压,而是由于理性过度膨胀之后的自我爆炸——自我解构,这个过程不是因为“康德之后的形而上学”,而是始于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及其古希腊的先驱亚里士多德。作为理性主义发展最高峰的胡塞尔也愿意承认,“作为启蒙运动时期的理性主义的那种理性的发展形态乃是误入歧途,尽管这毕竟是一种可以理解的误入歧途。”[14]这样疯狂的理性的确已误入歧途,这种失误似乎也的确“可以理解”——但且不说是否可以原谅,至少不能以一句“可以理解”就完事不管了。
从本质上说,近代形而上学化的哲学运动实际上不过与古希腊的智术师运动一样,是一种新的启蒙运动而已,只不过“思想更成熟丰满、种类更丰富多彩、内容更深刻,因而矛盾也就更加尖锐”[15]600-601。的确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在古希腊智术师运动与近代形而上学化之间,“整个倾向、思维对象和观点以及哲学研究成果,在这时间相距辽远、文化背景又如此悬殊的两个时代里,却表现出富有教育意义的相同性和亲缘关系。在两个时代里,占统治地位的是:同样的对主体内在本性的反省,同样的带着怀疑的厌恶心情扬弃形而上学无谓的苦思冥想,同样的喜欢从经验的发展观点来考虑人类的精神生活,同样的对科学知识的可能性和极限性的探索,同样的对社会生活问题的讨论的人情关注。”[15]600-601正如这些颇具慧眼的哲学史家所见,这场被人顶礼膜拜的哲学造神运动,与备受诟病的古希腊智术师运动一样,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所有激动人心的煽动和美丽的许诺,都不过是智术师们的伎俩。
归根结底,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如果不可能有所改变、有所发现和增益,哲学也就没有必要再追求什么智慧了:拥有这种能够“认识”乃至“创世”理性的人类本身已经成为了神明,当然拥有至高无上的智慧,还用得着费劲去爱什么智慧吗?
[1]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康德.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M].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163.
[3]罗克莫尔.康德与观念论[M].何向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14.
[4]F.Kerr.After Aquinas:Versions of Thomism[M].Malden: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2:22.
[5]笛卡尔.谈谈方法[M].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3.
[6]笛卡尔.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M].管震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1.
[7]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卷4[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262.
[8]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9.
[9]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M].李秋零,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49.
[10]戴维斯.民主政治与古典希腊[M].黄洋,宋可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68.
[11]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M].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6.
[12]黑格尔.逻辑学[M].梁志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2.
[13]赫费.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现代哲学的基石[M].郭大为,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6.
[14]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M].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93.
[15]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M].罗达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