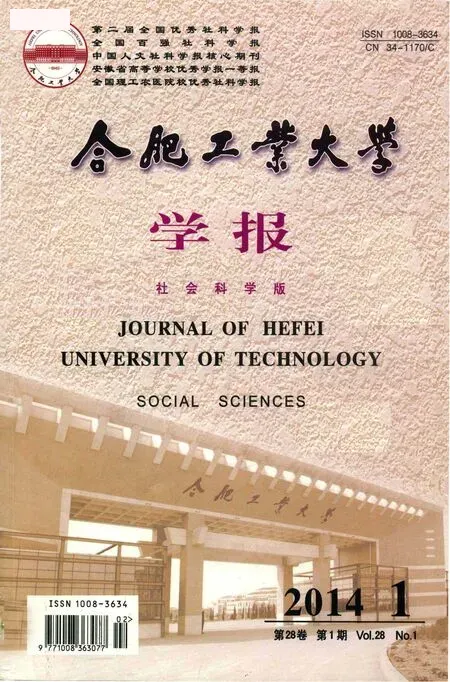跨文化语境中的《古韵》
沈 忱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40)
20世纪初,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西方的艺术思想和创作技巧开始被引入中国现代文学实践活动中,而一些作家的英文译介和创作也让中国文学开始进入西方视野。京派文学的不少作家都在这一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其中凌叔华是20世纪初在英语世界进行创作并获得世界声誉的为数不多的中国人之一。《古韵》是凌叔华1938年至1952年间陆续创作完成的,在中国和英国两地用英文写就。这部作品由多个短篇故事连缀而成,取材自作者的童年生活。大多数传记作家和学者都将这部作品视为凌叔华的自传,但是真实故事在自传中有多处改动和虚构的成分。这部作品作为凌叔华为数不多的英文作品,和唯一的自传文字,向来被很多学者关注。
凌叔华一生和英国布鲁姆斯伯里交流甚多,西方文化对她的文艺创作和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而凌叔华作为一名欲在西方世界发出声音的中国女性,其双重身份也备受关注。由于作者的独特身份,以及这部作品创作过程所涉及的跨文化语境,学者常将《古韵》置于后殖民理论中下加以阐释。如史书美认为,凌叔华的写作是后殖民主义霸权压迫的结果。而另一些学者,如帕特里卡·劳伦斯,则认为凌叔华的写作是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完成的,并不包含霸权与屈从。我们不可否认《古韵》的写作过程中帝国主义的权力关系的介入,但同样不可忽视东方自我表述的冲动。德里克指出,“东方主义”是出于西方对东方的文化霸权,但在这一过程中,东方也不是完全沉默的他者。东方为了争取世界地位的民族话语的策略是“自我东方主义”[1]96-118。“自我东方主义”相对“东方主义”来说更隐蔽,东方为了在西方世界赢得话语权,不得不作出迎合的姿态,而主动表述自我。对《古韵》创作之由、文本策略、性别意识等进行分析,可以考察出其所反映的自我表述冲动。
一、从东方到西方
凌叔华1945年从中国迁居英国,她的写作经历了从东方到西方两种不同文化空间的跨越。实际上,跨国交流在此前就开始了。凌叔华去英国之前,就和英国的弗吉利亚·伍尔夫等布鲁姆斯伯里成员通信,她在此时萌发了写作《古韵》的冲动。中英两种异质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不仅促成了《古韵》的写作,该书后来在英国的出版和走红的过程,也无不是异质文化相互吸引、相互诉求所产生的结果。如果将两种文化放在殖民与被殖民的结构中,英国文化作为殖民主体,自然对被殖民主体起到引导、吸引的作用,然而被殖民主体的自觉应对也是不容忽视的方面。在这里,东方已不是萨义德所说的沉默的“被表述者”,而是有强烈欲望的表述者。
从《古韵》的创作动机看,凌叔华一方面是不满西方作家对东方的不实描述,而产生向西方世界表达中国文化的强烈欲望。当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赛珍珠的《大地》在英美读者中流行[2]217。凌叔华认为这部作品是西方人的偏见,她期望写出真实的中国生活,并希望向西方世界传递真实的中国文化,这反映了东方人想要表述自我的心理已在凌叔华的心中萌芽。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凌叔华想借此机会摆脱国内战争的阴影,这一点从这段时间作者与弗吉利亚·伍尔夫通信中可以看出。凌叔华和弗吉利亚·伍尔夫的通信始于1938年,在第一封信中,凌叔华就说“除了打仗的灾难,我还有内心深处的伤痛,永远挥之不去。”[3]376当时中国正处在日本侵华的战争阴影下,而英国同样处在战争的紧张气氛中,伍尔夫鼓励凌叔华通过工作、创作来忘记现实中的痛苦。“想一下如何才能集中精力去做那些值得去做的事情。我还没有看过你写的东西,但是朱利安在信中经常提到。他也说到了你过着极有趣的生活”(1938年4月5日)[3]385。凌叔华也的确开始通过写自己童年生活的来排解战争的痛苦,写完一章即寄给伍尔夫,直到1941年伍尔夫投河自尽,凌叔华的自传写作也因之而中断。
由于这部作品是用英文写作,伍尔夫在致凌叔华的信件中便不断地给以鼓励。从有些论者的观点看,这种鼓励和引导对作品的创作起了或压迫或主导的影响。史书美认为这是伍尔夫“欧洲中心论”的表现,她认为伍尔夫建议凌叔华用英文创作,带有语言和读者的阶级观念:英语即使不是优越的写作语言,至少是真正的创作语言,西方读者是唯一值得为之写作的读者群体[4]。魏淑凌也同样认为,伍尔夫鼓励凌叔华用英文写一部自传,这表明她在文化上不无偏见[5]231。在这里,我们不能断定伍尔夫指导凌叔华写作是否仅仅基于对女性作家的同情与关怀,其中又是否掺杂帝国主义情愫,但从被殖民主体的角度来看这段文化交流,容易忽视被殖民主体本身的追求。帕特里卡·劳伦斯认为,伍尔夫不是基于欧洲中心论的观点来强迫凌叔华迎合西方读者,反而是作为一个师者引导凌叔华的英文写作。而凌叔华则是在历史时机中无法在自己文化和文学中找到表达的渠道,于是转向其他文化和文学去寻找[3]379-383。劳伦斯注意到《古韵》的创作也是凌叔华个人的艺术追求。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正处在民族危难之际,救亡是时代的主题,个体自我的表达不是当时文坛和读者所关注的中心。所以,凌叔华用英文写作,第一次尝试自传体小说,这无不是西方艺术赋予她的灵感。凌叔华个人的艺术追求让她有反叛的冲动,而伍尔夫的鼓励则推波助澜。
凌叔华在中国的写作时期,其与西方的交流主要表现在书信方面,写作也主要是为了摆脱战争的痛苦,这最初的冲动尚属萌芽。在迁居英国之后,凌叔华希望在西方世界发声的欲望更加强烈,而西方世界也在陌生的中国文化中寻得理想的庇护所。
在陌生的文化环境,凌叔华做了一系列努力来唤起英国人对东方文化的注意。1949年,凌叔华在纽邦德大街亚当斯画廊举办画展,她用中国人的眼睛去看欧洲风景,用中国画的技法去表现欧洲风景,这些风景画在展出期间获得了很多关注。她的画给英国观众带来熟悉环境的疏离感,她凭借这样独特的美学风格获得了西方艺术界的认可[5]251。
在文学创作上,凌叔华也是通过用英文表现中国情调来寻求西方世界的认可。她到了英国之后积极与布鲁姆斯伯里群体的成员保持联系,在维塔·塞克威尔·维斯特和伦纳德·伍尔夫的帮助下,终于完成并出版了《古韵》。凌叔华通过截取多个童年生活片段,用英文向西方读者展现东方文化,这一方面是基于生活与生存的考虑,另一方面也出于自己的文化立场。“我希望我能写一本书,很好地表现中国和中国人。西方有许多关于中国的书,大部分都是来满足西方人的好奇心的。那些作者有时全凭想象挖空心思地区编造有关中国人的故事。他们对读者的态度是不真诚的。于是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人看上去总有点不人不鬼的”(1952年7月6日)[3]418。她希望西方世界的英国人民能看到真实的中国人的生活,让他们发现这些中国人和英国人一样,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
《古韵》的创作出版过程,是中西方文化互相交织、互相影响的过程,这其中既有中国文人在西方世界表达自我的愿望,又有西方读者对异域文化的想象和诉求,东西方文化的扞格与共谋交织其中。
二、表达的迎合
有了表达的欲望,则要选择合适的方式进行表达。地理空间的跨越直接导致的是语言的转变,要在西方世界表述自己,并能被听见,只能用西方世界的通行语言。这不仅是殖民文化强迫植入,而且是被殖民者的文化策略,被殖民者试图以此获得在西方世界说话的机会。这在《古韵》写作中,就体现在用英语进行写作,并选择符合西方读者想象的题材和内容。
凌叔华选择用英语进行创作一方面是在中文处于失语状态的西方世界进行沟通的必须,更在于通过生涩的第二语言表达本国传统能给西方带来陌生感。凌叔华一开始用英文进行自传写作时并不得心应手,也害怕用英语表达损害了原有的中文意思,会使文意失去原有的美妙意境。但是伍尔夫却鼓励她继续写下去,并认为直接把汉语译成带有汉语表达习惯的英文,“与众不同、美丽非凡。发现一种陌生而诗意的微笑。”[3]416伍尔夫珍视这种生疏的语言表达传达的陌生感。
凌叔华的《古韵》在题材选择和写作手法上也与国内时期的创作有所不同。凌叔华在国内的写作分两个阶段:前期多写女性生活小说,后期多写儿童视角小说。凌叔华在其前期的女性小说如《酒后》《秀枕》《花之寺》等篇中,多写闺秀女子的家庭生活,表达她对女性生活的关注,但也不乏温婉的嘲讽,她看到了时代转型时期女性思想的落后和缺陷。后期小说则更多以儿童为主角,如《小哥儿俩》《小英》等,模拟正常儿童心态,写他们的童趣、委屈和寂寞,用孩子的心灵感受世界。无论是前期小说还是后期小说,凌叔华都秉持京派的创作理念,以人性观念来观照人物,笔触细腻精致,其作品全部为短篇小说,简洁隽永。《古韵》同样继承了凌叔华中文小说创作特点,表现了人性的恒久美好,并以儿童的视角来写。然而为了迎合西方读者,《古韵》又有不同以往的特点。首先,作者为了营造异域情调,在文本中加入了大段介绍性的文字;其次,第一次尝试用自传体写作,而实际上,这是在史实基础上做了改动和虚构的自传。改动和虚构也是作者的写作策略。
凌叔华将这部作品的读者预设为英国读者,在《古韵》中详细记录了中国的家居生活场景、房屋结构和装饰,并对带有中国特色的书法、绘画、音乐等艺术形式做了详尽的介绍,也涉及了中国的科举制度、人情来往等社会内容。这些中国读者人尽皆知的事物,在其中文小说中无需详尽介绍,而在《古韵》中凌叔华却将其来龙去脉一一道来。
如《义父义母》一章,文章开头介绍义父时插入了一段中国文人对琴、棋、书、画的爱好。在后面对义母的介绍中,又花了大量笔墨来写中国的古琴文化。作者先借义母之口介绍了中国古代的音乐故事,将伯牙子期的“高山流水”,嵇康的“广陵散”、陆龟蒙的“醉渔唱晚”三个故事一一叙述,紧接着又详细描写了《流水》和《平沙落雁》,“她教我《平沙落雁》时,给我描绘出一幅秋夜图:月光照着沙滩,微风吹拂,芦苇摇曳,流水潺潺。她说,想想看,群雁在沙滩上嬉戏,冬天来临前,要飞到南方去。它们翱翔在空中,一只大雁掉了队,在秋夜中呼唤着同伴。最后,它们相逢,在美丽的新家沉浸于欢乐之中。”[6]560这样的描写极富诗意,但是没有推进故事发展,叙述每每至此都暂停下来,行文速度舒缓,稍显拖沓。
这样的例子在文中比比皆是,如在《中秋节》一章中对中国式庭院的介绍、《贲先生》一章中对中国书院的介绍、《叔祖》一章对《镜花缘》内容的介绍、《老花匠和他的朋友》中对兰花的介绍、《老师和同学》中对《庄子》的介绍,等等,几乎每一章故事中都有详细的中国风物描写,当然作者也知这样详细描写无助于行文,所以匠心独运凭借孩子无知懵懂的口中说出,因而并不突兀。
作者在叙述中一方面尽可能插入中国传统文化的介绍,另一方面却又增加了不少有违史实的虚构,尤其是涉及人物关系、人物身份的虚构。从陈学勇和魏淑凌结撰的关于凌叔华的传记可以看到,凌叔华对自己的童年生活做了如下改写:凌家在《古韵》中变成了丁家,凌老爷的四房妻妾变成了六房;凌叔华本还有个妹妹,但在《古韵》中的“我”却变成了家中最小的孩子,而真正最小的孩子却变成了老三梅姐;凌叔华的义父义母本是军阀,不识音律,却在《古韵》中化身精通琴棋书画的中国传统文人。
凌叔华的改动引起了很多学者的讨论。《古韵》一直被大多数中外学者视为凌叔华的自传,由于《古韵》先在英语世界发行,大陆有了中译本也是很久以后,除了发表之初英国几位评论家对其传奇色彩和异域情调表现极大的兴趣和大加赞扬之外,在国内也多将其视为记录作者童年生活的自传作品,或作为史料加以引用。而在关于凌叔华的传记作品中,《古韵》的自传性受到了质疑,进而质疑作者的人格。在魏淑凌的《家国梦影》中,《古韵》是被看作自传的,但是作者表示读完后有被欺骗的感觉,里面包含了很多虚构和夸张。在陈学勇的《高门巨族的兰花》中也对《古韵》表示质疑,认为应该将其看作小说而非自传。从作者给伍尔夫的信中可知,《古韵》是按照自传来进行写作的。事实的虚构是作者故意为之的写作技法,也是自传作者自我展示的方法。且不论作品的体裁是自传还是小说,作者的故意为之的虚构和改动,虽然在魏淑凌和陈学勇的传记中可以被视为个人性格的缺陷所导致,但这并不能视为作品本身的缺陷。我们可以视之为在跨文化语境中希望求得西方世界认同而进行自我书写的一种策略。而《古韵》在西方世界的成功也证明这种策略的成功。
再者,萨义德认为,对东方主义文本的分析,应“将重点放在这种作为表述的表述、而不是作为对东方的‘自然’描写的表述。……人们关注的是风格、修辞、置景、叙述技巧、历史社会背景,而不是表述的正确性,也不是其逼真性。”[7]28虽然萨义德强调的是东方学应建立在外在性前提之上,但也提醒我们不必因为文本的虚构而否认其外在权力关系的指涉。
三、女性身份的探索
如果说空间的跨越是跨文化语境的一个维度的话,那么性别的跨越则是另一个维度。凌叔华作为第三世界的女性作家,一方面要面对西方世界对东方世界的霸权,另一方面也要面对男性世界对女性世界的霸权。面向西方,凌叔华不仅代表东方向西方世界自我表述,也代表女性向男性主导的世界进行表述。周蕾曾指出,中国现代女性写作发生的背景,不是中国或者西方传统单方面所决定,而是在中国和西方的对话中产生,它不是个人的,而是超越个人意志的历史因素的影响下产生的[8]xi-xii。考察《古韵》的跨文化性,其空间的跨越是重要方面,性别意识的觉醒也是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女性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凌叔华小说的主题,然而不同于她以往所描述的闺阁女性,《古韵》中她首次将笔触深入旧式家庭的姨太太们的生活,这是自我表述的愿望下对女性自我身份的自觉探索。
凌叔华的中文小说就表现了对女性身份问题的关注。她擅长描写闺阁女性,她们处在新旧时代交替变迁之时,一方面受传统文化熏陶、教育,习惯将自己定位于闺阁生活之中,而新思潮的冲击改变了外面世界,长居闺阁中的女性因此无所适从,她们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绣枕》中的大小姐就是这样的悲剧角色,她自认为能体现她心灵手巧传统美德的绣枕,实际就是她个人命运的寄托。她不能主动追求自己的幸福,就只能被命运所遗弃。也有一些走出闺房,但又未能完全接受现代思想的女性,在传统和现代交替中不知何去何从。比如《吃茶》中的芳影,对殷勤的“外国规矩”会错了意,盲目给自己留下了伤口。这些女性虽然外表现代化,但内心仍恪守传统思想,徘徊在现代和传统之间。凌叔华并没有像同时代的女性作家那样一味地宣扬女性解放,而是在解放和恪守传统之间彷徨。
《古韵》之前的小说对女性意识的探索就像早前埋下的种子,在寻找破土而出的出路。在西方女性意识的影响下,这颗种子发芽了。凌叔华从对闺秀女性婉转的嘲讽到对旧秩序下女性压迫深刻的思考,这样的转变和伍尔夫的影响不无关系。史书美认为,凌叔华的女权意识是西方化的女权主义。帕特里卡·劳伦斯同样肯定了伍尔夫的女性思想对凌叔华的影响。凌叔华曾说非常喜欢伍尔夫的作品,特别是《一间自己的屋子》[3]389。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是一本著名的关于女性主义的论著。伍尔夫在书中呼吁女性争取自己的经济地位,获得自己的生活空间,要在男权社会中获得平等的地位。
在《古韵》里,凌叔华不再写有知识的闺秀小姐,她着墨最多的是大家庭内部姨太太之间的勾心斗角及她们纷繁复杂的思想状态。这些女性之间的家庭竞争都是围绕着一个男性即父亲。尽管六位姨太太都各有个性:三妈算计刻薄、四妈贤惠识大体、五妈刚烈、六妈尖刻,然而始终都臣服于男性,都逃不过悲惨的结局。在旧时代不平等的婚姻中,女性仅仅是男性的附属品,男性漠视女性感情,女性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凌叔华并不止步男女关系的不平等,她也看到在旧式家庭中,女性之间的关系并不和谐。在这个大家庭中,大妈死的早;二妈处心积虑地控制财产,从而控制其他太太;四妈并不关心这些利益,经常扮演调停人的角色;五妈受尽二妈凌辱;六妈被二妈拉拢生子。有时这些姨太太会因为经济利益争吵厮打,也会在脆弱的时候惺惺相惜。高墙中的女性就是随时等待枯萎的花。
尽管要将这样复杂的家庭关系介绍给西方读者,并不一定会获得凌叔华期待的理解;另一方面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如此赤裸裸地展示家庭成员之间的厮杀打斗并不符合京派小说家一贯倡导的温和节制的美学理念。而且凌叔华出身仕官之家,家产丰厚,不会面临经济问题。她的绘画才能被发现后,其父亲也对她着意培养。她本人并不存在要改变不平等境遇的生存诉求。但是,凌叔华还是千方百计去描写旧习俗旧秩序压迫下女性的悲惨境遇,唤醒她们的解放意识。如果说伍尔夫在论著中在为被压迫的女性摇旗呐喊,那么凌叔华也借着童年自传的外衣,直面中国女性的根本问题。当然,为了保持温和,作者对于成年之后的生活都不曾涉及,回忆的文字都笼罩在儿童的天真和感伤中,在朦胧的影子中隐现着敏感锐利的笔锋。
与其说《古韵》是一本自传,不如说是一个符号,它沟通中西两个文化空间,也反映了作为东方女性作家“自我东方主义”的写作策略。《古韵》写作自始至终都将西方人作为接受对象而设置情境,但《古韵》中又承载了作家对古老中国的深情回忆。《古韵》向西方社会宣扬中国文化最优美的那一部分,同时也揭露了中国女性最悲惨的人生境遇,即作者一方面在写作中满足了异国接受者对于古老中国的想象,又基于自己的文化背景对于我们的老中国进行着深刻批判。在后世西方文坛华文作家登场之前,凌叔华可以说比较早地做出了一个可贵的尝试。
[1]Arif Dirlik.Chinese history and the Question of Orientalism[J].History and Theory,Vol.35,No.4,Dec.,1996.
[2]陈学勇.高门巨族的精魂——凌叔华的一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3]帕特里卡·劳伦斯.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M].万江波,韦晓保,陈荣枝,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
[4]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M].何 恬,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5]魏淑凌.家国梦影,凌叔华与凌淑浩[M].张林杰,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
[6]凌叔华.古韵[C]//凌叔华文存.傅光明,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
[7]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艰,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
[8]Chow Rey.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Westand East[M].Published by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