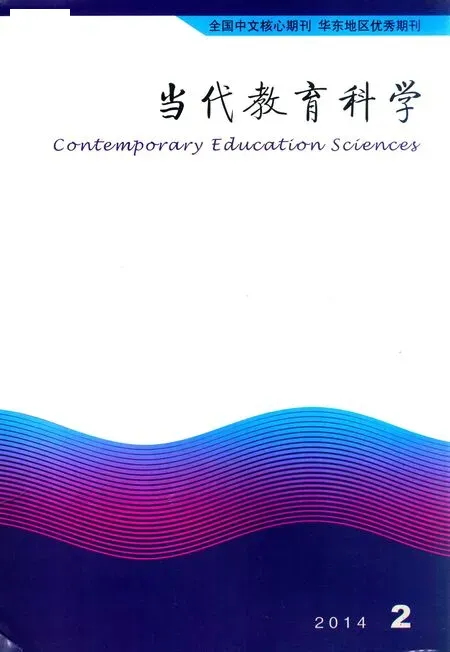论日常教育生活批判
●刘胡权
论日常教育生活批判
●刘胡权
日常教育生活是指教育—学习者在教育活动过程和领域中维持与满足自身教育需要的日常生活过程。日常教育生活较之非日常教育生活更具有“批判性”,日常教育生活批判的目标在于“日常教育生活非日常化”和“非日常教育生活日常化”。这一批判目标的提出,对于人们正确认识日常教育生活与非日常教育生活的关系,对于人们关注与研究日常教育生活,对于教育现代化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与现实价值。
日常教育生活;非日常教育生活;批判;日常化;非日常化
一
日常教育生活,是世纪之交伴随哲学理性位移——“向生活世界回归”而出现的一个新概念。西方一些有远见的思想家们纷纷把理智的触角伸向日常生活这块地方。现象学大师胡塞尔的“日常生活世界”等等。这些理论基础共同指出了生活世界包括日常生活世界与非日常生活世界两个领域。
从日常生活世界与非日常生活世界的理论出发,对于“教育学回归生活世界”,“回归怎样的生活世界?”学者们提出了质疑。有的学者认为教育生活应该分为两种基本形态,即专业教育生活与非专业教育生活。前者是“教育社会成员在教育实践活动领域通过教育专业生活而体验和享受到的社会生活。”后者是“教育——学习者在教育活动和过程中满足普通的或非专业教育需要的日常生活过程。”[1]也有的学者认为教育生活应该是日常生活与制度生活的统一。“前者具有明显的自生性、习惯性和情感性等基本特征,更具有活力,总是试图摆脱社会规范给定的约束;后者具有模式化、稳定的特色,具有思维和理性的色彩,认可制度或规则的理所当然性。”[2]还有的学者认为“日常生活”只涵盖生活世界的一部分,特指生活世界的亚领域,即生活世界中的日常的领域,与之相对的是“非日常中的非日常生活领域”。前者代表个体再生产,后者则构成社会再生产或类的再生产。生活世界中的教育同样也分为日常生活中的教育和非日常生活中的教育,二者在含义、实现机制、基本特征等方面有着不同的本质属性,但又同是“一块金币的两面”。[3]由此可见,教育生活包括两个亚领域,一个是日常教育生活,另一个是非日常教育生活。有的学者也意识到了日常教育生活的批判性,但这些缺乏一种哲学的理论基础,缺乏一种理性的系统分析。“日常教育生活”作为一个在教育学研究中难得一见的词,还刚刚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对日常教育生活进行系统分析,建构日常教育生活的批判理论,理性认识日常教育生活与非日常教育生活的关系,就显得十分必要且具有现实意义。
二
“批判”一词仍需要做出批判,并不是意识形态和政治化的“否定、舍弃、扬弃或抛弃”,其基本含义是“解读或识别、讨论或批注、评价或判断”。[4]从教育哲学意义上讲,“批判”就是使教育生活中的研究对象真实、自在的显现过程,是系统、全面、完整地对研究对象做出理性地显现,呈现研究对象的历史过程与现实影响。本文也正是在此种意义上使用“批判”一词的。日常教育生活何以比非日常教育生活更具有批判性?日常教育生活的批判性点在哪?这只能在日常教育生活与非日常教育生活的对比中显现出来。
日常教育生活与非日常教育生活是根据生活世界包括日常生活世界与非日常生活世界两个亚领域而划分的。“日常教育生活”概念的提出也是根据“日常生活”这一概念而提出的。日常教育生活是与非日常教育生活划分的标准是对象化领域的不同,前者是个体的再生产领域,以自在性为基本特征;后者是社会或类的再生产领域,以自为性为基本特征。二者具有不同的本质规定和结构特征,正是这种不同决定了日常教育生活较之非日常教育生活更具批判性。具体说来:
(一)日常教育生活的本质是自在性,是“人的一种自在性的生活,以人的自生习惯为基础的生活,是在非制度约束情境中的生活。”[5]“自在性”是黑格尔提出的一个概念,是指自身所包含的对立面尚未发展和显露的绝对理念发展阶段,表现为存在本身及其客观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又将其引申为“自发”。日常教育生活中的自在性是指在日常生活过程中教育——学习者所从事的教育活动是自在的、自发的,并不是发自主体自我内部的欲求,而是在自然状态下现实的进行。这些活动并不是直接指向教育目的的,具有一种非自觉的性质。日常教育生活的自在性主要表现在:第一,在思维上,它关注的是“是什么”,而不是“为什么”的“我思”性。日常教育生活是由日常概念、判断与推理所构成的世界图景与思维方式,它缺乏“为什么”的维度,只停留在“是什么”层面上。因为教育生活中日常的概念不具有明确的规定性,反而有强烈的情景性,只有在特定的场景下才能模糊、朦胧理解概念所代表的寓意。日常生活中的概念具有极大的随意性、非自觉性,它只服务于场景,只要交谈的主体双方明白,不造成费解即可,至于概念的外延与内涵的分析,那是学术研究的事,生活就是自在、自由和随心所欲的。日常教育生活中的判断和推理缺乏严密的逻辑性,或者可以这样说,它只遵从日常逻辑,妄图对它进行学理上或形式逻辑的分析注定是失败的。一句简单的谚语只是出于劳动人民经验的长期累积,主要告诫子孙后代不要在此问题上再犯错误,这是它的目的,至于逻辑,或许只有当时场景下即时的经验逻辑,经不起仔细的推敲与反复验证。基于这一点,日常教育生活更关心“是什么”,而缺乏“为什么”的“我思”性。“当人们尚未充分意识到人的活动的意义时,他的活动属于自在的活动,与此相适应,他只是一个自在存在。”[6]日常教育生活中的人们不可能对自己每一行动的教育意义都有充分的意识,他只是作为一个缺乏“我思”的主体参与日常教育活动中,他并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教育主体,这种自然状态下的非理性正是日常教育生活自在性的最好体现。第二,在内在结构上,日常教育生活是由重复性复制机制所构成的,日常教育生活的自在性决定了它的重复性复制机制。教育具有保存——传递传统的功能,日常教育生活更多地承担了这一功能,比非日常教育生活更具有传统性。我们之所以会融入到传统或习惯中去,都是因为在日常教育生活中通过反复地练习逐渐融入的。社会传统或习惯的传承也是依靠在日常生活中无数次重复才得以继承前人的知识。事实上,教育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重复,在日常教育生活中尤其如此。日常教育生活关注“是什么”,而不问“为什么”,知识的习得、习惯的形成、传统的传承,无不靠重复。重复不需要严密的逻辑推理与判断,不需要“我思”,不用问“为什么”,只是“接受”、“非批判性”、“理所当然”。这一复制机制保证了日常教育生活的稳定与延续,保证了日常教育生活自在的存在。日常教育生活自在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凝聚为日常教育生活个体共同的文化心理,这种文化心理又塑造着新的文化个体。日常教育生活的产生及文化心理与个体之间的这种相互传承,就是日常教育生活活动重复性复制机制的实质性。
日常教育生活的自在性、非自觉性是与非日常教育生活的自为性、自觉性相对的。日常教育生活的自在性体现在思维上的“是什么”与非“我思”性;体现在内在结构上的重复性复制机制。与日常教育生活不同,非日常教育生活的自为性、自觉性则体现在思维上的“为什么”与“我思”性;体现在内在结构上的创造性再生机制。二者相比,日常教育生活更具“批判性”。第一,在思维上,“是什么”与非“我思”性的世界图景与思维方式导致了日常教育生活概念的模糊、朦胧与不明确性,导致判断与推理无严密的逻辑性,导致教育主体意识的松懈,导致思维与理性色彩的淡化。第二,在内在结构上,重复性复制机制导致日常教育生活的传统性,导致日常教育生活缺乏鲜活的生机与活力,导致日常教育生活缺乏创造性与自我更新的再生能力。
(二)日常教育生活是以习俗与习惯、常识与经验为调控方式的,而非日常教育生活是以制度为调控手段的。习俗与习惯总是自发的在日常教育生活中起着规范、引导的作用,被称为“自然法”。日常教育生活是习俗与习惯的寓所,超出日常教育生活进入非日常教育生活,只能是制度、理论在起着规范与引导的作用。所以,习俗与习惯调控的范围是有限的。在时效上,习俗与习惯作为民族深层文化心理的凝结,一旦养成,对其持有者的控制总是持久的,这种持久的效用一方面保证了民族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保守性的产生,带来一些问题,如民众日常教育生活中的蒙昧主义与神秘主义。大多数中国人仍没有走出那种弥漫着深厚伦理本位意识和自然经验的日常生活态度。人的生活仍缺乏科学理性精神,对科技及现代教育还没有形成广泛而健康的认可与追求心理。蒙昧主义出于对理论的无知与封闭,而神秘主义则多出于对理论的敌视与拒斥,二者在本质上是互释的,都寓于习俗之中,习俗又寓于日常教育生活中,作为日常教育生活的集中表现,是传统的“统”所在。但是其中不免存在许多消极的陋俗,诸如蒙昧主义与神秘主义。我们生活于传统与习俗之中,生活于日常教育生活之中,虽难以避免,但也应对它有清醒的识别。理性的认识、知性的启蒙、理论的武装,都意味着对习俗的正确态度,既判定其“统”的合法性,又能通过理论的工具理性判定其中的消极成分。理论是指导实践前行的灯塔,制度是保持社会有序化的系统架构,是理论的现实化。制度作为人的理性构思与设定,总还是人制定的,不免存在问题,此外还要受制于社会内的各种因素,又不能摆脱周边社会对它的影响,所以其控制的时间相对短暂,发挥的效用也相对有限。在方式上,习俗与习惯是在“直接生活”过程中形成的,立足于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这种生活方式及观念与基本需求间形成一种“天然”认同。在这种条件下就抑制了人们“自我反思”意识的产生,因为习俗与习惯与个体的关系总是自发的、天然一致的。习俗与习惯源于“直接生活”,关注“直接生活”,在“直接生活”中发挥其作用,所以在方式上是自发的、非自觉的、自然状态下的。而制度超出人们的直接生活范畴,虽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既与社会性生产相联系,又与财产、社会生活需要密切相关。作为一种强制性的社会制度,必须要求社会成员服从。其中设定的规则是不能违反的,制度不具有自在性,不是人的自在性生活,而是一种社会制约性生活。
常识,是直接以经验的共同性为中介和基础的思维方式,它体现了经验主体与世界的直观联系,因为经验具有重复性与非批判性,所以常识以共同经验的历史性遗传形成传统,在本质上是僵化、保守和混沌的。常识具有直接给予性与自在性的特点,只有“是什么”的维度,而缺乏“为什么”的维度。此外还具有简单性与狭隘性的特征。常识的积极作用在于“以实用主义和经济化原则使个体生活经验浓缩化和普通化”,[7]使个体可以“不假思索”地从事日常教育活动,从而实现日常教育生活的简单化和集约化;其消极作用在于阻碍了创造性思维的发展。
日常教育生活就是以习俗与习惯、常识与经验作为调控方式的,而非日常教育生活则是以制度为调整手段的。习俗与习惯的保守性所导致的蒙昧主义与神秘主义值得“批判”;常识与经验的重复性、非批判性所导致的创造性思维的窒息也同样值得反思与重构。
总之,日常教育生活以自在性为本质特征,它决定了日常教育生活的重复性复制机制与自足的封闭静止状态;同时日常教育生活又以习俗与习惯、常识与经验为调控方式。这种本质规定和结构特征决定了日常教育生活的“批判性”。而非日常教育生活与日常教育生活相对,以自为性、自觉性为本质特征,以创造性再生机制为内在结构,以制度为调控手段,在时间上相对流变,空间上呈现开放状态,对比之中,更加凸显了日常教育生活的“批判性”。很显然,日常教育生活确实具有“批判性”,那么,如何进行日常教育生活的批判呢?或者说日常教育生活批判的目标在哪里?
三
日常教育生活与非日常教育生活是教育生活的两个亚领域,它们之间存在着冲突对立。人类的教育就是在日常教育生活与非日常教育生活的冲突对立中找到教育发展的动力并创造新的教育文化的。它们二者之间存在着适当的张力,是一种动态平衡的关系。既然是动态的平衡就需要不断打破和不断重建二者之间的静态平衡。教育的发展也正是在不断更迭、不断创新中获得自己的生命力与活力的。日常教育生活需要超越日常状态进入非日常状态,非日常教育生活又不能完全脱离日常教育生活,也只有在关注和完善日常教育生活基础上才能超越日常教育生活。因此,日常教育生活批判与重建不是简单地“走出”或“回归”的问题,而是实现二者既各得其所,又互渗互动,即日常教育生活的非日常化与非日常教育生活的日常化。
第一,日常教育生活的非日常化,即日常教育生活的自觉化。日常教育生活的本质特征是自在性、非自觉性,这决定了它的内在结构是重复性复制机制;它的思维是“是什么”而非“为什么”的“我思”性;它的内容是传统的;它对事物是不问“为什么”的“接受”,认为其“理所当然”,不具有“批判性”。正是这种“非批判性”的自在特征需要加以“批判”。日常教育生活的缺乏理性与思维,造成了日常教育生活的琐碎与庸常,疲劳而单调与乏味,缺乏生命的质感与气息;造成了对日常教育生活缺乏反思与批判的意识,而只是一味的接受;习俗与习惯以它特有的持久效用顽固地占据着人们的思想意识,长期处于蒙昧与神秘主义之中而缺乏理性光芒的照耀、理论的指导;常识与经验的重复性与非批判性更加埋葬了六轮的践履。“教育即解放”,[8]解放日常教育生活的这种庸常与重复,解放日常教育生活的这种单调、沉闷与保守。如何解放?只能通过日常教育生活自身的自觉性,由自发到自觉,由传统到现代,由重复性复制机制到创造性再生机制,由习俗与习惯的保守走向制度的架构,由常识与经验的非批判走向理论的批判与反思,由“是什么”的思维方式走向“为什么”的思维方式。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转向必须依靠教育主体自身意识的觉醒与努力。此种转向要求发展日常教育生活中的文化启蒙,用科学理性的精神和人文精神塑造整个社会成员;通过价值重建和社会改革促使每一社会成员形成适应于现代文明教育的非日常教育生活。日常教育的自觉化并不意味着对非日常教育生活中的具体知识体系简单吸收,而在于“日常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由自在向自由提升,在于日常教育生活主体内在化的精神升华要求与文化素质的全面提高。”[9]所以日常教育生活的自觉化有赖于每个社会成员对日常教育生活与非日常教育生活的本质规定与结构特征有清醒的认识,在此基础上适应当前社会发展要求,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与知识涵养,提升自身的理论水平,自觉认同并内化非日常教育生活的精神实质,实现自身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由自在向自觉的提升。因此,日常教育生活与非日常教育生活的理论研究是必需的,但同时深入实践层面,进行理性运思和实证分析,展开对实践层面的批判和重建则更为艰巨与困难。
第二,非日常教育生活的日常化,即非日常教育生活的生命化与理论的践履。非日常教育生活的本质特征是自为性、自觉性,这决定了它的内在结构是创造性再生机制;它的思维是“为什么”的“我思”性;它的内容是现代的,具有批判性与反思性;它以制度为调控手段。制度的调控方式总是强制的、生硬的。制度化的僭越容易导致非日常教育生活的高高在上,远离社会成员,远离人生,缺乏一种人道化与生命化的生活情趣。制度化的教育生活是寓于非日常教育生活中的,是非日常教育生活组织架构的核心,比日常教育生活更富于思维与理性的色彩,往往具有模式化、稳定性的特点,但同时也缺乏日常教育生活的情感性与情景性。当前的学校教育生活往往是以制度化教育生活方式出现的。教育生活的制度化或者说将日常教育生活制度化会导致日常教育生活的缺失,将非日常教育生活扩大化,从而使儿童的日常教育生活失去“斑斓的色彩、生动的情感和生活的情趣”,[10]儿童的人生也失去了灵活性与丰富性,生活丧失了情趣。儿童日常教育生活的制度化、理性化是以制度化的教育生活来取代日常教育生活,体现了非日常教育生活的自觉性,但同时丧失了人生的社会性,用哈贝马斯的话说,日常教育生活被“殖民化”。
非日常教育生活的生命化即消弭制度化教育生活对日常教育生活的僭越,凸显人的生命本真存在,敬畏和善待生命,尊重日常教育生活的情景性、情感性和自在性,尊重完整的自由自在有情有义有血有肉的全面发展的人。非日常教育生活的理论践履即非日常教育生活不仅仅是对日常教育生活中习俗与习惯、常识与经验的简单认同和联系,而是立足于习俗与习惯、常识与经验又超越习俗与习惯、常识与经验,从习俗与常识中汲取营养加以完善自身,并以非日常教育生活的态度反思和批判习俗与习惯、常识与经验。这就要求理论的践履或理论的习俗化、非常识的常识化。主要是以非日常教育生活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去变革和更新习俗、常识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理论的习俗就是用理论的特质去反思和批判习俗的保守性与非科学性;非常识的常识化便是从哲学的高度理性认识、变革和更新常识的概念框架(直接给予性、自在性、简单性和狭隘性)。非日常教育生活的日常化过程,从现代化过程人的存在的变革和人的素质的提高来看,实质上是人自身的现代化的过程。[11]由此看来,非日常教育生活的日常化是非日常教育生活的生命化与理论的践履的统一,从中也说明了制度与理论在非日常教育生活中的重要性。知识的创新和文化的进步均有赖于好的制度建设,同样好的制度建设也会避免制度对日常教育生活的僭越;理论作为指导实践的灯塔,能有效避免常识经验的片面、习俗习惯的保守,从而保证理论的反思与批判特质。
综上所述,日常教育生活是人的熟悉而封闭的家园,非日常教育生活是人的自由而陌生的异在,二者之间保持着一种适当的张力,是一种动态的平行。日常教育生活的非日常化,即日常教育生活的自觉化,非日常教育生活的日常化,即非日常教育生活的生命化与理论的践履。二者既各有其所,又互渗互透。日常教育生活的自觉化与非日常教育生活的生命化与理论的践履是日常教育生活批判与重建的目标。
“日常教育生活”是伴随当代哲学理性位移——“向生活世界回归”而出现的一个新概念,这一概念是与非日常教育生活相对立而存在的。日常教育生活的自在性、思维方式的非“我思”性、内在结构的重复性复制机制及习俗与习惯、常识与经验等特有的调控方式,较之于非日常教育生活的自在性、“我思”性、创造性再生机制、制度化的调控手段更具“批判性”。而日常教育生活的批判目标,日常教育生活的非日常化与非日常教育生活的日常化,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自觉。
[1]卜湘玲,李亦桃.民俗:不容忽视的教育资源[J].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5,(1):6-8.
[2][10]郭元祥.生活与教育——回归生活世界的基础教育论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01.
[3][6]项贤明.泛教育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311.278.
[4]石中英.教育哲学导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6 -37.
[5][匈]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M].衣俊卿译.成都:重庆出版社,1990.163-180.
[7][9][11]李小娟.走向中国的日常生活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25.80.236.
[8]肖川.教育的理想与信念[M].长沙:岳麓书社,2002.7.
(责任编辑:曾庆伟)
刘胡权/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教师教育、教育政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