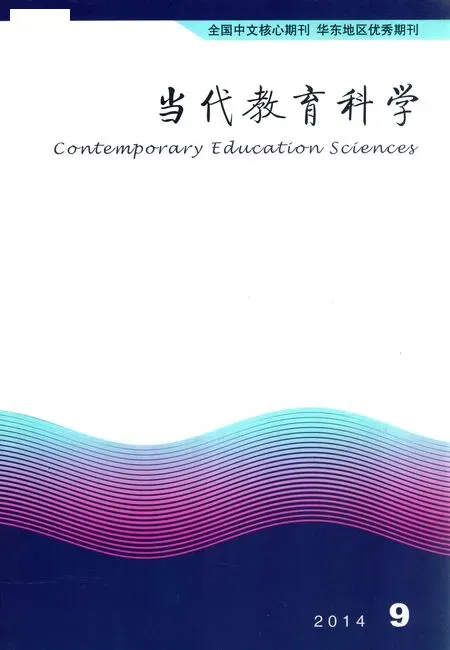高校内部治理中学生权力的谱系分析*
● 罗建河 潘甲甲
高校内部治理的核心问题就是决策权力在学校内部不同利益群体间如何分配的问题。而正如约翰逊指出的,所谓的学生权力主要就是学生影响学校决策过程的能力。因此如何配置学生权力便成为高校内部治理必须面对的一个研究主题[1]。要为学生权力的合理分配与协调运作找到依据,有必要从历史的源头开始对高校内部治理中学生权力的变迁予以梳理。
一、西方高校内部治理中学生权力的变迁
西方中世纪大学享有高度的自治权,由学生或教师组成行会实施学校内部治理。波伦亚大学是“以学生为主体”管理学校的典型。来自不同地区或不同国家的学生仿效行会的形式组织起来,管理和掌控学校内部的所有事务。他们自己制定规章,聘用并监督教师的工作,确定学费金额、决定教学时间等等。大学教师的几乎每项活动都要经过学生的允许。“大学和地方当局进行交涉,都由学生代表出面。教授的聘请和薪金的支付,也由学生负责。甚至教授上课迟到或讲课过于拖拉,他们还向教授追索罚金。为了防止教授中途为别校重金聘走,教授有时还须预付押金,由学生掌管。”[2]从12世纪到15世纪,在波伦亚大学模式基础上建立的意大利大学其内部治理结构大都以学生权力为主导。这个时期是学生权力发展史上一个特殊的兴盛时期。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时期,中世纪大学的基本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改变,但其性质却有明显的改变。首先,大学的国际性消弱,民族性增强;随着大学校址的固定,永久性大学开始出现。大学间的交往和流动也不再具有国际性,意大利学生型大学的逐步消失正反映了这一变化。[3]其次,大学的世俗性增强,逐步实现“国家化”。宗教改革之后各派别亦认识到高等教育在权力斗争中的特殊功用。高等教育的作用比以往更为重要,教会需要具有新的信仰的神职人员,政府需要更多的受过教育的官员,只有高等教育才能承担这项使命。而且高等教育还是处于上升的中产阶级让其子弟从事政治和工商业职业的无法替代的训练场所。宗教改革“以地方世俗政府的智力权威取代天主教会的权威”,这一变化意味着高等教育机构较之以往更加成为政府的工具。“政府一定要使所有的大学活动分子服从于政府监督,并使大学社团的所有成员都与官方的政党路线相一致。”于是,不仅教师,学生也要处于严格的限制之下,大学逐步被“国家化”。伴随着“国家化”发展,大学内部治理中学生的权力日益削减,聘任教师、选择课程、考核评价等都转由国家或地方政府任命的管理人员负责。在此背景下,学校对学生进行父母式的控制管理,依靠学校的规则制度来严格限制学生行为。据哈佛大学的一部早期校规的记载,学生在“地方行政长官、长老、教师及老年人面前”,必须保持缄默,叫他们说话时才能开口,大学“具有传统中学的束缚气氛,连体罚这种老规矩也保存了许多年”。[4]中世纪“学生大学”一去不复返了,高等学校的管理权力旁落教会、政府、教授、校外人士的手中。
20世纪60年代,西方高校学生运动掀起高潮,大学内部治理中学生权力进入爆发期。为了迫使高校分权,学生们通过各种各样甚至过激的集体行动如游行示威、占领房舍、破坏校产等方式争取更多的决策权力。1968年3月至5月,在各种社会矛盾尖锐激化的情况下,法国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学生运动。正是这场运动直接促成了 《高等教育方向指导法》的出台。“参与”是《高等教育方向指导法》的核心理念之一。这里的“参与”主要指集体管理,即大学的所有成员乃至社会人士,均可以通过其各种委员会的代表参加对学校本身的管理。只允许少数知名教授有发表意见的特权的现象不复存在。具体操作就是在校、系一级均设立由学生、教师、科研人员、行政技术人员、服务人员及校外知名人士代表经过选举组成的学校理事会作为大学的决策机构。不仅如此,在教学科研单位、大学及地区审议会各级都要求有学生代表。[5]在美国,50年代的学生还被称为“沉默的一代”,进入60年代学生运动就在美国各大学此起彼伏。在 1968-1969年学生运动的高峰期,许多高校的学生被允许参与教师的聘用、解雇和有关课程设置的决定。1971年美国教育理事会的调查发现,全国14%的高校董事会中有学生代表,而且这个比率还在逐年增长。[6]在英国,自20世纪 60年代以来,学生对参与高校内部治理的权力诉求迫使绝大多数大学允许学生代表成为各种委员会的成员,包括特别建立的师生联合团体和评议会、理事会的各种常规委员会。英国高校的最高权力机关、最高行政管理机关是董事会,而学生正可以通过董事会来参与学校事务的管理决策。在德国、意大利等国家,学生也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到学校的各项决策与管理工作中来。在西德和丹麦,从校到系,各级委员会中都有规定比例的学生代表,一般情况下是高级教师、年轻教师和学生各占三分之一。20世纪70年代以来学生权力进入理性回归期,学生权力的诉求主要集中于对多元化权利的维护,逐渐走向与学校行政权力、教师权力之间的多元制衡关系。[7]
二、我国高校内部治理中学生权力的变迁
1840年后中国才开始学习西方建立新式高等学校。众新式学堂建立之始沿袭封建权威对过去国子监、太学机构的管理,校内一切事务的决定权往往集中在学堂主管一人手中,学生权力基本处于缺失状态。如《奏定各学堂管理通则》规定:“学生在学堂以专心学业为主,凡不干己事,一概不准预闻;各学堂学生,不准干预国家政治及本学堂事务,妄上条陈;……各学堂学生,凡有向学堂陈诉事情,应告知星期值日学生,代察本学堂应管官长;不准聚众要求、藉端挟制、停课罢学等事;……各学堂学生,遇有本学堂增添规则,新施禁令,概不准任意阻挠,抗不遵行;以上各条,犯者除立行斥退外,仍分别轻重,酌加惩罚。”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到,学生在学堂中完全处于被管制和被规训的地位,毫无参与学堂事务管理的权力。[8]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设立教育部,随后颁布《大学令》和《大学组织法》。然而无论是《大学令》还是《大学组织法》强调的都只是教授或教师在学校内部治理中权力,学生则被排除在学校决策权力之外,甚至作为学生权力主要载体的“学生组织”都受到了严格的控制。1943年11月22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的《学生自治会规则》不仅对学生自治会的目的、活动范围、机构构成和人员任用等方面作出了具体的规定,还明确了自治会的禁止性事项。《学生自治会规则》第十六条、第十七条和第十九条规定:“学生自治会举行各项会议时,均应先期请求学校派员指导。学生自治会之决议以在规定之任务范围以内为限,并不得干涉学校行政。有违反上项情形者,学校得撤销之。学生自治会如违背校规,情节重大时,学校得解散之。”[9]学生自治会完全被置于学校管理层的监视、规制之下,其自治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异化。
新中国成立后,学生权力首次在制度上得以确认。1950年颁布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第二十六条规定,“校 (院)务委员会中要有学生会代表二人”。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进一步指出:“制定学校教育计划,制定教学大纲的时候,也应当采取在党委领导之下教师与学生结合的方法……”。1961年《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 (草案)的指示》规定,“教师要注意听取学生对教学的意见和要求”。这些制度规定展示着学生权力存在的事实。在“文革”十年中,学生权力发生了急速的膨胀,大学一切事务都要经由学生裁定,高校学生权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可惜的是,这种学生权力披上“革命”的外衣,在“革命”激情的催化之下这种学生权力运作逐渐突破了合理的边界,沦为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高等教育也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回归运动。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回归,学生从“管理大学”、“改造大学”的主人翁沦为需要加以管束和教化的对象,学校中的等级制是普遍的组织原则。等级制下学生感受到是日益增长的强制性和压迫性,主体地位和主体性亦遭致忽视与遮蔽,进而只能沦为规训、管制的对象。这就是为何在1990年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和《高等学校校园秩序管理若干规定》看到的只是对学生的规训与管制的规定,而看不到学生在学校内部治理中的决策权力。[10]
三、高校内部治理中学生权力的依据
在历史的谱系分析中可以发现,在诸如波伦亚大学之类的学校中学生缴纳的学费是教师生计和学校运作的主要经济支撑。学生籍此也就掌握着教师的生计和学校的命脉,从而可以对教师和学校其他组织成员施以压力,将他们的意志强加于教师和学校其他组织成员继而使之服从。这也就是所谓高校内部治理中的学生权力。从这里可以看到,高校内部治理中学生权力的首要依据便是学生对学校资源的掌控。中世纪“学生大学”存在的合理性也就在于学生掌控着学校所有的资源。如博洛尼亚大学在薪金制度的教学职位设立以前,大多数教师的收入主要依靠学生的学费,学生所拥有的经济权力使他们更有能力抵制和反对那些不服从规定的教师;到13世纪晚期,博洛尼亚市政当局建立了有薪金的教师职位,不再依赖于学生的学费,博洛尼亚大学中学生的权力也随之有所消退。到1350年,博洛尼亚的学生已丧失大部分权力,大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市政当局的保护,大学的管理权重新回到教师手中。然而作为永久性大学的现代高校中,学生的学费和学生本身仍然是学校赖以存在的不可或缺资源。学生是学校生存之本,即一定数量的学生是一所学校得以存在的价值之源。一所没有学生的学校也就不成其为学校;没有任何学生选择某所学校,那么这所学校也就自然消亡了。越优秀的学生对于学校生存的价值越大,相应地其资源性权力也就越大。这也就是美国学者所指出的学生通过“以脚投票”来彰显自己的权力。事实上,学生不仅是学校存在的可能性依据,而且也是学校存在的目的性依据。大学只能是为了学生而存在,这是大学区别于专门科研机构的一个重要标准,因而学生权力理应成为高校内部治理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正因为高校内部治理中学生权力首先源于学生对学校资源的掌控,也决定了学生权力必须是一种集体权力。集体行动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高校内部治理中学生权力的又一重要依据。单个的学生无论是其缴纳的学费还是其本身的去留对一所大学的存亡是无关紧要的,只有学生个体集聚起来达到一定数量之后,才能成为影响学校决策的重要力量。如波伦亚大学的学生行会维护自己管理学校事务的权力的主要策略就是集体行动,一旦自己的管理权遭到某种控制或干涉,学生行会就以举校迁移的形式捍卫自己的权力。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也有一些典型的学生通过集体行动彰显自己在高校内部治理中权力的事件。如1919~1921年间清华大学学生“三赶校长”事件,1922年10月北京大学因“讲义费”引发的学潮等。当然,这些行动往往会被当局定性为“非法”行为,而合法的学生权力往往只能依赖于外部制度的设定,这一点在不具备行会历史的中国近现代大学中更是显著,以至于当前学者们在为学生权力寻找依据的时候也多要从《高等教育法》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等文本出发。因而,政策法制亦可以算作高校内部治理中学生权力的现实依据之一。
从“知识与人生”的关系考察,大学作为传递知识的重要基地对于学生的人生未来有着莫大的影响,面对自己的人生未来每个人理应拥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力。基于每个人对于自己人生未来的决策权,学生理应参与高校内部事务的决策;因为学生参与高校内部事务的决策就是在对自己的人生未来承担责任。所以,对于自身命运的决策权也可以说是高校内部治理中学生权力的重要依据。
四、结论与启示
从高校内部治理中学生权力变迁的谱系分析,可以发现学生权力的依据主要包括学生对学校资源的掌控、学生的集体行动、外部制度设定和学生对于自己人生未来的决策权。从学生权力的资源性看,自20世纪末我国高等教育实施教育成本分担之后,我国大学生也就相应地具备了这种资源性的学生权力。学生作为高等教育的投资者和高等教育服务的购买者,理应分享高校内部的决策权。作为投资者,学生缴纳的学费只是高等学校经费的一部分,因而学生不能像在中世纪的“学生大学”中一样掌握着高校内部的完全决策权,换言之,高校内部治理中的学生权力应该是有限的权力。作为高等教育服务的购买者必然对高等教育服务的质量有着相应的要求和必要的关注。当投资者身份与购买者身份合而为一的时候,学生对于自己投入的资金也就有着监管权,即要求自己投入的资金能够生产出让自己满意的教育服务;要求自己投入的资金主要用于提供让自己满意的教育服务。据此,学生在高校内部治理中的权力范围至少包括对学校经费运作的知情权和对教育教学质量的评价权。
从外部制度的设定看,我国高校内部治理中学生权力的长期缺位与法律制度层面的缺失不无关系。《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世界宣言》与《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优先行动框架》所确认的学生权力并没有在我国相关教育法规中得到确认,无论是《教育法》还是《高等教育法》,学生权力都没有进入其规定范围。虽然2005年出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四十一条规定了“学校应当建立和完善学生参与民主管理的组织形式,支持和保障学生依法参与学校民主管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学生权力的合法身份得到了完整、有效的确认。因为,一方面所谓“学生参与民主管理”的表达过于模糊,并未廓清学生权力的范围;另一方面,《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属于行政规章,其法律效力远不如《教育法》、《高等教育法》,难以成为法律诉讼之依据。因此,要在外部制度的设定上保障我国高校内部治理中学生权力的地位,颇有必要在《教育法》或《高等教育法》中就学生权力作出明确规定。
当学生的资源性权力和法律确认之正式权力过于微弱时,学生很有可能会通过集体行动的方式来行使自己的非正式权力。然而学生集体行动一旦扩散极有可能造成全社会性的集体行动,进而成为极具破坏性的力量。对于学生群体可能发生的集体行动,亦遵循“疏胜于堵”的原则。充分发挥各种学生组织的利益表达和权力诉求功能,让各种学生组织、社团成为高校学生利益表达和权力诉求的畅通渠道。同时,也不妨利用电子邮箱、网络留言、论坛等方式充分了解学生动态,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表达与沟通平台。当然,在让学生表达自己的权力诉求、赋予学生内部治理权力时,也要防止出现学生权力过度膨胀的情况。因此,明确学生权力的范围与界限是当务之急。
从学生权力的资源性分享,我们指出学生的权力应该包括对学校经费运作的知情权和对教育教学质量的评价权。而从学生对自己人生未来的决策权出发,我们认为学生权力还应该包括参与课程与教学改革的权力、参与制定学校教育教学决策的权力、参与学校重大教育问题商讨的权力等,因为课程、教学以及学校重大教育问题都与学生的人生未来直接相关。至于学生权力的界限,依据高校内部治理中权力的构成,我们认为相关决策过程中学生持有的票数不宜超过三分之一。
[1]Johnstone D.B.The Student and His Power[J].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1969,Vol.40,No.3,p.205.
[2][英]阿什比.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M].滕大春,滕大生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64.
[3]胡钦晓.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社会资本视角下欧洲传统大学的没落[J].江苏高教,2011,(1).
[4]赫钦格.美国教育的演进[M].香港:美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处,1984,154.
[5]苏昀,徐士元.欧美高校学生权力发展历程及启示[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2,(1).
[6]陈学飞.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201.
[7][10]于海棠.高校学生权力变迁及其配置[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9,(12).
[8]陈元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487-488.
[9]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史研究室.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1912-1949)[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