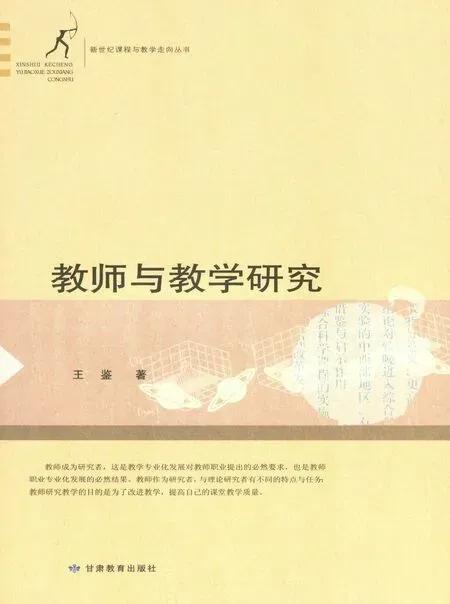走向“理解”的教学理论
——哲学解释学视角下的教学论写作观反思
曹周天
(北京师范大学 课程与教学研究院,北京 100875)
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对于教师如何学习掌握并熟练运用教学理论始终是一个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一线教师,特别是从事教学论研究的理论工作者的问题。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了“实践性知识(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这一概念,试图寻找一种“教师专业特有的将所教内容与教育学结合起来达成的一种新的知识”,从“知识型”的角度为填平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鸿沟提供了有益的指导。但对于教学这样一个诉诸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实践活动,仅从静态的“知识”革新入手,并不能够解决教学的复杂问题。有鉴于此,本文想尝试用哲学解释学的视角,从“理解”这一核心概念出发,对教学理论介入教学实践的相关问题,作些理论思考,就教于诸位同仁。
一、“理解”内涵的历史梳理
解释学(诠释学Hermeneutics)一词来源于赫尔默斯(Hermes)。赫尔默斯本是希腊神话中诸神的一位信使的名字。它的任务就是来往于奥林匹亚山的诸神与人世间的凡夫俗子之间,迅速给人们传递诸神的消息和指示。因为诸神的语言与人间的语言不同,因此赫尔默斯的传达就不是单纯的报导或简单的重复,而是需要翻译和解释,从而使一种意义关系从陌生的世界转换到我们自己熟悉的世界。[1]1-2解释学最初的含义是指“把一种意义关系从另一个世界转换到自己的世界”,即将一种意义从陌生的环境转换到熟悉的环境中。
“理解”是哲学解释学中的核心问题。解释学诞生之初,欧洲就具有了解释古代文献的传统。在东方,人类只要有文字以及文字记载的历史,必定会有理解和解释。在基督教盛行时期,解释学成为圣经的文献学,它格外关注圣典文字背后的真意。文艺复兴时期,解释学逸出了解释圣典的范围,扩大应用到对整个古代文化的解释和理解上,给解释学洞开了作为整个人文科学的一般方法论之门。真正使解释学发生转折的是哲学家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在他看来,理解不再是圣经解释学中“真意”的破译术,理解的对象是人类及其生活史。他认为,理解只能在语言的联系中进行,理解是语义结构中的理解。不过他所谓的“理解”,只是一种认知方式,是一种心理功能。继施莱尔马赫之后,解释学的又一位思想巨匠是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在他看来,理解作为人认识自己的方式,被视为人文科学的主要致知途径。狄尔泰把理解扩大为整个人文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人文科学关注的是人的自我认识和意义,而人取得对自身认识的途径正是理解。狄尔泰赋予理解以生活方式的认识论地位,是解释学历史的里程碑。到了海德格尔(Heidegger),他完成了解释学向本体论的转折。他把人定义为“此在”(Dasein),以别于传统的一切关于人的定义,“此在”最基本的存在方式就是理解,“此在”的理解展示存在的意义。海德格尔的学生伽达默尔(Gadamer)继承了老师对解释学的本体论规定的思想,他把理解和解释看作是人类世界经验的源泉,强调解释学是以“理解”为核心的哲学。他在1960年出版的《真理与方法》标志着哲学解释学的诞生,这本书已被公认为当代西方哲学的经典性著作。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就是从理解入手,说明人与传统、历史、文化的关系,人与语言的关系,以及人生意义等问题。总之,解释学试图对人类面临的诸多现代课题加以解答,并对当代西方人面临的困境进行反思,使西方思辨哲学和分析哲学逐渐走向“生活”,走向实践哲学,并从理解的历史性、语言性出发,强调理解的创造性和主体性,注重理解的多元性和差异性。[2]31-52
二、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鸿沟
笔者在翻阅众多教学理论书籍时发现,有关教学理论的论述与教学实践过程中的实际情况存在鸿沟,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立场上不对称
教学理论的写作者多半是在高校或科研院所从事理论研究的专门人员。他们长期从事教育教学研究工作,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与思辨能力。由他们执笔的教学理论著作能够从较高的理论高度把握教学活动的方方面面,对于一线教师清晰地了解教学的实际工作提供了便利。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王策三所著的《教学论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李秉德主编、李定仁副主编的《教学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钟启泉编译的《现代教学论发展》(教育科学出版社,1992)。[3]105-106而广大教师,作为教育教学活动的亲历者与践行者,长期奋战在教学第一线,与学生们开展日常的教学活动,他们对于教学有赋予个性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者和教师处在不同的立场之上。一线教师直面课堂,考虑的是“什么样的教学理论可以解决当前的问题”;而研究者则是在书斋内建构教学的理论体系,他更多考虑的是“教学应当怎样”这个问题。前者注重问题的现实性,后者则关注问题的前瞻性。如此在立场上的不对称,使得研究者所撰写的教学理论与教师在工作中的教学实践存在“理解”偏差,教学理论难以有效地服务于教学实践。
(二)内容上不照应
作为由实践抽象后的教学理论表达,其更多关注的是如何用精炼的语言表达较为全面的意思。而提炼往往就会有取舍,难以面面俱到。在内容层面,研究者看到的是某一类教学问题,是抽象化、理论化了的问题类型;而教师脑海中所记录的则是某一幅具体的教学场景,是具体化、经验化了的问题事件。因而,教师常常苦于教学理论的高度概括,而从中找不到解决教学实际问题的“行动指南”。如此在内容上的不照应,使得研究者所撰写的教学理论与教师在工作中的教学实践缺乏“对话”的背景基础,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难以在解决实际问题的层面展开互动。
(三)逻辑上不匹配
研究者的著作,高屋建瓴地将整个教学活动建构在缜密的逻辑框架之中,它遵循的逻辑是以结构化、系统化的体系为先导,再将之细分为诸多模块,把教学活动的环节按照一定的分类放置于逻辑体系的各个部分。在研究者看来,理论中的教学建构是全面深刻的,它既可以追溯历史、审视传统,从历代先贤那里获得丰富的精神养料,也可以放眼未来、面向当代,汲取世界各国先进的教育教学理论。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教学理论可谓是博古通今、贯通中外。教师获得教育教学理论当然得益于对于系统教学理论文本的阅读与学习,但这仅仅是其获取教学理论知识的一种渠道。一线教师建构自身教学理论的一般逻辑,更多的是通过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的实践摸索,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的总结,逐渐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或是通过校内或校际间的课堂观摩,相互交流,体验各家教法,以促进自我反思与进步。对比二者可以发现,研究者的逻辑往往是“理论先行”,先构建体系,再填补内容,颇有“未雨绸缪”之意;教师却常常由实践出发,通过不断地尝试与总结,上升为符合自身教学实践的教学理论,可谓是“摸着石头过河”。如此在逻辑上的不匹配,使得研究者所撰写的教学理论与教师在工作中的教学实践缺乏“视域融合”的交互平台,教师会不解于研究者的“杞人忧天”,研究者也会遗憾于教师的缺乏理论前瞻性与自觉性。
三、走向“理解”的教学论写作观
(一)教学论写作的原始冲动:“理解”为先
理解活动是人存在的基本方式。[4]479作为人的精神领域的思考与体悟,理解贯穿于人发展的始终。这就要求教学理论的写作必须要从人类的普遍经验入手,以此为基础展开论述。这当中便存在着一个写作的“原始冲动”,即创作动机的问题。所谓动机,是指引发并维持活动的倾向。心理学研究中往往用动机作用(motivation)这一术语来描述个体发放出能量和冲动,指引行为朝向某一目的,并将这一行动维持一段时间的种种内部状态和过程。[5]211
作为一种倾向,教学论的写作观首先要求研究者要站在“理解”的立场之上,对整个教学活动做整体的观照。意义是经过理解而产生的,并不能通过学习而掌握,它并不是知识本身所包含的意思,也不是个人意识强加于知识的,而是个人的精神与Text(文本)的意义形成融合后产生的可能性,正因为它是可能性,才能引导精神向可能性实现。[2]81教学理论不是研究者主观臆想或凭空捏造的事物,而是基于其对教育教学实践活动充分观察与深入体会之后的理论建构。研究者所撰写的教学理论文本也绝不是教育教学现象的一般描述与理论的简单抽象概括,而是将所观察与体会到的现象与个人精神层面的对于教学活动的理想追求相融合而产生的文字表达。这便是研究者站在“理解”立场之上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
其次,研究者要重视个体的“自我理解”。在理解中,自我的属于它自身的以往生活经历所包含的一切潜在意义都可能不停顿地无止境地涌现出来,构成为“自我”为它自身的存在意义而作的关于客观世界的总解释,而在这个解释中,世界作为“总体”,而呈现在自我的“反思”之中。[6]61教学理论的写作不是机械的闭门造车,一位能够写好教学理论著作的研究者首先必定是一位具有丰富教育教学经验的教师。教学理论关注的是“如何教会别人教学”的问题,既然能“教会别人”,他首先就要“会教”。若是研究者“不会教”,不会上课,那么他所撰写的教学理论就缺乏教学的现实指针性与必要的教学体验。然而,单纯是一位具有丰富教育教学经验的教师还不够,一位优秀的研究者必须具有深厚的理论修养,能够将自己对教学活动的理解与运用通过简明通俗的文字表述出来,便于人们的阅读与学习。因此,教学理论的写作应当是这样一位兼具教师与研究者双重特性的学者,通过对自己教学实践的不断反思与追问,在与个体对话,自我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理论建构。由此推知,要求解释者抛弃他的主观性是完全背理的;事实上,他所要做的一切只是排除任何有关结果的个人偏爱。[7]138
(二)教学论写作的语言定位:“对话”为重
在哲学解释学中,对话不仅指交往双方二者之间的狭隘的语言谈话,更重要的是双方的“敞开”与“接纳”,是对“双方”的倾听,是指双方共同在场、互相吸引、互相包容、共同参与的关系,这种对话更多地是指相互接纳和共同分享,指双方的精神的相互承领。[2]81
良好的对话是教学论写作的交流基础。教学理论的写作与其说是在阐明研究者对于教学活动的理解,不如说是研究者与教师之间敞开心扉的对话与互动。这在写作中就关涉到语言表述的问题。现行的教学理论著作的叙述话语多半是指导性的,大多数情况下是研究者自己的演说,忽略了教师群体的阅读感受与体验。甚至一些研究者在著作中仅凭主观臆想,片面否定一线教育教学实践,认为这些不符合教学理论的科学规律,这样一种以“专家”姿态自居的教学论写作观,不但不能给予教师有益的指导,相反严重削弱了教师学习教学理论的热情,甚至引发教师对于教学理论的诸多抵触情绪。基于“对话”为重的要求,研究者在教学理论撰写过程中,要尽可能用对话的语言,讨论的方式,把教师当作知心朋友,共同商讨、切磋教学问题。如我国著名教学论研究专家王策三先生的教学论写作就是讨论式,他不采取传统教科书式的方法宣讲道理,构建体系,而是通过分析和解决问题(特别是实际问题)来阐发理论。发表自己的看法,进行商量、讨论,留有余地,不勉强做结论。[8]4这样淳朴的学术态度值得我们学习。
重视对话的情境性是教学论写作的话语方式。对于教学问题的探讨都是在一定教学情境中进行的,教学理论的写作要抓住这一契机,以问题情境为突破口,激发教师对教学问题的思考。在进行某一教学理论阐述时候,研究者不妨先叙述一段教师在日常教学工作中熟悉的教学场景,在此基础上追问几个问题,这样就较为自然地将教师引入到具体的教学情境之中。由实践中的问题出发,再进行理论层面的探讨,就能使教师进一步明确相关理论的现实指导意义与价值,从而避免出现实践与理论错位的认知困境。
不把话说满,留有讨论的空间是教学论写作的取舍之策。海德格尔说过,语言是存在的家。当代语言哲学也认为,语言本身就包含着意义,并不是客观的工具。同样一个意思,可以这样说,也可以那样说,语言在细微之处展现出了张力。教学理论文本作为教师阅读与学习的蓝本,其本身应当具有无限地被阐释性,这既是哲学解释学的应有之义,更是“对话”为重教学论写作观的价值追求。教学理论的写作语言更重要的是抛出问题,暴露研究者思考问题的具体过程与方式,这样,教师在阅读教学理论时,也可以学习研究者思考教学问题的方式,对自身的教学实践问题进行反思。教学理论的文本也不再是被奉为经典的金科玉律,而成为具有生成性的,可以用来讨论的“教学对话录”。
(三)教学论写作的价值归属:追求“视域融合”
哲学解释学的理解观认为,理解是一种意义创造和不断生成的过程,理解不是一方一定要抛弃自己的观点而去符合对方的观点与意见。在理解过程中,理解者视域(视界)不断与被理解者的视域(视界)交流,不断生成发展丰富,以达到不同视域(视界)的融合,伽达默尔称之为“视域(视界)融合”。[9]129视域也就是地平线(英文中二者是同一个词horizon)。“地平线是视域的区域,这个区域包括了从一特殊的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所能看到的一切。一个没有地平线的人是一个不能充分登高望远的人,从而也就是过高估计近在咫尺的东西的人。与之相反,具有一个地平线就意味着,不被局限于近在咫尺的东西而能够超出它去观看。一个有地平线的人能够认识到在这个地平线之内的一切东西的相对意义”。[10]在伽达默尔看来,理解就是解释者在语言游戏的框架内通过与文本进行对话,达成视域融合的过程。而由此生成的“新视域”则超越于理解者与文本自身原有的“视域”,从而开辟了无限可能的世界。在教学论的写作中,研究者要树立“地平线意识”,即站稳脚跟,打开视野,以开放包容的心态达成“视域融合”。具体来说,可以从与历史、现实、未来三个维度展开。
第一,研究者与历史传统的“视域融合”。在对历史的理解中,个体的精神世界——视野总是延伸在历史之中,也就是把自己置入历史境遇,在历史中汲取经验,而获得自己经验的更新。[2]49我国古代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著作中已有了丰富的教学思想。在西方,古希腊的许多学者,特别是以传授知识为职业的智者学派,也发表了关于教学的言论。到了我国战国末期,又出现了我国教育史上的也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光辉著作《学记》。罗马的昆体良写了《演说术原理》一书,被誉为古代西方的第一部教学法论著。[11]197-198此后的众多教育家,虽然并不都是专注于从事教学理论的研究,但有关教学的论述散见于他们的教育学论著之中,这些都是当代研究者值得不断挖掘的知识宝库。在吸收与借鉴历史上的教学理论过程中,一方面要能够深入到这些理论产生的历史语境与社会背景,了解它们在当时的特定时代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要立足当下,用今人的眼光,批判地评价这些教学理论,在理解历史,与历史对话的过程中,获得历史层面的“视域融合”。
第二,研究者与现实生活的“视域融合”。生活实践是教学理论产生的土壤。“就人类来说,信仰、理想、希望、快乐、痛苦和实践的重新创造,伴随着物质生存的更新。通过社会群体的更新,任何经验的延续都是存在的事实。教育在它最广的意义上就是这种生活的延续。”[12]3研究者研究教学理论的视野必须要投向现实生活,投向课堂教学,投向教师与学生的内心世界。与教学理论的历史传统不同的是,现实生活反映了当前一线教育教学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比起那些美好的教学理想,这些问题具有较强的社会现实性,针对这些问题展开的理论思考对于推动教学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教学论的写作中,研究者既要深入一线实践,用敏锐的眼光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也要多与教师与学生交流,充分发掘教育行动研究与教育叙事研究在学校语境中的独特生命力,把这些通过面对面的互动获得的一手材料作为教学理论思考与建构的重要事实支撑,在理解现实,与现实对话的过程中,获得现实层面的“视域融合”。
第三,研究者与未来世界的“视域融合”。教学的发展需要理论前瞻性的指导,这就要求研究者对于教学理论的思考必须面向未来,对其发展态势作出较为科学的理论预测,对其未来形态进行较为宏观的模型建构。只有研究者顺利地带进了他自己的假设,理解才是可能的。[13]753当前,我国已进行了十多年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仍然在稳步推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也正处在实施的关键时期,这些改革都是基于对未来教育图景的规划与描摹而做出的战略性部署。放眼世界,日本正进行构建“学习共同体”的“静悄悄的课堂革命”,欧美的一些国家也积极借鉴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思潮,开展多样化的课程改革实践。纵观国内外的教育形势,作为教学论写作的研究者,需要广泛地涉猎国内外最新发展方向与理论研究成果,并通过理论的分析与教育测量与评估的相关数据,对未来教育教学发展作出合乎逻辑的预测,在理解未来,与未来对话的过程中,获得未来层面的“视域融合”。
哲学解释学视角下,以“理解”为核心的教学论写作观将研究者置于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衔接处,力求以“理解”为契机,通过“对话”的互动方式,在历史、现实与未来层面达成多样化的“视域融合”。在重视研究者的教学论写作的同时,作为教学理论的学习者,广大教师也要积极地参与到教学理论的建设中来,通过基于个体经验的主动建构,将教学理论通过理解,内化为自己的教学风格,在教学实践中不是刻意而是自然地运用。在实践中,教师也应该加强与教学理论文本的对话,与研究者的对话,讲述个体独特的教学经验与心得体会,对教学理论保持批判的接受态度,在教育教学实践中撰写赋予个性的教学理论,这或许才是基于哲学解释学视角下教学论写作观最深刻的反思。如此,“理解”的教学理论就会真正在教育教学实践中蔓延开来,教学理论也将与教学实践一道成为构筑我国基础教育教学园地的基石。
[参考文献]
[1] 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2] 金生鈜.理解与教育——走向哲学解释学的教育哲学导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
[3] 杨小微,张天宝.教学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4] 刘放桐.新编现代西方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5] 陈琦,刘儒德.当代教育心理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6] 高宣扬.解释学简论[M].台北: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8.
[7] 埃米里奥·贝蒂.作为精神科学一般方法论的诠释学[M]//洪汉鼎.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洪汉鼎,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8] 王策三.《教育论集》评介[M]//王策三.教育论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9] 严平.走向解释学的真理——伽达默尔哲学评述[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10]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J]//效果历史的原则.哲学译丛.1986,(3).
[11] 成有信.教育学原理[M].郑州:大象出版社,1993.
[12] 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13] 陈启伟.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