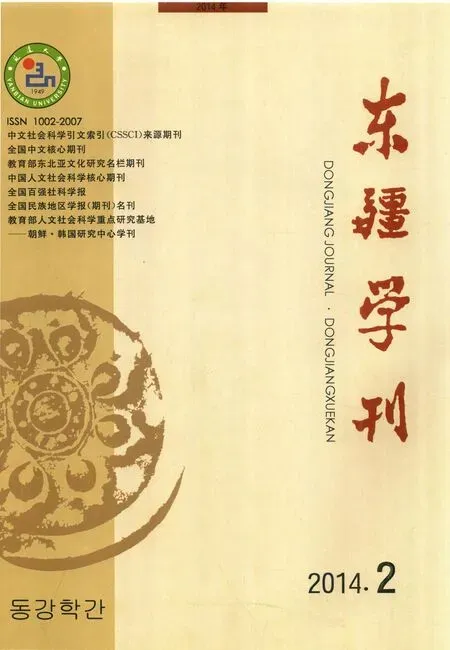论朝鲜音乐家韩悠韩作品的混融性特征
崔玉花
[责任编辑 丛光]
韩悠韩 (1910年 2月~ 1996年 6月,原名韩亨锡)是长期在中国生活并从事音乐创作的朝鲜抗日斗士和艺术家。韩悠韩自 1933年创作处女作《新革命军歌》直至 1948年回到韩国,在中国共创作了100余首歌曲和7部歌剧。他创作的《新革命军歌》、《光复军歌》等歌曲在中国军队和朝鲜抗日部队乃至广大的朝鲜民众当中广泛传唱。另外,他创作的歌剧《丽那》、《啊哩郎》等在西安上演后受到中国文艺界的高度评价。
对于韩悠韩及其音乐作品的研究,国内外学界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如,中国学者梁茂春的《关于抗日时期作曲家韩悠韩的基础调查报告》(《韩国音乐史学报》第20辑,1998年)等论文①梁茂春的研究成果还有《中韩音乐交流的一段佳话——音乐家韩悠韩在中国》(《音乐研究》,2005年第 1期)、《韩悠韩的歌剧〈啊哩郎〉——一部特殊的韩国歌剧》(《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第 1期)、《永恒精神的绽放 — 在釜山聆听韩悠韩的抗战歌曲》(《人民音乐》,2005年第 11期),另有金德钧的《韩国接触的抗日音乐家韩亨锡(韩悠韩)》(《音乐与民族》,第 19号,1999年)等。以及韩国学者金昌旭的《韩亨锡的光复军歌研究》(《港都釜山》,2008年 )等论文,对韩悠韩的艺术活动及其作品的思想性、艺术价值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
笔者在上述先行研究的基础上,在下文中将着重关注其中国体验,从文化研究的视角阐明其在中国时期音乐创作的意识倾向及音乐创作的混融性(hybridity)特征。
一、韩悠韩作品的文化语境
韩悠韩 1910年生于韩国的釜山,1917年随投身于朝鲜独立运动的父亲韩兴教②韩悠韩的父亲韩兴教(1885年~ 1967年)是一名毕生致力于韩国独立运动的爱国者。韩兴教早年留学日本,就读于冈山医学专科学校。他在日本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10年朝鲜被日本吞并,完成学业的韩兴教流亡到中国,在北京、上海等地开展韩国独立运动,并积极主张中韩联合战线。韩兴教还与申奎植、申采浩等韩国独立运动家们一起设立了“同济社”等独立运动团体。在中国开展韩国独立运动的同时,韩兴教还积极参与中国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曾经担任国民革命军救护医长、北伐军红十字会队长等职务。韩悠韩就是在这样一位父亲的影响下形成了对民族和祖国现实的认识。九岁时,韩悠韩曾受父亲的嘱托,参与发布“三一运动”独立宣言的重任。这一段经历给韩悠韩的意识倾向,尤其对其反帝反封建意识以及中韩反帝反封建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来到中国,先后在北京、上海等地生活。 1929年~ 1933年,韩悠韩在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学习音乐,毕业后积极参加抗日革命运动,先后担任音乐教师、国民党中央军政治部干部、少校音乐教官、韩国青年战地工作队艺术组长、韩国光复军干部等职务,直到 1948年回到韩国。
中国文化体验、教育体验、生活体验等丰富的中国体验,造就了作为一名进步艺术家的韩悠韩。身为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韩国离散者(diaspora),父亲的身传言教,使韩悠韩具有了抗日救国的反帝革命意识,即民族意识。当时韩国和中国具有共同的历史使命 —— 反帝反封建革命,而中国体验进一步加深了韩悠韩的民族意识。两种文化体验在离散者韩悠韩的意识中形成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升华的关系。事实上,当时流亡到中国的韩国革命家普遍具有这种“双重革命家”的身份,即以朝鲜的反日独立革命为主要使命,同时也积极参与中国的反帝反封建革命。
通过韩悠韩的音乐创作,也可以确认这种意识倾向。中国出版的歌曲集《难忘的旋律》[1](179~180)中收录有韩悠韩创作的歌曲《黄河边的月》(李嘉词),歌剧《新中国万岁》中的插曲《春天的阳光》(李嘉词)、《故乡月》(丁尼词)等抗日歌曲。这些歌曲在抗战岁月中广泛地传唱于中国军队和韩国光复军中。韩悠韩将中国革命意识和抗日意识融入并表现在音乐作品当中,很好地反映了时代精神及其美学要求。同时,韩悠韩用中文写歌词,体现出作为一个离散者(diaspora)在接受和融入异国文化时所具有的适应性。
一言以蔽之,韩悠韩拥有作为一个流亡者或离散者的生命体验和文化体验。中国革命意识和反日独立意识融合在一起,同时也相互影响,塑造了韩悠韩独特的意识倾向。这种意识构成的混杂性(hybrid)也体现在韩悠韩的艺术创作中,促成了艺术表现的独创性。
二、韩悠韩音乐作品的混融性特征
霍米巴巴曾指出,准确地分析和理解混融性(hybrid)对于摆脱后殖民状况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他还提出了“间隙的空间”概念,意指一种文化在所难免地被异文化所同化或者从属于异文化的空间。而对于艺术家而言,“间隙的空间”会与自己所经历的文化的、政治的体验相结合,成为新的创作原动力,韩悠韩正是如此。中国体验给予其强烈的中国革命意识和反日独立意识,并使其得以在艺术创作中实践中国音乐与韩国音乐乃至西方音乐的融汇与贯通。从某种意义来讲,韩悠韩在音乐创作中取得的成功得力于他通过“间隙的空间”获得的文化的混融性。具体而言,韩悠韩在音乐创作中融入了跨文化的因素并加以变通,极具代表性地体现了文化的混杂性。
就调式而言,韩悠韩的作品中大调占绝大多数,以 4/4拍居多,终止音大多为“do”,这种音乐结构性,充分体现了作品通过各种相异的节拍、节奏与旋律构成等的融汇与贯通来实现其混杂性。
音乐的节奏是通过有序的持续运动所组织的。①就节奏特性而言,中国传统音乐中 2/4拍、4/4拍占据大多数,日本传统音乐几乎全部都是2/4拍,韩国传统音乐中 3/8、6/8、9/8、13/4等三节拍、符合三节拍的系列节拍居多。而西方音乐的节奏具有附点音符以及乐曲的开始起于弱拍等特点。节奏由节拍、速度、重音等构成,其中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化都会引发整个节奏的变化。例如,3/4拍的任何一个重音发生变化,都会产生不同节奏形态。
(一)韩悠韩音乐的混融性体现在西方音乐的 3/4拍和韩国传统音乐的 6/8拍的结合上。
抗日歌剧《中国万岁》中的插曲《故乡月》(李嘉词,1937年)、《朝鲜的母亲》(申德泳词,1943年 )、《飘去的云》 (申德泳词 ,1943年)等抒情歌曲就很好地体现了上述特征。
《故乡月》是一首女高音独唱曲,它深情地表现了朝鲜民族悲伤的思乡之情。这首歌曲是以宫调式5音阶、3/4拍构成。尤其是3/4拍的节奏形态具有“半古哥里长短”②“半古哥里长短”是运用“古哥里长短”的一半节奏形态构成的长短。“半古哥里长短”是古哥里长短的后三脚,着重点位于第五个拍子上。中的对称关系,形成一种长短形象。而“半古哥里长短”是 6/8拍,一个小节由 3/8+3/8拍组成,前一个 3/8拍是前角,后一个 3/8拍是后角。《故乡月》中,第 1~ 2小节是前角的节奏形态,第 3~ 4小节是后角的节奏形态。这体现了“半古哥里长短”的对称关系特征,呈现出独特的形态,即在一唱一和的对称关系中表现出典型的统一性与一定的形象意义。
作品将韩国的传统 3节拍节奏“半古哥里长短”适当地与西方的 3/4拍相结合,实现了韩国传统节奏的现代转型,从而使其更符合现代音乐的美感,“谱写时应该是考虑到了韩国传统的‘长短’概念”。[2](210~263)
西方进行曲的节奏特征多见于韩悠韩的军歌作品中。《黎明之歌》、《飘去的云》等歌曲虽然以4/4拍为主,同时也适当地使用了3/4拍或2/4拍,从而通过节奏的变化实现了音乐性的变化。而《光复军第二支队歌》、《新出发》、《光复军歌》、《祖国进行曲》等歌曲中的节奏极具特征,尤其是《祖国进行曲》是一首 4/4拍、西方七音阶、C大调与a小调式混合的进行曲,因为使用附点,具有强烈的推进力,给渐次提升的旋律赋予了强有力的统一性。同时,从第9小节到第11小节利用三连音、鲜明的强弱对比以及附点音符带来的推进作用等,都是在以往中国和韩国的民歌节奏中不具备的。
如上所述,韩悠韩为了尝试使传统音乐向现代音乐的转型,接受了西方音乐的节奏。尤其是因为传统节奏无法很好地承载现代情感,韩悠韩试图将西方的节奏形式融入到韩国和中国的传统音乐中,以探索全新的节奏。
(二)韩悠韩音乐的混融性体现在作品旋律的构成上。
从音响学角度看,旋律只是音的连续,从心理学的角度则是音的材料被赋予艺术形式的方式之一。韩悠韩作品在旋律构成上体现了中国音乐与韩国音乐的整合以及对西方音乐与日本音乐的接受等混融性特征。例如,歌剧《啊哩郎》中的插曲《牧歌》、儿童歌剧《丽那》中的插曲《流浪人之歌》和歌曲《朝鲜的母亲》。
《牧歌》是体现中韩两国音乐混融倾向的代表作。这首歌曲是以 4/4拍构成的纯粹的“lado- re- mi- sol- la”五声音阶,使用了“lami/re- la”完全 4度相连接的基本框架。
这首歌曲与 1934年录制唱盘的韩国新民谣《姑娘小伙》(具完会作词、金骏泳作曲)有着相似的音程结构和旋律进行,只有调性、调式、节拍以及终止式不同。《姑娘小伙》的第 13~16小节采用 Si- la- so- mi-re- do- la旋律法,si音只出现在主音域范围的 10度中的 8度以上音组中,只是作为修饰 la音的装饰音使用,对总体结构没有影响。
《牧歌》的第 9~ 12小节的乐曲结束处,以羽调式的主音la的完全 4度上行re音终止,形成不完全终止式。这种不完全终止式在中国的黄梅戏音乐中极为常见。采用其他调式的主音作为终止式,形成了色彩反差。这种韩国式的明快旋律与“安挡长短”的节奏形式,对于期待和平时代的大众而言是一种“田园的风格、轻快活泼的旋律”[3],取得了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的音乐效果。
儿童歌剧《丽那》(1937年)[4]是由韩悠韩自编、自导、自演的首部综合艺术作品,其中的插曲《流浪人之歌》采用了极具哀伤感和东方色彩的5声调式,以2度、3度音调为主。其进行方向是从第一段落的高音向下滑落,以跌宕起伏的旋律表达了远离故乡的人内心的寂寞与悲哀。同时,这首歌曲的歌词语言的音调与旋律的音高形成了统一。歌曲的旋律严格地使用中国语言的四声调,旋律的进行与歌词的声韵紧密结合,准确地表达了歌词的内容。歌曲的音域为d1— f2,由于从d2到f2的最高音域开始,在动机部分明确了d调式的色彩性质,使作品具有丰富的内涵,情感上更为符合东方人的思想情绪。
儿童舞剧《胜利舞曲》的第一段落《农村舞曲》是剧中农村姑娘跳舞时的舞曲,与中国北方民间歌曲“对花”①我国北方广泛流行的一种传统小调。歌唱者以互相问答、对猜花名的方式比赛智能、传授知识、娱乐嬉游。它的演唱形式也很多样,有的用乐器伴奏,有的伴以锣鼓边舞边歌。相似。但这首舞曲没有使用中国民歌中常见的la-do-la终止式,而是使用韩国新民谣中多采用的la-sol-la,给整首曲子增添了独特的色彩。
如上所述,韩悠韩的作品体现了其对中国音乐营养的吸收。究其原因,是因为他自幼生活在中国的北京、上海等地,得以广泛地接触中国音乐。韩悠韩曾经在回忆录中称,他从中学时代起就深深陶醉于中国的说唱艺术,中学三年几乎天天到茶楼欣赏“三国志”、“水浒传”等表演。[5]音乐天赋颇高的韩悠韩后来进入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学习音乐,系统学习了作曲、和声、钢琴等西方音乐知识。
(三)韩悠韩音乐作品的混融性还体现在对西方音乐与日本音乐音阶整合与借用上。
韩悠韩作曲的《朝鲜的母亲》(申德泳词曲)中就有西方 a小调和声音阶与日本“四七拔音阶”的混融。第1乐句,即动机部分的最核心音型“四七拔音阶”的“la- fa- mi”下行音型在第 1、第 3、第 4乐句中都有使用。
第 1、第 3、第 4乐句的旋律进行是由不同节奏形态组成的同一音型,使用了移度法,第 4乐句的最后一个乐段使用了“四七拔音阶”。第4乐句的旋律进行具有“四七拔音阶”的上行旋律“la-si-do”因素,终止式则以西方和声小调的属和弦的主音到主和弦的主音结束。
第 2乐句的旋律进行与第1、3、4乐句不同,使用西方和声小调式的“la-si- do- re- mi- fa-#sol- la”的正三和音 (主和弦 )和Ⅴ (属和弦)进行,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特色。
这部作品的整体虽然是由 4个乐句组成的单 1部西方a和声小调式,但是由于反复使用日本“四七拔音阶”的“la-fa- mi”下行音型,从而部分接受了日本音乐的旋律,体现出韩悠韩音乐的混融性特征。
此外,《陕西第二保育院院歌》(宋凯沙词,1941年)是大小调式相互结合的旋律,第 1乐句使用了西方作曲技法——扩大法。即,第 4小节的旋律“mi-#re-ml”加倍延长了第 1小节动机部分的核心音型的节奏形态。
第 2乐句使用了西方作曲技法——移度法。即,第 8小节中将第 6小节的旋律音型“si- la- fa- mi”降 4度 ,以“ fa-mi- re- do”的旋律音型进行。
第 2乐句的特征具有日本“四七拔音阶”—— “la- si- do- mi- fa”的旋律进行特征 ,反复使用“la-fa-mi”的下行旋律 ,体现出东方音乐的特征。
有些研究者认为,这部作品具有韩国音乐的风格和中韩音乐混融的特色[6](45)。但是笔者认为,这部作品的总体旋律进行是以日本“四七八音节”和西方调式b自然小调式音阶进行的。
三、结语
中国著名的音乐研究家梁茂春将韩悠韩评价为“天才的艺术家和杰出的爱国者”。的确,韩悠韩为中国的抗日斗争和韩国的独立运动献出了全部的热情与精力,是一位杰出的抗日斗士和天才的音乐家。韩悠韩以其革命生涯和艺术成就,在中国和韩国的政治文化交流史,尤其在中韩两国的现代音乐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足迹。
韩悠韩通过跨文化体验获得了多元的意识倾向,在其艺术创作中体现为混融性特征。在音乐构成上,尤其在节拍、节奏、旋律上中国音乐与韩国音乐乃至西方音乐的混融,赋予了韩悠韩作品的音乐现代性美感的创新性,这证明了艺术创作实践中跨文化视角的重要性。韩悠韩的跨文化视角使他发现了民族艺术之间的差异,促使他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接受其他民族艺术的优秀因素,并最终在现代歌剧和军歌创作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韩悠韩极具进取性的艺术创作精神堪称后世艺术家们的楷模。
不可否认,混融性同时也给韩悠韩的音乐创作带来了一些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如韩悠韩的部分作品没能体现出鲜明的创作个性。对此,还需要更深层的探讨和阐述。总而言之,对韩悠韩音乐创作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阐明东亚现代音乐的发生发展以及中韩音乐交流史的诸多特征。
[1]钟立民编:《难忘的旋律》,北京:知识出版社,2001年。
[2]金昌旭:《韩亨锡的光复军歌研究》,《港都釜山》,2008年。
[3]梁茂春:《中韩音乐交流的一段佳话——音乐家韩悠韩在中国》,《音乐研究》,2005年第 1期。
[4]韩悠韩、李嘉合编:《新歌剧插曲》,西安:新中国文化出版社,1940年。
[5]韩悠韩:《韩亨锡回顾录—— 我的人生,我的成就》,《釜山日报》,1977年 9月~ 11月。
[6]梁茂春:《中韩音乐交流的一段佳话——音乐家韩悠韩在中国》,《音乐研究》,2005年第 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