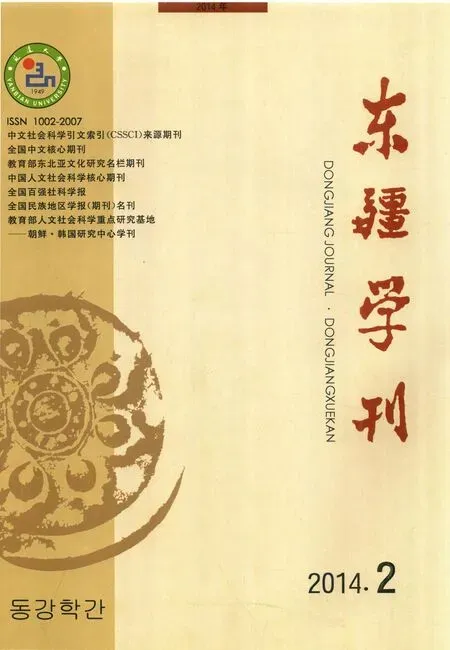论日本明治时期中国语教科书的“政治化”倾向
于冬梅
[责任编辑 全华民 ]
近几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日本明治时期中国语教科书语言,并且有了一些新认识。比如在汉语史、汉语语言学史以及在世界汉语教学史上的“国别”价值研究上取得的成果,等等,尤其是李无未教授等人贡献突出。①李无未等:《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课本语言研究》,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2012年结项成果。但也不能否认,有关日本明治时期中国语教科书“政治化”倾向的研究还有不足,更未能系统化加以研究,所以需要进一步分析和梳理。
一、明治时期日本汉语教科书的“政治化倾向”
《满洲语会话一个月毕业》[1](以下简称《会话》,1904)是一本日本人编写的,供日本人学习东北官话用的初级教科书(按:《会话》作者据其《序》是石冢猪男藏。他作为日军的翻译,随军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后来又来到了东北。)
其体例,先是本书的“说明”,然后有正文计80页。第一编 ,词语类;第二编,散语类;第三编,问答类。无论是词语,还是问答会话都有相应的日语对译。其编写缘起于作者自己的调查,他编写的“应用日常必需”的会话书,也是由官话“本音”而理解“土音”的。
其第三编“问答类”有这么一段对话,其中有“日本兵规矩得很哪!俄罗斯兵很不规矩枪(抢)东西杀良民。我救他。我打他他逃去了”,俄罗斯兵“他们枪(抢)了一匹马”等信息。
《会话》是一部教科书,教学对象是日本人,它折射出了日本人非常明显的政治意识,宣传和引导的政治化倾向十分突出。它实际上也反映了一个真实的历史事实,即在中国领土上为争夺东北控制权而爆发的日俄战争的一个片段。从1904年 2月 8日日本袭击旅顺港俄军舰队,到 1905年3月11日奉天会战结束,日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关于这场战争,许多学者已经做过研究。本书应该是在战争期间编写的,战争结束后不久就出版了。
这些中国语对话说明了什么呢?第一,在中国的土地上,即沈阳到大连一带,日本兵和俄国兵恣意横行,好像在自己的国土上一样自由行动。第二,褒日贬俄。通过老百姓的口,说俄罗斯兵不规矩,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而日本兵“规矩”,花钱购物,非常文明,其政治倾向一目了然。第三,侦察俄军动向。比如俄军来过否、做了什么及人数等。很显然,编写对话者,是在其“政治化倾向”指导下突出了政治性目的和潜移默化的教学效果。
二、折射出日本“拓疆殖民”的政治目标
《日清韩三国通语》[2](1894),天渊著,是一本以日本人学习汉语、韩语为主要目的的教科书。该书无论是汉语,还是韩语的词汇、会话,都有日语翻译。其《序言》直言不讳地道出了编写的政治目的。
同样,圆山真逸编《汉语问答篇》(1895)[3](5)也是如此。比如宫川律在《序言》里说:“兵法云,知彼知己。盖为此语,乃作战行军之诀。行旅通商于域外者,不守此语,不速败衅者,殆希也。圆山大迂,久游清国,语人以此四字,可谓得其概者也。”虽然迂曲委婉,但为了“知彼知己”而学汉语的目的性昭然若揭。
田墨介为《汉语问答篇》所作的“序”则比宫川律《序言》更为露骨:“日清开战,发军于海外,彼我言语不通,是最为不便。我县士人学华语者,奋然应募,续之从军。华语之用,固为紧切矣。……本邦屹立东洋,势与清国为唇齿,背则公争,和则邻交。战时探刺情、抚降伏、施政治,非通华语不为便也。平时访风俗、察形势、行通商,非通华语不为便也。”
中日甲午战争,是 1894年 7月末— 1895年 4月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汉语问答篇》的编写应该是在战争期间,所以,它也是以备日本侵略战争之急需的产物。无论是夸耀日本人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所谓的战果也好,还是以日本“与清国为唇齿,背则公争,和则邻交”所表现的虚情假意的姿态也好,都离不开为实现其“拓疆殖民”政治目标所采取的实际行动,教科书的编写当然是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之一。
三、灌输中国知识,渗透情报意识
日本军部情报机构介入日本中国语教科书编写出版事宜,有着十分明确的目的。
1879年6月,日本人广部精出版了第一部日本编写的北京官话教科书——《亚细亚言语集支那官话部》(七卷),另有总译本《总译亚细亚言语集支那官话部》(四卷)。它是以威妥玛《语言自迩集》(1867)为底本编写而成。[4](113~117)
这样一部重要的北京官话教科书编写缘由、编号人员与内容架构如何呢?六角恒广《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1992)[5](113~117)分析:编写人员主要是一些军部人员,比如陆军少尉益满邦介,他曾去上海、天津等地侦察清朝对台湾的动向,以便为日本“征台”作前期准备。陆军曹长中村义厚和陆军曹长大尉野崎宏毅也都是日本军部派谴到中国侦察地形、地理、军情、政情的谍报人员。其他9个人也大体和日本军部有关。六角恒广虽然没有明说,但也肯定了广部精的身份与日本军部关系密切。
1879年 11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派遣 16名军人去北京学官话,实际上是培养谍报人员。后来,这些人中有一些在编写中国语教科书上非常卖力,比如御幡雅文 (参与《华语跬步》,1886年;《官商须知》,1889年;《便商沪语》,1892年 )、平岩道知 (《日清会话》,1894年;与金国璞合编《北京官话谈论新编》,1898年 )、原田正德(《日清会话》,1894年 )、木野村正德 (《支那语学教程》,1901年)等。其中,《北京官话谈论新编》渗透着比较强烈的情报意识。后来的《言文对照北京纪闻》[6]则更是如此,已经不像是教科书了,而是地道的北京情报大汇要 ,其“目录”就表现得非常明显。比如:“目次”就有“车站外移、蒙王到京、比使到京、整顿税务、北京开埠、蒙王练军、流通圜法、俄兵入藏、旅顺戒严腾踊、建路踌躇、伊犁金矿、邮政分局、工巡分局、密查出票、学界风潮、商报购机、诽笑练兵、各部总署、伪票欺人”等各类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信息。
其中,第五十六,“旅顺戒严”:
文言语体:近接旅顺友人来函云,屯扎旅顺之俄兵日日操演,近颇(频)戒严,其守垒台者,日以习放大炮为事,非有凭照不能近垒台一步,并每日夜间有俄兵出外梭巡,远望兵营,电灯如星,云云。
北京官话白话语体:近来接到旅顺的朋友来信,说是旅顺口屯着的俄兵,天天儿操演,防备的很严,那守垒台的兵,见天演放大炮,没有执照,不能到垒台近处去,并且,天天儿夜里有俄国兵出来巡察,远处一看,那个俄国的兵营,电灯如同星星似的。
第七十三“川汉铁路”:
文言语体:四川旅京及各埠商人禀请商部,承修川汉铁路,共计章程二十条,计自汉距蜀四千一百余里,所需经费五千万两,专集华股,其一切用人运料,统用中国自己者,以免利权外移等语,尚未知商部如何批示。
北京官话白话语体:在北京和各口岸的四川商人商量,禀请商部,要承修川汉铁路,共总订了二十条章程,从汉口到四川,通共四千一百多里地,得用五千万两的经费,专招华股,所用一切用人用料,都要用中国自己的,免得利权到外人手里,还不知道商部是怎么样批下来的呢!
按,前者是军事情报,后者是交通建设情报。作者对课文的原始文献的选取是别有用心的,一切以学习和理解情报为中心。
胡平著《情报日本》[7](30)专门辟有“明治时代的情报活动”一章,对日本政府和民间参与收集中国情报活动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可以参见。它说明,在日本明治时期,一些日本人热衷于学习汉语,并且极力主张通过编写汉语教科书来向日本军事人员灌输情报意识,这是他们情报活动的再延伸,以及“汉语政治情报意识”理论的进一步强化。
四、体现出语言暴力倾向[8]
教科书一旦进入了公共性领域,其语言的选用就要受到公共性领域的科学规范的制约,并最大限度地抵制语言暴力在教科书中的浸染,这当然是国家语言制度所赋予的学术权利。如果抵制语言暴力的国家语言制度缺失,教科书充满语言暴力就会成为现实。日本明治时期奉行的是国家扩张政策,其语言政策也与此相契合。语言政策的附庸地位决定了其编写的中国语教科书必然沦为政治化的产物,语言的选用也没有受到公共性领域科学规范的制约,所以,必然出现语言暴力现象。
日本明治时期中国语教科书充斥着“语言暴力”,比如《支那南部官话》[9](1895):“狗入的”、“该死的奴才”(24页);“狗奴才”、“捏狗屁”(25页);“放什么屁”(245页);《满韩土语入门》[10]“我们不知道俄国兵有没有?你若撒谎我杀你!”(42页)。这种“语言暴力”的政治性倾向是十分明显的,其以低俗化的汉语表达方式代替高雅的汉语表达方式,故意丑化汉语,玷污了汉语的纯洁性。日本大正、昭和前期所编写的中国语教科书,有相当一部分存在着“语言暴力”问题,不言而喻,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日本明治时期中国语教科书“语言暴力”影响的结果。[11]
五、体现了话语霸权
以中介语代替常规汉语。所谓中介语是指第二语言学习者建构起来的介于母语和目的语之间的过渡性的语言。日本明治教科书以带有日语特征的汉语替代规范汉语,就是要有意识地改造汉语,让汉语变成日语的变种。《北京官话常言用例》[12](1905)第 11页:
例 1.年轻的人总要“勉强”用功,古人也说过,少年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按:“勉强”,日语是学习的意思。日语汉字词,这里借用不妥当,还是用“读书”或“学习”更好一些。
例 2.孩子们很多,越过越穷的。(同上)第 12页:
按:“孩子们”,已经指很多的孩子,表复数,谓语又在强调“很多”。正确的表述应该去掉“们”。
有一些现代汉语常用语,其实已经被“日式”词语替换,这种情况,从与明治时期中国语教科书对比上就能够看出来。以下是《最新清语捷径》[13](1906)的第 10、 12、 14、 17页的部分内容。

汉 语 日 语 汉 语 日 语来历 沿革 火药 焰硝酒席、宴会 宴会 领儿 襟领带 襟饰 缓限 延期岔道 枝道 救兵 援兵结亲、作亲 绿组 算命的 易(第 10页 )开仗 开战 洋布 金巾胜仗 胜军 佩服 感服执照、腰牌 监札(第 12页 )好运气 幸运 海腰 海峡换替 换わゐ 商量 挂合收帐的 挂取 造化 幸福细作 间者 交情 交谊白醭 微 硬 固い定神、决意 觉悟 兜儿 衣囊单子 书付(第 14页 )挂心、悬心 气挂 左近 近处古板 旧弊 规矩、章程 规则仿造 伪造 打听、听见 闻工钱 给金(第 17页 )
如上所示,正式场合不用“酒席”而用“宴会”;说“开战”不说“开仗” ;说“海峡”不说“海腰”;说“援兵”不说“救兵”(除口语外);说“沿革”不说“来历”;说“枝道”不说“岔道”;说“感服”不说“佩服”;说“衣囊”不说“兜儿”;说“给金”不说“工钱”;说“间者”不说“细作”。这种语言的借用,不是语言的自然借用,而是编写者有意而为之,基本方式就是“偷梁换柱”,让人们误以为当时的汉语常用词语就是如此,人们丝毫察觉不到它的“替换”,但它却在悄然改变着汉语的自然生态,危害了汉语的正常发展变化,这种替换将汉语“日本语化”的意识十分明显。
根据语言异质化理论,两种语言在直接接触中,会因语言特点不同,语言承载的社会文化内容不同而互相影响产生变异。日本明治时期中日两种语言的互动,尤其是中日汉字词汇的互动,是处于由日语向汉语“逆输出”状态,这是中日学界公认的事实。但是,这种“逆输出”的缘由却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先于中国研究与引进西方科学知识与社会制度,他们借用中国汉字词或利用汉字造新词,来翻译西方先进的人文、科技书籍,因而产生了大量的现代汉字词。这些词通过旅日华人和留日学生的文章、演说得以传播,随着中国人对西方的学习与研究,自然地融到了汉语系统中,成为现代汉语里的生力军。这种语言的“异质化”现象,是汉日两语在各自发展道路上自主选择、自然相遇的结果。其二,伴随着日本军队对中国军事上的胜利而发生了汉、日两语非自然的具有强暴色彩的特殊接触。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随着日本入侵中国、攫取满洲策略的实施,日本人编写的各类日中词典、实用中国语教科书增多了。其中充斥着日式汉字词,协和语的政治用语、军事用语、日常生活用语及口语会话占据了突出位置,为日本军人、情报人员、商人、公司职员在中国的行动与生活提供汉语帮助的意图非常明显。实际上,这是一种“政治意识”下的语言“侵略”行为。
到了大正时期,日式协和语对汉语的改组和侵袭更加肆无忌惮。如“支那”、“大东亚共荣”、“协和”、“皇军”、“慰安妇”、“良民”、“花姑娘”等汉字词的频繁使用,口语中“米西米西”(みし:吃、吃饭 )、“要西要西” (よし:好 )、“开路”(かえる:走、回去)、“死了死了的”(让你死)、“大大的好人”(非常好的人)等的广泛普及,甚至日本的国骂“八嘎牙路”(ばかやろう:傻瓜、混蛋),都变成了中国北方的流行语,给汉语的自然生态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与破坏。
伪满洲国成立以后,日本则完全摒弃了汉语,公然实施奴化的语言教育政策及语言管理方式。当时的小学、中学每天升日本国旗,唱日本国歌,国语课本全是日语,学校里禁止使用汉语。连从农村抓来的劳工,集合时都要用日语报数,凡是说错的都要挨打受罚。这种政治高压下的语言接触,人为地抬高日语,打压汉语,使被统治的汉语母语者失去了母语话语权,这是日语消灭汉语,进而取代汉语的非正常的“异质化”现象。
而同时期的汉语,无论在中国本土还是在日本,都处于弱势地位,对日语的影响微乎其微,逐渐丧失了对等的话语权。
六、结论
强调日本明治时期中国语教育的政治化因素,不是说其语言学、教育学、历史学视角研究不重要,而是说明治时期日本中国语教育的兴起与日本明治时期军国主义政治意识紧密相关,这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徐艳对政治概念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解释:“政治这个概念在西方也并非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概念,建筑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基础上的本体论政治概念,其核心是一种国家对行为和道德的规范;而 Niccolò Machiavelli的现实主义政治范畴则是对权力的阐释,韦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把政治定位在敌我关系的处理上。马克思主义有关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政治关系的阐释我们都是比较熟悉的;而法兰克福学派则在继承了某些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泛政治论,即在非意识形态、非政治化中寻找政治,政治存活于文化、技术等载体中。近年来,实验社会学则认为,上述种种学说没有采用科学的方法,对政治给予量的定义,这个流派把政治视为形式(即结构)、内容和进程的三项组合,政治即是在一定政治结构下,借助某种政治进程来对一定政治内容的实现。”[14](62-79)
日本明治时期中国语教科书政治化内容,是日本明治政治结构下推行其政治进程的特定产物。政治存活于中国语教科书这个载体中,我们就是要通过对中国语教科书政治化内容的挖掘,而实现对这个时期政治结构的基本认识,从而明确日本明治时期中国语教科书政治化的基本性质。
[1][日 ]石冢猪男藏:《满洲语会话一个月毕业》,东京:石冢书店 ,1904年。
[2][日 ]天渊:《日清韩三国通语》,东京:薰志堂,1894年。
[3][日 ]圆山真逸:《汉语问答篇》,熊本:圆山真逸出版,1895年。
[4][日 ]六角恒广:《中国语教本类集成》,东京:不二出版社,1994-1997年。
[5][日 ]六角恒广:《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
[6][日 ]冈本正文:《言文对照北京纪闻》,东京:文求堂,1904年。
[7]胡平:《情报日本》,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
[8]袁伟时:《语言暴力的根源》,《经济观察报》,2009年 1月 19日。
[9][日 ]小仓锦太,金泽保胤:《支那南部官话》,东京:博文馆 ,1895年。
[10][日 ]平山治久:《满韩土语入门》,东京:博文馆,1904年。
[11]王承君:《语言暴力的认知条件及对策研究》,《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2007年第 2期;郑超越:《语言的暴力》,“博客中国”,2011年 4月 12日。
[12][日 ]小路真平,茂木一郎:《北京官话常言用例》,东京:文求堂 ,1905年。
[13][日 ]西岛良尔:《最新清语捷径》,东京:青木嵩山堂,1906年。
[14][德 ]徐艳:《晚清的外语教育及其政治层面》,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