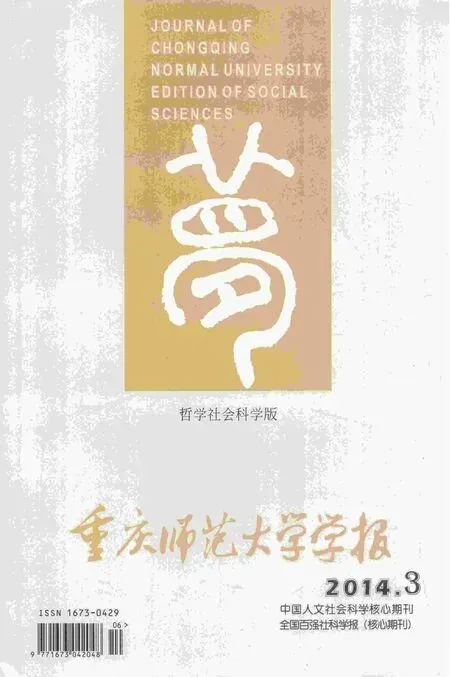流动的性相与身份的确立——酷读《紫色》
李雪梅
(四川文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四川 达州 635000)
艾丽丝·沃克在美国当代文坛上的地位已经家喻户晓,她的作品在世界各地广为传颂。近十几年来,专注于黑人女性文学研究的学者们对她的作品表达了较高的研究热情,对其作品,学者们从黑人女性主义、文化定位、女性的书写、后殖民主义理论等多角度进行了解读和研究。搜览这些研究成果,却极少有人从酷儿理论这个视角解读艾丽丝·沃克的作品,但其作品中独特的黑人女性形象显示了黑人女性在成长过程中,身份的最终确立与她们打破传统男权统治,大胆地进行性探索密切关联,酷儿理论为这种身份的抗争与诉求提供了很好的解释视角。黑人女性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原因遭受到种族压迫和性别桎梏,女性之间常常存在一种相互依赖、相互帮助、共同谋求生存的同性情感欲望。这种同性情欲帮助她们在主流社会里寻找了自己失落的身份而走向人格独立,为形成良好、和谐的黑人性别关系奠定了基础,因此,酷读《紫色》无疑拓展了黑人文学的研究广度和深度。
对于艾丽丝·沃克的《紫色》,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酷读《紫色》,沿着作品中茜莉、莎格以及索菲亚这三个黑人女性纠缠于性相的人生经历,从性/别的维度探视人物的心路历程:女主人公茜莉从被动的,压迫的异性恋情流向同黑人女歌手莎格的同性恋情,这种性相的流动促进了她人格的独立和主体的建立;另一位女性角色莎格在这复杂的异性恋社会里经历了痛苦的、被人歧视的异性初爱,虽然强烈的爱情支撑着她勇敢地走过无数岁月,但传统的社会规制永远把她排挤在主流之外,而茜莉的爱抚慰了她受伤的身心,使她更加自信和完美,个人价值得到更大的展现;索菲亚婚姻遭受异性恋男权的压抑和损害,经过抗争,勇敢地打破了异性恋性别特征的桎梏,并帮助爱人走出了强制的男权误区,最后走向完美和谐的婚姻。她们的故事颠覆了传统社会的性/别规制,展现了黑人女性在摆脱种族和性别压迫的过程中,同性之间由互相理解、帮助发展到了热爱。她们顽强挣扎最终获得了身体和精神自由的表达权。她们大胆的性实践不仅颠覆了异性恋强制传统——男权中心主义,而且为建立完善的、和谐的性别关系提供了有资可寻的参考。本文拟从酷儿理论的视角走入三位黑人女性的生活和内心。
一、性/别的解构
“酷儿”是由英文queer音译而来,本意是“怪异”的意思。起初,性学家借用这一词来概括所有被社会常态边缘化的激进的反主流文化的同性恋群体,后来,“酷儿”包括所有在性倾向方面与主流文化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性别规范或性规范不符的人,既包括男女同性恋、双性恋也包括所有其他潜在的,不可归类的非常态的人群。[1](54)20世纪90年代开始,酷儿理论在西方社会广为流传,本理论杂糅了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以及福柯的话语权等复杂的哲学思想,二十几年来,一直受到很多学者的关注,其基本理论被用于社会学、文学艺术甚至政治学领域的研究和应用。“酷儿理论是一种质疑和颠覆性与性别的两分模式,挑战男权文化的思想武器。”“它将会彻底改造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使所有排他的少数群体显得狭隘,使人们获得彻底摆脱一切传统观念的武器和力量。”[2]它是对异性恋男权制度冲击和颠覆最为彻底的理论。
酷儿理论的一个重要使命是解构同性恋和异性恋的两分结构,它认为异性恋传统的性相并非天生的生理构造,而是特定社会文化建构的结果。在传统的社会体制里,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确保人类社会的繁衍,把以生殖为目的的异性恋规制为社会常态,把同性恋和双性恋确定为社会异态。然而,性异态在人类社会中却客观存在,“根据金西报告,有50%以上的男性和30%以上的女性在一生中曾经有过同性性行为经验”[3]。弗洛伊德曾提出了具有颠覆潜能的原初双性情欲说,认为人生来就具有两种性相,异性恋不是人类初期唯一的性样态,他企图解构异性恋传统的自然天成的假说,但是,以弗氏为首的心理学家们又因其男性自身的利益提出了阳具中心论,阻隔了双性情欲说的发展,否认了原初同性情欲。在此基础上,著名的哲学家、女性主义者和酷儿理论的开山鼻祖朱迪斯·巴特勒发展了弗洛伊德的理论,认为同性恋,异性恋或双性恋都不是由固定的性别身份决定的,人类的性相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许多时候是模糊不定的,常会发生变化。在她看来,获得自身身份的称呼并不是终点,身份是不断建构的过程。[4]巴特勒的理论重在消解性相的二元对立,还原人类性相多元化和多样化,反对对性少数群体的压迫。
酷儿理论的另一使命是解构男性和女性的二元论性别结构。巴特勒继承和发扬了女性主义理论家波伏娃在《第二性》里提出的观点,“一个人不是生来就是女人,而其实是变成的。”[5](301)和伊里格瑞提出的女性不是一个性别,是男权话语的一个虚构,她认为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性相这三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传统异性恋规制(人的生理性别决定其社会性别,社会性别决定其异性恋的欲望)只是一种生物假设,即女人是女性就具有女性气质,欲望对象是男性;男人是男性就应该具有男性气质,欲望的对象是女性。酷儿理论认为“人的社会性别并不严格对等于其生理性别——男女两性的界限长期模糊不清,即女性身上可以同时存在男性的特质,男性也可能具有某些女性的特点。”[1](67)酷儿理论的去性别属性的自然化的努力为女权主义质疑性别压迫做出了重要贡献。
酷儿理论起源于女性主义,经过发展深化明显有别于女性主义,在解构传统父权话语及体制、解放女性和性少数异己方面,又较之于女权思想更加彻底深入。对传统性别文化的解构是酷儿理论的中心议题。在《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一书中,巴特勒借鉴福柯的谱系学方法批判性地重读了女性主义和精神分析有关性别的重要理论,提出了具有开创性的论点:生理性别的文化建构性,原初同性情欲禁忌与它造成的抑郁异性恋结构,以及基于这些批判分析而提出的性别操演理论和性别戏仿政治策略。[6]巴特勒认为:“性别是通过一系列行为的因袭与重复建构起来的某种内容空洞和不足为信的东西,并不是某个天衣无缝的内在身份的表达,也不是决定人们行动的本质基础....性别本身是经由行为举止的不断重复而得以形成的,这些行为总是试图接近那个拥有着某种物质根基的身份理想,但是,它们身上间或出现的不连贯性却揭示了……这一根基的无所依傍。”[7]141这是酷儿理论性别建构的重要思想:性别不是先天的生理存在,而是后天的文化建构;性别不是静止的状态,而是建构主体的流动的过程;性别不应该成为社会规制的一个固定符号,对性别的建构为打破这种囚笼提供了多种可能。
然而,正如有学者指出:“时隔20年,证诸女性主义的发展,巴特勒的激进性/别政治构想似乎并没有对女性主义政治造成改弦易辙的改变。”[6]但现实的没有彻底改变并不标志方案的不可行,在黑人女性小说《紫色》里,酷儿理论的思想得到了较好的诠释,我们愿意把它看作是酷儿理论思想在黑人女性社会里的演绎。
在《紫色》里,女性人物在美国南方重建期间,深受各种压迫,挣扎在混沌的黑暗里,妇女之间的同性情感和性实践帮助她们重塑主体,在建立独立人格和寻求黑人社会美好和谐的人际关系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女主角茜莉的“出柜”,莎格双性之间的游离,索菲亚婚姻拐弯等酷儿现象展现了传统的男女性别二元论、同性恋和异性恋的二元对立的错误,从这些性相的流动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性别建构的曲折历程,感受到对女性主义政治的强大推动力量。
二、无奈“出柜”的茜莉
女性主义者艾德里安娜·里奇的“女同性恋连续统一体”理论认为:“存在于女人之间与之中的各种强烈感情,包括对丰富内心生活的分享,对男性专制的抵抗,对实践及政治支持的给予与获得,以及对女性性爱关系的珍视。”[1](77)茜莉在小说的前部是一位被损坏的黑人妇女形象,父亲被白人私刑处死,母亲病重,继父在她十四岁时就强奸了她,并生下了两个孩子,后来继父卖掉两个孩子,强行把她嫁给了一位有四个孩子的鳏夫——X先生。她是X先生的性奴隶,孩子们的保姆,家庭经济来源的主要劳动者,还经常受到X先生的殴打和孩子们的歧视。生活对于茜莉来说已经变得麻木,只能像一颗树一样毫无感情的活着。[8](23)在由92封书信组成的小说中,茜莉曾求助上帝,给上帝写了五十几封信,但命运并没有得到改变。茜莉本能地对男性产生心理障碍,“我连男人都不敢看一眼,这是真的,我看看女人,哟,因为我不怕她们。”[8](35)莎格、索菲亚以及妹妹聂蒂等黑人女性开启了茜莉的自主意识,帮助她成长为独立的主体。莎格无疑是黑人妇女反抗男权的精神领袖,“莎格是上帝的化身,是摆脱男性压迫而骄傲又自由生活的女皇。”[9]儿媳索菲亚无论从体格上还是意志上都不屈服于夫权的压迫,她敢于漠视白人种族的优越,顶撞白人市长夫人和殴打市长。妹妹聂蒂为躲避继父和X先生的性骚扰,追随宗教组织流浪到非洲,这些黑人女性捍卫自己尊严的努力深深震撼了茜莉,是茜莉勇于生存下去的楷模,而最终启迪和改变茜莉的却是莎格的同性爱。
莎格是茜莉崇拜的对象,不仅是因为莎格性感洒脱,而更多的是莎格独立自主,能够游离于男人的控制之外,有时还能牵制男人。长期以来,菲勒斯中心主义通过贬损女性的身体来建立父权的威性。认识身体是莎格带领茜莉走出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第一步,莎格通过抚摸和亲吻茜莉的身体,教她认知和激发茜莉体内的原初多元内驱力,逐渐消除了对性的恐惧和厌倦心理,体会到在性爱中自身价值的存在和两个相爱的人之间平等美好的关系。身体的复苏迎来了对身份的追问,“在这长期被人们遗忘和低估的战场:身体”[6]里,她们赢得了胜利的第一步。在莎格的启发下,茜莉学会了与心爱的人分享丰富的内心生活,不再把命运的一切寄托在对上帝的祈祷上,为了自身的权利她拿起剃须刀指向了对她作威作福多年的X先生,最终走出了男权藩篱,随同性爱人莎格去孟菲斯。在孟菲斯,莎格鼓励和支助茜莉开始自己的全新生活,创建了“大众衬裤非有限公司”,开创了自己的事业,茜莉通过自己的艺术审美观缝制各式各样的裤子,实现了人生的价值。
经济的独立给茜莉带来了尊重和自信,促使她的人格更加完善。“打破欲望规范化,释放身体,在此时此刻,实实在在的欲望行动中获得自由和主体意识相互认同是酷儿理论的主旨追求。”[10]在异性恋男权社会制度里,茜莉身份的确立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斗争过程,她遭受到了贬损,身体被物化,精神被愚化,一度使她产生自我否定,异性恋对茜莉的摧残使她对同性敞开了心扉,是莎格的爱开启了茜莉丰富多彩的人生。从异性恋流向同性恋是她人格独立,身份确立的必然过程,在小说的后半部,茜莉已经成长为一个成熟、自信、独立的女性。正如有人说:“茜莉并非天生的同性恋者,而是她特殊的悲惨经历逐步促成了她与异性恋的背离。”[9]
引导茜莉认识自己的身体,并享受到来自同性的爱抚,从而唤起自尊和自信的莎格并不是一个坚定的同性恋者,如酷儿理论质疑男性和女性的绝对的二元论性别结构一样,莎格并无固定的性相,而是游走于双性之间。
三、游离于双性之间的莎格
蜜蜂女王莎格是一位深受黑人男性喜爱的女歌手,多少年来被黑人男性欲望却遭贬损,她以独特的方式独自地游走、抗争在充满敌意的黑人社会里。她曾经沉溺于一段狭隘的永不会被社会承认的异性爱中,黑人男权社会无数次对她的贬损、打击和摧残逼迫她走向黑人妇女之间的相互温暖和安慰的同性爱。她的感情经历了从全心全意想拥有异性爱人阿尔伯特,到最终觉悟虚伪的异性恋只能带给她沉重的伤害而无可奈何地放弃,再到发现和呼唤同性恋人的觉醒,共同揭发和批判异性恋。莎格的性爱觉醒唤醒了黑人女性独立意识的成长,在黑人妇女抗争性别歧视的过程中具有代表意义。
从异性恋的传统观念看,莎格被定位于一位出生下贱(母亲是妓女,没有父亲),行为放荡的坏女人。她性感是男性欲望的中心;她不依赖男人,却勾引别人的男人;她需要异性却从内心深处鄙视异性。母亲的身份从生命的开始就定位了莎格的人生,注定了她被男权社会边缘化的现实。莎格和阿尔伯特是相爱的,但由于母亲是妓女,她的爱情遭到男方父母的坚决反对。倔强的莎格却一直同恋人保持联系并生了三个子女,即便如此,她仍然没有得到社会和男方家庭的认可,恋人阿尔伯特被逼娶了另外的女孩,他的怯弱和屈服增加了莎格的痛苦,也使她的社会地位进一步边缘化了。
在这个异性恋男权社会里,莎格用充满磁性的歌喉吟唱自己的悲剧,她独立却遭社会贬损、她坚强却是悲愤的、她追求美好却命运坎坷。“莎格·阿维里病了,这镇上没人愿意收留这位蜜蜂女王。”独立拼搏多年以后,她身心疲惫,差一点死于非命。当她奄奄一息被阿尔伯特拖回家后,善良的茜莉悉心照顾使她慢慢恢复了体力,也重塑了她的精神。在这一过程中莎格了解了茜莉的悲惨故事和阿尔伯特卑鄙、自私、残忍地欺压女性的事实,认识到黑人女性的悲惨命运不仅仅与种族相关,黑人男权思想也是压制妇女的另一座大山。女性共同的命运让她充满对女性朋友的同情和正义,毅然弃绝了阿尔伯特,两个女人培养了超出平常女人之间的友谊,结成了牢固的联盟。莎格从原初的异性恋走向更为稳固的同性爱,变得更加自信和完美,事业也发展得更加辉煌,日子过得更加舒心。从对阿尔伯特的热爱到弃绝标志着莎格的自爱自强成熟经历,她的性相流动和变化无疑强烈地宣泄了黑人女性挣扎在强制性的异性恋男权中心的痛苦。
莎格和茜莉的同性爱是建立在抗争种族、性别压迫而形成的妇女之间的联盟之上的,这个联盟对于帮助唤醒黑人社区里其他人的意识有巨大作用,如果莎格和茜莉的同性爱是一种柔性的对男性性别统治抗争方式,那索菲亚则是用一种爆烈的抗拒男权和种族压迫的方式,注定了她的道路更为曲折和艰辛。
四、带弯的直线——索菲亚和哈泼
带弯的直线是指称所有那些观念“越轨”或比较“酷儿”的人,索菲亚和哈泼就是一对“带弯的直线”。他们俩相识、相爱到结合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婚后又共同拥有五个孩子,就在生活本可以过得平静美好的时候,哈泼脑袋里根深蒂固的菲勒斯中心的霸权观念阻隔了他们,传统的性别本质主义认为,男性和女性的生理差异决定男女社会地位的不同。“男性体格强壮,多参加社会活动,处于中心的、统治的地位。女性娇小柔弱,适合留在家中,处于从属的、被统治的地位。”[11]女性就应该成为“家中的天使”。“妇女不同形式的桎梏与压迫是通过性别化来施为的。”[6]哈泼希望象父亲一样主宰家庭和女人,而索菲亚却是一位非常有主见、能干的女人,喜欢从事各种重体力劳动,行为举止男性化。在以父亲为代表的男性霸权思想的影响下,哈泼决定回家惩罚妻子,可笑的是,上帝似乎有意开了一个玩笑,哈泼的男性生理特征并不强壮,索菲亚的女性特征也并不柔弱,她壮实而自信,经过几次身体搏斗,哈泼都以惨败告终,最终引起索菲亚的反感带着孩子离家出走。
传统父权制的性别观念是男性是主动、理智和强壮好斗的;女性则是被动、感性、柔弱和胆小的,但小说中的人物索菲亚和哈泼则很好地消解了这种传统的二元性别对立的规制。索菲亚作为女性,并不具有社会文化和话语系统设计的女性气质,哈泼也没有异性恋体制规定的男性气质,他俩的性格特征在小说中的自然流露充分表达了作家对社会性别规定的反驳思想,证明了酷儿理论的性别身份建构说的思想,“建构论者区别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将女性受压迫的原因归诸文化,以此反驳生理命定论,寻求打破以性别为基础而物化的社会分工与性别阶层”[6]。酷儿理论对性别二元对立的消解似乎更能阐释他们的故事。
哈泼在索菲亚离开之后找到了他心目中的“家庭天使”——斯贵克,她身材娇小玲珑,性格温顺,完全听命于他,哈泼的男性气质似乎得以彰显,然而当索菲亚带着拳击手再次出现时,哈泼的嫉妒和不顾新欢的感受纠缠索菲亚的行为都清楚地显示了哈泼真心的爱恋。后来索菲亚因殴打白人市长被监禁,哈泼的勇于承担迎来了前妻宽恕,两人终于言归于好。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认为男性并非一定具有男性气质,女性并非一定具有女性气质,这两种气质只是社会的一种规约。哈泼和索菲亚在婚姻路上的拐弯以及最终的拨正厘清了异性恋男权中心主义对两性间和谐共处的离间,他俩通过流动的性相和探索找到了真正和谐的爱。
对于代表异性恋男权的继父和X先生,命运给了他们不同的报应。自私、残暴无情的继父一生中给母亲、茜莉、梅、艾伦·黛西等数名女性制造了厄运,作者在小说的尾部宣布他离开人世。X先生残酷压制和迫害过茜莉,但是他性格软弱,优柔寡断,真心爱过,却不敢冲出黑人男权社会的传统观念间接伤害了女性,在结尾处他孤身一人,生活在恐惧和不安中,最后只能通过不停地劳动来减轻心中的负疚,作者安排他在赎罪中寻找宁静。对于其他的人物,作者给予了幸福美满的结局,对茜莉表达了高度的同情心,热情地赞赏莎格的反抗精神并给了她俩美满幸福生活的完美结局;索菲亚经历了种族和性别的压迫,作者极大地褒扬了她勇敢的抗争行为,哈勃最后的拐弯变直并重新回到索菲亚身边阐释作者对她的厚爱。
五、结语
酷读《紫色》不难发现,对小说人物命运的安排流露了作者对异性恋男权主义的因果报应思想。在小说的尾部,作者描绘出一幅黑人社会通过抗争而获取的两性多元和谐的大团圆的美好前景,在黑人社区创设了新的人际关系模式的理想社会,这种理想社会明显地颠覆了传统的性取向和规制的性别模式。“通过《紫色》,沃克对性别霸权与性别角色固定化思维模式发起了挑战,并明确地表达了建立平等和谐人际关系的良好愿望。”[9]这与酷儿理论在女权主义政治上的主张高度吻合。
巴特勒对身份的建构寄予厚望,对性相的流动保持乐观。她说:“将身份重新设想为一种结果,亦即被生产的或被生成的,这反而打开了‘能动’的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一开始就被那些将身份范畴视为基础的以及固定的立场给狡狯地排除了。将身份视为一种结果,意谓它既不是宿命地被决定,也不全然是人为的和任意的。”[12](191)关于巴特勒的乐观人们多少持怀疑态度,但酷儿理论所要带给我们文化和观念的荡涤,即“社会的和谐必然离不开对观念多元化和人性多样态的包容”[3]。这既是多年来饱受摧残和折磨的黑人女性的奋斗目标,也更应该成为当下世界文化生活的最低准则,由此,酷读《紫色》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从酷儿理论的视角看茜莉、莎格和索菲亚三个黑人女性,无论在白人主流社会还是在黑人男权社会的眼里,她们必定被事先套上了身份的枷锁,但她们不懈地抗争所赢得的完美结局,表达了沃克对酷儿的包容、对黑人女性的赞美和对和谐社会的坚定信念,正如巴特勒所断言的那样:“如果身份不再被定位一个政治三段论的前提,而政治也不再被理解为一套实践、衍生自所谓从属于一个既有群体的主体的利益,那么一定会有一种新的政治设定从旧有的废墟中浮现。”[12](193)
[1] 杨洁.酷儿理论与批评实践[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2] Enku.baidu.com/view/604d4q350b4cze3f57276353.ntml[EB/OL].
[3] 李银河.酷儿理论面面观[J].国外社会科学,2002,(2).
[4] 孙婷婷.性别跨越的狂欢与困境——朱迪斯·巴特勒的述行理论研究[J].妇女论丛,2010,(10).
[5] [法]西蒙·德·波伏娃.第二性[M].纽约:温提子出版社,1973.
[6] 宋素风.《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后结构主义思潮下的激进性别政治思考,[J].妇女研究论丛,2001,(1).
[7] Judith Butler,Gender Trouble: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New York,Routledge,1990.
[8] 艾丽斯·沃克.紫色[M].沈阳出版社,1999.
[9] 毕文静.酷儿理论视域下的《紫色》[J].大众文艺,2012,(2).
[10] 王影君.论西方后女权主义对女性身体的文化批判[J].山东外语教学,2012,(4).
[11] 胡晓军.性属研究[J].天府新论,2012,(6).
[12] [美]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M].上海三联书店,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