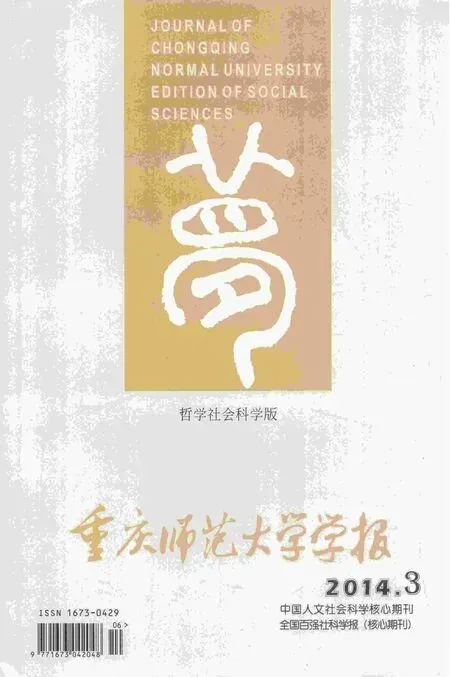与国际行政法的产生有关的几个基本问题——基于全球化、全球治理的视角
林 泰
(重庆工商大学 法学院,重庆400067)
“‘国际行政’是指履行全球治理职能的国际组织或机构对国际公共事务的规制性行为以及其内部的组织、管理活动。”[1]所以,从宽泛上理解,国际行政法即有关全球治理实践中实际存在的跨国或者国际性行政权力行使的法律规制,是全球治理法治化的表现。国际行政法的产生是全球化向纵深发展以及全球治理中一个法律发展现象及趋势。在学术史的发展中,国际行政法的概念与传统国内行政法的理念以及国家主权观相悖而历来都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德国行政法立法者之一的奥托·迈耶(O.Mayer)就认为:“国内公权力在自己的统治范围内是国王,可以排除其他一切权利;外国权力在另一国范围内只能在极特别情况下适用;如果国际义务存在的话,也必须通过国内法的过滤,将其转化成国内法。”[2](354)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陈新民也认为:“行政法是基于国家主权而制定的,主要是为规范国家行政机关有效行使行政权力的法。即使存在某些涉外因素,效力也只及于本国领域,其在性质上仍属于国内法的范畴。国际行政法之成立及承认,除非宪法规定国家主权可让渡到一个国际组织之上,否则,所谓国际行政法的概念,仍是不实际及未成熟的”。[3](8)但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使全球治理成为可能,全球治理带来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一种全新治理方式,也使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行政法的产生成为可能。本文所述即为国际行政法的产生所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试图由此厘清以往各种观念误区。
一、国际行政法的产生语境——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的提出源于全球化的推动、国际性公共问题的不断增加,而单个国家无法自力解决等综合因素。诚如一些学者认为:“全球治理可以被看成是全球化时代全球公共事务的管理方式。全球公民依照某种普遍认可的规则参与及管理各层次国际公共事务并形成新的得到认可的规则或制度,由此世界得以有序发展。”[4]相对应的,全球治理是人类治理方式、广度、深度、范围的一次变革,其中蕴含着涉及整个人类的生活方式、制度构造、文化理念等的改变均是革命性的。全球治理最终要落实到规则层面的解读,因为全球治理的核心目标,在于致力于“健全和发展一整套维护全人类安全、和平、发展、福利、平等和人权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包括处理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全球规则和制度。”[5](2)所以全球治理必然意味着大量全球性规则的增加以形成制度性支撑,那么,其理所当然带来的是国内法、国际法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一次巨大变革。正如有学者认为:“全球治理表现在法律方面,就是国内法与国内法、国内法与国际法、国家法与非国家法等各种形式的法之间以极其复杂多样的方式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其中任何一种法律体系的变动,可能会立即引起其他法律体系的变动或者反应。”[6](20)
正是在全球治理的背景下,大量的有关国际经济与社会管理制度得到爆发式发展,这些制度都是对全球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社会、环境、信息和其它相互依存的形式发展的结果以及由这些纯粹通过国家间解决这些问题存在的不足而产生的后果的回应。这些管理制度包含了各种各样的学科领域:贸易、银行业和金融规制;环境、健康和安全;医药品;交通和通信等。市场失灵和那些分散的用于维护重要的经济和社会价值的国家管理体制的失败也都导致了这些制度的产生,其当然也包括那些国内实施的具有行政管理特征、做出行政监管决定和创制行政监管法律的领域。这些国际监管制度应当如何对他们所应当服务的制定者或者公众的利益负责,这是对以新的形式出现的行政法所提出的问题。提及责任的追究时,又立即提出了向谁问责以及通过什么方式问责的问题。其中一个方面就是确保行政决策者(包含国内和在国际范围内执行跨国或者全球性管理规范的官员)忠实于一套得到认可的新的行政法体系。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对最终受这些制度影响广泛的大众的责任,包括自然人、企业、法人,和在某些情况下涉及到的非政府组织,以此来确保他们的权利得到保护,利益受到尊重。全球化带来了一系列从实践到制度层面的难题,各种行使实质性规制权力的跨国组织或机构的权力在全球治理中急剧膨胀,对其问责成为一个难题。如果把全球治理理解为一种规制型行政,各种类型的跨越国家界限的国际组织或机构在全球治理中承担了各种国际公共管理职能,规制型行政的作用和影响在不断增强,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很多承担全球治理职责的国际机构直接面对私人主体行使权力。在一国的国内法中,公权力机关面对私人主体我们一般可以理解为行政法律关系,而对公权力机关的问责和监督一般都有比较完善的行政救济法予以明确,比如我国的《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尤其是行政诉讼(或者称为司法审查),是由法院作为独立的第三方来终局裁决行政行为的效力及合法性。这样,主要是私人主体的行政相对人在面对异常强大的公权力机关的时候,也能借助司法来维护自己的人权和其它合法权益。但是在国际层面上,目前既不存在一个超越国家主权界限的“世界政府”或者“超国家政府”,也不存在拥有充分管辖权的“世界法院”,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大量履行全球治理职责的国际机构的权力行使没办法沿着国内行政法的进路得到有效的监督,这就产生了一系列的难题。行政法只是用以促进问责制度的完善以及确保事实上的国际监管制度最终的正当化的方式之一,其也提出了在与其他制度并行的实施过程中所应当扮演的适当的角色问题。除此之外,履行全球治理职能的组织并不仅仅是正式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大量公私混合,甚至是私人机构、非政府组织也承担了这一国际行政性职能,私人因素成为行政规则的主体,这同样带来了一系列国际法层面上的难题。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都是国际行政法产生的必然性与必要性因素。
总之,在阐述“全球治理”这个概念的同时,我们必须同时承认法律全球化的进程正在发生,尽管在全球的范围内,一套表述明确、内容合理、结构妥当并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尊重和遵守的规范体系尚未成型,[7]所谓“国际法治”的完全的理想图景还十分遥远,但其进程已经逐步呈现。学者周永坤教授曾经乐观的预计,人类可以在21世纪中叶初步达成法律的全球化这一目标。[8]国际行政法的产生已经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据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国际行政行为、国际规制主体(权力行使者,最后达至“国际行政主体”的完全表述)、国际行政相对人等概念已经有一定相对清晰的雏形和基础,一个规范等级逐渐鲜明的“国际行政法”体系正在产生并逐步形成。正如国外学者所认为的,国际行政法体系的形成本身表明在“国内法层次的行政法和单纯的国际法已经不能完整的说明或者阐明这些创造出新的跨国或者全球性行政和行政法的新的国际监管制度”[9]。
二、国际行政法产生的两个现实驱动因素
(一)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
“全球公民社会”是全球化背景下“公民社会”这一概念的飞跃性嬗变。美国的艾利斯·勃丁是较早提出“全球公民社会”这一概念的学者,其在1988年发表的《建立一种全球公民文化》一文中将在国际视野下的全球公民社会的功能定位为:游说政府、培育世界公民身份、新的关于国家的思想观念、北方了解南方的新方式、创造和维持信息渠道和作为对国家失望的一副解药等。[10]放在本文背景下来讨论全球公民社会对国际行政法产生的推动,主要意义更多在于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为国际行政法的产生提供一种政治文化与氛围。全球公民社会孕育出的从国内民主到国际多元民主理念的嬗变,是国际行政法产生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国际多元民主理念的指引下,更多的国家、组织、团体参与到国际公共事务的治理中去,后面所谓“国际行政空间”的形成才具有正当性。因此,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是国际行政法产生的一个直接而现实的驱动力。全球公民社会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得到不断壮大,对于跨国监管制度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产生了全球公民社会各种阶层、团体,包括“跨国私人规制者、诸如国家、国家间组织或其行为具有终局效力但可能并不受控于中央行政当局的国内公共规制者参与的公私合作组织这样的混合机构、无条约基础的非正式国家间机构(包括“无同盟意愿”的),以及通过行政性行为影响第三方的国家间组织(如联合国)”[11]等,他们具有明确的参与到跨国监管制度和行政服务的诉求,这有力地促进了国际行政法体系化的形成,包括主体结构、运行结构,以及问责结构等。而国际化行政法的产生、完善又提供一种适当的有别于传统国际法的对全球公民社会的调整机制,包括运作方式、行动模式等的支持以及规则依据。
(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快速发展是全球治理中一个突出的现象,自上世纪末以来,业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并有大量著述发表。讨论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对国际行政法产生的驱动,主要在于全球治理中国际非政府组织为国际行政法提供参与的主体支持。除了主权国家及特殊地位的地区之外,国际非政府组织是全球治理过程的重要参与主体。因为普通公众通过对非政府组织的参与这种形式可以表达自己的某种倾向性或者意愿,以此与政府机构和其他公法组织进行互动和博弈。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共同的治理目标的实现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民主参与的程度也通过组织的自主性和自治方式而得以提高。[12]由此,国际非政府组织成为全球公民社会参与国际公共问题解决的主要渠道,也是国际政治体系与公民进行有效沟通的基本方式。因此,全球治理,不可能缺乏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参与与协助。约瑟夫·S·奈认为:“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治理机制中发挥的直接作用至少包括以下方面:指出全球化可能被忽视的、存在问题的后果;阐明全新的价值观和规范,以引导和约束国际实践;建立跨国联盟,倡议和支持容易被忽略的替代政策方案;改革国际制度,回应未得到满足的要求;推广有国际应用价值的社会创新;协商解决跨国冲突与争执的方法;动员资源,对重要的公共问题采取直接行动。”[13](284)对于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治理中这些具体的作用和功能,即为成型中的国际行政法律规则和制度调整的范围和领域。无论是全球公共问题的甄别,还是适用何种程序、动员什么资源,以及对这些全球公共问题的处理与决定,都需要国际行政法律规则提供基本的依据和方式。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主体地位、机构设置、以及全球行动、权力配置与救济运作程序等都为国际行政法律制度所涵盖。从另一个层面讲,非政府组织在国际行政法中的角色难以替代,其职能的扩张所在往往正是一国政府、正式的政府国际组织所无法触及之处,在特定领域,一定程度上甚至充当了规制的主体,对被规制对象(如私人、公司法人、另外的非政府组织等)拥有巨大的权力,甚至涉及个人健康、工作等基本人权范畴,这种独特的角色安排又更加促使国际行政法向纵深发展。因此,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成为驱动国际行政法产生的直接因素之一。
三、国际行政法的产生路径
如前所述,解决全球公共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发展更为有效且适当的行政法监管体制,追究行政管理决策和国内执行的责任。国际行政法的产生是一个动态过程,这个动态过程可以称之为行政法国际化进程。以一个国家为基点考察,这种国际化不外乎“输入”和“输出”两种方式:“输入”即国际上的行政法的国内化;“输出”则可以理解为国内的行政法的国际化。在体系化的国际行政法形成中,金斯伯里、斯图尔特教授等人将“输出”、“输入”的路径总结为“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路径。[14]他们认为在跨国规制权力的运用中产生了问责缺失现象,从而开始引发两种不同的回应:一是试图将国内行政法延伸到对国家产生影响的政府间规制决策中;二是在全球层面发展新的行政法机制以应对政府间机制形成的决策和规则。“自下而上”即延伸了一国国内行政法的触角并对国内法规中的超越国家部分以更加有效的控制和审视。比如在美国,相关法院在执行国内机构对全球管理规范政策做出的决议时,试图采取多种途径进行行政法程序要求下的司法审查和纯粹运用于国内监管措施进行的司法审查,并使美国的行政官员能够参与到这些标准和国内措施的全球发展进程当中。例如,他们可能要求美国的行政官员在开始进入全球监管讨论和谈判之前给予公众以公告和评论的机会。要求美国的行政机构在拟通过执行一个新的全球监管标准规则时,提供一个全球监管制度讨论和决议的摘要,并提供监管机构在全球探讨和最后决议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分析和论证。对于已通过决议程序但又不符合基本监管标准要求的全球监管决议或者规范,国内的法院有时甚至会大胆地拒绝承认。其他参与国家可能也会有类似的要求,这很可能促成跨国行政法的产生。“自上而下”的方式下,以条约为基础的监管制度,甚至网络或者横向监管制度都会采用相应的决策程序,以此来促进更大的透明度、为利益相关者提供更多的参与和反馈机会、建立审查机构或其他机制以促进完善对国际或跨国界监管决议的问责制度。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从以法院为中心的行政法概念中将自己解放出来。国际实践中已经开始运用多种途径来解决这一问题:世界银行的检查小组,北美贸易自由区环境合作委员会制定的程序,食品法规委员会在国际食品安全的标准中和在国际濒危物种贸易公约中都将国际非政府组织纳入到其决策程序当中。[15]
在评估这两种国际行政法的实现路径后,我们可以发觉,发展中的国际行政法机制有可能会对国内行政法提出挑战,特别是在国内整体法律设置中有可能起否定(权力制衡)或者肯定(权力导向)作用的行政法。[16]在国内,行政监管机构一般受制于民选的代议制机构,并受到独立法院的审查。但是国际监管网络和组织并没有受到类似国内的民选代议制机构过多的干涉,也没有所谓的审查法院。这可以作为采用安全的传统外交规范、进行秘密谈判和采用非正式的全球监管治理模式的好理由。此外,在很多全球行政监管制度当中,监管功能并不是由能够明显区分、易受制于行政法管理的固定行政机构所承担。
不管哪一种路径,所达至的结果就是最终形成国内国际两元结构逐渐淡化的一个规则等级鲜明的“国际行政法”体系,行政法国际化体现的是这一过程所表现出来的某些特征。所谓“国际行政法”体系,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国内行政法体系类比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其和国内行政法有某些内核或基本理念的相似性。
四、国际行政法的基本特征
首先,由于大量不同的国际规制机构的存在,国际行政法是存在于各个行业(或者部门)的。这个特征直接起源于国际规制本身,它追随第一个不能为某个国家单独行动所能达到的特殊公共目标的出现。这种部门性本身通过多种实体提供多种国际行政形式对全球管理的组织产生了影响,从正式的国际组织(例如WTO)到具有管理功能的民间机构(例如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OSCO),皆是如此。[17]而且,不同组织的联系逐渐取代了过去协助的缺乏,表现为很多国际规制实体为其他国际体系所形成,例如由联合国粮农组织与世界卫生组织创设的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ODEX);另外,连接不同组织的协议或者协助网络得以建立,例如在WTO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之间,或者是在WTO与世界卫生组织(WHO)之间的协议;再之,由一个组织创设的争端解决实体可能用于解决产生于其他组织之间的争议,例如解决英特网域名争议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与调解中心。总之,国际行政法针对的主体范围极其广泛——从国家、国内公共行政管理、全球性机构、非政府组织乃至自然人等。虽然国际行政管理不能真正被说成是独立于国家层面而存在,但在全球舞台上国家的角色变得越来越多层面,并且在全球和国家层面存在着一个互动的过程。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国际组织的决策程序揭示出技术上的联合行动和共同的调整是多数主体的意见。正如有外国学者所说的,无论从实证主义还是从经验主义方法,都没有将全球从国内层面分离开来的清晰方法。[18]
其次,国际行政法超越国家界限进行运作,这种运作与国内行政法特征的主要区别就是与任何宪法基础相脱离。在国际乃至全球层面,没有超国家政府或者更高的权力机关,仅仅有某些部门准政府形成的多数意见。[19]国际行政和行政法、宪法基础的缺乏又一次产生了新的具体的问题——权力行使的正当性和问责性。而且在更深一层的相关方式上,国际行政法的主焦点致力于在操作层面增加多样的保护机制以确保国际管理机构对那些其行动所影响的利益做出适当的回应。如前面所论述的,宪法基础的缺乏,关于追求全球民主的任何可能性在任何时候和将来会强迫对其他正当性和责任促进机制的重视,例如来自国内法原则如透明度、参与、给出理由的职责、司法审查等。[20]
最后,从一个严格的法律角度,国际行政空间带有“国际”与“行政法”的双重性质,既不能否定这两个概念的共存,也不能作为一个僵硬的分裂而概念化,而是应该单纯的作为一个新的挑战被认可、接受和面对,以促使一个新的概念工具设置的发展。[21]
从以上这些特征看,尽管界限和范围还不是非常清晰,但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国际行政空间”目前是事实存在的。在这个空间中,很多履行全球治理职能(或许是无意的)不同类型的组织或机构作为行使规制权力的主体,包括正式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或其机构)、一个国家的国内当局、私人机制组织(非政府组织)、公私混合型组织等。这种观点很可能会引起争议,很多学者坚持最为传统的观点,认为行政与传统的国家主权观相连结,是一个国家与政府中的特定范畴,严格意义上的行政法只能存在于一个主权国家的内部,“国际行动可以协调和协助国内行政,但由于缺乏国际执行权力和能力,它本身不构成行政行为”。[22]所以所谓“国际行政”的提法从理论到实践上都是有问题的。对该观点,笔者认为从逻辑上,一个实证例子就可以驳倒,这就是欧盟行政法。随着欧洲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深入,目前在学理上和司法实践中已经形成了欧盟行政法这一全新法律部门,而对这一法律部门有着不同的定义。通说认为,欧共体法主要由行政法规则所构成,而欧盟行政法包括所有缘自欧洲共同体法以及保障共同体法实施的法律规范和法律文件。[23]著名的行政法学者施瓦茨教授认为:“就某种程度而言,欧洲法院将欧共体描述为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共同体,更确切地说,是建立在行政法基础上的共同体。”[24](4)因此,欧共体近年来不断发展的实践正在促进统一的“欧盟行政法”的形成。问题在于:欧盟是一个国家吗?尽管一体化程度之高让人瞩目,甚至在《里斯本条约》基础上已经产生了“欧盟总统”,但是无法否认,欧盟现阶段还不是一个主权国家,但是欧盟从欧共体诞生那一天就有若干统一的行政法渊源,这是非常值得深究的。这说明了基于绝对主权观的行政及行政法概念并非牢不可破,起码人类早已经有了行政及行政法“超国家化”的实践。另外,从现时的实际情况看,“这种观点与具有行政要素和职能的国际和跨国规制机制的迅速扩张是相矛盾的”[22]。
五、国际行政法体系化的阻碍因素及克服
国际层面相比国内层面的很多特殊性使得国际行政法的体系化发展面临诸多挑战,从前述新兴国际行政法的若干特征中也可从另一侧面看到国内行政法的模式在国际层面的很多领域事实上是无法实行的。国际行政法体系化面临的挑战包括:超国家决策过程通常是繁冗的,因为权力由不同的机构分享;国际决策过程的非正式性也会减损行政法的应用;私人利益在一些国际决策机制中起重要作用;国际、国内,政府和私人机制的混合使得行政法的应用更加复杂化;现存的国内行政法模式总是被理解为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产物,是用来扩张发达国家权力的工具等。[25](1537)另外,国际层面,也存在权力滥用的风险,现存的国际组织甚至缺少对权力的最基本的控制,且没有全球范围内的公众检查官员是否滥用权力,是否对自己的行为负责。[26](34)当然,从另一个层面分析,这些国际行政法体系化的阻碍因素并非不可克服,虽然国际行政法不如国内行政法成熟,但是如能改进合法性,就能够将超国家机构的全球治理职能发挥得更好。下面简要阐述在国际领域应用行政法如何克服各种阻碍因素。
(一)责任划分的难度。对某一事项的决策权力往往是在几个级别上划分的,这使得对决策结果的问责很难精确地追溯到源头,在这一点上国际决策和国内决策区别并不明显。从国内行政法布局来说,划分责任并在各级政府之间布置好几方如何连接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在美国,环境保护局和能源部对环境变化政策都有责任,并且还有其他几个对该政策有从属作用的机构和部门,这些互相重叠的决策机构是确保政府官员间审慎商议的重要途径。同理,在全球范围内,当有权限的决策机构间相互重叠时,首先要确保有解决管辖权纠纷的程序规则。
(二)非正式性。国际决策的非正式性可能会使决策过程模糊化。在这个方面,有两个不同的问题需要解决。一方面,非正式性意味着不透明,解决它就需要强化透明度以及更加明确的程序规则。然而另一方面,非正式性往往产生约束力优先的软法,在谈及全球治理合法性的时候,软法的产生有其一定意义,但是也有可能更进一步产生合法性障碍。所以,更强调程序严格和程序法更能使公众产生对集体行动的信心,也更能接受其结果。
(三)私人的角色。国际层面的一个特征就是私人结构性参与国际规制秩序,事实上,在决策过程中私人机制的存在在国际层面和国内层面没什么不同。在很多发达国家,商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游说可以说无处不在。在国际决策过程中,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具有重大意义,即使现存的在全球层面的特殊利益游说缺少制度约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解决方式如上所述,不但不能放弃在超国家领域尝试适用国际法原则,而且要为特殊利益参与设立规则,以免决策结果的歪曲。
(四)混合性。国际国内、政府与私人的混合使得国际层面适用行政法更为复杂,每个国际组织都是国内和国际官员的连接处。规定国内和国际官员的角色,寻找混合国内和国际权力的方式是制度设计的主要挑战。然而成熟的行政法制需要解决这个问题。一些问题可以通过国家政府间的协商解决,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授权给国际机构并允许他们在授权的范围内解决问题;另外,还需要在国际层面明晰并调和国际机构的利益,且能相对应每个特定的国际组织以显示其特殊的决策情况以及治理结构的深度和特点。
(五)制度缺陷。把国内行政法应用到国际领域的最重要的问题来自于在国际层面缺少类似国内领域那样限制决策者权力行使,使其对自己行为负责的机制。[27]值得注意的是,国际行政法通常需要保护因全球治理机构权力滥用而损害的个人和经济实体的权利,在一些国际组织中,争端解决机制则提供了必要的机制。另外,由国家政府监督其权力行使的机制也应该确立。[28]由于缺少类似国内的直接司法或检察权力行使,产生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是缺少问责。在国内领域,代议制民主制度保证了问责制度:无法达到公众标准和期望的首长官员将在下次选举中落败并交出其权力。[29](1540)对于政务官员来说,如不按照法律行使权力或按照首长制定的政纲则会导致承担相应责任或者被解雇。[30]我国国内也有相对完善的行政诉讼及行政问责制度,确保了对权力行驶者的有效问责,而在国际层面,问责就成了一个难题。目前的现实情况是只能寄望于一些比较宽泛的监督机制,比如市场压力、法定的监督机构、非政府组织、媒体等能促使权力行使者证明其权力行使的正当性。有学者提出了七个可供选择的规则国际政治决策的问责制度:即责任分级、国家政府监督、预算和财政监督、法律约束、市场激励、同行压力以及声誉风险等。[31](35~41)具体、微观的有关的国际行政法规则和程序,以及对它们产生的决策结果的监督,也应该加入到上述机制中。
(六)意识形态与政治偏见。前述有关国际行政法的观点很容易被误认为专属于西方的意识形态,并且规则对发达国家有利,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机构化的国际组织克服,晚近国际社会的发展也证明了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并非一定就处于劣势,在个别时候这些国家甚至更具优势。更重要的是,虽然本文提出的行政法规则绝大多数都以发达国家法制为基础,但是很多国家的管理机制都采用了其中一些程序性要素。部分行政法元素能独立于意识形态而具有普遍应用的意义或深远的影响,并且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得到了应用。不论国家对提出的国际行政法有多大程度的了解,在务实的基础上,本文所提出的这些行政法工具可以在很多情况下由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应用。
六、结语
在依存度极高的世界,超国家治理乃至全球治理不可避免,从打击恐怖主义,到控制全球变暖,再到制造全球公共产品,以及自由贸易和公共健康计划等,有效的国际规制机构有助于实现上述目标。当超国家机构扩张其治理职能,它们的合法性更令人关注,而合法性意味着按照规则指定的方式行事、明确性和稳定性、效率的系统和制衡机构、提升政治对话的能力、以及对程序的严格遵守等,行政法工具是建构合法性的核心,所以国际行政法的产生是应有之义。尽管不会在短期内形成“全球政府”或全球性中央权力的行使,所以行政法国际化仍然是一个漫长、复杂且多元化的进程。但是由于某些利益的共同性,在世界上呈现某些共同的标准和制度,在全球治理中依然是完全可能,也是完全可行的,全球治理语境下国际行政法体系的形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全球范围内对集体行动的需求以及对善政的越来越多的强调使得对这方面持续努力的需要也将会越来越急迫。
[1] 林泰,赵学清.全球治理语境下的国际行政法[J].南京社会科学,2011,(3).
[2] O.Mayer.Le droit administratif allemand[M].Paris,Giard-Briére,1906.
[3] 陈新民.中国行政法学原理[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4] 王乐夫,刘亚平.国际公共管理的新趋势:全球治理[J].学术研究,2003,(3).
[5] 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论[A].全球化:全球治理[C].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6] 高扬.论域名与网络知识产权保护[D].贵州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
[7] 何志鹏.国际法治:全球化时代的秩序构建[J].吉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1).
[8] 周永坤.全球化与法学思维方式的革命[J].法学,1999,(11).
[9] Richard B.Stewart.U.S.Administrative Law:A Model for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68 L.& Contem p.Probs.63(Summer/Autumn 2005).
[10] 刘贞哗.国际政治视野中的全球市民社会——概念、特征和主要活动[J].欧洲,2002,(5).
[11] Benedict Kingsbury.The Concept of'Law'in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IILJ Working Paper 2009/1 available at http://iilj.org/publications/documents/2009-1.GAL.Kingsbury.pdf.
[12] 郁建兴,刘大志.治理理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2).
[13] [美]约瑟夫·S·奈,约翰·D·唐纳胡.全球化世界的治理[M].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14] See Richard B.Stewart.U.S.Administrative Law:A Model for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68 L.& Contem p.Probs.63(Summer/Autumn 2005).
[15] See Lori M.Wallach,Accountable Governance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The WTO,NAFTA,and International Harmonization of Standards,50 U.KAN.L.REV.823,836-38(2002).
[16] 欧盟专家委员会特别程序为全球监管机构提供了另外一种组成模式,See generally EU COMMITTEES:SOCIAL REGULATION,LAW AND POLITICS(Christian Joerges& Ellen Vos,eds.,1999).
[17] See C.H.KOCH Jr."Judicial Review and Global Federalism",54 Administrative Law Review 492(2002).
[18] See M.S.BARR,G.P.MILLER."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The View from Basel",17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5(2006).
[19] See W.MATTLI,T.B?THE,"Global Private Governance:Lessons from a National Model of Setting Standards in Accounting",68 Law & Contemporary Problems 225(2005).
[20] See G.R.WINHAM,"NAFTA Chapter 19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Administrative Law",32 Journal of World Trade 65(1998).
[21] E.BENVENISTI,"The Interplay Between Actors as a Determinant of the Evolution of Administrative Law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68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323(2005).
[22] [美]本尼迪克特·金斯伯里等.全球行政法的产生[J].环球法律评论,2008,(5).
[23] 娄宇.欧盟行政法法典化初探——一个德国法的角度,载中国公法评论网,http://www.publaw.org/xzfyj/xzfyj_xzfwg/200706/t20070624_14138.htm.访问时间:2010年1月12日。
[24] Jürgen Schwarze.European Administrative Law[M].London:Sweet& Maxwell,1992.
[25] See Daniel C.Esty,Good Governance at the Supranational Scale:Globalizing Administrative Law,Yale Law Journal(2006).
[26] See Ruth W.Grant& Robert O.Keohane,Accountability and Abuses of Power in World Politics,99 AM.POL.SCI.REV.29,(2005).
[27] Jerry L.Mashaw,Structuring a"Dense Complexity":Accountability and the Project of Administrative Law,ISSUES IN LEGAL SCHOLARSHIP,Mar.2005,at 11,http://www.bepress.com/ils/iss6/art4.
[28] See Richard B.Stewart.U.S.Administrative Law:A Model for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68 LAW & CONTEMP.PROBS.63,76-88(2005).
[29] See Daniel C.Esty,Good Governance at the Supranational Scale:Globalizing Administrative Law,Yale Law Journal(2006).
[30] See Elena Kagan.Presidential Administration,114 HARV.L.REV.2245(2001).
[31] Ruth W.Grant& Robert O.Keohane.Accountability and Abuses of Power in World Politics,99 AM.POL.SCI.REV.29,30(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