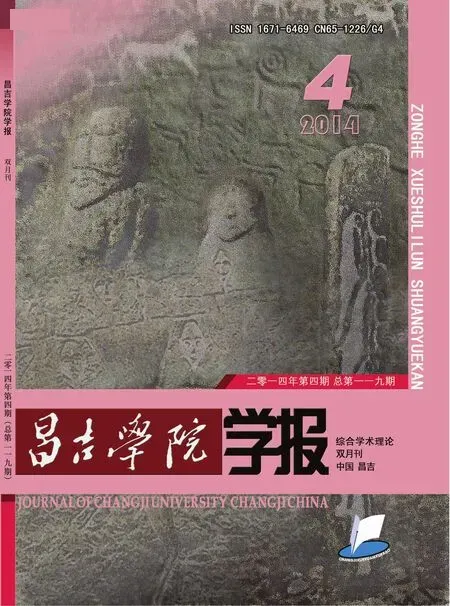唐诗中胡姬形象的文化传播与民族融合的媒介价值探析
邹淑琴
(新疆大学人文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唐诗中有许多诗作写到来自西域的胡姬形象,如“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李白《前有一樽酒行》)、“胡姬酒垆日未午,丝绳玉缸酒如乳。”(岑参《青门歌,送东台张判官》)、“双歌二胡姬,更奏远清朝。举酒挑朔雪,从君不相饶。”(李白《醉后赠王历阳》)、“胡姬春酒店,弦管夜锵锵。红毾铺新月,貂裘坐薄霜。”(贺朝《赠酒店胡姬》)、“落日胡姬楼上饮,风吹箫管满楼闻。”(章孝标《少年行》)、“金钗醉就胡姬画,玉管闲留洛客吹。”(温庭筠《赠袁录》)等等。由以上诗句可见,唐代的胡姬往往豪放洒脱、神采飞扬,充满了西域草原游牧民族特有的自由爽朗、无拘无束的性格气息。她们带来的西域热烈激宕的乐舞艺术与她们那非凡的容颜、美酒一起,被唐代文人名士和民间大众们所接收,渐渐成为唐代诗歌、艺术的内容之一,也成为唐代社会文化生活中不可分离的一个部分。唐诗对胡姬形象的书写恰好代表了唐代中原传统文化对西域文化的接纳和认同。可以说,唐代的胡姬是西域文化、艺术的传播者,也是民族融合的媒介。
一、西域文化艺术的传播者
胡风盛行的唐代是中国历史上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最为繁荣的时期。胡姬虽然不是来自西域的官方的文化使者,但她们作为西域文化、艺术的代表之一,来到中原和内地其他地区,并受到热烈欢迎。无论在她们侍酒还是表演时,她们自身的异域文化因素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唐代文化的各个方面。因此,她们在无意中成为了西域文化、艺术的传播者,不觉承担了传播异域文化艺术的功能,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唐代社会的审美观念。
首先,胡姬对于西域风俗文化的传播影响了唐代的日常生活审美。在唐代的一些发达的大都市、对外贸易港口城市中,如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胡姬酒肆生意兴隆。胡姬的影响更是达到了都市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首先体现在胡姬的服饰方面。元稹《法曲》中说:“女为胡服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我们知道,传统汉服的特点是宽袍大袖的裙装,而西域胡姬的服饰是窄袖、束腰、半臂、披肩以及裤装等,这种服饰一时间引领了都市时尚,成为当时女性纷纷效仿的时髦打扮。如高宗永徽后流行仿吐火罗的长裙帽;天宝初年,以穿着龟兹的半臂、窄袖和波斯披巾最为时髦;安史之乱后社会上又流行“回鹘衣装回鹘马”,这种男扮女装的着装风格在之前的传统汉文化礼教观念中是不被认可和允许的。而这种来自西域草原游牧文化风格的女性服饰特点,能在唐代风靡一时,上至帝王的妃子、下至文人百姓,纷纷女着男装,显然是受到当时胡姬的影响。据《新唐书·五行志》载,唐天宝年间“士流之妻,或衣丈夫服,靴衫鞭帽,内外一贯矣”。而且,唐代很多壁画中描绘的西域女性往往身着紧身翻领窄袖裤装骑马,这在当时中原王朝也成为一种时尚风景,花蕊夫人《宫词》中就写到了宫娥们学习骑马打球的情景:“自教宫娥学打球,玉鞍初跨柳腰柔。”另外,盛唐宫廷和社会上流行的袒胸露乳的着装风格,强烈地凸显女性意识,突破礼教,这显然也是受到唐代表演歌舞的胡姬的着装影响,如周濆《逢邻女》:“日照邻女笑相逢,慢束罗裙半露胸。”白居易的诗中写了不少这种穿着打扮的汉族女子,如“脸如芙蓉胸似玉”等。另外,胡姬舞女的眉妆、粉妆、眉间点靥子等妆容风格在唐代日常生活中也很普遍,这在本文的第二章第三节中已经做了分析,在此不予详述。总之,胡姬所代表的西域文化内容已经渗透到唐代日常生活,尤其是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唐代的日常生活审美往往带有西域风俗、文化特点。
其次,胡姬对西域乐舞艺术的展示在唐代传播影响广泛,极大地影响了唐代的艺术审美观念。艺术是一个时代审美风貌的集中体现。胡姬对唐代艺术审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乐舞与文学两方面。胡姬带来的西域乐舞风格以热烈奔放为主要特征,唐代的“十部乐”、或“坐部伎”、“立部伎”都是载歌载舞,热闹非凡。《旧唐书·音乐志》中记载,唐代社会深受胡人乐舞影响,“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王建《凉州行》提到胡乐在洛阳的风行:“洛阳家家学胡乐”。可想而知,胡人酒肆遍布唐代的繁华都市中,胡姬歌舞随处可听可见,市井街巷中的百姓对其歌舞、曲调节奏一定非常熟悉。本文第三章在分析胡姬的乐舞艺术时论及胡姬舞蹈时的伴奏乐器可知,不论是胡旋舞还是胡腾舞或柘枝舞,胡姬出场前、舞蹈过程中及舞蹈结束收场时,往往都以鼓类打击乐器为主,以营造热闹的氛围,同时使用管弦类吹奏、弹拨乐器伴奏,如箜篌、横笛、琵琶、筚篥等。这些乐器、乐曲节奏及舞蹈在唐代都备受推崇和喜爱,以至于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传统乐舞艺术,《通典》卷一四六记载:“管弦杂曲数百部,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并且,由于对胡姬带来的这种西域乐舞艺术的广泛接受,唐代音乐融合了胡乐与汉乐的多种因素,发展了胡汉结合的燕乐,创造出一些新的音乐形式,称为“胡部新声”。武平一《谏大飨用倡优狎书》中说:“伏见胡乐施于音律,本备四夷之数,比来日益流宕,异曲新声,哀思淫溺。始自王公,稍及闾巷,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咏歌蹈舞,号曰‘合生’。”[1]此处所谓“合生”,是以歌咏为主,用胡乐伴奏,穿插舞蹈的一种“俳优歌舞杂奏”。[2]这是一种有故事情节的歌舞戏,显然是融合了胡汉两种乐舞文化因素的新型乐舞。由这段记载也可知,胡乐胡舞已经逐渐渗透到唐代社会的各个层面,上至宫廷士大夫宴饮,下到坊间百姓的娱乐,无不深受胡乐胡舞浸染。唐代“西域乐舞……赢得了观众的深深喜爱,以至于风靡一时,连皇帝也无法阻止它的传播流行。上至贵妃重臣,下至女伎百姓,人人喜欢看胡舞。”[3]胡乐与汉乐水乳交融,形成独具特色的唐代乐舞艺术风格,使中国的音乐舞蹈文化在唐代完成了一次整合。而胡姬在此过程中,显然发挥了表演传播的作用。正是这些胡姬们在歌楼酒肆、街头里巷的精彩表演,使唐代文人大夫、官僚平民们能够亲眼目睹耳闻西域乐舞的具体内容与风姿,它才能受到唐代社会的广泛接受和喜爱。
胡姬对唐代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唐诗中。其独特的外貌、洒脱的性格、令人目眩神迷的舞蹈艺术,以及时而忧愁的情态等等都成为了唐代诗人们关注和书写的对象,拓展了诗人们的题材领域和想象空间,也为唐代文学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气息。有些诗人写到胡姬的绿色眼睛的魅力,如“胡雏绿眼吹玉笛”(李白《猛虎行》)、“卷发胡儿眼睛绿”(李贺《龙夜吟》);有人书写了胡姬的白皮肤与高鼻梁,如“肌肤如玉鼻如锥”(李端《胡腾歌》)、“眼睛深却湘江水,鼻孔高于华岳山”(路岩梦《桂州筵上赠胡子女》);李白笔下的胡姬“当垆笑春风”,李贺则写了月下的胡人美女“望乡哭”;更有诗人专门描写了胡姬高超的乐舞技艺,如白居易、元稹、岑参都对胡旋舞做过精湛的描绘,李端、张祜等人都写过胡姬表演胡腾舞、柘枝舞等的诗句。正是唐代诗人的书写,我们才看到了胡姬那鲜活生动的神态和样貌。唐代胡姬为诗人们开启了一个新的表现领域,为唐代诗歌,乃至中国文学增添了特有的西域文化质素。胡姬带来的西域丰富的文化,如一股清流,汇入大唐的诗歌海洋之中,增加了唐代诗歌的体裁和史诗深度,唐代的诗歌文化才会比中国古代其他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绚烂夺目。
二、民族融合的媒介
胡姬不仅是来到中原王朝的西域文化的使者,极大地促进了西域文化艺术的传播,同时,她们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唐代各民族间的融合。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胡姬在唐代民族融合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媒介作用,或多或少具有贯通胡、汉民族之间融为一体的桥梁的意义和价值。
“民族融合是在经济文化影响力的作用下,自然而然发生的无强制手段的过程,无论是一个民族合于另一个民族,或者若干民族聚合为一个新的民族,都是无意识无目的的。”[4]前文已述,唐代胡风盛行。唐代社会无论民风民俗、审美观念、道德观念、文化艺术、甚至价值观念等等都受到西域文化的影响。归根到底,胡风盛行的原因是胡、汉各民族间的密切交流与融合,这是基于平等、尊重立场上的交流与融合。可以说,唐代是我国古代民族交流与融合的顶峰。这种民族大融合的局面的形成首先要归功于唐代统治者的“华夷一家”的观念。唐初,太宗李世民对隋炀帝大忌胡人的做法很不赞成,据《贞观政要·慎所好》载:
“贞观四年太宗日:隋炀帝性好猜防专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谓胡床为交床,胡瓜为黄瓜,筑长城以避胡,终被宇文化及使令狐行达杀之。又诛戮李金才及诸李殆尽,卒何所益?”[5]
唐代的这种政治、文化背景,是形成整个唐代社会民族融合的前提和基础。在此基础上,唐代开明的政策更是实现民族融合的重要条件。“岑仲勉《隋唐史》总结有四个特点:(1)不强迫同化,只顺其自然;(2)不掠取俘虏分散为奴婢;(3)不使杂处通婚;(4)不排斥各族不同之宗教,任其自由信奉。”[6]唐代这种自由开放的民族政策对促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起到很大作用,更极大地促进了民族团结与交流。另外,李唐王朝对待各族民众不分彼此,同样信任;在政治思想方面也比较宽松,对于自西域传入内地的袄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等宗教,也不横加干涉。这种文化背景,使唐代在融合各民族文化方面比较积极,亦比较通达。因此造成一种统一的和谐的思想文化局面,以至整个社会胡风盛行。“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况纷泊。”(元稹《法曲》)可见当时胡、汉文化交流之盛。唐传奇《东城老父传》:“今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长安中少年有胡心。”这些文学作品真实再现了唐代民族融合的空前盛况。
这种民族融合体现在文化层面,则表现为,唐代汉文化逐渐把西域胡文化容纳在自己的生活方式、文明视野当中,扩张了唐文化的广博视域,同时还把西域文化特色汇入华夏文化的历史浪潮之中。这种文化上的融合,某些情形下,是通过一定的媒介和桥梁得以实现的,而胡姬就是其中之一。唐诗中的胡姬象征着唐代文化和西域文化从相互拒斥到相互交融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是通过战争讨伐或武力征服,也不是通过宗教信仰上的强制改变,也不是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上的统治,而是通过人文、艺术的相互影响和渗透而形成的。这种影响和渗透持续了整个李唐王朝近三百年的历程,其意义是广泛而深远的。
胡姬的这种民族文化融合的媒介和桥梁作用首先体现在,她们是唐代来自西域的胡人与汉人在中原等地区进行文化交流的窗口。我们从很多唐诗中可知,当时的文人名士、官僚士大夫们常常光临胡姬酒肆,甚至有的人,闲暇时间都是去看胡姬歌舞来消遣娱乐。李白最具代表性,去的次数很多,如“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且就胡姬饮。”(《横吹曲辞·白鼻騧》)、“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少年行二首》);甚至有的人来到胡姬酒肆就不愿离开,连家都不想回了,如“羌儿吹玉管,胡姬踏锦花。却笑江南客,梅落不归家。”(温庭筠《敕勒歌塞北》);有的人就算赊账也要来这个有胡姬侍酒的地方:“有客需教饮,无钱可别沽。来时长道贳,惭愧酒家胡。”(王绩《过酒家五首》);有英俊少年在这里流连忘返:“落日胡姬楼上饮,风吹箫管满楼闻。”(章孝标《少年行》);也有白发老者忘年寻欢:“今日头盘三两掷,翠娥潜笑白髭须。”(元稹《赠崔元儒》)等等。可以说,胡姬与西域美酒对于唐代名士们来说,具有无尽的吸引力,令当时崇尚异族胡风的汉人们能够在不用远赴西域的情况下,在当地亲身感受到胡文化的风采。他们来到胡姬酒店,吃着西域民族特有的美食,喝着葡萄酒,听着西域特色的音乐,看胡姬踏着锦毯旋转腾跳,不知不觉起身与胡人们一起应声而舞,鼓声、琴音、吹奏之乐热闹激烈,一时间,所有在场的人,不分胡人、汉人,都陶醉在这种欢快的气氛之中。这种融洽的民族关系所生发出的是一种深厚的民族情谊。他们离开后写下了一首首赞叹胡姬、西域乐舞以及胡文化的诗句,流传开来,产生的影响也更广大。而且,从岑参、李白等人的送别诗可见,当时很多文人官僚常常以胡姬侍酒、出青门送别,如李白《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何处可为别?长安青绮门。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岑参《送宇文南金放后归太原寓居,因呈太原郝主簿》:“送君系马青门口,胡姬垆头劝君酒。”等等。可见,酒、胡姬、青门这些意象共同构成了唐代文人官僚送别的固定场景。送往迎来是人之常情,其中不乏胡姬的身影。显然,胡姬与酒已经融入到当时中原文人们的文化生活当中。胡姬的乐舞技艺更是受到唐代社会各个阶层的广泛欢迎,无论男女老少,几乎“人人学圆转”,街头巷尾尽是胡音胡乐。由此可知,胡姬乐舞与西域酒在汉人生活中已经变得日常化了,是胡、汉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集中显现。
从胡姬的角度来看,她们除了获得了一定的报酬,而且,她们也通过与酒客们的交流欢饮而传播了她们特有的文化内容,同时,她们在与汉人接触的过程中,耳濡目染,也或多或少地了解了汉文化,这对她们来说,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或者改变了她们固有的文化观念,如岑参在《送宇文南金放后归太原寓居,因呈太原郝主簿》一诗中就说到:“送君系马青门口,胡姬垆头劝君酒。为问太原贤主人,春来更有新诗否。”显然,这位当垆的胡姬已经具备较高的汉文化水平,能够关注诗文了。那么,当这些已经受汉文化影响的胡姬们再与本民族进行交流时,就会不自觉地把汉文化的某些观念传输进去,无意识中就实现了胡、汉各民族间的双向文化交流与融合。
总之,胡姬在唐代社会中,不仅是西域文化、艺术的直接展示者和传播者,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西文化的交流,更是唐代民族融合的重要媒介。正是有了胡姬这一媒介,西域文化(尤其是西域乐舞艺术)才能在唐代这一特殊的开放包容的时代直接栽种在中原汉文化的沃土上,并生长、开放出崭新的、多民族文明之花。唐代诗歌、乐舞、绘画等等领域都有许多展现胡姬形象的内容,具体直观地为我们展示了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大唐盛世中各民族融为一体的、多姿多彩的文化景观。胡姬在唐代民族融合的壮丽画卷中,无疑留下了一抹亮丽色彩。
[1]《全唐文》卷二六八[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1203.
[2]《旧唐书·音乐志》。据黄宝生考证,“合生”可能是梵语Prahasana(笑剧)一词的音译略称。它是由名词hasana(“合生”义为“笑”)加上前缀par(婆罗)组成的,详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黄宝生《印度古典诗学》一书第17~20页。
[3]王克芬.古西域与中原乐舞的交流及互相影响[A].影响世界的中国舞蹈[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215.
[4]陈通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J].云南社会科学,1993,(2):57.
[5]唐.吴兢《贞观政要》卷六《慎所好》第二十一.
[6]郎樱、扎拉嘎主编,邓敏文等撰稿.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先秦至唐宋卷[M].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