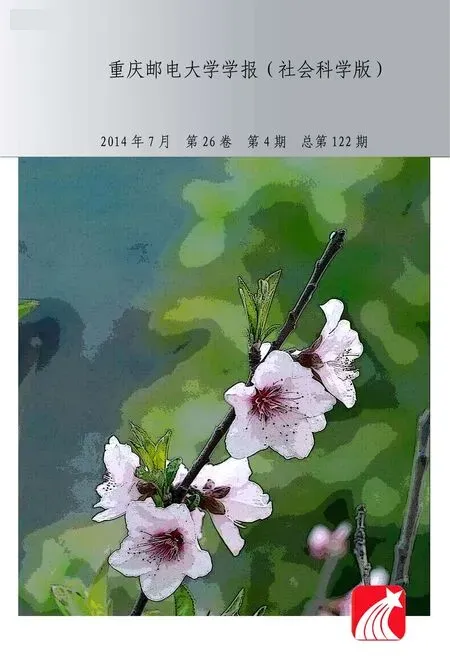从江淹《杂体诗三十首》看玄言诗的发展流变①
郭晨光
(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300071)
玄言诗是魏晋时期独特的诗歌样式。历来研究玄言诗,大多以玄言诗人为数不多的玄言诗和南朝诗论家对玄言诗的品评为主,尚不能完全反映这段诗歌史的发展流变。笔者以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中几首拟玄言诗为切入点,探讨作为南朝文人的江淹以模拟的形式对这段诗歌史的理解:其中涉及到玄言诗的形成、发展、新变、衰落以及玄言诗和游仙诗的关系等方面。这为我们今天全面了解玄言诗史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一、玄言诗的发生和流变
《嵇中散言志》[1]143
曰余不师训,潜志去世尘。远想出宏域,高步超常伦。灵凤振羽仪,戢景西海滨。朝食琅玕实,夕饮玉池津。处顺故无累,养德乃入神。旷哉宇宙惠,云罗更四陈。哲人贵识义,大雅明庇身。庄生悟无为,老氏守其真。天下皆得一,名实久相宾。咸池飨爰居,锺鼓或愁辛。柳惠善直道,孙登庶知人。写怀良未远,感赠以书绅。
《孙廷尉杂述》[1]153
太素既已分,吹万著形兆。寂动苟有源,因谓殇子夭。道丧涉千载,津梁谁能了。思乘扶摇翰,卓然凌风矫。静观尺棰义,理足未常少。冏冏秋月明,凭轩咏尧老。浪迹无蚩妍,然后君子道。领略归一致,南山有绮皓。交臂久变化,传火乃薪草。亹亹玄思清,胸中去机巧。物我俱忘怀,可以狎鸥鸟。
《许徵君自序》[1]154
张子闇内机,单生蔽外像。一时排冥筌,泠然空中赏。遣此弱丧情,资神任独往。采药白云隈,聊以肆所养。丹葩曜芳蕤,绿竹荫闲敞。苕苕寄意胜,不觉陵虚上。曲棂激鲜飙,石室有幽响。去矣从所欲,得失非外奖。至哉操斤客,重明固已朗。五难既洒落,超迹绝尘网。
嵇康身处魏末,孙绰、许询为东晋人,将其三人置于一组,主要是为了通过拟作来分析江淹对于玄言诗的产生以及流变的文学批评观。由于所处的时代,嵇康的诗不免沾染上“诗杂仙心”的特点。但与两晋典型的玄言诗直接抒发玄理的方式截然不同,他不是执于玄理,不是为了说理而说理。如其《赠兄秀才入军诗》等,正如王士禛在《古夫于亭杂录》中评嵇康诗“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二句为“妙在象外”[2],即指这些诗句含义悠远。这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写法,使得诗中所包含的哲理,不是以直说的形式,而是以让人联想的方式来阐述娓娓玄意,故钟嵘评其“托谕清远”。罗宗强先生认为:“嵇康的意义,就在于他把庄子的理想人生境界人间化了,把它从纯哲学的境界,变为一种实有的境界,把它从道的境界,变成诗的境界。”[3]即诗意是主要方面,玄理是次要的,并未脱离诗歌艺术的创作规律。我们来看拟诗:“庄生悟无为,老氏守其真。天下皆得一,名实久相宾。”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玄言诗句,完全脱离了嵇康诗的意境和风格,直接吟咏老庄抒发玄理,十分接近东晋成熟的玄言诗。这两句玄言,虽然在拟嵇康诗中占的篇幅不大,离通篇玄言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它已经完全脱离了嵇康“诗杂仙心”的特点,而成为讲说玄理之诗了。
玄言诗是东晋的主要诗体,但是,诗中谈玄并不是到东晋才产生的:
“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左,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4]
“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馀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5]675
可见,以诗谈玄早在西晋末年就有的,只是到了东晋时期才“流成文体”。在拟嵇康诗中穿插不类嵇康的玄言,江淹敏锐地捕捉到了后世所盛行的诗体(果)在前代已经埋下种子(因),这种诗体的对应,客观上收到了“草蛇灰线,伏延千里”的效果。所以,这首拟诗,已经完全带有文学批评的意味了。
孙绰、许询同为东晋玄言诗的代表诗人,对于二人的诗风,当时即有许多评论,认为二人各有千秋。但从拟诗来看,江淹拟许诗明显比拟孙诗在辞采上要生动得多,像“丹葩耀芳蕤,绿竹荫闲敞。……曲棂激鲜飙,石室有幽响”这样的写景摹状佳句,就是放在元嘉诗坛上也不逊色。对于玄言诗,胡大雷指出:“玄言诗的标志,即叙写玄学人生境界与体悟玄理。其方式有三:甲,单纯述说玄理、体悟玄理;乙,从人事和自然现象体悟玄理;丙,通过对人物风度的称赏来体悟玄理。”[6]江淹的拟孙诗,鲜明地体现了第一种玄言诗,拟许诗则体现为第二种。人们通常理解的玄言诗,只记得它“淡乎寡味”,其实玄言诗中有不少富有辞采、描写山水的名句,已开刘宋山水诗的滥觞。而且,拟许诗有一种非常奇特的游览方式,即“神游”:“遣此弱丧情,资神任独往。”当时的许多诗人都有“神游”之作,如支遁《咏怀诗》其三:
“晞阳熙春圃,悠缅叹时往。感物思所托,萧条逸韵上。尚想天台峻,彷佛柳阶仰。凌风洒兰林,管籁奏清响。霄崖育灵蔼,神蔬含润长。丹沙映翠濑,芳芝曜五爽。苕苕重岫深,寥寥石室朗。中有寻化士,身外解世网。抱朴镇有心,挥玄拂无想。隗隗形崖颓,冏冏神宇敞。宛转元造化,缥瞥邻大象。愿投若人踪,高步震策杖。”[7]
该作品描写诗人心目中的理想境界,想象一个高士在如此美景中专心修行,遗世独立、物我两忘。这种景致,不是诗人所见或生活在其中的,而是纯粹出于想象,并且表现出景物多于玄理的倾向。张廷银认为:“魏晋文人有一种很奇特的游历方式,它不是直接步入山林、走向田园,而是端坐于斗室之中,甚至横卧于几榻之上,遥望山色,静聆水声,或者闭目敛颔,沉思冥想。身形不动,而心驰神往,此为卧游或心游、神游。”[8]
这种游览方式,直到《殷东阳兴瞩》才完全改过来,变成一种“真游”:“晨游任所萃,悠悠蕴真趣。”这反映了江淹对玄言诗发展及其流变的清晰意识,山水诗取代玄言诗,通过士人真正参与其中,以亲身经历发现它们的美,而不是依靠纯粹的想象。
二、庄老告退、山水方滋
从“神游”到“真游”方式的转变,使得真实的山水景致大量进入到玄言诗中来,并且在数量上逐渐压倒玄言。后世的山水诗就是沿着这条线路取代玄言诗的。南朝人论说玄言诗的终结,一般都会归结于谢混、殷仲文二人①因为殷仲文、谢混流传下来的诗作极少,对于二人的诗风,我们已经不能具体判别了。。
“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单乎此。自建武暨乎义熙,历载将百,虽缀响联辞,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丽之辞,无闻焉尔。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9]
“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至过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询、绰并为一时文宗,自此作者悉体之。至义熙中,谢混始改。”[10]
“永嘉时,贵黄、老,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先是郭景纯用俊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逮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4]
诗歌史由玄言诗到山水诗的发展走向,在江淹的相关拟诗中得到了鲜明呈现,且看下面几首:
《殷东阳兴瞩》[1]155
晨游任所萃,悠悠蕴真趣。云天亦辽亮,时与赏心遇。青松挺秀萼,惠色出乔树。极眺清波深,缅映石壁素。莹情无馀滓,拂衣释尘务。求仁既自我,玄风岂外慕。直置忘所宰,萧散得遗虑。
《谢仆射游览》[1]156
信矣劳物化,忧襟未能整。薄言遵郊衢,总辔出台省。凄凄节序高,寥寥心悟永。时菊曜岩阿,云霞冠秋岭。眷然惜良辰,徘徊践落景。卷舒虽万绪,动复归有静。曾是迫桑榆,岁暮从所秉。舟壑不可攀,忘怀寄匠郢。
《谢临川游山》[1]157
江海经邅回,山峤备盈缺。灵境信淹留,赏心非徒设。平明登云峰,杳与庐霍绝。碧鄣长周流,金潭恒澄澈。桐林带晨霞,石壁映初晰。乳窦既滴沥,丹井复寥泬。嵒崿转奇秀,岑崟还相蔽。赤玉隐瑶溪,云锦被沙汭。夜闻猩猩啼,朝见鼯鼠逝。南中气候暖,朱华凌白雪。幸游建德乡,观奇经禹穴。身名竟谁辩,图史终磨灭。且汎桂水潮,映月游海澨。摄生贵处顺,将为智者说。
拟殷仲文诗,详细描述了诗人晨游所见,最后才是借景抒发玄理。虽然还是以说理为目的,但是其中的山水秀句已经绝非作为玄理的陪衬,而是开始成为诗篇中独立的部分。以往的玄言诗,虽然也是借助山水之景表述玄理,但是玄言诗人认为观赏山水同体悟玄理是可以合二为一的,他们眼中的山川大地,缺乏了本身的自然美,呈现出一种辽阔、抽象、玄远的境界。
拟谢混诗,全篇充斥着玄言,中间偶有写景之句,在当时也可称之为佳句,但主要目的还是为了玄理服务。相比较而言,拟谢诗不如拟殷诗那样气韵生动,显得更加酷不入情。
拟殷、谢二公诗表达了江淹对玄言诗终结的看法,他们二人的诗中虽然出现了一些写景佳句,但仍然是玄言诗的继续。也就是说,江淹是不同意“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这种说法的;相反,“逮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这种观点,也许更加符合江淹对二人诗风的认识。刘勰曾说:“袁、孙已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5]67认为殷、谢仍然属于玄言一派。江淹在这点上与刘勰有相似之处。这也许与当时士人如沈约等的文学批评观相左,从今日可以看到的诗作也很难还原当时的具体情况,但这仅仅代表江淹本人的观点,相较于文学批评专论,他以拟诗的形式表达文学变革时期的文学批评,更显别致。
那么,在江淹眼中,谁才是真正变革玄言诗风的人呢?那就是“元嘉之雄”——谢灵运。江淹模拟谢灵运,以谢最擅长的登游之作为对象,描写登山游览的经历,展示游览的全过程和山水景物的整体形象。
诗人天亮时分开始登山,沿途看到了大自然难得的奇景:“碧鄣长周流,金潭恒澄澈。桐林带晨霞,石壁映初晰。乳窦既滴沥,丹井复寥泬。嵒崿转奇秀,岑崟还相蔽。赤玉隐瑶溪,云锦被沙汭。”诗的最后是那条“玄言的尾巴”——“摄生贵处顺,将为智者说。”整首诗宛如一篇短小的旅行日记。
江淹认为真正改变永嘉平淡之风的是谢灵运,而非殷仲文、谢混二人。
首先,在数量上,谢灵运诗中的山水秀句在全诗中占压倒性的比重,玄言的成分已经大大减弱。
其次,谢灵运诗中的山水景物已经完全脱离了玄理的附庸,具备独立的价值。诗人对山水不是没有感情,相反,他是抱着真心喜爱、欣赏(赏心)自然山水的审美态度,使得客观的山水也带上了主观色彩,呈现出一种物我交融的和谐状态。
最重要的是,谢灵运的山水诗奠定了以诗歌表现景物为主的艺术发展方向。殷仲文、谢混的诗中虽然也有山水佳句,但呈现出的是主观(悟理)对客观(山水)的代替,乃至客观(山水)被吞没。
在江淹眼中,殷仲文、谢混还属于玄言诗人,而谢灵运已经完全脱离了玄言诗人的范畴,他开辟了一个新的诗歌领域——山水诗。虽然江淹仍将“玄言的尾巴”带入拟作中,但这正是他看到了新的成分在旧的母体中孕育的标志。陆时雍《诗镜总论》云:“诗至于宋,古之终而律之始也,体制一变,便觉声色俱开。”①陆时雍《诗镜总论》,参见《历代诗话续编本》。又,沈德潜《说诗晬语》:“诗至于宋,情性渐隐,声色大开,诗运转关也。”其中“体制一变”,指的是诗歌体裁的变化(如山水诗的勃兴)、语言风格的变化(如去永嘉平淡之风)以及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探索(如对仗、炼字炼句、声律);“声色俱开”,指的是注重描写物象外在形式的美,元嘉诗人无不在诗歌“体物”方面踵事增华。
可见,无论是在江淹的文学观念里,还是后人的文学观念中,谢灵运都是无可置疑的“诗运转关”的关键之人。
三、仙与玄的结合
郭璞以《游仙诗》著名,对此历来有很大的争议。《游仙诗》到底是“列仙之趣”还是“坎壈咏怀”,究竟是游仙诗还是玄言诗,江淹在拟诗中做了回答,详见其《郭弘农游仙》[1]152一诗。
崦山多灵草,海滨饶奇石。偃蹇寻青云,隐沦驻精魄。道人读丹经,方士炼玉液。朱霞入窗牖,曜灵照空隙。傲睨摘木芝,凌波采水碧。眇然万里游,矫掌望烟客。永得安期术,岂愁濛汜迫。
虽然历来大家对《游仙诗》的创作时间有很大争议②聂恩彦《郭弘农集校注》认为是在322年以后;连镇标《郭璞研究》认为在323-324年之间;钱志熙《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述》中认为在渡江前任临沮令时的吏隐之作。,但是大多都承认非一时一地所作。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收《游仙诗》19首,其余的未收录的大多为断章残句。江淹距郭璞的年代较近,可能见到的诗作较多。这首拟诗刻画了隐士采药、服食、炼丹,飞升成仙,在天界恣意游乐,长生不老等,表达的是对“羽化成仙”的追慕之情。
在拟诗中,未见到所谓的“坎壈咏怀”,所吟咏的是一种令人神往的“列仙之趣”。《游仙诗》表达的仙味是十分明显的,比较突出的有《游仙诗》其六③《游仙诗》其六:“杂县寓鲁门,风暖将为灾。吞舟涌海底,高浪驾蓬莱。神仙排云出,但见金银台。陵阳挹丹溜,容成挥玉杯。姮娥扬妙音,洪崖颔其颐。升降随长烟,飘飖戏九垓。奇龄迈五龙,千岁方婴孩。燕昭无灵气,汉武非仙才。”主要描写隐逸生活,表现作者高蹈求仙的志向。、其十等。但也还存在一些“非列仙之趣”的作品,如其五④其五:“逸翮思拂霄,迅足羡远游。清源无增澜,安得运吞舟?珪璋虽特达,明月难闇投。潜颖怨青阳,陵苕哀素秋。悲来恻丹心,零泪缘缨流。”,表达诗人怀才不遇的苦闷和对乱世的悲凉哀叹。这一类作品被钟嵘称之为“坎壈咏怀”之作,并受到后人的重视。
那么,为什么以“善拟”著称的江淹在拟作时,会漏掉其咏怀、寄托的内容呢⑤三十首诗中《王侍中怀德》、《陆平原羁宦》、《左记室咏史》等,江淹试图把握作者不同时期、境遇和心态的作品,使其在一首拟诗中得以反映,篇幅所限,现不展开说明。?这一方面可能与郭璞《游仙诗》的写作时间有关,另一方面是江淹以及南朝士人对郭璞的奇特理解造成的。
郭璞是跨西晋、东晋两个时代的文人,他的诗风肯定会带有这两个时代的印迹。那些颇多咏怀的作品,极有可能写于西晋末年,即他南渡之前,也就是钱志熙先生认为在渡江前任临沮令时的吏隐之作。因为“八王之乱”后,中原已经破败不堪,同时期稍早的刘琨也有很多“伤乱”之作。
江淹把郭璞看作东晋的第一个诗人,而不是西晋诗人。这极有可能是那些“列仙之趣”的《游仙诗》的大部分篇章创作于东晋时期⑥东晋时期,郭璞以术艺受到许多名士甚至皇帝的欣赏,社会地位有很大的提升,其中的“怨愤”之情就可能有所减少。《晋书》本传称他“辞赋为中兴之冠”,说明郭璞的很多作品都产生于东晋。。东晋政权偏安的局面,江南的名山秀水以及郭璞本人的学术传统①郭璞的学术传统有别于王、何代表的魏晋玄学,是典型的汉代学术传统,下文会有所说明。,很可能使郭璞放弃了言志之作,而回归到传统游仙诗的范畴中去,即追求隐逸、长生、成仙。
另一方面,这与江淹和南朝士人对郭璞的奇特认识有关。在他们眼中,郭璞是一位方士,《晋书》本传说他以自己特殊的本领求得官职。同时期的葛洪在《神仙传》记述郭璞,就把他描绘成道教的尸解仙了。该书记载,郭璞下葬三日之后,南州商贩看到郭璞“货其平生服饰,与相识共语,非但一人。(王)敦不信,开棺无尸。璞得兵解之道,今为水仙伯”[11]。萧统《昭明文选》选诗很严,仅收《游仙诗》7首,偏重的也是他遁世隐居之作。唐初官修的大型类书《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等收入的《游仙诗》,均表现其超凡脱俗的求仙之志。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认为:“六朝人虚造神仙家言,每好称郭氏,殆以影射郭璞。”陈寅恪先生论述陶渊明受天师道影响时,就说郭璞“本道家方士”,郭璞属于“求长生学神仙”之类“旧自然说”者[12]。
因此,江淹拟郭璞诗作中没有“坎壈咏怀”的内容,就不足为奇了。这一点和钟嵘的看法相反,也很好理解,钟嵘论诗强调“风骨”、“寄托”、“丹彩”,在东晋“平典似《道德论》”的诗风中,郭璞的《游仙诗》确实是与众不同的。
那么,基于以上分析,郭璞的《游仙诗》是否属于玄言诗的范畴呢?拟诗之中都是描写求仙及神仙生活的,全无半点玄味。“拟郭弘农诗,只是砌道书景物。”[13]看似讥弹之语,实则揭示了郭璞《游仙诗》并非玄言诗的本质。《世说新语·文学》注引《续晋阳秋》指出:“至过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认为郭璞是玄言诗发展的关键人物,这是不确切的。
相比较而言,萧子显的说法比较接近事实,也和江淹的观点相近。他认为:“江左风味,盛道家之言。郭璞举其灵变;许询极其名理;仲文玄气,犹不尽除;谢混清新②清,原作“情”,据百衲本影宋本《南齐书》改。,得名未盛;颜、谢并起,乃各擅奇;休、鲍后出,咸亦标世。朱蓝共妍,不相祖述。”[14]“举其灵变”与“极其名理”是相对的概念,它们“朱蓝共妍,不相祖述”,即从不同的系统流变而来。不可否认,郭璞《游仙诗》中确实有一些玄理,但那是由魏晋时期的时代特征决定的。刘大杰先生认为:“至于《老》、《庄》,可以说是魏晋士人的灵魂。我们看《魏志》和《晋书》,在社会上稍稍出色一点的人物,无不是精通《老》、《庄》之学。时流学术,俱以谈玄说道闻名于时。父兄之劝戒、师友之讲求,莫不以推求《老》、《庄》为第一事业。”[15]就连西晋末张协抒写个人情志的《杂诗》都沾染着玄风,更何况是郭璞这样跨越两晋的人物呢?萧子显认为郭璞“举其灵变”,应是指郭诗中引自《老子》、《庄子》、《山海经》、《穆天子传》或者其他道教书籍的灵怪故事和典故,这与玄风有一定的扭结点,因而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是玄言诗。
江淹选择三十位诗人的诗作进行模拟,这一行为并不是随意的,而是从诗歌发展角度出发,推源溯流。他在拟诗中略去了玄言,表明了他对《游仙诗》从先秦《楚辞》流传下来的文学传统的清晰认识。拟诗中全无玄理,是因为江淹认为郭璞《游仙诗》并非玄言诗。郭璞应该祖述的是从《楚辞·远游》留下来的传统——与孙、许不同的传统。因其《游仙诗》中表达的都是隐居、采药、服食、求仙等两汉游仙传统。更重要的是,郭璞本人的学术背景决定了他擅长卜筮、阴阳、历算之学,属于汉代京房、管辂一派,与王弼、何晏一派有所不同③余嘉锡先生《世说新语笺疏》认为:“郭璞《游仙诗》亦滥觞于王、何,而加以变化。与王济、孙楚辈,同源而异流。特其文采独高,彪炳可玩,不似平叔之浮浅,永嘉之平淡耳。”似可商榷。。他本人并无清谈、贵游之举,与当时的流俗不同。他注释《尔雅》,别为《音义》、《图谱》,又注《三苍》、《方言》、《穆天子传》、《山海经》、《楚辞》、《子虚》、《上林赋》数十万言,这些都延续了汉代的注疏学术传统。此外,在文学上,模拟汉代东方朔作《客傲》以表达不满。可见,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郭璞都与魏晋之际的玄学学术传统不相符。江淹拟制郭璞,可谓得其实也!
总之,江淹《杂体诗三十首》用拟诗的形式生动表达了他对玄言诗由滥觞到兴盛再到衰落的全过程的理解。这从另一个角度丰富和补充了《文心雕龙》、《诗品》等文学理论专著中有关玄言诗部分的文学史的内容,可视为一种别具一格的文学批评。
[1]胡之骥.江文通集汇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M].赵伯陶,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30.
[3]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3:104.
[4]钟嵘.诗品笺注[M].曹旭,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15.
[5]刘勰.文心雕龙注[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6]胡大雷.玄言诗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7:297.
[7]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1081.
[8]张廷银.魏晋玄言诗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211.
[9]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8:1778.
[10]刘义庆.世说新语[M].徐震堮,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143.
[11]李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3:95.
[12]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M]//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04.
[13]潘德舆.养一斋诗话[M]//郭绍虞.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2144.
[14]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908.
[15]刘大杰.古典文学思想源流[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8:20.
——兼与赵沛霖先生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