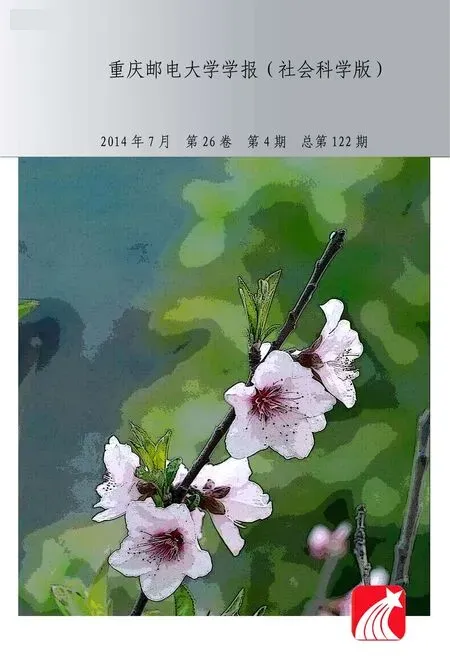信息法学研究与教学中的困境及应对——主要从学科定位的角度探析①
李 仪
(重庆三峡学院政治与法律学院,重庆 404100)
按照我国著名信息法学家齐爱民教授的阐释,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是人类社会的第三次转型[1]。随着信息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一些新的社会关系逐渐形成,新的社会问题(如信息隐私危机、数字鸿沟等)也由此而凸显。为应对这些问题,探索良法而治的法学家与法学教育者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信息领域。在这一背景下,信息法学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应运而生。在该学科从产生到现在不到20年的历程里,进步与发展固然是主旋律,但一些弊端与困境仍然如影随形。本文旨在探析信息法学教学与研究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之成因,进而提出应对之策。
一、信息法学研究与教学中的困境解析
(一)信息法学的诠释与溯源
按照学科设置与划分的相关原理,独立的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得以确立与发展的标准。据此,一门学科只有具备了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方得以被设置,其内容也才能不断得到丰富与完善。本文所要探讨的信息法学,则是以信息法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而按照传统的概念法学的表述方式,“信息法”(information law)可以被界定为调整与信息的产生、归属、交易与保护有关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总和[2]。在比较法上,信息法及信息法学的基本内容正是以此为核心和主线展开的。欧盟数据保护工作组即在《关于公共机构信息的再利用和个人数据保护的7/2003意见书》中阐述道,信息立法以及信息法学的关注重点,在于维护主体保有与处分信息的资格;而根据2007年修订的美国联邦《信息自由法案》第552条,信息的归属、获取与传输是该国立法者与学者关注的重点。据此,笔者将信息法学定义为:从制度安排与实施等角度研究信息产生、归属、交易与保护等现象的法学学科。
如前文所述,信息法学与信息法的产生与勃兴的过程和人类发展的步伐迈入信息社会是息息相关的。而我国信息法学的发展,也几乎同步于信息社会法制的建设进程。20世纪70年代,我国首次出现了信息政策与法规,但信息法学作为一门学科还未正式确立;80年代,随着一批高位阶的信息法律(如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统计法与档案法等)相继出台,信息法研究问题开始在学术界得到重视;进入本世纪后,随着与个人信息和政府信息保护和公开相关的法律规范的颁行,信息法学逐渐成为学术界与教育界所关注的学科。从2008年12月到2011年5月,笔者在重庆与四川等近十所开设了信息法学课程或者专业的高校进行了近两年半的调研,发现这些高校都是从2000年以后开设该门课程的。
(二)困境透析
当下的信息法学研究与教学面临重重困境,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理论体系未真正得到确立。在系统论视野中,“体系”特指同类内容成分按照一定的秩序和标准组成的整体[3]。据此,在信息法学的理论体系内,学科的主要内容成分需要得到确立进而被有机地组合。从本源与功能而言,信息法学的理论体系立基于其研究对象与学科定位,并且直接关系到研究和教学方法的选择。而迄今为止,对于依照何种标准确立信息法学学科内容的问题,学界并未形成主流意见,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以及研究教学工作的展开。譬如,多数法学家主张按照传统的法学思维方式构建体系;而一些信息管理家与信息科学领域的学者认为我国在构造体系时,应更多体现管理科学与自然科学的逻辑进路[4]。统一的理论体系的阙如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理论研究与教学工作的系统开展。
第二,研究方法繁杂而缺乏学科交融。在实践中,研究方法的采用将对一项学科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形成明显的制约。对于信息法学这门法学学科,相当多位法学家主张用传统的法学分析方法加以研究[5]。同时从信息法学被初创至今,新的研究方法逐渐被运用于该学科。譬如一些学者提出,研习者通过“运用系统科学方法研究信息法学,可以发现不同事物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进而把研究对象看作是一个整体的过程”[6];又如另一些学者主张,新制度经济学契约理论与图书情报理论中的方法论思想应被有效运用[7];更有学者主张引入实证分析与定量分析等方法[8]。然而这些研究方法均来自于不同的学科,从而它们的应用者往往出自不同的学科领域(如传统法学、新制度经济学、法社会学与图书情报学),由此他们往往各自为阵而较少交流。其直接后果是,信息法学的研究工作零散且缺乏深度,学科之间缺乏必要的交融。
第三,教学效果难如人意。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等缺陷制约了信息法学的预期教学目的的实现。一方面,从笔者掌握的资料看,受到不同的理论体系构建思路的影响,很多已出版的信息法学教材与专著在篇目编撰与内容选定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极易造成不同教材的研习者对学科基础理论与基本知识的分歧甚至误认①对此可比照马海群主编的《信息法学》(科技出版社2003年出版)与周庆山主编的《信息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另一方面,信息法学的性质决定了,其研习者以法学专业的本科生与研究生为主,他们所能接受的是传统法学的分析方法(如概念分析法、比较分析法与价值分析法)。而随着新制度经济学、法社会学与图书情报学等学科的定量分析法被引入信息法学的著述编撰与课堂讲授过程中,研习者接受理论知识的难度加大,甚至对一些内容不知所云。从2009年3月到2012年12月,笔者先后给重庆三峡学院4个不同班级的法学专业本科生讲授信息法学课程,他们对图书情报以及新制度经济学方面的原理就不甚感兴趣,对藉此而阐发的原理也不易理解。
二、应对教学研究困境的基础:信息法学的学科定位
(一)学科定位的功能描述
从功能主义的立场观之,学科定位决定着信息法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与研究方法的确立,也主导着该学科的教学模式。因为一方面,不同于传统法学的是,信息法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强烈的跨领域特征,其横跨了法律、信息管理、经济与信息技术等社会甚至自然领域。主研这些领域的传统学科——法学、信息管理学、信息科学与经济学性质各异,从而它们在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等方面判然有别。一旦信息法学被定位为其中某一特定学科,它的体系构建与方法选取必定偏重于该学科。例如,在经济学视野中,信息法学的研究工作需要以成本-收益以及合作博弈等方式展开[9];又如,在信息科学视域中,研习者需要多采用定量分析手段;另一方面,根据西方著名教育家菲利普·杰克逊所提出的内隐理论,特定学科或专业的从教者对课程的规划安排以及对课堂事件的处理能力取决于其教学观念与知识结构,而教学理念与知识结构形成于特定“解释框架”(interpretative system)。这一解释框架立基于学科的研究方法与理论体系,方法体系则正源自学科定位[10]。
而信息法学所面临的诸多困境之根源,正是在于信息法学作为学科的定位与归属不明。迄今学界对信息法学的定位问题存在着不同学说(详见后文),而这几种学说之间又存在着相当大的冲突性。譬如,传统法学的定位将会排斥经济学与自然科学式的定量分析方法,而信息科学的定位将会使传统法学的理论体系无从构建。这正好诠释了何以学界对信息法学的理论体系构建问题存在着根本性分歧,也能解释为何被用于该学科的研究方法失之于庞杂与零散。同时按照前文中菲利普·杰克逊的阐释,教师依据不同的学科定位方式,将形成不同的教学观念与知识结构,从而间接导致了教学效果的参差不齐。譬如笔者在位于重庆市渝北区与万州区的三所开设了信息法学课程的高校进行调研后,发现政法类或综合类院校(如西南政法大学与重庆三峡学院)将该学科定位为法学专业本科或研究生选修或必修课程,而信息技术类院校(如重庆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将其定位为信息技术专业专科生的选修课程。受此影响,三所高校在制定课程教学大纲、选订教材、教案编排等工作中采用了完全不同的路径。
(二)信息法学的学科定位——跨领域的独立法学门类
关于如何对信息法学进行学科定位的问题,学界形成了以下三种代表性观点:一是信息科学或信息管理学分支说。论者主张从数据控制原理、管理绩效与定量分析等角度从事研究工作,按照信息科学与管理科学的研究路径搭建学科平台。论者进而认为,信息法学属于信息科学或信息管理学下属的分支学科[11]。二是法律部门说。持该主张者认为,信息法学一经用于实践,将对相应社会关系做出有效调整。因此信息法学所研究的信息法有着自己所特有的调整对象,即“信息法律关系”。基于此,信息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12]。三是交叉学科说。根据此说,信息法学是涉及到刑法、行政法、民法甚至于宪法的交叉性学科,同时该学科的研究对象还包括知识产权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及数据库保护法等等。该学说的倡导者进一步阐释道,信息法所调整的范围本身就具有跨领域性。随着现代社会分工不断明确化,信息法学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一种研究方法,而需要综合运用其他方法[13]。
显然,第一种学说歪曲了对信息法学的学科定位,因此不足采。从根本意义而言,一门学科定位取决于其研究对象。而如前文所述,信息法学研究对象固然范围无限广阔,但其落脚点仍然是法律制度的安排与实施。对该活动的研究工作只能由法学来主导,这一角色是其他任何学科(包括自然科学与管理学)所无法取代的;与此同时,信息法学的特定研究对象决定了,其理论体系仍然需要按照“总则-主体与客体-权利义务-责任”式的传统法学思维进路来构建与设置,概念分析、价值分析与比较分析仍然是主要的研究方法。而按照信息科学与管理学的研究范式,定量分析方法等势必替代价值分析与概念分析,效率也将取代公平而成为学科研究的价值圭臬,这必将背离公平配置信息资源的学科研究初衷,阻碍信息社会中应有的“人性价值寻回”[14]。
笔者认为,信息法学既非部门法学也非交叉性学科,而是应用法学中的一个独立法学门类。部门法学(departmental jurisprudence)是以某个单一的部门法为依托和研究对象的,部门法学的任务是揭示部门法的产生、发展历史、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等规律。而按照法的本体理论,部门法的划分标准是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不同性质[15]。如前文所述,信息法的调整对象是与信息归属、交易与保护有关的信息法律关系。就属性而言,这一社会关系跨越了民事、行政以及国际交易等若干领域,由此其无法被单一的部门法所调整,进而任何一个部门法学的原理与方法论都不能单独被用以诠释与研究这一关系中的法律问题;与此同时,信息法律关系仍然是单一且独立的社会关系,这决定了信息法学不属于交叉学科的范畴,毕竟后者所研究的是多种复合且有关联的社会关系(譬如网络法所调整的与网络有关的关系,又如金融法调整的金融关系)。按照英国《牛津法律指南》的标准,在应用法学部类下面包含了国际法学、国内法学与附属学科(如律师法学与会计师法学)等若干门类(section)。类似于律师法学与会计师法学,信息法学也以特定的社会关系为研究对象,从而属于附属学科下的一个独立门类。在比较法上,2002年修订的俄联邦总统令《俄罗斯联邦的法律分类》就将“信息和信息化”(информация·и·информатизация)作为俄联邦法律的21个门类中的一个,与宪法、民法、刑法、劳动法等并列[16]。
三、应对教学研究困境的具体思路
(一)信息法学理论体系之构建:独立与开放
信息法学的学科定位决定了,其理论体系应当按照应用法学的套路来构建。而法学界内部对于如何具体构建信息法学理论体系的问题,又存在两种代表性的主张:一是沿循总论——核心理论(信息犯罪与信息安全、信息资源管理、信息自由与公开、知识产权保护)——有关信息的具体制度——实务操作(如信息法律纠纷及解决)的路径构建[4];二是按照信息的不同性质以及信息所在的不同社会领域,将信息法学分为信息公开法学、个人信息保护法学、信息安全法学、计算机信息网络管理法学等不同学科[17]。
笔者认为,为契合法学教学传统并回应信息时代的社会问题,我国应兼采两种观点的精髓而不宜有所偏废。一方面,作为大陆法系国家,我国的法学(尤其是应用法学)学科的理论体系设计以及教学内容安排是按照“从一般到特殊”的演绎逻辑思维进路完成的,而第一种关于构建总分式结构的主张更加符合这一传统,加之如前文所述,信息法学依托于以信息法律关系为调整对象的信息法,这一法律关系的基本原理在总论中能得到系统的展开,不同社会领域中的特殊原理则可由分论来阐释,对此,俄罗斯学者 B.A.Копылов 在2000年发表的《论信息法的体系》已作了充分论证[18];另一方面,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改进,新的信息种类不断涌现,随之而来的是新的社会问题与法律纠纷。因此正如我国一些学者所阐述的,信息法学应当保持一定的动态性与开放性,从而应对前述新问题[4]。
据此,信息法学的理论体系应当按照如下思路构建:第一部分,总论。其中包括信息法的研究对象、信息法的一般理论(含义、沿革、调整对象、理念和基本原则)、信息法律关系以及相关法律责任的认定与承担。信息法律关系按照其基本要素——主体、客体与内容展开。主体包括信息生成者、所有者、管理者与利用者等,客体包括政府信息、商业秘密、技术信息与个人信息等,内容以信息产权、个人信息权、公众知情权等为主干;第二部分,分论。在这一部分中,在不同社会领域里出现的信息归属和利用问题以及相关对策将得到重点阐释。分论下属政府信息公开法学、商业信息(商业秘密)法学、个人信息法学等;第三部分,信息交易与安全论。这一部分主要阐释与信息管理、公开与交易(包括信息的国际交易与流通)相关的规则、信息安全的基本要素以及相关主体为维护安全而采取技术措施的义务等。
(二)研究方法选定:以法学为主兼容其他学科
作为应用法学下的独立法学门类,信息法学研究者与教师应当坚持概念分析与价值分析等传统的分析方法。因为只有概念被精确地厘定,相关信息法原理才能得到系统与科学的阐释。诚如一位学者所言,如果信息时代的法学缺失对人文的终极关怀,那么它必将陷入利益的泥沼[19]。在信息法学的教研活动中,研究者与教育者需要保持自然法学式思辨的传统,注重对信息主体人格尊严与自由等基本价值的实现,并且以维护信息社会的公平为本旨,而不宜一概以效率价值尺度替代公平。毕竟,不论在新自然法学代表罗尔斯还是新制度经济学代表诺斯的眼中,公平与正义都是实现与维持效率的前提条件,制度设计者只有在确保公平与正义后方能实现效率[20]。譬如在论证个人信息的归属与交易规则时,研究者应遵循公平尺度而将本权利配置给信息主体,而不宜盲目追求效率地赋予处理者。
然而,作为一门跨领域的学科,概念分析与价值分析存在着不敷使用的地方,由此教研者有必要吸收其他学科研究方法之精长。理由是,按照概念法学的思维进路,法律被先验地视为独立于现实生活之外的自主体系。同时,这一研究进路“狭隘地集中于教条问题,论述于联邦最高法院最近期的决定,专注于细小的短暂的区别,而不是大胆的、科学的和描述性的著作,学术界没有产生出法官、律师和立法者为操作一个现代法律体系所需要的知识”[21];而在价值论的视野中,正义、效率、秩序等法的价值很容易被视为内容永恒不变的真理,从而忽略了人们在特定国情与时代环境下对价值的再选择以及对价值尺度本身的变更。对于信息交易以及信息科技等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前述传统分析方法就存在着回应能力上的欠缺。为辅其不足,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分析方法与信息科学的定量分析和数据分析等方法可发挥作用。
(三)教学工作开展:注重多学科的知识结合与资源整合
信息法学理论体系的开放性以及研究教学方法的兼容性决定了,该学科的教师在坚持以法学课程的教学手段与方法为主的同时,应当注重引入其他学科的先进成果。根据教育心理学理论,社会性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受教育者对课程内容的心理状态,从而极大地制约着教学质量的提高[22]。目前,信息法学课程的讲授对象主要是90后的本科生与硕士研究生,其思维方式与70、80后有着很大的不同,相对于传统法学式的概念解析与原理分析,他们对新视角与新问题更加感兴趣[23]。为了提高学生对于学科的关注度与兴趣,教研者有必要将信息管理学等学科中的原理与研究成果和法学知识结合。譬如笔者在调研中发现,重庆三峡学院就利用维格课程的模式向法学本科生展示我国的网络治理模式,这一教学方法显著优化了教学效果。
为了达到前述目的,教学工作者应当注重多种资源的整合。在信息法学的授课当中,除了知识资源(由教师和学生共同组成)与智慧资源(包括教科书与参考资料等)之外,网上资源也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对此,美国韦恩州立大学法学院的李特曼教授(Jessica Litman)开设的网络法课程(Seminar:The Law in Cyberspace)、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萨缪尔森教授(Pamela Samuelson)的个人网站主页、美国坦普尔大学法学院波斯特教授(David G.Post)的网络信息法课程等都提供了极好的范例[24]。
四、结 语
在语境论者的视野中,影响一门学科教学科研工作开展状况的因素是多样的。就信息法学而言,信息社会的整体发展程度、信息法治建设进程、教学研究人才与资料等知识资源储备状况乃至各教研单位学科与课程建设条件等因素,都起着制约与影响作用。然而从根本意义上言,信息法学教研工作的理念确立以及资源配置等均受制于学科定位,因此本文仅试图在对该学科做合理定位的基础上,对困境的应对提出几点具体建议。而如何优化其他影响因素从而完善信息法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则是学界需要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1] 齐爱民.拯救信息社会中的人格[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2.
[2] 马海群.信息咨询与决策[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34-37.
[3] 苗东升.系统科学大学讲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9.
[4] 宗诚,马海群.信息法学学科体系构建刍议[J].情报资料工作,2004(4):12.
[5] 罗冰眉.我国信息法学研究综述[J].情报杂志,2003(6):13-17.
[6] 马海群,乔立春.论我国信息法学的研究基础与学科建设[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1(l):18.
[7] 王知津,金胜勇.图书情报领域中的信息法律问题研究[J].图书与情报,2006(2):1-5.
[8] 国磊,马海群.系统科学方法在信息法学研究中的应用[J].图书馆论坛,2006(4):19-22.
[9] 卢现祥.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1.
[10]佐藤学.课程与教师[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32.
[11]周丽霞,马海群.信息法学的学科价值及学科归属问题探讨[J].情报科学,2004(11):1388-1390.
[12]齐爱民.论信息法的地位与体系[J].河北法学,2006(1):39.
[13] 周林.知识产权与信息法[EB/OL].[2013-09-21].http://www.iolaw.org.cn/shownews.asp?id=4904.
[14]林立.波斯纳与法律经济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4.
[15]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00.
[16] Russian Federation Council 2007 annual legislative report[EB/OL].(2009-01-30)[2013-02-10].http://www.council.gov.ru/files/journalsf/item/20090130153251.pdf.
[17]赵正群.信息法概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43-45.
[18] Копылов В А. О системе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го права[J].Сб. НТИ,2000,1(4):14.
[19]胡平仁,梁晨.人的伦理价值与人的人格利益[J].法律科学,2012(4):19.
[20]青木昌彦,奥野正宽.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M].魏加宁,等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264.
[21] MEHIGAN S,GRIFFITHS D.Restraint of Trade and Business Secrets:Law and Practice[M].Hongkong:Longman,1996:47.
[22]张大均.教育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43.
[23]刘建新,程昌华.基于专业建设内涵式发展的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探索[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99-101.
[24]马海群,周丽霞,刘迎红.信息法学课程网络教学环境构建[J].黑龙江教育,2010(5):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