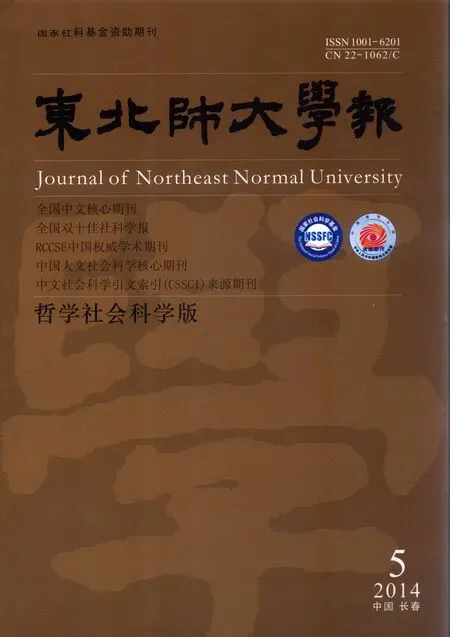走向“情感”的文化政治
——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的“情感教育”论
张 冠 夫
(北京语言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83)
走向“情感”的文化政治
——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的“情感教育”论
张 冠 夫
(北京语言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83)
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修正早期的启蒙主义的文学观,回归文学的审美属性,将文学的功能定位在“情感教育”上,而这并非标榜唯美的文学立场,其中正体现了深刻的现实关怀。梁启超将文学视作对现代国民进行人格教育的有力手段,从而为“开拓新政治”奠定民众和人才的基础。他发扬孔子开创的“诗教”传统,强调借助文学培养国民“趣味化”的人生观,并将传统文学作为教育现代国民的重要资源,着重指出文学在重构转型期国民的文化认同、铸造民族精神当中所能发挥的特殊价值。梁启超的“情感教育”论与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启蒙主义的文学功能观显出差异,构成对话。
梁启超;新文化运动;国民教育;情感教育;诗教
20世纪20年代,正当以《新青年》同人为代表的将文学作为宣传新思想、新道德,改造“国民性”的有力武器的启蒙主义文学观结出硕果的时期,梁启超却改变了自己早年将文学作为“新民”和“改良群治”[1]10之利器的认识,转而从情感的角度界定文学,强调文学的审美属性,并将文学的功能最终定位于“情感教育”[2]72。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梁氏将“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3]作为个人和同人的实践宗旨。梁氏此期对于文化与国民教育以及政治的关系的思考,为我们认识其有关发挥文学的“情感教育”功能的思想提示了方向。而这恰恰为既有的相关研究所忽略。对于梁氏后期转而强调文学的“情感教育”作用而与其早期的启蒙主义的文学功能观显出差异,这已为一些研究者所关注,然而截至目前的研究普遍存在三个主要问题:一是仅仅将其放在梁氏个人的文学思想的线性发展脉络中予以认识,而未将其置于复杂的时代文化语境中予以阐释;二是研究者多单纯采用文学、美学的研究方法,这一定程度上将梁氏的文学思想与其新文化运动期间丰富、复杂的思想面向割裂开来;由以上两点所导致的第三个不足是,对于梁氏“情感教育”论的现代性理论特征及现实关怀缺乏深入认识,因此也就难于对其价值和贡献做出准确评价。本文的一些思考即是针对上述不足的初步尝试。
一、“情感教育”与“开拓新政治”的内在关联
20世纪20年代梁氏经由将文学的功能定位于“涵养”“趣味”[4],终至定位于“情感教育”,回归其审美价值。梁氏对于“情感教育”的讨论始自1922年年初在清华学校为学生所做的系列演讲《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何谓“情感教育”?梁氏将其解释为“情感的陶养”;为何要对国民进行“情感教育”?梁氏首先强调“天下最神圣的莫过于情感”,情感“是人类一切动作的原动力”,继而指出情感具有美丑、善恶的两重性,以此他提出:“情感教育的目的,不外将情感善的、美的方面,尽量发挥;把那恶的、丑的方面,渐渐压服淘汰下去。”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艺术被梁氏视作“情感教育最大的利器”[2]71-72。为何梁氏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要在高扬科学理性大旗的时代主潮中强调“情感”和“情感教育”的重要性?
可以说,梁氏的“情感教育”思想一方面是其建设新文化和新文学的理论和实践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其国民教育思想的具体落实。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氏对蒋百里受欧洲文艺复兴启发而提出的“我国今后之新机运,亦当从两途开拓”:“一为情感的方面”;“一为理性的方面”表示赞同[5]84。而梁氏对文艺复兴所体现的理性与情感和谐发展的人文主义历史经验的肯定,是与其对启蒙运动以来片面强调科学理性所造成的19世纪以来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偏颇的反思同步的,以此,就中国新文化建设而言,梁氏反复强调在提倡科学理性的同时不能忽视情感维度的建设,必须两者并重。在新文化运动期间蔡元培早在梁氏之前就已经提醒新文化运动者“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6],梁氏是否受到蔡元培,甚至世纪初的王国维的“美育”思想的影响不得而知,但与后两者比较起来,梁氏的“情感教育”论融入了更多的反思现代性的因素则是无疑的。但这并不是说梁氏对于启蒙现代性就抱着否定的态度,梁氏也是科学精神和思想解放的积极倡导者,只是他强调要警惕启蒙主义的极端化。就梁氏的新文化建设观而言,启蒙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和谐共存是其特色,这在其“情感教育”论及其现实关怀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梁氏的“情感教育”论虽然以文学的审美价值为基础,但他将丰富的社会人生以及现实政治都纳入其审美视野中。在1922年所写的《情圣杜甫》、《屈原研究》、《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这三篇诗人专论中,梁氏对三位诗人与现实社会和政治的关联着墨较多,可以说它是梁氏观察三诗人以其情感品质为核心的人格构成的重要切入点,但梁氏对此的讨论都是围绕其作品的艺术特征,特别是其抒情方式进行的。如《情圣杜甫》中,当进入杜甫的情感和艺术世界,梁氏在强调其“极热肠”的同时也指出其“极有脾气”,对于前者而言,梁氏谈到:“他的眼光,常常注视到社会最下层。这一层的可怜人那些状况,别人看不出,他都看出;他们的情绪,别人传不出,他都传出。”对于后者而言,梁氏高度肯定杜甫的讽刺艺术,如在谈到杜甫的五首《后出塞》中的第四首时,他谈到:“读这些诗,令人立刻联想到现在军阀的豪奢专横——尤其逼肖奉直战争前张作霖的状况。最妙处是不著一个字批评,但把客观事实直写,自然会令读者叹气或瞪眼。”梁氏在文末针对当下新文坛以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为代表的,“主张人生艺术观”和“主张唯美艺术观”的各持一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依我所见,人生目的不是单调的,美也不是单调的。为爱美而爱美,也可以说为的是人生目的,因为爱美本来是人生目的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诉人生苦痛,写人生黑暗,也不能不说是美。因为美的作用,不外令自己或别人起快感,痛楚的刺激,也是快感之一。”[7]他将杜甫的关注人生、社会和重视艺术之美的并行不悖作为新文学家的典范,其中体现出的正是梁氏对于文学的审美价值的全面理解。
虽然20世纪20年代的梁氏并未将文学疏离于现实政治,但其对两者关系的理解与早期相比已有显著不同。1920年9月,在为《解放与改造》杂志更名为《改造》所写的发刊词中,梁氏代表研究系同人所表述的“宣言”之一即是:“本刊所鼓吹,在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相辅并行”[8]。梁氏一方面强调文化不能脱离政治,同时又强调文化相对于政治的独立性,两者既平行发展,又相辅相成。所以,虽然在《“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1921)、《学问之趣味》(1922)等中,梁氏反复重申自己对于学术的“无所为而为”[9]68的非功利主义的“趣味主义”[10]立场,但梁氏选择的并非是不关政治的纯学术态度,“开拓新政治”仍是他的归结点,只是要通过“宣传新文化”和“培养新人才”这样的兼顾社会教育和精英教育两者的途径而实现。梁氏将文学纳入其国民教育构想中,视其为“趣味极丰富之民众的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5]90。1922年7月3日在济南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所作讲演《教育与政治》中,梁氏将现代教育界定为:“教人学做人——学做现代人”,而所谓的教人“学做现代人”,就包括了让国民“学会做政治生活”,而这就需要从学会过“团体生活”,培养德谟克拉西精神入手。梁氏强调,现代大学教育的典范是“把智识教育放在第二位,把人格教育放在第一位”[11]。强调“人格教育”重于“智识教育”是他20世纪20年代一直坚持的主张。可以说,梁氏强调发挥文学的“情感教育”价值,正是希望在国民的现代人格形成中发挥其影响,这当中即包括了政治人格的塑造。但此期梁氏不再如“三界革命”时代那样将文学作为服从于政治改良需要的工具,而是从文学的审美属性出发,发挥文学的“无所为而为”的特殊功能——“情感教育”作用,培养具有健全的现代人格的新国民,从而为“开拓新政治”创造新的政治基础,培植新的政治主体。
梁氏的“情感教育”论不仅仅作为理论构想而存在,它体现出鲜明的实践品格。梁氏将教育的对象既指向国民个人,也指向国民整体。就前者而言主要指向以人生观为核心的个人人格塑造,后者则指向国民集体人格,即民族精神的建构。而就教育手段而言,梁氏尤其强调了传统文学对于当下的价值,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梁氏排斥新文学,梁氏恰恰强调新旧文学间的继承性和就共享文学的情感本质而言的一致性。以下分述之。
二、回溯传统与国民“趣味化”人生观的“陶养”
如果说“三界革命”时代梁氏将文学作为启蒙之利器的思想有较多的来自西方和日本影响的痕迹,其“情感教育”观则主要体现为对于中国以诗教传统为代表的思想资源的自觉继承。这与作为中国现代美育思想的提出和开创者的王国维以及作为奠基者的蔡元培明显不同。王国维早在1903年即在《论教育之宗旨》中提出了作为完整的教育所不可缺少的、与智育、德育相对而言的“美育”概念,并将其也称为“情育”[12]。蔡元培1912年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中,也同样在建立全面的现代教育体系的意义上使用了“美育”概念[13]。但无论是王国维,还是蔡元培,他们的美育思想都主要借助了德国的思想资源,是对康德、席勒等奠基的美学和美育思想的吸收和移植。梁氏则在对于文学的“情感教育”作用的讨论中较之前两者更多地利用了中国自己的传统资源,可以说,这是梁氏“以复古为解放”[5]6思想在对于文学功能的认识中的体现,而解放的对象正是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仅将文学作为启蒙工具的认识,这容待下文论述。
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1923)中梁氏通过讨论孔子的“诗教”来阐发文学的“使人养成美感”的功能,他谈到:“孔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孔子于文学与人生之关系看出最真切,故能有此言。古者以诗为教育主要之工具,其目的在使一般人养成美感,有玩赏文学的能力,则人格不期而自进于高明”,孔子“合文学音乐为一以树社会教育之基础,其感化力之大云胡可量”,“谓以诗教也,谓美感之能使社会向上也”[14]。在《文史学家之性格及其预备》(1924)中梁氏又将“诗教”传统直接从“情感教育”的角度予以阐释:“《诗经》的性质,温柔敦厚,乃是带有社会性,用以教人涵养性灵,调和情感的。所以称为‘诗教’”[15]。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不仅为梁氏发挥文学的“情感教育”价值的认识提供了支持和借鉴,也启发了他一种使生活艺术化的人生哲学,这体现了梁氏欲使文学艺术的审美取向变为一种健康的人生观的思想倾向。在《“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中,梁氏谈到其人生观“是拿两样事情做基础”:一为“责任心”;二为“兴味”。进而,他将自己的人生观与孔子的“知不可而为”主义和老子的“为而不有”主义联系起来,又将二者“归并”为“无所为而为”主义,并将其解释为“是生活的艺术化,把人类计较利害的观念,变为艺术的情感的”。梁氏将“无所为而为”主义的实现一方面指向社会改造,“求得适宜于这种主义的社会”,一方面指向个人的精神修养,即“把这种主义拿来寄托我们的精神生活,使他站在安慰清凉的地方”[9]60-69。在《为学与做人》(1922)中梁氏也如王国维、蔡元培一样谈到现代教育应该包括智育、德育和情育(王国维和蔡元培主要使用“美育”概念),不过他是将中国传统哲学的“智”“仁”“勇”与西方哲学和心理学的“知”“情”“意”相对应,围绕孔子所说的“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阐释智育、德育和情育的内涵和目标。在谈到“情育”的目标,即“仁者不忧”时,他将“仁”理解为“宇宙即是人生,人生即是宇宙,我的人格和宇宙无二无别”的“普遍人格之实现”,将其视为超越现实功利、不计个人成败得失的人生观。他又引了老子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认为“有了这种人生观,自然会觉得‘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自然会‘无入而不自得’。他的生活,纯然是趣味化艺术化。这是最高的情感教育,目的教人做到仁者不忧。”[16]梁氏借助中国传统哲学,将追求“仁者不忧”的“趣味化艺术化”的人生观视作“情感教育”的最高目标。如果我们将其与他在《欧游心影录》(1919)中对于西方世界由科学主义和唯物主义等的理性化偏颇所造成的“唯物的机械的人生观”[17]的批评联系起来,这正是他试图通过发挥光大“固有国民性”等“中国固有之基础”[18]833-835,使中国的新文化建设避免重蹈西方的覆辙。
饶有意味的是,梁氏主要借助中国本土的思想传统对于“情感教育”问题的阐发,与席勒的美育思想颇有契合之处。作为法兰克福学派后期代表人物之一的赫伯特·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中指出席勒《审美教育书简》一书的“潜在思想”,即,在席勒看来,文明的弊病是“理性对感性施以压抑性暴政”,要想消除这种“暴政”,“就必须恢复感性的权利”,总之,“要拯救文化,就必须消除文明对感性的压抑性控制”[19]。席勒在德国自身的文化传统中寻找抵抗文明的弊病的资源,梁氏也正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能够对现代病予以免疫的因素,这正是两者形成契合的根本原因。在《治国学的两条大路》(1923)中梁氏谈到:“我们有极优美的文学艺术作品。我们应该认识它的价值,而且将鉴赏的方法传授给多数人,令国民成为‘美化’”[20]。发挥文学,包括传统文学在现代国民教育中的“美化”功能,这正是梁氏“情感教育”论的实践方向。
三、以“情感教育”建构转型期国民的文化认同
20世纪20年代梁氏对于文学的“情感教育”价值的强调在指向国民个人的同时,也指向国民全体,即全民族。他在《美术与生活》中谈到:“审美本能是我们人人都有的。但感觉器官不常用或不会用,久而久之麻木了。一个人麻木,那人便成了没趣的人;一民族麻木,那民族便成了没趣的民族。”[21]梁氏在对于文学功能的相关论述中,也强调了其对于民族性的塑造和对于全民族的集体认同的构筑所能起到的作用。具体而言,梁氏在讨论中将文学与自己思想的两个面向结合起来,其一是发挥固有的“国民性”,其二是铸造国民的共同意识。梁氏在1921年10月作了题名为《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的演讲,其中他指出辛亥革命激发了国人“民族精神的自觉”和“民主精神的自觉”,就前者而言,梁氏把它看作是数千年国人的一种“觉悟”,即“确信我们是世界人类的优秀分子,不能屈服在别的民族底下”,“这便是我们几千年来能够自立的根本精神”[22]。以上所谈的梁氏思想的两个面向,就其根本而言,正指向“民族精神”的铸造。这正是梁氏20世纪20年代在对于中国传统文学和文化的重新阐释中,使孔子、墨子等先贤以及屈原、陶渊明、杜甫等大诗人在与现代思想、情感的相通中重新获得典范性,使《论语》、《诗经》等典籍以及大量的文学作品在现代语境下获得新的经典性的一个不应忽视的用心所在。
1920年3月刚刚欧游归来的梁启超发表了《在中国公学之演说》,演讲的最后他提出,中国不能盲目效法西方,必须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这就需要“吾人当将固有国民性发挥光大之,即当以消极变为积极是已”[18]834。梁氏认为中国固有国民性有“消极”和“积极”两面,应消除前者而发扬光大后者。梁氏此时对于“国民性”的两面观既不同于自己侧重于“改造国民之品质”的“新民”[1]10时期,也与当下《新青年》同人的国民性批判分歧明显。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的引子部分梁氏谈到,自己演讲的目的是启发大家把中西方文学中所表现的情感以及表现情感的方法进行比较,“看看我们的情感,比人家谁丰富谁寒俭,谁浓挚谁浅薄,谁高远谁卑近?我们文学家表示情感的方法,缺乏的是哪几种?”这是因为,“先要知道自己民族的短处,去补救他,才配说发挥民族的长处。”[2]72-73梁氏所谈的要比较的两个方面中,尤其是前者与“国民性”的关联紧密。如果说早期梁氏的批判国民性的思想是受到以日本为中介的西方国民性话语的影响,其对国人国民性之“劣下”[23]的评断是相对于西方人而言的,此时他则强调的是平等比较的立场,而比较的目的是“发挥民族的长处”,而“补救”“自己民族的短处”。同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的主流话语着力以文学展开国民性批判相比较,梁氏所强调的平等比较的立场,特别是他对于从文学中去发现“民族的长处”的强调就更体现出其现实针对性。该演讲中梁氏对于《诗经》的讨论尤其能够体现他的这一努力。在分析《诗经》中“回荡的表情法”时梁氏谈到,诗篇中“那情感的丰富和醇厚,真可以代表‘纯中华民族文学’的美点”,“《诗经》中这类表情法,真是无体不备”,其所表情感“真所谓‘温柔敦厚’,放在我们心坎里头是暖的”,“《诗经》这部书所表示的,正是我们民族情感最健全的状态。”[2]79-81就此而言,20世纪20年代梁氏对于以屈原、陶渊明、杜甫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诗人的情感品质的高度肯定,以及对于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的梳理,皆可看作是其对于“民族的长处”的发掘,而其目的是以此教育国民,将之发扬光大。
对现代中国而言,这是一个国民对固有文化的信仰遭遇危机,而新文化尚在孕育中的转型期,如何铸造现代国人共同遵循的新的价值体系,形成全民族新的文化认同,这是梁氏此期的另一重要的关注点。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1922)中梁氏谈到:“民族成立之惟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24]即“民族意识”的形成有赖于一个民族对于作为主体的自我的发现,而这主要体现为一个民族文化认同的独特性。在《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附录二”《治国学杂话》(1923)中梁氏有言:“好文学是涵养情趣的工具,做一个民族的分子,总须对于本民族的好文学十分领略,能熟读成诵,才在我们的‘下意识’里头,得着根柢,不知不觉会‘发酵’”。随后他又谈到“圣哲格言”“已在我们全社会上形成共同意识,我既做这社会的分子,总要彻底了解它,才不至和共同意识生隔阂”,“我们应事接物,常常仗它给我们的光明”[25]。如何铸造全民族在文化转型时代的集体认同,这个问题对于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梁氏强调文化的继承性,他坚持将传统文化作为建构国人现代的集体认同的重要资源,其对于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的梳理即含有借此形成国人的心理和情感共鸣乃至认同的意图。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将“民族”定义为“想象的政治共同体”,这个定义已经得到了相当广泛的认可。虽然他一再强调“想象”并非意指“虚假”、“捏造”,而是指其建构性[26],但这一定义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混淆了“民族”和“民族意识”这两个概念,以此“民族”作为由多种客观历史因素所形成的一个现实存在的本质受到忽视。而作为实际存在的“民族”以及其所携带的诸多历史因素才是形成现代的民族意识的最为重要的客观基础。梁氏在“情感教育”论中对于民族传统和历史经验进行不断回溯和重新阐释,正是将其作为构筑现代中国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的重要基础。
四、结 语
作为新文化运动以及文学革命的积极参与者,梁氏将文学功能定位于“情感教育”,这与以陈独秀和胡适为代表的《新青年》同人的启蒙主义的文学功能观产生分歧。首先,陈独秀和胡适等人主要强调的是文学的认识功能,而梁氏则更为强调其审美价值。其次,陈独秀和胡适等人的文学功能论就其思想基础而言是启蒙现代性,而梁氏则有意识地借鉴了西方反思现代性的思想资源,在其思想中既有启蒙现代性的一面,又有反思现代性的一面,两者相辅相成。再次,陈独秀和胡适等人主要突出的是文学在思想启蒙中的价值,所以其对于文学价值的认识与进化论相结合,强调当下的优先性;而梁氏的文学功能观则兼顾了文学的启蒙价值和文化价值两者,即其对于文学价值的认识在着眼当下的同时,也注意其对于精神和文化的传承发扬的功能。需要明确的是,梁氏对于文学功能的认识与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主流话语间固然差异明显,但两者间并非是对峙关系,而是多元互补的富于建设性的对话关系。
新文化运动的发生距今已近百年,而那些渐行渐远的思想者的身影则始终伴随着中国近百年的现代历史进程,甚至今天的我们仍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覆盖在这些先行者的身影中。学界不断地在呼吁重新认识和反思这场启蒙运动,但对于来自这场运动内部的反省和与主流的对话的实际存在,及其所具有的意义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梁启超20世纪20年代包括“情感教育”论在内的独特而丰富的文学思考的遭遇即如此。著名学者李长之在其写于四十年代初抗战建国气氛下的《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对五四启蒙运动做出这样的反思:“‘五四’精神的缺点就是没有发挥深厚的情感,少光,少热,少深度和远景,浅!在精神上太贫瘠,还没有做到民族的自觉和自信”。他所期待于当下的民族文化重建运动的是纠正五四运动的不足,使文化建设“从偏枯的理智变而为情感理智同样发展,从清浅鄙近变而为深厚远大,从移植的变而为本土的,从截取的变而为根本的,……”“这不是启蒙运动了。这是真正的中国的文艺复兴!”[27]李长之的认识是否受到梁启超的影响姑且不论,而两者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主义的警醒和对于中国文化建设应该真正走文艺复兴的道路的思考的相近之处颇引人深思。梁氏如若有之,不知是该为吾道不孤而欣幸,还是为其担心出现的新文化运动的某些偏颇在后人眼里竟成为现实而伤感?
[1]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M]//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北京:中华书局,1989.
[2] 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M]//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9.
[3]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584.
[4] 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M]//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79.
[5]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朱维铮,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6] 蔡元培.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M]//文艺美学丛书编辑委员会.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83-84.
[7] 梁启超.情圣杜甫[M]//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9:39-50.
[8] 梁启超.《改造》发刊词[M]//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743.
[9] 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M]//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9.
[10] 梁启超.学问之趣味[M]//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15.
[11] 梁启超.教育与政治[M]//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9:68-76.
[12] 王国维.论教育之宗旨[M]//周锡山.王国维集:第四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7-8.
[13] 蔡元培.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M]//文艺美学丛书编辑委员会.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4-7.
[14] 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M]//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68.
[15] 梁启超.文史学家之性格及其预备[M]//夏晓虹.《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940.
[16] 梁启超.为学与做人[M]//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105-108.
[17]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M]//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12.
[18] 梁启超.在中国公学演说词[M]//夏晓虹.《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9]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M].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39.
[20] 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M]//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112.
[21] 梁启超.美术与生活[M]//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24.
[22] 梁启超.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M]//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9:2-3.
[23] 梁启超.论中国国民之品格[M]//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5.
[24] 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M]//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1.
[25] 梁启超.治国学杂话(《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之附录二) [M]//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26.
[26]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5-7.
[27] 李长之.迎中国的文艺复兴[M]//李长之文集:第1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25-26.
[责任编辑:何宏俭]
Cultural Politics towards “Emotion”: Liang Qi-chao’s Research on “Emotional Education” in 1920s
ZHANG Guan-fu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Beijing 100083,China)
In 1920s,Liang Qi-chao revised the inchoate didacticism literary concept and regressed to the aesthetic attributes of the literature in positioning the function of literature as emotional education. His assertion reflects the profound concern for reality instead of advocating the aesthetic literature standpoint. Liang Qi-chao regarded literature as a powerful tool for personality education of modern national that laid the public and talents foundation for developing the new politics. He developed the “poem moralization” tradition which was created by Confucius and emphasized to develop the national and interesting outlook on life with the help of literature and also he regarded traditional literature as an important resource for educating modern national. Liang Qi-chao also mainly pointed out the special value that literature would play on the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in the period of reconsitution and transformation and the founding of national spirit.
Liang Qi-chao;New Culture Movement;National Education;Emotional Education;Poem Moralization
2014-03-1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13YJA751061);北京语言大学校级科研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12YBB04)。
张冠夫(1969-),男,吉林长春人,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G40-09
A
1001-6201(2014)05-021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