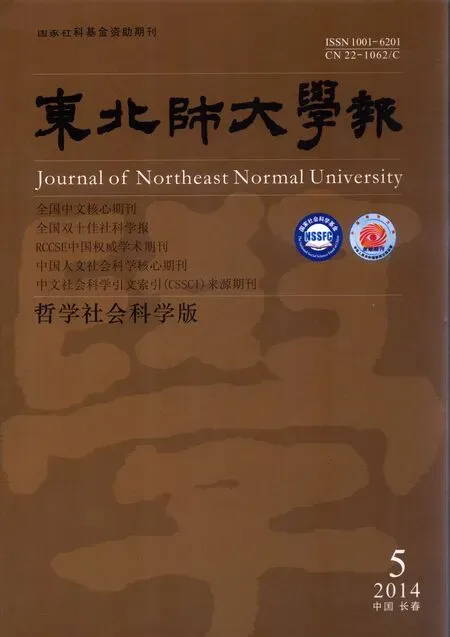“大礼议”与明代后期士人心态蜕变
赵 强,王 确
(东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大礼议”与明代后期士人心态蜕变
赵 强,王 确
(东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嘉靖“大礼议”以还,专制皇权的高度强化、社会文化和思想禁锢的加剧与经济发展、繁荣之间存在的错位,导致了明代中后期知识分子与君主间的严峻对立以及知识分子内部的急剧分化。士人阶层在政治和社会层面受挫,转向建设和享受日常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和生活观,使人得以正视自己的身体、欲望和个体生存。但与之相应的,却是对国家前景、社会事业的淡漠。
大礼议,士人心态,生活觉醒
嘉靖朝所爆发的“大礼议”,是明代中期一次牵连广泛、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孟森先生曾指出,“大礼议”对明代政局、世道与士心的影响极为深刻,实际可视为晚明衰亡局面的先声[1]191-205,因此它成为明清史研究的焦点之一。关于“大礼议”,海内外学者已在本事考证、议礼中各种政治势力的较量及其对明代中后期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的影响等多个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就“大礼议”对士人阶层心态及人生选择方面的影响研究还稍显薄弱。本文拟从“大礼议”入手,考察士人阶层在“大礼议”中所呈现的非理性心态及行为,进而探讨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对明代中后期知识分子心态及人生选择之蜕变的影响。
一、嘉靖“大礼议”始末
“大礼议”争论的焦点是“继宗”与“继统”的分歧。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丙寅,明武宗朱厚照病死于“豹房”。他没有子嗣和兄弟,生前亦未定立皇储,只留下一纸革除自己在位期间所行荒政与“召兴献王长子嗣位”的遗诏[2]212,这就在确认皇位后继者的世系身份上留下了遗患——按照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祖训》和帝王继承惯例,兴献王朱祐杬的长子即朱厚熜继承皇位本在情理之中,然而兴献王本是明宪宗(朱见深)之子、孝宗(朱佑樘)之弟,朱厚熜要名正言顺地继位,首先要明确自身在法统上是承续武宗的帝统,还是直接上承孝宗的帝统。这直接涉及朱厚熜在宗统、世系中的身份确认,即他是继伯父孝宗之嗣(过继),还是保持兴献王子嗣的身份由藩王入继大统。如果是前者,朱厚熜要脱离“宪宗—兴献王”这一宗支,进入“宪宗—孝宗—武宗”的宗系;如果是后者,则兴献王世系的地位就要被抬升为正统、与“孝宗—武宗”世系分庭抗礼。
这就是嘉靖年间朝野聚讼纷争长达20余年的“大礼议”的缘起。正德十六年四月,朱厚熜由安陆抵达京师,便在继位程序问题上与礼部官员及内阁首辅杨廷和等重臣发生冲突。按照礼官及内阁的意见,他应从皇城东安门直接入居文华殿,然后按照皇太子即位仪式择日登极。这一建议遭到朱厚熜强烈反对,他坚称“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双方僵持不下,在孝宗皇后张氏调停下,朱厚熜以百官“劝进”的姿态,“入自大明门,遣官告宗庙社稷,谒大行皇帝几筵,朝皇太后,出御奉天殿,即皇帝位”[2]215。正如世宗在《即位诏》中所宣示的那样,他如此讲究即位的程序,意在强调自己“属以伦序,(由外藩——引者注)入奉庙社”[3]卷54。换言之,世宗即位之初就想确立自身权威不容置疑的正当性和自主性,这对以辅臣元老自居的杨廷和等人来说不啻为当头棒喝。在后者看来,原来远居湖广外藩、年仅幼冲的世宗“与朝内佞臣、宦官及各派勋戚贵族势力关系较少,不易受武宗的错误影响”;同时,他“在政治上可能不够成熟,而易于接受以清除武宗弊政为中心的新的国是安排”[4]。
事实证明,明世宗并非一个从谏如流、可由他人掌控的皇帝。即位六天后,世宗就命令礼部讨论其生父兴献王的封谥问题。阁臣杨廷和、梁储、蒋冕、毛纪与礼部尚书毛澄等依据传统宗法制度中的“大宗”、“小宗”论,参照汉代定陶王和宋代濮王故事,认为“宪宗—孝宗—武宗”这一宗系是大宗,不可绝嗣,世宗继位必须入嗣大宗;“宪宗—兴献王”这一宗支本是小宗,本身没有皇位继承权[5]。因此他们建议“宜尊孝宗曰皇考,称兴献王为皇叔考兴国大王,母妃为皇叔母兴国太妃,自称侄皇帝名,别立益王次子崇仁王奉献王祀”[2]5036-5037。世宗对这一决议强烈不满,认为父母不可移易,其母蒋氏也坚决不从。这时,观政进士张璁上《大礼疏》,强调世宗继位乃是“伦序当立”,而非预先过继,因此与汉、宋故事不同。他驳斥杨廷和等人的大宗、小宗之说,认为“礼本乎人情”,不能因继帝统而斩断其与“宪宗—兴献王”一系的血缘关系,否则便是无父无母、违背天伦。这一建议虽然得到南京刑部主事桂萼等人附议,但他们人微言轻,在人数上也处于劣势,朝臣近200人联合支持杨廷和等人。明世宗情急之下,竟以退位相要挟。于是双方达成妥协:世宗称孝宗及张太后为“皇考”、“圣母”;对于兴献王及蒋氏,则分别加“帝”、“后”称号,无“皇”字,且冠以“本生”二字。
世宗对这一妥协并不甘心,一再敦促朝臣重新议定,欲称孝宗为“皇伯考”,而直接称兴献王为“皇考”,去掉“本生”二字,且在谥号中称“皇帝”。论辩日趋激烈,嘉靖三年(1524),杨廷和致仕,蒋冕、毛纪等重臣也相继罢官;张璁、桂萼等被委以重任,他们力主实现世宗意图。随即爆发了著名的左顺门哭谏:礼部侍郎何梦春、修撰杨慎等人率九卿、翰林、给事、御史及各部主要官员229人集体跪伏左顺门哭谏抗议。世宗震怒,下令锦衣卫先后逮捕200余人,为首的朝臣8人被流徙戍边,四品以上者被夺俸,五品以下被施以杖刑的多达180余人,其中17人被杖死[6]卷50,735-764。“大礼议”以世宗与张璁、桂萼等人的完胜暂告一段落。
后来,在世宗授意下,张璁等人总结战果,编撰《明伦大典》,由世宗亲自作序颁示天下。其后,世宗颇以制礼作乐的“圣王”自诩,又相继更定祭祀天地、祖宗、孔庙的礼仪,但凡有大臣抗谏,必遭杖刑、夺官。嘉靖十七年(1538),在权倖严嵩怂恿下,世宗下诏为其父兴献皇帝立庙号为“睿宗”,祔太庙、配享上帝,且在宗庙次序上先于武宗。至此,明世宗的“正名”计划终于完结。
就政治作为而言,世宗在位期间,除了革除部分武宗在位时的弊政与推动“一条鞭法”的大范围实施外,再无成就可言。由“大礼议”引发的君臣斗争、朝臣分化堪称朝野上下群体性的舍本逐末。“大礼议”有更加深刻、复杂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内涵,它实际上为当时的各种政治势力提供了一个历史契机,各派人物都试图借机彰显自身存在、实现自己的政治动机:以杨廷和为代表的阁臣之所以竭力反对世宗,实际上蕴含着内阁限制皇权的政治企图[7];士人阶层内部的分化与对立,一方面反映出政治守旧派与革新派的政见扞格[8],另一方面也映射了勋戚贵族与下层官僚的利益冲突[9];参与议礼的士人,既有操守坚正的正人君子,又有见风使舵的政治投机者,还有不明就里以究明礼仪、考辨学术为己任的迂腐学究;王阳明的多名弟子加入张璁、桂萼的队伍,支持世宗“正名”的行为,更是长久受到压制的新兴王学对正统程朱理学的反戈一击[10]……
如此说来,“大礼议”实则是一笔难以清算的糊涂账,不仅在当时,议礼的各方各执一词、难有定论,不得不凭借政治手段压制异议;即使在事后,关于“大礼议”的争论依然热闹非凡。清代毛奇龄回忆其在康熙年间修《明史》时的经历说:“向入史馆,纂修明史……然起草之隙,每闻同馆官论及大礼,辄两端相持,无所专决。偶或左右,必彼我争执,而不相下,一如当日之纷纷者。”[11]卷1在毛氏看来,自、汉、唐、宋、明以迄于清,其间博学鸿儒不可胜数,却无一人能拿出令人信服的依据和论证,着实令人费解。如前所述,“大礼议”这笔糊涂账之所以难以清算,除毛氏所谓诸议礼者不明汉、唐、宋、明的历史外,还因为它羼杂了复杂的政治、社会文化方面的矛盾纠葛。
二、“有明一代升降之会”:士人非理性的抗争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礼议”是明代士人阶层偏执型人格、非理性行为的集中爆发。士人的偏执和非理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对明世宗进行劝谏时胁迫同僚,发动群体性事件,不计代价以死相搏;二是面对异议者党同伐异,罔顾事理与是非,广泛制造舆论,以政治高压和道德、舆论压力打击异己,甚至威胁对方的人身安全。其影响所及,不仅导致了君臣关系势同水火,而且造成了士人阶层内部不共戴天的分裂与对立,而究其成因,则不得不追溯到自明代开国以来长期紧张的君臣关系等政治文化因素。
“大礼议”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左顺门哭谏事件。这一事件为不少史家所激赏和标榜,以其为有名一代“士气”之表征,是明初诸帝“扶植清议,作养士气”的遗泽[1]170。然而,如果详细分析当事人的言行,则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事件起于诸臣得知世宗决意改称孝宗“伯考”,金宪民、徐文华等人号召群臣效法宪宗朝大臣集体“哭谏文华门”事——在该事件中,明宪宗曾因群臣哭谏而放弃自己的立场。为了号召朝臣集体参与,杨慎倡言“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王元正、张翀更放言“万世瞻仰,在此一举,今日有不力争者,共击之!”于是群臣229人集体跪伏左顺门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起初,世宗不以为意,命令司礼监谕退诸臣。但群臣不达目的不罢休,朱希周等人扬言“辅臣尤宜力争”,胁迫内阁大臣毛纪、石珤等人也参与进来。世宗多次谕退无效,勃然大怒,下令司礼监记录诸臣姓名,逮捕为首的张翀等8人,而杨慎、王元正则“撼门大哭,一时群臣皆哭,声震阙廷”[6]卷50,750-752。显然,在这次事件中,大部分朝臣是迫于杨慎、张翀、朱希周等所营造的舆论压力与威胁下,不得已参与其中的。
罔顾现实、不计后果的非理性的“哭谏”甚至是“死谏”,不仅有损士人形象,很不体面,而且本身缺乏理论和思想支撑。谏议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制衡君权、避免政治决策失误、保证国家行政不至脱离正轨的途径之一。历史上著名的谏臣如商之比干、汉之主偃父、唐之魏征、杜如晦等备受推崇。但古人同样讲求谏议的智慧与限度,并不主张对君主无限度的“忠”与不计代价的“死谏”,如孟子就曾以大臣与君主关系不同,对谏议做出区分,认为贵戚之臣“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而异姓之臣则“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12]卷10。也就是说,劝谏君主要保持理性和克制,如果君主不能虚心纳谏,就要根据所谏过错之大小与自身处境对君主或自己的去留做出决断。这当然是理想的状态,历史上少有因不纳谏而被废掉的帝王,所以士人们更倾向于“讽谏”:一方面主张劝谏,另一方面强调自身的独立自主性,即有道则仕,无道则隐。如《白虎通》、《说苑》、《长短经》等多部著作就借孔子之口说:“谏有五,吾从讽之谏。事君,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去而不讪,谏而不露”,且批评比干等强谏之人“以区区之一身欲正一国之淫昏,死而无益”[13]卷7。就左顺门哭谏士人而言,他们的行为的确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现,意气用事,务求“结党求胜,内则奴隶公卿,外则草芥司属,任情恣横”,被后世史论家目为“言官恶习”[14]卷35。
君臣相激,上下争胜,意气膨胀之中自然难有公允、平和的舆论环境。史家万斯同认为“大礼议”不仅是嘉靖一朝“升降之会”,而且是“有明一代升降之会”。其所以具有历史转折意味,就因其影响所及,乖气致戾,衣冠夺气,严重助长了社会舆论和世道人心的非理性:“至大礼议定,天子视旧臣元老真如寇雠。于是诏书每下,心怀忿疾,戾气填胸,怨言溢口……君臣上下,莫非乖戾之气。”[15]卷5因此,所谓“清议”也就流于乖戾之气、怨愤之情的倾泻。对此,王夫之的认识尤为精辟:“既使之隐忍而幸于得生,则清议之讥,非在没世而非即唾其面,诅咒之作,在穷檐而不敢致乎其前,又奚不可之有哉?”[16]卷2,86-87“大礼议”中,士大夫阶层内部的分化与斗争,尤其暴露了明代士人非理性的一面。
天启年间曾担任内阁首辅的朱国祯在回顾“大礼议”时,批评张璁一派的做法说:
永嘉(张璁——引者注)议礼,佐成圣孝,是也。及修大礼全书,身为总裁,上疏曰:元恶寒心,群奸侧目。元恶者,指杨石斋(廷和)父子也。夫大礼只是议论不同,其心亦惟恋恋于孝宗之无后而争之强,叩门伏哭,失于激,为可罪耳。乃曰奸曰恶,不已过乎?乘时侥幸之人,放泼无忌……[17]卷2
朱国祯的评议可谓公允,只是他未曾注意到,张璁等人“曰奸曰恶”、“放泼无忌”的做法,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议礼之初,杨廷和等就开启了这种以借题发挥、无限上纲甚至是诬陷诅咒为主导的政治斗争和社会舆论的恶劣走向。“大礼议”发端时,杨廷和授意毛澄援引汉定陶王和宋濮王事为例,说:“是足为据……有异议者即奸邪,当斩!”这种不容置疑、压制异议的铁腕姿态并非虚张声势,面对张璁、桂萼等人根据儒家传统礼教“礼出于情”的思想提出的“继统”而不“继宗”的理论,杨廷和一派并未从学理上做出驳斥,而是粗暴地给后者扣上“赋性奸邪”、“立心险恶”的帽子,并且以集体辞职威胁明世宗说:“臣等与举朝大臣、言官言之不听,顾二三邪侫之言是听,陛下能独与二三邪侫共治祖宗天下哉!”[2]5038这种与异见分子势不两立的情形固然表明了政治斗争的险恶,历史上也不乏严重打击、迫害政敌的先例,但从“大礼议”可以看出,明代士人将这种斗争手腕发挥到了极致,以至于当张璁、桂萼等人被世宗从南京召回再次议礼时,举朝哗然,士大夫“咸切齿此数人”,欲杀之而后快。史书这样记载:“众汹汹,欲扑杀之。萼惧,不敢出。璁阅数日始朝。”就连掌管法律、刑名的刑部尚书赵鉴也丧失理智,立请“捶杀之”[2]5175-5176。这种群情激奋的场面并非声张恐吓,因为,在“土木之变”后,就发生过多起士大夫在议政时当廷施暴,殴打政敌的事件,甚至有多人被朝臣聚众打死[2]4701-4706。
平心而论,议礼只是观点和立场的不同,即便涉及政治立场、实际利益冲突,由于各方持论各有理据,也很难据以判断孰是孰非、孰忠孰奸。但“大礼议”的参与者们无论在议礼相持不下、还是在事后盖棺定论时,都从未有过将争议限定在对话与辩论层面的克制,而是师心使气,固执己见,将士人阶层应有的节制、理性、温和一概弃之不顾,充分暴露了人性的尖刻、阴暗、偏狭、矫激等非理性一面。这不仅是对传统士大夫温润尔雅、从容大度的理想形象表述的颠覆;而且,它促使我们不得不去思考,为何在讨论以规范人之行止、仪态、言论为宗旨的“礼”时,士人们竟然对自身的行止、仪态、言行无所顾忌?
究其原因,士人群体的偏执人格、非理性的行为的集体爆发,既非明代前期君主“扶植清议,作养士气”的遗泽,亦不是少数言官“任情恣横”的个体性情所能掌控,而是与明代开国以来严酷的政治环境、持续紧张的君臣关系长期积渐所致。考之历史,明代实为中国士人阶层的政治生存环境最为险恶、最没有尊严和自主性的时代之一。明代诸帝中,能勉强称得上礼贤下士的,只有享国不长的建文帝和明孝宗,其余均对待文人士大夫如蓄奴婢,动辄捶辱,乃至籍家灭族;而明太祖自胡惟庸案后废除宰相制度,将国家行政、司法、人事任免等权力全部集中到皇帝手中,即便是权倾朝野的内阁,也只有建议权而无决定权[18]。这使君主专制的程度空前加剧,皇权缺少有力的监察与制衡,士大夫的职能仅限于遵命办事,皇帝本人也独断专行,肆无忌惮。尤其是明太祖制定《大诰》,将“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其罪至抄札”列为“十大罪”之一[2]2284,以暴力强迫士人出仕,斩断后者“无道则隐”的退路,更剥夺了他们自主选择人生出路的独立性,加剧了士人阶层在出处之间无所适从的惶惑和恐惧。洪武九年(1376),平遥训导叶伯巨上疏言朝廷用人时说:
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网罗捃摭,务无余逸。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师,而除官多以貌选。所学或非其所用,所用或非其所学。洎乎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诛戮,则必在屯田工役之科。率是为常,不少顾惜,此岂陛下所乐为哉?诚欲人之惧而不敢犯也[2]3991-3992。
时隔半个多世纪后,士人的政治际遇没有丝毫改观,争取尊严和最起码的礼遇,仍然是士人阶层不可企及的奢侈想象。正统八年(1443),翰林侍讲刘球上疏言:
古之择大臣者,必询诸左右、大夫、国人。及其有犯,虽至大辟亦不加刑,第赐之死。今用大臣未尝皆出公论。及有小失,辄桎梏箠楚之;然未几时,又复其职。甚非所以待大臣也[2]4404。
终明一代,正如王夫之所言,“天子孤高于上,举群臣而等夷之”,士大夫的升降陵替全凭君主喜怒,充满偶然性和悲剧性。“身为士大夫,俄加诸膝,俄坠诸渊,习于呵斥,历于桎梏,褫衣以受隶校之凌践”[16]卷2,86。关于这一点,史家早有关注,这里仅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永乐二十二年(1424),明成祖朱棣召集群臣商议北征事宜,大臣夏原吉、方宾等以军饷不足、国库空虚劝谏获罪,系之大狱。成祖一意孤行,令佞臣礼部尚书吕震兼领户部、兵部事。吕震恐惧异常,为防止他自杀卸事,成祖“令官校十人随之,曰:若震自尽,尔十人皆死。”[2]4181即使被委以重任,士人所体验的亦非“得君行道”的成就感,而是生死一线,如履薄冰。这不仅造就了终明一代君臣离心、持续紧张对立的君臣关系,而且给士人心理蒙上巨大阴影。
明末钱谦益曾将险恶、恐怖的政治生态及其对士人心态的影响比喻为“寒宵噩梦,缠绵淹抑,能使人精销虑耗”,“雷震暴雨,错遌旁迕,能使人心悸魄夺”[19]卷58,1428。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偏激、乖戾、刻薄、激切成为议礼士人之人格的显著非理性特征。在“大礼议”之初,我们就看到,内阁首辅杨廷和起草世宗即位诏书受到阻挠时,曾异常愤怒:“往者事龃龉,动称上意,今亦新天子意耶?”议礼过程中更是“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几三十疏”[2]5038,这种寸步不让、偏至执拗的坚守,与后来左顺门哭谏群臣的矫激行为,无疑是明代士人长期饱受君主陵辱后所做的孤注一掷的反抗。而士人阶层内部不共戴天的搏杀,正是长期政治高压下士道沦丧、士人阶层无法在政治和思想上达成共识并为之奋斗,转而不计手段谋取个人或所属派系利益的恶果。
三、“大礼议”对士人心态、人生选择之影响
“大礼议”可谓明代政治文化中君臣对立与士人阶层内部斗争的临界点,士人阶层偏执、非理性人格与高亢激昂的言行,在皇权的绝对强势与粗暴镇压中一败涂地。部分士人如张璁、桂萼等人依附皇权、迎合上意以求攫取高位的做法鼓励了政治舞台上的奔竞之风,以至于时人不得不以更加偏激的方式抨击士风与士习,认为嘉靖以还,士风浇漓、士习败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如王阳明就说“近世士大夫之相与,类多虚文弥诳而实意衰薄,外和中妒,徇私败公,是以风俗日恶而世道愈降”[20]卷21。他所抨击的士大夫结党营私、世道人心败坏的危局,无疑是切中时弊的,但这也仅指出了“大礼议”在政治层面产生的消极影响,即国家政权已经变成了充斥着私欲的乌烟瘴气的名利场。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王阳明等人虽没有言及,但却以自身的行动与人生选择展现出来,那就是士人阶层政治参与积极性的消退,与之相对应的,是走向社会、走向生活之热情的高涨。
正德、嘉靖两朝后,抛弃举业、以“帖括故艺”(八股文)为俗成为一时士人竞相标榜的好尚。在明中后期的传记、笔记史料中,我们经常能读到某人“不试故艺”的风雅之举。在今人的研究中,我们也常能看到对这种鄙夷名利的高尚气节的赞赏。然而,若细究起来,促成士人政治积极性消退的原因,除了所谓的“风雅”、“高尚”的气节之外,最为直接的,恐怕还是仕途之险恶、政治生态之颓败。在大礼议“左顺门哭谏”事件中表现尤为突出的朱希周,因与议礼新贵桂萼不合,在嘉靖六年(1527)称疾隐退,乡居三十余年,其间三十余次被引荐、征召,终究没有复出。他致仕后曾作有《张良归山图》一诗:
袖却朝簪别汉家,赤松相候在烟霞。
而今悟得全身计,不似从前博浪沙[21]。
诗中所言“博浪沙”,指张良招募力士,以铁锥狙击秦始皇于博浪沙的典故,后世常借此表达舍身为国的情志,如李白《猛虎行》曾谓“朝过博浪沙,暮入淮阴市。张良未遇韩信贫,刘、项存亡在两臣”,以示胸怀天下而不遇的愤慨。但在朱希周诗中,“博浪沙”是一种不自量力之举,全身远祸、保全性命是他在大礼议中目睹死者枕藉的惨相后的人生感悟。即便未曾参与的士人,大礼议所带来朝不保夕的恐惧与焦虑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文征明一生九试不第,就在晚年即将对仕途绝望之际,受到朝廷大员举荐,召赴京城,被授予翰林待诏的职位。此时大礼议如火如荼,文征明目睹明世宗对“左顺门事件”的处置后,心惊胆寒,在致岳父的信中写道:“征明比来因跌伤右臂,一病三月。欲乘此告归,又涉嫌不敢上疏……前日议礼杖死者十六人……充军者十一人……为民者四人。”[22]卷27,1431作为一个旁观者,文征明由议礼士人的惨状体会到了“身在彀中”的矛盾、恐惧,虽已绝意于仕进,却唯恐此时上疏请辞会被视为消极抵抗,内心的惶惑与焦虑自不待言。联系到他此后诗中屡屡流露出的致仕归乡之思,如《旅怀》:“事事浮荣外,幽怀久病中……短发垂垂白,那堪犯朔风”、《才伯过访》:“归心闻断雁”、《对酒》:“世事有千变,人生无百年。还应骑马客,输我北窗眠”[22]卷6,118-119、《内直有感》:“野人不识瀛洲乐,清梦依然在故乡”[22]卷11,298……不难理解,他为何在《谒江浦庄先生留宿定山草堂》中说:“就中何事尤堪羡慕,国是人非了不关!”[22]卷7,127甚至在以究明天道人伦为己任的道学先生眼里,无兵祸、无饥寒、无病人、无囚人的基本生存,都成了津津乐道的“清福”[23]卷2。无怪乎有学者断言明代知识分子“有意切断与权力世界的关联”,认为在他们身上找不到任何“得君行道”的儒者抱负[24]175。
事实上,保全身家性命、绝意于仕进的心态转变,并不意味着中晚明士人群体完全放弃“治平”与“行道”理想,只不过他们在人生价值实现的平台选择上,由国家政治层面,转向社会和个体生活。这一士人群体在人生选择上的向“下”与向“内”的转变,主要体现为下述两种倾向:
一是积极投身社会事业,倡导“亲民”与“经济”,致力于民众教化和下层社会公序良俗的营造。关于这一士人群体的人生动向,余英时先生曾将其概括为“觉民行道”,即将目光由庙堂转向民间社会,通过讲学传播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与思想、信仰,进而建构理想的社会秩序[24]188-211;王汎森先生则通过更为细致的考察,总结出明代知识分子所担当的三种社会角色:社区运动者、草根性启蒙者、心理咨询者[25]。就历史实际来看,明代士人尤其是阳明学派、泰州学派的心学家们通过身体力行以影响底层民众、改造社会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如修宗祠、兴办教育、移风易俗、规划建设社区环境、发展公益事业等[26]。但好景不长,士人们走向社会的举动很快引起朝廷的警惕,加之部分士人矫俗好名、藉讲学之机横议时政,所以在嘉靖年间,明世宗就将王学斥为“伪学”、“邪说”加以禁止;到了神宗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又动议禁讲学、毁书院,士人阶层的社会积极性极度受挫。即使在张居正死后,讲学、书院之禁不复存在,知识分子们躬亲践履“知行合一”的盛况也再难重现。以晚明负有极高声誉的冯梦祯为例,他早年以文章、气节名声甚著,对张居正剪除异己的专横颇为不满,又无从宣泄,以至于“潠血数升”。其父深谙政治斗争之险恶,“不忍见壮子流血死墀下”,劝其辞官南归。张居正事败,冯氏受到排挤,郁郁不得志,曾从罗汝芳(近溪)讲性命之学、师事名僧真可修习禅学,但这都不过是为求得个体心灵宁静罢了。等到他应诏出任南京国子监祭酒时,社会的讲学、经济之风荡然无存,他看到的是“成均(国子监)教衰,横舍鞠为园蔬,博士倚席不讲”的荒凉颓败之景[19]卷51,1299-1302。从政凶险、走向社会的道路受阻,一代文人士大夫只能退回个体生活层面,“流连山水,品香斗茗,如悠游退士”。
二是摒弃传统压抑日常生活的观念偏见,亲近、拥抱方兴未艾的商业化、世俗化、奢侈化的时代生活风潮,将心思灌注于建设并享受安逸闲适、富足美好的日常生活。中国传统士人历来崇尚“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的人生信条,人的物质性欲望及其他日常生活需求向来被限定在很低的层面,不治生产、不问家计、不理生活是士人阶层竞相标榜的人生姿态。因此,翻检中国古典文献,往往能看到如下话语: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纵化大浪中,不喜亦不惧”、“仰咏尧舜言,俯遵周孔辙。所贪既仁义,岂暇理生活。纵有旧田园,抛来亦芜没”、“家计一不问,园林聊自娱”、“生计抛来诗是业,家园忘却酒为乡”……这是一种以精神、道义压抑和克制人的欲望,或以艺术想象置换日常生活需求的生活策略。其影响所及,就是在观念中形成了以精神性压抑物质性、以终极关怀取代日常生活需求的生活结构。明代正德、嘉靖、万历以还,士人对国家政治的失望、社会关怀的受阻,以及经世致用思想的高涨,导致了士人阶层对人的俗世日常生活的价值发现和重新定位,物质欲望和日常生活需求从逼仄卑微的空间中解放出来,投身生活、将生活视为人生的主体和目的被赋予正当性。同时,嘉靖、万历年间,中国的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区域化、商品化程度空前提高,物产丰饶、工商流通发达、城市崛起使人们的生活内容变得日趋丰富,一时间号为“盛世”;甚至在旁观者看来,“凡是人们为了维持生存和幸福所需的东西,无论是衣食或甚至是奇巧与奢侈,在这个王国的境内都有丰富的出产”[27]。因此我们看到,生计日用、平居处事、养生保健、日常娱乐从士人生活观念结构的底层崛起,“不试故艺,推以治生”,安享“清福”、“努力寻个好生涯”,成为士人阶层尽情拥抱的人生目标。不仅“闲适消遣”斯风日炽,即使是在任何文明中都难以得到认同的奢侈性消费,也在某种程度上被鼓励、标榜,如张岱就对自己的奢华生活津津乐道:“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袁宏道甚至认为只有挥霍、奢侈才能展露人的真性情、体现人生的真境界[28]。当然,这种生活风气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世,都曾遭到严厉指责,需要指出的是,明代士人生活热情的高涨并非“欲壑难填”、“玩物丧志”之类简单的道德判断所能一言以蔽之,其间交织着复杂的政治、社会思潮、文化和经济因素等驱动力[29]。其中,士人阶层的政治与社会理想及其实践方面所遭受的巨大挫折,无疑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明中期嘉靖“大礼议”以还的政治、社会、经济发展与士人心态及人生选择方面的蜕变[30],体现了专制皇权的高度强化、社会文化和思想禁锢的加剧与经济发展、繁荣之间存在的严重错位,导致了明代中后期知识分子与君主间的严峻对立以及知识分子内部的急剧分化。士人阶层生活意识的觉醒固然是合理和正当的,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古代社会压抑人性和欲望的生活观念,使人得以正视人的身体、欲望和个体生存[31]。但与之相应的,却是他们对国家前景、社会事业的漠不关心,对于中晚明社会来说是不可估量的伤害。因此,在晚明短暂的繁华、太平迅即走向衰朽之际,才出现了一批从政治和社会制度层面反思皇权专制、力图重构君臣关系、“天下”与国家关系的启蒙知识分子。
[1] 孟森.明史讲义[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 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 傅维鳞.明书[M].丛书集成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1046.
[4] 李洵.“大礼议”与明代政治[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5):49.
[5] 张显清.明嘉靖“大礼议”的起因、性质和后果[J].史学集刊,1988(4):10-11.
[6]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1977.
[7] 张显清.明代政治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338-339.
[8] 田澍.嘉靖革新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57-59.
[9] 南炳文.嘉靖前期的大礼议[J].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2):91.
[10] 张立文.论“大礼议”与朱熹王阳明思想的冲突[J].南昌大学学报:人社版,1999(2):65-69.
[11] 毛奇龄.辨定嘉靖大礼议[M].丛书集成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1.
[12]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3:324.
[13] 郭沂.孔子集语校补[M].济南:齐鲁书社,1998:155-157.
[14] 赵翼.廿二史札记[M].北京:中国书店,1987:507.
[15] 万斯同.石园文集[M].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485.
[16] 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7] 朱国祯.涌幢小品[M].笔记小说大观影印本.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144.
[18]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92-102.
[19]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20]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823.
[21] 王鸿鹏.中国历代状元诗:明朝卷[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129.
[22] 文征明:文征明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3] 黄宗羲.明儒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2008:45-46.
[24] 余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
[25] 王汎森.晚明清初思想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2-28.
[26] 梁洪生.江右王门学者的乡族建设:以流坑村为例[M].台北:新史学,1997,8(1):43-87.
[27] 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M].何高济,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10:10.
[28] 赵强.闲情何处寄——《闲情偶寄》的生活意识与境界追求[J].文艺争鸣,2011(2):129.
[29] 李佳.论明代君臣冲突中士大夫的政治价值观[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140-143.
[30] 徐林,郝文.徐渭养生生活初探[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100.
[31] 王确.生活美学的多元对话——“新世纪生活美学转向:东方与西方对话”国际研讨会综述[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6):289-291.
[责任编辑:赵 红]
The Great Rites Controversy and Its Effect on the Metamorphosis of Scholar’s Mentality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ZHAO Qiang, WANG Que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China)
As one of the most high profile and the biggest political fallout during the late Ming dynasty, the great rites controversy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scholars’ mentality. Due to the feudal imperial autocracy run to the peak, and the economic indicators also reached histrionic heights, the imbalance between the late Ming politics and society had become intolerable. Thus the scholars began to enjoy the beautiful experience of the daily life, and they learned to show how to be looked very elegant. Next came their body, desire and everyday life. It provided a new way of life to the Chinese and seems to be vanguard and very important.
The Great Rites Controversy;Scholar’s Mentality;Ideal of Life
2014-02-20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2JZD017);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经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13QN041)。
赵强(1983-),男,山东郓城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王确(1954-),男,吉林蛟河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K248
A
1001-6201(2014)05-0013-07
——兼论 “训民正音”创制者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