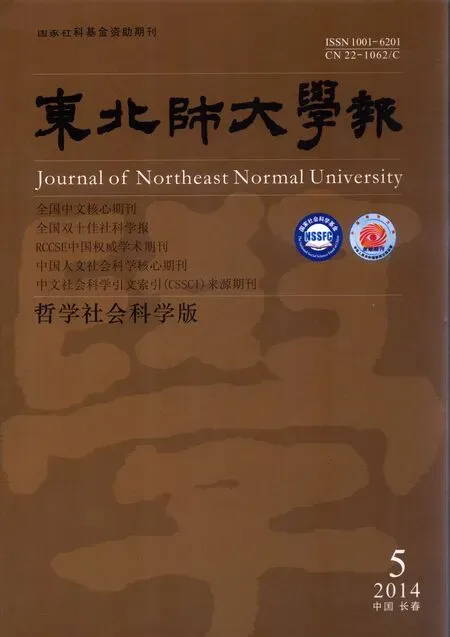从压力控制到社会支持:仇恨犯罪的治理转型
高 玥,单 勇
从压力控制到社会支持:仇恨犯罪的治理转型
高 玥1,单 勇2
在当前仇恨犯罪频发、犯罪风险高涨及社会管理创新的时代背景下,以往源自“压力维稳”的“压力控制”政策愈发不适应犯罪治理的新形势。借助底层视角分析仇恨犯罪,底层抗拒构成了仇恨犯罪频发的深层社会原因;化解底层抗拒的社会支持政策应获得高度重视,从压力控制到社会支持构成了仇恨犯罪治理的新趋势。
仇恨犯罪;压力控制;底层抗拒;社会支持
一、“压力控制”政策无法有效应对仇恨犯罪
当前,由个人以报复社会为目的而实施的闹市行凶、校园行凶、连环枪击、公交爆炸、开车撞人、破坏铁路等交通设施的仇恨犯罪频发。这种仇恨犯罪也被称为个人恐怖主义、极端暴力犯罪,但由于仇恨犯罪更能反映该种犯罪类型的心理本质,所以学界更倾向于使用源自美国的“仇恨犯罪”指代此类犯罪*国内相关研究主要有:王文华:《“仇恨犯罪”若干问题研究》,《河北法学》,2011年第4期;王文华:《群体性暴力事件与仇恨犯罪:刑法与刑事政策的回应》,《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陆玮:《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仇恨犯罪现象研究》,华东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顾为平:《美国仇恨犯罪论纲》,《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第5期。。
在美国,基于种族和宗教等动因、针对“被污名化群体”的仇恨犯罪(又称偏见犯罪)屡禁不止。对此,以1968年《联邦仇恨犯罪防治法》、1990年《联邦仇恨犯罪统计法》、2009年《联邦地方执行仇恨犯罪防治法》等法案为主的反仇恨犯罪法律体系日臻完善;截至2009年,美国共有47个州规定对仇恨犯罪予以刑事处罚[1]。由于社会结构、法律制度、文化背景等方面差异,中美仇恨犯罪不可等量齐观。不同于在美国基于种族、宗教、性取向等偏见而实施的犯罪,仇恨犯罪在我国主要表现为底层群体实施的暴力抗拒。这种暴力抗拒一般由处于社会边缘的底层群体成员实施,不具有组织性;多针对公共场所的临时性聚集人群实施侵害,并不像恐怖犯罪一样针对军警、政府机构;多采用极端暴力的方式报复社会,这一点与恐怖犯罪具有相似之处。
以往仇恨犯罪的治理模式是在“维稳”总体框架下依靠政法机构及政府力量开展“压力控制”。这种“压力控制”政策由于下述原因,无法实现真正减少仇恨犯罪的治理目标:
第一,在治理理念上,源自“压力维稳”的“压力控制”政策往往更偏重于对仇恨犯罪的应急处置与事后打击,相对忽视相关群众基本权利的维护,仅能实现治标的效果。
学界较早地对盲目追求“刚性稳定”的“压力维稳”政策进行了反思[2],并指出中国必须由刚性稳定过渡到韧性稳定[3]。“压力维稳”导向下的“压力控制”政策具有明显的事后性、应急性及短期性。事后性往往表现为只有仇恨犯罪发生时,相关部门才行动起来采取事后处置、安抚、打击等相关工作,事前的社会政策和预防措施乏力。应急性表现为在仇恨犯罪发生后政府随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将仇恨犯罪视为社会危机事件,动员各种政府资源联合应对;针对仇恨犯罪的系统性、全局性的治理措施相对受到忽视。上述事后性和应急性特征必然导致仇恨犯罪治理的短期性。
第二,在治理主体上,“压力控制”政策更依赖和推崇政府力量的主导,社会参与乏力,不当维稳、体制性防卫过当等问题突出。当前,仇恨犯罪治理主体主要限于政府力量,在政法委牵头、公安机关打击、基层政府组织配合的治理框架下,仇恨犯罪的应急处置往往能够保持较高的效率;但个案的及时处置不能替代全局性的预防工作,有时政府处置措施还容易引发体制性防卫过当等问题。此外,由于社会参与的不足,如何监督政府的“压力控制”、防止权力异化和滥用也是仇恨犯罪的防控难题。
第三,在治理机制上,“压力控制”政策在客观上弱化了法律的权威,治理手段的强制性明显。“压力控制”政策往往依托各级政府的行政推动,政府行为的法律依据问题有时遭受冷遇。毕竟,事后性的应急处置无法替代系统性的法律保障,城市公共安全风险只有置于健全的法律体系之下才是可控的犯罪风险。
第四,在实践效果上,“压力控制”政策并未实现仇恨犯罪的有效控制,相反,近年来仇恨犯罪还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扩散趋势。基于新闻媒体的报道,仇恨犯罪不仅广泛发生于人口聚集的省会城市等大中城市,还发生在农村及铁路交通沿线*如2014年4月发生的K7034次列车脱轨案就系铁路职工基于报复社会目的而实施的。;仇恨犯罪的实施方式(如爆炸、校园行凶、闹市行凶等)具有明显的模仿效应*如在2010年福建南平校园惨案发生后的几十天内,在我国其他城市的中小学、幼儿园连续发生了数起校园行凶案件,造成了惨烈的后果,引发社会各界对校园安全的深刻反思。;仇恨犯罪的目标具有随意性,社会上的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被害人。
可见,以往“压力控制”政策弊端重重,仇恨犯罪治理模式已经到了必须转型的时刻;而仇恨犯罪治理转型则取决于对该罪深层次社会原因的认识。
二、底层抗拒:仇恨犯罪的深层社会原因
“底层研究源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印度学术界对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形塑下的精英主义史观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底层研究的影响迅速由印度波及美国、拉丁美洲和东亚等地,形成了以古哈、查特吉等为代表的印度‘底层研究学派’。”[4]“底层研究的崛起与底层群体的反抗运动不断涌现有关。”[5]底层抗争的研究范式获得深入探讨,国家在底层抗争中的角色、底层抗争的治理模式、通过互联网的社会抗争及刑事社会抗拒的实证考察等问题获得深入研讨。于是,底层研究和底层视角为仇恨犯罪原因探讨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首先,由于对社会转型的不适应,底层群体在社会失范背景下更容易遭受各种挫折且被边缘化,社会底层成为反社会心理最易集聚的群体,构成犯罪高危人群。
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社会各阶层、群体之间的分化与冲突已成为当前社会一个不争的基本事实。受以往单纯追求GDP的政绩考核影响,政府在社会保障、医疗、福利等领域对底层群体帮扶亟待提升。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各个行业的准入门槛日益提高,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日渐固化。于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某些群体逐渐被边缘化,社会矛盾频发的现实环境为仇恨犯罪提供了天然的“培养基”。按照默顿的社会失范理论,犯罪主要发生于以下两种情况[6]:第一种情况,当社会成员认同社会所提出的共同价值观或奋斗目标,而社会所提供实现这些目标的合法手段或方式极为有限时,必然会有人会试图运用不合法的手段来实现合法的目标。第二种情况,当社会成员不认同主流社会的价值观,也不认同实现目标的合法手段时,反抗、泄愤、破坏及敌意行为就会大量发生。对于社会一般人的犯罪动因来说,可能第一种情况最为常见;但对于底层群体来说,上述两种情况均较常见,尤其是对于频繁遭受挫折、具有较为强烈反社会心理的底层成员来说,第二种情况往往构成实施仇恨犯罪的基本动因。
其次,在“压力维稳”和“压力控制”下,底层群体与政府及其他阶层的冲突更易激化、更为突出。以往的“压力控制”政策尽管能起到较好的治标效果,但对社会底层群体的生存状况并未起到根本性的改变。每次应急处置的成功仅局限于案件告破、罪犯落网的层面;每次应急处置的不当之处还会引发新的矛盾和对立。当然,实施“压力控制”政策并非没有意义,但只有“压力控制”政策与其他治本的公共政策配合运用时,才能形成犯罪治理的合力。中国历史的丰富经验反复说明了一个道理,即对社会底层群体,面包比管制更有效。
最后,从犯罪亚文化角度看,对生存或基本生活遭受威胁的群体大谈道德与守法的效果可想而知,底层身份为底层群体实施暴力抗争提供了貌似“正当的理由”。
结合我国现实情况,群体性的底层抗拒往往表现为群体性事件,而个体实施的底层抗拒在极端层面往往表现为仇恨犯罪。这些群体性事件与仇恨犯罪频发的背后不仅有利益之争,还有支撑底层群体内在反社会心理的犯罪亚文化。这种反社会心理主要表现为在合法维权或谋利渠道屡屡碰壁后所形成的挫折感、绝望感支配下的报复社会、发泄不满情绪心理。如“仇富”、“仇官”、对他人权益的漠视等心态。由于底层群体成员本身缺乏一定技能、接受教育的水平有限、经济地位低下,该群体成员更易接受这种反社会心理。可见,仇恨犯罪与底层抗拒存在紧密关联,遏制仇恨犯罪必须改善该群体的生存状况进而消解犯罪亚文化。
三、以社会支持化解底层抗拒
通过对底层群体实施仇恨犯罪原因的剖析,可以发现以往重刑事政策轻社会政策、重事后应急处置轻事前预防的“压力控制”政策值得反思,政府以往“压力维稳”及自上而下的控制模式不利于化解底层群体的暴力抗争。而以改善底层群体生存状况、保障底层群体利益表达机制制度化的社会支持政策则有助于从根本上减少仇恨犯罪。
首先,社会支持政策不仅是刑事政策,更是改善底层群体的一揽子解决方案与系统性社会工程,从而为仇恨犯罪治理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治理模式。
美国学者卡伦较早地将源自社会学、心理学的社会支持理论系统引入犯罪学研究,通过对犯罪学中社会控制理论的反思,该理论强调对潜在罪犯给予各类型的社会支持构成了预防犯罪的有效策略。“社会支持理论无疑为犯罪学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也为社会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个‘正面的’、非控制性的预防和减少犯罪行为的理论依据。”[7]可见,“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社会支持政策不仅是刑事政策,更准确地说是社会公共政策。该政策是围绕改善社会底层群体的生活状况而提出的,该政策能够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慈善、救济、文化等多种手段,动员政府、社区、民众等多种主体,开展多层次、类型化的实践活动。该政策为仇恨犯罪治理提供了一种根本性的解决思路。
其次,社会支持政策能够有效改善底层群体的生活状况,为底层抗拒心理的化解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社会支持政策通过就业、教育、医疗、救济、住房等举措的实施有助于改善底层群体的生活状况,提高其生活水平。在发达国家,移民犯罪往往较为突出,但随着移民因逐渐融入所在社会而改善其生活条件,这部分移民的犯罪率就逐渐下降;在我国,农民工犯罪较为突出,但随着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加速,这部分农民工的犯罪率亦逐步下降。可见,生活条件的改善、经济收入的增加能够有效推进底层群体融入主流社会,能够有效化解社会抗拒心理。
再次,社会支持政策能够有效动员最广泛的社会力量关注底层群体,为底层抗拒心理的化解提供最为丰富的治理资源。作为综合治理系统,仇恨犯罪治理离不开多元社会主体的参与;作为系统工程,社会支持措施的实施也离不开各类社会群体的广泛参与。实际上,社会支持政策本身就需要依靠多元主体、在多个层面上、开展多种措施,尤其是在社会基层与基础领域,对底层群体的社会支持措施更易组织和发动社区力量深入参与。来自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帮助,是消除高危人群抗拒心理和反社会心理的最佳工具。
最后,社会支持政策重视为底层群体的利益表达、权利维护提供制度设计,为底层抗拒心理的化解提供法律保障。如何将各种社会支持措施的实施日常化和稳定化,这就需要法律制度的保障。社会支持政策中最关键因素就是社会支持体系的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实施。
总之,社会支持政策不仅表现为化解底层抗拒的具体措施,也是国家治理仇恨犯罪的总体方略,更代表了刑事政策的发展方向。
[1] 孙道萃.美国仇恨犯罪介评与我国刑法理论的应对:兼及群体性事件的刑事治理观[J].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2(3):27-43.
[2] 于建嵘.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类型及其基本特征[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6):114-160.
[3] 于建嵘.当前压力维稳的困境与出路——再论中国社会的刚性稳定[J].探索与争鸣,2012(9):3-6.
[4] 王洪伟.当代中国底层社会“以身抗争”的效度和限度分析 一个“艾滋村民”抗争维权的启示[J].社会,2010(2):215-234.
[5] 王庆明,陆遥.底层视角:单向度历史叙事的拆解——印度“底层研究”的一种进路[J].社会科学战线,2008(6):224-227.
[6] 张旭,单勇.犯罪学基本理论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135.
[7] 江山河.社会支持理论[M]//曹立群,任昕.犯罪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00.
2014-02-21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4BFX04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3YJC820013);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一般项目(Y14G030059)。
C91
A
1001-6201(2014)05-0292-03
1.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编辑部;
2.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
[责任编辑:何宏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