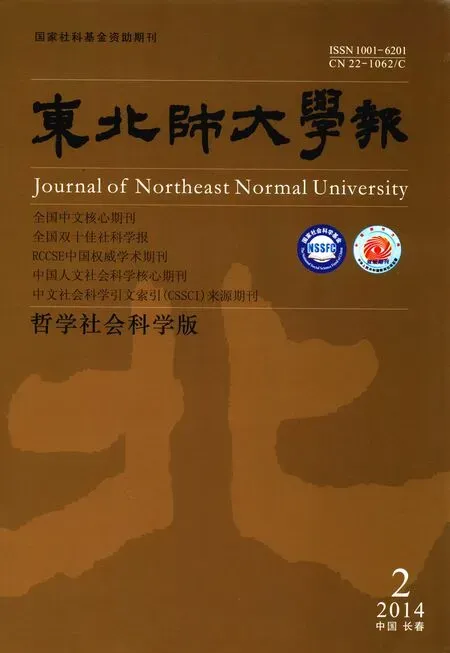“李约瑟难题”的长时段考察
(东北师范大学 物理学院,吉林 长春130024)
《中国科学技术史》(原文: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一书的编纂与刊印,奠定了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在中国科技史上的里程碑地位。尤为关键的是,该书所凸显的“李约瑟难题”之影响意义更是不言而喻。然而,从长时段的历史脉络、尤其是中西文明交流的过程中考察,“李约瑟难题”的现象并非始自李约瑟。事实上,鸦片战争之前来华的耶稣会士(传教士)们就已经意识到中国科技文明的独特之处,其中既有优点,也不乏缺点。并且,当他们把中国的科学技术传回欧洲之后,在欧洲诸国引起了“中国文明热”的高潮,欧洲各国的科学家在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崇拜不已的同时,也发现了诸多缺陷[1],并在李约瑟之前,对中国古代科学的特质及不足进行了分析,这些结论不亚于后人对“李约瑟难题”的解答。这意味着,对中国古代科学为何落后于西方近代科学的原因探求,有着长时段的历史过程,甚至说,这是中西文明交流、碰撞的“结晶”。
一、利玛窦对中国古代科学的认识与思考
中西文明为两种不同形态的文明,二者之间的较大规模接触在明代中后期。以利玛窦为主要代表人物的传教士们,伴着地理大发现的“西风”来到了中国。在传播基督教的同时,也将西方文明迅猛发展的成果带到了中国,拉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西方文明已不同于古典的、中世纪的西方文明,它是以近代科学为中心的近代文明,而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近代科学更是不同于古典时期的科学。按照一般说法,西方近代科学至少有以下三个源头:一是古希腊的演绎逻辑;二是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三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培根式”实验方法。这三个方面构成了西方科学的支柱,诚如爱因斯坦所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2]574所以,当明末的传教士们来到中国时,他们一方面肯定了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层面上取得的辉煌成就,同时,也意识到西方科学与中国科学的不同之处。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作为早期来华的耶稣会士,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与其他传教士一样,利玛窦来华的主要目的是传播天主教教义,但不同的是,利玛窦在传教的过程中,一方面翻译与撰写了大量的西学著作,把西方文艺复兴之后的天文、数学、地理等知识传入中国,使中国人开始接触到西方近代科学知识;一方面,又用西文记录了其在华经历以及用拉丁文译成的中国儒学经典“四书”,从而让西欧诸国进一步了解中国。并且,由于利玛窦长期客居中国的经历,使他对中国的制度、文化、法律、风俗等有过较深的接触与研究。他说:“我们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差不多三十年,并曾游历过它最重要的一些省份。而且我们和这个国家的贵族、高官以及最杰出的学者们友好交往。我们会说这个国家本土的语言,亲身从事研究过他们的习俗和法律,并且最后而又最为重要的是,我们还专心致志日以继夜地攻读过他们的文献。”[3]3正源于此,利玛窦对中国的认识与研究绝不是浮光掠影、走马观花式的结果,而是多年研究的心得。
其中,利玛窦虽对中国的医学、数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的成就惊叹不已,但也明显地察觉到二者之间的不同。他不止一次的指出中国人的机械工艺作法不同于西方人的作法,以及中国人在诸多方面没有掌握欧洲人的技巧等等,并特别指出中国人所熟悉的唯一较高深的哲理科学就是道德哲学,即便是中国人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但他们尤其是希望通过科举考试而做官的士阶层却没有人愿意去研习数学或医学,“结果是几乎没有人献身于研究数学或医学,除非由于家务或才力平庸的阻挠而不能致力于那些被认为是更高级的研究。钻研数学和医学并不受人尊敬,因为它们不像哲学研究那样受到荣誉的鼓励,学生们因希望着随之而来的荣誉和报酬而被吸引。这一点从人们对学习道德哲学深感兴趣,就可以很容易看到,在这一领域被提升到更高学位的人,都很自豪他实际上已达到了中国人幸福的顶峰。”[3]34从中可知,利玛窦对中国认识的结论还是较为客观的,并深刻地意识到西方世界所重视的自然科学在中国主体的士阶层中却是隐流、暗流,似乎并未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利玛窦虽认识到中国的自然科学与西方的近代成果存在着不同,但其中的具体不同为何?他未做过系统的研究,也未指出中国和西方的差距以及二者之间的孰优孰劣。这一认识,代表着一批明末来华传教士对中国自然科学的总体认识。
二、巴多明对中国古代科学落后原因的分析
利玛窦将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带回欧洲,此即《基督教远征中国记》。他在书中对中国古代科学的描述是17、18世纪的欧洲人了解这方面内容的重要窗口。继利玛窦之后,又有大批传教士来华。而此时的中国,正是明清鼎革之后的清朝,虽然清初的“杨光先教案”对欧洲传教士的冲击,但这一局面随着康熙的即位以及欧洲天文学知识的精准性而发生改观。这一过程中,南怀仁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他在取得康熙的信任之后,又不失时机地向皇帝进言为那些被流放的传教士平反;一方面,他又派信使到罗马和巴黎求援,希望两地再派传教士来中国传教。后一方面的结果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为其诚意所感动,派遣了传教士来中国。需要注意的是,这批来华的法国传教士不同于利玛窦诸人,他们还肩负着对中国的考察任务。这从1685年1月28日法国六位耶稣会士(白晋、张诚、刘应、李明、洪若翰、塔夏尔)领到的路易十四的签名授权书就可见一斑[4]。由于康熙对西方科学知识的重视,因而那些有科学特长的传教士受到皇帝的青睐,甚至有些人还充当皇帝的顾问与教师,向其介绍最新的西方科学知识。重要的是,他们还将中国的天文学、医学及工艺技术带回欧洲,掀起了法国及英国的“中国热”,促进了17、18世纪中国与欧洲的交流。在此过程中,来华的传教士将深入理解的中国科学知识用书信的方式传回欧洲,供当时皇家科学院的科学家们学习与研究。由于这批耶稣会士的学识素养不同于利玛窦等人,所以他们对中国古代科学的认识显然高于利玛窦诸人,并且已明确指出中国古代科学的缺陷与不足。其中,法国传教士巴多明的分析与解读最具代表性。
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3—1741)为法国来华传教士的佼佼者,他凭借其学习满汉语言的天赋、广博的欧洲科学知识以及外交能力博得了康熙与雍正的青睐,得以常侍康熙御侧,并长期担任教廷、葡萄牙和俄国使臣的翻译,又在宫廷中讲授拉丁文,培养外交人才。重要的是,巴多明在此过程中一方面研习中国的科学技术,主要集中在医学和天文学等领域;另一方面,又翻译了西学著作,向中国人介绍西学知识。犹如利玛窦一样,在中西科学技术的两相比对的过程中,巴多明也发现了中国古代科学与西方科学的差异,在他寄回法国的书信中向法国人介绍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历史与现状,并意识到中国的科学落后于西方。在信中,巴多明写道:“从前由中国人从事的天文观察均载于其史书、天文学论著或其他具有一种无可争议的古老性的史书中。它们是由对二十六次日食的观察组成的,宋君荣神父对此作了计算。他通过计算发现这些日食恰恰落到了由中国作家们指出的年、月和日中。”[5]38在这里,巴多明先承认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科学性与正确性,并且领先于欧洲至少数百年,并且,这样的话不止一次地出现在他的信中,但紧接着,他又指出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落后性,“中国在如此漫长的岁月中,在一片如此美丽的蓝天下,处于与我们的第一批天文学知识的出处迦勒底和埃及一样理想的方位中,中国人却再未于这一学科中取得更大的发展。”[5]130
与利玛窦不同,巴多明不止认识到中国科学的落后性,而且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在他看来,其因有二:一是那些可能会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的人,却不能期待得到任何报偿;一是无论是在外部还是内部,都没有刺激和维护竞争的任何机制[5]41-43。对于前者,巴多明说道,即便是在官方钦天监任职的天文学家,他们的收入仅能维持生计。这就使他们缺少了继续发展与创新的物质基础。官员们尚且如此,遑论其他手工业者。所以,中国若要发展科学,只靠皇帝的提倡是不够的,“而是要有数位连续执政的皇帝,支持那些以其研究和实用而成功地得出新发现的人;他们积累巨额资金,以赏赐功勋卓著的人员,为其提供必要的旅行和购置仪器的经费,他们必须使数术学家们从贫困的恐惧中解脱出来,或者是从看到被不大精通这类知识者的迫害中解脱出来……”[5]41-42而对于后者,巴多明则指出,中国的内部与外部皆无竞争,也无刺激和维护竞争的任何机制。正因如此,中国的古代科学技术在发展与应用过程中,无论对错,都没有对立方给予指出,只能任其发展,人们无法察觉其中的缘由。最重要的是,巴多明意识到科举制对科学的阻碍。他发现,支撑中国人努力读书的动力不外乎高中科举的欲望,于是他们日夜苦读儒家经书进而写出精彩的文章,以期考中科举,考中之后,他们关注的是伦理准则、法律知识以及皇帝的政令等等,至于那些不能带给他们荣誉与地位的科学,是不会引起读书人的过多关注的。在巴多明看来,中国人的思辨科学远远低于欧洲人。虽然,他们比世界其他任何民族都具有足够的思想和理智,但没有思辨科学的支撑,这些科学很难有进一步的发展。并且,与其他传教士的认识不一样,巴多明并未将汉语视为发展思辨科学的一大障碍,而关于其原因,他并未作出具体而详细的解答,但从这个意义上说,巴多明对中国科学落后性的分析与解答却是来华传教士中最为标准和客观的。
三、法国启蒙思想家与日本江户汉学家对中国科学落后的思考
随着来华传教士规模的扩大,天主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日渐明显,继清初的“杨光先教案”之后,康熙虽然看重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知识而允许他们继续在中国传教,但“尊祖”与“尊耶”的矛盾再次引起了“礼仪之争”,其结果是雍正驱逐了来华传教士,关闭了开放的国门。自此之后,18、19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大部分以利玛窦、巴多明等人来华传教士的见闻与书信为主,虽曾一度掀起了启蒙运动中的“中国热”浪潮,但却缺少了亲身体验。重要的是,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通过其对中国的间接认识,也意识到中国古代科学的落后性。
伏尔泰作为法国启蒙思想家之一,他对中国的兴趣源自于他少年时在路易大帝学校求学的经历,而这所学校正是来华的传教士所创建。在《路易十四时代》、《哲学辞典》、《风俗论》等著作中,既不乏对中国文明与文化的理解与认识,更含有他对中国古代科学落后性的论述与分析。从来华传教的见闻录中,伏尔泰认识到中国天文学的古老性与权威性,“根据最确凿的年表,远在公元前2155年,中国就已有观测日蚀的记载。这次日蚀观测业经前几个世纪派往这个陌生国度的一些西方传教士数学家验证。这些数学家对这个民族赞佩不已,并且向他们传授了有关知识。宋君荣神甫核对了孔子的书中记载的36次日蚀,他只发现其中两次有误,两次存疑。”[6]239显然,他对中国天文学的认识与巴多明一样,也是以宋君荣神甫的记录为主。同样,他也与巴多明一样指出了中国古代科学的落后性,并提出了“李约瑟难题”式的疑问,即:“既然在如此遥远的古代,中国人便已如此先进,为什么他们又一直停留在这个阶段?为什么在中国,天文学如此古老,但其成就却又如此有限?为什么在音乐方面他们还不知道半音?这些与我们迥然不同的人,似乎大自然赋予他们的器官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他们所需的一切,却无法有所前进……如果要问,中国既然不间断地致力于各种技艺和科学已有如此悠久的历史,为什么进步却微乎其微?”[6]248对于这一情形的原因,伏尔泰的分析为:“一是中国人对祖先流传下的东西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崇敬心,认为一切古老的东西都尽善尽美;另一原因在于他们的语言的性质——语言是一切知识的第一要素。用文字表达思想本应是一种极其简单的手段,然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却是极端困难的事。每个词都由不同的字构成。在中国,学者就是识字最多的人,有的人直到老还写不好。”[6]248-249第一个原因,伏尔泰曾不止一次地言道,中国人对祖先的崇敬阻碍了物理学、几何学和天文学的进步,因为对祖先的崇敬妨碍了他们对已有科学的深造与发展,所以,中国的古代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便停滞不前,很难再有新的突破。而关于第二个原因,伏尔泰则指出中国人的语言阻碍了中国科学的发展,至于汉语是如何影响中国科学的发展,似乎伏尔泰未作具体阐述,但从他的相关论述中似乎可见端倪。他说:“我们相当了解中国人现在还跟我们大约三百年前那时候一样,都是一些推理的外行。最有学问的中国人也就好像我们这里15世纪的一位熟读亚里士多德的学者。但是人们可以是一位很糟糕的物理学家而同时却是一位杰出的道德学家。所以,中国人在道德和政治经济学、农业、生活必需的技艺等等方面已臻完美境地,其余方面的知识,倒是我们传授给了他们的。”[7]323在这里,伏尔泰指出了中国人是推理的外行,言外之意,中国古代科学的发明者缺少理论支撑,没有理论支撑的科学只能停留在观察、实践及应用的层面,当这种局面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会衰落。
无独有偶,日本江户时代的学者在接受了兰学、洋学知识后,以此为参照系数来重新认识中国古代的科学,也意识到中国科学缺少理论方法。杉田玄白为日本江户时期的医学家,他在接触到以解剖学为根基的西方医学后,将其与日本社会长久信奉的中医比对,发现了中医“理论”的特别之处,即:“支那之书者有方无法也,非无法,所以为法者不明也。其法也,人人阿所好设说作论,立以为法也。故十书十说未一定焉,譬如隔铜器察热,或云炭火,或云柴火,或云热汤,或云热饭,不辨汤与火,唯知其热,而论之焉耳。”[8]241他以中医医治一病妇为例,说:“试使通支那学者三人诊之:一人云食积,一人云恶血,一人云饮癖。又使之施治,五日与消积之药,不治则十日与破血之药,如此而不治,则又十日与逐水之药也。幸治者,医以为我能知病也,病者亦以为幸遇良医也。若不幸而不治,则医者茫然不知因何死焉,病者亦不知其因何死焉。是其本不明,其法不正也。”[8]241所以说,玄白的“支那之书者有方无法也,非无法,所以为法者不明也”的说法,不仅是对中医理论方法的概述,更可以视为对中国古代科学理论方法阐述的点睛之笔。
余 论
按照李约瑟的说法,“李约瑟难题”的完整表达为:“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的或中古型的理论?……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了近代科学,这种科学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未能在亚洲产生与此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是什么?另一方面,又是什么因素使得科学在中国早期社会中比在希腊或欧洲中古社会中更容易得到应用?最后,为什么中国在科学理论方面虽然比较落后,但却能产生出有机的自然观?”[9]2这意味着,“李约瑟难题”是一个问题集,它至少包含了以下几个层面:(1)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6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2)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17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3)为什么中国传统科学一直处于原始的经验主义阶段,而没能自发地出现近代科学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自此问题提出之后,国内外的诸多学者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对其进行解答,其中既有不乏鞭辟入里的分析,更有接近问题真相的解答[10]。有学者指出近代以来中国科学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两因论即纯科学真空和连续性破坏,并进而列举出中国科学落后的8大原因,包括:中国文明停止在工匠文明和经验文明——没有心脏的民间技术与发展极限;缺乏持续性的发展——中华文明之光淹没在战火硝烟中;缺乏纯科学研究——中华文明终止于工匠文明;缺乏专利与股份——技术发明的催化剂与保护神;缺乏古希腊科学的哲学思想;缺乏交流与交通——科学是交流的产物;缺乏让大多数普通人中的优秀人才发挥潜力的机制——平等机会与天才的随机产生;缺乏解放普通劳动者的发明思想——技术发明的引擎[11]。
以上说法,几乎涵盖了目前学界对“李约瑟难题”解答的大部分说法,其中,“中国文明停止在工匠文明和经验文明”的说法已然说明了问题之所在。这意味着,我们常常将“科学”与“技术”连称,似乎是司空见惯的说法,而事实上,科学与技术的内涵与外延完全不同,中国古代的发明只能被视为“技术”,其支撑点是工匠文明与经验文明。与之相反,西方近代科学才真正属于“科学”范畴,它是建立在形式逻辑为核心的理论基础之上。在鸦片战争之前,利玛窦、巴多明、伏尔泰等人虽已意识到中国古代科学的不足之处,但并未完全贬低其价值。但随着中国在近代的衰落,中国文化及中国科学却等同于“落后性”的代名词,长期被西方学者所鄙视。所以,今天如何客观地审视“李约瑟难题”的历史与现实意义仍极具学术价值,对现在中国的教育及科学发展具有更大的启示,而长时段的历史脉络考察,无疑更接近历史真实。
[1]韩琦.关于17、18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科学落后原因的论述[J].自然科学史研究,1992(4):289.
[2]许良英,范岱年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3][意]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M].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
[4]朱静.康熙皇帝和他身边的法国耶稣会士[J].复旦学报,1994(3):108.
[5][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四[M].耿昇,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
[6][法]伏尔泰.风俗伦:上[M].梁守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7][法]伏尔泰.哲学辞典:上[M].王燕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8][日]杉田玄白.狂医之言[M].日本思想大系64[C].东京:岩波书店,1976.
[9][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一[M].袁翰青,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0]李成龙.“李约瑟问题”研究综述[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68.
[11]刘里远.中西自然科学思想[M].北京:中国大地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