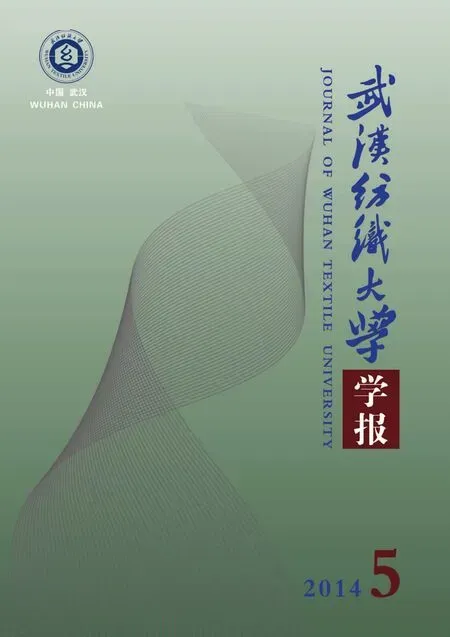从《青春之歌》到《上海滩》——关于“革命”与“后革命”的一种考量
李 展
从《青春之歌》到《上海滩》——关于“革命”与“后革命”的一种考量
李 展
(武汉纺织大学 传媒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青春之歌》和《上海滩》这两部经典作品蕴含了“革命”和“后革命”两段叙事。在“革命+恋爱”的叙事模式中,“革命”是其突破日常叙事的逻辑起点;“爱情”则作为一种日常生活传奇与革命象征性结合。革命和后革命暗示了生活的日常和传奇二元性质,并内在性地揭示了“红色经典”所蕴含的二律背反特质。
革命;后革命;爱情;日常;传奇
一、“革命”:一个相似又相异的叙事基点
将《青春之歌》和《上海滩》这种“红”与“黑”放在一起考量,之所以值得关注,乃是因为它们都有一个近似的叙事基点,即20世纪30年代中国青年因爱国而革命的人生选择。这个叙事基点分别由《青春之歌》的卢嘉川和《上海滩》的许文强两个主要人物展开。他们无论作为故事主人公还是作为作品叙事的结构性元素,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可比性及历史自觉。在这种革命叙事的意义上,我们将会发现这两部“经典”对于革命和人性的不同表达,具有非常深厚的历史内涵。
在《青春之歌》中,卢嘉川的社会身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和中共地下领导人,参与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救亡运动,领导学生到南京政府请愿以至被当局关押,最后牺牲。而许文强的故事其前背景同样发生在北平,他是燕京大学学生领袖并领导了学生运动,因为恋人被国民党军警打死和自己被抓进监狱,痛定思痛后毅然南下上海。但是,故事的不同在于卢嘉川因革命而牺牲,而许文强则离开了革命的道路。这里,爱国和革命对于卢嘉川是始终合一的,但对许文强则分属两事。在《青春之歌》之中,卢嘉川从学生运动到被当局关押的经历,不但没有使其放弃关于革命的“信仰”,而且以生命的代价实践了这种共产主义信仰。在卢嘉川,“革命”事关“民族大义”而与生命合二为一;相比之下,许文强的“革命”故事已经被基于“个体生命”的现实奋斗所取代。这样,在两个故事中“革命”的内涵在两人的个体生命中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并不等同。这种内在差异,导致了“革命”的叙事焦点在两部经典中发生“位移”。因此,《青春之歌》的革命叙事在《上海滩》中成为了故事的前在背景,换句话说,发生在上海的许文强的故事实际就是在南京监狱中的卢嘉川,——假若没有牺牲的话,继续南下上海发生的可能故事,这其实是一种“后革命”叙事。
但许文强的故事只是表明“后革命”叙事的一种可能。这种革命叙事和后革命叙事的不同,隐含了20世纪国人内在精神的演变。这种“后革命”叙事还有一个值得参考的上海故事,即徐訏1937年发表的著名小说《鬼恋》,它讲了一个“女革命者”“变鬼”的故事,这是对于“革命”的“另类思考”,与四十年代大型歌剧《白毛女》的“革命”主题正好相反。因此,《青春之歌》和《上海滩》就是两个几乎同时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两个大都市北京和上海的“革命”和“后革命”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在《上海滩》中,尽管许文强声称自己不再爱国,但是他最终还是明确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拒绝背叛自己的祖国,为此他处死了日本间谍山口香子。因此,就革命和个人的精神实质看,许文强实际并没有离开真正意义的爱国。这种“非革命形态”的“革命意识”的自觉,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生命自觉,其建立的前提基础更加内在,在电视剧中表现出极其丰富的美学内涵。许文强以生命觉醒和知识分子良知作为基础的“后革命”和卢嘉川以信仰作为基础的“革命”,实际就产生了相当的内在差异,特别是当“革命+恋爱”成为时代模式和艺术模式的时候,这种基于个体存在的生命自觉,就具有一种非凡的内在价值。这里,“具体的人”的现实建构与相对抽象的革命教义相映成趣,它就会为另外的一种叙事元素——“爱情”,提供切实的内在支撑。
二、“爱情”与“革命”:生命打破凡俗的传奇
对于爱情,人们都无法回避它作为文学作品、影视艺术具有的故事框架功能和审美要素功能。在《青春之歌》和《上海滩》两部作品中,确实都存在这样一段“爱情”元素。《青春之歌》作为“歌”(艺术)的叙事功能更主要体现在情感特别是爱情叙事上,只不过这段爱情因伦理问题使得女主人公煞费苦心的遮掩,令人颇为不屑[1];《上海滩》则如其主题曲一般,反映了爱情和人生命运相互纠缠的无奈与悲凉。因此,从这样的立场看待这两部“经典”里面的“爱情”元素,我们就会深深感到创作主体那种难以言说的创作冲动,其心理动力就是都想表达这段难以回避的沧桑爱情,革命或者后革命的故事都与这段情感经历,互为表里。
事实上,无论小说《青春之歌》还是电影《青春之歌》,作品对于林道静和卢嘉川的感情写得极其丰富细腻,这在十七年文学里中相当少见,这对于有着相当“自传性”的作家是不同寻常的,里面包含了作家那种深深的爱恋和无奈。林道静对于永泽的舍弃,这并不仅仅是革命话语对于小资产阶级的唾弃,而是直接与其爱情追求有关,这是一个包着革命外衣的爱情故事。[2]p15也正因如此,“青春之歌”又是一个“俗套”的“喜新厌旧”的日常叙事。但是在《青春之歌》中这样的情感故事,在20世纪50年代被作家小心地掩盖了,因为知识分子话语在当时整个“宏大叙事”中处在比较边缘的位置,而这种情感叙事则往往被看做“小资产阶级情调”,会受到严厉批判。因此杨沫叙说这是“连‘模特儿’都没有”的一个虚构的人物[3]p43。但是,在杨沫去世之后,谜底终于被她的儿子老鬼揭出来了,生活中实有其人原型路扬。老鬼在《母亲杨沫》中写道:“用母亲的话来说,她和路扬之间有过一段罗曼蒂克的友情,……以致于这段友情曾经让母亲痛苦。”路扬对她的感情让她惴惴不安,但他们不可能走在一起。“于是,在小说中,怀着对一个前线(朝鲜战争)战友的深情,对一个永远不能在一起的人的爱,用最真挚的感情虚构了一个栩栩如生的卢嘉川的人物形象。其实,这正是杨沫与路扬的这段情谊的美化与完善因真情实感隐于其中,所以会那么打动人心”。[4]p38在这里,爱情成为了作家的理想。杨沫自己在《再版后记》中也忘情地说,“在全书中我爱他(卢嘉川)和林红超过任何人”,“爱林红”显然是一个不得已的“装饰”[1]p83。在这个意义上看,革命确实是外在的。因此,卢嘉川尽管死去了,不符合现实中路扬的真实生平,但是对于这段感情的作者来说,卢嘉川的死恰好是实现其理想爱情的手段,正是因为现实中不可能的婚姻,造成了这段传奇的爱情,正应了那句“婚姻是爱情的坟墓”的格言。“革命”间离了“婚姻”,成就了“爱情”。
同样,这种感情叙事也是《上海滩》的中心内容,它与《青春之歌》对爱情的表达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单就电视剧本身看,当许文强来到上海认识了冯程程的时候,那种“一见钟情”的爱和后来世事沧桑的爱而不得,同样体现了爱之颂歌与挽歌并陈。因为许文强发现这个冯程程恰恰不是她父亲冯敬尧那样老奸巨猾的“政客+奸商”形象,而是一个非常单纯的女学生;许文强正是从这里复活了革命的痛苦记忆,这种痛苦中有过去牺牲的恋人影子,面对冯程程的真挚爱情,许文强的爱变得深沉而又犹疑,他真正害怕的正是自己内心那种“革命”的正义感,对于自己前途莫测,并由此可能株连到无辜爱人的担忧。这里,因“革命”和“正义”而起的对于“爱情”的伤害和恐惧,同时却也成就了真正的爱情。这种事实由许文强在冯程程与丁力的婚礼上得到了经典的表述,在电视画面中,那种真正的“心有灵犀”的“爱”,透过两人绝望的眼神,浸透了现实的无奈和伤感。当许文强因为杀死了日本间谍而成为冯敬尧的对手时,许冯爱情便被不死的爱国心开始尘封了;当冯敬尧杀死许文强的家小而成为仇敌的时候,爱情又被人间伦理尘封了;当许文强报仇冯敬尧的时候,现实的残酷已经将真正的爱彻底冰封了。假使许文强还活着,冯程程还会和许文强走到一起吗?一个象征性的细节就是程程的离乡去国,临走带了一本书,名字叫做《家》。不管这本《家》是不是巴金先生的《家》,这里真正的内涵是一种象征性描述,他们希望拥有一个真正的“家”,这个“家”里只有“程程和文强”。这显然是一种个体本位叙事。
但是,回过头来看《青春之歌》,我们发现当追求“生命”意义的“革命”在许文强变成真正悲剧的时候,卢嘉川的“革命”,却变成了抽象而又充满激情的“信仰”本身,这种“信仰”通过“爱情”的形式由林道静得到继承。这个时候我们发现“红色经典”的经典意义:纯洁性是它的本质,通过传奇象征性地将革命和爱情合流。即使卢嘉川也十分清楚林道静深深地爱着他,但是他不能拆散林道静的合法婚姻而背上伦理负担;也无法因为革命的信仰假公济私成就自己的爱情,这违背知识分子的良知;为此小说不惜牺牲掉生活的真正内容,那么卢嘉川就必须死,只有肉体的死亡才能保证精神的纯洁旗帜象征性地永远飘扬。红色经典的诞生及其现代中国的革命现实都证实了“革命”的本质性内涵乃是为了信仰而斗争。这个时候,革命成为了某种准宗教,这是红色经典的人性内涵。它弥补了五四以后传统文化的存在论断裂,揉合了难以实现的个体爱情和永恒的革命乌托邦冲动。正是在这种哲学意义上,我们说“红色经典”深刻地反映出超越现代中国虚无主义的努力,同时又是这种现代文化的一部分。“革命”,不仅是现实意义的民族国家建立,更是宗教文化意义上现代人安顿身心灵魂的寻“家”之旅,而爱情因其对日常的传奇性,恰恰提供了革命这样一种个体性的支持,而显得有了某种存在论合法性。
三、革命和后革命:传奇与日常的辩证法
革命和爱情,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成为一个无法相互绕开的问题。但是,在现实中革命对于民族国家的建立和现代人精神信仰制造的某种成功,却在文学或者艺术的层次上,基本失败了。由此,“红色经典”宗教学意义的悲剧与文学创作上的喜剧交织在一起,别具意味。
相对而言,《上海滩》这部反映上海“黑帮”的“后革命”叙事,其电视剧经典性的确立在于,它的传奇性建基于个体生命这种日常生活的基础上,“后革命”时代本质上属于凡俗世界。《上海滩》相比《青春之歌》其电视剧的展现方式大大增加了日常性因素,叫人感到更加真实,传奇便有了着落。悲剧“将有价值的东西撕毁给人看”,这种内涵被当年只有25岁的周润发和26岁的赵雅芝演活了。那段具有都市黑社会性质的江湖恩怨,被注入了现代知识分子精神气质,而令人耳目一新。中国传统的书香文化,成就了周润发那种儒雅气度和洒脱胸襟,具有典型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它虽然包装着黑道文化但却具有知识分子文化属性,这与毛泽东将农民文化看做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确实不同。那种雄姿英发的儒雅气度与江湖风云,表达的是一种知识分子情怀和现代都市气质,表达的是知识分子同样有能力从事革命的事业,这显然有别于《青春之歌》的工农兵文化表达。《上海滩》从革命理想回撤到世俗爱情,从宏大回到具体,成就的是世俗社会的爱情传奇,其实与革命传奇具有同样的乌托邦性质。许文强和冯程程的爱情不可能得到实现,这不符合中国伦理,一个人,怎么能和自己“杀父仇人”生活在一起?因此许文强也必须死。《上海滩》的结尾许文强被法国人打死,它竟然以“非革命”的现实形态又回到了被殖民的民族家国的解放问题。《青春之歌》从世俗奔向了传奇;而《上海滩》则从传奇再次回到了世俗。建基于日常生活的传奇,有自己可供升华的历史真实性逻辑;但是,建基于传奇的革命叙事,则否定了这种世俗性和生命的肉身性的现实性逻辑。因此,这种剔除了真正的历史内容及复杂性的“传奇”,被人讥笑为一个“俗套”的陈旧故事就不是不可思议的事了。
值得关注的是,这两部作品都写到了“婚姻”成为“爱情”的“替代品”,导致了两性关系的现实形态化,并使得丧失了爱情内涵的婚姻,终结了爱情传奇那种动人的艺术魅力。两部经典中的女主角婚姻结局,展现了一种令人永远伤怀永远遗憾的悲剧感受。这是传奇美学形态的日常终结。
这种表现在两部经典中同中有异,异中有同。《青春之歌》作为革命领导人的继承者江华,显然不是卢嘉川那种类型,他的黑黑的工人样子,他的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他的坚忍不拔,他的机警都使得他在现实革命中不同于卢嘉川的那种浪漫气质,但正是这样的实干家终于赢得了林道静的“肉体”,并用“革命”的名义实施了对于“爱情”的占有,以致女主人公明明感觉不对却又无法分辨明白,就成为了革命祭坛上的战利品。这种爱情叙事,无论对于爱情还是对于革命,都是虚伪的。无独有偶,在《上海滩》中丁力也是一位“实干家”,但他也与冯程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这对冯程程当然是悲剧性的。但这部作品的伟大在于它忠实于现实逻辑,用一种赤裸裸的真实揭穿了《青春之歌》之中的“双重虚假”,这样的真实表现在丁力对于程程的质问:在黑暗的婚床上,程程故意不打开灯是不是把他当成了许文强?!这种真实的情感逻辑没有《青春之歌》那种堂皇语言掩盖的某些虚假,因此丁力反而叫人觉得可爱,而不是江华那种令人感到的尴尬。可见,作为革命者的江华与作为黑帮头子的丁力,在“实干家”这点上并没有不同,在人性内涵上他们是同一种人,“嚣张的左派和嚣张的右派都是嚣张,正直的保守与正直的激进都是正直;景仰优美的敌手,厌恶平庸的同道,把人性的质量视为第一要素——这显然是文学家而不是政治家的目光”。[5]p123-124正是在这点上,某些“红色经典”的危机并不是所谓具有“史诗性”的宏大叙事,或者具有“崇高”内涵的普适性问题,而是它用一种道貌岸然的形态将人性的某些“渺小”穿上了华衮,将自己伪装成了一种虚假的崇高形象。
由此,我们看到了革命深刻的内在悖论:革命的精神和革命的现实形态其实处于对立状态。在那些革命的信仰者身上,我们发现的是革命的哲学性质,在美学上体现为传奇;在那些革命的实干家身上,我们发现的是更加功利的后革命的日常生活或者凡俗性质。《青春之歌》和《上海滩》这两部作品相对较好地解决了革命和爱情,传奇和世俗,精神和肉体的矛盾,反映了具体历史中个体的“生命”觉醒及其限度。因此,这两部表面看似“红”与“黑”的对立经典,其实都表征了革命对于现代中国的巨大影响,其作为传奇和现实的象征性符号而与个体命运相互勾连,并成为我们当下中国的文化背景。
注释:
① 《青春之歌》的文本形态,先有小说,后有电影和电视剧,这里以杨沫1957年版小说和1959年电影为主要参照对象;《上海滩》这里主要考察1980年港版招振强导演,周润发、赵雅芝主演的电视连续剧。
[1] 张清华.从《青春之歌》到《长恨歌》[J].当代作家评论,2003,(2).
[2] 李旭琴.革命与女性的纠结——小说《青春之歌》的一种解读[J].牡丹江大学学报, 2007,(2).
[3] 杨沫.《青春之歌》再版后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杨沫专集[Z].内部资料,1979.
[4] 孟红,袁佩红.《青春之歌》作者与卢嘉川原型的情缘[J].党史文汇,2007,(9).
[5] 南帆.后革命时代的诗意,后革命的转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23-124.
From Qingchun Zhige To Shanghai Tan ——Consideration about Revolution and Post-Revolution
LI Zhan
(School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3, China)
Qingchun zhige and shanghai tan, the two classic works contained "revolution" and "post-revolution" of the two narratives. In the "revolution and love" narrative mode, "revolution" wa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for its breakthrough daily narrative; "love" using as a legend of everyday life combined with the symbolic revolution. Revolution and post-revolution implied the routine and legend of everyday life, and revealed the inherent antimony nature of the "red classics".
Revolution; Post-Revolution; Love; Everyday Life; Legend
李展(1972-),男,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
武汉纺织大学博士科研基金启动项目(093782).
I206.6
A
2095-414X(2014)05-005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