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祝福》中的看客
邓远凌
邓远凌,教师,现居福建清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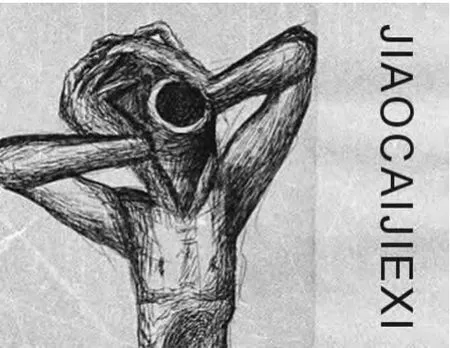
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说过: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中国人不但自己做戏,演给别人看,而且把别人的所作所为都当作戏来看。 《祝福》正隐喻了这样的一种状态:鲁镇的人看祥林嫂与祥林嫂的被看(不幸遭遇)。鲁迅意识到“改变国民的精神”重要,也因为这个理想,在《祝福》里,鲁迅塑造了三种看客的形象:
一.柳妈、鲁镇上听故事的女人是自私、冷漠、愚昧、麻木、冷酷的看客,这也是鲁迅最为关注,着力批判的一种“看客”
柳妈及听故事的女人都和祥林嫂一样,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她们似乎善良而富有同情心,当祥林嫂重复着阿毛的故事的时候“男人没趣的走了开去;女人们却不独宽恕了她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的话,便特意来寻来……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走了,一面还纷纷地评论着。”她们的同情心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对他人不幸遭遇的好奇。柳妈——“她是个善女人,吃素,不杀生的”。当祥林嫂继续重复自己的故事的时候,柳妈便从不耐烦转而嘲笑祥林嫂的伤疤,而“伤疤”就变为茶余饭后的谈资而传扬出去。她对自己的不幸无知无觉,却把别人的不幸和痛苦作为慰藉自己的娱乐,由于自身的麻木,对于弱者,她没有基本的同情,更不用说爱。而当她自认为“捐门槛”可以帮祥林嫂“赎罪”的时候,她“真诚”的关心却把祥林嫂推向了死亡的境地。
柳妈和鲁镇上的人们并没有恶意,他们只是因为自身的痛苦对他人也变得麻木而冷漠,祥林嫂丧子的不幸只是成为了他们自己“有幸”的证实,并通过不幸的反复展示和咀嚼,来加强和增大自己存在的幸福感。当别人的痛苦、悲哀“咀嚼赏鉴”殆尽,成为“渣滓”以后,就立即“厌烦和唾弃”,施以“又冷又尖”的笑。他们的这类情感与行为方式,实际是显示了一种人性的残忍。
这些看客们无处不在,遍布中国大地的各个角落,以自身以外的任何不幸和痛苦作为欣赏对象,他们构成“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消磨着、吞噬着“被看”对象,也成为“被看”者最严酷的环境因素。他们混沌,没有同情心、悲悯心,对生活麻木不仁,除开自身以外的一切痛苦灾难已没有了共鸣式的痛苦,也没有了悲哀的感觉。他们之间存在共同心理感受是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敌意。
二.“我”虽同情祥林嫂,但“我”的软弱与逃避的特点,同样也是“看客”
在鲁迅笔下,“我”是一个有着特殊作用的人。首先,用“我”来观察鲁镇,把鲁镇的人与祥林嫂的故事尽收眼底,并用我与四叔的格格不入显示出了“我”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及与当时世俗的不合,而我独特意义更在于随着我与祥林嫂相遇,祥林嫂对我的追问,我以“说不清”来回避了对追问的明确回答,也正因为如此,写出了我作为知识分子的软弱与逃避的特征。这类看客的意义在于点出了落后国民意识的巨大“同化”作用,它除了使“被看”者的处境更为孤立以外,更道出了改造国民性的紧迫性与艰巨性。
三.“鲁四老爷与四婶”是自私、冷酷的看客
鲁四老爷是个读书人,当祥林嫂首次到鲁家做工,中途被婆家劫走后,鲁四老爷说“可恶!然而……”。这四个字,即道出了祥林嫂被抓而他却只顾扫自家门前雪的冷漠与冷酷。全然不顾祥林嫂也曾在他家帮佣,也不顾他人的不幸,只是想到他人有损自己的家门体面及尊严,而第二次收留祥林嫂时,他的忌讳既有对寡妇的厌恶,也有她“克夫克子”的迷信思想,但即便如此,因为对于自身利益考虑——原来的祥林嫂勤劳、能干,再者雇佣女工难,他没有反对祥林嫂的留下,而当祥林嫂变得迟钝后,就把她赶出家门,因此他们也是一种自私而冷酷的看客,是更冷血而没有同情心的“看客”罢了。这种看客只是我们批判封建文化时的一个对象。
《祝福》里的看客集中体现了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对他人的不幸漠不关心,甚至从他人的不幸中获取审美价值,却从没有向别人伸出援助之手。他们是一群心中没有是非观念自私自利的“看客”,鲁迅先生正是通过刻画这些人物的行为表现,把国民这种内心孤独,精神空虚的心理状态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现在先生已经不在了,但他塑造的看客是否还依然存在呢,这是我们每个人要思考的。
——以《祝福》中三处细节描写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