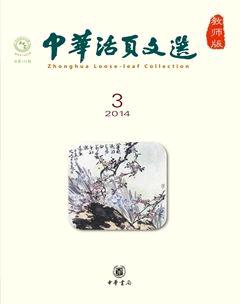钱锺书先生纪事
钱锺书先生的好友、我的老师郑朝宗先生在一九八六年一月六日给我的信中说:“《围城》是愤世嫉俗之作,并不反映作者的性格。”确乎如此,但钱先生在《围城》中所批评的文人喜作悼念文章,却也反映他内心的一种真实:不喜欢他人议论他、评论他,包括赞扬他的文章。钱先生对我极好、极信赖(下文再细说),唯独有一次生气了。那是一九八七年,文化部下属的文化艺术出版社,出于好意要办《钱锺书研究》的刊物。出版社委托一位朋友来找我,让我也充当一名编委,我看到名单上有郑朝宗、舒展等(别的我忘记了),就立即答应。没想到,过了些时候,我接到他的电话,说有急事,让我马上到他家。他还特地让他的专车司机葛殿卿来载我。一到他家,看到他的气色,就知道不妙。他一让我坐下就开门见山地批评我:“你也当什么《钱锺书研究》的编委?你也瞎掺乎?没有这个刊物,我还能坐得住,这个刊物一办,我就不得安生了。”他一说我就明白了。尽管我为刊物辩护,证之“好意”,他还是不容分辩地说:“赶快把名字拿下来。”我自然遵命,表示以后会慎重。第二年我回福建探亲,路经厦门时特别去拜访郑朝宗老师,见面时,他告诉我,钱先生也写信批评他。郑老师笑着对我说:“这回他着实生气了。不过,他对我们两个都极好,你永远不要离开这个巨人。”最后这句话郑老师对我说过多次,还特别在信中写过一次。八六年我担任文学研究所所长后,他在给我的信上说:
你现身荷重任,大展宏才,去年在《读书》第一、二期上发表的文章气魄很大,可见进步之速。但你仍须继续争取钱默存先生的帮助。钱是我生平最崇敬的师友,不仅才学盖世,人品之高亦为以大师自居者所望尘莫及,能得他的赏识与支持实为莫大幸福。他未曾轻许别人,因此有些人认为他尖刻,但他可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我与他交游数十年,从他身上得到温暖最多。一九五七年我堕入泥潭,他对我一无怀疑,六○年摘帽后来信并寄诗安慰我者也以他为最早。他其实是最温厚的人,《围城》是愤世嫉俗之作,并不反映作者的性格。你应该紧紧抓住这个巨人,时时向他求教。
郑朝宗老师是钱先生的知音挚友,对我又爱护之至。《管锥编》出版之后,他一再叮嘱我要“天天读”。我果然不忘老师教诲,二三十年从未间断过对《管锥编》的阅读,也终于明白郑老师所说的“巨人”二字是什么意思。钱锺书先生绝对是中华民族空前绝后的学术巨人,是出现于二十世纪的人类社会的学问奇观。如此博学博识,真前不见古人,后也恐怕难见来者。尽管我对钱先生的学问高山仰止,但对《围城》却并不特别喜爱,对此,我请教郑老师:我的审美感觉不知对否?郑老师回答说:平心而论,他的主要成就是学问,不是创作。
钱先生对《钱锺书研究》一事如此认真的态度,绝非矫情。他的不喜别人臧否的态度是一贯的,他自嘲说:我这个人“不识抬举”(参见一九九一年二月三日写给郑朝宗的信),这也非虚言。一生渴求高洁、安宁,确实是他的真情真性。只是求之太真太切,往往就对“抬举”之事怒不可遏,言语过于激愤。一九九六年,我听到法国的友人王鲁(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编辑)说,他看到国内报刊有一消息,说李希凡等人联名写了呼吁信,要求制止江苏无锡把钱先生的祖居旧址夷为商场,以保护国宝文物。知道此事后,他就致函杨绛先生,询问此事是否需要声援一下。杨先生在回函中传达了钱先生的话:“我是一块臭肉,所有的苍蝇都想来叮着。”一听到这句话,我就相信这是钱先生的语言,别人说不出如此犀利透彻的话。难怪人家要说他“尖刻”。然而,这句话也说明他为了保卫自己的安宁与高洁是怎样的不留情面。
真正敞开心胸的钱锺书,其实是年轻时期的钱锺书。尽管我敬爱整个钱锺书,但就个体生命状态而言,我更喜欢青年钱锺书。青年钱锺书心中没有一根弦,天真活泼,才华横溢,其文章全是率性而谈,直言无忌。这个青年钱锺书凝聚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钱锺书散文》一书的前半部中。此书搜集了三十年代钱先生所写的散文,即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九年,也就是《围城》问世之前的散文。这些散文篇篇有性情有思想,智慧之语全无文言的包裹,让人读后觉得作者不仅是才子,而且是赤子。例如写于一九二二年的短文《大卫休谟》,评介的是四百三十六页的英文版《大卫休谟传》,讲述的是英国大哲学家休谟的思想与故事,但钱先生以年轻学人的幽默与刁顽,把休谟自己概说十六项特性选择摘译数项于文中,实在很有趣。休谟如此自画:(1)好人而以做坏事为目的;(3)非常用功,但是无补于人亦无益于己;(8)非常“怕难为情”,颇谦虚,而绝不卑逊;(11)虽离群索居而善于应酬;(13)有热诚而不信宗教,讲哲学而不求真理;(14)虽讲道德,然不信理智而信本能;(15)好与女子调情,而绝不使未嫁的姑娘的母亲发急,或已嫁的姑娘的丈夫拈酸。笔者所以要提这篇散文而且注意钱先生在十六条中选择这七条,是觉得青年钱锺书很像青年休谟:坦率、顽皮、风趣,情感中放入理性,与众不同。这七条简直是青年钱先生的自白。晚年钱锺书就不完全是这样了,他很理智,很负责,很警觉,显得有点世故。能靠近他的人很少了。
因为钱先生的这种个性,因此常被误解为尖刻的冷人。文学所古代文学研究室的一位比我年轻的学子,有一次竟告诉我一条“信息”,说他的博士导师(在古代文学研究界甚有名声)这样评论:刘再复彻头彻尾、彻里彻外都是热的,而钱锺书则彻头彻尾、彻里彻外都是冷的。我听了此话,顿时冒出冷汗(不是热汗),并说一声“你们对钱先生误解了”。有此误解的,不仅是文学所。
然而,我要说,钱先生是个外冷内热的人。郑朝宗老师说“他其实是最温厚的人”,绝非妄言。对钱先生的评说各种各样,但我相信自己所亲身体验的才是最可靠。
我和钱先生、杨先生真正能坐在一起或站在一起说话的是在一九七三年社会科学院从五七干校搬回北京之后,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那时我住在社会科学院的单身汉宿舍楼(八号楼),钱先生夫妇则住在与这座楼平行并排(只隔十几米远)的文学所临时宿舍楼。因为是邻居的方便,我竟多次冒昧地闯到他的居室去看他。他们不仅不感到突然,而且要我坐下来和他们说话。那种和蔼可亲,一下子就让我感到温暖。“四人帮”垮台之后,社会空气和人的心情变好了,我们这些住在学部大院里的人,傍晚总是沿街散步,于是我常常碰到钱先生和杨先生,一见面,他们总是停下来和我说阵话。那时我日以继夜写批判“四人帮”的文章,写得很有点名气。见面时我们更有话可说。一九七九年我调入文学所,又写学术论著,又写散文诗。一九八四年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决定出我的散文诗集(《洁白的灯心草》),我就想请钱先生写书名。因此就写了一封短信并附上在天津百花文艺社出版的《太阳·土地·人》散文诗集寄到三里河南沙沟钱先生的寓所。没想到,过了三天就接到他的回信和题签。这是我第一次收到他的信。信的全文如下:
再复同志:
来书敬悉。尊集重翻一遍,如“他乡遇故知”,醰醰有味。恶书题签,深恐佛头着秽,然不敢违命,写就如别纸呈裁。匆布,即颂
日祺
钱锺书上二十日
收到信与题签后我光是高兴,把他的“墨宝”寄出后,又进入《性格组合论》的写作,竟忘了告诉钱先生一声。而钱先生却挂念着,又来一信问:“前遵命为大集题署送上,想应毕览。”我才匆匆回了电话,连说抱歉。而他却笑着说:“收到就好。”香港把书推出之后,我立即给他和杨先生送上一本,他又立即回应,写了一信给我:
再复同志:
赐散文诗集款式精致,不负足下文笔之美感尧尧,当与内人共咀味之,先此道谢。拙著《谈艺录》新本上市将呈雅教而结墨缘,即颂
日祺
钱锺书杨绛同候
对于我的一本小诗集,钱先生竟如此爱护,如此扶持,一点也不敷衍。那时我除了感激之外,心里想到:中国文化讲一个“诚”字,钱先生对一个年轻学子这么真诚,中国文化的精髓不仅在他的书里,也在他的身上。生活的细节最能真实地呈现一个人的真品格,为我题写书名一事,就足以让人感到钱先生是何等温厚。
(节选自《师友纪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