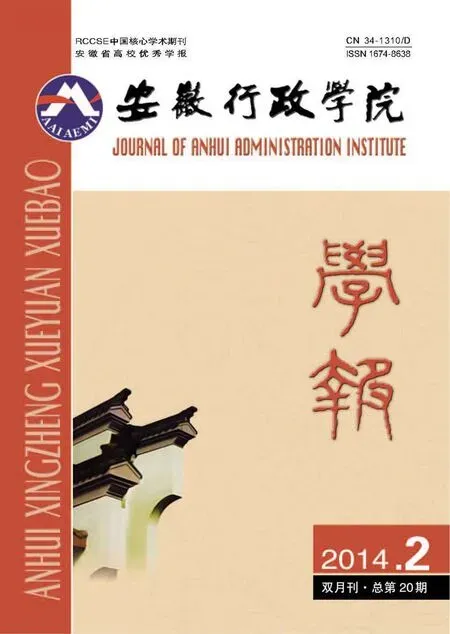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弹性研究
丁岭杰
(中共中央党校 政法教研部,北京 100091)
一、治理兴起的社会背景和问题意识
但是受援助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现实和制度经济学的理论都向世人揭示这样的规律:没有稳定的政治秩序、公正的法治体系和有效的政府管制力,自由市场也只能是镜月水花。针对非洲国家在社会管理和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1989年世界银行首先提出了治理危机(crisis in governance)这一概念。此后,联合国的全球治理委员会在《天涯若比邻》(Our Global Neighbourhood)报告中,较为系统和权威地阐述了治理概念,认为治理是多元主体的利益在持续互动中得以协调的过程[1]。从此体现着公正和效率的治理理念以及平衡市场机制和政府管制的治理实践便在学界和政界大行其道。正如杰索普指出的,治理已经成为了“时髦的词语”[2]。处于社会大转型时期的中国,更为紧迫地面临着完善国家的经济宏观调控体系和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这两个重大课题。中共十八届三中全就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纳入全面社会改革的目标体系中。
国内关于治理的研究很多将重点集中于介绍国外理论、分析治理的结构与功能以及描述治理实践的发展,而且大多研究将治理定位于行政管理的层面,而非国家这个宏观的政治体系层面。然而治理是个动态机制和互动过程,其也不只局限于行政管理中的政治输入和政策输出。迪瑞切斯雷(Dreehsler)就指出治理体制本身就包含了国家、社会和市场这三者的互动[3]。所以研究治理的特征、动态机制以及治理改进同国家建设的耦合,对把握治理本质和完善治理实践更有裨益。
国家治理体系是,治理主体、治理目标、治理过程的改进和治理过程的稳定等因素,在国家政治体系层面上相互协调,进而整合成的有机系统和动态机制群。美国行政学者彼得斯将弹性化和解制型政府的理论看成是四大政府治理模式理论之一[4]。其实制度弹性是大多治理模式,特别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特征。治理体系的制度弹性主要体现为,体系能包容日益多元的政治行为主体和公共的善,并在保持自身的开放性和适度刚性的基础上,根据权益诉求和政治生态的变化来进行动态的制度调整,以实现整个体系的适应性和稳定性。强制推行全面管制并固守单一意识形态的政治体系难以有效协调社会矛盾,更难以摆脱革命的魔咒[5]。相反,具有制度弹性的国家治理体系打破了传统统治体系的排斥性和刚性,降低了在社会运行和政治转型中发生革命的风险。
二、国家治理体系中治理主体的多元性
作为治理基本政治前提的民主规定了治理体系对多元主体和价值的包容。此外,对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的整合也需要能包容多元、互惠各方、明定权责和寻找利益相互适应性的,并具有广泛道义支持的政治机构和体系[6]8-9。所以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效性和正当性就须臾难离,罗西瑙所阐发的:体系本身包含了政府体系和非政府,并能让不同的个人和组织借助一定的机制来实现多元化的权益[7]。而且治理体制还需要随着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和利益主体的分化,不断调整治理主体的范围。
(一)治理主体多元化是民主伦理对治理体系的价值设定
“人民的统治”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表征。在人本哲学的层面上,人民统治的伦理基础是达尔总结的民主的弱势和强势原则,人在本质上皆平等和大多成年人皆有自我统治的资格[8]。在功利主义的层面上,约翰·穆勒将民主的伦理基础阐发为:个人是自己利益的最好判断者和保卫者,而且促进繁荣的个人力量越强大越丰富,普遍繁荣就越能实现[9]。
两个层面的民主伦理基础都论证了国家治理体系的治理主体多元特征:凡是具备基本的自主理性和公共德性,并且自身的权力与责任、权利与义务都受到了公共决策重大影响的政治主体,如政府机构、企业、非政府组织以及个体公民都能也应该平等自由地参与到国家治理当中。在早期的现代民主中,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投票、游行和读报。这大大限制了公民和公民社会介入政治过程的深度,扩大了普通公众与政治精英之间的鸿沟,疏远了公众与公共政治体系的距离,使得民主制呈现出“选主制”(选择主人来统治的制度)的特征[10]。
随着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国家干预并没能协调好多元的利益和价值,反而暴露出了严重的政府失灵。此外,随着西方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公民的实利主义目标被后实利主义目标所超越,公众更期许民主的基本伦理与参与式民主在国家管制、社会自治和经济运行中的回归,而不愿只做选举中消极的投票者、官僚制度中的服从者和公共产品的被动接受者[11]。社会组织和企业也被卷进治理体系成为治理主体,以表达、综合和协调各方利益。
(二)主体多元化是治理体系发挥治理效能的基本路径
阿尔蒙德将政治文化世俗化和政治结构的分化看成是政治发展的标准[12]。整个社会体系的发展也离不开社会文化的世俗化和社会结构的分化,即个人和社会组织越来越认可自身的独立主体资格和参加国家治理的能力,在精细的社会分工下社会主体和关系日益多元化。
在城市地区,负荷相对集中、用能需求多元,且用能的梯级利用潜力和互补性强,适合发展以多种能源综合利用为特征的泛能网。泛能网是以为用户提供多能互补的泛能机/站(即高效分布式能源系统)解决方案切入,利用信息网和气、电、热、水等物理网,搭建多种能源设施互联互通、多主体智慧交互的能源物联网,形成多能源智能调配、互联网能源共享的新生态,实现能源清洁、高效、经济、安全的目标。泛能网具有多种能源融合、分布式为主体、设施互联互通、需供智慧互动、实施调度交易、储能技术支撑等特征。泛能网的原理如图1所示。
在多元社会中,很多社会政治主体(包括政府)都能也愿意参与国家治理,但它们又只具备有限的公共理性、社会资源和技术手段,也只能代表部分的公共的善。它们都无法单独有效地治理社会,也不该排他地把持治理权力。因此,只有多元的主体自由地参与到国家治理体系中,如自由市场一样纷繁复杂的治理场域才能形成理性和伦理秩序。依据这两个秩序,治理资源才能实现最优化配置,被排斥者遭遇的治理风险也就更低,国家治理体系才更具合法性。此外,国家治理体系将能够且应该参与治理的主体(而不是所有政治社会主体)有限度地纳入到治理决策中,既能避免治理体系高度排斥性造成巨大的外部风险,也能防止参与主体无限扩大带来高昂的治理决策成本,从而达到“社会组织或政治组织的合适目标”[13]。除了带来直接的治理效果,治理主体多元化还提供了开放的政治试错机制。通过亲自参与治理,公民能养成自我管理的自主能力、维护规则的公共伦理、尊重他人的包容心态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政治智慧,推动了社会的普遍繁荣和长远发展。
(三)国家治理体系中主体多元化的两种类型
学者徐湘林将国家治理定义为,国家权力在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之间以及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被分配后,社会受到管控的过程[14]。这一定义遗漏掉了国家治理的很多重要内涵。国家治理除了涉及以上权力分配模式外,还包括保障公民权利以及公民、公民组织和企业对治理权力的共享。而且国家治理的运行方式主要特征为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商、合作、妥协和相互认同,而不只是国家公权力的全面控制。
国家治理体系的主体多元化直接体现为:多元的政治和社会主体公平自由地参与到治理活动中来,而且治理体系的开放性也会逐渐将新兴的社会主体纳入到治理主体的范畴中。但这不是主体多元化的全部内容,主体多元化更为深刻地体现为国家、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权能的有限度,各自行为的有边界。“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四者相互合作并适当改变原有的角色分化和影响力界限,但它们又相互独立而非相互融合。如果家国不分、政社不辨,那么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就无从谈起。赫尔德认为全球化和区域化下的网络治理体系重构了国家的角色和功能,而非简单地腐蚀国家权力[15]。这种国家重构不是将国家权力肆意扩张,而是为治理体系提供了权力有限但治理有效的公正政府。这样的政府不会过度侵害其他主体的自主空间,而是有效地界定和保护各方的产权与自由,并公正地协调冲突,从而防止企业垄断市场进而控制政治体系和公民组织并逃避对公众的民主责任,也遏制了被民粹主义所动员的大众冲击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
三、国家治理体系中公共善的包容性
在古希腊时期,确立和实现公共的善就是城邦治理的首要问题。现代主权国家的治理同样也要面对如何明确公共善的基本内涵。疆域广阔的现代国家是一个包含了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本国公民和外来移民、主流文化和亚文化、传统宗教和外来宗教、传统经济实体和新兴经济关系的多元文化集合体。全球化和经济发展带来的新兴社会、政治和经济主体的不断涌现也加剧了这一集合体的多元性。
在多元而多变的社会中,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分别扮演着多元的社会角色,承载着多元的权利(力)诉求、行动目标和社会伦理。而且在经济增长、资源离散化分配、教育和信息科技发展的推动下,非政府的社会政治主体的公共参与和分享权力的能力与意愿也在不断提高,它们不愿固守于政治等级体系的服从者、公共产品消费者和政治上被动员者的角色定位。这些意味着国家所设定的,被政治社会化系统所灌输的,最后被政治过程和政策所实现的,相对狭窄而固定的公共善,在公民觉醒和多元社会中已经逐渐褪去了合法性的面纱并失去了有效整合社会和协调冲突的能力。
因此,国家治理体系不但要厘定公共的善,还要实现公共善的包容性。治理体系中的善的包容性主要包含两大维度。一方面是善的多元内涵维度。国家治理体系以一定的社会政治的根本价值(如自由、平等和人权)为底线,把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和价值目标,如政府的社会稳定目标、企业的利润目标、公民社会的自主目标和公民个人的自由安全目标都纳入到公共善的范畴中加以协调,而不是把某一固化的意识形态奉为圭臬,并刻意地排斥其他的价值。开放性的治理体系还能对新兴社会政治主体提出的新的权益诉求做出积极回应,从而使不违背社会政治根本价值的诉求进入到公共善的内涵之中。
另一方面是善的网络体系维度。在传统的非民主政治统治系统中,经济和政治精英根据既有的意识形态、当前的政治压力和特定群体的利益来设定公共的善,并通过等级式的政治社会化体系来灌输公共善的正当性论证。而且等级制的社会化体系中的每个结构都在强化和扩展这种论证的说服力并消除干扰杂音[16]。在民主的国家治理体系中,公共善是在一个由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组成的治理网络中形成的。四方以平等的治理主体资格参与到公共善的设定当中,并依据一定的规则自由平等地获取信息、表达观点、设置议题和选择公共善的内容。对公共善的认知、态度和感情也是在多元而自由的信息交流体系中得以传播。
四、国家治理体系的改良柔性
国家治理体系不只是由具有特定功能的治理结构组合而成的规约和协调体系,还是能不断适应新的社会政治环境和各种主体权益诉求的动态自我调节系统。亨廷顿把政治组织适应性的外在表现概括为三点:组织的较长的生命、多次的领导人换届、组织职能的灵活转变[6]10-14。除了以上这三点,国家治理体制的适应性还体现为:体系合法性的持续、治理主体和公共善的包容性以及公平分配权益的有效。这些特征都依靠于国家治理体系的改良柔性。在一定的社会资源状况和技术水平的前提下,受到新的公众利益诉求和公共伦理的规模压力,国家治理体系通过调整直接的治理目标、治理主体的范围和治理的运行方式,来实现以上几个适应性特征。
以往的学者在解释体系的自我改良时,往往注重宏观变量,如经济的发展、历史传统的积淀、社会文化的变迁、国际因素的影响等。但是单单这些变量都不能准确解释这样的改良功能为何能实现。除了这些宏观变量,民主伦理框架、民主制度框架以及社会运动的动力机制都影响着国家治理体系改良柔性的实现。
首先是民主的伦理框架。“人民的统治”和“统治基于人民同意”分别是现代民主的最高和最低的功能标准,而人的本质平等和平等人的自由与尊严构成了两个功能标准乃至整个现代民主制的核心价值和基本伦理。当然在不同的民主国家中,政治精英和普通公民认知和判断人的尊严的侧重点、实现人的尊严的各种权利在政治制度中的权重谱系、保障和救济公民权的具体制度安排都不尽相同。比如在欧洲国家中,公民的福利权、经济权和政治权同等重要[17],而到了美国,公民政治自由拥有的宪法地位是经济和社会权利无法企及的[18]。但是,完善的民主国家中的各个政治主体都普遍地认同民主制度和基本的人权与公民权,对多元主体的文化和利益也更为宽容,这为民主制下国家治理体系在包容度上的不断提升提供了政治文化基础和社会心理动力。
其次是民主的制度框架。民主制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大前提,治理体系的改良弹性也只有在民主的制度框架内才能实现。在国家层面上,自由公正的选举是实现人民主权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选票产生代理政治权力的政治精英,而公众支持率、反对党的监督和多次选举博弈的压力又迫使当权精英对民众的权益诉求做出积极回应,并适当调整国家治理体系以更好地生产政治产品和协调产品的分配。除了选举和投票权,其他的公民权也支持着民主的大厦,如果单以选举来判断民主,那就会陷入“选举的谬误”[19],并曲解现代民主体系。利用结社、集会、言论和游行等公民权,原子化的公民个人可以组织成独立于市场和政府的公民社会,并借此来直接参与国家治理过程,或对治理体系的改进提供相应的信息与资源和施加道义与政治上的压力。此外,民主的制度框架能使政治活动去暴力化和去激进化[20]。民主制度为和平有序的政治参与、利益表达、政治博弈、甚至是政治抗争提供了开放而稳定的政治和法治平台。借助该制度化平台,各个社会政治主体更能倾向于提出符合基本自由和人权原则的权益主张,并且在政治制度内外采取非暴力的政治行为,以争取人数众多的中间选民,从而对治理体系的构建、运行和改进施加影响。政治行为的非暴力和非极端性不但强化了行为本身的道义力量,也相应地较少了当局使用武力强制的频度、强度和广度。
最后是社会运动的动力机制。既有的民主伦理设定了社会政治主体认同权利和需要治理体系改良的基本政治心理倾向,民主制度安排为治理体系改良过程中的多方博弈提供了规则平台。但这两点静态的结构性要素,其本身不能直接带来治理体制的改良。以实现和协调特定权利为基本目标的社会运动激活了静态结构性要素并为体制改良提供了动力。美国学者蒂利将社会运动定义为,对政府提出利益诉求的、公开运行的、带有抗争意涵的持续性集体行动[21]。在由运动的动员、运动的持续和扩散、多方协调与决议达成和运动遣散所构成社会运动周期中,社会抗争的主体往往依据民主和人权的伦理基础并结合流行的本土文化提出“集体行动框架”[22]144-148,以明确运动的目标、抗争的意义和行动的战略,并在对“机遇和限制结构”[22]26-27作出判断后,利用民主制度下的公民权和合法组织来提升社会运动的合法性与推动治理体系改革的有效性。而作为抗争对象或调停人的政府和政治精英也倾向于为自己的治理行为贴上民主的标签,并在选票、税收、政治道义和国际压力的影响下,通过利用或改革现有国家治理体系来协调利益、平息冲突和保障权利。
重大的社会运动促成改革后,国家治理体系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得到提高并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直到重大的新兴社会政治主体出现并再次借助社会运动来对已有的治理体系施加改革的推动力。国家治理的改良弹性就在权益诉求提出与治理体系功能调整的动态平衡过程中实现。比如正是工人运动和民权运动分别推动了英美两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扩大治理主体和政治产品获得者的范围,并进一步承认和保障英国工人福利权和美国黑人的平等公民权。
五、制度弹性中刚性原则
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弹性意味着治理体系根据政治生态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新的社会政治主体与新兴权益诉求的发展,在社会运动的推动下来调整治理主体、治理过程和治理产品的分配,从而增加体制的合法性、适应性以及治理有效性。但是治理体系本身并不是能被任意定义和构建的制度安排,其必须具有民主法治和确定性规则两大刚性原则以保持自身的稳定性。
一方面是民主法治刚性原则。 民主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制度预设,没有这一大前提,整个社会难以跨越国家统治和权力强制的制度藩篱,国家、企业、公民社会和公民个人之间不可能建立起平等的契约关系,以自由参与、平等合作、多方互动、共同管制和公正分配为主要内涵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最终也难以成功构建。民主法治的刚性原则体现为三个维度上的制度刚性需求。立法维度上的制度刚性需求表现为突破精英议会民主。立法机关和代议士同选民间的权力代理—委托关系不能只体现为投票竞选和议会争执的电视直播,而还要在突破“表演性政治”和精英民主的基础上,体现为选民和立法机关在治理议题的选定、治理过程的控制和治理效果反馈上的互动。行政维度上的制度刚性需求表现为行政机关在治理中承担更多的民主责任。行政机关早已突破决策和执行的两分法,并日益扮演着决策者和准立法者的角色。这不但意味着行政权力的扩张,也意味着行政机关在治理上必须承担更多民主责任,即畅通社会政治主体参与治理的渠道,并保障政策产品生产的透明度和分配的公平性。司法维度上的制度刚性需求表现为司法途径可接近性的提升。在西方发达国家,独立和公正的司法体系确实是保民权和护法治的坚实防波堤,但繁琐的诉讼程序、高昂的诉讼费用、法官缺少治理信息的反馈和司法系统独立于民主责任等都限制了司法维护民主制度的功能[23]。在保持司法独立和公正的前提下,司法系统需要拓宽诉讼渠道,提高司法效率和增加对治理问题的敏感性,以强化自身对治理问题的纠错机制。
另一方面是确定性规则刚性原则。国家治理体系中公共的善是个包容的价值和目标体系,但其并非是一个囊括所有政治目标和利益诉求的具有文化相对性特质的价值系统。《天涯若比邻》报告就主张:普通公民和精英的道德是提高全球治理质量的最重要因素,在治理中,人们要共同坚守被全人类普遍认同的核心价值,如自由、公正、爱心和人的尊严等[1]。因此在筛选和确定什么样的目标能进入公共善的体系时,价值基础明确的治理规则要将推崇极端暴力、政治歧视和蔑视人权的主张预先过滤掉,将推崇或实践这些目标的政治社会主体隔离在治理主体范围之外。
对于新兴的民主国家(如南美和东欧的后社会主义国家),委任制民主[24]和伦理性公民社会[25]往往阻碍了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效运转。委任制民主下,政治领导人(主要是总统)被赋予只受很少制约的统治权力,而且政治精英和大众也普遍认为问题丛生和矛盾尖锐的国家需要这样“父亲般的”总统来整合。此外,某些政治领导往往越过现有正式制度,以正义的旗号、革命的话语和民粹的激情直接进行社会动员并建立起伦理性公民社会,以此来获取个人魅力和扩大法外权力。此后再利用法外权力来影响法理职权和俘获公共政治。以上这些都削弱政治制度的自主性[6]16-19,最后为政治专断和政治衰朽埋下隐患。所以治理规则需要将治理体系制度化,即明确治理体系的根本价值和各个主体的权能边界,设定能固定主体预期的治理行为模式,使治理体系保持一定独立性和稳定性。
[1] Comm 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Our Global Neighbourhood:The Report of the Comm 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2-3.
[2][英]鲍勃·杰索普.治理的兴起及其失败的风险:以经济发展为例的论述[C]//俞可平.治理与善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53,71.
[3] Dreehsler W.Governance,Good Governance and Government:The Case for Estonian Adm inistrative Capacity[J].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2004,(4):388-396.
[4][美]B·盖伊·彼得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M].吴爱明,夏宏图,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25-131.
[5][法]让-马克·夸克.合法性与政治[M].佟心平,王远飞,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259.
[6][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7][美]詹姆斯·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M].张晓军,刘小林,译.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5.
[8][美]罗伯特·A·达尔.民主的及其批评者:下卷[M].曹海军,佟德志,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104-105、121.
[9][英]约翰·穆勒.代议制政府[M].段小平,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7:81.
[10]王绍光.民主四讲[M].北京:三联出版社,2008:47.
[11] Inglehart Ronald.The Renaissance of Political Culture[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88,(4):1065-1087.
[12][美]阿尔蒙德,等.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曹沛霖,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20-22.
[13][美]詹姆斯·M·布坎南,弋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M].陈光金,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45-50,67,73.
[14]徐湘林.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中国的经验[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5).
[15][英]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M].杨雪冬,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608.
[16][美]萨托利.民主新论[M].冯克利,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15.
[17]埃里克·S·爱因霍恩.自由主义与西欧的社会民主//[美]霍华德·威亚尔达.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榕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9-38.
[18][美]亨金.权利的时代[M].信春鹰,译.北京:知识出版社,1997,201.
[19] Karl Terry Lynn.Imposing Consent? Electoralism versus Democratization in El Salvador[M]//Paul D rake and Eduardo Silva ed.,Election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Latin America,1980-1985.San Diego:Center for Iberian and Latin American Studies and Center for U.S. —Mexican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nia at San Diego,1986:9-36.
[20][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M].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161-162.
[21][美]查尔斯·蒂利.抗争政治[M].李义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140.
[22][美]塔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M].吴庆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144-148.
[23] Bellamy R ichard.R ights as Democracy[J].Critica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2012,(4):449-471.
[24][阿根廷]基尔摩·奥唐奈.论委任制民主[C]//李柏光,译.刘军宁.民主与民主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53.
[25][英]林茨,[美]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M].孙龙,等,译.杭州:浙江人出版社,2008:277-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