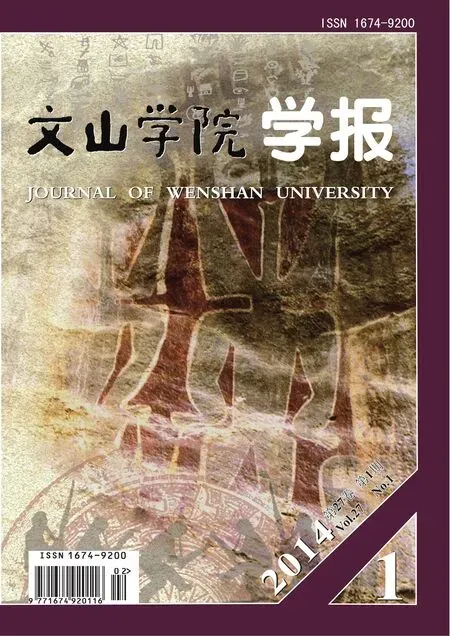清人编纂云南诗文总集思想述论
茶志高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清人编纂云南诗文总集思想述论
茶志高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清人编纂云南诗文总集,是基于历代云南诗文创作所取得的实绩、清代总集编纂的风气以及地方文献散佚较为严重的现实背景之上的。其编撰思想的核心集中表现为通过总集编纂达到引领观念和改变士风的目的,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梳理学术源流、求备文献;二、广为流播、沾溉艺林;三、恭敬桑梓、表彰先贤。从选诗标准上看,强调“性情之正”是清人编纂云南诗文总集的一贯主张。
清代;云南诗文总集;序跋;凡例;编纂思想
所谓清人编纂云南诗文总集,是指清人编纂的成书于清代的云南诗文总集。按此限定共有七部总集,分别为《滇南诗略》《滇南文略》《滇诗嗣音集》《滇诗重光集》《滇诗拾遗》《滇诗拾遗补》《丽郡诗征》《丽郡文征》。本文拟就上述七部总集的序跋进行一番考察,发掘他们在编纂思想上体现出的某些共性特征。清人编纂云南诗文总集的序跋数量可观,有《滇南诗略》序10篇、凡例1篇、后序2篇;《滇南文略》序4篇、凡例1篇;《滇诗嗣音集》序2篇;《滇诗重光集》序1篇、跋1篇;《滇诗拾遗》序1篇;《丽郡诗征》序1篇、《丽郡文征》序1篇,凡例25篇。清人编纂云南诗文总集思想主要是编纂者有感于地方文献的漫漶散佚,并以梳理地方学术发展源流、阐扬乡贤之志愿为核心。从保山袁氏兄弟《滇南诗略》肇始,形成了清人编纂云南诗文总集的风气,此风气从清中叶开始,一直持续到清末。然而学界对如此浩大的总集编纂活动关注不够,①清人编纂云南诗文总集的研究目前还处于相对薄弱的阶段,应予以足够的重视和系统的研究。
一、风会日趋:诗文创作的实绩与总结云南古典诗歌发展源流的迫切要求
云南诗文总集的编纂者对明清以来云南诗文创作的实绩有较多的描述,均认为云南社会风气的开放,诗文的勃兴,是自明代开始的。罗瑞图《重刻〈滇南诗文略〉序》指出,明代到清初,云南在学术、文章、经济方面的发展,几乎能与中原地区相媲美:
(瑞图)弱冠披览,窃叹滇虽边陲,然自有明以迄国初,风气宏开。其间名公钜卿,高人咏士,后先辉映,矫然特出。学术、文章、经济埒于中邦。[1]35
其实,像这样的见解已经成为当时人们的一致看法。江濬源在《国朝滇南诗略序》中说:“迨由元历明,风会渐渍而日上,至我皇朝累洽重熙之世,轩豁呈露,懋启人文。律龢而谐,声大而远者,遂各得随所遭逢以直见。”[1]50袁文典在《明滇南诗略序》中亦云:
迄于有明,尽变蒙段旧习,学士大夫多能文章、娴吟咏,一时名流蔚起,树帜词坛,滇诗始著。[1]37
袁文揆《明滇南诗略·弁言》云:
滇自明初,风气渐开。迄于中叶,声名文物之美,几埓中州矣。我朝声教覃敷,建宁诸郡户诵家絃。百六十年来,诗歌声律,翊运抚轮,视明为盛。[1]39
初彭龄在清嘉庆四年(1799年)出任云南巡抚,嘉庆五年(1800年),初彭龄为昆明五华书院、育才书院的课士之文进行选定,正好保山袁氏兄弟在编纂《滇南诗略》并请他写序,他读过之后,大为赞赏:
适保山袁氏昆季典揆裒辑全滇《明诗略》暨《国朝滇诗略》,请余鉴定且序之。余反复讽咏,喟然曰:“滇固非无声韵之学也!”当在前明,自郭舟屋、杨文襄、“杨门七学士”以下,代不乏人。皆能以天赋超逸之才,加稽古之功,师友之益,江山之助,缘情托物,沉冥发抒,金碧吟坛已非复赪木盘蛇之旧矣。迨我皇朝削平滇乱,士竞沐浴咏歌,国初能诗者不下数十家,而以赵玉峰、徐石公、朱子眉、张退庵为最。自是而何石民、段浴川、王筹五、张月槎、李鹤峰继之。近则周立崖菊畦、李载庵、唐药洲、孙髯翁、万荔村、钱南园、彭南池、李松屋诸公,典雅雄浑,劲正淳古,不相蹈袭,自名一家。足以超迈前贤,凌跨圣国。是岂非圣泽涵濡,风会日趋于上之验哉?[1]45
明王朝统治者加强了对云南的管理,军屯、民屯、卫所等官方的施政以及经商、人口迁移等因素,使云南社会出现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在文学领域上表现为诗文别集的大量出现,并出现了作家群体。明代除了初彭龄提及的郭文、杨一清,“杨门七学士”(李元阳、张含、杨士云、王廷表、胡廷禄、唐锜、吴懋)以外,还有很多水平很高的诗人如布衣兰茂,明遗民赵炳龙、高应雷、陆天麟、陈佐才、文祖尧等,诗僧释法天(号无极)、释普荷(唐泰,号担当)、读彻(号苍雪)、释禅(号本无)、释大错(钱邦芑)等,又有家族文学群体如丽江木氏家族、浪穹何氏家族、蒙化左氏家族等都有诗文集传世。清代是云南文学发展的高峰期,云南本土能诗者,更是数不胜数,这些作家的出现,着实为云南文学之一大观。这些作家和他们的作品的出现,是搜集、编纂云南诗文总集的前提和基础。
还有一个外部的刺激和动因。乾隆皇帝进行大规模的《四库全书》编纂,笼络了各地士子参与,并使一些符合所谓“正学”的地方文献开始进入官方视野。它所搜罗的文献典籍之广博,前所未见。“《四库》卷帙之富,集中国古来典籍之大成。论其完备,虽未尽包罗古今一切载籍,然当清代中叶,凡无背正学之典册,几全荟萃于斯,则固事实也。”[2]1《四库全书》的编纂大抵与当时汉学的鼎兴不无关联。乾隆皇帝下诏访书,以奖励私人进书及严饬督办二者结合,双管齐下,并以维持世道人心之大义号召。《四库全书》的编纂虽是出于政治上的目的,却成为了地方性诗文总集编纂学习和模仿的对象。
《滇南诗略》的编纂者袁文揆就有在四库馆工作的经历,袁氏在《明〈滇南诗略〉序》中云:“文章之出与续,出亦自有时会,为曩志乘所载,兰止葊以下遗稿空存其名者,几二十种,今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于它省所进滇南遗书已收录十余种。如杨文襄公之《关中奏议》《石淙类稿》,闪仲侗之《鹤和篇》,他省见而进之。”[1]42-43袁文揆看到其他省份所进的云南人之著作有所触动。他在《滇南文略·凡例》中提到,因找不到杨一清的文稿而预留了一二卷的空白准备以后把它补刻进去。“再,杨文襄《关中奏议》业经登诸《钦定四库全书》馆。滇处僻远,册府之书既难购,致遍求无获。”[3]10事实上,如前所述,云南诗文取得的实绩是不容忽视的,需要认真搜罗梳理,使它们广为流传。因此,从《滇南诗略》到《滇诗拾遗补》,形成了一系列云南诗文总集。清人编纂云南诗文总集,是以总集的方式对云南古代诗文创作成果的一个全面的展示,也是不断学习前人优秀的总集编纂思想、经验的典范。
二、观念引领:清人编纂云南诗文总集思想之核心
风会日趋,势所必然。由于梳理学术源流、求备文献的迫切需要,清人编纂云南诗文总集的编纂思想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就是希望通过总集的编纂为人们提供征文考献之助,总结云南古典诗歌发展的轨迹,进而改变士风世俗,起到引领社会风气和改变固有迂腐观念的作用。通过总集的编纂把那些不为人所知的私家著述发掘出来,使它不至于淹没无闻,从而驳斥人们所谓“滇无诗”的偏见。《〈滇南诗略〉后序》:“滇无诗?滇非无诗也。浮夸者无论矣,秀杰之材,负性迂僻。一吟一咏,唯求适情而已,多不存稿。其子孙之贤者,珍如拱璧,秘不示人。不数传而化为乌有。其愚者则以供妇女之针包线夹,或同废纸鬻之市肆。其一二名作非拾自水火之余,即夺诸鼠蠹之口。此滇之所以无诗也。”[1]761袁文揆在这篇序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们对“滇无诗”的误解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个人原因,一个人作诗的主要目的是适性,这样的观念使作诗者注重抒泄自己的性情而不注重保存诗稿,缺乏文献保存意识,这是一种极端。同时又有一种极端,那就是“保存意识”太重,不轻易把存稿拿出来给别人看,没有学术“公器”意识,这样传递几代人之后,就化为乌有。其次,大多数人不知道这些文稿的价值而难以流传。诗文集或当作“针包线夹”或“同废纸鬻之市肆”,残存下来的还要经历水浸火焚,或者鼠咬虫蛀。书稿之厄,莫此为甚。
清人编纂云南诗文总集的思想就是围绕着“观念引领”进行的。具体地讲,又可概括为三个主要方面:一、梳理学术源流、求备文献;二、广为流播、沾溉艺林;三、恭敬桑梓、表彰先贤。现分别论之。
(一)梳理学术源流、求备文献
清人编纂云南诗文总集的思想之一就是通过梳理历代云南诗文发展的脉络,编纂通代总集作为征文考献之助。读者通过阅读乡贤先达的诗文,可以了解他们的事迹、品行等,可以达到“以诗存人”的目的。罗瑞图《重刻〈滇南诗文略〉序》:“读之者不第见乡先达之诗文荟萃,兼可识其伟烈丰功,品量卓犖与。夫独伦纪抒性情,学术之精纯,文章之典奥,实足以资考镜而备滇南掌故,诚于《通志》、《滇系》外可为征文考献之助。”又说:“自兹以往,获是书者可以观乡先达之品量功烈,以及学术、经济、文章。即就此考献征文,亦足以备滇南掌故。”[1]35诗文总集的编纂,亦可以部志书之不足。另外,在清人编纂云南诗文总集过程中,亦有感于滇南文献的散佚之严重,搜罗之困难。《明滇南诗略序》:“顾劫火之余,闻见异词如郭舟屋,只存游览数什,张南园仅载《春园叠韵》一编,即杨升庵所称七子文献,亦惟禺山、中溪尤有鋟板,而蠹蚀,漫漶不可卒读。其他率皆断简残编,等于吉光片羽,欲求备一代之文献,戛戛乎其难哉!”[1]37因此,从《滇南诗略》之后的几部诗文总集,都接续了这种“求备文献”的思想。袁文典、袁文揆《滇南诗略》,袁文揆、张登瀛《滇南文略》收录了云南乾隆朝以前的诗文,黄琮《滇诗嗣音集》编选嘉庆至道光朝诗人诗作,许印芳基于道光至光绪间诗坛的活跃和诗歌创作的繁荣,编成《滇诗重光集》,王先谦《〈滇诗重光集〉序》:
嘉庆初,保山袁广文、文典昆季有《滇诗文略》之刻,而乾隆前作者赖以有传。咸丰初,昆明黄文洁公琮刻《滇诗嗣音集》,道光以上风雅略备。丙辰后毁于兵。大乱初平,文物凋丧,学人间作雅音未衰,率以无力梓行,旋就湮佚。吾为此惧,辑光绪以前文踰十家,诗踰四十。先刻诗,编仿《嗣音》例,命曰《重光集》。[4]1
除上述几种外,另还有陈荣昌《滇诗拾遗》、李坤《滇诗拾遗补》等,形成了一种自觉的总集编纂活动,他们尤其重视文献的流播,使那些诗文得以流传。袁嘉谷《〈滇诗重光集〉跋》:“时逢国变,樾村先生与虚斋师及我同志诸友,为滇文献之辑刊《滇南丛书》,将欲续百七十余家于《重光集》中。佥日不可重光者,始道光,迄光绪。”[4]2在社会动乱和变革中,还能够以阐扬地方文化之精粹为己任,这种精神尤其值得称赞。
(二)广为流播、沾溉艺林
云南地处边疆,起初文献保存、流传的方式极为单一,大多藏于家,靠手抄传世。“文章关乎气运,信不诬也!然书仅藏家,集尠传世。”[1]39再者,前已提及人们观念还未改变,认为诗文就是为“适性”而作,不必自我标榜。这种观念说好听一些就是朴实、不张扬,正如陈荣昌在《滇诗拾遗序》中所言:“吾滇僻在天西南,其人士往往安于朴陋,不以文采自炫于当时,则身后寂寞无名,亦何足怪。”[5]369这种观念造成了诗文流播的困难。作诗却不刊刻诗集,是“士风近古”的体现,这是大家普遍的观念。“吾滇之士不为此,故曰士风之最近古者,不妄刻诗文是也。夫自我作之,不自我刻之。其所聊以课其子孙者,一听其什袭而藏,而必且博搜密访,出诸箧笥,标其名氏以为某某者,为是某某者,为是刻之不已而补之,补之不已而续之。”[1]56-57自作而不自刻的观念过度了,就变得鄙陋、迂腐,诗文集也得不到很好的保护。陈荣昌《重刻〈滇诗嗣音集〉序》:
道山、喆嗣、香圃继其志,卒刊之,印百部以饷同人。呜呼!幸载!吾滇士习朴,其失则鄙。先辈所著书往往藏之家,不以问世,朴故也。即问世矣,历年久,板片残缺,甚且煨烬,其书亦渐就消灭。后之学者既不加搜访,偶得其书,又不甚珍惜,间有能珍惜者,亦只插架束阁,不能再付剞劂,以广其传。终亦必亡而遭穷措,大固不任,其责有力者,但治家人生产,视此等事若无与。于己然,他人或议及之匪雄,弗賛其成,且谓此迂所为生,相与非笑之。呜呼!岂不谬哉![6]167-168
陈荣昌指出,云南诗文流传不广,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重视所造成的,他对这种现象感到非常痛惜。云南诗文总集的编纂者的编纂动机也就明显了,他们想把那些不容易见到的云南诗文集发掘出来,使其广为流传,沾溉艺林。陈荣昌希望“乡之士大夫有藏先辈遗稿者乎,谅此苦心,庶几出以示我矣。”[5]369因此,改诗文集从手抄流传到刻印流传,使大家乐意把私人收藏的诗文集自愿奉献出来,不再作为秘笈深藏而作为“公器”使用,遗稿渐出,逐步改变人们的观念,把刻印总集作为一种引领观念的渠道。《滇南诗略·凡例》:
集名《诗略》者,以吾滇作者多不刊稿厥。子孙虑祖父钞本为人剿袭,珍秘存之。故向无萃集梓行之诗文。兹集既成,或遗稿渐出,尤望同志者博采而增益之。以诗存人,不以人存诗。[1]58
将诗文总集的刊刻流传作为改变士人风气、观念的办法,使编纂诗文总集上升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使总集编纂与社会风气结合起来,这一点在清人编纂诗文总集的风气中至关重要,值得深入发掘研究。
(三)恭敬桑梓、表彰先贤
清人编纂云南诗文总集的过程中,恭敬桑梓、表彰先贤的思想亦有明显体现。袁氏兄弟、黄琮、许印芳、陈荣昌、李坤、赵联元等都有着赤子之心,他们以阐扬地方文化之精粹、表彰乡贤之品量为己任。袁文揆《明〈滇南诗略〉序》:“余谓生当右文之世,景仰前微,阐扬幽隐,凡恭敬桑梓之心,皆从文同律之义。”[1]42萧霖年《〈滇南诗选〉序》云:“三千里内之文人学士,尽看日丽星县;四百年余之雅制名篇,肯作云蒸霞蔚。汇丛编而成钜帙,照耀缥緗;读遗什而缅先型,敬恭桑梓。使知西方乐土,原不乏楩楠杞梓之林,南国偏隅,无弗沾礼乐诗书之泽。功何大乎!”[1]49又赵联元《〈丽郡文征〉序》云:“拾遗掇佚,显微阐幽,是其职志,尤《诗征》之辑也。书成序其首,以质后之人,冀赓续为之,庶几文献之足征,而文运之日昌以大,亦郡人士之责。”[7]739云南诗文总集的编纂者们对先贤怀有恭敬之心并充满着责任感,通过搜访、编刻他们的诗文,以诗知人,以诗论人。或者以诗存人,以文存人,从而表彰先贤,表达文章报国之志愿。
三、性情之正:清人编纂云南诗文总集之入选标准
选诗标准也是总集编纂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考察清人编纂云南诗文总集的选诗标准,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是理论层面,主要体现在诗文总集的序跋和凡例中,这是编纂者思想的集中体现。其次是实践层面,体现在总集编纂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对选诗标准执行的忠实程度。因篇幅关系,本文主要从序跋凡例入手来分析,兼援引总集中一二条具体的选诗例子以及其中的诗文评点来说明。
清人编纂云南诗文总集的入选标准强调的是性情之正,所谓性情之正,就是主张总集编纂过程中重视那些抒发真性情的诗人以及符合“温柔敦厚”诗教的诗作。袁文典《〈明滇南诗略〉序》云:
余谓:“子云有言:‘雕虫篆刻,壮夫不为。’昌黎亦言:‘余事作诗人。’盖贵乎弹豪属笔,祖述六艺。若徒骋风云月玉露之词,究四声八病之学,虽多庸愈乎?”兹集本得性情之正,由此而衔华佩实,征存亡,辨得失。赋以见志,歌以贡俗,登太史之輶轩,为五经之鼓吹,则取精用宏,即非小补。[1]38
袁文典认为诗人贵在“祖述六艺”,得“性情之正”的诗作才能“衔华佩实,征存亡,辨得失。赋以见志,歌以贡俗,登太史之輶轩,为五经之鼓吹”,强调诗歌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他又在《刻〈滇南诗略〉后序》中有同样的观点:“然尝身亲海珊、南冈、息圃、兰泉、云岩、曙堂诸公,近与默斋常以尺牍往还,其说诗各随其性之所近,亦有不免于方隅者。要其大旨,亦惟以诗言志、本乎性、发乎情、止乎礼仪,温柔敦厚不离乎三百篇者近是。次则变而为楚骚,乐而不淫,怨而不乱,犹有风雅之遗意焉。”[1]760初彭龄《〈明滇南诗略〉序》中亦指出《滇南诗略》中所选诗歌的总体取向,“余谓诗以言志,苟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上不悖于三百篇、骚赋、汉魏六朝、唐宋以来诸大家,则具体可也,一体亦可也;连篇累牍可也,一鳞片甲亦可也。使不本诸性情之正,关于伦纪之大,古今之治。忽安危所系、人物之贤否?邪正所判,徒流连景物,驰骋才华,寻章摘句,袭貌遗神。言愈工而理愈失,词益支而意益违。于风雅奚取焉?是编所选,悉以大雅为宗,譬之于水,涧溪沼沚,派别支分而同归于海;譬之于山,峰峦冈阜,雄峙卓立而环拱乎岳。上自台阁名贤,下至山林隐逸,以及闺秀流寓,收撷靡遗。洪纤浓淡,不出乎兴观群怨之旨。滇之人士,即是编以求其性情之正,由是而涵濡乎朝廷道德之泽、礼乐之化渐于心志,而鬯于咏歌,将所谓资于事父事君者,其庶几乎?”[1]46不论收诗多少,来源如何,凡“有当于雅音者概存之”。初彭龄的诗歌观念亦不超出“性情之正”“温柔敦厚”,以“大雅”为宗,不悖兴观群怨之旨。江濬源称“其于三迤十邦郡、七厅州,百有五十余年之作者,自名公巨卿、文人学士,旁逮寓迹天涯,樐心尘表之流,诸有关于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大伦,显之存劝戒微之道、性情以及穷通隐见、欢愉悲戚,因寄所托,游目骋怀,不悖诗人宗旨者,虽散寄于残笥,賸帙之中,罔不博取广征,都为一集。”[1]50-51所强调的也是同样的观念。翁元圻《序》云:“是编上自馆阁钜公,下至山林隐佚。凡我朝百余年来滇之工于诗者,采撷靡遗而流寓亦附焉。要以大雅为正宗,格律次之,才华又次之。”[1]53综合上述几点,《滇南诗略》的编纂者十分重视诗作是否能够以大雅为宗,而格律、才华等并不是首先考虑的因素。赵联元《〈丽郡诗征〉序》:“盖准诸古人,陈《诗》之遗制,抑亦小雅。诗人所谓桑梓敬恭之义也。”[7]561又如陈荣昌《〈滇诗拾遗〉序》:“吾意古圣贤者,淫哇绮调则不屑为,正大之声,和平之响,忠厚悱恻之词,慷慨悲歌之语,得志则为之,以鸣国家之盛;不得志则亦为之,以自鸣其不平。《诗》三百篇,其彰明较著者也,奚为而不重。”[5]369从陈荣昌的观点看来,他也反对“淫哇绮调”,主张诗歌要有“正大之声”,与前面的“性情之正”同调。《滇南文略·凡例》就以分门别类的方式先列奏疏、经史、劄子,以体现尊君尊经的思想。然后以檄、上书、策议、教,重视义正事公。再按论、书、启、札、喻、解、辨、考、说、铭、颂、赞、引、序、碑、记、传、杂体、题跋、墓表、墓志、行述、诔词、拟骚、拟表的顺序编排,都以义与事为权衡。最后以赋与骈体结尾,也是体现了以尊君的思想。
对诗歌内容进行评论和注释是清诗总集中常见的方式,清人编撰云南诗文总集中评论和注释非常多,而且灵活随意。在具体的编选过程中,通过诗文的评注可以看出编纂者对“性情之正”的强调,如《滇南诗略》卷三选杨一清《王太史舜卿谪戍茂州过镇江相见怆然因忆乃兄尧卿感而有作共得三首并录赠之》(其一):
岐路岂不多,君胡此行役。朝为近侍臣,暮作遐征客。
平生忠信心,偃仰无欹侧。江山助诗豪,风露壮行色。
欲语不得尽,云鸿渺南北。岷峨故崔嵬,剑阁何逼仄。
税驾行有期,君恩本无极。[1]92
袁文揆对此诗有一段眉批云:“此章蕴藉而深挚,次章踔厉而酸楚,三章益沉痛而转致慰免,皆出自真性情,无一字装饰。”张允檝又评第二首云:“诗本为舜卿而作,其昂藏磊落,时露英雄本色处,皆忠爱之无已也。”又如卷十四选释普荷(唐大来)诗《子夜歌四首》,有陈继儒评语云:“灵心遒响,丽藻英词。调激而不叫号,思苦而不呻吟。大雅正始,而不入于鬼诗、童谣、方言俚语之俳陋。即长吉玉川复生,能惊四筵,岂能惊大来之独座乎?”[1]240类似的诗例不少。
清人编纂云南诗文总集之入选标准强调诗歌性情之正,主张“温柔敦厚”的宗旨,与清代主流的诗学批评以及整个清代的总集编纂思想显然是合拍的,我们通过对清代云南诗文批评著作的考察可以看出其“温柔敦厚”的诗教。需要指出的是,“性情之正”的标准在云南诗文总集的编纂序列中并非那么呆板,也有一些变化。从《滇南诗略》到《丽郡诗征》,可以明显地看到对这一标准的逐渐放宽,这当然与时代背景的变化有密切关联。
综上所述,从序跋凡例看清人编纂云南诗文总集的思想,可以看出编纂云南诗文总集乃风会所趋,有现实的客观需要,也有地方先贤的努力运作。通过总结、梳理地方诗文发展的脉络以求备文献,广为流传,从而表彰先贤,表达恭敬桑梓之心,体现了总集编纂者在保存、传播地方文献上的观念先觉和引领意识。从总集的入选标准看,主要强调“性情之正”,即“温柔敦厚”宗旨,但这个标准有逐渐减弱的趋向。清人编纂云南诗文总集在编纂思想和体例上的一些特征亦值得进一步分析研究,如清人编纂云南诗文总集时对其他优秀总集编纂经验的借鉴和吸收、各总集编纂体例的特色等,细致地从文献学的角度进行总集文本的研究,从而从具体的操作实施层面考察清人编纂云南诗文总集的编纂思想及特点(包括编纂背景、编纂意图及意义、地域文化因素及特点、诗人诗作数量在时代和地域上的分布、选诗标准等),同时指出总集编纂过程中体例不一、局部失当或者相互抵牾,小传错误,重复收诗,目录与内容诗文数量统计不符,校勘不精等缺陷,从而对清人编纂云南诗文总集的成就作出合理客观的评价,这些工作还亟待进行。
注释:
① 有关清人编纂云南诗文总集的研究论文,目前有肇予:《浅谈云南的几部地方总集》,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云南文化典籍介绍一则》,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张梦新,吴肇莉:《云南诗歌总集的开山之作——论滇南诗略的编纂体例》,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吴肇莉:《清人诗文总集总目提要订补——以十五位云南籍作家为中心》,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茶志高:《〈滇南诗略〉目录及作者小传订误》,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3年第4期。
[1] 袁文典,袁文揆.滇南诗略[M]//丛书集成续编(集部第150册).上海:上海书店,1994.
[2] 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M].长沙:岳麓书社,2010.
[3] 袁文揆,张登瀛.滇南文略[M]//丛书集成续编(集部第152册).上海:上海书店,1994.
[4] 许印芳.滇诗重光集[M] // 丛书集成续编(集部第151册).上海:上海书店,1994.
[5]陈荣昌.滇诗拾遗[M]// 丛书集成续编(集部第151册).上海:上海书店,1994.
[6]黄琮.滇诗嗣音集[M] //丛书集成续编(集部第151册).上海:上海书店,1994.
[7]赵联元.丽郡文征[M] //丛书集成续编(集部第151册).上海:上海书店,1994.
The Study on Qing Edited Collection of Yunnan Poems and Articles’ Compiling Ideas
CHA Zhi-gao
( School of Litera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China )
Qing edited collection of Yunnan poems and articles, is based on the realistic background that allprevious dynasties poetry achievements obtained in yunnan, the edited collection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situation that the local literature is scattered and lost. The core of the compiling ideas i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leading ideas and change social ethos: First, searching the academic origin, preparing documents; second, benefitingart circles; third, respecting the native place, recognizing the sages. Looking from the selected poetry standard, toemphasize "a positive disposition " is the advocacy of the collection of Yunnan poems.
Qing people; the collection of Yunnan poems and articles;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legend;compiling ideas
I209.974
A
1674-9200(2014)01-0066-06
(责任编辑 王光斌)
2013-11-02
茶志高(1986-),男,彝族,云南巍山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献的整理与研究。